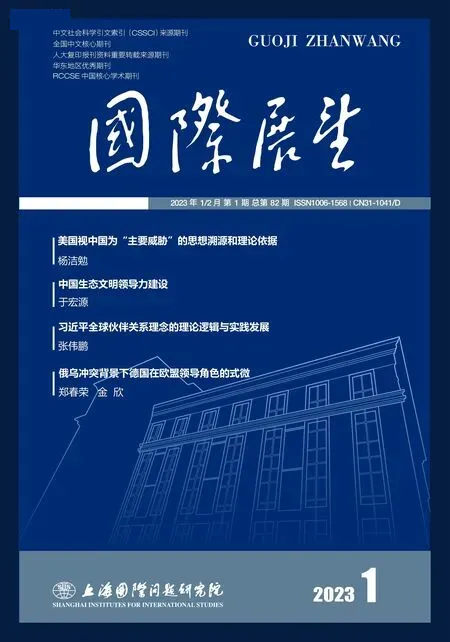中國生態文明領導力建設*
——基于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視閾的分析
于宏源
在百年變局、地球生態危機、大國競爭加劇等多重疊加背景下,全球環境治理轉型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此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也是構建基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方案。生態文明是“人類世”時代①Cameron Harrington,“The Ends of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Anthropocene,” Millennium,Vol.44,No.3,2016,p.489; 劉學、張志強、鄭軍衛等:《關于人類世問題研究的討論》,《地球科學進展》2014年第5 期,第646 頁。全球治理的目標原則和全球氣候環境治理的戰略要點。中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指引,堅持全球發展倡議,協調主要國家間關系并重視發展中國家權利,“積極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與國際社會共同推進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②習近平:《堅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創后疫情時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的演講》,新華社,2022年 1月 17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1/17/c_1128271799.htm。。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已從被動學習者、應對者、獲益者,轉變為全球環境治理的參與者、貢獻者、分享者,并進一步轉向積極的建設者、創制者和引領者,同時也持續提高國際話語能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參照、可復制的生態文明轉型實踐范例。
一、中國生態文明國際領導力的內涵與實踐
中國生態文明實踐經驗是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知識產品,也是中國生態文明領導力的鮮明標志,也將引領人類未來文明發展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綜合統籌內政外交兩個大局中的生態文明建設,在本國生態建設取得根本性進步的同時,也在全球治理中擔任主要角色并深度參與協作,不斷創新并提供生態公共產品以滿足國際社會需要,為全球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中國方案。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現代化國家滿足自身綠色發展的需要,也幫助中國深度參與和融入全球綠色低碳產業鏈,積極貢獻綠色公共產品。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國際社會要秉持生態文明理念,攜手同行,開啟人類高質量發展新征程。我們要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引領,協調人與自然關系;以綠色轉型為驅動,助力全球可持續發展;以人民福祉為中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國際法為基礎,維護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2021年4月,習近平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強調,“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中國堅定踐行多邊主義,努力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①習近平:《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1年 4月 2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4/22/c_1127363132.htm。
(一)中國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中國環境治理實踐的理論指南,②李琴、陳家寬:《全球環境治理視角的生態文明建設:中國方案與智慧》,《科學》2021年第5 期,第1—6 頁。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治理被提到重要地位,形成了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方案,并建成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在實踐上,中國已探索出“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劃定生態保護紅線”“促進生態修復和技術創新”“建成生態補償機制”等具體措施。③于宏源:《全球環境治理轉型下的中國環境外交:理念、實踐與領導力》,《當代世界》2021年第5 期,第18—25 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需要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中國制定形成了“雙碳”目標下的“1+N”政策體系,并結合自身環境稟賦和實際經濟發展狀況,先立后破,精準把握自身定位,分類施策、因地制宜、上下聯動,梯次有序推進碳達峰。④國務院:《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中國政府網,2021年10月26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技術和資源大國,并積極構建以可再生能源產業為主體的新型供應鏈。⑤于宏源:《能源轉型的市場嬗變、大國競合和中國引領》,《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13 期,第34—44 頁。2021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和發電量穩中有升,可再生能源生產和消費實現較快增長,有力地推動了清潔、低碳、高效能源體系的構建。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2.48 萬億千瓦時,占全部發電量的29.7%,可再生能源發電累計裝機容量10.63 億千瓦。⑥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報告2021》,2022年6月24日。根據BP 發布的《2022年能源統計年鑒》,中國水電消費占全球總量的30.4%,光伏發電占全球總量的31.7%,風電則是35.2%,可再生能源裝機和消費總量都遙遙領先世界各國。①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June 23,2022,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2020年水電、風電、光伏發電利用率分別達到97%、97%和98%;②姚金楠:《水電總院:2025年我國半數發電裝機將來自可再生能源》,北極星電力新聞網,2021年7月7日,https://news.bjx.com.cn/html/20210707/1162471.shtml。2020年中國多晶硅、硅片、電池片及相關組件產量分別占全球總產量的76%、96.2%、82.5%、76.1%,多晶硅產量連續十年位居世界第一,風電、光伏發電設備制造形成完整產業鏈,③《2019—2020年中國光伏產業年度報告》,中國光伏協會網站,2020年7月8日,http://www.chinapv.org.cn/annual_report/821.html。并已成為全球綠色低碳供應鏈和產業鏈的主力軍。
(二)為全球環境治理轉型不斷貢獻中國方案
中國一直強調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全球各方實現互惠共贏,應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建全球生態文明,創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中國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天人合一”的智慧。全球環境合作需要不斷彰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格局和底色,踐行以人為本的綠色發展理念和系統治理戰略,中國充分體現負責任大國形象,不斷在全球綠色復蘇中提供“中國方案”,通過自身資金、技術和經驗以及綠色“一帶一路”的搭建來幫助其他國家解決環境和發展問題,在聯合國、大國合作和多邊主義框架下推動實現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建設。中國主張在推進全球氣候治理上,各方應拋棄“零和博弈”狹隘思維,思考探索未來全球治理模式。在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中國提出“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相關議題獲得與會各國的廣泛共識,推進世界各國重視自然途徑,并把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融入《巴黎協定》國家自主貢獻(NDC)以及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實施進程中。我們應該積極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三)積極參與國際環境領域政治談判、落實履約義務、推動國際合作
中國積極投身環境領域談判,承擔自身義務,切實參與環境領域全球治理,為全球生態文明轉型注入中國動力。
第一,中國以綠色“一帶一路”為合作樣本推動生態文明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區域治理并向地區國家提供發展公共產品,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徑。①郭樹勇:《區域治理理論與中國外交定位》,《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12 期,第47—54 頁。在“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中國頂層設計完整、沿線國家與中國開展環境合作的意愿強烈、技術和項目等具體方面的現實需求高漲、多層次合作機制效能彰顯,這些都賦予中國環境外交以重大契機。綠色“一帶一路”的環境外交以團結合作不斷推進國家總體外交進程,不僅可以填補綠色公共產品赤字,也將引領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
第二,中國堅持通過多邊國際機制推進國際環境合作。中國積極支持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機制發揮領導力,推進生態文明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主題。中國與聯合國系統相關環境機構、世界氣象組織等密切合作,積極參與亞太環境部長論壇、亞太可持續發展論壇、東盟“10+3”環境合作機制等多邊合作機制以發揮引領能力。
第三,中國積極推進大國環境外交,通過中美、中歐間大國協調并在G20 和基礎四國等框架下引領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取得成功。2016年,中國作為G20 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的主辦方,推動G20 第二次協調人會議發表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的主席聲明,這是G20 歷史上首次就氣候變化問題專門發表聲明。中國推進囊括減緩、透明度、適應信息通報、全球盤點、資金、履約等問題在內的《巴黎協定》實施細則談判。中國還創造性地構建了部長級多邊磋商平臺,與印度、巴西、南非等國共建了“基礎四國”部長級磋商協調機制,與立場相近的發展中國家建立協調機制,與加拿大、歐盟共同發起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機制。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公約以外的談判磋商,調動發揮多渠道協同效應。②張銳:《全球氣候治理的中國方案》,《光明日報》,2021年11月3日,第10 版。
第四,中國一直積極推進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和適應領域的合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權益。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進行合作、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合作是中國對外援助和促進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的主要途徑。2021年《中非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宣言》確立了中非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①《中非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宣言(全文)》,生態環境部網站,2021年12月2日,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112/t20211202_962652.shtml。這是中非開展氣候合作的應有之意,也為中國與非洲國家共建綠色“一帶一路”指引了方向。
二、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演進與中國參與
自工業文明時代開始,人類社會物質財富的快速積累是建立在加速對自然資源攫取、打破自然原有生態平衡的基礎之上的,人與自然的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愈演愈烈的生態危機推動了全球治理的發展,并呈現漸變、長期、難以逆轉等特點。②Miles Kahler,“Global Governance: Three Futur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0,No.2,2018,pp.239-246.應對環境危機必須采取跨界型、公共性、系統性的“人類世”全球治理。③蔡拓:《全球學與全球治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7 頁。Oran R.Young,Governing the Complex Systems: Social Capital for the Anthropocene,Cambridge,Mass.: The MIT Press,2017.由此而來的全球環境治理研究始自20世紀60年代,已經歷時半個多世紀。以羅馬俱樂部報告、1972年于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以及1992年于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等為標志,④Michael W.Manulak,“Multilateral Solutions to Bilateral Problems: The 1972 Stockholm Conference and Canadian Foreig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70,No.1,2015,pp.4-22.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朝著寬領域、多學科、架構復雜化的方向發展,全球環境治理以聯合國相關公約談判為主線,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為原則,⑤王曦:《國際環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 頁;李淑云:《綠色轉型新階段:全球環境治理制度安排的再思考》,《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 期,第149—157 頁。通過雙邊、多邊和多型互動,⑥于宏源:《美國氣候外交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第20—25 頁。來實現應對氣候變化、臭氧層污染物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全球合作。⑦Anthony Giddens,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London:Profile Books,1999,p.10.20世紀90年代初期初步形成的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核心、其他國際環境機構為補充、全球環境大會和公約締約方會議為紐帶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正在經歷深刻轉型。首先是“東升西降”下的權力結構變化與全球環境集體行動困境的加劇。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日益忽略乃至犧牲全球環境治理的公共產品利益,在此情況下全球環境與氣候領域集體行動偏離原有軌道,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赤字問題加劇,集體行動困境日益顯著。其次是與低碳轉型相關的生產、供應鏈、金融、規則、技術創新逐漸成為環境治理的重點。①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1),Emissions Gap Report 2021: The Heat Is On – A World of Climate Promises Not Yet Delivered – Executive Summary.Nairobi,pp.1-9.隨著全球氣候災害和極端天氣問題日益頻發,綠色經濟主張、碳中和與零碳技術快速發展,推動著各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面對增長的極限問題,應對氣候變化、發展綠色低碳經濟和推動產業升級被普遍列入國家議程和發展軌道,從而共同推動世界向清潔綠色可持續方向發展。再次是隨著全球化進入新階段,全球環境治理的各主體參與和影響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發展的能力不斷上升,并與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及其他環境發展議題形成交互作用,在演變過程中逐漸發展為多元行為體和多維治理機制在內的機制復合體。地方、企業和社會組織等作用日益凸顯,既能與國家氣候治理政策建立緊密聯系,也能促進國家和全球氣候治理結構的相互協調。②Kirsten J?rgensen,Anu Jogesh,and Arabinda Mishra,“Multi-leve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Level,” Journal of Integrative Environmental Sciences,Vol.12,No.4,2015,pp.235-245.
在復雜深刻的轉型背景下,全球環境治理架構面臨領導失衡與制度多元化問題,③Rajeesh Kumar,“The United Nation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ategic Analysis,Vol.44,No.5,2020,pp.479-489; and Sebastian Obertur et al.eds,Global Governance of Genetic Resources: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fter the Nagoya Protocol,London: Routledge,2015.呈現治理低效和體系碎片化特征。④于宏源:《全球環境治理內涵及趨勢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59頁。一方面,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世界氣象組織(WMO)、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多邊環境條約秘書處等無法協同治理;另一方面,多邊環境協定的爆炸式增長又引發全球環境治理的“談判疲勞”。⑤Johannes Stripple,“Reconsidering Authority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European Environment,Vol.16,No.5,2007,pp.259-264.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制度改革仍在進行中,隨著聯合國大會第67/251 號決議將UNEP 理事會升格為隸屬于UNEP 的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理事會的原會員也擴大為包含聯合國所有成員的普遍會員制,并開始賦予UNEA 直接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政策建議的權力。過于集中的治理架構難以發揮協同力量以應對日益多樣化的環境問題,而權力多中心化的轉變方向又導致聯合國領銜的環境治理體系面臨多重挑戰。
第一,南北認知差距和發展鴻溝將不斷擴大。南北矛盾貫穿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歷程,在全球化受阻和發達國家國內矛盾激化背景下,南北認知差距和綠色鴻溝不斷加劇。全球環境治理中南北矛盾的實質是雙方在經濟上的實質性不平等與在全球環境議題上的形式平等之間的矛盾,發達國家日益淡化甚至忽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斷向發展中國家施加減排壓力、轉移排放責任、轉嫁減排成本,并在談判上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通過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和氣候俱樂部(Climate Club)模式提高議價能力并強推環境規則。這不僅削弱了發展中國家間的政治團結,也嚴重惡化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危機和國內不平等,加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不平衡現狀。在貿易關系上,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試圖通過政策手段建立本國產業優勢,影響全球自由貿易的公平發展,在氣候融資、技術援助、碳關稅、環保議題等方面制造隱形壁壘并轉嫁生態成本。發達國家以環境容量設限來持續“規鎖”①規鎖(confinement):利用規則主導權優勢對他國進行規范、鎖定、控制。發展中國家。歐盟將碳邊境調節機制作為其綠色轉型的政策重心,引發發展中國家廣泛疑慮,②2021年2月歐盟發布《貿易政策回顧:開放、可持續和自信的貿易政策》報告,突出碳邊境調整機制作用,凸顯了歐盟欲將碳邊境調節稅等手段在國際貿易規則中“合法化”的意圖,“Commission Sets Course for an Open,Sustainable and Assertive EU Trade Policy,”February 18,202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644。美歐通過碳定價或綠色標準來削弱發展中大國的貿易競爭力,通過主導海外投資環境標準給發展中國家合作制造障礙,并損害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拜登政府推出《通脹削減法案》(IRA)等來突出綠色供應鏈的在岸和回岸。歐盟則以《歐洲綠色協議》為政策框架和路線抓手,制定貫徹綠色新政的行動路線;③氣候中和(ClimateNeutrality)作為展示歐盟普世價值體系的重要抓手,總體目標是于2050年過渡到氣候中和、環境可持續、資源高效以及具有韌性的經濟,到2030年至少減少55%溫室氣體排放量,并且保護、維持和增強歐盟的自然資本的雄心European Commission,“The European Green Deal,” November 12,2019,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88580774040&uri=CELEX:52019DC0640。在全球范圍內打造綠色價值鏈,利用自身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于多領域開展行動。上述行為阻礙了綠色技術向發展中國家的推廣,并將導致全球公平貿易和可持續發展鴻溝的進一步加劇。
第二,隨著綠色經濟日益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經濟高地,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正經歷深刻變革,環境治理領導力的內涵也在不斷指向產業主導權、能源安全和相關領域技術引領等多個維度。發達國家習慣于從經濟主導權、能源安全和技術等領域的領導力競爭維度理解環境治理,日益將新興大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傾向于通過以鄰為壑的競爭性綠色經濟政策維持結構性優勢。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生態文明國際領導力的不斷提高,美國將中國視為關鍵對手并通過發展領域的規鎖和地緣政經領域的合圍,不斷擠壓中美環境治理合作空間。拜登政府在一系列行政令中明確表示,其針對清潔能源的政府采購必須嚴格遵循在美國生產、使用美國材料、創造美國就業的“美國制造”原則;在繼承前任政府對外政策遺產基礎上,利用人權議題來打壓中國環境和低碳產業。此外,拜登政府高度重視綠色供應鏈安全問題,強化國內綠色供應鏈韌性和構建盟友間的綠色供應鏈聯盟,打造“去中國化”的供應鏈體系,在生產、制度、標準等方面限制中國綠色產業競爭力和領導力。
第三,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突出環境治理領域的大國競爭屬性,加劇了全球環境治理轉型的碎片化和陣營化趨勢,小多邊主義和氣候俱樂部、“跨大西洋伙伴”等削弱了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全球環境治理機制的完整性。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借“綠色國家理論”作為新自由主義環境治理在全球金融危機后演化出的一種偽裝形式,來強化這些國家金融資本壟斷全球市場的局面。隨著氣候變化等全球環境問題的凸顯,環境治理呈現由低政治向高政治轉變的趨勢。當前由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環境治理和綠色經濟體系動態仍未改變,且美歐領導力呈合流態勢,雙方在政策、產業、技術、市場、標準等領域展開前所未有的廣泛協調。拜登政府借助“綠色復蘇”和“清潔能源計劃”來實現應對氣候危機、維持經濟增速以及消除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多重目標,其氣候新政重視保持美國在全球氣候議題中的領導地位,①Justin Worland,“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Already Calling on China to Do More on Climate Change,” Time,January 21,2021,https://time.com/5933657/john-kerry-china-climate-change/; and Mark Elder,“Optimistic Prospects for US Climate Policy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 Briefing Note,February 2021,pp.1-26.通過建立“俱樂部式”氣候和能源聯盟,以便重建美國的全球環境領導力。美國同G7 盟友倡導建立發達國家的“氣候俱樂部”、同礦產資源國打造“俱樂部式”伙伴關系、重視并贏得小島嶼國家的支持以及拓展美國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規范。②DOE,“DOE Launches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Initiatives to Tackle Climate Crisis,”April 23,2021,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doe-launches-international-clean-energy-initiatives-tackle-climate-crisis.
三、全球環境治理轉型有賴于中國的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方案
全球環境治理面臨的諸多挑戰迫切需要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是維護聯合國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和地球生態安全的適宜路徑,為協同解決環境公共產品赤字提供體系規則保障。在生態文明建設上,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生態文明既是可持續發展和人類世時代全球治理的目標原則,也引領了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的戰略方向。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強調,“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③習近平:《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講話》。。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涵蓋“堅持生態優先、實現綠色發展”“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以生態系統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并倡導建設“地球生命共同體”“發展共同體”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代表的中國理念抓住了綠色轉型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為世界整體可持續發展找到了生態環境這一關鍵支撐。
第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重新凝聚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共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時代的國際社會提供了目標導向,為化解國家間的利益矛盾提供了可行性路徑。①欒林:《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全球治理體系的當代構建》,《人民論壇》,2021年第11 期,第53—55 頁。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完善全球環境治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②習近平:《堅定信心 共克時艱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人民網,2022年 9月 2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922/c1024-32232511.html。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國際社會需要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模式。國際學者在生態經濟學、全球環境治理與生態民主協商制度等領域的既有研究也為全球生態文明轉型提供了參考。③王學義,鄭昊:《工業資本主義、生態經濟學、全球環境治理與生態民主協商制度:西方生態文明最新思想理論述評》,《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9 期,第137—142頁;郇慶治:《文明轉型視野下的環境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版,第5—29 頁。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人類集體利益的“匯合點”或“最大公約數”,是中國為全球生態文明轉型貢獻的理念型指引,體現了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理念型領導力。應對環境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要重組人類與自然系統之間的整體關系。西方主導的綠色經濟標準、國際環境規則的政治結構失衡、環境法律體系的碎片化制約了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的效果,激發了全球生態文明轉型的現實需求。人類社會無法依賴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的領導力實現轉型,必須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協同推進。在全球生態文明轉型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能夠有效統籌公平、效率和國家利益的平衡。總體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旨在完善全球環境治理的價值觀、治理體系、治理機制及治理格局,將構建周邊環境共同體作為切入點,從而實現循序漸進發展。中國已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需要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增強自身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進而積極引導國際秩序變革方向。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中國向可持續、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需要,也是中國參與、融入構建國際綠色價值鏈、提供國際綠色公共產品的重要途徑。這有利于推動建設全球生態文明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全球治理體系的當代構建、為化解國家間的利益矛盾提供了可行性路徑。
第二,中國應對環境與氣候挑戰的舉措為世界生態文明轉型提供了路徑建議。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系統治理方案,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指引,堅持多邊主義框架,協調主要國家間關系和重視發展中國家的權利。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內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應有之義。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清潔能源領域的顯著成就,為世界環境治理提供了另一種可供他國選擇的中國特色方案。中國在積極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應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國際制度建設和國際話語能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參照、可復制的轉型樣本。奧蘭·揚①Oran R.Young,Governing the Complex Systems: Social Capital for the Anthropocene.提出了“人類世”下全球治理的“適配性難題”(Problem of Fit),即需要提高全球環境治理和經濟社會系統的匹配度。聯合國《2030 可持續發展議程》也強調政治、經濟、社會等17 項指標的協同治理。環境問題不應孤立分析,而要厘清人類與自然系統之間的整體關系,②Philipp Pattberg and Oscar Widerberg,“Theoris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Key Findings and Future Questions,” Millennium,Vol.43,No.2,2015,pp.684-705.全球生態文明轉型是建設地球系統安全的理想路徑,為協同解決環境公共產品赤字提供體系規則保障。③畢軍:《環境治理模式: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4 期,第9—10 頁。習近平強調,“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④《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人民網,2013年11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5.html。,并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綠色發展繁榮”“熱愛自然情懷”“科學治理精神”“攜手合作應對”等圍繞地球美麗家園建設的系統性路徑。習近平在闡述生態與文明的關系時指出:“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⑤《生態興則文明興——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系列評論之二》,求是網,2019年 5月 1日,http://www.qstheory.cn/llwx/2019-05/01/c_1124441093.html。清潔生產、綠色能源和低碳產業既是自然生態財富,又是社會經濟財富。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明確要求努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作為全球主要碳排放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加速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不但有助于兌現碳達峰、碳中和承諾,更可為促進《巴黎協定》實施細則的全面落實和有效運轉、減緩全球氣候變化、達成溫控目標作出貢獻,還能為在氣候變化危機中尤為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環境公共產品,并有助于推動中國的全球公共產品供應,促進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國內治理實踐既有力回應了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質疑,也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環境治理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寶貴經驗。中國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以自身的示范性提高全球生態文明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為世界樹立了榜樣,并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綠色現代化提供了經驗,①樊陽程、徐保軍:《基于量化國際比較看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世界價值》,《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 期,第27—39 頁。中國將繼續發揮善治力量的作用并與國際社會深化合作,共同改變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的負面部分。②郇慶治:《“碳政治”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批判及其超越》,《中國社會科學》2016第3 期,第24—41 頁;王曦、郭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擺脫全球環境治理困境的啟示》,《環境保護》2021年第6 期,第58—61 頁。中國可以從環境權保護、分配正義等維度來整體推進全球環境治理改革,并推進國家責任、國際環境規制、國際環境爭端解決路徑等的建設和完善。③張文彬:《從國際合作視角看如何構建生態文明社會》,《理論導刊》2013年第2期,第109—112 頁;王琪:《氣候正義視域下的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救濟路徑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年第12 期,第31—38 頁。面對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的單邊環境貿易行為,中國可與發展中國家一起制定環境稅收國際協調新機制。④劉桂昌:《全球治理視閾下環境稅收國際協調的挑戰與對策》,《經濟體制改革》2020年第5 期,第120—126 頁。
第三,中國生態文明建設與多邊、普惠、包容原則相適宜。生態文明建設有助于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當前,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導致地緣政治博弈凸顯,大國關系中戰略互疑、戰略競爭的側面不斷放大。全球化的不斷深化進一步凸顯了全球治理中的集體行動困境,個別大國的單邊行動加劇了治理赤字。國際社會需要各國拋棄零和博弈思維,以切實的減碳行動共擔國際責任。因此,在日益嚴峻的全球氣候與經濟危機面前,一方面,中國應釋放開放和合作的信號,以推動全球氣候和能源治理作為穩定國際關系、為脆弱的大國關系提供良性互動的渠道和穩定支持的新途徑;另一方面,中國應積極推進國內能源轉型,積極承擔國際氣候治理中的重要責任,提振全球氣候治理信心,推動全球主要排放國的減排行動。習近平指出,“國際社會要加強合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①新華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論習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主旨講話》,2021年10月12日。全球生態文明理念應高舉多邊主義的旗幟,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意愿和利益,從而更有效地應對全球環境與氣候挑戰,②汪萬發、許勤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國際展望》2021年第4 期,第134—151 頁。致力于形成各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擺脫囚徒困境和改進現行的國際環保規則。作為認識論與實踐論的統一,③陳鵬,奚潔人:《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國際領導力探析》,《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1 期,第15—24 頁。中國將生態文明不斷融入綠色“一帶一路”建設④Johanna Coenen et al.,“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Vol.31,No.1,2021,pp.3-17.等多邊合作機制或平臺,與各國一道推動聯合國系統吸納和推廣生態文明理念。⑤董亮:《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全球環境治理觀》,《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12期,第30—38 頁。
四、中國生態文明國際領導力助力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改革
人類正在面臨著諸多全球性生態環境挑戰,⑥傅聰:《氣候變化的安全意涵:溯源、概念及啟示》,《歐洲研究》2015年第5 期,第35 頁。全球生態文明轉型關乎公平、效率和國家利益三者的平衡,當前一些大國對于全球治理領導力和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爭奪十分激烈,一些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等領域的既有優勢仍較為明顯,如何建成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仍是全球難題。習近平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強調,“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完善全球環境治理”⑦習近平:《堅定信心共克時艱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全球環境治理緣起于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在工業化進程中對自然資源的無序開發和過度攫取,西方發達國家負有全球環境問題的歷史性責任。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還在持續推動環境污染轉移,并使用負外部性權力影響總體談判進程和其他行為體以獲取利益,形成一種生態殖民主義,帶來南北差距和全球環境非正義現象。人類社會無法依賴美西方國家的領導力實現轉型,必須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協同推進。①于宏源:《中國環境外交的歷程、成就和展望》,《人民論壇》2021年第33 期,第50—55 頁。領導力是指行為體通過綜合運用自身在政治、經濟、制度等場域的優勢,以形成在國際范圍內對全球治理體系的價值、規則、效果和權責分配等進行引導和形塑的力量。在全球生態文明轉型下,領導力事關地球系統環境容量分配、大國軟實力競爭和發展中國家發展權益。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生態文明轉型重點體現在經濟、政治和制度三個場域,與之相關的領導力建設也將圍繞三個場域延展,并指向全球生態文明政治共同體、全球生態文明經濟共生體和全球生態文明制度復合體建設。在多重挑戰和多元博弈背景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力量在全球治理中趨于平衡,中國領導力建設將推進全球生態文明轉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以理念培養和機制建設雙軌推動全球生態文明轉型,通過領導力形塑助力全球生態文明轉型,以爭取實現自然生態環境與人類的和諧相處。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的清潔美麗世界的愿景和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一環,具體而言,中國是從完善全球環境治理的價值觀、治理體系、治理機制、治理格局入手,以構建周邊環境共同體為切入點,實現相關國際領域的循序漸進發展。②盧光盛、吳波訊:《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的“清潔美麗世界”構建——兼論“瀾湄環境共同體”建設》,《國際展望》2019年第2 期,第64—83 頁。
第一,以國內生態文明建設為全球環境治理發揮示范作用。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應對全球轉型的要求,也是國內綠色低碳發展的切實需要。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充分發揮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領導作用,承擔應有的國際責任,將“雙碳”目標提上發展議程,積極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經驗,以幫助其解決環境問題,共同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在堅持環境友好、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同時,中國同樣面臨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消除貧困、治理污染等一系列艱巨任務。今后,中國應通過推動國內綠色轉型引領經濟社會的綠色發展,加速構建國際綠色經濟產業鏈和國際綠色公共產品供給,積極參與國際清潔能源外交,開放分享生態文明發展理念,同時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利益,以國內發展經驗促進國際社會共同發展,從而形成由內而外的中國生態文明國際領導力,進而引領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二,繼續深化建設以多邊平臺、共同體為基礎的治理機制。生態文明建設國際合作和生態文明共同體建設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①劉雯:《構建全球環境利益共同體的使命與路徑》,《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6 期,第100—103 頁。圍繞環境合作的共同體也是全球生態文明轉型的重要特征。②李慧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背景下的全球氣候治理新形勢及中國的戰略選擇》,《國際關系研究》2018年第4 期,第3—20 頁。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是多邊環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的話語權和談判主導權是領導力的重要表現。隨著中國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重視和對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參與度的提升,中國可積極引導大國競合關系、協調各國環境治理共識、提升環境公約談判中的話語權,積極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治理和發展權益,通過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逐步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構建中國話語權。當前主權國家的競合關系往往涉及生態安全、地緣和合作問題,生態文明共同體要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重視環境外交和生態安全能力,重視國家在全球生態文明共同體中的領導力作用,最終實現生態合作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應以全球視野推進生態文明共同體建設,以開放合作為核心,逐漸構建起多方廣泛參與的生態文明共同體。
第三,扮演全球環境治理機制復合體中的協調者角色。一個國家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是否具有領導力體現在其是否具備建立機制和制定規則的能力。全球環境治理制度體系已經形成了專門性多邊國際環境條約機構、聯合國及其相關下屬機構議事平臺、多利益攸關方共同參與的合作機制、小多邊及區域間論壇機制等耦合交疊的機制復合體。不同機制擁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規則,中國宜積極參與在各機制框架下的環境與氣候治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制一策”治理模式,進而在全球生態文明制度復合體轉型中彰顯中國智慧。中國應在相關領域國際合作過程中充分宣介本國先進的綠色轉型、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和經驗;③孫成龍、潘曉濱:《中國引領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路徑探索》,《未來與發展》2019年第12 期,第1—7 頁。應進一步明晰和深化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核心的話語優勢、傳播機制和傳播路徑,①李昕蕾:《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國際傳播及其路徑優化》,《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9年第4 期,第3—14 頁。并嵌入全球生態文明制度復合體建設中,構建屬于中國的話語體系,以獲得充分的國際話語權。
第四,推進全球生態文明經濟共生體建設,以市場機制形成刺激機制。經濟領導力體現為本國產業在全球綠色生產鏈和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是領導力的物質基礎。全球生態文明轉型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但在實踐過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所處的發展環境和階段不同,其對綠色經濟的貢獻能力也不盡相同。發達國家作為既得利益者,應該作出表率,在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中承擔自己的責任。中國作為在全球氣候體系中影響力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要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當利益,也要為全球綠色轉型作出中國貢獻。通過落實“雙碳”目標,將中國的氣候治理實踐轉化為經濟引領力和影響力,進而在全球生態文明轉型和經濟共生體構建中發揮自身力量,彌合綠色鴻溝。在生態文明建設國際合作和綠色“一帶一路”建設中堅持維護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定位并深化國際合作力度,②于宏源、汪萬發:《綠色“一帶一路”建設:進展、挑戰與深化路徑》,《國際問題研究》2021年第2 期,第114—129 頁。推動實現專業化、制度化的國際合作。
第五,聯合發展中國家,為其提供可借鑒的轉型樣本。作為新興經濟體,中國在推動能源轉型中面臨著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挑戰,其路徑和經驗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平衡短期經濟社會發展和長期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具有特殊的借鑒意義。中國推動自身綠色能源轉型有助于通過知識生產和制度外溢共享發展經驗,為世界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好地提供能源轉型方案、綠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經驗及技術等全球公共產品,為實現全球2030 可持續發展目標貢獻中國智慧。首先,在生態理念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理念為發展中國家推動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導向。其次,在轉型路徑上,中國將頂層設計與市場導向結合在一起。中國可再生能源市場的發展從早期的政府扶持階段逐漸向市場主導階段過渡,未來將充分發揮市場導向的綠色金融制度,同時深化可再生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將企業作為主要行為體、市場導向作為優先驅動力的低碳技術創新體系。再次,在機制建設上,中國逐漸改革完善生態環保和能源轉型的國內法律與制度框架,有助于發揮制度外溢作用,為全球環境治理和能源轉型的具體制度設計提供中國方案。
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亟待深刻變革的背景下,王毅在2018年的《世界環境公約》主題峰會上強調要推動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國際環境治理多邊體系。中國重視在多邊主義框架下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中國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角色正加快從追隨者向引領者的轉變。中國一向堅定支持、執行、推進《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巴黎協定》等國際共識和公約,也一直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貢獻自身經驗、力量和智慧,中國將繼續堅持多邊主義,引領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走出現實困境、①馬麗、張首先:《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治理困境、邏輯必然與中國貢獻》,《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 期,第55—63 頁。推動全球環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并以負責任的態度維護全球生態安全。②莊貴陽、薄凡、張靖:《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與戰略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4 期,第4—27 頁。在當下全球治理改革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復雜環境下,生態文明建設是全球可持續發展和構建美好世界的切實抓手,也是推動后疫情時代經濟復蘇的有力保障。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方案可以為解決當前全球低碳轉型問題提供切入點。展望未來,中國將以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為導向,將氣候治理嵌入安全與發展的統籌機制之中,通過加速國內生態文明建設和推動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助力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轉型,平衡大國能源轉型中的競合關系,積極參與引領碳中和的綠色公共產品供給和全球環境法治體系建設,并促進全球生態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③于宏源:《能源轉型的市場嬗變、大國競合和中國引領》,第34—4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