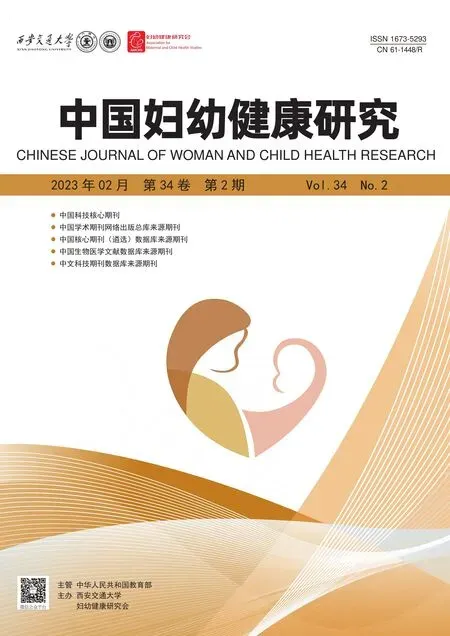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微生態研究進展
郭 杉,劉瑞霞,陰赪宏
(1.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中心實驗室,北京 100026;2.北京婦幼保健院中心實驗室,北京 100026)
胎齡在28~37周的新生兒定義為早產兒。因胎齡小,出生體重低,易并發新生兒疾病,早產或低出生體重是我國部分地區2015年5歲以下兒童死亡主要原因[1]。早產兒胃腸道發育不成熟,腸道微生態在多樣性、結構組成、代謝功能等各方面均與足月兒不同。腸道菌群在新生兒代謝、免疫系統建立等生理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腸道菌群失調與壞死性小腸結腸炎、晚發型敗血癥等多種新生兒疾病相關[2]。早產是低出生體重主要原因之一,極低出生體重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發病率為5%~10%,死亡率高達25%[3]。闡明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菌群定植影響因素及遠期關聯有利于改進現有干預措施,防治低出生體重早產兒新生兒疾病及生長發育遲緩。因此,本研究綜述了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微生態的研究進展。
1新生兒腸道菌群的建立
1.1產前
既往認為,子宮宮腔內為無菌狀態,新生兒腸道菌群在出生后開始定植[4],即曾被廣泛接納的無菌宮腔假說。但新近研究表明,胎盤、羊水、胎糞中均存在微生物群落,其中大部分胎盤及羊水中的微生物源自母親口腔[5],這表明胎兒在母體內已開始接觸微生物環境,由此產生宮腔定植假說,即宮腔和胎盤是有菌的,胎兒的菌群定植在宮內已開始。
一項納入486名中國孕婦的臨床研究分別收集剖宮產胎兒出生時的羊水、唾液、胎糞樣本及孕婦產后2天的唾液、陰道分泌物及糞便樣本進行16s rRNA基因測序,發現無論腸道菌群豐度還是共現性,新生兒和孕婦均有相同的變化趨勢,且新生兒多部位菌群源自母親腸道。母嬰菌群傳遞也給新生兒帶來了潛在的危險。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婦和胎兒腸道患病菌群趨于同質化,可能導致胎兒代謝功能降低,疾病易感性增加[6],提示懷孕時母親的身體健康狀況可影響自身腸道菌群結構進而傳遞給胎兒,臨床上在孕期時密切關注孕婦的腸道菌群情況并做出調節可能有利于新生兒健康,未來需進一步探討研究。
1.2產時產后
分娩時胎頭下降過程中,胎兒首先接觸到陰道菌群,陰道菌群在新生兒體內定植后,消耗腸道內氧氣,因腸道內氧氣含量較低,腸桿菌、腸球菌、葡萄球菌、鏈球菌等兼性厭氧菌在腸道內占據優勢[7]。
出生后,新生兒在吮吸母乳過程中接觸到母親的皮膚菌群,同時,母乳中特有的不同種類低聚糖,可抑制致病菌生長,使新生兒腸道環境更適合有益菌定植[8]。兼性厭氧菌的定植使腸道內氧氣含量進一步下降,為專性厭氧菌如雙歧桿菌、擬桿菌、梭菌等定植提供了條件。雙歧桿菌可促進母乳中多聚糖代謝,在早期新生兒腸道菌群比例中占據優勢。隨著輔食添加、固體食物引入,為了代謝復雜食物中含有的淀粉等成分,新生兒腸道菌群種類逐漸增多。從斷奶開始,新生兒腸道日趨成熟,腸道菌群組成逐漸與成人相同[9]。
2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微生態特征及影響因素
2.1腸道微生態特征
孕周及出生體重是腸道微生態差異產生的最主要因素。與足月兒相比,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出生后早期雙歧桿菌等有益菌群定植較晚,α多樣性、β多樣性降低。在屬水平上,大量菌群豐度存在差異,具體表現為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共生、專性厭氧細菌普遍減少,而機會致病菌和兼性厭氧菌腸球菌、克雷伯菌、鏈球菌豐度較高[10]。分娩方式、喂養方式及治療手段在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微生態的建立中亦發揮重要作用[11]。
2.2腸道微生態影響因素
2.2.1分娩方式
分娩方式是決定胎兒早期腸道菌群組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2]。由于產婦合并妊娠期高血壓綜合征、胎盤功能不良、臍帶異常等高危因素,醫源性早產剖宮產率高達89.4%[13],低出生體重早產兒達75.5%[14]。順產新生兒經產道過程中,先后接觸母親的陰道、糞便及皮膚菌群;剖宮產新生兒只接觸母親皮膚和來自環境中的菌群。生后1周至1個月,順產胎兒擬桿菌屬豐度較高;剖宮產胎兒雙歧桿菌屬豐度較低,克雷伯菌屬、嗜血桿菌屬豐度較高[10]。生后1至3個月,菌群豐度差異逐漸變小,但順產胎兒腸道菌群中乳酸桿菌和雙歧桿菌仍占優勢。順產胎兒和剖宮產胎兒在腸道菌群豐度及多樣性的差異可持續至3~5歲[15]。
2.2.2外界環境
出生后所處的環境條件是新生兒腸道微生態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出生后即被轉入新生兒重癥監護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NICU中設備呼吸機、導管、聽診器、安撫奶嘴等表面存在鏈球菌、奈瑟菌、假單胞菌、葡萄球菌、腸桿菌等[16]。NICU的低出生體重早產兒糞便樣本測序分析發現克雷伯氏菌屬、腸桿菌屬、腸球菌屬豐度較高,且同一監護室的新生兒腸道菌群間的差異隨住院時間增長而逐漸減小[17]。因此,探究醫院環境條件致病菌定植對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菌群的影響,對防治壞死性小腸結腸炎、敗血癥等新生兒常見感染性疾病有重要臨床意義[18]。
2.2.3喂養方式
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出生后即與母親分開,在NICU使用配方奶粉喂養,足月兒生后多為母乳喂養。母乳喂養的新生兒,出生后數周腸道擬桿菌和雙歧桿菌豐度增高,腸桿菌屬和葡萄球菌屬豐度下降。母乳中含有人母乳低聚糖(human milk oligosaccharides, HMO),HMO經過雙歧桿菌代謝后產生乙酸,可降低腸腔內部pH值,抑制病原菌的生長;HMO還可作為可溶性配體類似物與病原菌結合,阻止病原菌粘附于腸道上皮細胞的多糖蛋白復合物上而引起疾病[8]。盡管配方乳中已逐步添加益生菌等對早產兒腸道微生態有益的組分,但與母乳喂養相比,配方乳喂養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桿菌目豐度顯著增高,梭菌和乳桿菌目豐度顯著降低[19]。
2.2.4抗生素使用
出生后即轉入NICU的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因預防或治療敗血癥等感染性疾病,抗生素應用較為普遍。使用廣譜抗生素固然能降低早產兒感染性疾病的發病率及死亡率,但同時也影響早產兒早期腸道微生態的建立[20]。收集入組嬰兒生后1個月、6個月、12個月、24個月時糞便樣本,測序發現抗生素組嬰兒腸道菌群中雙歧桿菌屬受影響最大,豐度始終偏低,種類偏少[21]。使用抗生素的早產兒腸道菌群多樣性降低,雙歧桿菌屬定植時間落后,耐藥菌群如克雷伯桿菌屬、埃希氏桿菌屬、腸桿菌屬、腸球菌屬豐度增加。隨著用藥時程增加,早產兒腸道微生態多樣性下降更明顯,雙歧桿菌屬豐度恢復時間增長[20]。停止使用抗生素后,早產兒腸道微生態至少需要2個月的時間來建立新的平衡[22]。
2.2.5呼吸支持
低出生體重早產兒由于出生時肺部發育成熟度不同,多采用無創或有創等氧療方式。氣道正壓呼吸支持可給新生兒原本缺氧的胃腸道帶來氧氣,胃腸道有氧環境更利于需氧菌和兼性厭氧菌的生長,使專性厭氧菌繁殖受阻[23]。氧療持續時間與新生兒腸道菌群組成密切相關,治療時間越長,新生兒腸道中需氧菌和兼性厭氧菌越占優勢。專性厭氧菌粘附于腸黏膜上可加固腸黏膜屏障,抵抗病原菌的入侵。腸道中專性厭氧菌減少使腸道通透性增加,而早產兒院內感染病原體多為兼性厭氧菌,可能損害早產兒腸道防御功能并增強院內感染的發生[24]。同時,足月兒通過厭氧發酵代謝母乳或配方乳,而呼吸支持的早產兒因腸道中氧氣含量增高,腸道通過好氧分解代謝配方乳,影響能量供給、營養成分及生物活性物質的合成,進而影響生長發育[25]。
3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微生態與遠期關聯
3.1新生兒疾病
3.1.1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
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的發病與低出生體重早產兒的腸道菌群特征相關。NEC表現為新生兒腹脹、便血、腸黏膜壞死,危及患兒生命。早產兒生后兩周,腸道中的產氣莢膜梭菌可能會導致NEC的發生[26];腸道菌群中腸桿菌科占優勢,也可能是NEC發生的原因之一[27]。患有NEC的新生兒腸道中普遍變形菌門豐度升高,厚壁菌門、擬桿菌門豐度降低[28]。變形菌門為革蘭氏陰性菌,富含脂多糖。脂多糖增多可使Toll樣受體4(toll-like receptor 4,TLR4)表達量升高,而早產兒免疫系統適應性反應尚未發展健全,增多的變形菌門通過TLR4使免疫系統反應過度,引起腸道損傷壞死[29]。
3.1.2遲發型新生兒敗血癥
遲/晚發型新生兒敗血癥(late-onset neonatal sepsis, LONS)是新生兒出生后7~10天發生的嚴重感染性疾病,收集LONS患兒糞便樣本測序發現常見遲/晚發型敗血癥致病微生物來源于腸道,并非皮膚轉移,如克雷伯氏菌屬、大腸桿菌屬、鏈球菌屬、腸球菌屬等[30]。同時,LONS患兒腸道微生物多樣性降低,變形菌門及厚壁菌門豐度較高,雙歧桿菌屬豐度低[17],與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雙歧桿菌屬定植偏晚、機會致病菌豐度增高的特征一致。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早產兒早期腸道菌群穩態對遏制LONS的發生極為重要。
3.2生長發育
生長發育指標是衡量早產兒健康狀況的重要依據[31]。低出生體重早產兒住院期間配方乳無法完全模擬人類母乳成分,腸道發育不成熟,腸蠕動異常,熱量吸收不足,均導致超過一半的早產兒在出院后生長發育持續落后[11]。而大多數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在NICU中使用過抗生素,相比于未接觸過抗生素的兒童,生后14天內接受抗生素治療的男童在6歲前身高、體重普遍偏低。將經抗生素治療組嬰兒的糞便菌群移植給無菌小鼠后,相比于無抗生素移植組,抗生素治療組菌群移植雄性小鼠生長速度變慢,這表明早期應用抗生素可能通過腸道菌群影響兒童的身高及體重增長。
3.3神經發育
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微生態穩態并未建立[32],腸腦軸紊亂,影響胎兒遠期神經發育,表現為認知能力偏低等[33]。孕晚期是胎兒大腦發育成熟關鍵期,在此階段,胎兒大腦皮質灰質已成熟,白質軸突、膠質細胞及少突膠質細胞之間的復雜連接將逐步構建[34],因此相比于足月兒,早產兒早期神經系統發育不足。頭圍追趕生長與兒童早期建立良好的認知能力及行為表現相關。出生后糾正胎齡6個月內頭圍追趕生長至正常范圍的早產兒腸道菌群內沙門氏菌、黃桿菌屬、伯克氏菌屬豐度較高,而在糾正胎齡6個月后頭圍追趕生長至正常范圍的早產兒腸道菌群中普氏菌屬、水棲菌屬、慢生根瘤菌屬及不動桿菌屬占優勢。功能預測表明,糾正胎齡6個月內頭圍追趕生長至正常范圍的早產兒腸道菌群中轉運體(如ATP結合盒轉運體)相關基因表達增高,具體通路及影響機制需更多的研究進一步闡明[35]。
4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微生態干預措施
4.1益生菌
益生菌主要成分為足月兒腸道中占主導地位的雙歧桿菌屬。益生菌干預低出生體重兒腸道菌群組成更加穩定,脂肪酸生物合成通路、淀粉、糖類、脂肪酸、酪氨酸、過氧化物酶體、丁酸甲酯的代謝通路表達顯著增高;無益生菌組中,腸道菌群的脂多糖生物合成及感染定植相關的代謝通路表達較高[36]。合理應用益生菌制劑是否利于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后期的生長發育,是后續值得探討的研究問題。
4.2益生元
益生元是通過發酵作用改善腸道菌群組成并有利于宿主健康的生物制劑。早期使用益生元制劑可有效降低低出生體重兒感染發生率、死亡率,縮短住院時間及較早達到完全腸內營養[37]。益生元的主要成分之一HMO,目前已被添加到配方奶粉中。但需注意的是,隨著母乳分泌時間的變化,HMO的種類及分泌量也在改變,配方奶粉的益生元添加也需在成分上做出相應的改變,以更好地調節嬰兒的腸道菌群[8]。
4.3糞菌移植
一項臨床試驗中,研究人員將提取的7位母親的糞便菌群分別摻在母乳中,在剖宮產嬰兒出生后第一次母乳喂養的過程中喂給各自的孩子。干預3個月后收集嬰兒糞便樣本測序發現,7名嬰兒中有6名腸道菌群擬桿菌群屬和雙歧桿菌屬豐度增高,為優勢菌群,腸道菌群結構與順產嬰兒更為相似;而未接受糞菌移植的剖宮產嬰兒乳桿菌目、梭菌目、腸桿菌目細菌及條件致病菌總相對豐度較高[38]。糞菌移植手段作為大膽的嘗試,其安全性、有效性后續仍需要大規模的臨床研究來進行驗證。
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菌群微生態與足月兒不同,且影響追趕生長及神經發育。雖然已有諸多手段以期建立與足月兒相似的腸道菌群結構,但其對遠期生長發育改善仍是需要研究的科學問題;低出生體重早產兒腸道菌群影響生長發育的具體分子機制,也尚未闡明。未來希望研究者們不斷嘗試,通過調節腸道微生態改善低出生體重早產兒的預后,降低死亡率,給社會帶來更高的經濟和社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