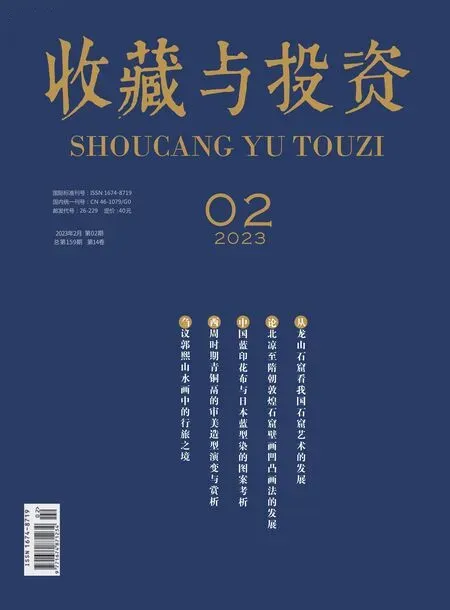趙培智繪畫語言的探索與特征
李夢嬌,陽 爽,譚江麗,吳春麗(貴州師范大學,貴州 貴陽 550001)
一、趙培智語言風格的演變
探究畫家繪畫風格的演變和現今藝術面貌的形成,都繞不開對畫家的繪畫歷程的深入挖掘。作為中國寫意油畫的代表人物趙培智,分析其藝術語言之演變和內心情感的傾斜,對藝術家們有啟示作用。趙培智生活在祖國的邊疆—新疆,這里地域遼闊,遠離時代的喧囂。在這個多民族聚集的地區,他開啟了自己的藝術人生。他自小熱愛繪畫,在初中時就已經臨摹學習過許多古代名畫,這為他打下了堅實的繪畫基礎。趙培智在大學期間從歐洲古典油畫的臨摹學習入手,也受到了俄國巡回展覽畫派的影響[1],他的繪畫創作方向似乎一直是傳統油畫,他的畢業作品《母親》體現了他這四年古典油畫學習的成果。畢業后他便留校任教,一直到40歲才離開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這片土地,迎來了藝術生涯中第一個轉折點。2004年,單位送他去巴黎美院進修深造,之后,他又去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進行考察。這時的趙培智似乎和當年的吳冠中、趙無極游歷歐洲時的心境一樣,對繪畫產生了新思考。他開始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樣的繪畫,自己適合哪個方向。這種深刻而理性的思考使得他非常迷茫和掙扎。他把過去所形成的經驗打破,深度剖析自己并自我反思,做了很多關于繪畫本體語言的研究。為了尋求有意味的形式,他將繪畫語言拆解,進行抽象的排列組合,形成新秩序和新形式。趙培智的繪畫不是單純的創新,實際上是一個對于經典規律再創造可能性的探索。《心靈空間》《無語·花季》《致·未來》是他在這一階段探索的成果,重構破碎的意象空間,張揚而又控制的筆觸,人物的面部神情完全被掩蓋在陰影之中,這是他繪畫語言的第一次探索。
在斬獲全國美展金獎之后,趙培智的繪畫風格經歷了相當長的一個穩定期,畫面的色彩語言如同帕米爾高原上由泥土、山石和少數植被組成的山脈,依著山脈生活的塔吉克族人也染上了這種顏色。他在這個時期的作品色調多使用暖黃色和暖灰色。地處高原,日光充足,人的膚色在太陽常年照射下發紅發棕,人物面部表情多混沌,頗有中國古代寫意畫的意蘊,逸筆草草,不在形似,而在意的表達。因為帕米爾高原的環境惡劣,屬于高寒氣候,所以趙培智畫面中的塔吉克族人常常身著厚重而堅硬的御寒大衣。對于衣紋的處理,趙培智有一套自己的形式法則。為體現衣服材質的特點,他經常用干硬的筆刷順著相同的方向排列組織,匆匆幾筆,瀟灑而自由,不拘泥衣褶的細節處理。豬鬃筆上的顏料有層次地落在畫布上,靈活地舞動著節奏,一蹴而就,顏色統一但不單調。顏料厚重地堆砌,色調偏暖灰和熟褐,人物之間簇擁緊密,人物排列趨于平面化。從下往上,類似于中國畫中的高遠構圖。對于一個表現少數民族的人物畫家來說,趙培智不落入俗套,他筆下的塔吉克族不是我們所熟悉的穿著美麗民族服飾載歌載舞的群體,讓我們感受到的不是熱情洋溢的精神面貌,而是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原始粗獷、深沉質樸的精神世界。畫家總是希望揭示事物背后的某種東西,趙培智也努力通過造型和色彩向我們傳達真實美好的人性。
趙培智對繪畫語言的探索受到了羅馬尼亞畫家科爾內留·巴巴的影響,巴巴的人物肖像中簡練概括的造型語言、厚重樸美的色彩表現以及對人物精神世界的極致刻畫都帶給趙培智不小的啟發。趙培智2014年開始創作的《面孔》系列作品可以讓人明顯地感受到統一的膚色但自由而微妙的顏色變化。趙培智用筆如斧劈皴,凌亂的筆觸更增添了寫意性,給人物的內心世界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他不會對面部的肌肉走向精雕細琢,即使是最重點的“眼神戲”也不費筆墨,但依然能很好地傳遞情緒。趙培智能從巴巴的影響下走出來,獨樹一幟,自成一家,是因為他在學習的過程中有所創新。趙培智對色彩的把控非常精妙,他近些年的寫生人物肖像似乎比以往的群像人物畫像更加輕巧活潑、開朗明艷,變化更加豐富,相比之前充滿鄉土氣息的中性色調,明朗的色調體現了塔吉克人民別樣的生活氣息和生命體驗。《面孔》系列能夠很好地說明趙培智已慢慢轉向了對人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關注,從特定的人轉向了特定的群體。塔吉克族或許是一種載體,用來承載畫家本人對于審美、繪畫甚至社會和人類的理解,是一種超脫形象本身,超越地域、民族和國家界限,試著去揭開事物背后秘密的態度。此階段的群像人物和組像人物也呈現不同的面貌。趙培智對于色彩的調配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深紅、湖藍和果綠等明亮的色彩開始慢慢地在他的作品中占據重要地位,從隱藏在擁擠的暖灰色顏料下到小面積地顯露在表面,充滿趣味性。在語言表現上,趙培智對人物形象作了巧妙的減法,把真實的一面表露在外,更加進一步地指向了內心的精神世界。
趙培智說優秀的畫家都是在不斷探求中完善自身藝術的,不能把風格作為藝術的最終目標。他的藝術充滿理性思考,不斷突破與完善繪畫語言[2]。趙培智是一個不斷否定自己的人,他每個階段的風格并不是有意而為之,在繪畫前他并不預想自己該如何進行繪畫語言的表達。這使得他經常在繪畫的過程中對已形成的畫面結構進行大面積涂抹修改。與之前的作品相比,趙培智畫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概括,色彩和畫面結構關系也趨于單純。相比之前,后來的作品平面化傾向更為突出,早期強烈率性的筆觸在別人的反復強調下被趙培智毅然決然地否定了,他開始收斂這種情緒外露的表達,在繪畫的過程中有時干脆用平涂的顏色把之前的痕跡大面積覆蓋掉,只為追尋更加原始和質樸的一面,努力去達到更理想的狀態。
近幾年來,趙培智的藝術探索又有了新的突破。《相馬圖》《沉默的人》等作品更加充滿意味性和趣味性,在繪畫材料上,丙烯與油畫的完美結合,流動的紅棕色丙烯顏料被涂抹在臉頰的皮膚下似熾熱的、流動的、具有生命溫度的血液。人物造型上的突破極大,較之前寫意的形體,更加趨于簡練、概括的平涂。刻意的夸張變形,同時增添了幾何形的元素,人物的肩膀通常被畫家主觀塑造成高高聳起的樣子,寬大而充滿力量,形體的真實感已被畫家的主觀概括完全取代,畫面結構在意識的支配下更加破碎,這種破裂在某種情況下可以被理解為對以往經驗作了一個減法處理。畫面突顯出來的野生感和生澀感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這種突破也許就是趙培智口中的隱藏在景物背后“看不見的東西”。這種進步是巨大的,呈現他高度概括的能力和成熟風格的形成。

趙培智 《塞上曲之二》 150 cm×150 cm

趙培智 《沉默的大多數之六》 100 cm×100 cm

趙培智 《面孔7》 30 cm×30 cm
二、內容與形式的高度契合
有人問趙培智:“你為什么總是畫新疆人?”塔吉克族人像是被時間定格住,生活在這個世界之外的。畫中塔吉克族的老大爺像是路邊和山上的石頭一樣不被輕易地改變,堅毅、沉默又憂郁。這種獨特的人文品質深深地吸引著趙培智,這種贊賞與向往刺激了畫家的創作欲望。趙培智畫中的塔吉克人們沒有穿著傳統的民族服飾,他們靜默地坐在街頭或是走在田間路上,眼眸低垂,表情沉穩無變化,樸拙而又真摯。趙培智的油畫語言完全適合描繪這種精神,其語言形態沉雄樸厚而深刻的特征和所表達的主題歷史氛圍、悲劇史詩性高度契合。在如今的當代藝術圈子里,形式主義盛行,大多數畫家內心浮躁,急于用新的形式去迎合大眾文化,內容缺乏深度,經不起推敲和挖掘。趙培智說要取得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他所探索的繪畫語言與塔吉克族人的精神面貌相得益彰。寫意性的筆觸是對精神家園的追問,沉悶而有力量的色彩代表著塔吉克人的性格,畫面的張力就是塔吉克人生命的張力。趙培智的油畫語言和表達主題內容的高度契合值得推崇和解讀。
三、趙培智繪畫語言中的寫意性
寫意是中國傳統繪畫的核心,傳統繪畫的重心,不求藝術形象的真實,而強調內在精神的真實,常對所描繪的形象有所寄寓。趙培智的繪畫在中國當代藝術的語境中被納入“寫意油畫”的范疇內。但趙培智的繪畫并不是對東西方兩種傳統繪畫進行簡單的結合,他認為中國油畫的本土化必須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去思考和發展。對于自幼學習國畫的趙培智來說,寫意觀念在繪畫的過程中會不由自主地表達出來,這體現在筆觸的書寫性、人物形象平面化的處理和平面化的空間結構上。
趙培智的寫意性首先體現在簡練的筆法上,簡單的大色塊一氣呵成,再大刀闊斧地平涂。這種筆觸的表現力完美地呈現了服飾質感的表達。對衣紋褶皺的處理也似刀削一般,簡單直接,亦潛藏著中國傳統碑刻的刀砍斧鑿。趙培智畫他對塔吉克人的情感,表現塔吉克人的精神面貌,畫家的注意力都在傳神上,沒有細致地描繪五官,特別是眼睛,雖然點到為止,反而大放異彩。造型上他不受對象固有形象的約束,直抒胸臆,在寫實與寫意之間找到平衡。既不受累于形體的像,也沒有肆意而忘形,這個分寸拿捏得非常準確。趙培智繪畫語言的寫意性還體現在中國傳統繪畫的平面化表現,中國山水畫里有平面中不規則的正負形所產生的有意味的形式,視覺上給人營造一種虛幻的空間。趙培智也一直從生活里尋求這種有意味的形式,一種均衡的結構形式來給人以美的享受。
四、結語
從獲獎至今,趙培智完成了一個從穩定期到轉型期的過渡,努力擺脫特別客觀的人物塑造開始主觀化的概括表達,從描繪塔吉克族的生活到描繪對于個人的精神狀態的理解,更多關注人本身而不是人在做什么,由內容表達到精神表達,在熟知的體驗中尋找人本身真實的狀態。趙培智的轉型期就是在有限的范圍內挖掘無限的可能性。趙培智的繪畫語言的演變,并不是刻意為之的,是一個順其自然的過程。趙培智的繪畫是在傳統的范疇內,對恒定感、經典規律的找尋或是在創造方面的探索,不是一種單純的創新和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