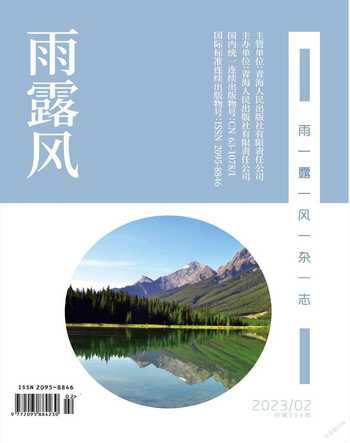螞蚱菜餅子
過年嘛,都要回老家。
大娘和三嬸兒在天井里支起糊面板板,搖得馬扎咯吱咯吱響,半圓的餃子就在幕天席地里誕生,天冷,一呼就是一口白霧。
這里與沸騰的城市相距甚遠,小轎車被排除在寂靜之外,只有麻雀劃破天空的聲音,然后落到干枝上,柿子是它們的儲備糧,秋天時是我的。
我想捏個面人待會兒下鍋一塊煮了。
沒人理我,大娘已經談到了堂哥學期末的成績,比去年升了整整兩個名次,從倒數第一變成了倒數第三。趁著嬸子面露難色的空隙,我說,這學期我考了第七名,拿了兩張獎狀,我們班一個人最多能拿兩張,為啥?因為老師說要把機會給更多的同學……
去去去,出去玩去。
大娘臉上茶褐色雀斑擠到一塊,努著嘴,從面團邊角揪一小塊送到我手上。
我朝屋里瞅一眼,爸和大爺、三叔正在準備上墳的東西,這我也知道,往上數三代的人都要在除夕這一天通過某種神秘儀式回家過年,也許就跟老鷹抓小雞似的后面抓著前面的衣角。以前奶奶說祖宗們回家之后會住在房梁上吃煙火,人越來越多,不知道奶奶回來能不能在房梁上排上位置。
我看著冰箱里還有凍的螞蚱菜,能不能蒸啊?
剛回來我就翻了冰箱,我跟爺爺的感情可是堂兄堂弟比不了的,只是話沒人理,白白飄在空中。
我揪著手里的面團轉身跑出了天井。爺爺一個人坐著馬扎在東墻邊靠著大磨盤曬太陽,到處都是明亮的光,他的影子小小的蜷縮在地上,有一部分折疊在墻邊,旱煙吹出來的裊裊白霧籠罩他。我湊過去,一下子就跳上這個磨盤,它只是發出一聲沉悶的“咚”的聲響。
爺爺依舊看著前方,眼睛沉沉地看著前方的墻面,那里其實什么也沒有。他不跟我說話,也不在意我。很遠的地方有鞭炮聲,是小孩們在玩摔鞭,時斷時續的聲響,炸得這個年也斷斷續續的,新鋪的柏油路邊停了很多車,幾個一看就不是村里長大的孩子穿梭其中,等過完年它們和他們都會消失不見。我覺得我應該說點什么。
爺,屋里的電視這都多少年了?
來來回回就這么幾個頻道,不好看。
這長著大屁股的電視還是從我家搬過來的,它的年齡和我一樣大,爺爺沒看過我家在市里新買的液晶電視呢,就跟紙片似的,卡在墻上占了半壁江山。他沒去過我家,不知道也是應該的,我想了想,極力伸展開雙臂。
這么多人聚在一塊,他為什么看起來不高興呢?
爺爺臉上的褶皺沒有變化,被煙熏黃的牙也沒有露出來,我覺得不對,新年應該讓爺爺開心開心,還有一種微妙的憐意。
等我以后工作了咱馬上換新電視,換個大的,得這么大,爺爺你看我,這么……這么大才行。
我許下舊年最后一個愿望,給爺爺換個大電視。
他終于笑了,冒著火星的煙屁股碾進黃土里,把等待春天的枯草燙出一個疤。
你好好學習,以后換個大的。
好。
我又問,水餃快好了,你吃不?
行啊。
我從側后方看爺爺斑白的發茬,風聲、鳥叫聲、車聲和人交談的聲音混在一起,時遠時近。一切都暴露在蒼白淺黃的太陽下。
他已經老了,我跟另一個自己說,衰老本身就是一件讓人難過的事情,更何況我曾經見過他充滿活力的時候。
我跟著爺爺生活過一年。
在爸媽都搬去市里之后,原本的家被掏得面目全非,我站在巷口圓柱子上看著被五花大綁的家具,柜子門扇上還貼著我攢了兩個星期的錢才買下來的貼畫。
他們一起在汽車尾氣中消失不見了,而我則繼續在鎮上的學校讀書,一周回家一次。在我什么都沒有想的情況下,他們已經做好了全部安排。
于是,周五傍晚我就會跟幾個伙伴一起騎自行車從鎮北到鎮南。大概一個半小時之后,后街最西角馬路旁的老房子里就會傳來幾聲異常嘹亮的聲音。爺爺會給我留門,木板大門敞著口,一條不長的廊路邊全是綠油油的絲瓜藤蔓,東邊是一株葡萄藤和糧屯,我喊爺爺,直到收到答復。
他經常在堂屋里喝濃茶看電視,說是堂屋,也不過放了一張圓桌幾把馬扎,馬扎散了線,糊里糊涂支撐起木棍。有些昏暗的桌子上擺著要解凍的雞鴨魚肉,冰箱里有四個兒女送過來的東西,零零碎碎的吃食。
一看到這些東西,我就知道,爺爺這是在等我呢。
桌子旁邊那個看電視喝茶的絕佳位置就是我的,爺爺泡的茶葉總是一個味兒,濃稠的咖啡色,雖然每次他給老朋友介紹時,分花茶、綠茶、紅茶……當然我從來沒有異議,就像現在遙控器轉到了我手里。
爺爺在外間吆喝我,問吃雞還是吃魚,今天正好是集,他買了好幾個面魚,已經在鍋子上蓋著了,要我餓了就先吃個墊墊肚子。
這確實很難選擇,不出所料的話鍋子里還會有巧克力花卷,包子和炸貨,這是每次回來的保留節目,爺爺以為我很喜歡吃,但事實是因為吃的次數太多,我已不感興趣。
我選擇吃魚。
靛青的夜晚逐漸籠罩住這個村莊,家家戶戶升起了炊煙,暖和的風透過細紗窗飄進來,擠進房子更深處,昏黃的燈光里是爺爺轉來轉去的身影。我的眼睛里只有五彩的電視屏光。這個狐貍變的女人終于要對書生下手了,毛茸茸的尖嘴伸出來,我起了一層雞皮疙瘩,腳有些冷。
電視旁邊有一個四四方方的大黑柜子,原本是在炕上的,里面放的是奶奶的嫁妝,她去世后就搬到了旁邊,在柜子后面露出一個黑色塑料袋的邊角,里面裝是奶奶的遺像,我很害怕看到遺像。你要知道,我奶奶平時可不是那樣笑的。
我搬了個馬扎坐在中堂里繼續看電視,爺爺轉頭看我一眼。
是不是餓了?
一邊把弄好的菜倒進盤子里。盤子里黑乎乎的一片,只能看出大塊魚肉的白。
實事求是地說,不太好吃。奶奶在世時爺爺很少做飯,無論奶奶的手有多么不方便,爺爺仍然堅持在大棚里勞作,他說做飯是女人的活兒。
現在他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我們倆硬著頭皮各自干掉一碗魚肉之后,他趕忙掀開鍋子,還套著透明塑料袋的面魚就熱乎乎的鋪在上面,很少見,我跟它們打了個招呼。
我看著很多人買,你嘗嘗好吃不?
爺,你這是又熘了一遍?
早上買的,吃吧。
爺爺直接拎著塑料袋給了我一個最大的,袋子上都是面魚的香氣。我奶奶就不會用鍋子加熱塑料袋,她雙手叉腰微微彎著身子告訴我們塑料袋加熱有毒。但是在這個暖融融的夜晚,我沒有跟爺爺說,甚至在他鼓勵的目光里吃了兩個。我們都是被拋棄了的人,無所畏懼。
塑料袋被爺爺團成一團,塞進了旁邊掉了色的棗紅櫥柜里。
下回吧,下回一定告訴他。
同樣需要鋪在鍋子上面而非站著或者擠著的,是一種季節性的植物,也是少數幾個爺爺不會弄錯的蒸餅子的原材料。
夏秋,幾乎村里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會長出奇怪的匍匐在地上的草,一節一節地向上抽,只有嫩芽會朝著天,混在一叢叢的狗尾巴草中。但我奶奶可說了,這不是苦菜子、薺菜或者小蒲公英,這叫螞蚱菜。
奶奶還說,要是你不吃的話,等螞蚱在上面蹦跶過后人就沒法吃了。因為舊疾,她的手指和手掌相連的地方凸出了一大塊骨頭,看著就像發育不良的雞爪,她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把螞蚱菜的芽尖掐掉。我看到每個被折斷的螞蚱菜橫截面都會流出一點點清色的汁液。
今兒晌午就給你一個任務,把簸箕裝滿一半螞蚱菜。
現在還是半晌就這么曬,我當然不干,橫豎躺在門口槐樹下的搖椅上擺賴,奶奶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她拎不動我。
要不就沒飯吃了。
那我就不吃了。
奶奶“你”了半天都說不出第二句話來,回屋里頭摸索半天之后手里攥著兩塊餅干來到我身邊。
下次我要吃帶奶油的毛毛蟲面包。
在T字形柏油路口的交接處,往西還有條路,一條很窄的土路,通往連綿不斷的蔬菜大棚,大棚旁邊也被開辟出一塊塊的田字格地,種的多是小蔥山藥豆,有時趁著沒人我們幾個就會兜著衣服采上小半兜子,再從旁邊雜草堆里抓點剪刀手、賴蝗蟲、土蟀,用一根抽了葉的狗尾巴穿起來在火上烤,山藥豆就扔進火堆里悶。
我順著一直往西的土路,掐螞蚱菜尖尖,甚至都不用爬過土坡走到爺爺的大棚,就夠我掐的了。一路上還順帶吃了三表嬸家的黃瓜,田嬸子種的甜辣椒,還有不知道哪家種的小洋柿子。
噢,還帶回了爺爺,在我一腳踩進一片光禿禿的、新翻過的松軟土壤時,立馬就被土坡上的一聲吼叫嚇了回去。這是林三叔家剛下了種子的土地,還沒來得及搭棚,可不能踩。爺爺一邊吼著,一邊拎小雞似的拎著我,搖搖晃晃踩著太陽回家了。
奶奶已經在廚房里忙碌起來,土灶臺上的鍋子四周有灼熱的白氣縷縷,棒子骨頭成群結隊地走進火坑,我大聲叫她,在進門之前就把簸箕從爺爺的手上拿了過來,邀功一樣放到奶奶面前。她的臉笑成一朵菊花,轉身又從鍋里挑了一個裹了糖的小卷子給我。
屋里有白糖,蘸著吃,別在這搗亂。
燒灶的人已經變成了爺爺,空氣中還有一種奇特的味道,被雨打濕又加熱的香氣,悶悶的,說不上來。
很多年后,我才想清楚這種味道本身就是一個形容詞性的概念,就跟薄荷味餅干一樣,它就是螞蚱菜的味道。
見我半只腳踏進來,爺爺努著嘴把我往外趕,說奶奶在小房間,讓我去找她玩兒。
我偏不走,搬了個低矮的木板凳在旁邊,不偏不倚地正沖著灶門,一句話還沒開始說就吐出一連串的咳嗽,今天的煙實在有些嗆。
爺爺抓住我的小辮往旁邊移,緊接著站起來雙手各拿了塊濕抹布攢在鍋子旁邊的兩只耳朵上,手上青筋一起,屜子就掀開了,我這才湊上去看清了里面的樣子。
最底下鋪著白墊布,墊布上薄薄一層螞蚱菜,上面撒了白色的糊糊,爺爺告訴我說這是面粉,“熱了就粘糊了唄,你抓點再撒一遍,悶悶就開飯。”我把手擦了才去抓的面粉,標準量度就是九歲時我的手,一把正好,均勻地撒上去。
香氣里還加了面粉的味兒,讓人想起軟乎乎剛出鍋的大饅頭,到處是熟悉的麥香氣。
大概過了十分鐘——我吃西瓜的時間大概就用了十分鐘——爺爺就把鍋子整個搬起來走進中堂,看見吃得滿嘴瓜瓤的我,開始埋怨奶奶。
吃飯了還給她吃西瓜!
這啥啊爺爺?
爺爺沒理我。奶奶招呼我去擦手,一邊給我解釋,這是螞蚱菜餅子,蘸著白糖吃,以前那時候可是好東西。
一種比干澀剌嗓子的青草更舒緩扎實的口感,還有點粘牙。
我知道規矩,糖不能多蘸多吃,只能趁著他們不注意的時候用手托著一塊餅子捏成圓,再悄悄把糖裹進去,可惜上面一咬糖就從下面漏了一地,還沒蘸幾下,碗就被收走了。
盛糖用的邊角豁了口的小青碗,我再也沒見過它。
餃子煮好了,一群人浩浩蕩蕩左手拿右手提著去上墳,村里人好像都是踩著這個點去的,還沒靠近村北頭就聽見噼里啪啦一陣響,尖尖的青柏下除了一個個隆起來的土包子還夾雜著很多桿兒似的生面孔,都是回來過年的。
大爺很快找到了一個墳,用鏟子往上掘了兩抔土,又在墓碑前畫一個圓圈,金銀元寶全都撒進去,忙活了半天的雞鴨魚肉也盛在黃屜子里擺在一邊,爸跟三叔站在兩側,等大爺跪叩說可以之后,三叔麻溜兒地從黑包拎出一串長鞭,臉上笑得很得意,說今年買的鞭好,長、沒空響。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面兒。
等鞭噼里啪啦唱完獨角戲,各路祖宗也接到了一年一度回家的邀請,比來時更龐大的一群影子在黃昏的背景中原路返回。
我在最邊緣走著,大爺他們開始討論起了晚上的年夜飯,豬凍和茅萵(雞的一種做法)必須得有,這可是一年的盼頭。趁著他們說話我頻頻回頭看,土包子漸漸消失了,轉過路口青柏也被北墻擋住了,一座座住著不同人的平房慢慢向后退,然后是寬廣的柏油路,是赤橙黃綠的人不斷交疊,是幼兒和老人,是一張張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和一聲聲到嘴邊又不知道該喊哪個的稱呼。
也許奶奶還記得。
我跟他們一起回家了。
作者簡介:林璐曉(1996—),女,漢族,山東壽光人,西北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碩士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