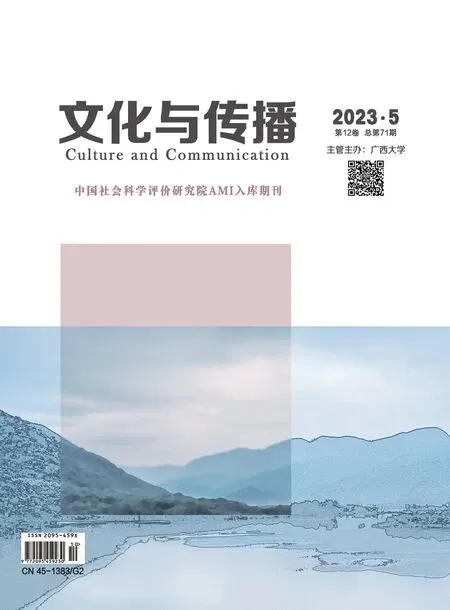戲劇經典的再現:“恐惑”視域下孟京輝改編話劇《等待戈多》研究
李永琪,楊俊婷
作為荒誕派戲劇的奠基之作,愛爾蘭作家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 年)的《等待戈多》(EnattendantGodot)表現了二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大眾普遍存在的惶恐焦慮、空虛絕望的精神狀態。該劇被認為是世界戲劇史上真正的革新,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力,并在全世界掀起一股“戈多”浪潮。原作法語版于1952 年發表,1953 年在巴黎的巴比倫劇院首演。隨后,它的英語版、德語版相繼上演。從《等待戈多》的創作背景來看,貝克特當時正身處法國二戰后新舊思想與理論急劇交替之際,在這場新舊之爭中,他嘗試“以詩意的手法、戲劇的形式來解構世界,表現處于潛勢的新價值”。[1]54劇中,貝克特對傳統戲劇語言的摒棄、對時間和空間的模糊處理以及對人物對話的不合邏輯、矛盾怪異的設置均具有解構意味。顯然,《等待戈多》“是一部創新與實驗戲劇,脫離了自然主義戲劇的傳統”。[2]
作為荒誕派戲劇的經典之作,《等待戈多》對中國戲劇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國內劇作家紛紛對其進行改編,將中國版的《等待戈多》搬上舞臺,如高行健的《車站》、孟京輝的《等待戈多》、任鳴的女性版《等待戈多》、林兆華的《三姊妹·等待戈多》等。其中,作為國內先鋒戲劇的倡導者,孟京輝利用大膽創新的舞臺設計向傳統僵化的戲劇模式發起挑戰。1991 年,由孟京輝改編的話劇《等待戈多》在中央戲劇學院上演,標志其導演藝術風格的成型乃至成熟。[3]正如孟京輝所說:“《等待戈多》點明了人類所處的最無可奈何也是最真實的狀態。同樣,這次演出也體現了創作者個人和集體最真切的渴望和最內心的躁動。”[4]7孟京輝在劇中展現了令人回味的奇思妙想:近乎純白的戲劇空間,白色柳樹懸掛在天花板之上,白色自行車倒置在舞臺中部,窗戶玻璃猛地被擊碎……他在臺詞方面基本忠于原著,但在舞臺布景、角色定位以及情節設計方面進行了別出心裁的改編,展現了該話劇的“恐惑”①國內關于“the uncanny/unheimlich”的中文翻譯有多種不同的譯法,主要包括“恐惑”“暗恐”等。文章采用“恐惑”這一翻譯,以凸顯孟版《等待戈多》給觀眾帶來的“恐懼”和“困惑”之感。特征,凸顯了人物的心靈創傷,使經典戲劇體現了改編者匠心獨運的藝術探索與創新。鑒于此,本文擬從舞臺布景、角色安排和情節設計三方面來分析孟版《等待戈多》中的“恐惑”特質及其所表達出的創傷主題,從而展現孟京輝高超的創作藝術。
一、舞臺布景:增加恐惑的氛圍
先鋒戲劇始于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的歐洲現代主義學派,一直以來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獨特產物。這使得中國的先鋒戲劇常被誤讀為是對西方先鋒戲劇的模仿。實際上,與西方迥異的演出場地、演員以及獨具特色的本土文化注定了中國的先鋒戲劇有其自身的特征。孟京輝執導的《等待戈多》便凸顯了這一特色,劇中另類的舞臺設計便是他對中國先鋒戲劇探索的絕佳例證,這也成為該劇的一大特色。
“恐惑”的概念出自1919 年弗洛伊德的《恐惑》(DasUnheimliche)一文,這是他闡發的一個跟創傷有關的心理分析學概念。它是一種“壓抑的復現”,即“有些突如其來的驚恐經驗無以名狀、突兀陌生,但無名并非無由,當下的驚恐可追溯到心理歷程史上的某個源頭”。[5]106這種恐懼、焦慮的感覺因人們回憶起以前經歷過的熟悉的、可怕的事件或情境而產生。“恐惑”的對象往往不是新的事物,而是腦海中早已存在的事物,它們經過壓抑的重復異化出來。[6]526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人類的家園、生活和世界秩序,人們在其中體會到戰爭的無情殘酷,戰后內心焦慮壓抑,戰火的陰影久久纏繞在他們的心頭,歷史的創傷記憶揮之不去,很多人不時受到“恐惑”情緒襲擊,難以適應現實生活,對世界的前途和個人的命運感到悲觀絕望。在此背景之下,貝克特創作了《等待戈多》,展現了備受“恐惑”困擾的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危機。他將戲劇的舞臺空間構建在鄉間的一條小土路上,第一幕空曠灰暗的舞臺空間中,小路旁僅有一棵光禿禿的小樹,象征戰后滿目瘡痍的荒蕪景象,給人一種空落落的、惶恐不安的感覺。第二幕小樹長出了幾片葉子,貝克特并未指明光禿禿的小樹長出葉子用了多久時間,這使得狄狄和戈戈等待的時間極具模糊性,增強了戲劇的荒誕感。孟版的《等待戈多》的舞臺設計正和戰后人們壓抑、悲觀的精神狀態相呼應,反映了戰爭的精神創傷使人們內心變得恐懼不安。不同于原劇的室外背景,孟版的話劇將故事發生的地點改為室內。在中央戲劇學院的一個大教室中,孟京輝創造了一個另類的舞臺空間:舞臺兩邊高大、緊閉的窗戶,舞臺上一架黑色三角鋼琴和一輛倒置的自行車孤獨地立著,一棵樹倒掛在天花板的吊扇上。這些舞臺道具及其擺放顯然與通常的房間布置不同,給人一種陰暗壓抑、怪異可怖的感覺,也使得整部劇的荒誕感陡增。正如孟京輝所言:“視覺上的可看性,爆發力和刺激的節奏方式,怪誕的超現實色彩和詩化的技巧是這次演出最明顯的特點。”[4]6這一另類的舞臺設計突出了人物生活環境的荒誕滑稽,它銘刻著人物對過去的歷史記憶,營造出壓抑、不安、恐懼的“恐惑”效果,凸顯了戰爭給世界造成了混亂無序的局面,給人們生活帶來毀滅性的破壞和難以治愈的創傷。該劇的“恐惑”特質是一種負面美學,弗洛伊德認為負面美學“并非以前曾被簡單斥為墮落、消極、反動的資產階級美學傾向。恰恰相反,負面美學所強烈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代表的是一種積極的反思能力”。[5]111無論是貝克特的原作,還是孟京輝的改編,都有著積極的教育意義,它們讓人們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所引發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損害和創傷,啟發人們不斷反思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問題。孟京輝通過更改原劇舞臺空間的布景來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促使觀眾更加積極主動地反思戰爭的危害性。
“恐惑”的內涵既是“家的感覺、熟悉、友好,等等”,也是“隱秘的、看不見的、無法得知的”。[6]516孟版《等待戈多》中,緊閉的窗戶暗示敘事空間的隱蔽,它里面的情況對外人來說是秘密的,而里面的人對外界發生的事情也一無所知,或者說外界由于人物自己的故意回避,成了“自己似知非知的秘密”,[5]109這樣的封閉空間營造出一種壓抑且無處安放的“恐惑”氛圍。這樣的舞臺設計使得觀眾無法確切感知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近乎于缺失的模糊的時空要素對作品意義的建構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時間與空間并非戲劇語言,但它是一種延伸的戲劇語言”。[7]154相比原作室外的場景,室內這一封閉的空間更容易使人產生焦慮恐懼之感。孟京輝通過改變舞臺的設計更加直觀地揭示了戰爭對人造成的心理創傷的延展性。原作第一幕借助光禿禿的小樹,展現了二戰后滿目瘡痍、毫無希望、人們飽受迷茫焦慮的桎梏之苦的荒蕪景象。然而,第二幕中小樹長出了幾片綠葉,狄狄和戈戈在樹旁繼續等待戈多,此時的舞臺呈現的并不只有等待,還有荒誕之下如新葉般的初萌的希望。孟京輝的舞臺設計也為該劇注入了希望的元素。舞臺正中間除了鋼琴、自行車等這些毫無生機的擺放物,還掛著繪有波提切利的名畫《春》的局部的簾布。過去的壓抑、創傷表現為焦慮等負面情緒,窗簾作為單調、壓抑空間中的一抹亮色,顯然成了舞臺上釋放壓抑情緒的唯一出口。此外,窗簾是“該劇最初給予觀眾的唯一可稱之為邊界的空間布置”,[8]81簾布后方有一扇門,連接著前臺和后臺兩個空間,話劇演員由此進出。通過這樣的舞臺設計,孟京輝開啟他對《等待戈多》的新闡釋。前臺和后臺的并存既是敘事空間和真實世界兩個空間的并置,又是家與非家、熟悉和不熟悉的并存。當演員穿過簾布走到舞臺前,他們是人為構建的、不熟悉的話劇空間中的角色;而回到舞臺后臺,他們是真實的、熟悉的世界中的自己。在人為構建出的不熟悉的空間中,任何不符合現實常理的事物都可以出現。這就解釋了為何舞臺上會出現倒掛的樹以及倒放的自行車。此外,樹的意象在原作中頻繁出現,已經成為《等待戈多》的重要標志之一,它的意義不只是為等待這個行為提供背景,也是能夠推動劇情發展的重要元素。孟版《等待戈多》在保留原作極簡主義色彩的同時,也進行了具有中國先鋒戲劇特色的創新。樹是為人所熟悉的,可是其存在的狀態(姿態),即倒掛在轉動的吊扇上則顯得異常。原作第二幕中長著幾片葉子的小樹與孟版倒掛在吊扇下的樹都模糊了戲劇的時間,觀眾無法從樹葉的長出和樹周而復始的單調旋轉中去判斷時間。此外,孟京輝一方面給倒置的樹賦予動態之美,另一方面這一另類怪異的安排也增加了“恐惑”的氣氛。
孟京輝在舞臺燈光及背景音樂上的改編也賦予該劇極大的美學價值,展現了孟版《等待戈多》強大的藝術表現力。第一幕結束后,舞臺上僅留有一束燈光直直地打在倒掛在轉動吊扇上的樹,光影投射在樹后的白墻上,白樹黑影,一黑一白,一大一小,一動一靜,給觀眾帶來了視覺沖擊。在背景音樂方面,孟京輝選擇以笛子演奏的純音樂《光明大道》作為幕間曲。正如這首歌曲的名字“光明大道”,其歌詞也表達了積極的意義:“沒人知道我們去哪兒/你要寂寞就來參加……我們穿著新棉襖/天空樹木和沙洲/挺起了胸膛向前走/嘿嘿嘿別害臊/前面是光明的大道。”①引自張楚作詞作曲的歌曲《光明大道》。這首歌曲本身所傳達的內涵是,盡管未來的生活是個未知數,盡管并非每個人都能夠大有作為,但人們不能就此消沉,而是應該勇敢、積極地面對眼前的世界,如此迎來的必然是光明的大道。這處幕間設計利用光影以及伴奏,既在視覺上營造出陌生怪異的“恐惑”氛圍,又從聽覺上表現積極的一面。兩種元素的相互較量自然能夠引起觀眾對該劇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作為導演,孟京輝顯然希望有過內心創傷的人們能夠走出陰霾,迎接光明的未來。總的來說,這一舞臺設計既能傳達導演之心境,又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在強化劇場現場感的同時,還提高了話劇的審美價值,拓寬了中國先鋒戲劇對舞臺設計的探索。
二、角色安排:凸顯人物的內心創傷
除了舞臺設計,戲劇人物也在戲劇表演中占據重要位置,可謂是戲劇表演的靈魂。因此,導演們往往借助人物來推動戲劇情節的發展,傳達戲劇表演所蘊含的精神內核和主旨內涵。與貝克特原作相比,孟版《等待戈多》中最突出的特點便是對戲劇人物進行了增補替換。孟京輝不僅在改編版本中添加了角色“那人”,而且以兩位女護士替換了原作中的小男孩,即戈多的信使。此外,角色的服裝和臺詞也做了一定的改動。他在人物塑造上的改編目的是為了凸顯劇中人物壓抑的“恐惑”情緒,呈現他們的創傷心理。
原作中的狄狄和戈戈雖為流浪漢,但出場時卻穿戴整齊。兩人頭戴帽子,身著西裝,腳穿靴子,看起來和常人無異。貝克特對兩人的帽子和靴子給予特別關注。顯然,帽子和靴子是人物塑造的重要符號。帽子戴在頭上可被看作是思想的象征,而靴子穿在腳上則可被看作是行動力的象征。劇中一幕是狄狄脫下帽子,往里邊看了看,伸手進去摸,然后把帽子抖了抖,吹了吹,重新戴上。幸運兒戴上帽子就開始演講,但是演講內容不僅冗長,而且毫無關聯和邏輯,令人疑惑不解。貝克特此處的人物塑造明顯是為了突出人物的精神出現了問題。另外,象征行動力的靴子也因不合腳而被戈戈脫掉了。一個精神出了問題又缺乏行動力的人顯然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只能生活在壓抑絕望的環境中。比較之下,孟版《等待戈多》中狄狄和戈戈的裝扮與原劇大相徑庭。兩人穿著隨意,上身僅穿西裝外套,前胸和腹部徑直裸露在觀眾面前,下身穿著西褲,腳上穿著靴子,給人一種不協調、怪異的感覺。外表的不協調是內在的精神世界失衡的表征,而精神的失衡正是戰爭所造成的創傷。與原劇不同的是,孟京輝并未讓人物戴上帽子,而是選擇用雨傘代替。此處加入的雨傘道具促使觀眾想起世界著名的幽默大師查理·卓別林(1889—1977 年)。因此,有學者認為,孟京輝用雨傘代替原作中經典的帽子“角色”,是“將‘悲中之喜’的承載者賦予了貝克特的先輩——卓別林”。[8]154這處改動顯然是孟京輝導演對中國先鋒戲劇的又一實驗。通過將帽子改為雨傘,孟京輝不僅向卓別林表達了敬意,同時也以卓別林式的幽默諷刺方式凸顯了戲劇人物生活的荒誕:雨傘在屋內并無作用,而撐開的傘必然會遮擋光線,使狄狄和戈戈原本的等待顯得更為漫長,也更容易使人物產生壓抑、焦慮的情緒,從而增加該劇的“恐惑”氛圍。另外,在屋內使用雨傘體現了人物行動的錯位,歸根到底還是內心創傷在人物乖張荒誕行為上的外化。
此外,孟京輝添加了角色“那人”。作為身份不明的角色,“那人”在第二幕的突然出現不僅使狄狄和戈戈極感不安,也使觀眾感到困惑。直至話劇結束,孟京輝都并未對“那人”的身份作具體的說明,觀眾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那人”會是狄狄、戈戈一直等待的戈多嗎?至少在兩人看來,“那人”不是戈多,因為“那人”的出現顯然對狄狄和戈戈造成了威脅。第二幕中,兩人身上多了原作中不存在的領帶,但奇怪的是領帶并非系在他們的脖子上,而是蒙在他們的眼睛上,暗示了人物不愿直面現實,只愿意沉浸在自欺欺人的對未來的幻想中。隨著劇情的推進,狄狄和戈戈竟然用領帶將最后登場的“那人”活活勒死。這一行為不僅令觀眾瞠目結舌,而且引導了觀眾對其背后的原因進行思考。結合該劇創作的戰爭背景,觀眾不難猜出將“那人”勒死這一行為表現了狄狄和戈戈對外部世界任何不確定因素的排斥與拒絕,戰爭留下的創傷使他們無法忍受陌生事物的侵入。弗洛伊德通過分析霍夫曼的作品《沙人》說明恐惑感與“復影”(double)有關,即某些忘記或壓抑的事情卻在無意識間在某些情境下以其他的形式再現。[6]523“那人”就是一種復影的形象,他在房間內的突然出現無疑觸發了深藏于狄狄和戈戈內心的“恐惑”情緒,使兩人把當下不熟悉的情感和事物與過去的熟悉經歷聯系起來,從而突出了該劇的創傷主題。
最后,孟版的《等待戈多》以兩位護士替換了原劇中的小男孩這一角色。作為戈多的信使,小男孩的角色具有推動戲劇發展的作用,因此受到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有學者認為劇中的小男孩是能夠“給人們帶來希望的使者,是潛在的創造者”,[9]92也有學者認為小男孩的存在狀態是對“得救說”的嘲諷,體現加繆哲學的超越精神,是荒誕派戲劇與存在主義相通之處。[10]80實際上,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陰霾之下的貝克特時刻關注著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持久性的精神創傷,他深知戰爭的創傷必然會留下難以去除的消極影響,受到創傷的個體無法輕易地掙脫創傷的困擾。因此,他選擇用戲劇的方式進行創傷敘事,以達到幫助受到創傷的個體走出創傷陰影的目的。《等待戈多》雖以碎片化的敘事結構來表現這世界的荒誕與虛無,但小男孩的存在暗示著滿目瘡痍和一片狼藉之下希望猶存。孟京輝設計兩位穿著護士服裝的雙胞胎女演員來替代貝克特原作中的小男孩,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護士的人物形象是一種矛盾的結合,一方面,護士的出場意味著疾病和創傷的存在。她們也是一種“復影”的形象。弗洛伊德認為文學中互為“復影”的兩者往往有諸多共同點,能產生心靈感應,他們有“共同的知識、情感和經歷,他們相互產生身份認同,所以對自我產生懷疑,或者將外來的自我代替真正的自我”。[6]522孟京輝以這兩位雙胞胎女護士塑造了能產生心靈感應的“復影”形象,她們動作僵硬統一,木訥呆板,像是會說話的提線木偶,僵硬地重復著同樣的話,“不認識,先生”“不是,先生”“是的,先生”“沒有,先生”[11],①本文所引人物臺詞均根據視頻資料聽寫整理而成。她們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該劇的“恐惑”氛圍。另一方面,護士的形象也暗示了治病療傷的可能。與小男孩相比,成年女性顯然對事物具有著更為成熟的應對方法。面對病人時,女性身上所具有的女性氣質會拉近與病人之間的距離,從而使得病人的情緒更加穩定。劇中,雖然女護士的出現并未解決狄狄和戈戈眼前的問題,但作為醫護工作者,護士可以給予平復受創者心靈的撫慰,也可以治療困擾受創者許久未愈的創傷,從而幫助他們激發樂觀面對生活的熱情,增強他們努力追尋自身意義的信心。因此,兩位女性角色也是希望的象征。可以看出,孟京輝通過戲劇人物設計所渲染出的“恐惑”情緒雖是一種負面美學,卻有著積極的意義,他在展現人物創傷心理的同時,也在探討療傷的可能性,讓人們在悲觀情緒困擾中看到一些希望。
三、情節設計:突出戲劇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荒誕派戲劇區別于傳統戲劇的重要特征之一,而“恐惑”理論對熟悉與不熟悉、家與非家的困惑惶恐心理的闡釋突出了這種心理狀態的不確定性特征。如郭雯指出,“恐惑”的概念“如今它已不只局限于心理學,而是被運用于文學、藝術、建筑、文化等其他領域,是日常生活的普遍現象,它不僅能讓人對似曾相識的人和事產生恐怖感,更重要的是似是而非、令人困惑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12]所以荒誕派戲劇由于不確定性的特質,其本身也滲透著“恐惑”的藝術韻味。
《等待戈多》中的人物身份、人物語言、戲劇主題、結構、場景、情節和時間,都具有不確定性的特點。冉東平認為:“貝克特的靜止戲劇用直喻的、心靈外化的手法來表達荒誕的主題,戲劇表現出來的不確定性和朦朧性的特點,使觀眾在觀看戲劇時只能根據戲劇提供給自己的暗示性語言和動作來認識戲劇所發生的一切。”[13]66就劇中“等待”這一情節來說,戈多是誰,他是否會來,狄狄和戈戈為什么要等待戈多,他們已經等了多久,他們是否會繼續等下去,這些問題都無從得知,甚至連劇中人物對此也未必比觀眾知道得多。正因為“等待”的不確定性,戲劇才留給觀眾無窮的闡釋空間,也正因為對未知事物的不確定,才讓人產生一種難以解釋、不知緣由的“恐惑”情緒。由于對未來的不確定,狄狄和戈戈對外面的世界產生抗拒心理,不敢輕易邁出行動的第一步。他們代表了戰后仍無法走出戰爭陰影、對社會現實不滿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底層人物,他們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只能痛苦地、無奈地在漫無目的的等待和幻想中尋找慰藉。20 世紀70 年代“恐惑”概念被理論化后,它就常與“異化”的概念聯系在一起,被用來分析“在高度物化的世界里人的孤獨感與被遺棄感、人與人之間感情上的冷漠疏遠與隔絕以及人在社會上孤立無依、失去歸宿”。[14]134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狄狄和戈戈也象征了徘徊于現實和幻想之間、處于迷失狀態的、孤立無助的現代人。與原劇相比,孟版的《等待戈多》在情節上也做了一定的改編。孟京輝主要通過加入鬧鐘鈴聲以及砸破窗戶的情節,改編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具有中國先鋒戲劇特點的方式來增加該劇的“恐惑”氛圍,展現在幻想和現實之間搖擺不定的人物形象,突出該劇的不確定性和人物經歷過戰爭創傷和西方現代社會異化后精神上的迷惘焦灼。
原劇中,狄狄和戈戈涉及記憶問題的對話體現了他們混淆了虛幻和現實,成為戲劇不確定性的表征之一。孟京輝在保留原作這些對話的同時,也對其進行了別出心裁的改編設計——在對話結束后加入了鬧鐘鈴聲,更加突出了虛幻與現實的問題。《等待戈多》中的人物行為具有“壓抑的復現”這一“恐惑”特點。心理分析學采用的時間策略和歷史學不同。在歷史學中,過去和現在是截然不同的分割,而心理分析學“通過個人的負面情緒把過去和現在連在一起”,人們無意識間將過去和現在混同的那個片刻稱為“轉移”(transference)現象。[5]112原劇中狄狄和戈戈經常混淆前天和今天發生的事情,而正是這一記憶的混亂引發了兩人話語的重復以及場景之間的重復,構成了該劇的荒誕特色。例如,以下狄狄(弗拉基米爾)和小男孩的對話便體現了人物記憶的混亂:
弗:我過去見過你,是不是?
孩:我不知道,先生。
弗:你不認識我?
孩:不認識,先生。
弗:昨天來的不是你?
孩:不是,先生。
弗:這是你第一次來?
孩:是的,先生。[15]
對于兩人的對話,梁超群認為這處只能理解為狄狄出現了記憶混亂的問題,因為男孩是整部劇中的配角,如果記憶力嚴重缺陷的是男孩,角色設置略顯無趣,故而只能理解是狄狄的記憶混亂。[16]34從韋恩·布斯關于“隱含的作者”與“敘述者”的區分來看,該劇雖沒有敘述者,但卻“隱含”一個“不可靠的劇作者”。[16]36在“不可靠的劇作者”的幫助下,原作者悄然退場,只留下一些信息給觀眾自己去解讀。此外,“不可靠的劇作者”的存在使得這個劇場空間所建構的世界存在一種隱性的解讀:這個建構的世界是矛盾的、不受控制的,其效果在于打破觀眾的“戲劇性諷示”(dramatic irony),模糊邊界感,破壞秩序感,使觀眾在感受戲劇的不確定性的同時,也積極思考人物經常出現記憶混亂的原因,即戰爭的荒誕導致他們對世界認知的混亂。從“恐惑”的視角來看,被壓抑的傷痛常以偷偷摸摸的、無意識的、不被人馬上辨認出來的方式復現。復現的形式和過去的情形不同,卻又相關聯。[5]112由于歷史的記憶永遠纏繞著狄狄,并以新的形態浮現在他的心頭,所以他常常把現在的事物當作以前的事物。他記憶的錯亂和往事不定時的復現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恐惑”的特征。
如果說臺詞和場景的重復意味著狄狄和戈戈不愿面對戰爭留下的創傷而終日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之中,他們在漫無目的的等待中消磨時間,懶于采取行動去面對現實,解決現實問題,那么,孟京輝改編的劇情則利用鬧鐘鈴聲打破了狄狄和戈戈的幻想。在孟版《等待戈多》的演出中,人物在說完“咱們在等待戈多”這句話后,舞臺上隨之傳來一陣響亮、刺耳的鬧鐘鈴聲。聽到鬧鐘鈴聲之后,狄狄和戈戈驚恐地立刻上前關掉鬧鐘。從劇中人物的表情和行動可以看出,他們對這突如其來的、破壞和諧的怪異聲響感到驚訝,甚至不安。顯然,鬧鐘鈴聲使他們從沉浸已久的等待和幻想中驚醒,回到不愿意面對的現實世界,而將鬧鐘鈴聲關掉則表明了他們對回歸現實的恐懼和抗拒。演出最后,當人物再次說完“我們在等待戈多”時,舞臺上沒有出現觀眾所預期的鬧鐘鈴聲,留下的僅僅是狄狄、戈戈以及觀眾的漫長等待,戲劇至此也戛然而止。結尾鬧鐘鈴聲的缺席似乎暗示了人物要走出幻想、付諸行動的艱難,他們又重新陷入等待中。盡管如此,通過添加鬧鐘鈴聲,孟京輝為狄狄和戈戈的生活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即直面現實,采取行動,走出內心的創傷,創造美好生活。
除了鬧鐘鈴聲,孟京輝還通過砸破窗戶這一情節來對原劇進行改編。在孟版《等待戈多》的結尾,狄狄猛地用他手中的黑傘砸破高大的玻璃窗。他一邊敲碎玻璃,一邊喃喃自語地說道:“我們已經守了約!我們已經盡了職責!我們生來就是瘋子!有些人始終就是瘋子,我們只能變成瘋子!”[11]這一行為可被看作是一種壓抑許久的負面情緒的釋放,這種情緒隨著聲聲清脆的玻璃破裂聲得以發泄。劇中的狄狄和戈戈一直處于被動的等待狀態,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等待,也不知道還要等多久,更不知道戈多是什么或者戈多是誰。他們甚至不確定他們所處的世界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這一系列問題都沒有準確的答案。“戈戈和狄狄等待的戈多就來自簾布后的世界,這個世界能否實現他們等待的愿望在數輪打擊后似乎已不被期望。”[8]82他們內心長期的抑郁情緒最終化為打破玻璃這一“暴力”的行動。砸破窗戶釋放了兩人的負面情緒,是一種“壓抑的復現”,增加了戲劇的“恐惑”氛圍;同時,禁閉的室內空間象征一個與外界隔離的自我世界和生活幻影,砸破窗戶就是打破室內(或者說自我)與外界的隔閡,使人物走出幻想,直面生活現實。
砸破窗戶只是戈戈和狄狄從幻想中走向現實的第一步,外面等待著他們的將是什么,他們將何去何從,這些依然是個謎。而砸破窗戶后劇情的發展并沒有清晰地呈現人物的最終走向,反而留下撲朔迷離的結局任由觀眾猜測。“那人”的登場使話劇走向了新的高潮。作為“身份不明”的角色,“那人”的出現是讓狄狄和戈戈感到不安的因素。他們長期宅居室內,本就已經產生一種與外界交際的恐懼癥。面對這個突然的闖入者,他們令人意外地、發瘋似地用領帶將其勒死,意味著他們對不確定因素的抗拒。對弗洛伊德而言,無意識始終是活躍的存在,“壓抑的復現”正是無意識的證明。“恐懼不安因素一旦出現過,就會形成心理歷史;恐懼不安存在于個人,也存在于文化。”[5]111也就是說,“恐惑”成了一種個人的或集體的無意識,心靈創傷一旦形成,則難以愈合,會茫然不知地重復上演。由于“那人”勾起了戈戈和狄狄對過去創傷事件的回憶,所以他們對其出現才產生了極大的恐懼心理和過激的反應。克里斯蒂娃在《陌生的自我》中指出:“恐惑在想象和現實的邊界消失的時候產生。”[17]“那人”正好出現在戈戈和狄狄兩人剛剛砸破窗戶、打破幻想和現實的界限的時刻,雖然對接觸外界、直面現實已經躍躍欲試,但其實他們還沒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過去的創傷如同幽靈一般,伴隨著“那人”在他們無意識間又飄然而至,“他們只能頹然地走向門框切割出的光區之中并停留于此,面對現實的進與退成為一個無解的懸念。”[8]82歷史創傷的記憶使他們在即將走向現實的時刻,又畏懼地退縮回來。“那人”的死與狄狄上臺時拿著的一個插著點燃的蠟燭的生日蛋糕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一片黑暗之中,蛋糕上的燭火微微閃爍,而臺前倒著一具尸體。顯然,生日蛋糕意味著生命,象征了戈戈和狄狄企圖走出過去創傷的陰影,開始新生活,而尸體則意味著死亡,生與死雜糅共存于同一畫面,人物生活的世界又似乎重新陷入荒誕之中。他們最終是成功回到現實,還是繼續待在屋內等待,觀眾依然無法從結局得到答案。盡管戲劇沒有讓觀眾看到人物成功走出幻想、直面現實的結局,但孟京輝已經讓觀眾看到他們企圖擺脫歷史創傷記憶的努力嘗試,表達了改編者對經歷過創傷的人們的關懷,以及試圖通過藝術的形式引導觀眾進行積極的反思,進而為人們的生活提供指導,達到文學治愈人心的效果。
結 語
作為荒誕派經典戲劇的改編劇,孟版的《等待戈多》“無疑是中央戲劇學院創作集體共同合作最成功的演出。”[4]6該劇是中國先鋒派戲劇實踐者孟京輝導演經過深思熟慮的設計和不斷求新而創造的產物,更是他作為20 世紀90 年代新一代中國戲劇創作者敢于實驗、勇于顛覆傳統的有力證明。通過對經典戲劇的再思考,孟京輝以創新的藝術姿態闡明了中國先鋒戲劇的真正意義,體現了其精湛的戲劇創作藝術。《等待戈多》原作具有“恐惑”的特征,孟京輝的改編不但契合這種特征,而且對其起到強化的效果。通過另類的舞臺設計、戲劇人物的增補替換以及大膽的情節設計,孟京輝不僅為觀眾提供了一場頗具“恐惑”氛圍的視覺盛宴,展現了經歷戰爭創傷的人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更為那些曾遭受心靈創傷的人們給予精神安慰。負面美學雖然以消極的面目出現,但卻具有積極的教育和啟發意義。無論是原作還是孟版的《等待戈多》,其藝術呈現都發人深省,其批判的矛頭都直指西方戰爭和社會荒誕的根源,即資本主義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