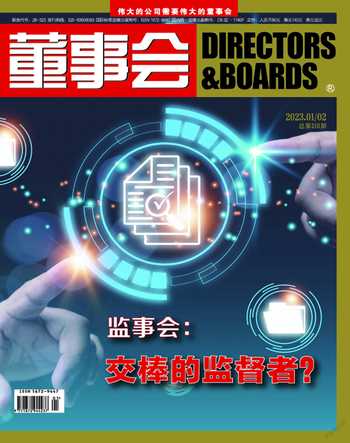產出的驅動力:大公司還是小企業?
張曉萌 曹理達
一個經濟體中大企業占的就業比例越大,它就越富有。未來,充滿活力、資本密集的科技企業,趨于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大,而提高生產率的最好辦法就是消除阻礙,用這樣的企業取代規模較小、勞動力密集、技術停滯不前的夫妻雜貨店。但這樣做就需要戳破“小企業好”的神話,同時努力恢復大企業是進步和繁榮引擎的聲譽
一個神奇的數據
如果我們告訴你,知道了一個國家的一項統計數據,就可以知道它的人均收入處在全球排名的頂端、底部還是中間,還可以相當準確地推測這個國家的總體經濟狀況,甚至知道它可能位于世界的哪個地區,你相信嗎?
的確有這樣一個窺一斑而見全豹的統計數字,它就是自雇者人口的百分比。一個國家越窮,人口中的自雇者就越多。2016年,6.4%的美國人是自雇者。在布隆迪,自雇者或在家族企業工作的人占到了89.9%。2016年,布隆迪的人均年收入(購買力平價)為800美元,而美國為57300美元。
通常,最富有的地區是自雇職業最少的地區,而最貧窮的地區是自雇居民最多的地區。自雇者占北美勞動力的7%,歐盟的1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22%,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6%,以及東南亞的41%。原因很簡單:通常企業越小,生產率水平越低。
還有另一個有趣的技巧。如果我們知道一個國家自雇者的百分比,我們也可以準確地推測該國出口的是什么類型的商品。自雇者水平低的國家出口的主要是高附加值制成品,而自雇者數量多的國家出口的則主要是低附加值產品,如原材料、農產品和旅游等服務。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最貧窮的國家是馬拉維、布隆迪、中非共和國和尼日爾,其出口產品包括煙草、鈾和釷礦石、茶葉、糖、咖啡、棉花、香料和寶石等。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美國、日本和德國這三個最大的先進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出口產品:機械、電子設備、飛機、航天器、車輛、醫療設備、鋼鐵、有機化學品、發動機和藥品。富國主要出口高附加值的制成品。窮國主要出口低附加值的商品,其中大部分是用原始的勞動密集型方法,而不是現代機械收獲或手工制造的。
小企業比例與收入不平等之間也存在正相關的關系。戴維斯的一項研究發現,在53個樣本國中,收入最平等的國家是丹麥,大約四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其最大的10家公司。相比之下,在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哥倫比亞,最大的企業雇傭的工人不到1%。總體而言,各國的收入不平等與在大企業就業的工人比例之間存在負相關(-0.47)。
新的初創企業情況如何呢?根據世界經濟論壇一份調查初創企業數量占全部企業比例的報告,烏干達排名第一,泰國第二,巴西第三,喀麥隆第四。這些國家幾乎不是經濟強國。
自雇率、人均收入、出口構成、收入不平等和初創企業比率,怎么解釋這五個看似不相關的因素之間存在的顯著相關性?答案在于大企業,更確切地說,是追求規模報酬遞增的行業中的大中型企業。不發達的窮國由小農場主、小作坊和小販主導,往往在非正式的經濟部門;而在北美、歐洲和東亞的先進技術國家,大企業在為不成比例的產出和就業盡責。
為什么是大企業?
用加爾布雷思的話說,現代經濟是一種“雙峰經濟”,分為規模收益不變或遞減行業以及規模收益遞增行業兩類。在規模收益不變或遞減行業,額外增加一產品或服務的生產成本與前一個產品或服務相同(如按摩);在規模收益遞增行業,由于技術的原因,生產第一萬個單位的平均成本低于第一個產品的成本(如汽車)。在軟件等數字行業,第二個單位產品比第一個單位產品便宜得多,因為第二個單位可以大量地免費生產(電腦復制)。收益遞增行業往往屬于貿易行業,而收益不變或遞減行業往往屬于非貿易行業。
在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貿易行業規模很小,可以忽略不計,僅限于一些奢侈品,如香料和絲綢,這些奢侈品只被富紳消費。其他的一切(工具、衣服、食物等)都是在家里或附近制造或種植的。工業化是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越來越多之前由人力和畜力在當地生產的商品和服務,變成由機器(包括計算機)使用能源生產,而不再使用人力或畜力,其中許多商品和服務被從非貿易行業轉到貿易行業(無論它們實際上是否銷往國外,理論上都是可以出口的)。由于在收益遞增行業中效率最高的公司通常規模較大,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自雇者和夫妻雜貨店的數量在下降,貿易業尤其明顯,而為大中型企業工作的工薪階層人數在增加。公共部門的就業亦是如此,因為經濟的日益繁榮使得不用費多大勁就可以增加稅收,擴大政府的職能。
隨著更高效的大企業獲得市場份額,它們為員工提供了更好的機會。這就是富裕國家的自雇者也相對較少的原因。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很多人的收入也在增加,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次優的“創業者”轉向為工資而工作。這也解釋了自歐洲和美國的經濟衰退以來,臨時工或零工在近期有所增加的原因。對零工經濟增長的關注,大部分集中在新的網絡平臺上,如優步和Task?Rabbit,但是更多的工人在用接活的APP而成為自雇者,可能正是因為其他更高質量的就業機會不足。
隨著國家的工業化,以及勞動力和資源從傳統的小企業轉向創新型的大企業,國家正是因為大企業的增長而更加富裕,并非受制于大企業的增長。信息技術革命正在使更廣泛的服務業也成為規模收益遞增的產業和貿易行業。比如隨著“金融科技”和電子銀行的出現,銀行業務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跨境辦理,網絡銀行業也變得像制造業一樣規模收益遞增,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在許多行業可以看到這種信息技術的轉型,包括新聞、保險、旅游服務、零售、法律和其他一些行業,其中技術正在支持規模收益遞增,并使它們跟大多數制造業一樣具有可貿易性。
企業規模在不同國家的變化
美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格局與歐洲和東亞其他先進工業國家非常相似,其特點是技術創新與更大企業規模的共同演進。技術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公司的規模,而這些工具在全球隨處可見。
鑒于技術的發展趨勢,人們可能會認為其他發達國家像美國一樣實際上也會看到企業規模的擴大。然而,盡管美國的企業規模一直在增加,但一些地區的企業規模卻一直在縮小。在歐洲,公司的平均規模從2005年的平均每家公司7人降至2013年的6.2人(見圖1)。葡萄牙則從1986年每家公司15.7人減少到2008年的9.1人,任何行業的企業規模都沒有增加,但自雇者的比例增加了10倍。同樣,中國小企業貢獻的就業比例從2004年的22%左右增至2009年的32%。
什么原因導致一個國家企業規模的變化?有兩個因素:生長效應和混合效應。
混合效應指各行業之間工作崗位組合的變化,增長效應指總體趨勢。幾乎在每個國家,制造企業都比非制造企業的規模大。因此,隨著就業向服務業的轉移,混合效應導致公司總體平均規模的減小。但增長效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信息技術使得一系列服務企業擴大規模。在企業規模日益縮小的國家,部分原因是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減少,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似乎與增長效應有關,即其他行業的平均企業規模也不是在擴大,甚至正在縮小。
為什么服務性企業在有些國家變小,而在美國變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可能是各國在努力消除原先的國有化行業的壟斷。另一種可能是政策明確有利于小企業,同時對大企業增加稅收和加強監管。如在韓國,大企業的產出份額從1970年的72%降至2006年的50%左右,而中小企業的就業比例從2000年的80%,升至21世紀10年代初的87%。韓國已經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明確要求其競爭主管機構為中小企業創造一個“競爭性的環境”,從而使得大企業更難發展。
小企業生產率普遍較低
對很多國家來說,這種企業規模的停滯甚至下降事關重大,因為大企業的平均生產率高于小企業。若要估計二者之間的這種差異,方法就是看它們在就業和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20世紀90年代初,在14個經合組織國家中,除西班牙外,小企業的就業份額都超過了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換言之,小企業工人的生產率較低。在英國,小企業占就業的三分之二,但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而大企業工人的生產率是1~9人小企業員工的兩倍多。芬蘭大企業(1000人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比小企業(15人以下)高出13%,如果控制行業類型的話。
巴特·范·阿克(Bart?van?Ark)和埃里克·蒙尼克霍夫(Erik?Monnikhof)的研究表明,在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大企業的生產率比小企業更高。在加拿大,員工人數在100人以下的工廠生產率為行業平均水平的62%,但在員工人數為500人或以上的工廠,生產率為行業平均水平的165%。即使在對其他特征(如外國控制、出口強度、工會化和企業年齡)加以控制后,這些差異仍然存在。事實上,從1980年至2000年,大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繼續增長,但中小企業要么停滯不前,要么下降。在總共18個歐洲國家中,250人或以上的企業,生產率比不足10人的企業高出80%。(見圖2)
發展中國家情況如何?畢竟,國際發展界的一個信念是:將小型甚至微型企業的數量成倍增加將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但世界銀行對76個國家的研究發現,沒有證據表明中小企業有利于經濟增長或減少貧困。另一項對10個非洲國家的研究發現,大小企業創造了同樣數量的凈就業機會,但大企業支付的工資卻持續走高。這是因為大企業的生產率比小企業更高。
亞洲的大企業也比小企業的生產率更高。與大企業相比,印度尼西亞小企業的生產率為19%,菲律賓為21%,韓國為22%,泰國為42%,馬來西亞為46%。我們在非洲看到了同樣的動態,那里的大企業比小企業生產率更高。
這就是為什么,推測經濟有多富有的方法,是看大企業員工所占比例。一個地區大企業的就業比例越大,它就越富有。這也是小企業就業比例較高的美國各州居民平均收入較低的原因。事實上,雇員少于20人的企業所占就業比例與該州人均收入之間為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27。例如,蒙大拿州的人均年收入僅為39800美元,小企業的就業比例超過31%。馬薩諸塞州的人均年收入為62900美元,小企業的就業崗位只占16%。
各國均呈現同樣的模式。一般來說,高收入國家的大企業就業比例要高得多。此外,小企業的增長似乎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不是正相關。如斯科特·沙恩發現,“除去國家之間不同的所有其他因素的影響,一年的新企業創建率,對一國下一年的實際人均GDP有消極影響”。此外,從2000年至2004年44個國家新企業創建率的數據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企業創建率遠高于發達國家。企業創建率較高是貧窮的標志,而不是富裕的象征,因為它們反映了那些成熟且能實現較高生產率的企業缺乏真正的經濟機會。
各國企業規模為何差異很大
為什么企業規模的分布在各國之間差異如此之大?一個因素是一個國家是否擁有大量平均規模較大的企業,如制造企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制造企業較多的國家往往企業平均規模較大。同樣,研發密集型產業往往規模較大,因此,在這種產業較多的國家(其他所有條件都相同),企業規模將大于平均水平。但這些因素在解釋國家間的差異方面似乎并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影響國家企業規模的因素似乎是人口規模和市場準入規模。人口越多,市場越大,更多的企業就能利用大規模生產技術實現規模經濟。事實上,在29個經合組織國家,人口規模與250人以上企業的就業份額之間呈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45;人口規模和少于51人的企業的就業份額之間呈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2。同樣,通過貿易協定和其他市場開放措施可以更好地進入外國市場,從而增大企業規模;改善運輸網絡和通信網絡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如果能夠改善物流運輸或基于寬帶網的信息傳輸,企業就能進入更多的市場,它們可能就會變得更大。
較高的人均收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高的收入不僅擴大了市場規模,而且使一個人更有可能愿意成為一個領工資的工人,而不是一個自求生存的企業家。很多研究發現了這種關系,如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E.Lucas,Jr.)研究發現美國企業平均規模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而馬庫斯·波施克(Markus?Poschke)的一份報告表明,富裕國家擁有更多的大企業和更少的小企業,也擁有相對較多的管理職位。簡而言之,隨著各國越來越富裕,其企業規模普遍增大。小企業在貧窮國家更為普遍,部分原因是窮國為所需的規模經濟提供的市場較小。因此,擁有大量小企業不應被視為成功的標志,決策者還應該再接再厲;相反,它應被視為不發達的跡象。一個國家自雇者人數眾多,意味著沒有足夠的全職工作,因此,許多人被迫通過為自己工作而獲得低收入。
文化也起一定的作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中指出:牢固的家庭關系不利于大企業的形成,因為它們使個人更難信任非家庭成員。很多研究發現:統計數字表明,給予非家庭成員較高信任度的國家,其大企業的經濟產出明顯占有較大的比重,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更高的信任度也讓管理者可以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將責任委托給個人,并更加確信他們會為企業的利益而采取行動。
監管和法律環境也發揮了作用。幾項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嚴格的國家擁有更大的企業。理由是:“有效的法律制度使管理層能夠利用有形資產以外的關鍵資源作為權力來源,從而導致大規模企業的建立。它還可以更好地保護外部投資者,并使得大企業獲得資金。”在次國家層級上也是如此,如擁有更有效法律制度的墨西哥的州擁有較大的企業,因為法律制度更有利的州降低了企業所有者面臨的風險,使得他們可以擴大投資。另外,金融市場比較發達的國家,那些所處行業更依賴外部融資的企業規模也就更大。
讓企業保持小規模的政策
有些國家企業規模較小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想要小企業,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向小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監管要求、稅收優惠和補貼。當政策獎小罰大時,其結果就是遍地小企業。
大多數國家的政府會讓小企業免除監管,或放松其要求。歐盟委員會的官方政策是按規模區分對待:“有利于中小企業的政策應該成為主流。為此,‘首先為小企業著想的原則應根植于從監管到公共服務的決策之中,不可取消。”在法國,很多法規要求僅適用于員工人數在50人或以上的企業。在葡萄牙,少于50人的公司可雇傭由公共資金補貼工資、并優先獲得培訓補貼的工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小企業的豁免力度甚至更大,如巴西的大多數勞動執法檢查都集中在正規的大企業,而不是非正規的小企業。
很多國家還通過進入壁壘、地區限制法規和商店規模的限制,來保護低效率小雜貨店。例如,在阿根廷,大企業被迫將食品“捐贈”給社區組織,并面臨價格控制和進口限制。由于擔心法國消費者會從亞馬遜網站購買太多的書籍,減少當地小書店的銷量,法國議會下院一致通過一項法案,禁止任何線上賣家將圖書打折,從而有效地迫使網上書商以高于實體店的價格出售。在日本,限制大型超市進入和鼓勵小型零售商持續營業的法律,說明了為什么日本存在那么高比例的生產率低下的家庭零售商。
大多數國家要求大企業繳納更高的稅收。在墨西哥,從1998年到2013年,銷售額低于200萬比索(約等于2008年的12.5萬美元)的公司,要統一繳納約2%的銷售稅,并免征工資稅和增值稅。超過200萬比索門檻的公司需要繳納15%的增值稅、38%的所得稅和35%的工資稅。在印度尼西亞,超過一定規模的公司需要繳納10%的增值稅。在韓國,小企業要繳納10%的企業所得稅,而大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率則為22%。
很多國家的特殊稅收優惠要么只適用于小企業,要么對小企業更為慷慨。在韓國,只有小企業才有資格享受工業設備或先進辦公設備支出的5%稅收抵免。英國提供新的企業免稅額,但只適用于小企業。在加拿大,小企業有資格獲得比大企業高出75%的研發信貸。中國最近又出臺了一輪針對小企業的特別減稅措施,其中包括對小企業的退稅計劃。
在大多數國家,小企業還受益于補貼貸款、直接撥款、政府服務費降低,以及政府合同的小企業補貼。韓國要求銀行向小企業放貸,導致債務過剩,2012年78%的銀行貸款流向了中小企業,而美國的這一比例為25%。此外,韓國政府還實施了1300個中小企業項目和涉及稅收、營銷和就業的47項扶持措施。
很多政府只是簡單地給小企業發放現金。雖然歐盟委員會嚴禁國家補助企業,卻把很多小企業排除在了限制之外。歐洲國家可以直接向小型的漁戶、農場主、煤礦公司、造船企業、鋼鐵公司和合成纖維公司伸出援手,但不能向大企業提供援助。歐盟委員會希望減少“對國內龍頭企業的救助,那會扭曲競爭,轉而支持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的措施。”這意味著他們想把錢交給小企業。這就是法國“創辦個人企業或小企業的人可申請的財政撥款和補貼有250多種”的原因。
許多國家支持小企業,因為它們不想經受失業造成的經濟混亂,也因為政策制定者不相信市場能創造就業機會。因此,從本質上講,它們使效率低下的小企業繼續效率低下。但這只會阻止生產率更高的公司獲得市場份額。由于整個社會對就業中斷極度厭惡,韓國政府延續了一系列限制企業倒閉的政策,2012年全球創新指數上將韓國列為解雇員工成本的第120位。該國政府推行一系列國內政策,以保護小企業免受競爭,如負責“為中小企業指定合適的產業”的“國家企業伙伴關系委員會”,曾規定中型餐館不能在收入低于4800萬韓元(合42800美元)的小餐館150米范圍內開設新店。
韓國的情況表明規模歧視如何限制了經濟增長。韓國中小企業的就業占87%,而美國僅為44.4%。中小企業享有慷慨的福利和監管豁免,意味著很少有企業愿意發展。2002年,在韓國數百萬家中小企業中,只有696家在2012年脫離了中小企業的身份。制造業中小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不到大企業的三分之一,服務業中小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為大企業的45%。政府對小企業的大規模偏袒降低了勞動生產率,低于工人在低、中、高生產率企業之間隨機分布時的水平。相比之下,在美國,實際分布比生產率較低的企業擁有同韓國一樣的市場份額時,可能有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了50%。
如果競賽場有偏向,那結果都是相似的,這在很多國家都能看到。在法國,員工在50人以上的公司比員工少于50人的公司面臨更多的監管。路易斯·加里卡諾(Luis?Garicano)的一項研究發現,這樣做的結果是:許多法國公司故意停留在50名工人的神奇門檻之下,導致法國國內生產總值下降多達5%,而工人承擔了大部分成本。導致這種低增長的一個相關原因是,通過降低工資,這些監管鼓勵“太多管理能力低下的代理人成為小企業主,而不是為生產率更高的企業家當雇員”。
這些政策不僅阻止效率更高的大企業獲得市場份額,還會抑制小企業向大企業增長,因為它們不愿意失去讓其輕松安逸的特殊待遇。如此,通過將產出從生產率較高的大企業轉移至生產率較低的小企業,損害了增長。因此,有研究發現將企業分支機構的平均規模減少20%的政策,致使總產出和平均每個機構的產出分別減少了8.1%和25.6%,而企業機構數量大幅增加,增加了23.5%。
這種小企業偏好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甚為廣泛,而且鑒于其人均收入已經很低,因此更具破壞性。研究發現,由于稅收政策差異,巴基斯坦、韓國、加納和塞拉利昂的大企業成本比小企業高出10%~26%,而因為勞動法規,加納、塞拉利昂、突尼斯和巴西的大企業成本要高20%~27%。這些扭曲的現象使得國內生產總值減少了6%~18%。謝長泰(Hsieh)和基諾(Kienow)發現,在印度和中國,小制造商的市場份額,比實現生產率最大化目標時應有的份額要大得多。他們認為:“生產率更高的公司難以成長。但在印度,生產率較低的公司反倒比在美國更容易生存。”
此外,在發展中國家,很多小企業不受監管,也不納稅。例如,在巴西,大多數用工檢查都集中在正規的大企業,而不是非正規的小企業。如世界銀行所寫,非正規的地位“賦予不合規的公司以不公平的優勢,從而扭曲了資源的分配”。墨西哥財政和公共信貸部長路易斯·維德加雷·卡索(Luis?Videgaray?Caso)寫道:“非正規勞動力降低了生產力,從而削弱了經濟增長。”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發現:“墨西哥生產率總體增長乏力的一個原因是,一半以上的非農業工人受雇于非正式部門;事實上,由于建立正規企業的監管成本很高,而且執法不嚴,非正式經濟正在增長。非正式經濟拖了經濟增長的后腿,而不是促進發展的力量。”
國際發展界采用的支持微型企業和非正式經濟活動等流行的做法,并不能解決問題。例如,歐盟委員會寫道:“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特別是微型、中小企業的擴張,是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也是創造就業的主要來源。”根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知識平臺鼓勵可持續增長的第8個目標,其中一個手段是“鼓勵微型、小型和中型企業的正規化和成長”。世界銀行“通過系統性和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促進中小企業的增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政策導致了與其意圖完全相反的結果:阻礙發展。這種對小企業的癡迷致使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增長放緩。
教訓再清楚不過了。如果目標是推動全球發展,特別是低收入國家的發展,應側重于保持企業規模的中立。以創造就業或社會包容的名義,支持、補貼或保護小企業,都是一些不明智的國家政策,它們不利于實現經濟發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長期目標。
正確的小企業政策
規模中立政策即是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借此取代在稅收、監管和其他政策領域對小企業的偏袒。
對于規模中立政策有兩種常見的反應。第一種反應認為,這將意味著小企業和就業的減少。我們的回應是,我們希望這意味著小企業的減少,因為大企業對經濟更有利。在就業方面,正如我們所表明的,小企業滿足的消費需求大企業也可以滿足,并在此過程中創造就業機會。我們不需要效率低下的小企業來創造就業機會。
第二種反應認為,規模中立政策會損害新興企業的利益,其中一些企業可能會發展為大企業。但是規模中立與企業存續期中立不同。如果說基于企業特性的政策差異化有理,那也應當以企業存續期為基礎。新企業起步可能很困難,很多企業撐不過5年就垮了。因此,政策應對新企業較為寬松。但不是說只要是新企業就側重,如有可能,要側重有能力且有雄心擴大規模成為大企業的新企業。換句話說,政府幫助蘋果電腦公司起步很有意義,而幫助賈斯汀和阿什莉開一家比薩店則毫無意義,它的規模也就是幾個員工,不會再大了。政策應支持“尋求機會”的創新型初創企業的創建和成長。
為此,政府首先應該調整小企業管理機構的目標,以促進新企業的建立。隸屬于小企業管理局的維權辦公室應該改變其使命,使其側重于消除或改進那些對高增長的初創公司設置障礙的法規。其次,政府應重點針對新企業做靈活的監管。在美國,國會應改革《監管靈活性法案》,以便審視該法案對成立兩年以下的新企業的影響,并考慮讓兩年以下企業免于遵守大部分法規,因為它們基本處于制定和實施商業計劃階段。此外,政府應該讓新企業更容易起步,應該效仿葡萄牙和智利的做法,允許新企業花不到1小時的時間在互聯網上注冊。最后,這不僅僅是各國政府的事。州(省)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應取消小企業優惠及其反大企業政策,如限制倉儲式大賣場的法規。地方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企業或其供應商的地方分支機構,對全國和全球供應鏈的參與。
接受大企業
我們的觀點是:從對技術創新的促進,到創造高薪就業機會,再到推動國家和全球生產率的增長,私有大企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所以大企業對于一個繁榮社會仍然必不可少。從蒸汽時代到今天的信息時代,歷次產業革命都使充滿活力、具有效率的企業應具有的規模變得更大,在農業、制造和服務等行業中皆是如此。新技術的確會縮短某些供應鏈,或使其離消費者更近,但制造業、食品生產、能源、零售和各種信息服務等行業中的規模報酬遞增不會終結,以高科技為基礎的小生產者構成的世界也不會出現。
從19世紀到21世紀,在現代經濟演變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些人在想方設法捍衛舊經濟秩序,而舊經濟秩序表現為更多的小企業,以及權力和利潤的更加分散。在公眾壓力、誤導性的分析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大多數國家會保護和補貼小企業。但是,相對于一個多世紀的失敗,信奉小企業好一派的這點成功,只不過是小小的安慰。《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從來不能阻止大企業寡頭占據美國制造業、能源、農商、零售和通信等行業的制高點。阻止連鎖店和超市蔓延的努力,以及每一代人試圖恢復小規模生產和工匠式制造業的“回歸土地”運動,只吸引了少數人。跟其他現代國家的民眾一樣,美國人也喜歡為小企業唱贊歌,同時駕駛著自己的豐田汽車到沃爾瑪購買由全球供應鏈制造的蘋果手機。重塑了發達經濟體的進程,也正在重塑許多低收入的國家。正如美國的歷史經驗一樣,這些當地社區的小企業精英們,正在尋求阻止這種變化,以便為自己的福祉服務,并在必要時犧牲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和工人的利益。
總而言之,提高社會經濟體系的生產率,會讓其他所有公共政策更易實現。充滿活力、資本密集的科技企業,趨于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大,而提高生產率的最好辦法就是消除阻礙,用這樣的企業取代規模較小、勞動力密集、技術停滯不前的夫妻雜貨店。但這樣做就需要戳破“小企業好”的神話,同時努力恢復大企業是進步和繁榮引擎的聲譽。
18世紀的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說過:“任何能讓一處原來只長一根玉米穗或一片草葉的地里,長出兩根玉米穗或兩片草葉的人,都是在增進人類的福祉,其對國家的貢獻比所有政客加起來還要多。”我們不應因為留戀鄉村生活和理想化過去的小規模經濟,而被蒙蔽了眼睛,以至于看不到那類最有可能產出兩根玉米穗或兩片草葉的企業的好處。
作者系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主席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D.?Atki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