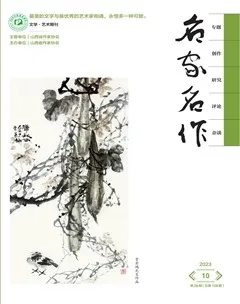感覺(jué)主義視域下佩索阿的觀看之道
林 雨
活躍于20 世紀(jì)初的葡萄牙詩(shī)人費(fèi)爾南多·安東尼奧·諾格拉·佩索阿(Fernando Antnio Nogueira Pessoa,1888—1937)創(chuàng)造了“異名”(Heteronymy)寫作方式,并創(chuàng)造了72 個(gè)異名作者,其中非常重要的有寫作《牧羊人》組詩(shī)的阿爾伯特·卡埃羅(Alberto Caeiro)和他的門徒里卡多·雷斯(Ricardo Reis)、阿爾瓦羅·德·坎普斯(lvaro de Campos),以及創(chuàng)作《不安之書》(The Book of Disquiet)的貝爾納多·索阿雷斯(Bernardo Soares)等,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職業(yè)、思想觀念和文學(xué)作品等都區(qū)別于佩索阿本人。阿爾伯特·卡埃羅作為佩索阿最重要的異名作者之一,主要?jiǎng)?chuàng)作了《牧羊人》組詩(shī)49 首和《戀愛(ài)中的牧羊人》組詩(shī)8 首等,他的兩個(gè)門徒和佩索阿本人都在某種程度受到了卡埃羅的影響,共同組成了“感覺(jué)主義者”團(tuán)體。“感覺(jué)主義”(sensacionismo)運(yùn)動(dòng)由佩索阿和他的好友詩(shī)人馬里奧·德· 薩-卡內(nèi)羅(Mário de Sá-Carneiro)發(fā)起,目的是復(fù)興民族詩(shī)歌,融入當(dāng)時(shí)歐洲的現(xiàn)代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阿爾伯特·卡埃羅在感覺(jué)主義流派里充當(dāng)導(dǎo)師的角色,他明確反對(duì)形而上學(xué),拒絕隱喻和思考,以《牧羊人》組詩(shī)重新定義了形而上學(xué)與宗教,試圖重建異教信仰,并且強(qiáng)調(diào)“感覺(jué)”和“觀看”,為人類提供了一種與世界建立聯(lián)系的全新方式。本文通過(guò)理解感覺(jué)主義的原則,并且深入分析阿爾伯特·卡埃羅的《牧羊人》組詩(shī),以明確卡埃羅所提出的“觀看”之道究竟是什么,從而進(jìn)一步理解佩索阿的異名創(chuàng)作對(duì)于文學(xué)發(fā)展的重要意義 。
一、感覺(jué)主義的起源與原則
佩索阿在一封信件中回應(yīng)一位英文編輯時(shí)提到出版葡語(yǔ)“感覺(jué)主義”詩(shī)選一事,這意味著佩索阿曾自覺(jué)地推動(dòng)感覺(jué)主義運(yùn)動(dòng),不僅通過(guò)“異名”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感覺(jué)主義”小團(tuán)體,還試圖發(fā)行相關(guān)出版物,1915 年創(chuàng)辦的雜志《奧爾弗斯》(Orpheu)成為感覺(jué)主義運(yùn)動(dòng)的陣地。在異名作者托馬斯·克洛澤(Thomas Crosse)寫作的《葡萄牙感覺(jué)主義者》的序言中,他對(duì)感覺(jué)主義詩(shī)人這樣評(píng)價(jià)道:“費(fèi)爾南多·佩索阿和薩-卡內(nèi)羅與象征主義最相似。阿爾瓦羅·德·坎波斯和約瑟·德·阿馬達(dá)·內(nèi)格雷魯則最接近現(xiàn)代的感受方式,其余人介于這二者之間”[1]。里卡多·雷斯在介紹卡埃羅的詩(shī)時(shí)提到,他的門徒坎普斯用“感覺(jué)主義”來(lái)形容卡埃羅面對(duì)自然與形而上學(xué)的態(tài)度。“感覺(jué)主義”的基礎(chǔ)在于用感覺(jué)替代思想,不僅將感覺(jué)作為靈感的基礎(chǔ),還當(dāng)作表達(dá)的手段,這代表著一種新的世界觀,也是人與世界建立聯(lián)系的一種全新方式。感覺(jué)主義運(yùn)動(dòng)具有很強(qiáng)的革新性,《奧爾弗斯》的出版在當(dāng)時(shí)引起了劇烈的爭(zhēng)論,直到第三期被迫終止出刊,這場(chǎng)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于是在葡萄牙這片土地上同其他現(xiàn)代運(yùn)動(dòng)一樣夭折。
在佩索阿看來(lái),感覺(jué)主義起源于三個(gè)古老的運(yùn)動(dòng),分別是法國(guó)象征主義、葡萄牙超驗(yàn)泛神論以及無(wú)知覺(jué)且矛盾的混亂事物。法國(guó)象征主義注重極端微小和病態(tài)的感覺(jué)分析,佩索阿認(rèn)為法國(guó)象征主義在某種層面上已經(jīng)算是“感覺(jué)主義”的初步形態(tài)。超驗(yàn)泛神論源于文藝復(fù)興精神和浪漫主義精神的融合體。感覺(jué)主義詩(shī)歌中表現(xiàn)出來(lái)的精神與肉體彼此滲透、互相超越,正是得益于超驗(yàn)泛神論的詩(shī)人及其作品。“自然”概念在超驗(yàn)泛神論中至關(guān)重要,“自然”即“肉體和靈魂完全交融在一起,形成了超越這二者的存在”[2]。這一影響反映在阿爾伯特·卡埃羅的創(chuàng)作中,就是他的《牧羊人》組詩(shī)對(duì)“自然”的推崇,接近自然意味著直接用眼睛去觀看,擯棄思考與形而上的哲學(xué)觀念。而無(wú)知覺(jué)且矛盾的混亂事物指的是立體主義和未來(lái)主義等現(xiàn)代運(yùn)動(dòng),它們對(duì)感覺(jué)主義者的影響體現(xiàn)在同樣承襲了對(duì)事物的感覺(jué),但這種影響并非文學(xué)上的。
感覺(jué)主義認(rèn)為,生活中的唯一現(xiàn)實(shí)是感覺(jué),藝術(shù)中的唯一現(xiàn)實(shí)是對(duì)感覺(jué)的意識(shí)。也就是說(shuō),感覺(jué)主義摒棄了哲學(xué)、倫理道德和美,甚至提及宗教與造物主也只是為了表達(dá)某些感覺(jué)。佩索阿對(duì)藝術(shù)作出了如下定義,即“和諧表達(dá)出我們所意識(shí)到的感覺(jué)”[2],這意味著每種感覺(jué)都應(yīng)該充分地表達(dá),而在表達(dá)的過(guò)程中可以激發(fā)更多的感覺(jué),這些感覺(jué)是一個(gè)整體的存在。由此,我們注意到感覺(jué)主義的三個(gè)中心原則:第一,藝術(shù)是崇高的構(gòu)筑,最偉大的藝術(shù)可以形象化,可以創(chuàng)造出有組織的整體,而這個(gè)整體的各個(gè)部分都處在恰當(dāng)?shù)奈恢蒙稀!爱?dāng)亞里士多德稱一首詩(shī)即是一個(gè)‘動(dòng)物’的時(shí)候他便宣明了這個(gè)偉大的原則。”[2]第二,所有藝術(shù)都是由各個(gè)部分組成的,每個(gè)部分本身必須完美。第一個(gè)原則符合古典主義原則,強(qiáng)調(diào)統(tǒng)一和結(jié)構(gòu)完美,第二個(gè)原則對(duì)應(yīng)的則是浪漫主義的“完美章節(jié)”原則。第三,構(gòu)成整體所包含部分的每一個(gè)細(xì)小碎片本身都應(yīng)該是完美的。這三個(gè)原則也可以用來(lái)形容由佩索阿的異名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文學(xué)空間的特征,每個(gè)文學(xué)空間都是微小的,但都是完整的。
“感覺(jué)”與“思考”在阿爾伯特·卡埃羅的詩(shī)歌中有著非常大的分野,感覺(jué)是在不產(chǎn)生思想的情況下思考,感覺(jué)不負(fù)責(zé)產(chǎn)生觀點(diǎn),而是通過(guò)感官對(duì)事物本質(zhì)的直接理解。也就是說(shuō),感覺(jué)就是去看、去聽(tīng)、去聞、去渴望觸摸。阿爾伯特·卡埃羅的態(tài)度就是如此,他在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中一再宣告:我們要感覺(jué),而不要思考。
二、從反形而上學(xué)到建立異教信仰
阿爾伯特·卡埃羅的主要作品《牧羊人》組詩(shī)整體語(yǔ)言質(zhì)樸,鮮少使用意象,但富有哲學(xué)意味。《牧羊人》組詩(shī)的第五首《豐富的形而上學(xué)》,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種不同于自柏拉圖以來(lái)的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xué)的哲學(xué)理念,甚至可以說(shuō)是完全推翻了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xué)的理念。從柏拉圖到康德、黑格爾,傳統(tǒng)意義上的哲學(xué)圍繞世界的本質(zhì)和自我問(wèn)題展開(kāi),人類的理性與思考在其中至關(guān)重要,但是佩索阿在詩(shī)歌的第一句就指明“豐富的形而上學(xué)存在于對(duì)任何事物的不思考中”[3],這無(wú)異于是一種口號(hào)式的宣告。阿爾伯特·卡埃羅所說(shuō)的豐富的形而上學(xué)朝向的不再是抽象的不可見(jiàn)的世界本源,而是具體的自然事物,諸如太陽(yáng)、花、樹(shù)、山和月光。對(duì)卡埃羅來(lái)說(shuō),自然事物的存在足夠豐富,不需要再通過(guò)思考去認(rèn)識(shí)它們,或者說(shuō)不需要越過(guò)具體事物去思考抽象本質(zhì),只需要“觀看”就能獲得事物表面之下的準(zhǔn)確性。
形而上學(xué)?那些樹(shù)有什么形而上學(xué)?
它們枝繁葉茂,綠意充盈
按時(shí)結(jié)出果實(shí),并不使我們思考,
我們甚至不知道如何注意它們。
但什么形而上學(xué)比它們更好?它們不知道它們?yōu)槭裁炊?/p>
甚至沒(méi)有意識(shí)到它們不知道。
“事物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
“宇宙的內(nèi)在意義……”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假的,所有這些東西毫無(wú)意義。[3]
卡埃羅通過(guò)詩(shī)句明確地反對(duì)形而上學(xué),拒絕思考意義,但是這種宣告式的語(yǔ)言卻不顯得生硬,反而擲地有聲,反映了一種準(zhǔn)確而清晰、充滿否定之后更加肯定的力量。
在論及世界的本源時(shí),卡埃羅既反對(duì)形而上的觀念論,也棄絕了宗教中作為萬(wàn)物之始的神,卡埃羅在詩(shī)中宣稱造物主是和樹(shù)、花、山、月光、太陽(yáng)一樣的存在。感覺(jué)主義者把造物主拉下高位,進(jìn)行去神秘化:“我愛(ài)他而不思考他/我通過(guò)觀看和傾聽(tīng)思考他/我和他時(shí)時(shí)刻刻在一起。”[3]由此,阿爾伯特·卡埃羅和他的門徒宣稱自己是異教徒。在另一首詩(shī)歌中,卡埃羅寫道:“想到上帝就是違背上帝/因?yàn)樯系鄄幌胱屛覀冋J(rèn)識(shí)他/所以他從不向我們現(xiàn)身……”[3]造物主的目的不再是讓人類見(jiàn)證他、認(rèn)識(shí)他,他和有限的人類一樣具有缺陷,他創(chuàng)造人類與自然萬(wàn)物的意圖是一樣的,只是“讓我們單純而安靜,像小溪和樹(shù)”[3]。由此可以知道,卡埃羅并沒(méi)有完全棄絕神,通過(guò)《少年耶穌的故事》塑造了一個(gè)具備真正的人性、像純真的孩子一樣會(huì)奔跑打鬧的耶穌:
待在我住處的這個(gè)新孩子
把一只手伸向我
另一只手伸向存在的萬(wàn)物
因此,無(wú)論走在什么路上,我們?nèi)冀Y(jié)伴而行,
又是跳又是唱又是笑[3]
在感覺(jué)主義的詩(shī)學(xué)宇宙中,阿爾伯特·卡埃羅將孩子般的少年、詩(shī)人(“我”)和存在的萬(wàn)物這三者重新建構(gòu)為神圣的基礎(chǔ),以講新故事的方式創(chuàng)建了一種新的異教信仰。這恰恰呼應(yīng)了佩索阿的另一主張。在論及人與自然萬(wàn)物的關(guān)系時(shí),人往往被放置于中心地位,“人是萬(wàn)物的尺度”。但是在卡埃羅的世界觀中,自然事物的存在具有它們自己的獨(dú)立性,人類中心主義遭到顛覆性的質(zhì)疑,自然事物去隱喻化,它們不再承載人類的意義世界而獲取了自身的真正本質(zhì)。
三、觀看之道:感覺(jué),及反對(duì)思考
由以上論述可知,阿爾伯特·卡埃羅在其《牧羊人》組詩(shī)中同步進(jìn)行著解構(gòu)與建構(gòu)的工作,一方面反對(duì)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xué)和宗教,另一方面又試圖建立異教信仰,確立了一種新的觀看世界的方式,即一種自然的、感覺(jué)的態(tài)度。在如此大的世界觀框架之下,卡埃羅還提出了許多具體的主張:
當(dāng)他們讀我的詩(shī)時(shí),我希望他們認(rèn)為
我是個(gè)自然的詩(shī)人——
就像他們兒時(shí)玩累了
在一棵老樹(shù)的涼蔭里
砰的一聲坐下來(lái),
用有條紋的棉罩衣袖子
從他們發(fā)燙的額頭上
擦去汗水。[3]
如何理解“自然的詩(shī)人”,首先要理解卡埃羅如何定義“觀看”。由上面的詩(shī)歌片段可以很直接地獲取卡埃羅所要表達(dá)的信息,他希望讀者在閱讀他的詩(shī)歌時(shí)能像自然界發(fā)生的一切,像純真的孩童會(huì)做的那樣,不需要加入任何思考地去閱讀。自然的閱讀方式就是:去閱讀,除此之外沒(méi)有任何別的事情,也就是不需要去了解作者的經(jīng)歷、歷史背景、寫作主題與意義等。“觀看”與閱讀一樣,就是棄絕思考的感知。“這個(gè)世界的形成并非為了讓我們思考,而是讓我們觀看并認(rèn)同……”這就意味著,人與世界之間是通過(guò)“觀看”來(lái)建立聯(lián)系的,“我思考用眼睛和耳朵/用手和腳/用鼻子和嘴巴”[3],即直接運(yùn)用人自身的感官直覺(jué)通達(dá)事物,而不再需要通過(guò)哲學(xué)理論來(lái)建構(gòu)一套解釋體系。在卡埃羅看來(lái),面對(duì)石頭和植物時(shí),如果進(jìn)行了某些思考:
我就會(huì)看不到樹(shù)和植物
也看不到大地
因?yàn)橹荒芸吹轿业乃枷搿?/p>
我會(huì)變得不快樂(lè),停留在黑暗中。
因此,不要思考,我就會(huì)擁有大地和天空。[3]
從這個(gè)層面來(lái)說(shuō),卡埃羅是反柏拉圖的,既反對(duì)一元論,也超越了物質(zhì)和精神的二分。人與世界之間的聯(lián)系由“觀看”建立,這種觀看是感覺(jué)主義之上的觀看,通過(guò)感官直接接觸事物,不加思考便得到對(duì)事物本質(zhì)的理解。這一觀看方式與現(xiàn)象學(xué)的還原非常相似,但是相較于現(xiàn)象學(xué)還原的混沌狀態(tài)來(lái)說(shuō),卡埃羅所要通向的是一種絕對(duì)的清晰。在佩索阿和卡埃羅看來(lái),任何事物都是自然且完整的,通過(guò)思考得到的抽象概念并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事物。與此同時(shí),佩索阿以感覺(jué)主義重新恢復(fù)了人類感官的重要性,通過(guò)感官知覺(jué)得到的不再是事物的表象,而是通達(dá)本質(zhì)。
法國(guó)當(dāng)代哲學(xué)家阿蘭·巴迪歐在《非美學(xué)手冊(cè)》(Handbook of Inaesthetics)的《哲學(xué)任務(wù):成為佩索阿的同時(shí)代人》一文中評(píng)價(jià)佩索阿,通過(guò)詩(shī)歌劃出了一塊真正脫離“推翻柏拉圖主義”清一色標(biāo)語(yǔ)的思想領(lǐng)域[4]。也就是說(shuō),佩索阿的異名創(chuàng)作在柏拉圖主義和反柏拉圖主義之外走出了一條不同以往的道路,因此巴迪歐提出了一種疑問(wèn),同時(shí)也是一種建議:當(dāng)代哲學(xué)能不能將自身置于佩索阿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條件之下?阿爾伯特·卡埃羅作為感覺(jué)主義異名團(tuán)體的導(dǎo)師,他的反形而上學(xué)、用感覺(jué)代替思考的詩(shī)學(xué)理念正表現(xiàn)出一種親近前蘇格拉底時(shí)代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放在當(dāng)代哲學(xué)的語(yǔ)境下并不是過(guò)時(shí)的,反而提供了一種新的回應(yīng)現(xiàn)代性問(wèn)題的方式。同時(shí),感覺(jué)主義者坎波斯、雷斯以及佩索阿本人對(duì)于卡埃羅也不是一味地追從,他們都有各具特點(diǎn)的詩(shī)學(xué)觀念與創(chuàng)作,而通過(guò)這一感覺(jué)主義團(tuán)體可以窺見(jiàn)佩索阿由“異名”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作者空間與文學(xué)宇宙之間的聯(lián)系。
四、結(jié)語(yǔ)
費(fèi)爾南多·佩索阿和馬里奧·德·薩-卡內(nèi)羅發(fā)起的感覺(jué)主義運(yùn)動(dòng)持續(xù)時(shí)間很短,在歐洲范圍內(nèi)沒(méi)有產(chǎn)生多大影響,但是這一運(yùn)動(dòng)及留下來(lái)的詩(shī)歌作品在葡萄牙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中充當(dāng)著重要的角色,既更新了葡萄牙新詩(shī)詩(shī)壇,又對(duì)歐洲面臨的現(xiàn)代性問(wèn)題做出了積極的回應(yīng)。“感覺(jué)主義者”阿爾伯特·卡埃羅在其詩(shī)歌作品中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觀看”之道,認(rèn)為建立人與世界連接的唯一方式就是“感覺(jué)”,即一種拒絕思考的“觀看”。即使發(fā)現(xiàn)佩索阿的價(jià)值已經(jīng)是20 世紀(jì)末的事情,但正如阿蘭·巴迪歐所呼吁的那樣,成為與佩索阿同時(shí)代的人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代的哲學(xué)任務(wù),他的文學(xué)和哲學(xué)價(jià)值還有很大的發(fā)掘空間。佩索阿創(chuàng)造的“異名”寫作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代一個(gè)重要的事件,他以這種方式拓展了眾多微小而完整的文學(xué)空間,“感覺(jué)主義”更是為我們看待世界與萬(wàn)物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觀看”方式,理解此種方式將有利于我們更好地面對(duì)現(xiàn)代性問(wèn)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