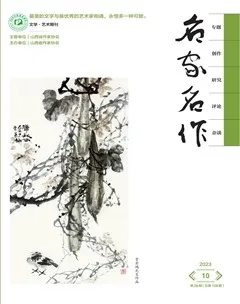作為文學流派的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研究
王思丹
布魯斯伯里(Bloomsbury)文化圈是20 世紀上半葉,由英國倫敦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的松散文化組織,不僅在英國有著巨大且深遠的影響力,對英語世界文學、藝術、哲學等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學是布魯斯伯里文化圈討論較多的內容,一方面,布魯斯伯里文化圈中作家人數較多,如被譽為20 世紀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先鋒的弗吉尼亞·伍爾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以傳記創作而聞名的里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等,另一方面,20 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文學是19 世紀英國文學的自然延續,呈現出一派多元、繁榮的新氣象[1],為文學批評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這個角度而言,布魯斯伯里文化圈可以視作一個特殊的文學流派,既有豐富的文學創作經驗,也有獨特的文學批評理論。
一、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簡介
布魯斯伯里為倫敦市中心一條街的街名。20 世紀上半葉,這里居住著許多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多出身于書香門第,畢業于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著名學府。相似的生活經歷與共同的價值觀念,使他們締結為英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文化團體——布魯斯伯里文化圈。與其他文化團體相比,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成員來源廣泛
一般的文化團體成員多來源于某個領域,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員來源則極為廣泛,覆蓋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如文學領域的弗吉尼亞·伍爾芙、藝術領域的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政治領域的萊昂納德·伍爾夫(Leonard Woolf)、經濟領域的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弗吉尼亞·伍爾芙突破傳統小說敘事的限制,推動了意識流文學的發展;梅納德·凱恩斯開創了現代宏觀經濟分析的先例,推動了經濟學領域的凱恩斯革命。
(二)崇尚自由
英國有著濃厚的保守主義傳統,布魯斯伯里文化圈則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既不迷信權威,也不刻意張揚,崇尚人際關系的自由探討及發展,被視作英國保守主義的反叛[2]。20 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動蕩不安,各種思潮激烈交鋒。布魯斯伯里文化圈不僅崇尚自由,更身體力行為自由而戰。西班牙內戰時期(1936—1939),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貝爾特·康弗德(Belt Conford)等布魯斯伯里文化圈成員奔赴前線,為自由而戰,并獻出了生命。
(三)組織松散
一般的文化團體多有完善的組織架構和明確的組織章程。布魯斯伯里文化圈則是基于血緣、姻緣、學緣、地緣等締結的松散文化團體,成員間多有著密切的個人關系,如萊昂納德·伍爾夫與弗吉尼亞·伍爾芙為夫妻,貝爾特·康弗德是詩人弗蘭西斯·康弗德(Francis Conford)的兒子,但并未形成嚴密的組織。他們多以朋友聚會的形式,輪流在某個成員的家中舉行茶會,分享各自領域的新訊息及個人的新體會。
二、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文學創作研究
(一)尊崇內心體驗的文學創作理念
文學創作具有主客觀合一的特點,從客觀的角度而言,文學創作發生于特定的時代環境中,必然受到時代環境的深刻影響;從主觀的角度而言,文學創作和作家個人的思想風貌、人格特質有密切的關系,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19 世紀是英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高潮,現實主義作家著力描繪物質世界的表象,將真實反映世界作為文學創作的主要任務,最為典型的便是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作家,如弗吉尼亞·伍爾芙、史蒂芬·斯賓德(Stephen Spender)等,其創作理念與19 世紀作家有著很大的差別,他們更加尊崇內心的體驗。
文學源自生活,而對生活觀察視角的差別則是布魯斯伯里文化圈作家與19 世紀作家的重要差別。諸如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等現實主義作家,多帶著批判的眼光來觀察現實,希望借助文學創作來展現現實社會的丑陋。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作家則將“愛”視作生活的首要目的,倡導發掘生活中的美好、享受生活,這顯然是受到了功利主義哲學以及唯美主義的影響。布魯斯伯里文化圈所謂的享受生活,并非單純的物質享受,而是更加側重心理上的體驗,他們將具有學術性、哲理性的“知識”作為享受生活的追求,并主張在文學創作中將內心體驗真誠地表現出來。
(二)意識流的敘事方式
意識流原為心理學術語,由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英國作家梅·辛克萊(May Sinclair)將其引入文學領域,用來指代一種有別于傳統敘事的新型敘事方式。在意識流小說的發展中,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弗吉尼亞·伍爾芙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其代表作品有《雅各的房間》《達洛衛夫人》《到燈塔去》等,均采用了意識流的敘事方式。以《達洛衛夫人》為例,小說在敘事視角的選擇上,同時采用了全知全能的零聚焦視角和敘述者等于人物的內聚焦視角,并以零聚焦視角與內聚焦視角的不斷轉換來展現意識的流動,同時,伍爾芙巧妙運用內心間接獨白中敘述者的聲音來引導讀者從復雜的意識流中找到秩序與和諧。
時空是敘事的兩大維度,以往作家在敘事中多嚴格遵循鐘表時間和物理空間,由此導致的結果便是敘事受到嚴重的束縛。意識流的敘事方式突破了傳統時空觀的限制,具有更強的自由性,也更能表現作家內心的想法。在《達洛衛夫人》中,弗吉尼亞·伍爾芙吸收、借鑒了電影藝術中的蒙太奇手法,通過時間蒙太奇、空間蒙太奇,將同一時間內不同空間的事件以及同一空間內不同時間的事件,巧妙地組合、交叉、重疊在一起,形成了多時空共存、交融的局面[3]。時空跳躍是《達洛衛夫人》的一大特點,意識流小說完全遵循意識流動的過程來敘事,意識的自由、無規則流動,使《達洛衛夫人》中的時空極具條約性,完全逾越了物理時空,時而現在,時而閃回到過去;時而此處,時而切換到彼處[3]。
(三)歷史與藝術相結合的傳記書寫新模式
傳記文學是英國文學的重要分支,早在中世紀時期,英國便涌現出了大量以主教、圣徒、殉教者為傳主的傳記文學。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里頓·斯特拉奇是英國傳記作家的代表,他以獨特的組織方式和戲謔的語言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傳記寫作方式,而《維多利亞名人傳》則是斯特拉奇享有盛譽的作品,被伍爾芙譽為“新傳記”。
歷史與藝術的結合是《維多利亞名人傳》有別于傳統傳記的根本特征。英雄史觀作為一種唯心主義史觀,廣泛存在于世界各地,英國則是英雄史觀的大本營。英雄史觀將英雄視作社會歷史的主宰,認為歷史發展完全由英雄推動,正如英國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所言,“世界的歷史就是偉人的傳記”。根據英雄史觀,英雄的傳記書寫與歷史書寫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英雄的生平經歷、思想性格、偉大功績本身便是歷史中最為閃耀的內容。《維多利亞名人傳》是英雄史觀的產物,斯特拉奇從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燦若繁星的英雄中選擇了亨利·愛德華·曼寧(Henry Edward Manning)、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作為傳主,透過他們展現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特色。
斯特拉奇既強調傳記的真實性,也強調傳記的藝術性。他認為,傳統的傳記書寫片面地強調內容的客觀性,而忽略了敘事的藝術性,致使傳記味同嚼蠟,助長了以紀實為幌子、實則敷衍了事的風氣,主張從組織架構、敘事方式、語言風格等多個層面強化傳記的藝術性。正如其所言:“偉大的史學家頭等責任便是做一名藝術家。”[4]
三、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文學批評研究
(一)強調英國傳統
維多利亞時期是英國最為強盛的時期,維多利亞女王帶領英國征服世界各地,創造了“日不落帝國”的神話。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逐步走向衰落,美國、德國等國家的崛起對英國世界領袖的地位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布魯斯伯里文化圈處于英國由盛轉衰的時期,其成員一方面通過追憶過往的榮光來增強民族自信、國家自信;另一方面則以文學批評的形式強調英國傳統,渴望維持英國在文學乃至文化領域的獨特地位。1776 年,美國獨立。南北戰爭后,美國經濟蒸蒸日上,并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主要由英國移民建立,英國傳統對美國文學有著重要的影響。伍爾芙據此將美國作家群體劃分為兩個陣營:擁戴英國的陣營、擁戴美國的陣營。前者代表作家為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后者代表作家則有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5]。在伍爾芙看來,擁戴英國陣營的作家更好地保存和延續了英國傳統,推進了英國文學范式的發展,而擁戴美國陣營的作家則背離了英國的傳統。
(二)注重文學的形式美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伴隨著工業革命的不斷深入,城鎮化進程持續提升,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市儈哲學盛行。以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為代表的藝術家,對市儈哲學以及虛偽的道德觀念持激烈的批判態度,提出了唯美主義的主張。唯美主義將美的享受作為文藝創作的根本目的,要求文藝創作為人類提供感官上的愉悅。唯美主義思潮對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文學批評理念是唯美主義思潮的延續與發展,正如S. P. Rosenbaum 所言:“唯美主義是布魯姆斯伯里集團在藝術方面的價值所在。”唯美主義思潮割裂了文藝的審美性和道德性,促使文藝向著注重形式美的方向發展。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作為布魯斯伯里文化圈文學批評領域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理論。對形式美的追求是布魯斯伯里文化圈的共同看法,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20 世紀上半葉英國文學乃至英語文學的創作。
(三)淡化文學的社會責任
強調文學的社會責任是文學批評發展史的一條主線。古代中國有“文以載道”的思想,魏文帝曹丕更是將文章視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無獨有偶,英國文學批評家同樣看重文學的社會責任,比如,以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弗·雷·利維斯(F. R.Leavis)等為代表文學文化批評家。阿諾德生活于維多利亞時代,提出了“藝術是承載道德的實用之物”的觀點,將文藝創作視作弘揚道德觀念的一種手段。利維斯與布魯斯伯里文化圈處于同一時代,他繼承了阿諾德對文學的看法,將社會功能作為文學的基本功能,主張弘揚文學文化,并以文學文化來抵御工業革命以來大眾文化的侵襲。布魯斯伯里文化圈受到了功利主義、唯美主義的深刻影響,將增進個人的幸福、活動感官上的愉悅作為文學的基本信條,有意識地弱化文學與道德的關系,淡化文學的社會責任。正如伍爾芙所倡導的,文學作品評判最重要的指標便是人類共有的生命趣味[6]。
四、結語
作為文學流派的布魯斯伯里文化圈不僅在文學創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動了英國文學乃至英語文學的發展,在文學批評領域也是成果斐然,他們以功利主義、唯美主義為哲學基礎,強調文學的形式美,淡化文學的社會責任,構建了以自我體驗為中心的文學批評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