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研究*
康 寬,陳俞全,郭 沛,陳景帥
(1.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院,北京 100083;2.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全球食物經(jīng)濟(jì)與政策研究院,北京 100083)
0 引言
農(nóng)業(yè)是影響我國(guó)碳中和承諾如期實(shí)現(xiàn)的重要因素[1,2]。根據(jù)政府間氣候變化專(zhuān)門(mén)委員會(huì)估算,2007—2016年農(nóng)業(yè)食物系統(tǒng)的溫室氣體排放占總排放量21%~37%,其中農(nóng)業(yè)活動(dòng)本身為9%~14%[3,4]。已有研究認(rèn)為,現(xiàn)有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模式的維持以及糧食的穩(wěn)定供應(yīng)需要以一定程度的碳排放作為環(huán)境代價(jià),實(shí)施碳減排行動(dòng)方案將限制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dòng)的開(kāi)展,糧食安全與碳中和目標(biāo)間存在內(nèi)在政策沖突[5]。相關(guān)研究估算,如果要在2050年實(shí)現(xiàn)全球氣溫增長(zhǎng)控制在1.5℃之內(nèi)的碳減排目標(biāo),將導(dǎo)致0.8億~3億人陷入糧食匱乏及營(yíng)養(yǎng)不良的局面,對(duì)全球糧食安全形成巨大挑戰(zhàn)。而在中國(guó)及印度等人口大國(guó),其情況更為嚴(yán)峻[6]。
誠(chéng)然糧食生產(chǎn)的碳源屬性不容忽視,但已有研究并不能證明糧食安全與碳中和存在零和博弈的觀點(diǎn)。提升生態(tài)系統(tǒng)碳匯能力已經(jīng)被列為“十四五”和 2035遠(yuǎn)景時(shí)期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目標(biāo)之一,實(shí)現(xiàn)碳中和目標(biāo)應(yīng)當(dāng)從碳源和碳匯兩方面著手[7]。一個(gè)亟待申明的觀點(diǎn)是,糧食生產(chǎn)不僅是溫室氣體排放源,同樣是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忽視其在碳匯方面的實(shí)際效果和巨大潛力,并不利于全面認(rèn)識(shí)糧食生產(chǎn)對(duì)于碳循環(huán)的影響[8-10]。Li 等[11]測(cè)算不同陸地綠色植被的碳匯貢獻(xiàn)率,發(fā)現(xiàn)糧食作物碳匯量占比高達(dá)27.95%。但不容忽視的是,農(nóng)地、林地、草地及其它綠色植被緊密關(guān)聯(lián),同屬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重要組成部分,與糧食生產(chǎn)相配套的田間管理措施及土地利用方式調(diào)整,同樣會(huì)對(duì)區(qū)域內(nèi)其他綠色植被碳匯水平產(chǎn)生影響,其外部性不容忽視。因此,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凈效應(yīng)并不確定,成為糧食安全與碳中和背景下亟待回答的重要課題。
與既有文獻(xiàn)相比,文章貢獻(xiàn)在于:首先,該文基于2000—2017年中國(guó)縣域面板數(shù)據(jù),直接考察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凈效應(yīng),從碳匯視角回答糧食安全與碳中和政策的兼容性。其次,構(gòu)建糧食生產(chǎn)影響生態(tài)碳匯的分析框架,廓清了二者間作用機(jī)制。最后,依據(jù)耕作制度和空間區(qū)域差異,多維度考察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異質(zhì)性,增強(qiáng)研究結(jié)論的針對(duì)性。
1 機(jī)制分析
已有研究集中于討論糧食作物本身的碳匯效應(yīng),強(qiáng)調(diào)糧食作物通過(guò)光合作用固定大氣中的碳元素[12],但不能展示糧食生產(chǎn)影響生態(tài)碳匯的全貌。該文認(rèn)為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同時(shí)存在正向碳匯和負(fù)向碳匯的雙重機(jī)制(圖1)。

圖1 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作用機(jī)制框架
1.1 糧食生產(chǎn)表現(xiàn)出正向碳匯機(jī)制
(1)光合作用固碳:糧食作物在籽粒期、幼苗期和作物期均可通過(guò)光合作用吸收空氣中的CO2,生成C6H12O6等有機(jī)物并釋放O2。
(2)肥料固碳:與糧食生產(chǎn)配套的田間管理措施,同樣可以起到正向固碳作用。第一,通過(guò)化肥(尿素等)及有機(jī)肥返田,可以人為將碳元素轉(zhuǎn)入土壤中。Jarecki 等[13]通過(guò)實(shí)驗(yàn)證明,施肥會(huì)增強(qiáng)土壤中的有機(jī)碳,且相較于化肥,有機(jī)肥更加顯著提高土壤有機(jī)碳固定水平。第二,為提高土壤肥力而實(shí)施的秸稈還田等措施,同樣具有固碳作用。糧食作物秸稈是典型的生物質(zhì)炭。采用秸稈還田等措施,可以有效抑制CH4、N2O等溫室氣體產(chǎn)生,且作物秸稈分解為CO2的速度緩慢,可穩(wěn)定存在數(shù)百年,具有顯著碳封存效應(yīng),因此秸稈還田有助于提高土壤固碳能力[14,15]。
(3)技術(shù)固碳:糧食生產(chǎn)中實(shí)施的輪作制度以及免耕、少耕等保護(hù)性耕作行為,可以緩解土壤中碳和氮的分解,同樣具有正向固碳作用。以玉米—玉米—大豆輪作模式為例,該輪作制度將使黑土層有機(jī)質(zhì)含量增加了0.15g/kg,比玉米連作條件下土壤有機(jī)質(zhì)提高7.5%,玉米產(chǎn)量提高了11.2%[16]。由此可見(jiàn),科學(xué)合理的輪作制度將顯著提高作物殘留物,有助于提高土壤中的有機(jī)碳含量及糧食產(chǎn)量[17]。
1.2 糧食生產(chǎn)也存在負(fù)向的碳匯機(jī)制
(1)過(guò)度耕作:追求糧食產(chǎn)量增長(zhǎng)而導(dǎo)致的過(guò)度耕作,將會(huì)引發(fā)土壤退化,惡化糧食作物和其他綠色植被的生長(zhǎng)環(huán)境,不利于作物固碳機(jī)制的實(shí)現(xiàn)。韓曉增和鄒文秀[16]研究發(fā)現(xiàn),當(dāng)其他生產(chǎn)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土壤有機(jī)質(zhì)含量每下降0.5%,作物產(chǎn)量則下降15.0%。因此,糧食生產(chǎn)導(dǎo)致的地力退化,將顯著降低糧食作物固碳能力。
(2)土地性質(zhì)調(diào)整:糧食生產(chǎn)將增加區(qū)域內(nèi)土地競(jìng)爭(zhēng)程度。農(nóng)業(yè)種植面積的增加可能會(huì)引起森林、草地、濕地等其他植被覆蓋面積的下降。以東北黑土地開(kāi)荒為例,劉興土等[17]研究發(fā)現(xiàn),糧食生產(chǎn)所帶來(lái)土地性質(zhì)調(diào)整,形成對(duì)森林、草甸和沼澤等自然植被的破壞,導(dǎo)致土壤中的有機(jī)質(zhì)、腐殖質(zhì)含量快速下降。鑒于森林等植被類(lèi)型的固碳能力顯著高于糧食作物,糧食生產(chǎn)引致的土地競(jìng)爭(zhēng)可能降低了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碳匯總量[18]。
以上分析表明,糧食生產(chǎn)同時(shí)具有正向和負(fù)向的雙向碳匯機(jī)制,其對(duì)生態(tài)碳匯總量的凈效應(yīng)取決于兩種機(jī)制的疊加,對(duì)于該效應(yīng)的準(zhǔn)確識(shí)別有待構(gòu)建計(jì)量經(jīng)濟(jì)模型進(jìn)一步檢驗(yàn)。
2 研究設(shè)計(jì)
2.1 模型設(shè)定
該文基于2000—2017年中國(guó)1 769個(gè)縣的面板數(shù)據(jù),設(shè)定雙向固定效應(yīng)模型實(shí)證甄別縣域?qū)用婕Z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模型選擇依據(jù)在于:一方面,雙向固定效應(yīng)模型可以控制不隨時(shí)間變化,但與特定縣域相關(guān)的變量,即縣域固定效應(yīng),包括土壤、地形、地貌等地理因素;另一方面,雙向固定效應(yīng)模型可以控制不隨縣域變化,但與特定年份相關(guān)的變量,即年份固定效應(yīng),用來(lái)控制特定年份發(fā)生的沖擊。此外,為盡可能避免遺漏變量導(dǎo)致的回歸結(jié)果偏誤,該文同時(shí)控制可能對(duì)生態(tài)碳匯產(chǎn)生影響的經(jīng)濟(jì)因素和部分具有時(shí)變特征的自然因素。模型設(shè)定為:
Sequestrationit表示縣i在第t年的生態(tài)碳匯水平;Productionit表示縣i在第t年的糧食生產(chǎn)水平;X表示一系列可能對(duì)生態(tài)碳匯產(chǎn)生影響的經(jīng)濟(jì)因素和自然因素,包括人口總量、財(cái)政支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平均降水、平均日照和平均氣溫;α0、α1和β為待估參數(shù),其系數(shù)α1衡量了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是該文關(guān)注的核心系數(shù)。μi表示縣域固定效應(yīng);v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yīng);εit表示隨機(jī)擾動(dòng)項(xiàng)。
2.2 變量說(shuō)明
(1)被解釋變量:生態(tài)碳匯(Sequestrationit)。Chen等[19]通過(guò)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提供的MOD17A3產(chǎn)品獲取陸地綠色植被的凈初級(jí)生產(chǎn)力①生態(tài)系統(tǒng)得以運(yùn)行的基礎(chǔ)是初級(jí)生產(chǎn)力,即綠色植被通過(guò)光合作用生成的能量(或有機(jī)物質(zhì))。而初級(jí)生產(chǎn)力扣除綠色植被自養(yǎng)呼吸所需能量(或有機(jī)物質(zhì))后的凈值便是凈初級(jí)生產(chǎn)力。凈初級(jí)生產(chǎn)力為除綠色植被之外的所有有機(jī)生命提供了能量和物質(zhì)基礎(chǔ),是理解地表碳循環(huán)過(gu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估算生態(tài)承載能力的重要指標(biāo),在此基礎(chǔ)上計(jì)算2000—2017年中國(guó)縣域陸地綠色植被固碳量,并公開(kāi)發(fā)布,為生態(tài)碳匯的相關(guān)研究提供了數(shù)據(jù)基礎(chǔ),是該領(lǐng)域引用率較高的數(shù)據(jù)集[20,21]。該文使用該指標(biāo)作為生態(tài)碳匯的衡量指標(biāo)。
(2)核心解釋變量:糧食生產(chǎn)(Productionit)。該文使用糧食總產(chǎn)量作為糧食生產(chǎn)的衡量指標(biāo)。糧食總產(chǎn)量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者日歷年度內(nèi)生產(chǎn)的全部糧食數(shù)量,按收獲季節(jié)包括夏收糧食、早稻和秋收糧食,按作物品種包括谷物、薯類(lèi)和豆類(lèi)。此外,為驗(yàn)證實(shí)證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選用糧食種植總面積進(jìn)行穩(wěn)健性檢驗(yàn)。
(3)控制變量(X):為盡可能減少遺漏變量導(dǎo)致的回歸結(jié)果偏誤,該文同時(shí)控制可能對(duì)生態(tài)碳匯產(chǎn)生影響的經(jīng)濟(jì)因素和自然因素。
控制變量中的經(jīng)濟(jì)因素包括人口總量、財(cái)政支出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Brandt等[22]研究發(fā)現(xiàn)人口與綠色植被覆蓋率呈現(xiàn)出相反的趨勢(shì),為滿足人口總量增加所需要的建設(shè)用地增加導(dǎo)致綠色植被退化,降低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承載能力,該文選用縣域戶籍人口作為人口總量的衡量指標(biāo)。財(cái)政分權(quán)體制下,地方政府財(cái)權(quán)與事權(quán)的失衡強(qiáng)化了地方政府的財(cái)稅激勵(lì),在此背景下,“以地生財(cái)”“以地引財(cái)”推動(dòng)土地出讓成為地方政府緩解財(cái)政壓力的重要途徑[23],不斷擠壓綠色植被的生存空間,該文選用政府一般公共預(yù)算支出占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的比率作為財(cái)政支出的衡量指標(biāo)。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同樣影響著碳中和的進(jìn)程,這不僅是因?yàn)楦呶廴尽⒏吲欧女a(chǎn)業(yè)在碳減排方面的壓力,同樣在于其污染物破壞了綠色植被的生長(zhǎng)環(huán)境,制約生態(tài)系統(tǒng)碳匯能力,該文選用第二產(chǎn)業(yè)增加值占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的比率作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衡量指標(biāo)。
控制變量中的自然因素包括平均降水、平均日照、平均氣溫。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來(lái)自國(guó)家氣象科學(xué)數(shù)據(jù)共享服務(wù)平臺(tái)提供的中國(guó)地面氣候資料日值數(shù)據(jù)集(V3.0),是各個(gè)觀測(cè)站點(diǎn)的日度數(shù)據(jù),使用 IDW 法插值成格點(diǎn)數(shù)據(jù),再分區(qū)域平均計(jì)算得到了中國(guó)各縣的分年的降水、日照和氣溫?cái)?shù)據(jù)。此外,為盡量保證該文回歸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該文在穩(wěn)健性檢驗(yàn)部分進(jìn)一步納入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作為控制變量,基于NASA提供的ASTER全球數(shù)字高程模型V003數(shù)據(jù)計(jì)算獲得。
生態(tài)碳匯的原始數(shù)據(jù)來(lái)自Chen等[19]發(fā)布在Scientific Data的2000—2017年中國(guó)縣域陸地綠色植被固碳數(shù)據(jù);糧食生產(chǎn)及控制變量中經(jīng)濟(jì)因素的原始數(shù)據(jù)來(lái)自《中國(guó)縣域統(tǒng)計(jì)年鑒》和EPS數(shù)據(jù)平臺(tái);控制變量中地理因素的原始數(shù)據(jù)來(lái)自國(guó)家氣象科學(xué)數(shù)據(jù)共享服務(wù)平臺(tái)和NASA。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見(jiàn)表1。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jì)
3 實(shí)證結(jié)果分析
3.1 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分析
表2匯報(bào)了基準(zhǔn)結(jié)果,第(1)列單獨(dú)考察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回歸系數(shù)在0.01的水平顯著為正;第(2)列及第(3)列分別納入經(jīng)濟(jì)因素及自然因素,糧食生產(chǎn)的回歸系數(shù)有所減小,但依然通過(guò)0.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yàn);第(4)列同時(shí)納入經(jīng)濟(jì)因素及自然因素,糧食生產(chǎn)的回歸系數(shù)進(jìn)一步減小,但依然在0.01的水平顯著為正①需要進(jìn)一步說(shuō)明的是,該文直接以生態(tài)碳匯總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回歸結(jié)果體現(xiàn)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總量的凈效應(yīng),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表明糧食生產(chǎn)的正向碳匯機(jī)制大于負(fù)向碳匯機(jī)制。以上回歸結(jié)果表明,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正向影響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能夠顯著促進(jìn)生態(tài)碳匯增長(zhǎng)。相較于森林和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已有研究對(duì)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碳匯價(jià)值關(guān)注明顯不足[24]。但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是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Zhi等[25]研究發(fā)現(xiàn)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初級(jí)生產(chǎn)力(GPP)和凈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產(chǎn)力(NEP)明顯高于草地和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該文研究結(jié)論進(jìn)一步印證了上述觀點(diǎn),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在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方面發(fā)揮著積極作用。

表2 基準(zhǔn)回歸
就控制變量而言,相關(guān)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與預(yù)期基本一致。第(4)列回歸結(jié)果表明,經(jīng)濟(jì)因素方面,人口總量、財(cái)政支出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對(duì)于生態(tài)碳匯均表現(xiàn)出抑制作用,除人口總量的回歸系數(shù)未通過(guò)顯著性檢驗(yàn)外,財(cái)政支出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回歸系數(shù)均在0.01的水平顯著。表明縣級(jí)政府財(cái)政壓力的增加激勵(lì)其“以地生財(cái)”“以地引財(cái)”,擴(kuò)大土地出讓面積,擠壓綠色植被的生存空間。而第二產(chǎn)業(yè)增加值占比的增加,意味著可能存在高污染、高排放產(chǎn)業(yè)的污染物破壞了綠色植被的生長(zhǎng)環(huán)境,同樣不利于生態(tài)碳匯的實(shí)現(xiàn)。地理因素方面,平均降水、平均日照和平均氣溫對(duì)于生態(tài)碳匯均表現(xiàn)出促進(jìn)作用,除平均氣溫未通過(guò)顯著性檢驗(yàn)外,平均降水和平均日照的回歸系數(shù)均在0.01的水平顯著為正,與已有研究結(jié)果相印證,如王金杰等[26]研究京津冀地區(qū)綠色植被凈初級(jí)生產(chǎn)力的驅(qū)動(dòng)因素,發(fā)現(xiàn)降水與植被凈初級(jí)生產(chǎn)力呈現(xiàn)正向關(guān)聯(lián);王軼虹等[27]研究農(nóng)作物凈初級(jí)生產(chǎn)力的驅(qū)動(dòng)因素,驗(yàn)證了日照對(duì)凈初級(jí)生產(chǎn)力的影響。降水及光照因素的增加,有利于改善當(dāng)?shù)厣鷳B(tài)環(huán)境條件,增加綠色植被覆蓋面積。
3.2 異質(zhì)性回歸結(jié)果分析
(1)耕作制度異質(zhì)性分析:依據(jù)積溫②指某一段時(shí)間內(nèi)逐日平均氣溫≥10℃持續(xù)期間日平均氣溫的總和,即活動(dòng)溫度總和條件,不同地區(qū)所采取的耕作制度存在差異,主要體現(xiàn)為復(fù)種指數(shù)的差異。復(fù)種指數(shù)是指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與耕地面積之比,表示一年內(nèi)單位耕地面積的種植次數(shù)。一般認(rèn)為,積溫增加會(huì)提高復(fù)種指數(shù)、增加收獲次數(shù)。那么耕作制度的差異是否會(huì)改變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呢?為探究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影響的耕作制度異質(zhì)性,該文依據(jù)復(fù)種指數(shù)的分位數(shù)劃分為低、中、高3個(gè)區(qū)間,表3匯報(bào)了分樣本回歸結(jié)果。隨著復(fù)種指數(shù)的提升,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回歸系數(shù)表現(xiàn)為先增加再降低的演變趨勢(shì),即積溫的適度增加有利于發(fā)揮糧食作物的碳匯作用,但當(dāng)積溫跨越某一臨界點(diǎn),反而會(huì)產(chǎn)生反方向的影響。可能的解釋在于,一方面,不同積溫條件下的糧食作物種類(lèi)存在差異,復(fù)種指數(shù)位于高水平及一年三熟的地區(qū)多為水稻種植,相較于小麥、玉米,水稻固碳能力較弱;另一方面,過(guò)高的積溫條件反而不利于糧食作物生長(zhǎng)[28]。鑒于該文主要關(guān)注糧食產(chǎn)量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控制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不再贅述。

表3 復(fù)種指數(shù)異質(zhì)性回歸
(2)區(qū)域異質(zhì)性分析:為進(jìn)一步分析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影響的區(qū)域異質(zhì)性,該文基于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的區(qū)域劃分①東部地區(qū)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qū)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qū)包括內(nèi)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東北地區(qū)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進(jìn)行分樣本回歸。表4匯報(bào)了相關(guān)回歸結(jié)果,第(1)至(4)列回歸結(jié)果表明,不同區(qū)域劃分下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均存在正向影響,且在0.01的水平顯著,再次表明研究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但從系數(shù)值上看,地區(qū)間存在顯著差異。東部及中部地區(qū)顯著高于西部及東北地區(qū)。可能的解釋為,東北及西部地區(qū)森林、草地及濕地等植被類(lèi)型比例較高,開(kāi)荒導(dǎo)致的土地競(jìng)爭(zhēng)程度高于東部及中部地區(qū)。

表4 區(qū)域異質(zhì)性回歸
3.3 穩(wěn)健性檢驗(yàn)
為進(jìn)一步確保研究結(jié)論的穩(wěn)健性,該文通過(guò)考慮非線性影響、替換時(shí)間固定效應(yīng)為時(shí)間趨勢(shì)、對(duì)核心解釋變量取滯后一期、增加控制變量、更換核心解釋變量的方式對(duì)基準(zhǔn)回歸進(jìn)行一系列穩(wěn)健性檢驗(yàn)。首先,為檢驗(yàn)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非線性影響,第(1)列增加了糧食生產(chǎn)的平方項(xiàng),糧食生產(chǎn)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但平方項(xiàng)系數(shù)不顯著,說(shuō)明模型不能拒絕線性影響的原假設(shè)。其次,考慮到技術(shù)等非觀測(cè)因素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第(2)列使用時(shí)間趨勢(shì)變量代替時(shí)間啞變量進(jìn)行回歸,系數(shù)為正且顯著,說(shuō)明在樣本觀測(cè)區(qū)間內(nèi),技術(shù)進(jìn)步能夠有效增加生態(tài)碳匯。第(3)列考慮到生態(tài)碳匯與糧食生產(chǎn)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guān)系,采用糧食生產(chǎn)的滯后一期項(xiàng)進(jìn)行回歸,結(jié)果顯示,滯后一期變量仍然為正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與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保持一致。考慮海拔和地形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影響,第(4)列將平均海拔、平均坡度納入控制變量,糧食生產(chǎn)的系數(shù)在0.01水平顯著為正。第(5)列使用糧食播種面積代替糧食產(chǎn)量作為糧食生產(chǎn)的衡量指標(biāo)。相較于糧食產(chǎn)量,播種面積的變化能夠更為直接反映出土地性質(zhì)的轉(zhuǎn)變。變量系數(shù)及顯著性與基準(zhǔn)模型一致。種植業(yè)播種面積的增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dòng)的提高,有利于增加生態(tài)碳匯,實(shí)現(xiàn)區(qū)域內(nèi)的碳平衡。綜上所述,表5穩(wěn)健性檢驗(yàn)中核心變量的系數(shù)始終為正,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驗(yàn)證了回歸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

表5 穩(wěn)健性檢驗(yàn)回歸
4 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4.1 結(jié)論
該文旨在證明我國(guó)糧食安全政策與碳中和行動(dòng)方案間具有兼容性。首先構(gòu)建糧食生產(chǎn)影響生態(tài)碳匯的分析框架,指出糧食生產(chǎn)同時(shí)存在正向和負(fù)向的雙重碳匯機(jī)制,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凈效應(yīng)取決于雙向影響的疊加。在此基礎(chǔ)上,采用2000—2017年中國(guó)縣級(jí)面板數(shù)據(jù)進(jìn)行實(shí)證檢驗(yàn),主要結(jié)論如下。
(1)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表明,在控制縣域固定效應(yīng)、時(shí)間固定效應(yīng)及可能影響生態(tài)碳匯的經(jīng)濟(jì)因素和自然因素的條件下,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碳匯視角證明我國(guó)糧食安全政策與碳中和行動(dòng)方案間具有兼容性。
(2)耕作制度異質(zhì)性回歸結(jié)果表明,隨著復(fù)種指數(shù)的提升,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的回歸系數(shù)表現(xiàn)為先增加再降低的演變趨勢(shì),即積溫水平的適度增加有利于發(fā)揮糧食作物的碳匯作用,但當(dāng)積溫跨越某一臨界點(diǎn),反而會(huì)產(chǎn)生反方向的影響。
(3)區(qū)域異質(zhì)性回歸結(jié)果表明,不同區(qū)域劃分下,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均表現(xiàn)出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具有明顯的區(qū)域異質(zhì)性。相較于西部和東北地區(qū),東部及中部地區(qū)糧食生產(chǎn)的碳匯效應(yīng)更大。
(4)穩(wěn)健性檢驗(yàn)回歸結(jié)果表明,通過(guò)考慮非線性影響、替換時(shí)間固定效應(yīng)為時(shí)間趨勢(shì)、對(duì)核心解釋變量取滯后一期、增加控制變量、更換核心解釋變量的方式對(duì)基準(zhǔn)回歸進(jìn)行一系列穩(wěn)健性檢驗(yàn),糧食生產(chǎn)對(duì)生態(tài)碳匯仍保持顯著的正向影響。
4.2 政策建議
(1)碳中和背景下糧食生產(chǎn)轉(zhuǎn)型需要從碳源和碳匯兩個(gè)方面著手。僅僅關(guān)注糧食生產(chǎn)的碳源屬性,忽視其碳匯屬性,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碳減排,可能危及糧食安全。應(yīng)明確糧食安全與碳中和不存在政策優(yōu)先序的權(quán)衡,在已有減排方案的基礎(chǔ)上補(bǔ)充增匯舉措,在確保糧食穩(wěn)定供應(yīng)的同時(shí),提高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質(zhì)量和穩(wěn)定性。
(2)糧食生產(chǎn)增匯需要因地制宜,制定差異化、針對(duì)性的增匯方案。一是基于積溫水平采用科學(xué)耕作制度,積極推廣少耕免耕,避免過(guò)度耕作導(dǎo)致土壤有機(jī)質(zhì)下降。二是加強(qiáng)重點(diǎn)地區(qū)生態(tài)系統(tǒng)保護(hù)和修復(fù),西部地區(qū)是生態(tài)環(huán)境脆弱區(qū),應(yīng)提高植被覆蓋率,增強(qiáng)生態(tài)系統(tǒng)韌性;東北地區(qū)是重要生態(tài)功能區(qū),應(yīng)優(yōu)化土地利用結(jié)構(gòu),降低糧食生產(chǎn)對(duì)林地、草地等其他綠色植被的干擾和破壞。
(3)構(gòu)建糧食碳匯補(bǔ)償機(jī)制,提高糧食生產(chǎn)主體參與碳中和行動(dòng)方案的積極性。一是推動(dòng)農(nóng)業(yè)補(bǔ)貼與糧食碳匯掛鉤,對(duì)于采納增匯方案的糧食生產(chǎn)主體,進(jìn)行成本補(bǔ)償、增加補(bǔ)貼。二是推動(dòng)糧食碳匯納入碳匯交易機(jī)制,通過(guò)市場(chǎng)機(jī)制將糧食生產(chǎn)的生態(tài)價(jià)值轉(zhuǎn)化為資產(chǎn)價(jià)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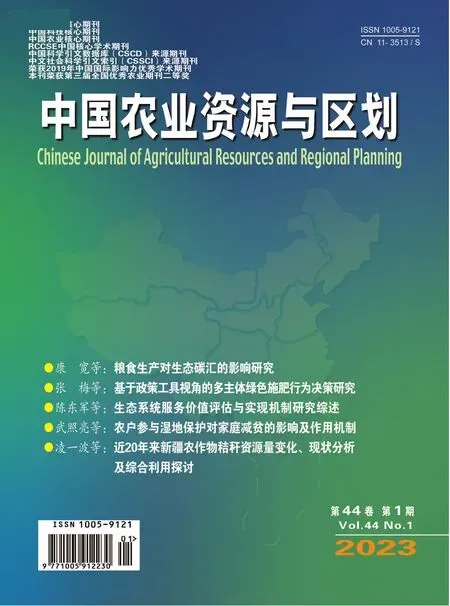 中國(guó)農(nóng)業(yè)資源與區(qū)劃2023年1期
中國(guó)農(nóng)業(yè)資源與區(qū)劃2023年1期
- 中國(guó)農(nóng)業(yè)資源與區(qū)劃的其它文章
- 計(jì)算機(jī)信息技術(shù)賦能鄉(xiāng)村生態(tài)產(chǎn)業(yè)化研究
- 新鄉(xiāng)土主義藝術(shù)設(shè)計(jì)的理論與實(shí)踐
- 堅(jiān)持三產(chǎn)融合發(fā)展 加快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升級(jí)
- 計(jì)算機(jī)與信息技術(shù)在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dòng)中的應(yīng)用
- 推進(jìn)和加強(qiáng)鄉(xiāng)村智慧圖書(shū)館建設(shè)
- 電子信息技術(shù)在智慧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應(yīng)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