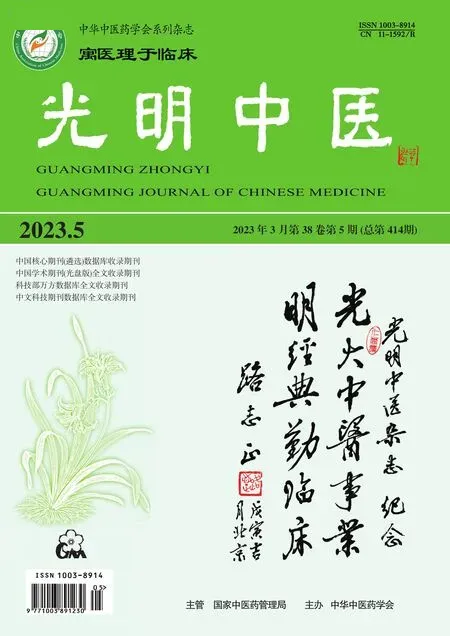基于數據挖掘研究李德新教授治療泄瀉的用藥規律*
張曉邦 王彩霞△ 翁 姣 武 爽
泄瀉是中醫病名,《黃帝內經》中將其稱為“諸泄、腸澼、腸僻、注下”等,是由于臟腑虛弱,情志因素,感受外邪或飲食所傷等引起的大便次數增多,便質溏薄甚或完谷不化,瀉下如水樣的病證,相當于現代西醫學的功能性腹瀉、腸易激綜合征、炎癥性腸病等以腹瀉為主癥的疾病[1]。李德新教授從醫50余載,熟諳經典,學驗俱豐,學貫中西,一生致力于脾胃學說的探究。本研究收集、整理了李德新教授治療泄瀉的醫案,通過古今醫案云平臺的數據挖掘技術對其治療泄瀉的用藥規律進行探求,以期為臨床上治療泄瀉提供新的治療思路。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本研究以2012年7月—2012年12月李德新教授在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名醫巷出診期間,收集的診斷為“泄瀉”的病歷掃描件和從中國知網、萬方、維普和校圖書館查閱的李德新教授的“泄瀉”相關醫案作為資料來源。從中篩選出患者資料信息(姓名、性別、年齡)、就診日期、初復診情況和辨證治療(病名診斷、證型診斷、處方用藥)信息完整的醫案,以初診病歷為來源,建立處方用藥數據庫。
1.2 納入標準符合中醫泄瀉診斷標準;醫案記錄完整;使用中藥治療;中藥處方內容完整。
1.3 排除標準未按規定用藥,或資料不全影響療效判斷;與處方有關的藥物組成、藥物劑量等信息不完整。
1.4 方法
1.4.1 數據錄入將上述收集的醫案信息雙人雙次錄入Excel表,并由第三人進行數據核查,以確保數據錄入的準確性。
1.4.2 數據標準化將錄入完成的數據庫導入古今醫案云平臺,通過軟件中的“醫案標準化”對數據庫進行標準化操作,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中醫臨床診療術語》[2](2021年11月版)將證候進行標準化;將處方中少量的藥物別名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3]進行規范,如“焦白術”規范為白術,“云苓”規范為茯苓,“扁豆”規范為白扁豆等。
1.4.3 軟件選擇本研究采用古今醫案云平臺(WEB端)對標準化的數據進行挖掘分析。包括藥物頻次統計、藥物屬性(性味、歸經、功效)、關聯分析、聚類分析、復雜網絡分析等多種算法進行結果分析。
2 結果
2.1 高頻藥物用藥頻次分析共納入295份處方,共涉及藥物129味,用藥共計3531次。中藥使用頻次由高到低排名前20位的藥物,其中排名前5位的藥物分別是炙甘草、白術、茯苓、黨參、黃芪,其使用頻率分別為100.00%、97.97%、92.88%、86.44%、66.78%。見表1。

表1 常用高頻藥物
2.2 用藥功效分析進一步對所用中藥功效進行研究,發現排在前5位的分別為益氣復脈、補脾和胃、燥濕利水、止汗、健脾益氣,其出現的頻次分別為295次、295次、289次、289次、289次。見表2。

表2 用藥功效分析(前5位)
2.3 用藥藥性分析對所用中藥四氣進行分析,發現藥物藥性以平、溫為多見,分別出現1473次、856次,所占比例分別為41.72%、24.24%。見表3。

表3 用藥藥性分析
2.4 用藥藥味分析對所用中藥五味進行分析,發現甘味、辛味、苦味藥物出現次數最多,分別出現2104次、1074次、985次,所占比例分別為59.59%、30.42%、27.90%。見表4。

表4 用藥藥味分析
2.5 用藥歸經分析對所用中藥歸經進行分析,發現藥物歸經主要以脾經、肺經、胃經為主,分別出現2293次、1739次、1376次,所占比例分別為64.94%、49.25%、38.97%。見表5。

表5 用藥歸經分析
2.6 藥物關聯分析對所有處方進行關聯規則分析,設置置信度≥0.5,支持度≥0.6,炙甘草多做調和藥使用,在關聯分析時進行剔除,結果得出12條關聯規則,按照支持度高低進行降序排列,以“白術—茯苓”這一藥對出現頻次最高,其次是“白術—黨參”“茯苓—黨參”等。見表6。

表6 藥物關聯分析
2.7 藥物聚類分析對所有使用頻次≥50的中藥進行聚類分析,距離類型為歐式距離,聚類方法為最長距離法,以歐式距離≥12進行分組,可得到5組核心聚類群。第1組:黃芪—柴胡—黨參—茯苓—炙甘草—白術;第2組:山藥—山萸肉;第3組:葛根—肉豆蔻—訶子;第4組:五味子—芡實—升麻—烏梅;第5組:雞內金—蓮子—白扁豆—干姜—陳皮。見圖4。

圖4 中藥聚類分析樹狀圖
2.8 復雜網絡分析通過古今醫案云平臺進行復雜網絡分析,將邊權重設置為60,對藥物進行過濾,提取治療泄瀉的19味核心中藥,具體為白術、炙甘草、茯苓、黨參、黃芪、柴胡、山藥、肉豆蔻、訶子、葛根、雞內金、蓮子、五味子、山萸肉、芡實、升麻、干姜、陳皮、白扁豆。見圖5。

圖5 復雜網絡分析圖
3 討論
泄瀉之為病,病位主要在腸,其主病之臟責之于脾,與肝、腎兩臟也密切相關。《景岳全書》曰:“泄瀉之本,無不由于脾胃”。脾胃虛弱,脾胃功能失健,不能正常運化水液,清濁不分,水谷并走大腸,從而發為泄瀉;肝主疏泄,若肝郁氣滯,情志不暢,從而肝失疏泄,橫逆犯脾,致使肝脾不和,亦會導致泄瀉;腎陽為命門之火,若腎陽虛衰,火不暖土,脾失溫煦,則腸寒而泄。李德新教授認為引起泄瀉的主要病因有感受外邪,飲食所傷,情志失調,臟腑虛弱等,但均是脾胃運化功能障礙而引起的[4]。
古今醫案云平臺是由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信息研究所研發的中醫藥數據挖掘軟件,具有多種數據分析方法,可對醫案數據進行多維度的分析探索,是名老中醫經驗傳承的優秀平臺[5]。
本研究頻數統計結果顯示,李德新教授治療泄瀉的高頻用藥包括炙甘草、白術、茯苓、黨參、黃芪、柴胡、山藥、肉豆蔻、訶子、葛根等,皆為健脾益氣,收斂固澀之類,兼有升陽止瀉之品。其中炙甘草的使用頻次最高,炙甘草性甘、平,可補脾和胃,益氣復脈,《雷公炮制藥性解》提到:“炙則健脾胃而和中”,除補脾益氣之功以外,亦起到調和方中諸藥之效。頻次排在第2位的是健脾益氣藥白術,其使用頻率高達97.97%,相關研究表明白術水煎液及多糖對腹瀉有良好的緩解作用,能夠調節脾虛泄瀉型大鼠的腸道菌群,且麩炒后止瀉作用更佳[6]。白術味苦、甘,性溫,有補氣健脾、燥濕利水、止汗、安胎的功效,《醫學啟源》云:“除濕益燥,和中益氣,溫中,去脾胃中濕,除胃熱,強脾胃……止咳,安胎”。李德新教授認為補脾重在運脾,純用補益,反使脾胃呆滯不運,白術可健脾助運兼燥濕利水,是為治療泄瀉之要藥。頻次排在第3位的是茯苓,茯苓利水滲濕,健脾寧心,《神農本草精讀》有云:“茯苓氣平入肺,味甘入脾,肺能通調,脾能轉輸,其功在于利小便一語”。茯苓淡滲利濕之功,可使腸中水液通過小便排出,從而達到止瀉的療效,現代研究發現茯苓的利尿作用是通過茯苓素的醛固醇受體拮抗作用,從而促進機體水液的代謝[7]。岳上賽等[8]認為茯苓與健脾益氣類藥物同用,寓通于補,補而不滯,乃補滲兼施之體現,使水氣得利,水道自通。
通過藥物屬性分析可知,李德新教授治療心悸藥物的四氣以平、溫為主,五味以甘、辛、苦為主,甘味可以緩急,補虛,補益后天脾胃;辛味能起到發散、行氣、行血的作用,若水濕、飲食阻于腸中或濕熱蘊結,腸絡受損引起的泄瀉,宜兼顧行氣活血,以達行氣導滯,行血則便膿自愈之效;苦味能泄、能燥、能堅,泄瀉日久必傷人體陰液,苦能燥濕,又能堅陰。藥物歸經統計結果顯示,藥物歸脾經者最多,其次是肺經、胃經,其他臟腑也有所涉及。泄瀉無論由于外感、情志或是臟腑虛弱,其最終均是歸咎于脾病濕勝,脾胃運化失調,以致腸道不能分清泌濁,傳導功能失司。藥物功效以補脾、益氣為主要,其次是燥濕利水之類,多選用白術、茯苓、黨參、黃芪等,補中有瀉,兼顧利水燥濕。《諸病源候論·泄瀉源流》中就提到“是泄雖有風、寒、熱、虛之不同,要未有不源于濕者”。《沈氏尊生書》也有云:“泄瀉脾病也,脾受濕而不能滲泄,致水入大腸而成泄瀉”。李德新教授認為泄瀉多是由于本虛標實或虛實夾雜,脾虛為本虛,濕盛為標實,往往二者相兼致病,互為因果,《醫宗必讀·泄瀉門》中就有“泄皆成于土濕,濕皆本于脾虛”之說。故治療時應標本兼顧,健脾益氣,運脾化濕雙管齊下。
通過關聯規則分析結果可得,臨床治療泄瀉用藥時應注重白術、茯苓、黨參、黃芪、柴胡等藥物之間的配伍應用,反映出李德新教授治療泄瀉多以健脾益氣,利水燥濕,兼顧升提氣機為大法。李德新教授認為久瀉之患者,其脾氣必傷,以致中氣下陷,若一味補益效果并不明顯,應佐以升提之品,鼓舞脾胃陽氣上升,恢復中焦氣機之升降,黃芪、柴胡共同配伍,其藥性趨上,能有效地升提脾胃之氣。
通過聚類分析可將高頻藥物分為5組,第1組:黃芪-柴胡-黨參-茯苓-炙甘草-白術,主要是健脾益氣,燥濕利水之類,取四君子湯之義,調補后天之本,又兼顧濕勝之標;《素問·氣交變大論》有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柴胡、黃芪又可鼓舞脾胃陽氣上升,使清氣上升,濁氣下行,從而止瀉。第2組:山藥-山萸肉,山萸肉補益肝腎,收斂固澀;山藥健脾,補肺,固腎,益精,《本草綱目》有云:“益腎氣,健脾胃,止泄痢,化痰涎,潤皮毛”。第3組:葛根—肉豆蔻—訶子,葛根升陽止瀉;肉豆蔻溫中行氣,澀腸止瀉;訶子澀腸止瀉,為治療久瀉之要藥。第4組:五味子—芡實—升麻—烏梅;五味子收斂固澀,益氣生津;烏梅斂肺,澀腸,生津;芡實補脾止瀉;升麻可升舉陽氣,為治療久瀉中氣下陷的常用藥。第5組:雞內金—蓮子—白扁豆—干姜-陳皮,可再細分為3類,第1類:雞內金健胃消食,可治療食積腸道引起的泄瀉;第2類:蓮子補脾止瀉,白扁豆健脾化濕和中,陳皮理氣健脾,燥濕化痰,三者常用于脾虛濕盛之泄瀉;第3類:干姜溫中散寒,取其辛溫之性以療虛寒,用于中臟虛寒之泄瀉。
通過復雜網絡分析,得出核心藥物組合為白術、炙甘草、茯苓、黨參、黃芪、柴胡、山藥、肉豆蔻、訶子、葛根、雞內金、蓮子、五味子、山萸肉、芡實、升麻、干姜、陳皮、白扁豆,可認為是補中益氣湯合參苓白術散加減化裁而來,共奏健脾益氣、升陽固澀、滲濕止瀉之功,充分體現了李德新教授在泄瀉的臨證治療中“補脾重在健脾,治泄善用升提”的遣方思路。相關研究發現參苓白術散具有調節胃腸運動、修復胃腸黏膜、調節腸道菌群平衡及增強免疫的功能,能較好地治療腸易激綜合征[9]。補中益氣湯是益氣升陽法的代表方, 臨床上對脾虛泄瀉有良好的療效,相關實驗表明其可以通過提高SGLT1蛋白的表達, 促進p38MAPK/Ezrin通路中蛋白的磷酸化從而降低實驗大鼠的腹瀉指數,亦可促進脾虛泄瀉大鼠小腸黏膜損傷的修復,上調SGLT1、GLUT2、NHE3 mRNA表達,從而促進葡萄糖及水、鈉的吸收[10,11]。
4 結論
綜上,本研究借助古今醫案云平臺,對李德新教授治療泄瀉的295則醫案進行標準化處理,通過數據挖掘方法對其進行了藥物頻次、藥性、藥味及歸經頻次、關聯規則、聚類分析和復雜網絡分析,初步發現李德新教授治療泄瀉的醫案中,高頻藥物有炙甘草、白術、茯苓、黨參、黃芪、柴胡、山藥、肉豆蔻、訶子、葛根等。藥物屬性四氣以平、溫為主,五味以甘、辛、苦為主,歸經以脾、肺、胃經為多,功效以補脾、益氣為主要,其次是燥濕利水。處方中常用藥對有“白術—茯苓”“白術-黨參”“茯苓-黨參”等。核心藥物組合為白術、炙甘草、茯苓、黨參、黃芪、柴胡、山藥、肉豆蔻、訶子、葛根、雞內金、蓮子、五味子、山萸肉、芡實、升麻、干姜、陳皮、白扁豆,可認為是補中益氣湯合參苓白術散加減化裁而來。李德新教授治療泄瀉以健脾益氣,燥濕利水,兼顧升提為主,具有“補脾重在健脾,治泄善用升提”的治療特點,可為臨床上中醫藥治療泄瀉提供一定的借鑒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