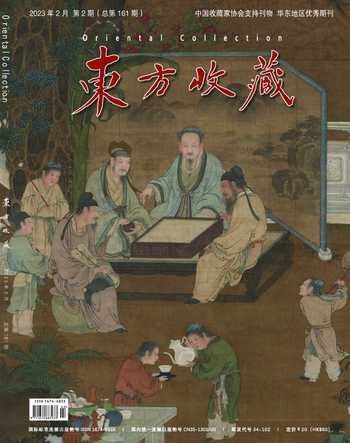民俗文物研究:美美與共的民族嬰兒搖籃
摘要:民俗文物是博物館藏品中常見的藏品類別之一,也是與觀眾們時代距離、心理距離最近的一類文物,優秀的民俗類陳列展覽極易引發觀眾的觀展共鳴。本文選取的嬰兒搖籃就屬于這類民俗文物,它的使用和收藏年代并不久遠,卻十分具有代表性。本文重點講述內蒙古東部地區在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間常用的嬰兒搖籃,它凝聚了至少三代人的兒時記憶。搖籃是指用竹、木或者其他材質制作而成的哄嬰兒入睡的實物,也稱搖車、搖床、睡車,或稱“悠車子”,其在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地區使用較為普遍,無論是漢族、蒙古族或者其他少數民族基本都有使用,這也正是各個民族之間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同時,各少數民族的搖車又呈現出較為獨特的文化特征。有的嬰兒搖車造型簡單樸素,主要體現了實用功能;而有的搖車在具備基本使用功能的同時,還融入了不同的制作工藝,兼具審美性。
關鍵詞:民俗文物;嬰兒搖籃;文化交融;民族融合
引言
隨著博物館事業不斷推進發展,各個博物館藏品也漸趨豐富,涵蓋面十分廣泛。其中,有一類文物被統稱為民俗文物,既包括珍貴的古代民俗器物,也包括距今較近的民間使用廣泛、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實用器物,這類文物在地市級和旗縣級博物館中收藏更多一些。博物館是歷史的保存者和記錄者,這個“歷史”并不是簡單的時空概念,那些能夠反映社會變遷、文化交融、城市發展關鍵節點、具有典型性文化內涵的民俗實物,即便時間還不夠久遠,也應該被重視和征集到博物館中來。首先,這類文物在陳列展覽中更容易引發廣大觀眾的強烈共鳴,更多的人熟悉它們甚至親自使用過,如此便減少了觀眾與展覽的距離感;其次,這類實物年代較近、保存難度較小且存世數量相對較大,更易于博物館進行征集、保管和研究。本文所選取的研究對象——嬰兒搖車應屬于上述系列,筆者主要探討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地區博物館館藏嬰兒搖車,它們凝聚著至少三代人的兒時記憶。
提及“搖籃”一詞,其一是指用竹、木或者其他材質制作而成的哄嬰兒入睡的實物,也稱搖車、搖床、睡車,或稱“悠車子”;其二是指詞匯的衍生意義,多指人在青年時代的成長環境或者某一文化、某一運動的發源地。明代李詡《戒庵老人漫筆·搖籃》中記載:“今人眠小兒竹籃,名搖籃。郭晟《家塾事親》曰:‘古人制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蓋搖車即搖籃。”清代學者、詩人屈大均在《哭殤女悅·其三》中寫道“姜酒香難已,方收滿月筵。家人將錦剪,鄰女把珠穿。囪髻寒難戴,搖籃煖尚懸。無端來誑我,孩笑在堂前。”清代趙翼《舟行》中也提及,“笑比搖籃引兒睡,老夫奇訣得還童。”本文所談及的搖籃,僅指嬰兒搖車實物,各個地區對之稱謂不同,但都是指嬰兒一兩歲內使用的臥睡工具,文字記載中多統稱“臥具”。
嬰兒搖籃在全國各地都有使用,材質和樣式也不盡相同。圖1為新疆塔城地區烏蘇市九間樓鄉保留的一張搖床,已陪伴4個民族的27個嬰兒進入夢鄉。照片中的海拉提·托依百克在給女兒講搖床的故事。一張搖籃承載和連接著幾個民族之間的深厚情誼,其從樣式上看應屬于哈薩克族育兒工具。[1]
筆者一直生活在內蒙古自治區,它是跨越經度最多的省份,東西部地區在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差異性,搖車這一嬰兒臥具在內蒙古西部地區基本看不到,而在東部地區卻較為普遍,無論是漢族、蒙古族或者其他少數民族基本都有使用,這也正是各個民族之間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同時,各少數民族的搖車又呈現出較為獨特的文化特征。[2]
一、質樸的鄉味兒搖籃
筆者小時候常用的搖車一般長約1米、寬約0.5米,搖車底板多用松木、榆木或柳木(諧音“留”)制作而成,整體呈長方形,頂部略寬,且鉆有兩孔,用以插立車弓(圖2)。車弓亦多為木制,弓處可遮蓋包布,也稱為頭襯,置于頭部背面,包于車弓處,多為半圓形,作防風保暖之用。比較講究的家庭做頭襯時,還通過刺繡或剪貼等技法繪制吉祥圖案或文字,除了美觀外,還取吉祥、康樂、平安之意。搖車底板長邊的兩側鉆孔5對,用于穿帶綁繩來固定嬰兒。那個時代的老人們大都認為通過搖車綁繩的約束,會使得嬰兒的腿部更直,而現在的人們更提倡讓嬰兒自由伸展。搖車底板的背面有兩個高四五厘米的弧形木板,一般頂部的弧形木板高度略高,這樣可以使得嬰兒躺著的時候頭部高度略高于腳部,舒適感更強,更為重要的作用在于利用弧度可使搖車左右搖擺蕩漾,便于嬰兒入睡。在搖車底板之上,還墊有三四厘米厚的裝有蕎麥殼的褥子,隨形且清涼,地方俗語稱之“炕口袋”。
二、內蒙古東部地區博物館藏嬰兒搖籃
筆者了解到,類似上述的搖籃形態在內蒙古東部地區包括赤峰市、通遼市、興安盟和呼倫貝爾市較為多見,現居住或曾經居住在那里的人們對其知之較多,甚至很多人小時候都用過。在這些地區的博物館里都收藏有實物,它們形態各不相同,制作工藝也有一定差異,多數在炕上或床上搖擺使用,便于看護嬰兒和哄其入睡。
圖3所示搖籃現收藏于霍林郭勒市博物館,木質,長100、寬40厘米,整體呈長方形,上寬下窄,頭高腳低,周幫較高,周幫兩側各留有三個較大的長方形穿孔,用于穿帶綁繩,可能也為了增加搖籃整體的透氣性,同時躺在搖籃里的嬰兒視野也更為寬闊,所以孔隙較大。搖籃底部上下各有一弧形木板,且頭部位的弧形木板略高,這樣在搖籃搖擺蕩漾時嬰兒更為舒適。從整體制作樣式看,各個構件的連接方式類似傳統的榫卯結構工藝;從使用方式看,應不屬于吊起來使用的,而是放置于平面之上使用的。
圖4所示搖籃收藏于興安盟科爾沁右翼中旗博物館,長104、寬37厘米,兩側高度分別為24、54厘米。木質,搖籃整體涂刷棕色油漆,周幫為雙層橫梁,其上繪制二方連續菱形套連紋及如意組合圖案。搖籃底部上下也各有一高低不同的弧形木板。搖籃頂部裝有大紅布的半圓形頭襯,搖籃內鋪棉褥子及綁帶,有長方體式的蕎麥皮枕頭。這是一個很完整的搖籃形式,頗具典型性。
菱形圖案應用較為廣泛,新石器時代菱形紋彩陶罐是我們如今所見較早的帶有菱形圖案的器物。經考古發現,早期的絲織物上也多有菱形圖案或云雷紋圖案,它是我國出現較早且使用延續時間較長的一種幾何紋圖案,它最早見于新石器時代。據專家考證,菱形紋由三角紋衍生而來,也有專家認為起源于甲骨文的“井”字,或者起源于“琮”的橫切面。[3]
圖5所示搖籃也收藏于興安盟科爾沁右翼中旗博物館,長104、寬34、高15厘米。其樣式與圖4大同小異,只是周幫為單層,沒有任何裝飾紋樣,未見涂刷油漆顏料,也可能是經過長期使用與磨損,導致所刷清油脫落或消失。整體而言,此搖籃制作更為簡易,只保留了搖籃最本質的使用屬性,這可能代表著最普通的人家最樸素的物件使用風格。
三、達斡爾族搖籃
提及搖籃,尤其是內蒙古東部地區的達斡爾族搖籃可圈可點。達斡爾族有著較為久遠的搖籃應用歷史,2007年,達斡爾族搖籃(民俗)被列入第一批內蒙古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達斡爾族主要分布于內蒙古自治區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縣、黑龍江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達斡爾族區一帶。達斡爾族搖籃最早的使用方式為懸掛式[4],“搖籃”一詞在達斡爾語中稱為“達日德”。早期的達斡爾族搖籃多選用輕便耐用的樺樹皮制作而成,現存較多的達斡爾族搖籃多由稠李木或柳木制作而成,在搖籃的頭部背面也設有頭襯,有的還裝飾有圖案紋飾,象征祥瑞。[5]
圖6所示搖籃現收藏于達斡爾民族博物館,制作精美。搖籃長約1米,整體呈半躺式,上下兩端為U形,周幫高約60厘米,且上下均繪有圖案,頭部周幫側面繪有耳朵形狀的云卷紋,也稱“齊克·依勒嘎”。圖案下方兩側掛有兩串串珠。搖車頂部也有一弧形柳條車弓,可用于遮蓋紗布、防止蚊蟲。此外,還配有兩個掛鉤,也頗具特色,結實而美觀,可將搖籃吊起來使用。
達斡爾族搖籃的頭襯相當講究,大致分三種:一是剪刻圖案,在頭襯鹿皮上剪刻成由下向上升騰的蘑菇狀云卷紋,底襯天藍、深藍色布,并在蘑菇狀云卷紋中鏤空幾個有規則的三角形、菱形小孔,小孔里襯以紅、黃、藍色布塊,醒目美觀。二是刺繡圖案,將鹿皮中間挖出半圓形洞,使布襯露出,在其上縫繡各種圖案。刺繡圖案以花草為主,花瓣由下而上由深紅漸為桃紅、粉紅等,呈現層次,富有立體感。三是剪貼圖案,用鹿皮或黑、紅色大絨布剪出各種圖案貼在頭襯上。圖案中間有“福”“喜”等圓形漢字或“卍”形、蝙蝠的對稱圓形圖案。這些圖案下邊兩側,又有底角圖案,有的是兩只蝙蝠,有的是云卷紋等。[6]
圖7所示為達斡爾搖籃較為多見的一種頭襯樣式,整體圖案講究且美觀,中心為卍字紋,底角兩側為蝴蝶對稱圖案。頭襯下方有短鹿皮條穗樣裝飾,圖8為其下方懸掛的大小不一的獸骨,達斡爾語稱“卡撇勒金庫”,當搖籃搖動時,會發出清脆的碰撞聲,獸骨可能還含有驅邪之意。其中的卍字紋是我國乃至世界上運用都較為普遍的符號,《辭海》載“卍”是“古代的一種符咒、護符或宗教標志”,此標志在古印度、波斯、希臘等國的歷史上均出現過,后逐漸演變為一種吉祥符號,超越原有的宗教意味,多用于表示吉祥如意、萬福萬壽之意。此紋飾在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中出現過,之后的陶器、青銅器以及織錦上都屢見不鮮。
達斡爾族搖籃里孩子所用的鋪墊里包裹的東西也十分講究。在搖籃的最下層鋪墊薄棉褥子,頭部枕蕎麥皮枕頭,薄棉褥子上放用薄樺皮做的類似簸箕的尿墊,達斡爾語稱“綽闊其”;上面再鋪蕎麥皮的布袋褥子,其上放包裹孩子的大方布,達斡爾語稱“訥日刻”,用約四寸寬的雙層長布包裹孩子的手,用菱形二尺長的方布包裹孩子的腿腳。最后,蓋上繡有花鳥圖案的長條小棉被,用一根幾尺長的鹿皮條穿搖籃底板上的五個皮條套,把孩子捆在搖籃里。[7]
結語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較為傳統的嬰兒搖籃已漸趨退出人們的視野,還在使用的更是少之又少,取而代之的是更為舒適的甚至電動化的嬰兒搖車了。但這些傳統的搖籃不僅僅承載著幾代人的童年記憶,體現著手工匠人的勤勞智慧,也聯通著各個家庭乃至民族間的深情厚誼,更蘊含了中華民族繁榮而多樣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精神。搖籃雖小,但其包含的文化內涵卻在現有的搖籃實物中得以體現和傳承,這也是文物保護傳承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方曉陽,徐偉,詹先旭,陳昌華,唐先良.基于傳統育兒民俗的家具研究[J].家具,2018,39(05):26-30.
[2]楊洪琦.搖籃 生命最初的承載[J].今日遼寧,2009(02):92-93.
[3]王娟.漢畫像石菱形類紋樣衍變考釋[J].四川文物,2015(03):60-67+82.
[4]劉玉林,張乘風.兒童家具——“搖籃”的演變分析研究[J].家具與室內裝飾,2019(04):28-29.
[5]馬晴雯,王瑞華.達斡爾族傳統搖籃探索與傳承[J].收藏與投資,2022,13(02):174-176.
[6][7]毅松.達斡爾族搖籃的文化特征[J].黑龍江民族叢刊,1992(01):99-102.
作者簡介:
吳紅波(1985—),女,蒙古族,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人。碩士研究生,呼和浩特博物院文博館員,研究方向:文物與博物館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