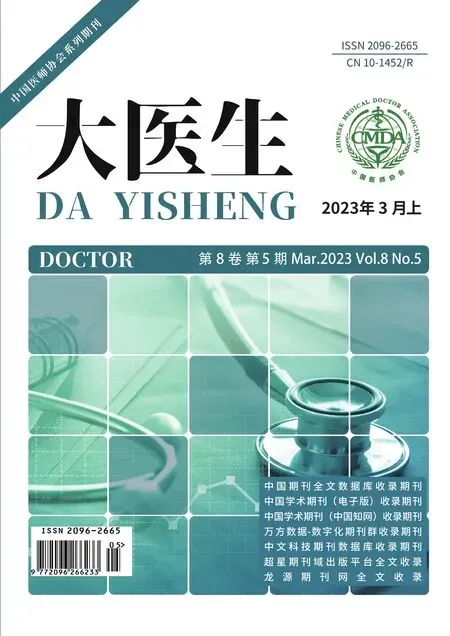椎基底動脈延長擴張癥伴急性卒中預后的相關因素研究
景 良,許學杰,舒 艷,羅 軍
(四川綿陽四〇四醫院神經內科,四川 綿陽 621000)
椎基底動脈延長擴張癥(vertebrobasilar dolichoectasia,VBD)以椎- 基底動脈延長、擴張及扭曲為主要病理特點。目前臨床有關VBD 流行病學仍缺乏大規模專項報道,但VBD 可引起缺血性卒中等腦血管疾病,預后較差,因而備受臨床關注[1-2]。近年來已有關于VBD 臨床特征的相關報道顯示,VBD 患者較非VBD 患者更易發生后循環梗死和神經功能缺損,預后較差[3]。因而,對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不良預后相關因素進行預防性干預,有助于降低不良預后風險。但臨床有關不良預后相關因素的報道仍較為少見,早期干預方案仍有待提高和優化[4]。本研究選取合并急性卒中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探討不良預后的影響因素,供臨床參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回顧性分析2017 年5 月至2022 年5 月四川綿陽四〇四醫院收治的75 例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預后不同將75 例患者分為預后不良組[16 例,改良Rankin 量表(mRS)評分>3 分] 和預后良好組(59 例,mRS 評分≤3 分)。預后不良組患者中男性10 例,女性6 例;年齡38~73 歲,平均年齡(60.47±10.38)歲;身體質量指數(BMI)19~26 kg/m2,平均BMI(22.56±2.19)kg/m2;基礎疾病:高血壓12 例,糖尿病8 例,冠心病9 例。預后良好組患者中男性37 例,女性22 例;年齡40~75 歲,平均年齡(61.06±12.63)歲;BMI 18~26 kg/m2,平均BMI(22.09±2.34)kg/m2;基礎疾病:高血壓52 例,糖尿病30 例,冠心病41 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四川綿陽四〇四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納入標準:①符合《血脂相關性心血管剩留風險控制的中國專家共識》[5]中VBD 伴急性卒中的診斷標準,均經DSA和CTA 檢查確診;②見基底動脈分叉高度或基底動脈位置偏移≥2 級,且基底動脈直徑≥4.5 mm;③年齡≥18 歲;④均在四川綿陽四〇四醫院接受規范溶栓治療;⑤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合并再生障礙性貧血、白細胞減少癥、血友病及淋巴瘤等血液系統疾病者;②合并惡性腫瘤者、嚴重感染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者;③合并先天性心臟病或凝血功能障礙者;④妊娠期或哺乳期患者。
1.2 研究方法以mRS 評分>3 分為不良預后[6]。記錄入院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評分和梗死部位[7],比較不同預后患者發病至入院時間、發病至再通時間。采用彩色超聲儀(德國西門子,型號:ACUSONSC2000)進行檢查,檢查時患者側臥,探頭置于枕大孔窗口,測量椎動脈收縮期峰值流速,儀器分析得出阻力指數(RI)及搏動指數(PI),以椎基底動脈頂端和匯合部的連接線為基線,以基底動脈中1/3 處為基底動脈直徑測量點,測量記錄基底動脈直徑。在入院時采集患者空腹肘靜脈血3 mL,采用離心機(中科中佳,型號:KDC2046)以2 000 r/min 離心10 min,采用酶循環法檢測血漿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采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貝克曼,型號:5800)檢測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水平。
1.3 觀察指標①比較兩組患者臨床特征指標水平(梗死部位、NIHSS 評分、發病至入院時間、發病至再通時間)和實驗室檢測指標水平(基底動脈直徑、LDL-C、HDL-C、Hcy、RI、PI 及收縮期峰值流速)。②分析影響患者不良預后的相關因素。
1.4 統計學分析采用SPSS 20.0 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行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組間比較行χ2檢驗;預后相關因素分析采用Cox 風險模型分析。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影響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預后的單因素分析發病后90 d 內mRS 評分>3 分者16 例,不良預后發生率為21.33%。預后不良組患者NIHSS 評分顯著高于預后良好組,發病至入院時間、發病至再通時間較預后良好組顯著延長,基底動脈直徑長于預后良好組,血漿Hcy、椎動脈RI 及PI 均高于預后良好組,收縮期峰值流速低于預后良好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兩組患者梗死部位、LDL-C、HDL-C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影響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預后的單因素分析
2.2 影響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預后的多因素Logistic 分析將可能影響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預后的相關因素以原值納入Cox 風險回歸模型,結果顯示NIHSS 評分高、發病至入院時間長、發病至再通時間長、Hcy 水平高是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椎動脈收縮期峰值流速高是不良預后的保護因素(P<0.05),見表2。

表2 影響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預后的多因素Logistic 分析
3 討論
VBD 發病機制復雜,涉及機體退行性變化、免疫及感染等多種因素。動脈硬化在VBD病理進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動脈粥樣硬化可損害椎-基底動脈血管彈性纖維,成為VBD 的誘因。另一方面,VBD 發生后血管走形迂曲,血液流速降低,使脂質進一步沉積,進而加速血管硬化[8]。對于VBD 伴急性卒中的患者,若椎動脈收縮期峰值流速異常減緩,不僅可造成脂質沉積,加快動脈硬化,還可引起血管內皮細胞功能紊亂,增加血栓事件風險[9]。本研究也顯示收縮期峰值流速是不良預后的保護因素,提示對于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動態監測收縮期血流峰值,積極進行抗凝治療將有助于改善患者預后。另外,本研究還證實血漿Hcy 水平也是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不良預后的高危獨立因素,這與VBD 患者血管硬化程度一致。Shang 等[10]還指出血漿Hcy 每增加5 μmol/L,卒中峰值增加59%,也說明Hcy 與VBD 患者病情相關。Hcy 可介導氧自由基的合成,促進脂質在血管壁沉積,破壞血管內皮功能,促進血管平滑肌細胞增生,加快動脈硬化進程。有研究還指出,Hcy 異常升高具有細胞毒性作用,促進血栓素A2 分泌,成為短期內再次卒中的誘因[11-12]。因而,VBD 伴卒中患者出院后定期檢測血漿Hcy 水平有助于指導臨床進行早期干預,降低致殘和致死率。本研究還發現不同預后患者椎動脈RI 和PI 水平差異顯著,提示血管順應性降低和血流量減少也與不良預后相關。但本研究顯示椎動脈RI 和PI 并非獨立因素,可能與樣本量較小有關。
本研究還顯示,NIHSS 評分是不良預后的獨立因素,這與既往報道一致[13]。NIHSS 評分能客觀反映神經功能缺損狀態,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多可見血管重塑和血管彈性降低,累及腦部微血管和神經元,增加不良預后風險。此外,發病至入院時間、發病至再通時間也是影響患者預后的高危因素,對于急性卒中的溶栓救治,目前臨床多推薦發病6 h內為溶栓治療的最佳時間窗,尤其是在4.5 h 內可保護腦組織細胞,促進神經功能的恢復,使患者獲得良好的生存效益[14]。近年來有學者提出應突破傳統時間窗的限制,根據卒中患者病理生理特點和缺血半暗帶的范圍、時限進行個體化溶栓干預[15],這一方案的實施將顯著改善患者預后,在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的治療中具有廣闊應用前景。
綜上所述,VBD 伴急性卒中患者不良預后發生率較高,其不良預后與NIHSS 評分、發病至入院或再通時間、血漿Hcy 水平及椎動脈收縮期峰值流速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