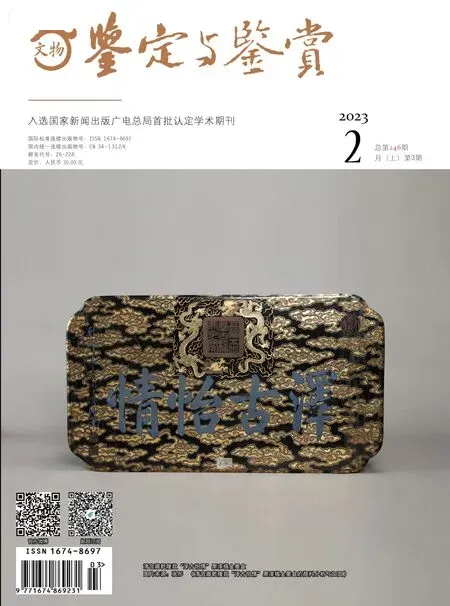集安高句麗四神壁畫墓的分期與討論
白沙平
(吉林大學,吉林 長春 130015)
壁畫墓是高句麗遺存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發現之日起就引起學界的持續廣泛關注。迄今為止發現的高句麗壁畫墓集中分布于我國的集安地區和朝鮮境內的平壤地區,共計123座,其中我國境內共發現高句麗壁畫墓38座①,除桓仁、撫順各有1座外,其余均位于集安地區。關于高句麗壁畫墓的分期研究,學界有諸多觀點,但已經基本形成共識的是高句麗墓室的壁畫主題由早及晚存在由生活風俗、生活風俗與四神、四神的總體演進脈絡②。
相較于朝鮮境內的壁畫古墓,集安的高句麗壁畫墓具有更為明顯的民族風格,并且還有相對完整的四神圖演變序列。目前對于集安高句麗壁畫墓的資料披露與相關研究亦較為充分,也為進一步探討壁畫墓中的四神圖像因素提供了可能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則多自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來探討高句麗壁畫墓中的四神元素,對于集安地區高句麗壁畫墓中的四神圖像的自我特色有所疏忽。
基于此,本文將試圖在前人論述的基礎上,綜合把握集安高句麗壁畫墓的分期與特征,再以四神圖因素為切入點,在重新討論分期的基礎上探討其文化淵源與顯露的民族特色。
1 集安高句麗壁畫墓概況
1.1 集安高句麗壁畫墓的統計與分期研究
現根據所在墓區,將集安市36座高句麗壁畫墓作統計列表如表1所示。

表1 集安市高句麗壁畫墓統計表

續表
由表1可知,集安高句麗壁畫墓的形制大致分為積石墓和封土墓兩大類。關于集安高句麗壁畫墓的分期,學術界一般認為積石墓年代比封土墓要早一些。
李殿福先生在《集安高句麗墓研究》[30]一文中把集安的高句麗壁畫墓分為三期,這一點與20多年前楊泓先生的分期大體相同。他將早期高句麗封土石室壁畫墓的年代定在公元3世紀中葉到4世紀中葉,中期封土石室壁畫墓的年代推定為4世紀中葉到5世紀中葉,晚期封土石室壁畫墓的年代大體上在5世紀中葉到6世紀中葉。
魏存成先生將集安高句麗壁畫墓劃分為了四期:第一期推測為4世紀中葉至5世紀初,壁畫內容以墓主人家內生活、出行、狩獵為主;第二期年代應在5世紀,壁畫中出現大量佛教因素;第三期年代應在5世紀末到6世紀中葉,壁畫內容與第二期大體一樣;第四期墓葬壁畫內容與前期比有了較大變化,墓室四壁四神成為主體,充滿了怪獸、盤龍等恐怖圖像和日月神、牛首人等各種古代傳說以及乘龍駕鳳的眾多伎樂仙人等,時間在6世紀中葉至7世紀初[31]。
2 集安高句麗四神壁畫墓的分期與討論
四神元素作為漢文化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自一開始就出現在深受漢文化影響的高句麗壁畫墓中。在36座集安高句麗壁畫墓中,有9座繪制有四神圖,且分布時間貫穿各個階段。
2.1 集安高句麗四神壁畫墓的分期
一般而言,高句麗古墓的斷代研究主要依據是高句麗古墓的形制結構、高句麗古墓中出土器物的系列研究以及高句麗壁畫內容及墓志等文字資料[32]。
現依據各類墓葬的相對早晚將墓葬內的四神形象列表如表2所示。除表中所列出的信息外,集安高句麗四神壁畫墓在位置上的變化也十分耐人尋味。在公元4世紀末到6世紀初,在舞踴墓等墓葬中的四神圖均繪制在藻井下部第一重頂石或抹角石上,并且形象較為拙樸,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而到了公元6世紀末到7世紀初,四神圖像則繪制在墓室四壁,形象生動,氣勢宏大[34]。

表2 集安高句麗四神壁畫墓中的圖像統計[33]
結合圖表中的演變序列與其位置的變化,集安高句麗四神壁畫墓的發展狀況大致有如下的特點:①就布局來看,四神分布從天井下部移到四壁,占據的篇幅越來越大;②就構成的特點來看,集安早期壁畫墓中的四神圖并不完全,而到了高句麗后期,壁畫墓中的四神圖占據整個壁面,并且構成完整,已然形成了一定的規范;③就繪畫形象與表現手法而言,四神形象歷經了由呆板古樸到生動精美的歷程。集安高句麗壁畫墓中缺少明確的紀年材料,只能通過間接類比方法建立相對年代序列[35]。
以高句麗壁畫墓分期為軸,在討論高句麗四神壁畫墓時,可以將高句麗四神壁畫墓分為三期:
初期(公元4世紀末至5世紀末):四神圖像主要出現在藻井位置,圖像有所缺失。并且形象大多從漢代粉本中所出,自然拙樸,如此時朱雀取自雞等形象。受到畫面位置和篇幅的限制,圖像的繪制筆法較為粗糙[36]。總的來看,這一階段主要是繼承中原粉本為主。
中期(公元5世紀末到6世紀末):四神圖已經從藻井下移到墓室壁上,分布的面積逐漸擴大。這個時期的四神少見缺失,并且在繪畫風格與技法上都走向了更為成熟的階段。
晚期(公元6世紀中葉到7世紀中葉):四神圖已經完全占據了整個墓室壁,有完整的構圖。此時的四神形象更為神化,取自自然生物形象的特色降低,以神秘的色彩和風格取而代之。在繪畫技法上,此時的四神圖線條流暢、繪制精美,加以火焰網紋裝飾,流云襯托,顯得不僅神秘而且莊嚴肅穆。這一階段體現出在不斷吸納漢文化的同時,高句麗人已經做出了自我完善、創造的舉措,將四神元素“本土化”了。
2.2 集安高句麗四神壁畫墓的文化淵源與民族特色
如前所述,早期的集安高句麗壁畫墓中的四神元素明顯是自中原而來。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由于五行學說盛行,四象也被稱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兩漢時期,四神往往是作為祥瑞而被崇拜,并演化成為道教所信奉的神靈,起到保護神的作用[37]。在這樣蘊意深遠的背景之下,高句麗壁畫墓從“形制結構、壁畫內容、繪畫技法、存在時間等方面考察,受到漢晉墓室壁畫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38]。
至中后期,高句麗壁畫墓在營造方法與壁畫風格上都體現出了與中原地區所不同的地域特征。高句麗地處北方石材較多地域,中晚期天然花崗巖的運用,使墓室墻面不再使用中原白堊土,自然也改變了壁畫創作風格與工藝[39]。此外,高句麗后期墓制以單墓室為主,壁畫空間的增加也為大幅四神圖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營造方法的改變不僅帶來了壁畫布局的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高句麗壁畫墓繪畫風格的轉變。到了中晚期,四神圖像充滿了整個墓室四壁,甚至取代了人物風俗圖,這一現象不見于中原地區。不僅如此,中原地區的人們對四神有著正四方的功用認識,但高句麗后期的壁畫墓中,四神僅僅作為一種引導升仙的保佑神,大多數情況下并不處在正四方的位置上。這樣的變化更多反映的是高句麗貴族思想意識的變化,或是當時政局動蕩下人們尋找精神慰藉的一個體現。
3 結語
作為朝鮮半島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高句麗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與中原漢文化始終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對其的研究與討論亦始終是中國學者筆耕不輟之域。文章對于集安高句麗墓葬進行了統計,在綜述先賢們對高句麗墓葬的分期觀點后縮小范圍,著力于壁畫墓的四神圖之上。而后,在對集安高句麗壁畫墓中的四神圖進行分期討論的基礎上,文章嘗試對其的特點、文化淵源等做了一個簡單的梳理,不當之處,懇請指正。
注釋
①[32][38]耿鐵華.高句麗古墓壁畫研究[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
②趙俊杰,馬健.平壤及周邊地區高句麗中期壁畫墓的演變[J].考古,2013(4):83-95,2.
③④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38.
⑤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57.
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61.
⑧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60.
⑨吉林省博物館.吉林輯安五盔墳四號和五號墓清理略記[J].考古,1964(2):59-66,3-7;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五盔墳四號墓[J].考古學報,1984(1):121-136,157-162;《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第59頁記載五盔墳4號墓封土的方形底邊長40米,封土高10米。
⑩吉林省博物館.吉林輯安五盔墳四號和五號墓清理略記[J].考古,1964(2):59-66,3-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59-60.
[11]吉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的兩座高句麗墓[J].考古,1977(2):123-131,151-15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46.
[1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禹山墓區JYM3319號墓發掘報告[C]//劉信君,王卓.中國東北考古與文物研究:《東北史地》考古與文物論文匯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
[13]林至德.集安高句麗壁畫墓的演進及分期[J].東北亞歷史與考古信息,1998(2):87-92.
[14]李殿福.集安洞溝三座壁畫墓[J].考古,1983(4):308-31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112.
[15]p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96.
[17]李殿福.集安洞溝三座壁畫墓[J].考古,1983(4):308-31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84.
[18]李殿福.集安洞溝三座壁畫墓[J].考古,1983(4):308-31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92.
[19]張雪巖.吉林集安東大坡高句麗墓葬發掘簡報[J].考古,1991(1):600-607,675.
[20]u高遠大.維修中發現的兩座高句麗積石石室壁畫墓[J].博物館研究,2000(1):69-70;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98.
[22]高遠大.維修中發現的兩座高句麗積石石室壁畫墓[J].博物館研究,2000(1):69-70;《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第98頁JSM1048只記為大型階壇積石石室墓和相關尺寸,并沒注明墓內有壁畫。
[23]吉林省博物館輯安考古隊.吉林輯安麻線溝1號壁畫墓[J].考古,1964(10):520-528,5-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146.
[24]耿鐵華.高句麗冉牟墓研究[J].高句麗歷史與文化研究,242-25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176.
[25]方起東,劉萱堂.集安下解放第31號高句麗壁畫墓[J].北方文物,2002(3):29-3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176.
[2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176.
[27][28]耿鐵華.高句麗古墓壁畫研究[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55-89.
[29]耿鐵華.高句麗釉陶器的類型與分期[J].考古與文物,2001(3):71-80.
[30]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J].考古學報,1980(2):163-185,263-266.
[31]魏存成.高句麗考古[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74-76.
[33]關于集安高句麗壁畫墓四神圖的繪制情況,參考耿鐵華《高句麗古墓壁畫研究》、魏存成《高句麗考古》。
[34][39]呂光.集安高句麗五盔墳5號墓四神圖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2020.
[35]韋正.將毋同:魏晉南北朝圖像與歷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36]白婧蕓.高句麗壁畫墓四神圖的文化淵源及其發展脈絡[D].長春:吉林大學,2020.
[37]楊峰.高句麗壁畫四神圖像審美淺析[J].東北史地,2014(3):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