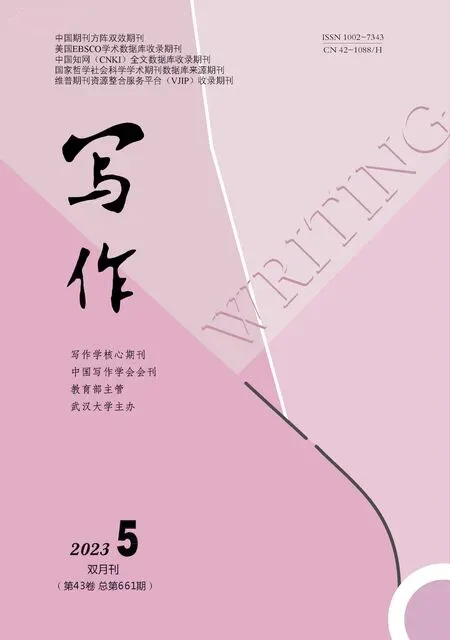“布局”的結構要件、藝術功能和審美原則
——亞里士多德散文寫作理論研究(三)
戴紅賢 沈鈺潔
在古希臘城邦,演說繁榮發展,解釋演說辭寫作方法的修辭學是西方古典散文寫作理論之源①羅念生編:《希臘羅馬散文選》,羅念生、嚴群、王煥生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頁。王煥生在《希臘羅馬散文選》序《古希臘羅馬散文概論》中指出:“當時的散文概念和今天的不完全一樣,散文是針對詩歌而言,指無需講究格律,又是行文如說話的文體,希臘人稱之為logographia,意為‘口語著述’……歷史著述、哲學著作和演說辭是古希臘羅馬散文的三個主要方面,其中演說辭占的地位尤為重要。演說理論實即散文理論。后來隨著文體的發展,散文的種類也逐漸增多,散文的概念和包括的范圍也有所變化,一些新的散文形式不斷出現,為后代散文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布局”是古典修辭學術語,意指演說辭的各個部分應如何安排,是“修辭五藝”之一②[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297-299 頁。“修辭五藝”是指演說者應當擁有開題(invention)、布局(arrangement)、文體(style)、記憶(memory)、表達(delivery)的能力。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主要論述了前面三種,即開題、布局和文體,并在文體部分討論了與表達有關的朗誦藝術。。古希臘早期修辭學著作中論述布局藝術者甚多,不過大多零散、繁復。柏拉圖記載,智者派論述文章結構包括以下內容:首先是序論,即文章的開頭,其功能是“藝術的點綴”;其次是陳述,即交代相關證據;再次是證明或近理③[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頁。朱光潛注:“‘近理’并非‘真理’,是指在某種情況下,某件事可能發生與否,說它發生,是否能自圓其說。”,包括引證和佐證、正駁和附駁、暗諷和側褒側貶等;最后是文章結尾,有復述、總結④[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25頁。。亞里士多德記載,忒俄多洛斯及其弟子把陳述分為“正陳述”“附陳述”“預陳述”,把反駁分為“正反駁”“附反駁”;利鏗尼俄斯的修辭學課本提出“推動法”“離題法”“分支法”等論證①[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355、354、354、372、369、372-373頁。;赫瑪戈拉斯在講完駁斥以后就講離題話,最后講結束語②[古羅馬]西塞羅:《論開題·第一卷》,《西塞羅全集·修辭學》,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頁。。亞里士多德收集古希臘早期修辭學著作,精心考察了每一位作者提出來的規則,用清晰的語言把它們記錄下來,在系統性和簡潔性方面超過了原著,并提出了新的觀點。熟悉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就熟悉了古希臘其他學者的修辭學③[古羅馬]西塞羅:《論開題·第二卷》,《西塞羅全集·修辭學》,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2頁。。
布局藝術,即結構理論,是亞里士多德散文寫作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亞里士多德全面系統地整理早期結構學說,重新闡釋了布局藝術:他針對智者派偏重訴訟演說而忽略政治演說和典禮演說之不足,建構可以涵蓋三種演說類型的通用結構模式,解析如何通過布局藝術來實現吸引與說服,并提出布局藝術的審美原則。
一、說明與證明:布局的結構要件
亞里士多德認為,一篇布局完整的演說必須包含的兩個結構要件是說明(state the subject)和證明(demonstrate the argument),“說明—證明”是適用于所有演說辭的結構模式。他之所以提出這一觀點,是為了修正當時流行的“序論—陳述—或然式證明—結束語”四分法,認為這是一種布局上的飽和狀態,并非通用的結構模式④[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355、354、354、372、369、372-373頁。。早期修辭學主要研究訴訟演說,所提出的結構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于政治演說和典禮演說:并不是所有演說類型都必須具備四分法的各個部分,如陳述是訴訟演說用來陳述案情的必要部分,但典禮演說和政治演說中并不需要陳述,因為這兩種演說中的聽眾已經對背景有所了解⑤[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355、354、354、372、369、372-373頁。。基于這一發現,亞里士多德以說明和證明作為演說的結構要件,提出了通用于三種演說類型的“說明—證明”結構模式。
訴訟演說中,說明是為了陳述案情,證明是為了化解爭論,二者是必不可少的環節。訴訟演說應如何說明,是早期修辭學詳細研究的內容,亞里士多德沒有作過多復述⑥[古羅馬]西塞羅:《論公共演講的理論·第1卷》,《西塞羅全集·修辭學》,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頁。從西塞羅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窺見早期修辭學中陳述學說的相關內容。西塞羅記載,訴訟演說的說明有兩種類型,其一是提供事實并轉向每一個對自身有利的細節,以便贏得勝利;其二是提供顯示對手有罪的事實,從而爭取聽眾的信任。前者著力于辯解事實,后者傾向于影響聽眾。,只是在此基礎之上補充了如何表現演說者美德、如何陳述生動等內容。至于訴訟演說的證明,有四種爭論點,分別是事情的有無、是否造成傷害、事情重大與否和事情正當與否⑦[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355、354、354、372、369、372-373頁。,修辭式推論是最適合用于訴訟演說證明的一種方法。
政治演說中,演說者需要明確提出自己要討論什么,接著可以采取例證法對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張加以闡釋和證明。政治演說要求,如果演說者在說明時涉及了難以讓聽眾認可或相信的內容,則應當立即把問題交由大會審議者審查,以保障政治演說的嚴肅性⑧[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355、354、354、372、369、372-373頁。,這也就反過來要求演說者,要進行事實正確、描述清晰的說明。在證明上,政治演說討論的是未來應當如何做,因此只能以古鑒今,用過去的事作為例子,這就是政治演說的例證法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355、354、354、372、369、372-373頁。。公元前380年伊索格拉底在奧林匹亞集會上發表的《泛希臘集會辭》是一篇布局完整清晰、具有典范性的政治演說:演說者先提出領導權問題,即伊索格拉底認為希波戰爭的領導權應該由雅典和斯巴達平分;然后以既往戰爭為例,證明雅典具有領導海軍的優勢,而斯巴達壓迫城邦不利于爭取希臘民心;最后得出由雅典和斯巴達平分領導戰爭則波斯必敗①羅念生編:《希臘羅馬散文選》,羅念生、嚴群、王煥生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109頁。。政治演說是在公民大會、議事會或其他重要會議上就未來的經濟、軍事、政治、立法等議題展開討論,其性質決定了聽眾往往了解演說的背景和內容。在這種情況下,政治演說可以不需要序論②[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59、367、356、354、382、298、145頁。。
典禮演說中,演說者需要說明主要人物的事跡或主要事件的經過,并通常采用夸張法來證明某人某事是高尚的或有益的。典禮演說的說明應當是斷斷續續的,通過夾敘夾議的手法錯落在證明之間,例如在贊美一個人物時,先介紹一些事實,證明他的勇敢,再介紹另一些事實,證明他的正直;同時,對于著名的人物及其事跡,說明不必過多,點到為止即可③[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59、367、356、354、382、298、145頁。,這樣才能使演說節奏有致、具有吸引力,避免落入冗長無聊。是否需要進一步采用夸張法來突出對某人某事高尚性和有益性的證明,則視該演說所談論的主角或主要事件而定:如果稱贊的英雄、善舉或譴責的罪人、惡行是公認的,則不需要進一步展開證明,反之才需要提供證明。至于典禮演說的序言和結束語,一般來說也是需要的。典禮演說的序言就像音樂的序曲,起到奠定情感基調、引出主題的作用;結束語可以再一次表達本次典禮演說的稱贊或譴責主題,并扼要地重述論證。
總而言之,亞里士多德認為演說者可以根據演說類型和具體場景而酌情取舍演說辭結構中的各個部分,但說明和證明不可或缺,序論、結束語等部分則可靈活調整。說明部分要用適中的節奏和篇幅把本次演說涉及的話題揭示清楚,盡可能減少語言上的過度修飾。證明部分是提供論據和提出結論的完整過程,常常使用修辭式推論、夸張法和例證法來完成。
圍繞“說明—證明”這一通用結構模式,序論、結束語等部分可以在運用得當的情況下發揮錦上添花的作用。序論可以“為后面的內容打開一條路”④[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59、367、356、354、382、298、145頁。,即吸引聽眾注意力、幫助聽眾進入傾聽狀態,也有助于聽眾對演說內容進行記憶⑤[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59、367、356、354、382、298、145頁。;結束語也不是對前文的簡單總結和重復,需要進一步增強邏輯說服、人格說服、情感說服和聽眾記憶⑥[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59、367、356、354、382、298、145頁。。這就涉及布局的藝術功能,即吸引與說服。
二、吸引與說服:布局的藝術功能
亞里士多德認為:“修辭術的整個任務在于影響聽眾的判斷。”⑦[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59、367、356、354、382、298、145頁。吸引并說服聽眾,是演說辭的核心功能。亞里士多德將說服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邏輯說服,它訴諸修辭證明,基于已有的事實進行邏輯推理,從而使聽眾接受自己的觀點;二是人格說服,它訴諸性格影響,根據說話者在受眾心目中的良好形象進行互動,創造出最為合適、有效的修辭人格,讓受眾容易接受自己的觀點;三是情感說服,它訴諸聽眾情感,調動起聽眾的同情心、注意力,讓他們樂意接受說服⑧[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59、367、356、354、382、298、145頁。。這些方法都有助于使人信服。布局藝術的目的,就是從結構的角度提高演說質量、展示演說者品性、激發聽眾情感共鳴。
邏輯說服主要是借助論證,筆者已另文論述,這里著重談談布局藝術的品格說服和情感說服功能。
品格說服的主要辦法是表現別人的惡和自己的善,這種說服貫穿全文。說明部分的品格說服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來進行。直接的方式是說出足以表現演說者美德的話,如:“我總是勸他為人要正直,不要撇下他的兒女。”或者講一些表現對方的邪惡的話,如:“可是他回答道,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能生一些別的兒女。”①[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8頁。該典故出自希羅多德《歷史》第2卷第30段。24萬埃及叛兵逃往埃塞俄比亞,埃及國王追上他們,勸說他們不要撇下他們的妻子兒女,可有兵士反駁說自己到了埃塞俄比亞照樣能另外娶妻生子。間接的方式是通過描寫性語言來暗含褒貶,如“他瞪了我一眼就走了”和“他嗤之以鼻,揮舞著拳頭”就能夠讓聽眾感受到對手的狂狷傲慢②[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9、374、359、382、356-357、359頁。,有助于演說者建立良好的品格形象。證明部分的品格說服往往同修辭式推論的邏輯說服交叉進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品格說服能證明演說者是一個好人、一個品格高尚的人,邏輯說服則更能夠體現演說者在語言和邏輯上的精明;演說者表現出自己是一個有德行的人要比表現出自己說話精明更能彰顯品格③[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9、374、359、382、356-357、359頁。。因此,需要在以邏輯說服為主的證明部分穿插使用品格說服。
品格說服也可以分散在序論、結束語等其他部分。序論部分使用品格說服主要見于典禮演說,即在演說伊始表明演說者本人或他的家族、事業等曾受到稱贊④[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9、374、359、382、356-357、359頁。,這樣,演說者發表的稱贊或譴責才具有說服力。結束語部分可以通過夸張和重申來進一步確立演說者的品格,完成品格說服,即在證明部分確定了事情的性質及其程度后,就可以將事情的性質上升到對方的品性,如指出對方易怒、嫉妒、好斗等,并適當采用比較極端的方式來再一次稱贊自己、譴責對方⑤[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9、374、359、382、356-357、359頁。。這樣,品格說服貫穿整場演說,演說者的良好品質通過恰當的方式確立起來,能夠提升演說的吸引力和說服力。
情感說服主要發力于演說的序論部分。如上文所說,序論的作用是“為后面的內容打開一條路”,吸引聽眾注意力,幫助聽眾進入傾聽狀態,因此在這里最宜影響聽眾的情感,也最應當使用情感說服。
由于三種演說應用場景不同,其序論的作用各有差異,因此進行情感說服的方式也有所分別。典禮演說序論的情感說服主要采取直抒的方式。因為,在公序良俗的制約下,演說者與聽眾之間一般能夠就稱贊或譴責的對象達成一定共識,所以這里的情感說服目的是明確和強化共識。演說者應當在序論部分直接稱贊美德與高尚,譴責惡德與可恥⑥[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9、374、359、382、356-357、359頁。。政治演說序論的情感說服常常采取夸大法或縮小法,往往具有很強的裝飾性和煽動性:一方面,政治演說往往有實在或潛在的“對手”,即持不同意見的政敵,因此需要在演說開頭提及這些不同意見,否則這次政治演說會顯得缺乏目的;另一方面,政治演說的目的是發表意見、獲得公民大會支持,因此當聽眾把某一項政治事務看得過于嚴重或不夠嚴重、不合乎演說者的期望時,就需要在序論部分激起或消除反感,夸大或縮小事情的嚴重性⑦[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9、374、359、382、356-357、359頁。。
訴訟演說的情感說服相對比較復雜。除了要在序論部分影響陪審員和法官的情感,結束語也是影響陪審員是否投定罪票的關鍵時刻。控告方要在序論部分抓住聽眾的普遍情感,盡早贏得共識,并在結束語部分激起聽眾的強烈反感,削弱對手辯護的力量。而辯護方則需要在開始答辯時消除陪審員和法官的反感,并在陳詞結束后、投定罪票之前重申自己的冤屈,喚起聽眾同情⑧[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365頁。亞里士多德在第3卷第15章專門總結了適用于訴訟演說的12種情感說服技巧,其中10種適用于辯護方,2種方法適用于控告方。。試看古希臘時代最經典的訴訟辭之一——呂阿西斯《控告忒翁涅托斯辭》:
在那次的訴訟中,忒翁涅托斯還控告我殺死了我自己的父親。他若是控告我殺死了他自己的父親,我倒可以饒恕他信口開合,認為他是個卑鄙的人,不值半文錢。……但是目前的案件涉及我的父親——我父親是應該受到你們城邦的尊重的——我如果不對說這句話的人進行報復,就會感到羞恥。
我請求你們對忒翁涅托斯投定罪票,你們要考慮到對我來說,再沒有比這件案子更為嚴重的訴訟。我現在雖然是控告他有誹謗罪,但是這次的投票判決卻涉及我被控告有殺父之罪。……請你們記住這些論證,拯救我和我的父親,維護既定的法律和你們發過的誓言。①羅念生編:《希臘羅馬散文選》,羅念生、嚴群、王煥生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9頁。
在這篇控告辭的序論和結束語中,控告者并沒有進行邏輯說服,而是牢牢抓住父子血緣這一基本人倫,反復強調自己之所以控告對方乃是因為對方誹謗自己有殺父之罪,性質極其惡劣,這容易牽動陪審團的普遍情感。在說明和證明當中,一旦控告方指出一點點忒翁涅托斯可能存在誹謗的痕跡,都容易激起陪審團眾怒,認為忒翁涅托斯罔顧人倫,嚴重傷害了呂阿西斯作為兒子的道德聲譽。可見,辯護方或控告方在序論或結束語部分采用情感說服,能夠增強訴訟演說的藝術效果,更好地實現說服目的。
在演說辭的適當位置進行情感說服,不失為站在聽眾角度提升演說吸引力與說服力的高明之舉。一方面,在謀篇布局時,作者要綜合考慮論題的性質、聽眾的特點,從而決定何處進行邏輯說服、何處進行人格說服、何處進行情感說服;另一方面,要想充分實現情感說服,作者必須要研究情感的性質、可能引起情感的刺激類型、不同聽眾的情感傾向性,因此,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第2卷花費了第1—11章的篇幅來分別詳細討論憤怒、溫和、憎恨、恐懼、羞恥、憐憫、羨慕等情感及其激發和抑制方式。然而,在亞里士多德之后的漫長歷史歲月,西方修辭學界還是以研究邏輯說服為主,長期難以走出“在修辭互動中訴諸情感不合法或不盡合法”的陰影;所幸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哲學家、修辭學家們對情感說服又有了新的認識,古希臘修辭學中的情感說服理論開始復興,并成為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情感轉向”的遙遠濫觴②參見劉亞猛:《“情感轉向”與西方修辭研究的自我更新》,《當代修辭學》2022 年第3 期。2005 年和2006 年,美國修辭學者丹尼爾·格羅斯(Daniel M.Gross)先后出版了專題論文集《海德格爾與修辭》(Heidegger and Rhetoric)和研究專著《從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到現代腦科學——一部不為人知的情感研究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Emotion:From Aristotle’s Rhetoric to Modern Brain Science),使得情感說服這一修辭方法開始重新引起廣泛關注。。
三、完整與嚴密:布局的審美原則
為了說清楚散文的結構,亞里士多德將演說辭拆解為若干部分,并詳細論述了各部分的主要內容和說服技巧。但是,從篇章整體而言,亞里士多德又強調各部分之間的聯系與合力,主張整體論、有機論。“整體”和“有機”兩個概念出自《詩學》,亞里士多德主張讓悲劇的每一個情節都成為“整體中的有機部分”,不僅強調作品的體積,也強調作品的安排與秩序③[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頁。。《詩學》討論史詩、悲劇,《修辭學》討論演說辭④[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 頁。《詩學》與《修辭學》是亞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后在呂刻翁學院講學的講稿,兩門課程同期進行,內容不同,但主旨一致、相互補充,且兩部著作記錄成文也幾乎是在同一時期,這使得兩部著作間具有不可忽視的互文性。,但如果細察兩部著作中關于布局的具體內容,會發現無論是敘事文學還是論辯散文,亞里士多德對于布局藝術的訴求都是一致的:“整體”意味著完整,“有機”意味著嚴密。這是散文布局的審美原則。
散文布局的整體論,意為演說辭符合“說明—證明”結構模式,并根據實際需要具備相應的其他部分,內容齊備。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說“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①[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41、43、42頁。。又說:“所謂‘完整’,指事之有頭、有身、有尾。所謂‘頭’,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發生者;所謂‘尾’,恰與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規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無他事繼其后;所謂‘身’,指事之承前啟后者。所以結構完美的布局不能隨便起訖,而必須遵照此處所說的方式。”②[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41、43、42頁。這也就是說,敘事文學追求的“完整”指的是情節要揭示行動內部完整的因果關系。投射到散文中,即指演說辭的立論從一而終,說明部分條件完整,證明部分邏輯一致、能推導出觀點,如果有序論和結束語,則是恰到好處地提供了充實的背景或呼吁。
散文布局的有機論,意為演說辭各部分內容不但齊備,而且各得其所。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對于悲劇各情節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嚴密”原則:“情節既然是行動的摹仿,它所模仿的就只限于一個完整的行動,里面的事件要有緊密的組織,任何部分一經挪動或刪削,就會使整體松動脫節。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無,并不引起顯著的差異,那就不是整體中的有機部分。”③[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41、43、42頁。因此,敘事文學追求的“嚴密”指的是情節之間要發生聯系,對整體敘事形成合力,各部分各在其位、各司其職,缺一不可。而亞里士多德對于散文結構的要求亦如此,他追求演說辭的各個部分都在適當的位置、采用適當的方法實現全面有效的邏輯說服、品格說服和情感說服,缺少任何一個部分都會削弱吸引與說服的藝術功能。
其實,遵循整體論和有機論、追求完整與嚴密,既是修辭術有別于論辯術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亞里士多德在散文文體上具有了篇章意識的重要體現。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開篇明確提出:“修辭術是論辯術的對應物。”④[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143-144頁。修辭術之所以有別于論辯術,是因為前者是“演說的藝術”(tekhne rhetorike),后者是“問答式論辯的藝術”(tekhne dialektike);論辯術通過問答來判斷命題是否真實可靠,修辭術則通過連續的講述來推出結論⑤[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143-144頁。。論辯術的產物是對話體,而修辭術的產物是散文,是一篇篇能夠獨立成篇的演說辭。因此,連續講述的方式、獨立成篇的特征決定了以修辭術為核心的散文必須關注布局,讓前后的講述完整圓滿,無懈可擊。
這一套整體論和有機論貫穿亞里士多德的全部思想,并且可以在柏拉圖那里找到影響的淵源。《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強調“和而不同”,“城邦應該是許多分子的集合,惟有教育才能使它成為團體而達成統一”,而不是“執意趨向劃一”⑥[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57頁。。這與《詩學》《修辭學》中的布局理論異曲同工。此外,羅念生在《詩學》譯注中提示,柏拉圖也曾以“有生命的東西”比喻文章的結構⑦[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41、43、42頁。。《斐德若篇》說:“每篇文章的結構應該像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種身體,有頭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體,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調和。”⑧[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2頁。這與亞里士多德在《詩學》《政治學》等著作中的表述幾乎如出一轍。柏拉圖還為文章寫作制定了兩條法則:“頭一個法則是統觀全體……第二個法則是順自然的關節,把全體剖分成各個部分,卻不要像笨拙的屠宰夫一樣,把任何部分弄破……這兩種法則,這種分析與綜合,為的是會說話和會思想。”⑨[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2頁。柏拉圖在這里從方法論的角度介紹綜合法與分析法,但“統觀全體”和“順自然的關節”這兩條法則,本質上也與整體論和有機論的藝術追求一致。
到了20 世紀,古希臘布局藝術回響在文學結構主義思潮中,結構主義提供的語言研究方法又深刻影響了現代人文和社會科學。1940 年,穆卡洛夫斯基發表《美學和文學研究中的結構主義》,認為結構是一個完整的具有能動性的功能系統,這一系統的整體大于部分的總和,其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系統整體性:“結構的整體意味著其每個部分,反過來說,其中每個部分,都意味著這個而不是別的整體。”①[荷蘭]D.W.佛克馬、E.貢內·易布思:《二十世紀文學理論》,林書武、陳圣生、施燕、王筱蕓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40頁。這一結構主義理論在糾正瑣細的原子論傾向時,接續起古希臘時代追求完整和嚴密的寫作理論,及自文藝復興以降中斷許久的、注重綜合方法的人文傳統。
結語
從古典修辭學中吸收對散文寫作有益的養分,是我們研究亞里士多德修辭學說的初衷。亞里士多德基于古希臘公共演說實踐和理論,從論辯術和說服術出發提出作為獨立藝術門類的修辭術并建立新的修辭學,也就是西方古典散文的寫作理論,內容大致覆蓋選題構思藝術、論證藝術、語言藝術和結構藝術,涉及“修辭五藝”中開題、布局和文體。選題構思藝術上,亞里士多德通過劃分題材明確了訴訟、政治和典禮三種演說類型,再借助范疇論的方法分析題材、尋找命題②戴紅賢、王海龍:《尋找命題與建構論證:論亞里士多德的“開題”藝術》,吳禮權、張祖立、李索主編:《修辭研究》第7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0-21頁。。論證藝術上,散文的寫作植根于修辭式推論,提出論題,提供論據,采用或然式證明、例證、夸張式證明進行論證并得出結論③戴紅賢、何曉路:《修辭術與論辯術:論證藝術——亞里士多德散文寫作理論(一)》,《寫作》2019年第2期。。語言藝術上,亞里士多德制定了明晰而適宜的用語原則,介紹了隱喻和夸張兩種主要修辭手法,并強調節奏和語氣④陳韜、戴紅賢:《文體與風格:語言藝術——亞里士多德散文寫作理論研究(二)》,《寫作》2020年第3期。。布局藝術上,亞里士多德針對智者派結構理論上的不足,制定了適用于訴訟、政治、典禮三種演說類型的結構模式,提供了利用布局來實現說服功能的方法,并提出影響深遠的布局觀。
而在研究亞里士多德修辭學說時,我們又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亞里士多德既研究了詩學,也研究了修辭學,二者實乃詩和散文這兩種文體的寫作理論。在亞里士多德那里,詩學和修辭學雖二水分流,仍兩相唱和,可以說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但是,近現代以來,西方詩論和散文理論的關系顯得劍拔弩張,甚至呈現出“揚詩抑文”的特點。例如,黑格爾說散文“只滿足于把一切存在和發生的事物當作純然零星孤立的現象,也就是按照事物的毫無意義的偶然狀態去認識事物……不能滿足理性方面的興趣”;但“詩的觀照把事物的內在理性和它的實際外在顯現結合成的活的統一體”⑤[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23頁。。又如,新批評著名學者蘭色姆把詩比喻為民主政府,把各種散文作品比喻為集權政府,認為“詩比散文好”云云⑥[美]約翰·克婁·蘭色姆:《純屬思考推理的文學批評》,張谷若譯,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95、100頁。。這種“揚詩抑文”的批評所關涉的不僅僅是詩歌和散文的文體競爭問題,也不僅僅是文學與修辭學或寫作學的學科競爭問題,而是寫作活動之價值和意義究竟何在的大問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修辭學研究開創了一種詩與散文平衡發展的格局,這或許也正是現代寫作學所要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