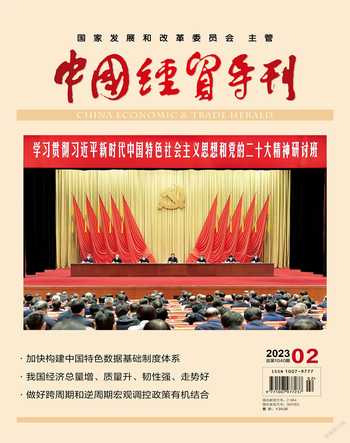高通脹背景下全球政府債務率進入復雜調整期
苑生龍
2021年,全球政府債務率自歷史高點回落,通脹減債效應被認為是關鍵影響因素之一。盡管2022年全球通脹率進一步走高,但在烏克蘭危機、經濟下行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預計2022年及2023年政府債務率走勢將更趨復雜。短期內,通脹減債效應仍將發揮一定影響。但長期看,優化經濟政策組合,穩定利率環境,適時縮減政府赤字,防范區域性債務風險爆發,才是有效調整政府債務率的關鍵。
一、高通脹背景下,全球政府債務率出現高點回落
全球通脹率在新冠疫情中探底反彈并持續沖高。全球疫情暴發后,主要經濟體通脹率一度下探走低。自2021年起,美、英、歐、澳、加等經濟體通脹率先后觸底反彈,并持續走高。特別是2022年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通脹率已達四十年高位,同期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伊朗等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高通脹亦呈現惡化態勢。IMF預計,2022年全球通脹率已漲至8.8%,其中發展中經濟體通脹率將達9.5%。
全球政府債務率在新冠疫情中自歷史高點回落。疫情以來,全球公共債務(即政府債務)出現近50年來的最大增幅。IMF數據顯示,全球政府債務率于2020年升至99.2%的歷史高點。但2021年以來,全球政府債務率下降至97%,國別債務率數據亦普遍回落。歐洲數據顯示,歐盟2020年政府債務率為92.3%,2021年降至87.8%。美國政府債務率于2021年底觸頂至137.2%,2022年10月已降至135.2%。
2022年全球政府債務率走勢將更趨復雜。IMF最新《財政監測報告》認為,2022年全球公共債務率有望進一步降至91%,但仍將比疫情前高7.5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的債務比率將下降5.5個百分點,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債務率仍將繼續上升。市場分析認為,一方面,俄烏危機、能源及糧食緊張等新一輪沖擊因素正導致各國政府支出及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全球經濟下行預期也在同步升溫;另一方面,全球通脹率漲至數十年高位,通脹減債效應亦不可忽視。標普預測認為,在多重因素影響下,2022年全球新增政府債務總額將達10.4萬億美元,比疫情暴發之前的平均水平高出近三分之一。
二、通脹率對政府債務率的長期走勢影響相對有限
數據顯示,全球通脹率與政府債務率走勢在部分時期存在負相關性。根據惠譽模型預測,受通脹減債效應影響,若維持其他變量不變,全球通脹率在4.2%的中值基礎上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使全球政府債務率下降0.5個百分點。但IMF、經合組織、世行年內報告均指出,高通脹的減債效應僅適用于通脹快速波動的短期。從長期趨勢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政府債務消減,均恰好出現于較低通脹時期(5%以下)。
(一)主要經濟體政府債務的規模擴張趨勢尚未見頂
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導致全球能源、糧食等多種關鍵原料市場與供應鏈緊張狀況加劇,主要經濟體政府在民生保障及國防安全領域支出激增,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及債務負擔,使全球政府債務規模持續上升。另據瑞銀的研究報告,相對于通脹上升對政府債務率的短期消減作用,通脹率大幅波動造成的市場不確定性,在長期中對債務的擴張作用反而更加凸顯。政府債務規模上升后,通常需要在中長期進行債務再融資,而高通脹將導致名義利率上升,進而抬高融資成本并持續放大市場風險,最終使政府債務陷入慣性擴張。因此,高通脹對政府債務的實際影響,會在短長期雙向博弈中衰減,而穩定的經濟增長及利率環境、持續性政府盈余才是實現政府債務規模收縮的關鍵。
(二)世界經濟的短長期增速預期在同步放緩
2022年以來,歐美等主要經濟體加息步伐不斷加碼,截至2022年底,年內上調利率在25個基點以上的中大型經濟體已超50個。需求萎縮正在導致世界經濟增長快速放緩,IMF、世界銀行、OECD等國際組織紛紛大幅下調2022年、2023年經濟增速預期,對主要發達經濟體、特別是歐元區國家預期尤為悲觀。與此同時,主要經濟體長期增長趨勢亦不樂觀,按照現有的人口預測結論,發達國家當前的結構性人口下行將至少在未來30年內持續存在。除非出現顛覆性技術革新,其經濟增速的長期緩降態勢不會改變。
(三)通脹或導致發展中經濟體政府債務狀況進一步惡化
IMF數據顯示,發展中經濟體(不含中國)的政府債務余額占全球比重不足10%,相對于發達國家,其政府債務率變化對全球影響有限。但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債務風險正在迅速擴張,可能成為未來引爆區域及全球性危機的導火索。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政府債務多以非本幣借入,在發達經濟體通脹上升時期,低收入國家通脹率往往先行惡化,同時伴隨本幣貶值及匯率崩盤,使政府債務、主權債務違約風險急升。目前,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根廷等多國通脹率均已超出預警,區域性主權債務風險不可忽視。
三、推進全球政府債務率下降、防范主權債務危機依然任重道遠
自上世紀以來,全球政府債務率曾多次在危機性事件中出現跳增,并在達到階段頂點后進入短期下調。通脹率及經濟增長反彈所引發的減債效應,被認為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機構研究指出,2021年出現的全球政府債務率下行,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明顯的一次。但歷史經驗同時顯示,通脹減債效應難以長期持續,如何有效控制全球政府債務率的累進式增長,仍然是國別經濟調控及世界經濟治理的重要難點。
(一)長期中,高通脹減債效應弊大于利
從機構預測數據看,2022年全球通脹率進一步攀升,但全球政府債務率進一步大幅下行的可能性已顯著下降。同時,高通脹所引發的生產、消費、民生問題正在陸續顯現,超預期貨幣及財政政策收縮,亦可能沉重打擊市場復蘇進程。因此,從長期看,不宜將高通脹減債效應視作經濟調控目標和工具,而應視其為危機事件的伴生現象,加以及時關注并合理管控。
(二)優化政策調控、加強國際經濟協調,才是減少全球政府債務率的關鍵
后危機時期,國別經濟調控重點已由刺激經濟重啟轉為提升復蘇韌性。宜精細化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組合,著力實現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及區域等多市場領域的穩定發展。應進一步加強國別政策協調,建立風險對沖及共擔機制,防范國別、區域風險外溢。
(三)關注發展中國家政府債務風險問題
2022年,發達國家高通脹引發的外溢效應正在加速擴散,中亞、南美、非洲等多國均已出現通脹惡化趨勢,政府債務違約、甚至區域性主權債務危機在中期內或已不可避免。當前及未來時期,應加強協商對話,在聯合國、G20、金磚等多邊機制框架下積極化解地緣矛盾沖突,防范因國際能源、糧食、原料等關鍵產品市場波動引發發展中國家債務風險進一步升級。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外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