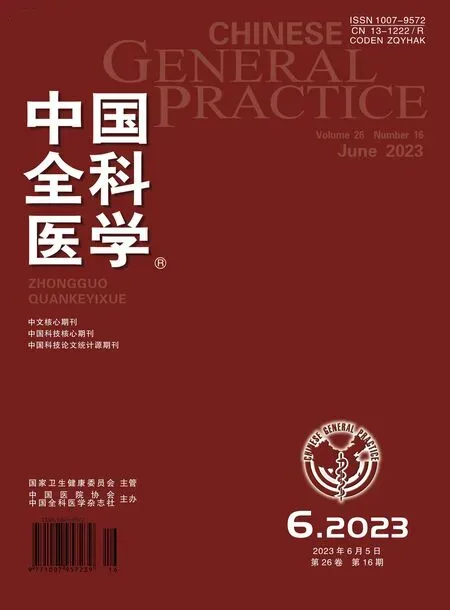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影響因素研究
賀嘉慧,李培雯,馬喜民,喬慧*
衛生服務調查是我國衛生調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衛生服務調查可以了解居民的健康狀況、醫療保障水平、衛生服務、需求和利用情況及其相互關系。衛生服務利用情況可以由衛生服務調查結果客觀反映,其作為描述衛生服務研究工作的重要指標,可評價衛生服務的社會效益及經濟效益,開展衛生服務利用調查可了解所在地區醫療衛生服務的水平和特點。兩周患病率是常被作為反映衛生服務需要的指標,兩周就診率是衡量居民衛生服務利用情況的重要指標之一,而兩周患病未就診率則是用來反映居民就診情況的負向指標,其現況和影響因素也是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發展、規劃和管理的主要依據之一[1]。全國第六次衛生服務統計調查報告顯示,相比于2013 年,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需求落實情況有所好轉[2]。與東、中部地區比較而言,我國西部地區經濟水平相對較低,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水平也較為有限[3]。因此,為了解西部地區農村居民衛生服務利用現狀,于2019 年12 月對寧夏回族自治區農村地區4 縣共21 451 例居民的衛生服務需求及其利用情況進行調查,對其兩周患病未就診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并提出針對性建議,以更合理地配置衛生資源。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寧夏回族自治區衛生行政部門與哈佛/牛津大學科研團隊合作開展的試點項目“創新支付制度,提高衛生效益”中2019 年的隨訪數據。于2019 年12 月,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隨機抽樣的方法,按經濟發展水平將寧夏回族自治區內的鹽池縣、海原縣、西吉縣、彭陽縣4 個縣各鄉鎮的所有行政村劃分為好、中、差3 層;采用隨機數字表法以40%的比例在每層抽取樣本村;采用系統抽樣法根據樣本村戶主花名冊,于每個行政村抽取現居住的20~33個家庭戶作為樣本戶(鹽池縣40 個村,每村33 戶;海原縣76 個村,每村33 戶;西吉縣58 個村,每村20戶;彭陽縣33 個村,每村20 戶),將其戶中所有常住 (當地居住時間≥6 個月)家庭成員列為調查對象,共抽取27 196 例。
1.2 研究方法
1.2.1 調查工具 采用項目組專家統一商討制定的問卷進行調查。(1)居民人口學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人均年收入與參保情況;(2)健康特征,包括自評健康狀況、是否患有慢性病及兩周患病臥床天數;(3)醫療衛生服務可得性和可及性,包括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時間、到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時間;(4)兩周就診情況等。
1.2.2 標準及定義 兩周就診定義為調查前兩周內,患者感到生理或心理不適而前往各級醫療機構就診的情況,不包含慢性病患者因配藥需求(無身體不適)發生的就診;人均年收入采用國際通用的經濟五分組法[4],根據被調查居民家庭的年經濟收入,將居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按由低到高排列,取正序百分位點20%、40%、60%、80%將被調查居民家庭依次劃分為最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組,即Ⅰ、Ⅱ、Ⅲ、Ⅳ、Ⅴ5 個組;兩周患病臥床天數定義為調查前兩周內,患者自覺身體不適(包括生理不適及心理不適)且未去醫療機構就診,在家臥床≥1 d;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時間定義為家庭住址至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所需的時間,到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時間定義為家庭住址至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如市(縣/區)級醫院〕所需的時間。兩周就診情況:(1)兩周患病率為調查前兩周內患病例數/調查總例數×100%[5];(2)兩周就診率為調查前兩周內前往各級醫療機構就診的例數/調查總例數×100%[5];(3)兩周患病未就診率為調查前兩周內患病未就診例數/兩周患病例數×100%,未就診包括未采取任何治療措施和自我醫療[5]。
1.2.3 調查方法 于2019 年12 月,由82 名調查員展開正式調查,取得調查對象知情同意后,采取“面對面”形式進行入戶調查。問詢前由調查員對調查對象說明“兩周就診”標準,隨后根據配備的問卷手冊對調查對象進行詢問并由調查員記錄并填寫問卷信息,本次調查所有信息均為調查對象自訴。家庭成員不在時由了解情況的其他成員代答,不確定信息通過線上方式與當事人確認,兒童(包括新生兒)由其常住監護人代答。問卷完成后,由調查員當場回收問卷并核查有無漏答情況。本研究共收集問卷27 196 份,有效問卷21 451 份,有效回收率為78.88%。
1.2.4 質量控制 調查前為每位調查員配備培訓手冊并集中培訓;調查過程中由調查員、組長、質控員組成的審核小組在每日調查完成后對問卷進行核查,排除存在缺失值和不明確值的問卷,確保納入的調查問卷完整有效;調查后采用雙錄入法錄入調查數據。
1.3 構建結構方程模型
1.3.1 模型介紹 結構方程模型由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兩部分構成,測量模型用于討論觀測變量與潛變量之間的關系,結構模型用于分析潛變量和潛變量之間的關系。建立結構方程模型的主要過程為:(1)模型構建;(2)模型識別;(3)指標估計(本文采用最大似然估計法進行模型指標估計);(4)模型評價與修正〔模型擬合指數主要包括擬合優度指數(GFI)、殘差近似誤差平方根(RMSEA)、調整擬合優度指數(AGFI)、模型正規擬合指數(NFI)、相對擬合指數(RFI)、增量擬合指數(IFI)、非規準適配指數(TLI)和比較擬合指數(CFI)等,如果模型擬合效果不佳,須對模型進行反復修正〕[6]。
1.3.2 變量選取 根據已有文獻及本文研究需要,模型具體包含2 個潛變量和相應觀測變量。潛變量分別為人口學特征與健康特征。人口學特征變量由性別、年齡等觀測變量進行測量;健康特征變量由參保情況、自評健康狀況、是否患有慢性病、兩周患病臥床天數、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時間和到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時間等觀測變量進行測量。使用結構方程模型描述各潛變量之間的關系,揭示潛變量與結局變量兩周患病是否就診之間的作用路徑。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Data 2.1 軟件建立數據庫,并對數據進行雙錄入及邏輯核查。采用SPSS 26.0 軟件進行數據描述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多組計數資料組間兩兩比較采用Bonferroni 法校正。采用AMOS 26.0 軟件擬合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并進行具體分析。
2 結果
2.1 居民的人口學特征 本次調查共納入男 11 172 例(52.08%), 女10 279 例(47.92%);15~<25 歲者3 788 例(17.66%);受教育程度為小學者6 659 例(31.04%);婚姻狀況為在婚者12 712 例(59.26%);職業為務農者8 540 例(39.81%);人均年收入為Ⅱ者7 736 例(36.06%),見表1。

表1 被調查居民的人口學特征情況〔n(%)〕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residents
2.2 居民的健康特征 本次研究調查的居民參保 21 399 例(99.76%),未參保52 例(0.24%);自評健康狀況好者11 066 例(51.59%),自評健康狀況一般者 4 582 例(21.36%);患有慢性病者4 826 例(22.50%);兩周患病臥床天數0~5 d 者20 833 例(97.12%);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時間0~10 min 者17 053 例(79.50%);到 二 級 及 以 上 醫 療 機 構 時 間≥46 min 者12 609 例(58.78%),見表2。

表2 被調查居民的健康特征情況〔n(%)〕Table 2 Heal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residents
2.3 兩周患病就診情況 本次研究共調查21 451 例,調查前兩周內自覺身體不適者3 212 例,兩周患病率為14.97%。調查前兩周內自覺身體不適且前往各級醫療機構就診者981 例,居民的兩周就診率為4.57%;在所有兩周患病者中,兩周患病未就診者2 231 例,兩周患病未就診率為69.46%。兩周患病未就診者中采取自我醫療者908 例(40.70%),其余1 323 例(59.30%)未采取任何治療措施。
2.4 不同人口學特征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情況比較 不同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及職業的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情況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及以上者的兩周患病未就診率高于未受過教育者(χ2=8.069,P<0.01);職業方面,學生的兩周患病未就診率高于務農者(χ2=7.163,P<0.01)、無業者(χ2=10.042,P<0.01)。

表3 不同人口學特征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情況比較〔n(%)〕Table 3 Comparison of non-treatment-seeking behaviors for two-week morbidity in rural residents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5 不同健康特征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情況比較 不同自評健康狀況、患有慢性病情況、兩周患病臥床天數及到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時間的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情況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不同健康特征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情況比較〔n(%)〕Table 4 Comparison of non-treatment-seeking behaviors for two-week morbidity in rural residents by health characteristics
2.6 兩周患病未就診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2.6.1 模型構建與修正 本研究所用結構方程模型的結果變量是兩周患病是否就診(賦值:未就診=0, 就診=1),表3~4 中P<0.05 的變量為觀測變量,以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職業作為潛變量人口學特征的觀察變量,以自評健康狀況、是否患有慢性病、兩周患病臥床天數和到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時間作為潛變量健康特征的觀察變量。運行AMOS 26.0 軟件建立初始模型(圖1),根據初始模型修正指數及相關領域的知識,刪除不合理和無效路徑(表5)。在進行模型調整的過程中,修正指數表明如果將年齡與是否患有慢性病的殘差相關,則模型的χ2值會相應下降,考慮實際情況,年齡確與慢性病患病情況有關,年齡越大,其患慢性病的概率就越高,因此考慮增加年齡殘差和是否患有慢性病殘差的相關路徑。按照以上步驟對初始模型進行反復調試和修正后,得到各適配指標符合要求的修正模型 (圖2)。

圖1 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影響因素的初始模型Figure 1 Initial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on-treatment-seeking behaviors for two-week morbidity among rural residents

圖2 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影響因素的修正模型Figure 2 Modified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on-treatmentseeking behaviors for two-week morbidity among rural residents

表5 初始模型修正指數Table 5 Modification indices of the initial model
2.6.2 模型評價 將寧夏農村地區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各適配指標與模型標準值進行比較,χ2/df=1.835,符合參考標準,各擬合指數GFI、RMSEA、AGFI、NFI、RFI、IFI、TLI 和CFI 值分別為0.998、0.016、0.995、0.991、0.982、0.995、0.996 和0.996,均在參考范圍內,擬合程度良好。
2.6.3 模型路徑分析 結構方程模型中可用標準化系數β來表示寧夏農村地區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各個影響因素影響程度,各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的路徑系數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6)。人口學特征對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情況影響的總效應為-0.101(β=0.110),其中直接效應為0.107,間接效應為-0.208;健康特征對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情況影響為直接效應,總效應為-0.210(β=-0.313,表7)。

表6 模型路徑系數估計結果Table 6 Estimated path coefficients i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7 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效應分解Table 7 Decomposition of the effect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ontreatment-seeking behaviors for two-week morbidity in rural residents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 討論
3.1 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率較高 兩周患病是否就診可以反映居民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情況[1]。本研究顯示寧夏回族自治區農村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率為69.46%,明顯高于第五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西部農村為22.2%),表明該地區居民利用醫療衛生資源的主動性較差。居民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識相對不足可能與調查對象來自經濟水平和文化教育相對落后的西部農村地區有關,而當地的衛生服務利用情況較差又與當地醫療服務提供能力有限有關。2019 年寧夏衛生健康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區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有床位4 099張,僅占全區醫療衛生機構的10.03%;全區衛生人員總數68 535 人,而鄉村醫生僅有3 240 人(含執業及助理醫師僅391 人),占比只有4.73%[7]。可見,市級與縣域內醫療資源分布結構尚不合理,本地區基層醫療資源,尤其是衛生技術人員及其技術水平相對匱乏,缺少吸引居民就醫的能力[8]。本研究調查對象居住地均位于偏遠地區,主要利用衛生服務的途徑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這也成為西部農村地區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率高的原因之一。在兩周患病未就診者中選擇自我醫療的居民占40.70%,自我醫療雖經濟、便捷,但其本身也是一種存在健康風險的治療方式[9]。應加強健康知識宣傳教育,普及健康知識并傳播健康理念,持續提升居民的健康素養水平。
3.2 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影響因素之間存在差異
3.2.1 人口學特征 人口學特征對兩周患病未就診的影響次于健康特征,其總效應為-0.101,包括直接與間接效應。(1)人口學特征中對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率影響最大的是年齡,<35 歲者的兩周患病未就診率較高(>75%)且15~<25 歲者未就診率尤其高(81.61%)。原因與年齡的特殊性有關,<35 歲者忙于學業、工作和家庭事務,在生小病時常會選擇自我醫療或者“硬扛”,疏于對健康的管理,提示<35 歲者的健康狀況更需要受到重視[10];而老年人群的未就診率相對較低,可能與其普遍患有慢性病或者存在軀體功能障礙有關,其疾病并發癥風險和持續的藥物使用增加了衛生服務和醫療咨詢的需求及利用[11]。(2)受教育程度高者衛生服務利用水平高于受教育程度低者,這與既往認知及部分其他研究結果相反[12]。可能原因為受教育程度會決定居民的選擇權廣度,受教育程度高者因其信息來源及所具有資本的更豐富,對自身的健康認識更全面,故其就診行為更積極;此外,其對疾病診療的認知程度可能較高,從而可以根據自身醫學知識儲備對所患疾病是否需要就診做出判斷。(3)職業類型中,學生的兩周患病未就診率較高,其原因可能與調查時學生處于忙碌的學習時期,減少了衛生服務的利用次數有關。務農者的兩周患病未就診率較低,可能與其在秋收后獲得全年大部分收入及進入冬季農閑階段有關,冬季成為務農者的就診高峰期[13-14]。(4)人口學特征在健康特征影響兩周患病是否就診中有間接作用,這可能與不同人口學特征人群的健康特征存在差異有關,如年齡可能會影響慢性病患病情況。
3.2.2 健康特征 本研究結果顯示,健康特征對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影響僅存在直接效應(β=0.313),與人口學特征比較,健康特征對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的影響更大,是居民決定是否利用醫療衛生服務的重要影響因素。(1)自評健康是個體對自身生活狀態、健康狀況的主觀感受和評價,因此此種方法測量健康的效果較為穩 定[15]。本研究結果顯示,居民自評健康狀況越好,兩周患病未就診率越高,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16]。本研究結果顯示,自評健康狀況為一般、差、非常差者的兩周患病率較高,提示人群的健康狀況不佳,但其兩周患病未就診率分別為70.66%、63.27%、56.25%,表明該人群在自覺身體狀況并不樂觀的情況下仍未選擇就診,提示其就醫主動性與主觀健康認知不足,保健知識與醫學常識的宣講與科普在農村地區尚須加強。(2)本研究結果顯示,與無慢性病者相比,患有慢性病者兩周患病未就診率較低,這可能與其為避免疾病發展及并發癥的發生而更傾向于前往醫療機構就診有關。此外,慢性病醫療保險及各項政策的實施為慢性病患者提供了有力的醫療服務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該人群的就醫需求。以上現象也從側面反映出當地醫療衛生機構的慢性病管理與健康宣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3)兩周患病臥床天數可用來描述疾病嚴重程度,在探究該指標對于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的影響時發現,臥床天數0~5 d 的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率最高(73.59%),但未就診率并未隨著臥床天數的增加而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臥床天數較少的居民自感疾病嚴重程度較輕,而臥床天數多的居民可能已了解自身疾病狀況,因此均沒有就診意愿。
3.3 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寧夏農村地區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現狀由多個因素共同影響。在政府部門制定全國衛生政策時,應根據各地區具體情況建立相應的政策措施。針對本文所研究地區居民兩周患病未就診率高的情況,為提高我國西部地區衛生服務利用水平,有效減少兩周患病未就診現象的發生,應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1)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在農村地區進行個性化和多樣化的健康宣傳和教育活動,提高居民的醫學保健意識和預防知識儲備,包括科學用藥的能力,確保不同群體意識到保持健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形成正確的就醫觀,做到未病先防患病早治[17]。(2)建立針對兒童青少年的健康醫療服務模式,結合當地實際,制定長期可持續發展計劃,保障和落實農村地區兒童青少年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工作,為其健康成長創造良好條 件[18]。(3)持續建立完善、科學的基層慢性病管理體系,采取各級醫療機構聯動方式,提升基層防治水平,促進患者的規范治療和管理。(4)加強基層全科醫療建設,借助醫療保險政策,引導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促使家庭醫生與居民建立穩定、持續且可及性高的健康服務關系,提高居民就診的積極性與主動性[19-20]。
作者貢獻:賀嘉慧負責文章的研究設計、數據分析與撰寫;李培雯負責數據整理與清洗;馬喜民負責模型指導、文章修訂及英文校對;喬慧負責文章理論指導與質量控制,并提出修改完善意見。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