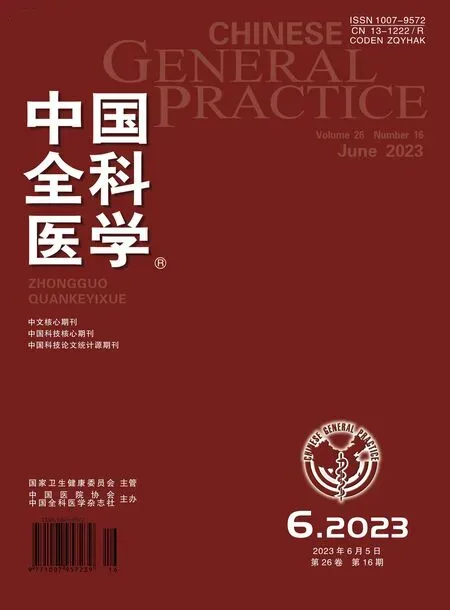廣東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變化及影響因素的灰色關聯分析
徐碧霞,姚衛光
建立分級診療制度是我國合理配置醫療資源、形成科學有序就醫格局的重要舉措,也是深化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分級診療秩序已初步形成,但分級診療制度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展的促進作用整體上不明顯[1],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展速度依舊相對緩慢。以廣東省為例,2020 年全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為34 912.4 萬人次,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占總診療量的48.1%,占比情況尚未達到≥65%的目標[2-3]。2021 年《廣東省衛生健康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十四五”期間要繼續支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健康發展,加快分級診療體系建設[4]。目前,關于分級診療影響因素的研究多從就醫距離等微觀角度出發,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人口結構等宏觀因素的關注較少[5],而宏觀因素對居民的就醫流向常具有廣泛影響。因此,本研究在對廣東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進行現狀描述的基礎上,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法探究基層診療人次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為衛生行政部門深化分級診療制度建設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開展時間為2021 年12 月,研究涉及診療人次源于2013—2015 年《廣東省衛生統計年鑒》[6-8]、2016—2017 年《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9-10]、2018—2020 年《廣東省衛生健康統計年鑒》[3,11-1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口數據信息源于《廣東統計年鑒2021》[13],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財政補助收入和醫療保險參保人數源于2015—2017 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14-16]、2018—2021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17-20]。本研究中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衛生院、門診部、診所、衛生所、醫務室和村衛生室。
1.2 研究方法
1.2.1 理論依據 控制論用白色、灰色和黑色來形容信息的明確程度,其中,白色代表信息完全明確,黑色表示信息未知,灰色則表示信息的明確程度介于完全明確與完全未知之間[21]。灰色系統理論最早由鄧聚龍[22]創建,該理論以具有“小樣本、貧信息、不確定性”特征的灰色系統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已知信息的挖掘和分析實現對灰色系統演化規律的探索和發展趨勢的預 測[21]。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受居民就醫行為、衛生資源配置、社會人口學特征和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是一個典型的部分信息已知而部分信息未知的灰色系統。
1.2.2 灰色關聯分析法 灰色關聯分析通過影響因素時間序列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比較關聯度,比較序列的幾何形狀與參考序列的幾何形狀越接近,表明該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的關聯度越高[23-24]。傳統的線性回歸分析方法要求數據量須達到一定標準且數據須服從某種分布特征,而灰色關聯分析不受上述數據條件限制。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本研究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影響因素的分析宜采用灰色系統理論的分析方法。分析步驟如下:(1)確定參考序列X0和比較序列Xi(i=1,2……m);(2)采用初值法或均值法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得X'0和X'i(i=1,2……m);(3)求X'0和X'i(i=1,2……m)對應數值之差的絕對值Δi,即兩級差值Δi(k)=|X'0(k)-X'i(k)|, 其 中i=1,2……m,k=1,2……n;(4)確定所有Δi(k)中的兩級差值最小值Min 與最大值Max,分辨系數ξ通常取0.5,計算關聯系數,i 與k 的取值同(2);(5)計算關聯度,其中i 與k 的取值同(2)。
1.2.3 潛在影響因素選取 參考美國蘭德公司依據醫療服務利用“一個過程四個組成部分”理論假設建立的四步模型法所選取的解釋變量[25],借鑒申笑顏等[26]、饒克勤[27]、石龍等[5]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本研究以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為參考序列,從資源配置〔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衛生技術人員數、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執業(助理)醫師數、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注冊護士數〕、社會人口特征(常住人口、65 歲以上人口占比、0~14 歲人口占比)、經濟因素(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財政補助收入)和醫療保險參保情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4 個維度選取影響因素。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Excel 2016 建立資料數據庫,采用均值法對參考序列及各影響因素序列值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2 結果
2.1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比情況 2013—2019 年,廣東省醫院診療人次從33 459.2 萬人次增長至40 131.7 萬人次,年均增長3.08%,同期全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年均增長2.10%,2019 年全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已達43 731.7 萬人次。從全省醫療機構總診療人次變化狀況來看,2013—2019 年廣東省醫療機構總診療人次呈現出穩定的增長趨勢,2019年總診療人次增長至89 104.6 萬人次,年均增長2.69%。2020 年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的影響,醫院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診療人次均有明顯下降,但整體而言,醫療機構總診療人次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的占比呈緩慢下降趨勢,而醫院診療人次的占比呈緩慢上升趨勢,見表1。

表1 分級診療實施前后廣東省醫療機構診療人次變化情況Table 1 The changes in patient visit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erarchical medical system (in 2015)
2.2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影響因素 本研究以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X0,萬人次)為參考序列,以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X1,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X2,張)、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衛生技術人員數(X3,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執業(助理)醫師數(X4,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注冊護士數(X5,人)、常住人口(X6,萬人)、65 歲以上人口(X7,萬人)、0~14歲人口(X8,萬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9,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0,元)、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財政補助收入(X11,億元)、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X12,萬人)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X13,萬人)為比較序列,2013—2020 年參考序列及各影響因素序列值見表2。

表2 2013—2020 年參考序列及各影響因素序列值Table 2 Values of reference series and valu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2013 to 2020
2.3 無量綱化處理結果 運用均值法對表1 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結果見表3。無量綱化處理后,求解各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同一年份數值的差值絕對值,本研究中,所有差值絕對值中最小值為0.001,所有差值絕對值中最大值為0.797,見表4。

表3 2013—2020 年各序列的無量綱化處理結果Table 3 Results of each sequence from 2013 to 2020 after dimensionless treatment

表4 無量綱化處理后各影響因素與參考序列的差值絕對值Table 4 Absolute value of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and reference sequence after dimensionless treatment
2.4 灰色關聯分析結果 計算各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的灰色關聯度,按關聯度大小排序,排序越前表明該影響因素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關聯度越強,排序結果為r6=r7>r13>r2>r1>r12>r8>r4>r9>r3>r10>r5>r11,即廣東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常住人口(X6,萬人)、65 歲以上人口(X7,萬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X13,萬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X2,張)、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X1,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X12,萬人)、0~14 歲人口(X8,萬人),見表5。

表5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影響因素的灰色關聯度及排序Table 5 Ranking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number of patient visits in primary healthcare settings by the coefficient of association derived from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3 討論
3.1 廣東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比呈下降趨勢 本研究結果顯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占全省醫療機構總診療人次的比例整體呈下降趨勢,從2013 年的50.7%降至2020 年的48.1%,距離65%的政策目標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2],與周明華等[2]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提示各類醫療機構診療量的比例仍不夠合理,醫療服務沒有很好地下沉基層。當前,廣東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衛生資源配置效率未達到最佳的投入產出狀態,省內大多數鄉鎮衛生院投入充足甚至出現冗余,而門診、住院等醫療服務產出偏少[28]。既往研究表明,經濟發展水平通過交通便利性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兩類因素對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比產生間接的抑制效應[5]。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逐漸完善,極大地提高了交通的便利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居民的就醫經濟負擔,但由于現有制度未對基層首診作嚴格限制,因此,居民到高層級醫療機構就醫的可能性增加,我國行政制度導致的優質衛生資源向公立醫院富集進一步加劇了公立醫院對患者的“虹吸效應”[29]。 與此同時,近年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的時間,導致基層醫務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積極性下降[30]。此外,廣東省尚未制定統一的雙向轉診標準和轉診流程,基層醫務人員在對患者實施轉診時多憑自身判斷與患者意愿,轉診行為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和主觀性,一些本應在基層就診的患者可能會被轉診至高層級醫療機構,另外雙向轉診通道的不暢通可能導致下轉 困難[31]。
3.2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與社會人口結構具有強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廣東省常住人口(r=0.913)、65 歲以上人口(r=0.913)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的關聯度最強,三者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速率非常接近,提示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動是引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變化的主要原因。國際上通常認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 歲以上人口占社會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0%或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大于7%時,意味著該國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廣東統計年鑒2021》數據顯示, 全省常住人口中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從2012 年的7%上升至2020 年的8.58%[13]。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老年人慢性病、失能、抑郁等健康問題凸顯,老年人衛生服務需求增加帶來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的增長。由于醫患信息的不對等,患者選擇就診醫療機構多以醫療技術水平、醫藥費用負擔、交通便捷性等為參考依據[32]。一項針對我國老年人就醫行為的大樣本實證研究顯示,老年人更信賴大型公立醫療機構,其整體上傾向于在公立、非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就診[33],老年人趨高就診的現象在選擇住院機構時尤為明顯,這可能是造成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3.3 醫保參保人數增加有助于帶動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增長 個體面臨的疾病風險具有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表現為疾病、傷殘或不適發生的時間及嚴重程度均是未知的,基本醫療保險能夠通過國家、社會和個人三方共同籌資建立互助共濟的疾病風險分擔機制,降低就醫成本,對居民的就醫行為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廣東省醫療保障局官方網站數據顯示,截至2021 年底全省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1.1 億[34],絕大多數居民已參加基本醫療保險。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醫保改革的深化,居民衛生服務利用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研究發現,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的關聯強度分別位列第二、第五,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在發展方向和速率上具有較大的相似性,提示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具有較大的影響。但既往研究表明,差異化的醫保報銷比例對居民基層就醫行為具有一定影響,當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的醫保報銷比例差距在10%~15%時,醫保支付杠桿對居民就醫機構選擇的約束作用較弱[35]。而目前社區醫院的醫保支付比例僅比三級醫療機構高出5 個百分點[36]。各級醫療機構醫保支付比例差距過小難以對居民的基層就醫行為產生有效的經濟激勵,出于風險厭惡偏好,居民更有可能選擇高層級醫療機構就醫,這可能是造成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3.4 衛生資源配置情況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具有一定影響 研究表明,設施設備、人員配置等衛生資源要素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服務產出具有正向影 響[37]。近年來廣東省先后制定并實施《廣東省城市衛生支援基層衛生實施方案(2013 版)》《廣東省基層衛生人才隊伍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等政策,支持農村偏遠地區新建村衛生室和鄉鎮衛生院,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標準化建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衛生資源配置狀況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診療量的增加。研究發現,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r=0.893)、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量(r=0.886)均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具有一定關聯,二者的關聯度排序分別位列第三和第四位,提示優化基層衛生資源配置對提高基層診療量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由于部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技術水平低、設備配置更新緩慢、藥品目錄不全、候診環境差、服務能力薄弱、技術創新不足等原因[38-39],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服務能力參差不齊,未能很好地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就醫需求,這可能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患者流失的重要原因。
4 建議與對策
4.1 多措并舉,夯實分級診療制度基礎 可通過短信推送、戶外廣告等方式加強宣傳,提高居民對分級診療的知曉率與支持率;完善醫師多點執業管理辦法,鼓勵醫聯(共)體內大醫院醫生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開設專家門診,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優質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加快基層收入分配改革,取消工資總額限制,提高基層衛生人員提供服務的積極性,繼續實施基層服務能力提升專項計劃,組織在崗人員定期到上級醫療機構參加業務學習,鼓勵專家以“師帶徒”的形式傳授診療經驗,提高基層診療水平;以特定病種為起點,探索建立統一的轉診標準與雙向轉診流程,增強醫務人員轉診行為的規范性。
4.2 結合人口老齡化的社會背景,提供便民化的基層衛生服務 針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健康挑戰,衛生行政部門應加強對居民健康危險因素的檢測、分析、評估和干預,強化重點疾病的預防控制,加強對轄區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隨訪管理服務,提高高血壓、糖尿病、骨質疏松等老年常見慢性病的早診率和規范化治療水平。建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根據患者就診量的規律動態調整號源量,開設“一站式”綜合服務窗口減少患者重復排隊,通過提供中藥煎服、病歷復印、用藥咨詢、藥品配送、衛生政策咨詢、膳食指導、輪椅租借等便民服務鞏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距離近的優勢,引導居民逐步形成基層首診的就醫習慣。
4.3 穩步擴大醫保覆蓋面,拉開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的醫保支付差距 針對未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居民,應繼續擴大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面,確保居民能夠享受基本醫療服務。建立各級醫療機構同向激勵機制,避免高層級醫療機構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互相爭搶患者,提高三級醫院疑難重癥病組的醫保支付比例,降低高層級醫療機構普通門診和普通住院服務的報銷比例,建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與三級醫療機構的醫保支付比例差距擴大至20%左右[24],通過醫保支付杠桿作用調整居民就醫流向,進一步為基層首診制夯實基礎。
4.4 全方位、多角度增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服務能力 開展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標準化建設,改善診療環境,及時更新設施設備,增加自助服務設施,建議加快大數據、云計算在基層的應用,以服務效率提升帶動服務產出數量。提高基層醫護人員績效工資占比和崗位津貼補助標準,鼓勵在職進修和競爭上崗,增加基層編制名額,建議對取得中級職稱并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連續工作滿一定年限的衛生緊缺人才直接認定副高級職稱,解決基層衛生人才匱乏的發展瓶頸問題。加快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與上級醫療機構藥品目錄對接,滿足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兒童、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特殊群體的用藥需求。
綜上,本研究從宏觀角度出發,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法探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的主要影響因素,為衛生行政部門采取針對性措施深化分級診療制度建設提供參考依據,在研究視角的選取上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但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影響因素紛繁復雜,由于灰色系統邊界的不明顯,仍有一些因素未被納入本次研究;二是關聯分析實際上是動態過程各序列數據發展態勢的量化比較分析,未能對影響因素進行統計學檢驗。
作者貢獻:徐碧霞、姚衛光負責文章的構思與設計、研究的實施與可行性分析、論文的修訂、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徐碧霞負責數據收集與整理、統計學處理、結果的分析與解釋、論文撰寫;姚衛光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