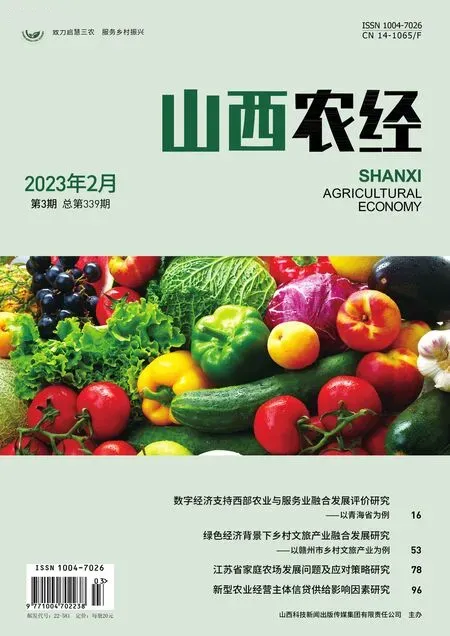江蘇省家庭農場發展問題及應對策略研究
□孫德權,丁麗萍
(新疆農業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2)
家庭農場可以有效推動農村農業現代化,利于整合碎片化土地,推動農業機械化生產。發展家庭農場經營主體是現代農業的新探索,可以在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同時,改善農業生態環境。
家庭農場多層次的經營活動可以有效減少化肥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綠色家庭農場通過專業化運作,生產銷售商品化農產品,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保護生態環境。
1 家庭農場的定義
1.1 家庭農場概念
美國農業部(USDA)將一年內銷售或生產產值超過1 000 美元的農業經營主體定義為農場;將任何農場的大部分業務由主要經營者和其家人擁有,這些人對農場的日常決策負有主要責任的農場定義為家庭農場;其余則是非家庭農場。
俄羅斯《農場法》定義,“農場是指有血緣關系或姻親關系的公民聯合起來,財產共有,在親自參與的基礎上共同進行生產和其他經營活動(生產、加工、儲存、運輸和農產品銷售)的組織。”
在我國,家庭農場屬于外來詞,國內學者對其定義不一。袁賽男(2013)[1]認為,家庭農場是以整個農戶為經營的主要部分、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業經營組織。家庭成員是農場的主要勞動力,其負責規模化、集約化以及商品化的農業活動。張朝華和黃揚(2017)[2]認為,家庭農場是一種以農戶為主要經營成員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但由于家庭農場在我國起步較晚,存在諸多問題。
1.2 家庭農場分類
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中的核心主體,按照農場主的身份類型可分為內生性家庭農場和外生性家庭農場。內生性家庭農場熟知周圍農戶需求,獲取服務信息容易,與服務對象對接的交易成本低,農機投資規模大。一般情況下,當地政府更愿意支持內生性家庭農場。
根據經營類別可分為糧食種植家庭農場、蔬果種植家庭農場、畜牧養殖家庭農場和水產養殖家庭農場。在江蘇省家庭農場發展類型中,糧食類家庭農場占主導地位,數量和經營面積占比分別達到55%和63%[3]。
2 江蘇省家庭農場發展現狀
2.1 家庭農場數量規模擴大速度快
2020 年江蘇省出臺了家庭農場名錄管理辦法和示范級家庭農場評定方法,確定了入選家庭農場名錄的標準和規范,建立了家庭農場信息收集制度。江蘇省入選全國家庭農場名錄系統管理的家庭農場總數超過17 萬家,培育省級示范家庭農場2 290 家,各級示范家庭農場超過1 萬家。
2014 年,經過江蘇省農業廳認定的家庭農場有2.18 萬家,相比2013 年,家庭農場的數量增長較快,總面積達143.33 萬hm2,占江蘇省耕地面積的35%,戶均經營面積6.67 hm2[4]。
2.2 家庭農場產業結構多元化
糧食種植業是江蘇省家庭農場的主力軍,占比達64.5%。從事糧食生產的家庭農場超過9 萬家,總經營面積達到10 萬hm2。漁業、畜牧業、種養結合的家庭農場分別占比19.9%、8.2%和5%。
雖然江蘇省家庭農場的主力是傳統糧食種植業,但各地均出現了結合當地特色和市場需求的特色家庭農場。例如,蘇州市吳江區彩楓家庭農場結合當地需求,培育特色彩葉景觀樹木,采用科學化管理、標準化種植方式,雖然占地僅6.7 hm2,但年銷售收入可達80 萬元[5]。
2.3 農場主年輕化、知識化
目前,江蘇省家庭農場經營者朝著年輕化、知識化方向邁進。家庭農場經營者的普遍年齡約為45 歲,50 歲以下的經營者占58%,中專及以上學歷的經營者占40%。家庭農場經營者年輕化,意味著經營家庭農場的積極性更高,農業科學技術普及更容易。同時,經過3 年的培育,現已培育出1 000 多名示范級家庭農場經營者[6]。
3 江蘇省家庭農場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3.1 土地流轉成本高
土地問題是制約家庭農場發展的重要因素,土地是農業經營生產的重要條件。隨著經濟發展,江蘇省城鎮化速度加快,對于農業土地的需求較大。目前,大部分土地流轉依托農戶之間的口頭協議,缺乏正規化的平臺。部分家庭農場經營不善會單方面毀約,嚴重打擊家庭農場主的積極性。此外,由于農村缺乏社會保障,農民流轉土地的意愿不高,害怕土地流轉之后基本生活無法得到保障[7]。
日益增長的土地流轉費用是限制家庭農場發展的重要因素。近年來,土地流轉費用逐漸增加,2018 年耕地流轉價格為12 826.95 元/hm2,2021 年第四季度已漲至13 695 元/hm2,漲幅較大的為養殖水面和四荒地,分別上漲23.9 個百分點和25 個百分點[8]。
3.2 家庭農場融資困難,經營風險大
家庭農場規模遠大于普通小農戶,前期建設農場、流轉土地、購買肥料需要大量的資金。通常情況下,家庭農場經營者由當地農戶過渡而來,資金有限,只能向別人借錢或向銀行貸款,償債壓力較大。同時,家庭農場很難從銀行貸款,原因是家庭農場缺乏抵押物,銀行不愿意貸款給家庭農場[9]。
3.3 家庭農場缺少足夠的社會保障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業經營風險種類多元化且集中化,家庭農場難以承受與控制,需政府發揮作用。從宏觀角度來看,家庭農場是近年來發展較快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缺乏金融、財政、保險和稅收優惠,需要政策扶持。同時,政策具體細化并落實到家庭農場的過程復雜,補貼申請手續繁雜,農場主壓力較大[10]。
《土地管理法》規定,我國實行的是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制度,農場主不能擅自占用或改變租用土地的用途。家庭農場形成一定規模時,有必要建設倉庫、曬場等,用于存放糧食、生產工具和部分農機,對家庭農場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礙。
3.4 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完善
家庭農場發展中存在農業社會化需求巨大和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完善之間的矛盾。相比于小農戶,家庭農場經營者對社會化服務的需求較強。普通農戶經營面積較小,家庭勞動力夠用,對農機沒有較大需求。家庭農場具有一定規模,純靠人力會耽誤農時,但單獨購買農機會導致成本過高,且過了農忙時期就會閑置,所以家庭農場經營者對農機服務需求較大。農耕土地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機規模化作業,土地長期碎片化經營使得部分土地機耕化條件較差,難以開展機耕作業[11]。
農產品銷售難是困擾家庭農場經營者的主要問題之一。部分家庭農場可以生產高質量的糧食,但由于缺乏合適的農產品銷售平臺、信息不對稱,只能將糧食按照普通糧食價格售賣,導致收益過低,嚴重影響了家庭農場經營者的積極性。
3.5 家庭農場縱向一體化不足
目前,江蘇省家庭農場還停留在生產初級農產品階段,縱向一體化程度較低,沒有建立獨特的品牌。農場主學習能力較低,只關注生產,不注重營銷和農產品定位,加之缺少政府補助、政策支持、社會化服務,致使成本過高,農場主縱向一體化的意愿較低。
家庭農場與合作社的合作程度較低。合作社可以幫助農場經營者統一購買化肥、農藥,提高議價能力,降低家庭農場主的經營成本,獲得更高的收益。農場經營者可以規避生產單一農產品的經營風險,但部分地區家庭農場未形成較為完善的合作社組織。
3.6 家庭農場現代化程度低,合作程度不高
農業現代化技術可以有效增強家庭農場在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經營效率,減少對人工的需求。目前,家庭農場現代化發展程度較低,2018 年調查顯示,通過網絡采購生產資料、智能電子控制技術、網絡營銷的占比分別為55%、38%、42%。只采購一種和未采購的占比分別為52%和27%。由此可見,江蘇省家庭農場的現代化程度較低。
江蘇省農業用地較為集中,家庭農場經營區域較為集中,若互相合作可以統一購買生產資料,有較強的議價能力。目前,大部分家庭農場采用“單打獨斗”的模式,合作意識不強,加入龍頭企業和合作社的家庭農場少之又少,家庭農場合作意愿較低。
4 江蘇省家庭農場發展的優化建議
4.1 合理推動土地流轉
明確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規范土地流轉價格指數機制,加強政府在農村土地流轉中的主導地位,監管土地流轉過程,處罰私自占用土地、違法占用土地的行為,嚴防混亂不合規的土地流轉情況。
建立規范的第三方土地流轉平臺機構或土地流轉信息平臺,涉及范圍覆蓋到縣、鎮、村,對農場經營者和家庭農場意愿者進行宣傳和普及,建設土地流轉微信公眾號,定期下鄉宣傳,加強土地流轉信息流通,增強農場經營者和農戶流轉土地的意愿,激發土地流轉活躍度。
加強土地市場監管,保護農民的合法利益。目前,江蘇省土地流轉部門管理不嚴格,法律不完善,常出現農民合法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需要強有力的市場監管,加強合同監管,規范農戶與農場主之間的流轉協議,建立規范的土地流轉模板合同和電子合同檔案機制。提高農民的職業素質,使其在發生土地糾紛后能夠通過合法手段解決問題。
4.2 加強農村金融服務
家庭農場經營中,花費最多、價值最大的是農業經營土地和農產品,但其無法用作抵押物獲取貸款。相關法律規定,農耕土地和流轉土地不得作為抵押物獲取貸款。盡管江蘇省各地出臺了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的新政策,但在具體實施方面存在審批周期長等問題。相關部門需放松對農用土地的抵押限制,建立規范的貸款資格審查制度。同時,出臺針對農產品的抵押政策,幫助農民銷售農產品。
政府需引導金融機構推出適合農村和家庭農場的金融產品,保障金融機構獲得一定的利潤,激發金融機構下鄉的積極性,使金融機構與江蘇省家庭農場合作,根據家庭農場不同的類型與規模,推出不同的家庭農場金融產品。
4.3 建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需加強農業基礎建設,推進農村的道路建設,使得農機覆蓋范圍更加廣泛。建立農機服務站點,保護農機戶的利益,激發其積極性,更新水利設施與電力設施,保證水電系統穩定運行。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力度,確保新技術快速、及時運用到農業生產中,提高生產效率,幫助家庭農場增收。加強家庭農場、小農戶、合作社、農業企業之間的聯系和溝通,避免獨立封閉的生產經營,使其利益緊密結合,降低經營過程中的風險,推進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
4.4 加強家庭農場產業縱向一體化
家庭農場不能僅局限于生產單一的農產品,要嘗試生產高利潤、高附加值的農產品,加工初級農產品,配合農業社會化服務機構,發揮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優勢,打造有特色的附加產品。一方面,家庭農場可以根據當地特色種植農產品,依托當地平臺提高附加值,幫助家庭農場主增收。另一方面,發展休閑農業,打造農業休閑模式,開發農業農村多種功能,挖掘農村旅游資源,促進農民農閑時再就業。建立家庭農場合作社或協會,建設家庭農場品牌。相同經營范圍的家庭農場可以為同一特色品牌服務,合作社或協會可提供農機服務、技術支持、管理服務,增強家庭農場在市場中的議價能力。
4.5 保障農村生存基礎條件,防止農村勞動力外流
加強鄉村文化教育基礎建設,提高農業從業者的素質,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產業化、集中化。在農村經濟建設中,需保證農閑時農民的基本生活支出,防止勞動力外流,建設農村經濟模式。推動城鄉一體化有助于家庭農場發展,有效防止勞動力外流,推動城鎮化建設,促進農村社會化服務進一步發展,提高農村就業服務水平,推動家庭農場健康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