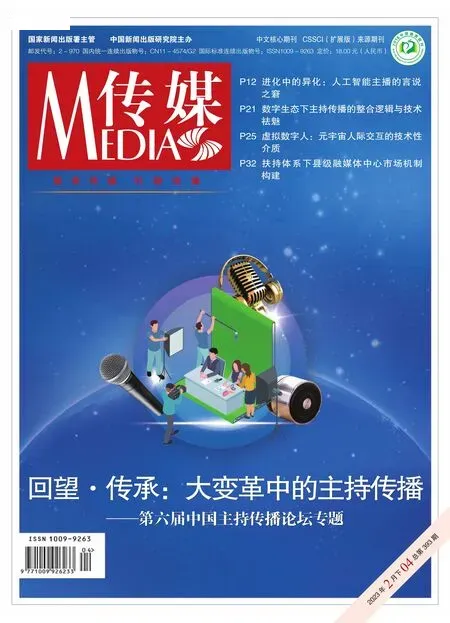主持傳播:關鍵變革與學界使命
文/周勇
1920年,由美國匹茲堡西屋電氣公司開辦的商業廣播電臺開始播音,呼號為KDKA,它被公認為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廣播電臺。1936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正式播出電視節目,電視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由此,大眾傳播不再是文字的專利,視聽的時代到來了。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傳統廣播電視的傳播模式受到巨大沖擊,影響力開始下滑。而另一方面,以短視頻為代表的互聯網視聽傳播迎來爆發式增長,成為一種全民生產、參與、共享的文化現象。社會文化向視覺轉向的特征從未如今天這般清晰。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傳播的節點進一步擴散,網民開始真正成為傳播的一極主體。與之相應,更簡易的拍攝工具和一鍵式編輯工具使視聽生產的專業性堡壘敞開了一扇大門。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描述的“景觀社會”一樣,中國數億網民在對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中顯現出極具大眾文化意義和后現代色彩的圖景。在向圖像轉向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視聽日益成為社會生活中最具活力的信息表達手段和傳播方式,視聽產業亦延續自二十世紀廣播電視興盛以來的繁榮軌跡,并在虛擬現實、人工智能、5G等新興媒介技術的助推下加速發展,呈現出廣闊的前景。
中國主持傳播論壇正是在響應了上述視聽時代之變的過程中,獲得了蓬勃生機,并將第六屆論壇主題定為“回望·傳承——大變革中的主持傳播”。題中的關鍵詞都具有豐富的意涵指涉。大變革到底指什么?以筆者的理解,主持傳播領域面臨的關鍵變革有二:一是作為一種職業和專業的“應用場景”的變化;二是來自于“技術”的變遷。
其一,主持傳播作為一種職業和專業,其應用場景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如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的“液態社會理論”所指出的,(早期)社會存在著確切、穩定的模式、規范和準則。而如今,這些已“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更不用說是‘不證自明的’”,“系統性結構的遙不可及,伴隨著生活政治非結構化的、流動的狀態這一直接背景,以一種激進的方式改變了人類的狀況”。簡言之,整個社會的樣態正在從一種傳統的、沉重的、規則明確的固態樣態,轉變為一種輕靈的、社會關系重構的動態樣態。那么新聞傳播及其從業者作為普利策口中的“社會的瞭望者”,也面臨著這一變革。職業新聞工作和非職業新聞工作共同構成了一種邊界消融的、高度融合的新樣態。新聞傳播活動,由過去被職業新聞工作機構所壟斷,轉向了“社會化”的新聞活動樣態。主持傳播領域亦受此影響。過去由于職業的專業性所構筑起來的職業壁壘,如今正被逐漸打破,主持傳播的應用場景發生改變,職業的社會評價標準隨之改變。回溯歷史,今天所探討的“主持傳播”,實際上是隨著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廣播和電視的登場而逐漸建立起來的職業場域。這一職業場域是有專業門檻和專屬應用場景的,是與職業新聞活動在全社會的地位、格局相匹配的。今天,職業新聞活動的邊界被打破,過去被職業所構建的應用場景逐漸變得更加多樣化。新媒體迅猛發展帶來的是信息量的井噴和“全民記者”時代的到來。隨著網絡媒介平臺的賦能,受眾亦可通過對信息的記錄和發布成為意見領袖,沖擊著傳統媒體在主持傳播領域一家獨大的局面。但也應看到,新媒體在時效性、互動性方面向傳統媒體提出挑戰的同時,也提供了技術便利、平臺便利和內容便利。
其二,主持傳播面臨的另一大變革,來自于“技術”。5G、人工智能、大數據、虛擬現實等技術方興未艾,元宇宙正在重新建構我們的社會生活樣態。在這種情況下,“人”和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如何相處,這一“人機關系”問題已成為新聞及主持傳播領域的一個亟待回應的核心議題,這無疑需要領域內的研究者與從業者進行思考、回望與傳承。筆者認為,研究視野的變化是十分必要的。過去面對職業新聞工作時,我們的評價目光是向“內”的,主要考慮職業領域內部的社會評價,由此來建立這一職業的規范和準則。但是在職業新聞活動逐漸走向“社會化”的今天,全社會各方面力量都對我們的主持傳播活動發出了大量的社會評價,并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敦促著我們的評價目光和研究視野也應由“內”及“外”——面向社會去建構主持傳播與社會大系統的關系。換言之,主持傳播這樣一種專業領域和專業能力,對于社會的價值是什么?對于社會化新聞活動的價值是什么?對這些問題,學界應該回到原點、回到基本脈絡上進行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