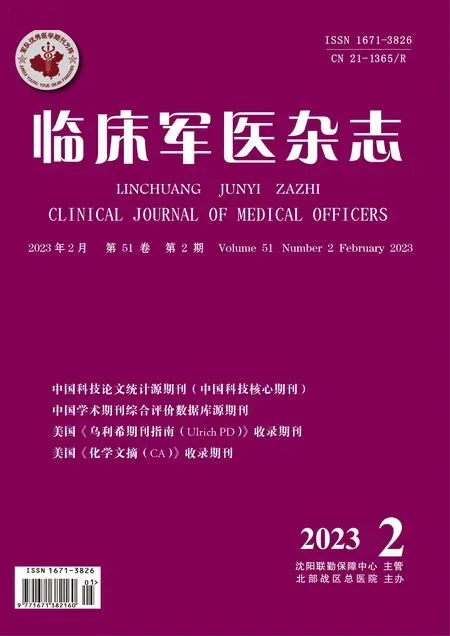戰傷動物模型助力提升戰傷救治實戰能力
梁國標, 金 海
北部戰區總醫院 神經外科,遼寧 沈陽 110016
戰傷救治能力直接影響傷員預后[1]。通過提高救治人員對急危重戰傷處置的敏感性及重視程度,熟練、合理、準確地使用救治器械,可以達到有效救治的目的[2]。戰傷救治能力必須通過大量的實戰化訓練生成、保持及提高[3]。目前,戰傷救治實戰化訓練的模型選擇多樣,訓練方法不一,缺乏系統、標準的戰傷動物模型[4]。本文就戰傷救治訓練的模型發展現狀、動物模型作用、動物模型選擇、動物模型傷情、動物模型發展等方面予以綜述。
1 模型發展的現狀
現階段,戰傷救治實戰化訓練常選用塑料假人、真人化妝傷員、仿真模擬人、虛擬傷員和動物模型等進行戰傷救治技能訓練[5-8]。不同模型的模型材質、模型造價、造模難度、生命體征、傷情真實感、應用范圍及訓練效果等均有所差異。塑料假人的傷情真實感極差,真人化妝傷員的訓練效果差,仿真模擬人造價高且易出現電子故障,虛擬傷員缺乏操作動作訓練,動物模型尚無成熟方案可行。總體而言,除動物模型外,其他模型的戰傷救治培訓“無血無肉”,訓練效果一般。有研究顯示,同時接受多媒體教學、高仿真模擬人教學、動物模型教學的軍醫中,約80%首選動物模型教學方式,動物創傷模型為基層軍醫較認可的培訓方式[8]。
2 動物模型的作用
美、德、法等世界軍事強國在戰傷救治方面積累了諸多經驗,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培訓機制,一般常規利用豬或羊等大型動物對一線急救人員進行止血、氣管切開和胸腔減壓的培訓和考核[9-12]。美軍軍醫在豬的氣管切開術成功率為85%,豬大動脈破裂出血模型的止血成功率為96%,山羊氣胸模型胸腔閉式引流成功率為93%[13]。德軍在戰傷訓練時,將豬進行局部解剖,讓基層戰士更直觀地了解環甲膜、大動脈、胸腹部等不同部位解剖特點,印象直觀且深刻[14]。鄭新華等[8]考核83名基層軍醫培訓前獨立完成山羊氣管切開、胸腔閉式引流、大動脈縫合的成功率分別為39%、33%、25%;培訓后分別為94%、86%、64%;培訓結束1年后分別為74%、62%、43%。與培訓前相比,培訓后3項技術水平均顯著提高;與培訓剛結束后相比,培訓結束1年后3項技術水平均顯著下降,提示多次重復培訓的必要性。
3 動物模型的選擇
在戰傷動物模型的選擇上,我國相關經驗較少,美軍與德軍多選用豬建立戰傷動物模型[13-15]。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點:鼠、兔子等小型動物由于體型過小,與人體相差甚大,許多操作不方便且訓練效果差[16-17];羊由于體表毛過多,需要備皮,實驗準備耗時較長,工作難度較大,且羊的皮膚及皮下組織與人類差異較大;犬由于與人類特殊的關系,面臨更多的倫理問題;豬作為戰傷救治模型的候選,其體積足夠大,無論活體造模還是局部解剖,均能滿足要求,豬體毛相對較少,備皮相對容易,豬的皮膚及皮下組織與人類非常相似,豬的腹腔結構和血流動力學與人體更加接近[18]。
4 動物模型的傷情
有研究顯示,目前絕大多數創傷模型是從科研角度造模,用以針對性開展沖擊傷、燒傷、骨折、感染性休克等科學研究工作,供戰傷救治訓練的動物模型的相關研究較少[19]。戰傷動物模型的建立需要考慮平時創傷與戰時戰傷的異同。常見的交通事故傷、墜落傷、鈍器打擊傷、刀刺傷等傷型,可通過日常醫療活動逐漸掌握。戰時特有的代表性傷型,只能通過戰傷模型加以訓練。一些戰傷常見的大動脈破裂出血、血氣胸、氣道阻塞、核輻射損傷等傷情,臨床工作中相對較為少見[20-21]。因此,創建一套救治訓練用戰傷動物模型至關重要。
5 動物模型的發展
戰傷救治水平直接影響戰場致死率、致殘率[10]。戰傷動物模型為一種可以提升戰傷救治能力的訓練工具和有效手段,探索并完善基于戰傷動物模型的實戰化訓練方案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戰傷動物模型的未來發展可能呈現出以下3個特點:(1)模型傷情更加豐富,除傳統的止血、氣管切開和胸腔減壓等動物模型外,還會出現重度燒傷、凍傷、低溫損傷、休克、開放傷、爆炸破片傷等新型戰傷動物模型;(2)應用推廣更加普及,標準化戰傷動物模型的造模過程更簡化,造模工具更便捷,造模視頻及講解也可以明顯助力戰傷動物模型的應用;(3)訓練效果更為顯著,通過基于戰傷動物模型的實戰化戰傷救治訓練,必將在不同層級(類別)人員的培訓和考核中取得良好的訓練效果,明顯提升受訓人群的戰傷救治能力。
6 結語
實戰化戰傷動物模型的缺乏是制約戰傷救治生成的一大限制因素,建立標準化的訓練動物模型極為必要。戰傷動物模型的建立,將緊急救命手術技術前移,可進一步實現戰傷時效救治理念,促進戰傷救治理論、裝備、技術的新革命;進而取得戰創傷救治關鍵技術的新突破,為我軍戰救培訓、戰救技術、衛勤裝備、理論等相關研究提供數字化的數據支持與理論依據,提升我軍后勤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