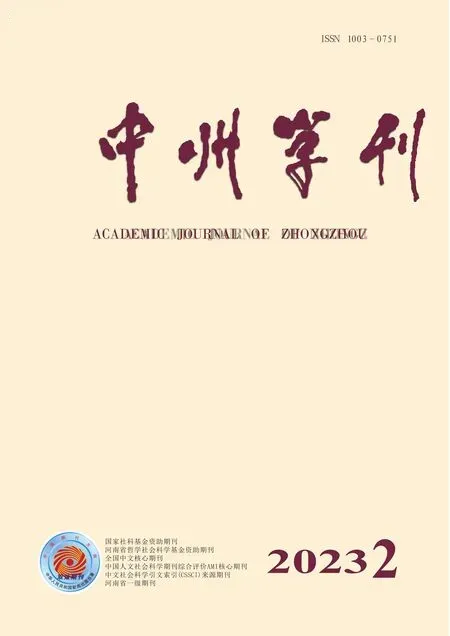論漢晉時(shí)期文章的集作形態(tài)
李德輝
古來文獻(xiàn)載體與文章體制有一定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甲骨、金石、繒帛、簡(jiǎn)牘、紙書抄本、印本,均對(duì)文章體裁、篇幅結(jié)構(gòu)、構(gòu)思撰寫產(chǎn)生過程度不同的影響,而以簡(jiǎn)牘為最甚①。簡(jiǎn)牘從周秦到晉初存在千年,這一時(shí)期恰恰為文體初成時(shí)代,它必然影響到文章體制風(fēng)格。漢晉時(shí)期文都書寫在簡(jiǎn)牘上,但簡(jiǎn)和牘的形制不同②,對(duì)著書作文的影響也不同。因而,漢晉時(shí)期文章存在一長(zhǎng)一短兩種形態(tài):篇幅短的詔令、尺牘、頌贊、箴銘,用簡(jiǎn)牘體制,書于牘片;篇幅較長(zhǎng)的奏議、策論、辭賦和專書,用簡(jiǎn)策體制,書于編簡(jiǎn)。簡(jiǎn)牘編冊(cè)可以接連書寫,無篇幅限制,因而這類文章往往容量廣大,氣勢(shì)恢宏。以往的研究多從審美角度來探究?jī)蓾h文章體制宏大、辭氣雄辯的原因,但說服力有限,本文嘗試從文獻(xiàn)載體與文章體制的關(guān)系入手,來尋求漢晉時(shí)期文體、文風(fēng)特征形成的原因。
一、集作的由來與產(chǎn)生的基礎(chǔ)
“集作”一詞,源于《后漢書·曹褒傳》:“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硏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xí)文書……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jīng),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于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zhǔn)舊典,雜以《五經(jīng)》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兇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jiǎn)。其年十二月,奏上。”[1]1201-1203這是集作的最早出處,其中集指匯集眾簡(jiǎn)連綴成文,作指獨(dú)立創(chuàng)造。集作是指紙書出現(xiàn)之前基于簡(jiǎn)牘編冊(cè)而形成的文章寫作方式或書籍編撰方式。具體做法是將平時(shí)搜集的資料或想出的短句書于簡(jiǎn)牘,日積月累,連綴成文。
之所以謂之集作,一是由于漢魏晉時(shí)期的著述和長(zhǎng)文篇幅都長(zhǎng),寫作要求高,資料搜集不易,必須整合多種資源。簡(jiǎn)冊(cè)以編繩編聯(lián)的形式,還對(duì)構(gòu)思撰寫形成物質(zhì)和心理上的雙重障礙。經(jīng)史和大賦各有注釋,排版上正文和注解還需要用長(zhǎng)短不同之簡(jiǎn)作為區(qū)別,這樣必須借助特殊的材料組織方式。二則因?yàn)楫?dāng)時(shí)文獻(xiàn)不足,文人知識(shí)有限,所用文體也多未發(fā)展到完備狀態(tài),文士臨文常常各自為體,寫法、體制都不統(tǒng)一。想要著書作文,難度很大。其書其文都靠匯編整合而成,故而謂之集作。
漢魏時(shí)期,凡經(jīng)解、子史、策論、奏疏、大賦之類都是篇幅長(zhǎng)、體制大,但在當(dāng)時(shí)的物質(zhì)條件下,必須跨越簡(jiǎn)牘單片的材料障礙,依靠集作來成文,故集作是適合漢魏晉初簡(jiǎn)牘時(shí)代長(zhǎng)文寫作的特殊方式。與在紙上書寫不同,這是一種十分艱苦、緩慢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其聚零為整的功夫之深之難,每一書、每一文的寫作耗時(shí)之長(zhǎng),非今人所能想見。晉代以后隨著紙張的普及,文人讀書作文的條件改變,集作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在個(gè)人文集出現(xiàn)前,與之性質(zhì)接近的是子史。子史相當(dāng)于多篇長(zhǎng)文的整合,其中收有詩文,寓有文體,含有辭章,本身就是周秦漢魏主流文學(xué)樣式。從內(nèi)涵來看,諸子之書本屬文章之一體,故而《文心雕龍》亦列有《諸子》篇,所以本文將其和單篇的長(zhǎng)文合論。漢魏時(shí)期的經(jīng)史注解都是集作而成的,故而集作之法與漢魏學(xué)者注經(jīng)修史之法有關(guān)。漢代學(xué)者在掌握了經(jīng)書集注和史書編撰方法以后,將其借用于著書作文也就順理成章。前文所引曹褒禮書就是通過集作而來的,所集的對(duì)象是兩漢行用的禮文,做法是以漢代儀注“舊典”為準(zhǔn),從中摘錄條文,就叔孫通《漢儀》,逐條補(bǔ)注,以為儀注。這種做法,正是漢人注經(jīng)的普遍做法——以經(jīng)書正文為準(zhǔn),就其字句音義逐條訓(xùn)釋,經(jīng)書用二尺四寸簡(jiǎn),傳注用一尺二寸簡(jiǎn)[2]。每條簡(jiǎn)牘各記訓(xùn)注,并與正文對(duì)應(yīng),經(jīng)與傳在用簡(jiǎn)上異制。南北朝時(shí)紙書代替簡(jiǎn)牘,經(jīng)傳才合刊。兩漢間史書《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也是集作的產(chǎn)物,書的原稿是由眾多單簡(jiǎn)編成的。不僅史書如此,對(duì)史書的注解也有此制。例如裴骃《史記集解》以徐廣《音義》為本,采九經(jīng)諸史及眾書之目,別撰而來。同類著作又如《隋書·經(jīng)籍志》中的《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杜預(yù)《春秋左氏經(jīng)傳集解》,二者融通不同學(xué)派注解,萃為一編,反映了漢末魏晉學(xué)風(fēng)的新變,表明起于漢代的經(jīng)書集注之體是文章集作的先導(dǎo)。
集作作為一種著作編撰和文章撰寫方式,其產(chǎn)生需要具備三個(gè)基礎(chǔ)。
首先是物質(zhì)基礎(chǔ)。集作的物質(zhì)基礎(chǔ)是簡(jiǎn)和牘的明確分工。漢晉時(shí)期的簡(jiǎn)牘有單用和合用兩種方式,單用的為木札牘牒,用于寫作一札可盡的短文;合用方式用于編成書冊(cè),寫作長(zhǎng)文。從出土文獻(xiàn)看,牘片有長(zhǎng)條形、長(zhǎng)方形、楔形、棱形、上圓下方等形狀,寬度0.8厘米—4.6厘米不等[3],長(zhǎng)度在漢尺二尺四寸到二尺八寸之間。一般根據(jù)事情的重要性來決定簡(jiǎn)冊(cè)的長(zhǎng)度,事情越重要,用簡(jiǎn)越長(zhǎng),所以漢晉時(shí)的官文書要比私人文書長(zhǎng)。但編簡(jiǎn)每枚只能書字一行,可容納的字?jǐn)?shù)非常有限,并不能滿足寫作需要。出土簡(jiǎn)牘實(shí)物中,郭店楚簡(jiǎn)《老子》甲乙丙編、上博簡(jiǎn)《孔子詩論》《容成氏》等,共有數(shù)十種先秦兩漢古籍都是寬1厘米的書字一行,寬2厘米以上的書字兩行,僅有特殊要求的歷譜簡(jiǎn)、標(biāo)題簡(jiǎn)、簿籍簡(jiǎn)除外。這表明,一般情況下每簡(jiǎn)書字一到兩行。為了增加每一簡(jiǎn)上字的容量,或加長(zhǎng)簡(jiǎn)牘,或縮小字體,或正反都寫。編聯(lián)以后,單簡(jiǎn)就變成書籍冊(cè)頁。從出土文獻(xiàn)來看,經(jīng)史及公文的編聯(lián)方式多是先編冊(cè),后寫字;民間文書的編聯(lián)方式則先寫好,再編冊(cè)。
西漢后期,簡(jiǎn)、牘、策的分工已明確,書籍冊(cè)頁的制作技術(shù)也已成熟。有了這個(gè)基礎(chǔ),人們就可寫作長(zhǎng)文、編撰著述了。在使用范圍上,牘札要比竹簡(jiǎn)寬。牘是書字的方版,容字較多,多用于經(jīng)史及公文寫作,每版可書字五到七行。這個(gè)優(yōu)點(diǎn)是竹簡(jiǎn)所不具備的,所以牘札的用途要比竹簡(jiǎn)寬廣。牘札文書在排版上與周代禮書不同,周代禮書是書名物于方版,每版書字五、七、九行不等;漢代札牘牒片都不寬,流行的格式是書字五行。《文選》卷一三謝莊《月賦》:“(陳思王)抽毫進(jìn)牘,以命仲宣。”李善注引《說文》:“牘,書版也。”[4]599卷二四潘岳《為賈謐作贈(zèng)陸機(jī)》李善注:“珥筆持牘,拜謁曹下。”[4]1155二者都是魏晉史事,寫作對(duì)象都是官文書,所以要用木牘。札是書字的木簡(jiǎn),長(zhǎng)條形,較窄,外形短小輕薄,用于寫作短文,適用面更廣。由此,漢代出現(xiàn)了筆札、遺札、札書等以札為中心的常用詞,和奏牘、書牘、負(fù)牘、持牘等以牘為中心的常用詞。
與簡(jiǎn)并行的是牒,《史記·荀卿列傳》裴骃《集解》云,牒是一種小木札,短簡(jiǎn)。《廣韻》卷五釋牒為書版,而《說文》也釋牘為書版。又說,簡(jiǎn),牒也;牒,札也,表明牒、牘、札是同義詞,都是指漢晉通行的短小簡(jiǎn)。牒的用途和札接近,但札以木為之,制作較難;牒則竹木均可,制作較易,使用更廣。《漢書·路溫舒?zhèn)鳌份d,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以寫書。顏師古注:“小簡(jiǎn)曰牒,編聯(lián)次之。”[5]2368牘、牒比簡(jiǎn)冊(cè)靈活,可以單執(zhí),版面較廣,書字比簡(jiǎn)多,可以寫作短文,摘錄資料,便于使用。
其次是文獻(xiàn)基礎(chǔ)。集作的文獻(xiàn)基礎(chǔ),是基于簡(jiǎn)策的文獻(xiàn)積累和文字表達(dá)功夫,這些已為漢魏士人所必備。因?yàn)閷懺趯iT制作的輕薄短小的木簡(jiǎn)上,故而這些文字也謂之札記。《漢書·張良傳》:“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dāng)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lián)次之也,聯(lián)簡(jiǎn)牘以為書,故云一編。”[5]2245這里說到需要將簡(jiǎn)牘聯(lián)編才能成書,表明單簡(jiǎn)所記是長(zhǎng)文著述的基本單位。《新序》卷一:“周舍曰:愿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后,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6]76文中周舍作記就是以單簡(jiǎn)所書為單位。王充著《論衡》,用的也是札記功夫。《論衡·自紀(jì)》云:“吾文未集于簡(jiǎn)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7]1195《定賢》篇云:“語筆墨之余跡,陳在簡(jiǎn)策之上,乃可得知。”[7]1120這兩處無異夫子自道,表明他著《論衡》的辦法是將平時(shí)積累的“集于簡(jiǎn)札”的資料編撰起來,“陳在簡(jiǎn)策”。這也表明,在漢魏時(shí)期,一個(gè)文士想要編書,必須將集于簡(jiǎn)札的文字綴合成文。《超奇》篇還談到一些失敗的典型,說不少漢代儒生不能在書牘上研治一經(jīng)一說,其中高者如谷子云、唐子高,也只能說書牘奏,而不能連結(jié)篇章。
最后是政治基礎(chǔ)。集作的政治基礎(chǔ),是漢代中央集權(quán)政治體制的成熟,以及察舉制度、議政制度的推行。兩漢時(shí)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xué)、明經(jīng)、尤異等十多種歲舉以及不定期開考的特科,還有鼓勵(lì)臣僚上書言事的政策。朝廷遇有大事,臣僚往往主動(dòng)上疏,帝王并不以為忤。隨著這些制度的有效運(yùn)作,數(shù)十位長(zhǎng)于寫作、工于議論的優(yōu)秀人士脫穎而出,利用各種機(jī)會(huì)頻頻上書,僅劉向一人就上疏數(shù)十次,大量奏議應(yīng)運(yùn)而生。漢代議政的奏疏因而也特別多、特別長(zhǎng)。這樣不僅左右了輿論導(dǎo)向,還引導(dǎo)了文壇風(fēng)氣,成為漢代士人修習(xí)長(zhǎng)文的重要?jiǎng)右颉!稘h書·張騫傳》就談道:“自騫開外國(guó)道以尊貴,其吏士爭(zhēng)上書言外國(guó)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yuǎn),非人所樂,聽其言。”[5]2695《東方朔傳》記載:“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xué)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shù),其不足采者輒報(bào)聞罷。”[5]2841可見,重大時(shí)事是臣僚上書的推動(dòng)因素,而帝王的號(hào)召和政策鼓勵(lì)是奏議文較快發(fā)展的根本因素。
在這些政策的推動(dòng)下,數(shù)十位名家應(yīng)時(shí)而起,成為兩漢奏議寫作的典范,奏議也成為成熟最早、發(fā)展最快的文體,不僅寫作數(shù)量多,而且被引用的也多。“前四史”中引用最多的就是奏議。漢代奏議更被譽(yù)為雄文,與詔令一起彪炳史冊(cè)。由于名家多,影響大,史上遂有所謂“漢名臣奏”之目,并以此作書名。《舊唐書·經(jīng)籍志》刑法類中就有陳壽的《漢名臣奏》,《新唐書·藝文志》故事類中另有《漢諸王奏事》《漢魏吳蜀舊事》《魏名臣奏事》,刑法類中別出《漢名臣奏》,這些都是漢晉時(shí)期的奏議總集。
二、集作的種類
《論衡》指出,漢代有“遵五經(jīng)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7]867四種著述方式,后三者指長(zhǎng)文和著述,皆與本文有關(guān)。我們以《論衡》所記為準(zhǔn),根據(jù)性質(zhì)的不同,可以將集作區(qū)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是匯輯眾簡(jiǎn)資料以記事說理的輯錄體。其特點(diǎn)是纂集他書資料為文,不是獨(dú)立創(chuàng)作而來,體式以史書和子書為主。史書方面,如《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guó)志》,以及東漢蘭臺(tái)、東觀、秘書省編撰的史書,漢末魏晉文士自作的史書,都是通過集作成文的。因?yàn)槠涫妨蟻碓炊嗤荆窌饔畜w裁,記事異體,每體對(duì)材料的要求不同,非一人獨(dú)立構(gòu)思所能成事,需要匯輯眾簡(jiǎn)材料。加之史書以敘事為主,不能過于依賴主觀創(chuàng)造。要做到這些,只能靠輯集材料。
輯錄體子書,可以《呂氏春秋》為典型。做法是先設(shè)綱目,再輯佚文,匯編眾書,以成著述。其八覽、六論、十二紀(jì)就是刪拾春秋戰(zhàn)國(guó)古事編成的[8]。由于內(nèi)容輯自他書,不是獨(dú)立成說,所以該書在思想上不能成一家。繼起的《淮南子》也有這個(gè)特點(diǎn),其書“錯(cuò)綜經(jīng)緯,自謂兼于數(shù)家無遺力”[9],總結(jié)了先秦多個(gè)學(xué)科的成果,是一部學(xué)術(shù)綜輯體著作。同類之書還有劉向《新序》,書中收錄先秦至漢初故事,春秋時(shí)尤多。察其來源,均出自《春秋三傳》《晏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國(guó)語》《戰(zhàn)國(guó)策》[6]2-3。做法是先立綱目,再采百家傳記成文。《新序》今本十卷,第一到五卷為雜事門,集合先秦子史古事一百零六條,六到十卷為刺奢、節(jié)士、義勇、善謀四門,各集古事十余條。《新序》雖然號(hào)稱子書,其實(shí)相當(dāng)于后世類書。劉向《說苑》二十卷,分二十門,每門收集一類資料,上自周秦諸子,下及漢代雜著,以類相從,各具篇目,便于稱舉。其材料來源十之八九仍可追溯[10]。據(jù)《漢書·藝文志》小注,劉向所序六十七篇都是這樣的書。賈誼《新書》后六卷也是采用這種方式編成的,由連語、雜事組成,部分談服色制度、禮樂官名,屬經(jīng)學(xué);部分論道術(shù),屬諸子之學(xué);部分言君道修政,屬史乘之學(xué)。每一種學(xué)問都有不同的資料來源,部分條文還可覆按,表明該書是靠輯錄成書的。以其多數(shù)論學(xué)術(shù),不切世事,故《史記》《漢書》未采用。其中《保傅》《保職》《胎教》《容經(jīng)》四篇,漢宣帝時(shí)被采入《大戴禮·保傅篇》,乃后人沿襲舊文。賈誼編撰此書時(shí),出于以立意為宗的目的,也各立門類。這表明部分漢代子書乃是一種以采摭史料見長(zhǎng)的文獻(xiàn)輯錄體,其集作之功主要體現(xiàn)在分門收集史料綴合成書上。
第二種是獨(dú)立構(gòu)思而成的創(chuàng)作體,有子書和長(zhǎng)文兩種形式。
子書方面,寫法是先立意,后作文。根據(jù)不同的主題,先寫成單文,再組合成專書。每篇單文,即為子書的一門。桓寬《鹽鐵論》即由六十篇單文組成,今本六十節(jié)。《法言》二十篇,即分二十節(jié)。《論衡》八十五篇,即列八十五節(jié)。其他如陸賈《新語》、揚(yáng)雄《太玄經(jīng)》、桓譚《新論》、崔寔《政論》、王符《潛夫論》、仲長(zhǎng)統(tǒng)《昌言》、荀悅《申鑒》、牟融《牟子》、曹丕《典論》、徐幹《中論》,皆設(shè)問難,論事析理,“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7]608,與輯錄體靠因襲前人成書異體。《論衡·超奇》指出,在漢代,“好學(xué)勤力,博聞強(qiáng)識(shí),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并出一時(shí)也”[7]606。桓譚“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zhèn)m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7]608-609。《佚文篇》云:“使長(zhǎng)卿、桓君山、子云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7]1195以上從多個(gè)角度指明其書之可貴、其人之難得。以其論事說理由意而出,無所假借,故謂創(chuàng)作體。寫法上以持論為主,故名其書曰論。據(jù)余嘉錫先生考證,漢魏人所著書,自桓寬《鹽鐵論》而下二十四家,皆獨(dú)造之書論,與經(jīng)書、史書異體。按照漢魏人的觀念,經(jīng)書稱“作”,史書稱“述”,漢魏人自作之子書,遂名曰“論”。這也表明漢魏諸子論事之書,實(shí)即后世之議論文[11]243-244,無論從文體還是著述看,都是如此。
子書之外,獨(dú)立的長(zhǎng)文方面,敘事物的大賦、論政事的奏疏也有這個(gè)特點(diǎn),《子虛》《上林》《二京》《三都》諸賦亦然,“皆以數(shù)篇,相為首尾開闔”[11]236。做法也是連綴多篇單文,最后合為一書。今日看來,這些儼然只是一篇篇長(zhǎng)文,拼合之跡已被湮沒。漢代士子應(yīng)朝廷詔舉上書,就是奏疏的一體,其內(nèi)部原來也分為不同篇章,各有專名,但因原稿不存,體例不可覆按。漢代最早的記載之一,是漢武帝時(shí)東方朔公車上書。《史記·東方朔傳》載其“初入長(zhǎng)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12],一篇上書竟然用去三千塊兒奏牘,以每牘容字百余計(jì),這篇奏疏有三十多萬字。像這樣的長(zhǎng)文,需要編聯(lián)眾簡(jiǎn)以成冊(cè)頁,如要增刪文字,就得打亂順序,插入新簡(jiǎn),重新排列。每增刪一二十字,竹簡(jiǎn)都要增刪一條。如用木牘,改得過多,也需要更換牘札。為避免反復(fù)刮削,作者在書簡(jiǎn)之前就必須先構(gòu)思好意思,再書簡(jiǎn)編冊(cè),但這樣成文緩慢,需要較長(zhǎng)的準(zhǔn)備時(shí)間。
這種集作的文獻(xiàn)形態(tài),是木札分書的長(zhǎng)文,每版書字五到七行,眾簡(jiǎn)相連,內(nèi)容銜接,組合成文。文風(fēng)隨所用文體而變化,但都有斗靡夸多的傾向,故而這種文章篇幅普遍較長(zhǎng),詞采趨麗,但閱讀起來費(fèi)時(shí)費(fèi)力。漢武帝讀東方朔上書,就需要“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天子“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12]。簡(jiǎn)札不僅用來作賦,還用來積累資料。《藝文類聚》卷五八引謝承《后漢書》:“王充于宅內(nèi)門戶壚柱,各置筆硯簡(jiǎn)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13]《太平御覽》卷六○二引王充《論衡》:“筆札之思,歷年寢廢。”[14]2710這里所記《論衡》成書背景、過程、方法,正是漢晉文士所常用的集作方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集作的創(chuàng)制過程
集作之法專門用于寫作長(zhǎng)文,特點(diǎn)是先誦習(xí)典范之文,掌握相關(guān)資料和知識(shí),然后在單簡(jiǎn)上構(gòu)思撰寫,最后再書寫上簡(jiǎn),制作書冊(cè)。寫作時(shí),將簡(jiǎn)牘悉陳于前,各盡精思,悉陳其義,“心思為謀,集札為文,情見于辭,意驗(yàn)于言”。名篇有“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7]611-612,此即集作。
集作的創(chuàng)制有兩個(gè)步驟:第一步,確立題目,選定體裁,依題定體,依體定名。先擬好大題目,作為一書或長(zhǎng)文的總名,然后再根據(jù)題目要求和寫作目的去總體構(gòu)思。由于長(zhǎng)文和專書結(jié)構(gòu)宏大,一般要分解為不同部分,所以總名之下還會(huì)再立若干小題目,寫成半獨(dú)立性質(zhì)的篇章,通過這種方式來確定整個(gè)作品的結(jié)構(gòu)和布局。第二步,在單簡(jiǎn)上輯錄資料,分撰篇章,整合成文。如是專書,則要寫好句子段落、不同篇章,安排好組織結(jié)構(gòu)。為了便于辨認(rèn)和區(qū)分,各個(gè)章節(jié)還要寫上“名題”。這一布局,適用于專書和長(zhǎng)文兩種著作形態(tài)。
對(duì)于專書來說,書名即作品的總標(biāo)題,里面分卷的各個(gè)門目即小標(biāo)題。1959年出土的武威《儀禮》漢簡(jiǎn)甲本七篇和乙本《服傳》就各有標(biāo)題。睡虎地秦簡(jiǎn)的標(biāo)題還有簡(jiǎn)牘背面寫標(biāo)題、首簡(jiǎn)寫標(biāo)題和編末列目錄三種不同的書寫格式[15]82。南北朝抄本圖書,還部分保存了這種大題目下包含多個(gè)獨(dú)立篇章的結(jié)構(gòu)形式,即是承自漢魏簡(jiǎn)冊(cè)的古老書籍制度。其中的獨(dú)立篇章相互之間看似聯(lián)系不強(qiáng),實(shí)則暗含一種總體設(shè)計(jì)思想和內(nèi)容關(guān)聯(lián)。這一過程,用司馬相如的話說,就是“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zhì)。一經(jīng)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必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nèi),不可得而博覽”[14]1482。前兩句說的是將摘抄在簡(jiǎn)牘上的資料連綴成文的集作方式,“合”“列”指將簡(jiǎn)牘札記組合成整一篇章。后面“一經(jīng)一緯,一宮一商”指書于單簡(jiǎn)的句段,乃作賦之跡,即辭賦語言,看似事象繽紛,其實(shí)各有來歷。“包括宇宙”指大賦對(duì)資料、構(gòu)思的要求。資料需要包括天地人事,范圍廣闊。構(gòu)思也要涵括宇宙,有較高的概括性。文中還談道,“相如為《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fù)與外物相關(guān),控引天地,錯(cuò)綜古今,忽然而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后成。”[14]1482之所以冥思苦想,百日后成,一是因?yàn)榇筚x宏偉,創(chuàng)作頗費(fèi)時(shí)日;二則因?yàn)橄嗳缥乃歼t鈍,為文緩慢,如《西京雜記》所說:“枚皋文章敏疾,長(zhǎng)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shí)之譽(yù)。”[16]并且創(chuàng)作這樣的長(zhǎng)文,需要擴(kuò)大閱讀范圍,如同揚(yáng)雄所說,要做大賦,先要讀賦千首,所以才久歷歲月。這樣兩種不同的風(fēng)格各有適用范圍,正所謂“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cè),用相如”[16]。可見,集作之文多施于廟堂,高文典冊(cè),其體莊重,寫作要求高,成文不能圖快;軍書檄文成于軍中,軍情緊急,急速為貴,所以成文較快。
集作對(duì)文獻(xiàn)資料有很強(qiáng)的依賴性,需要借助官府藏書。因此,兩漢魏晉時(shí)的著述及長(zhǎng)文,多有官方背景,只是原書不載,詳情不為人知。西漢尚書省、石渠閣、天祿閣和東漢蘭臺(tái)、東觀、秘書監(jiān)是理想的集作場(chǎng)所,從這里走出的名儒極多。之所以成為名儒,除了自身天賦外,依托文館這個(gè)育才之地亦為重要原因。他們正是因?yàn)檫M(jìn)入書府,遍覽經(jīng)籍,才能寫成偉大著述。司馬相如的大賦就是憑借官府藏書寫成的,漢文帝時(shí)枚乘、鄒陽、莊忌的辭賦,也是依靠了梁孝王府藏書,有了這個(gè)文獻(xiàn)寶庫,府中文士才能“抽秘思”“騁妍辭”[4]232。
集作的有序展開,還需要充足的物質(zhì)資料。漢代沒有紙張,只有簡(jiǎn)牘。只有官府才具備這些物質(zhì)條件,這也是漢代長(zhǎng)文和著述多成于官府的重要原因。東漢前期,文士主要在蘭臺(tái)、東觀集作。漢末魏晉成立秘書監(jiān)以后,則多在秘書監(jiān)、中書省等多書之地。這里簡(jiǎn)牘和筆墨都有穩(wěn)定來源,能夠保證及時(shí)供給。班固《漢書》八表及天文志,就是其妹班昭就東觀藏書續(xù)成的。黃香的賦箋奏書令五篇,也是成于東觀。左思的賦作也是這么寫成的。他先是居家,作《齊都賦》,一年乃成。后來要作《三都賦》,就只能利用其妺左芬入宮的機(jī)會(huì),移家京師,進(jìn)入秘書省查閱書籍,摘抄資料,博訪名儒,收集古事。即便如此,還“構(gòu)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17]。傅毅、班固、賈逵的著述之所以數(shù)量多、篇幅長(zhǎng),正是因?yàn)樗麄冊(cè)谔m臺(tái)、東觀點(diǎn)校秘書,利用在職的機(jī)會(huì)成文。漢晉賦家憑著上述條件,就能寫出凌跨一代的偉大賦作,“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jìng)于使人不能加”[5]3575。家貧無書的民間人士沒有這樣的條件,他們?nèi)绻蚕胍鴷魑模荒芡ㄟ^其他途經(jīng),比如出游市肆,閱所賣書,順便誦憶,或是從人假借誦讀,以此方式去通百家之言。
上引史料所載,正是典型的大篇章集作,往往先廣征文獻(xiàn),定好框架,再連綴成文。其中材料多數(shù)來自前代舊籍,所據(jù)資料,因所寫文章的性質(zhì)而不同,論經(jīng)義者多據(jù)經(jīng)解,論史事者多據(jù)史書。漢晉大賦多言都邑、地理、方物,具有“方志性”[18],備載一方之山川建筑、風(fēng)物英杰。東漢以下的京都大賦,敘事還有征實(shí)特點(diǎn),逐漸遠(yuǎn)離漫無邊際的夸張,這樣,憑空杜撰就更不能成事,只能多依地理方物之書來成文。如左思《三都賦》云:“擬議數(shù)家,傅辭會(huì)義,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tǒng)其異。”“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17]其篇章結(jié)構(gòu)、措辭命意多有模擬之跡,而少創(chuàng)造之功,成就明顯不及兩漢奏疏。張衡《二京賦》也是模擬班固《兩都賦》,精思傅會(huì),十年乃成。凡是這樣的書,名物訓(xùn)詁、類聚古事都多,各有來歷,后人閱讀,初看不明其義,所以需要注釋。《隋書·經(jīng)籍志》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薛綜、晁矯、武巽注張衡《二京賦》,張載、劉逵、衛(wèi)瓘、綦毋邃注左思《三都賦》,項(xiàng)氏注《幽通賦》,蕭廣濟(jì)注木玄虛《海賦》,徐爰注《射雉賦》。這表明,漢晉大賦莫不內(nèi)容繁富,成于集作,難讀難懂,需要跟隨專家學(xué)習(xí)。他們的制作,又成為后人集作的范本。據(jù)《文選》卷二四陸機(jī)《答賈長(zhǎng)淵》李善注引謝承《后漢書》,東漢帝王皇后、將相名臣頒發(fā)的策文通訓(xùn),都“條在南宮,秘于省閣”[4]1141,作為典范供人習(xí)讀,揣摩文體。就整個(gè)兩漢情況看,恐怕不止詔策,還有奏議、辭賦,也具有這樣的典范性。
簡(jiǎn)牘出土文獻(xiàn)也為我們提供了佐證,按內(nèi)容可分兩類:一類是文書簡(jiǎn),種類有政府公文、簿籍檔案、西北邊地關(guān)津驛傳文書等,體式有律令、書檄、信札、歷譜、名刺、卜筮之類,主要為應(yīng)用類文書,此類較多;另一類是書籍簡(jiǎn),《論語》《孝經(jīng)》《左傳》《國(guó)語》《法言》等六藝之書,主要選取其中可為世用的部分誦習(xí)傳承,此類較少,極少見到大賦、策論的出土資料[19]。由于其內(nèi)容專門、細(xì)碎,所以在傳世文獻(xiàn)中很難找到對(duì)應(yīng)物。但在文書制度上是一致的,我們從應(yīng)用類文書中可以窺見其體制。據(jù)程鵬萬《縑帛書寫制度研究》,簡(jiǎn)冊(cè)繕寫有連寫式、提行留白式、分欄式。連寫式主要見于篇幅較大、完整連續(xù)的成冊(cè)書籍,由于各有體例,內(nèi)容相連,不能留白或分欄,故需要連寫。提行留白式主要用于器物冊(cè),分欄式主要用于史書有表格的部分、日書、遣冊(cè)、喪葬類文書[15]71-95。另外,諸子類及《墨經(jīng)》等部分有傳注的經(jīng)書,為了便于識(shí)別,遂在排版上分為兩截,旁讀成文。本文所論的集作體制主要存在于連寫式,最后成書時(shí)不提行連寫,定稿前文章有較長(zhǎng)的材料積累和文句篇章構(gòu)思結(jié)撰功夫,以此方式寫出來的書籍,從標(biāo)題、篇卷到語句文風(fēng)都與紙書有異。由此可見,簡(jiǎn)牘文獻(xiàn)載體對(duì)文章寫作有多方面的限制。
四、集作之文的體制特征
“體制”一詞,相對(duì)于不同的對(duì)象,有不同的含義。就本文而言,指文章著述的外在形貌、內(nèi)部結(jié)構(gòu),與所用文體及文風(fēng)均有關(guān)系。漢魏晉初長(zhǎng)文用的是簡(jiǎn)冊(cè)體制,因而具有簡(jiǎn)冊(cè)之文的外在形貌和內(nèi)部結(jié)構(gòu)。
這種體制,反映在作品形貌上,是名為長(zhǎng)文,實(shí)是專書。《三國(guó)志·魏書·國(guó)淵傳》即云:“《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20]是大賦而稱為書,顯然是根據(jù)作品體制而言,在當(dāng)時(shí)人看來,它等同于一本書。而東方朔的公車上書,《史記》也稱為書,需二人共持舉,表明漢魏長(zhǎng)篇奏疏、宏大之賦,分量都等同于一本書。反過來看,則漢魏時(shí)期的一本書也只相當(dāng)于一到多篇長(zhǎng)文,不分卷的相當(dāng)于一篇長(zhǎng)文,分卷分門的相當(dāng)于多篇長(zhǎng)文。《史記·張良傳》中黃石公送給張良的“一編書”,就是編簡(jiǎn)。據(jù)同條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引劉歆《七錄》,老父帶來的是《太公兵法》,西漢藏本一帙三卷,表明還有書衣。雖有三卷,但估計(jì)也只有兩三千字,略相當(dāng)于一篇長(zhǎng)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的漢魏古籍,多數(shù)只有一到三卷,皆可作如是觀。
集作文獻(xiàn)的篇章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是,一篇長(zhǎng)文分為數(shù)篇,每篇皆有獨(dú)立篇名。《漢書·藝文志》內(nèi),凡諸子、史書、文集中的篇,皆簡(jiǎn)策之名,一篇即后世一卷。做法是每段長(zhǎng)文闡述一事,以說理為主,根據(jù)文意而截分為若干篇章。篇章既分,自不能不為之各立標(biāo)目,因而一書一文之內(nèi),又有各篇章之名。如賈誼《治安策》,原稿應(yīng)由多種論國(guó)家長(zhǎng)治久安的策書組成,每篇策書各有專名。《漢書·賈誼傳》所錄僅6486字,而所言“六太息”,書中只有其三,顯然是被班固刊落或整合掉了。由此反推,則原疏當(dāng)有一萬數(shù)千字,絕非一編簡(jiǎn)策所能容納,其勢(shì)不能不分為數(shù)篇,方便觀覽[11]235。《漢書·賈誼傳》云:“臣竊惟事勢(shì),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zhǎng)太息者六。”[5]2230由此可知,《治安策》原文由八篇策書組成,班固取其論事切要者,刪節(jié)成文,故首言“其大略曰”,篇末贊語復(fù)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5]2265今原文尚分散在《新書》卷一《數(shù)寧》《藩傷》《藩強(qiáng)》與卷二《五美》《制不定》《危亂》諸篇,為其明證,其原稿則為《漢志》諸子略之“賈誼五十八篇”[5]1726。此五十八篇與痛哭一、流涕二、長(zhǎng)太息六的篇章分合、具體名稱,王應(yīng)麟《漢藝文志考證》有詳盡考證,其論可信。賈誼《新書》分事勢(shì)、連語、雜事三部分。前四卷事勢(shì)三十一篇,有二十三篇被摘入《漢書·賈誼傳》及《食貨志》等史志。此二十三篇與《漢書》所引賈誼文之間的關(guān)系,閻振益、鐘夏《新書校注》前四卷于每篇下的校注首條各有詳細(xì)考辨[21],可以信從。這些校注提供的線索,更能分辨《治安策》與其下各策的總分關(guān)系,據(jù)此又可窺見漢代古人作書編撰之法。
“前四史”中,類似這種形式上為一書一文,其實(shí)由多篇單文組成的例子還有很多。另一部分子書則非原編,乃后代史臣或館閣校書者刪節(jié)之本,皆截取自當(dāng)時(shí)以聯(lián)編簡(jiǎn)策編撰的長(zhǎng)文。如賈山的子書《至言》,據(jù)晁錯(cuò)上疏所舉,篇名有《守邊》《備塞》《勸農(nóng)》《力本》等多個(gè),此即《漢志》諸子略之“賈山八篇”[5]1726,晁錯(cuò)采其說,著書三十篇,即《漢志》子部法家類之“晁錯(cuò)三十一篇”[5]1735,由多篇單疏組成,其中也有連接之功。桓寬《鹽鐵論》討論六十個(gè)問題,據(jù)文意分為六十篇,但行文上卻前后相接,并無拼合之跡。可見,合多篇為一書一文,乃漢代子書、辭賦、策論、奏疏的常用體例,今人或不通古書體例,對(duì)此頗有不解。
《漢志》中,此類長(zhǎng)文寫得最多的是董仲舒,有128篇,其次是賈誼58篇、劉向67篇、桓寬60篇、揚(yáng)雄38篇。凡此諸篇,皆可視為專書或長(zhǎng)文內(nèi)部之一篇,后被編入子書,而仍保留其篇目名,原稿則是一篇單疏或論議。此種做法,即《四庫全書總目》所謂“一段立一篇名”[22]。《史記·陸賈傳》云:“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12]2699此即為諸篇奏疏單獨(dú)成文上奏之明證,其中尚多處自稱為“臣”的地方,此等文字即奏疏原稿中的字樣。據(jù)《漢志》儒家類,陸賈共有23篇這樣的單文,這樣的文章一多,作者又是名臣,史臣修史必為其作傳,“連綴十?dāng)?shù)篇,合為奏疏一篇”[22],而不能全文摘錄。或?yàn)槭窌w例所限,而沒其篇目;或?yàn)閿⑹轮悖盍颜露危嵉勾涡颍允烦季庝浿E。
集作文獻(xiàn)在排版上,是“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5]583,即由單一的牘札組成書冊(cè),每牘書字五到七行,書寫時(shí)一般不提行,從頭至尾連寫,看上去是不分段的連排之文。寫作也沒有篇幅長(zhǎng)短的限制,可以“連句結(jié)章,篇至十百”[5]583。一般每版一欄,只寫正面,不寫反面。偶有分上下兩欄的,那是因?yàn)闀w例要求。書成之際,各有名題,一般放在簡(jiǎn)牘的首端或末尾,多數(shù)書于正面,少數(shù)書于反面[5]82-85。西晉太康二年(281年)竹書七十五卷,其中六十八卷都有名題,另五卷因簡(jiǎn)牘損毀,本有名題而不可復(fù)見。可見,名題是集作之文在文獻(xiàn)體制上的重要表征之一。
在句式上,西漢集作之文以散體短句居多,很少有對(duì)稱句式。東漢奏議則四、六、八字句式漸多,一句之中,節(jié)奏更為多變,散句和排偶句相參[23]124-125。這種趨勢(shì),從西漢后期就開始顯露,魏晉時(shí)更為鮮明,辭賦和奏疏中都有。這既是文學(xué)語言發(fā)展的規(guī)律使然,也與作品內(nèi)容不無關(guān)系。漢代奏議、子書多依傍經(jīng)義立論,受經(jīng)書觀點(diǎn)材料的限制,不能自由發(fā)揮,故多散體;脫離經(jīng)義自作的辭賦或其他文體則可追求語言對(duì)稱之美,因而整麗。
在篇章分合上,由于簡(jiǎn)冊(cè)都以竹木編成,每簡(jiǎn)都容納字?jǐn)?shù)不多,字多者則離析為若干牘札,所以就形成似斷實(shí)連的文意和文勢(shì)。既然在形式上已離析為不同部分,則必為篇名以別之,于是各有獨(dú)立篇名。此僅為習(xí)讀之便,并非如后人所說隱含某種微意。所以,一篇序文有時(shí)被分為三篇,一個(gè)門類有時(shí)被分為上下。漢代經(jīng)史子書都有這種細(xì)分的體制,皆由于簡(jiǎn)冊(cè)之繁多,其勢(shì)不可合而為一,蓋出于不得已。后世以紙代替簡(jiǎn)冊(cè),一篇所載足以容古書百余簡(jiǎn)的內(nèi)容,這種分合就失去了意義。但是,來自簡(jiǎn)牘時(shí)代的分合之跡仍被部分保留下來,導(dǎo)致今人疑惑或誤解。
集作之文在篇章結(jié)構(gòu)安排上,最為整密劃一的是獨(dú)立構(gòu)撰的奏議,如董仲舒的《元光元年舉賢良對(duì)策一》,全文1930字,有多個(gè)“臣聞”“臣謹(jǐn)案”,相當(dāng)于漢魏晉賦中的“爾乃”,都是段落的起訖、分層的標(biāo)志。但全文筆意連貫,辭氣完足,并未因分段而阻斷文氣,這得益于集作本身的優(yōu)勢(shì)。這種體制,有利于大文章的寫作。簡(jiǎn)牘聯(lián)編成冊(cè)后,就不再受單簡(jiǎn)的限制,相當(dāng)于紙書作文,創(chuàng)作者可以將精力貫注到撰文上,一簡(jiǎn)一句,鋪陳而下,再加編聯(lián),即可組成一篇大賦或策論,因而其體制也是整密的。
漢晉子書則是匯集眾簡(jiǎn)成書,文字各有來歷,獨(dú)立成條,所以結(jié)構(gòu)就顯得比較松散。如《說苑》卷一《君道》前三條,分別來自《左傳·昭公八年》《呂氏春秋》《管子》等,長(zhǎng)數(shù)十字或百余字,一簡(jiǎn)可容,當(dāng)時(shí)摘錄于三條單簡(jiǎn),聚合成編。編出的書類似唐宋史料筆記,形聚神散,但經(jīng)過編次,被統(tǒng)攝到同一門目。
漢代簡(jiǎn)冊(cè)實(shí)物的出土也為我們提供了證據(jù)。陳夢(mèng)家《由實(shí)物所見漢代簡(jiǎn)冊(cè)制度》提到,漢代簡(jiǎn)冊(cè),有五道、四道、三道、二道編繩四種類型[24]。截分為二道三段的形式為常見制度。居延所出永元器物簿,長(zhǎng)一尺,二道一段。共77枚漢簡(jiǎn),由五封不同的冊(cè)書拼接而成,先寫后編,各個(gè)部分獨(dú)立成編。長(zhǎng)沙楊家灣七十二簡(jiǎn),長(zhǎng)六寸,二道一段,也是先編后寫,這適合于一般的簡(jiǎn)單書寫名物登記。從用簡(jiǎn)數(shù)量看,有單簡(jiǎn)和雙簡(jiǎn)兩種形式。單簡(jiǎn)一般是牒書,一簡(jiǎn)僅記一事。如陽朔二年(前23年)傳車簿,一簡(jiǎn)僅記一輛傳車。雙簡(jiǎn)則為對(duì)上級(jí)部門作簡(jiǎn)要匯報(bào)的呈文,兩行字寫盡[25]。而甘肅臨澤出土的西晉簡(jiǎn)冊(cè)情況又不同,整套木簡(jiǎn)27枚,兩道編繩,編繩壓住了簡(jiǎn)文,說明是先寫后編[26]。先編后寫之冊(cè)主要用于需要繪圖之書,一般書籍都是先寫好再編冊(cè)。書寫方式如果是一部自有體例的專門書籍或長(zhǎng)文,則從頭至尾不分段,不提行,不分欄。如果是表格或器物冊(cè),則分上下兩欄或三欄,集作方式主要是先寫后編,獨(dú)立成篇[15]71。
余 論
集作促進(jìn)了大賦、奏議及諸子論說體著述的較早成熟。有了集作方式,辭賦就可以鋪張揚(yáng)厲,政論可以氣勢(shì)磅礴,著作可以深廣宏富,由此凝練成一代偉麗文風(fēng)。大賦研究成果較多,這里只談奏議及論說體諸子。這二者其實(shí)是一回事,因奏議為奏事之文,論議為論事之文,由論事之文發(fā)展為論說體諸子順理成章,由一種寫法凝練為一類文體,文體又聚合成一部著述,寫法—文體—著述,成為孕育作品、催生文體的重要機(jī)制。《論衡·對(duì)作篇》談到,漢人最重視的文章是上書奏記,寫作也最繁密。《佚文》更云:“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也……文人宜遵五經(jīng)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dāng)賢也。”[7]876由此可見風(fēng)會(huì)之盛。在王充的學(xué)術(shù)視野中,書論和奏議就是一體的。而簡(jiǎn)牘的普及又促進(jìn)了這類文章的寫作,因此奏疏是漢魏晉時(shí)期普及程度最高的文體,從論事的政論到說理的議論,全面覆蓋。嚴(yán)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guó)六朝文》兩漢部分收文3629篇,奏議即有1180篇,占近1/3。這僅是以篇計(jì),若以篇幅計(jì),則占大半。因詔策、箴銘、頌贊都是短文,十多篇才相當(dāng)于奏疏一篇。奏議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促使它成為兩漢文章體系中流行程度最高的文體,僅西漢即出現(xiàn)數(shù)十位長(zhǎng)于奏疏的名家。例如谷永,是西漢后期著名的筆札作家,在這方面與董仲舒齊名。《漢書》載其長(zhǎng)文7篇,文體為對(duì)策、疏、議,在西漢數(shù)量最多。《論衡》卷一三《效力篇》指出,能上書日記者為文儒,名家如谷子云、唐子高、董仲舒、揚(yáng)子云,“章奏百上,筆有余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7]582。東漢魏晉長(zhǎng)于筆札的文士更多,蔡邕、張衡都是這方面的名家。《后漢書》《三國(guó)志》《晉書》的列傳中,載錄有奏議和書論的作者有數(shù)十位,《典論·論文》更將奏議和書論連帶列舉,將其視為漢魏間最重要的四種文體,由此可見集作方式對(duì)奏議寫作及文體成熟的促進(jìn)作用。
奏議的繁榮固然是由于漢朝政府的提倡,但也與文獻(xiàn)載體提供的方便有關(guān)。漢魏時(shí)有鼓勵(lì)臣民上書的風(fēng)氣,而簡(jiǎn)牘取材及書冊(cè)制作的簡(jiǎn)易又為其發(fā)展提供了便利,多種因素使得漢代奏議制作繁多。明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分六十四門,雖然名目過繁,但類聚作品之多,足資參考。其中漢魏作品的分量之大,遠(yuǎn)過六朝。“前四史”中數(shù)百個(gè)上奏、上疏、上書、對(duì)曰,都是名臣對(duì)策上疏的顯著標(biāo)志。文中常有“臣聞”“臣謹(jǐn)按”等字眼,均為奏疏的常用語。從秦始皇時(shí)李斯上書諫逐客起,到漢代,奏疏形成一個(gè)持續(xù)四百年的高潮。西漢以上書著名的有賈誼、晁錯(cuò)、東方朔、公孫弘、鄒陽、終軍、梅福、司馬相如等。其中董仲舒最著名,《漢書》本傳稱其上疏條教百二十三篇,今本《漢書》尚載九篇。東漢魏晉風(fēng)氣稍歇,但亦不乏實(shí)例,表明上書言事,乃是漢魏士人為官立身的基本能力。奏疏因?yàn)橛写罅孔髡叩膮⑴c,而成為率先成熟的文章類別,政治地位亦僅次于詔策,而居第二。因此,曹丕《典論·論文》列舉漢魏文章四科八體,而首舉奏議,表明其地位之高。
集作的真正普及是在紙簡(jiǎn)并存時(shí)代,也即西漢后期到西晉前期。紙代替簡(jiǎn)成為主要書寫材料,則意味著集作的結(jié)束。據(jù)研究,從1933年新疆羅布淖爾發(fā)現(xiàn)西漢晚期紙張起,被發(fā)現(xiàn)的考古實(shí)物紙共有8次,最晚的為東漢甘肅懸泉置紙書。其所發(fā)現(xiàn)的紙,與成熟紙張有很大的差異,以致學(xué)界對(duì)于其是否可稱為紙都存在爭(zhēng)議[27]。紙張?jiān)跐h魏僅為少數(shù)人掌握,所產(chǎn)紙也質(zhì)量不高,書寫效果不佳,尚不能替代簡(jiǎn)策[28]。
在漢魏晉時(shí)期,真正對(duì)集作形態(tài)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是帛書。這一時(shí)期簡(jiǎn)牘、縑帛長(zhǎng)期并行,而東漢后期,隨著造紙術(shù)的進(jìn)步,紙張也應(yīng)用日廣。縑帛價(jià)格昂貴,并不適合大面積使用。所以,漢魏晉時(shí)的書籍文章一般都是先在簡(jiǎn)牘上寫初稿,做修改,最后才書寫上帛,當(dāng)時(shí)稱“上素”。漢魏晉時(shí)的官府藏書都有素書定本。由于縑帛和紙張都比簡(jiǎn)牘寬,便于整體構(gòu)思,所以其對(duì)創(chuàng)作帶來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帛書雖然不適合作為寫作的底稿,但可用于謄清和定稿。書籍文章“上素”之際,在書寫和排版上也和簡(jiǎn)牘有較大差異,“上素”和書紙以后帶來的文章形貌的變化,也會(huì)促使作者對(duì)創(chuàng)作做出調(diào)整。這樣勢(shì)必對(duì)基于簡(jiǎn)牘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反激,促進(jìn)作者在遣詞造句、布局謀篇上進(jìn)行調(diào)整和改進(jìn)。因此,紙簡(jiǎn)縑帛并行對(duì)文章書籍的集作形態(tài)確有影響。最明顯的改變就是,東漢以來,以立說和立意見長(zhǎng)的子書,以馳騁文筆為特征的大賦、策論、議對(duì)越來越多。反映在文章本身,則是體制越來越縝密,句式越來越整齊,文風(fēng)越來越宏肆。東漢以前書籍文章那種語意跳脫、語氣不接的結(jié)構(gòu)特征也發(fā)生改變,語法修辭錯(cuò)誤也越來越少。書籍形態(tài)改為紙書后,部分文章的集作形態(tài)依然隱約可見,這也反證了紙張縑帛對(duì)簡(jiǎn)牘書寫的影響。
集作之法也帶來一定的弊端:一是造成部分作品結(jié)構(gòu)松散,文意冗雜,閱讀困難。部分段落劃分拼合不合理,部分文章標(biāo)題與文意不合。二是造成言事不實(shí)的風(fēng)氣,如《論衡》所說:“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shí)……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7]381喜歡繁多、修辭夸飾是東漢著作的現(xiàn)狀,這種以多為美的審美觀以及連篇累牘的文獻(xiàn)形態(tài),不全是文藝觀使然,背后還有書籍制度的因素。
本文的研究表明,文章體式不僅因時(shí)代而異,更因文獻(xiàn)載體而異。有什么樣的文獻(xiàn)載體,就會(huì)有什么樣的文章體式,文獻(xiàn)載體的物理特征決定了所書之文的篇幅、式樣、文風(fēng)。漢晉時(shí)期的書籍以單簡(jiǎn)和編冊(cè)為載體,前者僅有一片,容字?jǐn)?shù)行;后者簡(jiǎn)牘聯(lián)編,容量無限,因而就產(chǎn)生長(zhǎng)文和短制兩種不同體制的文章形態(tài)。漢晉文章之所以呈一長(zhǎng)一短兩極分化狀態(tài),之所以有那么多短文體式和數(shù)種長(zhǎng)文成熟與通行,從根本上說,是文獻(xiàn)載體的物理特征造成的,這乃是古來文體發(fā)生的一個(gè)規(guī)律,是早期文體孕育萌生的一個(gè)生成機(jī)理。
注釋
①具體論述可參看查屏球《紙簡(jiǎn)替代與漢魏晉初文風(fēng)》(《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05年第5期)一文。②簡(jiǎn)形制狹長(zhǎng),每枚只能容字10到20多個(gè),并不適合作為文章書寫單位獨(dú)立使用,只能聯(lián)編書寫,制作書冊(cè)。牘短小靈活,僅長(zhǎng)尺余,可容納100至200余字,方便攜帶,是短文書寫的一般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