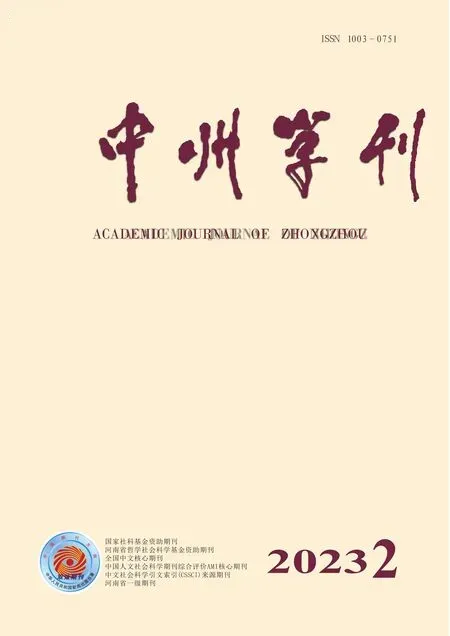老子不老:作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張再林
一、中國思想史的“阿喀琉斯之踵”:儒法之爭
一旦回顧中國思想史,我們就會發現,先秦至清末民初,一直都有儒法之爭以或隱或顯的方式貫徹始終。它作為中國思想史上最勢不兩立也最具聚焦性的理論之爭,如同我們民族身體的“阿喀琉斯之踵”,使我們對之欲罷不能。
可以說,儒學的開創者孔子正是這種儒法之爭的真正開啟者。在《論語·為政》中他曾對該思想爭論做出了高度概括性的總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對于孔子來說,前者以其刑、政的“他律”的力挺代表了法家的思想路線,后者則以其禮、德的“自律”的高舉代表了儒家的思想路線。一者治標,一者治本,其優劣自見。
緊步孔子的后塵,也伴隨著法家學說的與日俱顯,孟子將儒家對法家的批判推向新的理論制高點。他的“王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是對法家愈騖愈遠的“唯利主義”的奮力糾偏;他的“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的“王霸之辯”,則仰賴我們民族深深積淀的“厚古薄今”的文化習見,代表了戰國之際儒家后起之秀欲與法家一決高下的理論宣言。
另一方面,在這場沒有硝煙的儒法之爭中,挾春秋戰國群雄爭霸雷霆之勢,先秦法家同樣是不遑多讓,其理論攻勢亦咄咄逼人。就儒家所高標的道德“自律”,法家的理論集大成者韓非針鋒相對地指出:“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韓非子·用人》)對于韓非來說,正如從“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推出沒有“自圓之輪”那樣,從“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則推出沒有“自善之民”。這樣,儒家的道德“自律”顯然就成了欺世之談,而“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的法的“他律”大行其道就成了韓非子政治學說之理所當然。
人們看到,這場爭論不僅在深度上以其直切要害令人嘆為觀止,而且在廣度上也為世所罕見。就其涉獵人性、倫理及政治諸多論域而言,這場爭論實際上是中國古代“修齊治平”一切理論爭端的真正開山。因此,除了“自律”與“他律”之爭外,我們還看到了關于“性善”與“性惡”之爭,“取義”與“取利”之爭,“教化”與“賞罰”之爭,“尚文”與“尚功”之爭,“情本”與“威本”之爭,“禮治”與“法治”之爭,“法先王”與“法后王”之爭,如此等等。具體地說,當儒家提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時,法家則提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當儒家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時,法家則提出“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商君書》);當儒家提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賁》)時,法家則提出反對“濫于文麗而不顧其功”(《韓非子·七征》);當儒家提出“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時,法家則提出“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當儒家提出“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時,法家則提出“民固驕于愛,聽于威矣”(《韓非子·五蠹》);當儒家提出“為國以禮”(《論語·先進》)時,法家則提出“寄治亂于法術”(《韓非子·大體》);當儒家提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而以“先王”的忠實信徒自許時,法家則宣稱“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韓非子·五蠹》),并對那種“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法先王者皆盡嬉笑怒罵之能事,將其統統視為愚不可及的“守株待兔”之輩。
正是這種無處不在的兩極對立,使儒法之爭被置于先秦諸子之爭的核心,并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具根本性、最為代表性的爭論。同時,也正是二者之間水火不容的“二律背反”,使儒法關系一開始就處于此消彼長之中。故秦平定六國、一統天下的勝利既是政治上的勝利,又是思想上其所堅持的法家路線的勝利,并且這種勝利是以儒家節節敗退為巨大代價的。這也說明了為什么當秦的統治易幟為漢的統治時,漢代思想家紛紛倒戈,無不從儒家的立場觀點抨擊法家,從“尊法抑儒”變為“尊儒抑法”,從法家的“專決于名而失人情”變為儒家的“親親尚恩”“仁者愛人”。如司馬談謂:“法家不別親疏,不疏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論六家要旨》)班固談及法家時則稱:“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書·藝文志》)而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推出,與其說是統治者意氣為之的矯枉過正之舉,不如說是這種此消彼長之無可逃匿的大勢所趨。
固然,漢宣帝訓導太子所言“漢家自有制度”的“王霸雜之”,看似把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儒法熔為一爐,實際上只是使傳統的儒法之爭從顯性變為隱性,并未消解二者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縫。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正如從古至今的學者所揭示的那樣,這種振振有詞的“王霸雜之”的儒法兼舉,實則是打著儒家的旗號,走著法家道路的儒法兼舉,是以儒家為緣飾之具,實售法家之貨的儒法兼舉,一言以蔽之,也即“陽儒陰法”“外儒內法”。盡管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家對法家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制衡,但這并不妨礙“嚴而少恩”的秦制依然在現實中一意孤行。故在“視民如傷”“民貴君輕”的不無華麗的大旗下,人們看到的是天下無告之民的四處呼號奔走,是后儒“三綱說”這一新理法規定下的上下、尊卑之涇渭分明,是酷吏從“化虎而吃人”演變為“冠裳而吃人”的過程。因此,酒是舊的,裝酒之瓶卻是新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新瓶裝舊酒”不僅僅為“漢承秦制”的漢代所有,它在中國歷史上以其巨大慣性存在長達近兩千年之久。
職是之故,才使世事洞明如朱熹者在指出“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乃數代君王賴以成功之訣竅的同時,宣稱“千五百年之間……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朱文公集》三十六卷“答陳同甫”);明末啟蒙思想家黃宗羲亦指出,中國歷史上,“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后,古圣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明夷待訪錄·原法》);清末變法者譚嗣同則對這種“陽儒陰法”評價尤為鞭辟入里,“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于孔。被托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托之孔,又烏能知孔哉”(《仁學》);在批判“陽儒陰法”急先鋒的李贄那里,他的“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焚書·三教歸儒說》),是對當時偽儒學者真實面目入木三分的揭示,他的“然則《六經》、《論》、《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焚書·童心說》),使他成為中國思想史上最無畏的“打假英雄”。讀著這些話語會發現,三百年后的五四運動所掀起的波濤洶涌的“打倒孔家店”運動,與其說是對孔孟真面目的一場誤讀,不如說是李贄壯志未酬的“打假”事業的繼續。
這種不無丑陋而備受詬病的“陽儒陰法”現象之所以可能,除了中國歷史特定的社會政治原因之外,實在于為漢人所開啟的思想上的儒法和解工作困難重重。進而,這種儒法和解工作之所以困難重重,又在于先秦所開啟的儒法之爭因其極其尖銳的“二律背反”,始終難以找到二者理論和解的真正答案。然而,正是這種貌合神離的“陽儒陰法”的理論怪胎,這種難以消解、不無悖反的意識形態矛盾體,竟然主宰和統治中國歷史長達近兩千年。它的主宰和統治,不僅給我們民族帶來長期的貧窮、落后、動亂、黑暗,而且還一如朱子所說,使三王的“王道”,儒家的“仁民愛物”等社會理想“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朱文公集》三十六卷“答陳同甫”)。于是,這也意味著,如何解決這種積重難返的儒法之爭,既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大課題,又關乎我們的民族文化如何繼往開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如果我們把曹植這一詩句的語境置換于中國思想史中,就會驀地憬悟到,這種看似互不相讓、一決雌雄的儒法之爭,一旦回到二者的共同根基,它們之間的矛盾就會渙然冰釋于無形。這就把我們帶向了儒法學說的共同根基——老子的學說。
二、老子學說:儒法學說的共同之基
毋庸諱言,王國維“我中國真正哲學始于老子”之說實為至察之見。作為一種終極性學說,哲學為世界、社會、人生提供了堅實可靠、無可置疑和如如所是的理論的原點。而在老子學說里,這種原點恰恰是通過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和生命得以體現的,故“尊身貴生”不啻為老子哲學至高無上的核心理念,一個與“道”幾乎異名同謂的理念。
就“尊身”而言,除《道德經》“身”字出現23次外,尊身之旨在文中可謂隨處可見。它的“貴大患若身”(十三章)、“修之以身,其德乃真”(五十四章)、“圣人為腹不為目”(十二章)無不為我們表明身之尊,它的“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四十四章)以一種直擊我們每一個人心靈的叩問方式,把我們自身身體與身外之物孰輕孰重的問題第一次提上議事日程,并實為后來莊子“以身為殉”這一人類文明悲劇批判的先聲之鳴。它的“持滿戒盈”“功成身退”告訴我們的與其說是一種老謀深算的政治智慧,不如說是如何使我們臻至“身全之謂德”的天地之間以身為貴的思想洞見。至于它的“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十三章),按王弼的注解則是指,“無(物可)以易其身。故曰‘貴’也……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道德經注》),由是比起海德格爾,老子把身的獨一無二、無可替換的“此在”性認識整整提前了兩千年。
耐人尋味的是,在古漢語中,“身”與“生”同義①。故老子的“尊身”也即是“貴生”。在《道德經》中,關于“貴生”的強調也可謂俯拾皆是,“道生”“求生”“善執生”“重死”“根深柢固”的“長生久視之道”,不一而足。以至于老子在《道德經》里反復申說、一直強調的“道”,實際上就是如何“生生不已”、如何“長生久視”之道;以至于《呂氏春秋》之《貴生》篇“圣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恰恰也道出了老子之道的至要;正是基于此,才使司馬遷把“養生”目為黃老思想的真正根柢,才使《抱樸子內篇·明本》宣稱“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黃老是也”,也才使當代生命哲學家梁漱溟之于老子哲學一針見血指出,“反躬于自身生命,其所務在深切心體”[1]。
細繹其義,借用現代哲學術語的表述,老子“貴生”之“生”也正是海德格爾“生存”之“生”,即那種經過現象學還原的前謂詞、前反思的“生”,也即那種超越了一切規定性的“可能性”的“生”。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老子把這種生生之道與“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的“為道日損”聯系在一起,因為這種“為道日損”也恰恰就是一種“回到事物本身”的“現象學還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老子強調這種生生之道的不可言說、難以名狀,因為任何言與名都是“前謂詞”“前反思”的對立面;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老子就這種生生之道提出了“明道若昧”(四十一章),因為“昧”作為祛規定性為我們指出了生之超越規定性的“可能性”的內涵;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老子為這種生之道冠以“樸散為器”“樸之為名”的“樸”,因為“樸”作為未加工的樹木不外乎就是真正原生態的生的具體體現。
這一切,就為我們推出了“道法自然”“無為而為”這一老子生之道的無上圭臬。在這里,這種“道法自然”的“自然”并非“自然界”(nature)的自然,而是“自然而然”(naturally)的自然,而這種“無為而為”乃是行為、行動意義上的“自然而然”。這意味著,對于老子來說,生命并非上帝創造的產物,也非自然界規律和人為活動之結果,而是事物以一種“去存在”(zu-sein)的方式存在,其本身本來就不得不這樣做。故老子所說的生命不僅是一種“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四章)的超越了一切造物主的事物,同時也是“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帛書五十一章)的并非人所刻意為之的事物。因此,生命就是一種如之而來、如之而是的事物,一種不可解釋、不可把握的事物,故維特根斯坦所說“真正的神秘,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邏輯哲學論》6.44),用于表述老子的生命可以說是一語中的、一針見血。同理,先秦道法家推出的“因循”說,以其“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也”(《管子》)也為我們揭示了老子的生命之法則。這樣,“自然,然后乃能與天地合德”(王弼注),一如王弼所說,老子的自然而然的生命之道與不假人為的天生的“天之道”完全不謀而合了。唯其如此,一如《老子》所說,才使小孩子雖對男女之事茫然無知卻可以“朘作”(五十五章),才使水雖無可名狀、難以把握卻可以四處奔流、沛然莫之能御,也如莊子認為的,真正人生乃是“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莊子·大宗師》)。
一種“生命自組織”性就這樣在老子學說中和盤托出了。顧名思義,所謂“生命自組織”性,也即生命所固有的自組、自調、自穩、自我完善、自我修復、自我代償、自我療愈性質,它與完全借助于他物、他力、他律的非生命的“他組織”性迥然異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正是從這種生命自組織性出發,才使老子高度強調“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而這種自我生成(becoming)的“自化”決定了世界的變化既是“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的活動,又是一種“衣養萬物而不為主”(三十四章)的活動,在這里無論是強制性的種種規定還是主宰性的主體性都統統地銷聲匿跡。正是從這種生命自組織性出發,才使老子把事物的回饋性第一次提上中國哲學的議事日程。這種回饋性也即老子“反者道之動”(四十章)、“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二十五章)、“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十六章)的“反”(返)和“復”,而這種“反”“復”不僅使事物運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十四章),在事物的“物極必返”“無往不復”運動中為我們消解了時間上的先后,同時也使我們由此從“線性因果”走向了“互為因果”,并最終使生命的有機性結構得以真正建構。進而,也正是從這種生命自組織性出發,才使老子把“辯證的反轉”視為生命邏輯發展的應有之義。在老子那里,從“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禍福倚伏”“知白守黑”“知雌守雄”“有無相生”,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三十六章)都無一不是其顯例。從中產生了中國兵法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詭道”和“詭計”,產生了中國醫學“順勢而為”的“反治”的神奇,還使“齊萬物而為一”的莊子的相對主義得以最終確立。而這種相對主義既使是非、美丑、善惡乃至生死的劃分成為偽命題,又為我們實際上開出了社會等級制度解構的造始端倪。
老子學說的生命自組織性既明,思想史上儒法的思想和解就成為不言而喻的東西,因為通過深入的分析我們將會發現,無論儒家學說還是法家學說,實際上都是以這種生命自組織性為其終極性依據、終極性根基的。唯有從這種生命自組織性出發,我們才能在儒法之間“挫其銳,解其紛”,我們才能真正臻至老子那種“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之境地,并徹底消解諸子中“后老子”式的“名言之道”所泥于的“非此即彼”的孑遺。
先看儒家學說。
首先,儒家學說是一種“重禮”“復禮”的學說。那么,什么是“禮”呢?《論語·八佾》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答案卻是否定的。也就是說,禮固然是以“文”取勝的,但“情深”才能“文明”,唯有這種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才是禮的真實內容,故禮是一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的東西,而一種天生的、自發的“親親”之情才是情的內容的核心。這意味著,不僅“親親”之情的遠近厚薄決定了禮的隆殺,而且一如與宗法制互為表里的周代禮制社會所表明的那樣,一種“家”的自然而然的生命演義活動亦是社會禮制秩序賴以成立的唯一原因。由此就有了周易所謂“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序卦傳》)之說,和與之相應的、周禮所謂“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禮記·大傳》)之論。因此,在這里,既沒有一種宗教化的“君權神授”的國家學說,也沒有一種理性化的“契約論”的國家學說,有的僅僅是國家賴以產生的生命自組織原則。正是這種生命自組織原則,為我們民族奠定了“家”“國”合一、“宗統”“君統”合一的百世不遷之制,亦使孟子所引“《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孔子所謂“《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這一卑之無高論之隱秘得以大白于世。
其次,除“禮”之外,儒家學說亦是高舉“仁”的大旗的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中庸》),顯然,“仁”同樣是以“親親”為其核心內容的。故正如儒家之禮堅持對“親親”的因循是禮制社會賴以成立的唯一原因,儒家之仁同樣堅持,這種對“親親”的因循亦是仁愛社會得以大行其道的不可讓渡之根本。此即孔子的“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論語·泰伯》),孟子的“親親而仁民”(《孟子·盡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孟子·梁惠王上》)。盡管較之于儒家之禮,儒家之仁似乎更加強調從“親人”向“陌生人”的由己及人的“推恩”,但這種“推恩”以其“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孟子·公孫丑上》)的自然而然、不可自已的態勢,和禮一樣,同樣體現了一種不假他助的生命自組織性。再參以孔子的“為仁由己”,孟子的“反身而誠”,孟子對“拔苗助長”的嘲諷、孟子“人之性善猶水之就下”的“性善論”,以及后來王陽明“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傳習錄》)的“良知論”,并佐之以《禮記》無施不報的“禮尚往來”、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孟子的“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離婁下》)的“出乎爾反乎爾”諸如此類對人際關系的回饋性的力申,都無一不表明了儒家仁學鮮明的生命自組織性特征。無怪乎中國思想史上有孔子“問禮于老子”之說,也無怪乎在佛學大舉入侵之際,宋明新儒學崛起是以道家式“太極圖”推出為其先河,并從中實現了傳統儒學向更為明徹的“生命儒學”的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再看法家學說。
較之儒家,法家與老子師承關系似乎更為真切。這不僅由于司馬遷認為法家佼佼者韓非子學說“原于道德之意”,不僅由于諸如法家的管子、慎到、申不害被劃入“道法家”之列,更由于就其理論根本而言,法家和老子一樣都是以生命自組織性原則為其無上圭臬。然而,雖儒法兩家共同尊奉生命自組織性原則,但二者對該原則的切入方式、理解方式卻有著天壤之別。如果說儒家生命自組織性思想主要體現在“親親為大”的自然人性上,那么法家的生命自組織性思想則通過“趨利避害”的自然人性光大發揚。故與儒家“人之性善,猶水之就下也”的性善論觀點迥異,一如商鞅所說,“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商君書》),法家則以“趨利避害”的性惡論為其臬極;而在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韓非子那里,因其無比犀利的眼光,這種“趨利避害”的人性被徹底揭露,一覽無余。
韓非子說,“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韓非子·備內》),制作棺材的巴不得人都早點去死,制作車子的則希冀人人都大富大貴。這并不意味著前者“賊”而后者“仁”,只能說明二者都以贏利為自己的人生目的。雇主與被雇者之間關系亦如此。雇主千方百計地善待被雇者,被雇者則不遺余力地為雇主賣苦力,此間關系,并非可用“愛”字一言以蔽之,而是皆出于一種“自為心”的考慮。君臣之間關系也不例外。雙方是一種“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韓非子·難一》)的“君臣相市”關系,這里并無“君臣之義”,存在的只是“計數之所出也”這一錙銖必較的利害關系。即使父母與子女之間,也難以逃脫這一“經濟人”鐵律的擺布。世間流行著“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的習俗,為什么做父母的會向自己親生的女兒痛下毒手?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女子是人所謂的“賠錢貨”,這同樣是“慮其后便,計之長利”這一無所不用其極的“計算之心”的必然產物。至于主張“抱法處勢”的韓非子對“勢”的強調,也同樣基于對“利”的思考,因為但凡人“趨利避害”,也必然意味著人“趨炎附勢”,故韓非子重“勢”不過是其重“利”的注腳。因而其“勢”的學說之失,并非在于他對君主權力的一味討好,而只在于他無視這樣一個事實:這種君主所擁有的權力,同樣也是我們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需要。
這儼然是“上下交征利”了。但是,當孟子提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而主張“去利”時,韓非子卻認為,我們無須說什么“去利”,相反,人們對利益的競相追逐恰恰是“明主”可資利用的東西。只要我們善于因勢利導,我們就可以把天下之私利變成“人主之大利”,把“人自計慮其利害之私”的禍害、內耗變成符合社會政治需要的一種“治道”。故韓非在《韓非子·奸劫弒臣》中不無自信、躊躇滿志地寫道:“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國已治矣。”
因此,在這里,法家不僅為我們推出了一種“利之所至,趨之若鶩;害之所加,避之不及”的人性利害之道,并且這種利害之道就其“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八經因情》)而言,它既是“賞罰可用”的法治之道,同時又是一種“因循人情”的“無為而治”之道,背后是老子堅持生命自組織性的“看不見的手”。
一旦將韓非子與老子通過生命自組織性聯系在一起,韓非子學說里諸多撲朔迷離的疑云就會一掃無遺。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雖然韓非子學說看似與老子學說面貌迥異,卻并不妨礙韓非子對老子是那樣的備極頂禮,以至于可以說唯有了解了他的《解老》《喻老》才能了解韓非子法治理論的真正根基;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韓非子提出“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韓非子·解老》),他如同老子一般地同樣使自己皈依于不言而喻、天縱聰明的“天之道”,而非那種窮極作為、殫精竭慮的“人之道”;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正像堅持“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黃帝四經》)的黃老之說那樣,他宣稱“禍福生于道法,而不出于愛惡”(《韓非子·大體》),以“道法”的強調而實開中國古代“自然法”之先導;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韓非子提出“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韓非子·解老》),主張“禮為情貌者也”(《韓非子·解老》),而對流于文飾之具的禮制進行嚴厲的聲討,并將自己引為稱“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老子》三十八章)的老子的同道;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韓非子主張“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韓非子·六反》)、主張“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韓非子·六反》),從中與其說是體現了一種“天演論”式優勝劣汰的冷酷無情,不如說是作為生命自組織性的“辯證的反轉”,而使自己成為老子“大仁不仁”思想的忠實信眾。所有這一切,都使司馬遷所謂韓非子學說源于老子之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須要指出的是,如若把二者相通之處視為中國文化特有的“冷靜的理知態度”(李澤厚語)而非“前理知”的“生命自組織”,那么我們就可能完全錯失了對韓老共有的深刻而根本的哲學之道的洞悟。
顯而易見,這不僅為我們在道家與法家之間架起了一道橋引,同時也使儒家與法家之間的和解最終成為可能。因為如前所述,儒家學說同樣基于老子的生命自組織性。因此,對于中國思想來說,“回到老子”毋寧說具有一石雙鳥之義。一方面,它為中國思想的原點從事了終極性奠基;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國思想上曠日持久的儒法之爭的強力解劑。這種老子學說的特有魅力也決定了,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既是一部中國思想激進的改革史,又是一部徹底回歸老子思想的歷史。但凡具有除舊布新思想的近現代思想家無一不對老子頂禮膜拜,無一不各盡其所需地高高舉起“禮老”“尊老”“解老”的思想大旗。“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老子》七十章),被邊緣化千年之久的孤獨的老子在歷史新時代終于找到了自己的難能可貴的知己。
三、近現代回歸老子的思潮
近現代回歸老子思潮同樣是從兩個層面展開的。一是通過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組織思想的解讀,為我們呈現了古代法家法治思想的積極合理的現代意義;二是通過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組織思想的解讀,為我們呈現了古代儒家禮治思想的積極合理的現代意義。
就前者而言,這一工作是由明代啟蒙思想家李贄首開端倪的。他所謂“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伏競奔之子”[2]17,“勢利之心,亦吾人稟賦之‘自然’矣”[3],是對古代法家趨利避害的自然人性的再次大力提撕,而他所謂“率性之真,推而擴之,與天下為公,乃謂之道”[2]16,“民實自治,無容別有治之之方”[4],是一種有別于君主專制的“至人之治”。顯然,這種“至人之治”以其“無為而治”而打上了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組織治理思想的鮮明印記。無怪乎正是這種發前人所未發的熔韓老于一爐,才使李贄這位“一無所尊”的思想狂人既“喜讀韓非之書”[5],又尊老到了“可以一時而不佩服于身,一息而不銘刻于心”[6]的極致地步。
如果說在李贄那里,他的治理思想雖彌足珍貴卻由于尚未明確提及“法治”概念而給人留有遺珠之恨的話,那么,在明代又一位啟蒙思想家黃宗羲那里,則出于對“道法”的深刻理解而將“法治”概念正式提上議事日程,并繼往開來地實發中國近現代呼吁法治社會的先聲之鳴。為此,就不能不提到其《明夷待訪錄·原法》篇中的兩種法的區分。這種區分即“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篋者也”的“一家之法”,與“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的“天下之法”。前者是君主專制社會的人為的、私有的法,后者則為人類社會草創期間的恒順自然天道的,和“大藏不藏”的非私有的法。黃宗羲認為,若立“天下之法”,法雖疏而亂不作,故稱“無法之法”,而若立“一家之法”,法雖密而亂愈生,故稱“非法之法”。進而,針對前人“有治人無治法”,即依靠杰出人物才能實現社會治理的觀點,黃宗羲背道而馳,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黃宗羲認為,即使統治者是個不正直或無能之人,由于“法治”的存在,他也會受到法的約束和挾制,“亦不至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明夷待訪錄·原法》)。
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們看到,這些明人的驚世之見不過是現代一場波濤洶涌的以“老”解“法”思潮來臨的前奏曲。在這場思想大潮中,對現代法治精神洞若觀火的嚴復的觀點尤值得人們關注。一方面,嚴復認為,“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組織性是老子治道的集中體現。他就此指出,老子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又曰,此豈有政發徵期會哉!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7],并注《應帝王》宣稱“郭注云,夫無心而任夫自化者,應為帝王也”[8]。在他看來,即使老子斷言“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也不應像康有為那樣備加指責,它不過是順乎天則的自然進化中生存競爭必然之結果。另一方面,嚴復又認為,老子這一思想實與古代法家法治思想不謀而合。故他指出,就“聽民自謀”而言,老子思想與申不害思想二者幾乎如出一轍。這樣,對于嚴復來說,這不僅意味著“居今日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9],古代法家思想在今日必得以復活,同時還意味著中國之法與世界公法最終可以殊途同歸了,因為無論是老子對法的理解還是孟德斯鳩對法的理解,都是以從人類自然本性中導出的自然法為其原則。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胡適那里,嚴復這種以“老”解“法”思想被更為明確地一語點破。他毫不含混地指出,老子“理想中的政治就是極端的放任無為”,老子的天道觀就是“西洋哲學的自然法”[10]。在他看來,明確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確了老子與法家的聯系:“法家雖信‘無為’的好處,但他以必須先有‘法’然后可以無為。如《管子·白心》篇說:‘名正法備,則圣人無事。’”[11]除嚴復、胡適外,這種以“老”解“法”,進而推崇法家的思想,在現代改革思想家那里可謂比比皆是。從梁啟超后期“尊老”并視道家為“無治主義”,到劉師培稱中國古代政治“偏于放任,一任人民而自然”而自己篤信“無政府之說”,再到章太炎將韓非子《解老》《喻老》列入道家學說并批判人治而為法家正名,凡此種種都無一不是這一點的明示,都無不表明一種新“道法”之說在現代中國已幾乎呈燎原之勢。
再者,就后者而言,與這種“隆法”思潮一起,我們還看到一種“復禮”思潮在近現代同樣驟然興起。如果說這種“隆法”思潮是由李贄(以及黃宗羲)首開端倪的話,那么,這種“復禮”思潮則是由顧炎武率先開啟的。為此,我們就不能不提到顧氏著名的“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這一命題。所謂“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也即針對長達千年的強干弱枝、其專在上的中國古代郡縣制,顧炎武主張折中“封建”與“郡縣”,使古之分封制精神再次體現在今日郡縣制里。此即其“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12],也就是說,通過一系列措施加強州縣官員的權力,使之具有類似分封制中諸侯的部分權力,從而用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而天下治。正是基于這種休戚與共、公私一體的全新的政治共同體,才使顧炎武替我們發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振聾發聵的千古呼吁。
不無遺憾的是,當論者多以“分權”抑或“集權”對顧炎武的政治學說做出解讀之際,殊不知回歸“家國一體”“親親而仁民”的古代禮治才是其“封建之意”的應有之義,因為實際上“封建制”與“禮制”二者異名同謂、互為表里。如果對這一點還有所懷疑的話,那么,一旦回到明清之季另一位啟蒙者龔自珍的復古主義的政治學說里,就會發現問題之真正歸趣和所指。換言之,雖然龔自珍和顧炎武同樣意識到“方今郡縣之敝已極”,同樣主張擴大和強化地方權力,然比較起來,如果說顧氏為此提出建立“世官”制度的話,那么龔自珍則明確地將這種“世官”與“世家大族”聯系在一起。故龔自珍提出“宗者,尊也”,“大宗,尊之統也”[13],提出“君若父若兄同親”,“君若父若兄同尊”[14]49,“古之為有家,與其為天下,一貫之者”[14]49,主張“藥方只販古時丹”,把回歸古時的“君之宗之”“家國一體”的社會政治視為救世匡難的唯一方案。
耐人尋思的,殆至清末民初,這種看似歷史“開倒車”的社會思想非但沒有隨著社會日新月異的巨變中斷,反而又一次掀起狂瀾并蔚為大觀。如康有為稱“夫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也”,“自治之制,天理也,自然之勢也”②,如黃遵憲亦尊這種封建式的自治“能任此事,則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聯合之,收群謀之益,生于其鄉,無不相習,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縣專政之弊”[15],如馮桂芬言“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借天合維系之,而其合也彌固”(《校邠廬抗議·復宗法議》),如宋恕講“先王要道,遂與俱西乎,何其政多與周官合”(《津談·尊孔類》),王韜云“平治之端,必自齊家始”(《弢園文錄外編卷一·原人》),郭嵩燾亦指出“秦并天下,劃封建為郡縣,海內大勢盡易,三代政治掃地略盡”(《郭嵩燾日記》三)。
在這種勢如潮涌的回歸封建禮制的大潮中,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觀點尤值得一提。這不僅在于王國維認為周制之所以大異于殷制,其端在周人的“立子立嫡之制”的確立,從殷人的“兄終弟及”一改為周人的“父子相繼”之制,更重要的還在于王國維令人信服地為我們揭示出這一制度被深深掩埋的理論根據。按王國維的說法,這一根據就是其所謂的“夫舍弟而傳子者,所息爭也。兄弟之親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間不免有爭位之事”(《殷周制度論》)。換言之,就是其所謂的“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故天子諸侯之傳世也,繼統法之立子與立嫡也,后世用人之資格也,皆任天而不參以人,所以求定而息爭也”(《殷周制度論》)。
這里的“任天者定”的“天”,也即馮桂芬“親族以天合”的“天”。顯而易見,它恰恰亦是老子“道法自然”的“天道”之“天”。因此,一字點破天機,正是在這里,近現代“復禮”思潮的最終根據掘井及泉地得以揭曉了。故無論是近現代“隆法”思潮,還是近現代“復禮”思潮,都無一例外地基于老子的道。正如先秦諸子爭鳴為我們最終迎來的是漢初“尊老”那樣,中國近現代內源性思潮運動的結果同樣實際上是以“復老”為其代表。盡管許多復禮者由于尊儒而尚未提及老子,甚至諸如康梁一度還對老子學說發起理論上的嚴厲聲討。
無疑,這既是中國近現代“隆法”思潮和其“復禮”思潮的殊途同歸,同時又為始自先秦貫穿于整個中國思想史的儒法之爭提供了一劑徹底的解藥。它告訴我們,儒法之爭問題包括與之相系的儒法貌合神離的“陽儒陰法”問題的解決,既是一個有待認識深入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有待時機成熟的歷史問題,從而只有以一種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方式,才能在水到渠成之中發現問題解決的真正之道。而這種道恰恰就是那種“根深柢固,長生久視”的老子之道。一方面,唯有從這種老子之道出發,我們才能為儒家“親親而仁民”的德治思想奠定其終極性的依據,并在從事這種終極性奠基的同時,也才能對法家的“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法治思想之弊給予徹底的力辟;另一方面,唯有從這種老子之道出發,我們才能使備受爭議的法家“抱法處勢”的法治思想的合理性根本得以破譯,并在從事這種根本破譯的同時,也才能對儒家的“有治人無治法”這一制度建設的缺失給予深刻的糾弊。進而,正是基于這一切,才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中國近現代思潮實際上為我們推出一種呼之欲出并且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道家,一種“舉孟旗,走荀路”的新道家,一種“德法并舉”“德法互補”以及德法互為體用的新道家。其中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是以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天道”為其終極依據,也是以司馬遷“深遠的老子”為其立論的鼻祖。
放眼世界,這也是一種置身新時代語境并賦予了新時代意義的新道家。這種新時代語境,也即當代人類無論其法治生活還是道德生活,因其二者分離,都面臨在劫難逃的深刻危機。就前者而言,現代性的“去魅化”雖然導致工具理性的法治主義迅猛崛起,但由于資本邏輯強勢統治,卻使這種法治主義事與愿違地與社會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互為表里。而在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里,我們又如何保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法的價值中立?故與現代法治主義所向披靡相伴的,是老子的“法律滋彰,盜賊多有”,焦里堂的“理愈明訟愈繁”的法的危機,是“追隨德性”的全球社群主義風起云涌的興起。就后者而言,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雖然為道德生活奠定了深厚基礎,但他的“美德即知識”“惡行即無知”卻使道德打上理性主義深深的印記,而在日趨為資本邏輯所強化的“世俗化”的當代人類社會里,這種理性主義勢必與精于計算的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結為一體,沆瀣一氣。故與此相攜而來的,除了康德式道德與幸福的“二律背反”被無可救藥地推向極致,還有道德相對主義、道德虛無主義的風靡,以及熔社會正義與個人利益于一爐的“新自由主義”的異軍突起。
于是,正是這種特定的時代環境,使中國古老的“儒法之爭”又一次復活在當今世界里,并為我們凸顯了兼綜德法的新道家的時代意義。它告訴我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離婁上》),為了走出時代的困境,我們必須從唯法治和唯德治的由各執一端,走向二者并重,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般的須臾不可離。因為這種須臾不可離既忠實于二者同根共宗的“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組織原理,又服從于這種原理所內蘊的兩極相通的互為因果之鐵律。同時,它也告訴我們,今天中國社會生活的健康發展,既要順應我們民族闊步邁向現代法治社會這一大勢所趨,又要警惕法的一意孤行所流于社會中的“道德虛無主義”。故為荀子所提出的“德”與“法”一為“治之原”一為“治之流”區分的主張,以其鮮明的與道家思想格格不入的“還原主義”“基礎主義”性質,不僅在過去的中國被證明是不成立的,并且在今日中國也將證明是完全不可取的。
所有這一切,不正表明人類正面臨著“回到老子”的新思潮風暴?不正表明“老子不老”,唯有老子學說才是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真正的“根深柢固,長生久視”之道?不正表明無論我們身處何地、何時,無論我們面對何種深重而嚴峻的時代危機,老子之道都始終是我們妙手回春、返老還童的靈丹妙藥?
注釋
①如辛棄疾“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生”中的”身后”即生后。②康有為:《公民自治篇》,《新民叢報》第5、6、7號連載,19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