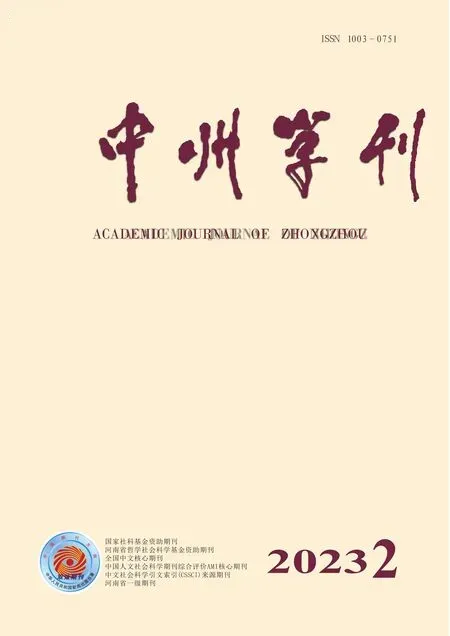杜亞泉多元主義文化觀再審視
左玉河 李永貞
長期以來,杜亞泉(1873—1932)被視為五四時期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實際上,他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科學教育家和啟蒙學者,創造了近代中國科學傳播史上的多項第一:最早創辦專門科學雜志《亞泉雜志》,最早編寫近代語文課本《文學初階》,主持編輯中國第一部《植物學大辭典》和《動物學大辭典》。作為五四時期著名刊物《東方雜志》的主編,杜亞泉一方面依守傳統資源,另一方面力求調適傳統與現代,因而被新青年派視為反現代的保守主義者而加以排斥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百余年后的今天,我們有必要超越狹隘的進化史觀,重新審視杜亞泉的文化調和主義及其多元主義文化觀。
一、為什么杜亞泉將東西文明差異視為民族根本性質的差異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狂飆突進、全面輸入西方新思潮的時代背景下,為什么會出現像東方文化派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這是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如果說晚清時期深受儒學熏習的守舊派對西學往往采取深閉固拒的強硬態度的話,那么,到五四時期持這種簡單的排外觀點者并不多見,故很少出現像倭仁那樣的政治保守、文化守成的頑固派。盡管仍然有辜鴻銘、林琴南等文化守成者,但他們所擁有的西學知識及世界眼光,已遠非晚清時代的守舊派和洋務派所能比擬。至于像杜亞泉、章士釗等人,雖然在文化觀念上趨于守成,屬于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者,即通常所說的東方文化派,但他們同樣具有更為廣博的西學知識和開闊的文化視野。他們正是運用自己較為深厚的西學知識及開闊的文化視野,與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派相抗衡。
將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出現的諸多堅守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者,統稱為“文化保守主義者”,乃是為了與晚清時期“政治保守主義者”區別開來。文化保守主義者著力發掘和肯定中國固有文明的價值,力圖融匯古今東西,站在中國文化的根基上有選擇地吸納外來文明,以適應時代需要的思想傾向或思想派別。這種守成的文化態度和立場,與政治上的保守與激進并不同步。五四時期的東方文化派是文化守成主義者,而不是政治保守主義者,遠非晚清時期的倭仁、葉德輝、王先謙等傳統守舊派所能比擬。他們鑒于當時中國固有文明的衰落及儒學正統地位的動搖,清楚地看到頑固地堅守儒家文明已不大可能,故往往為了接續和發揚儒家文明而有限度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更多的是強調在立足于儒家文明的基點上,調和折中東西文明,著力于東西文明交接點上的變通與調適。換言之,他們力圖在東西文明的調和、折中、變通與調適過程中,尋求儒家文明復興之新機,探尋中華文明的現代出路。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論戰雙方的領軍人物,東方文化派為《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新文化派則為《新青年》主編陳獨秀。以杜亞泉等人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構想出一種“東方精神文明”與“西方物質文明”的二元對立結構,企圖用以儒學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復興中國、超拔歐洲。以東方精神文明之優彌補西方物質文明之缺,以東方道德主義之長排斥西方功利主義之短,成為五四時期文化保守主義者共同的價值取向。杜亞泉在東西文明比較基礎上提出的文化調和主義,就是這種文化保守主義價值取向的集中體現。
杜亞泉從1911年出任《東方雜志》主編后,革新雜志內容,擴大雜志篇幅,將該刊物辦成了當時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術文化雜志。他除了主持《東方雜志》編務外,還勤于著述,著有《人生哲學》,譯有叔本華的《處世哲學》,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多達200篇的學術政論文章,闡述自己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看法。杜亞泉有著開闊的文化視野,關注國際政局和世界形勢,具有開放的文化心態,撰寫了許多精彩的文章,對東西文明進行學理意義上的比較,主張多元主義和文化調和論。這引發了五四時期關于東西文化的論戰,也因此被視為東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
1916年初,黃遠生撰寫《新舊思想之沖突》一文,將晚清以來西方文明輸入后導致的新舊沖突作了總結。他斷定:“自西方文化輸入以來,新舊之沖突,莫甚于今日。”②他認為中國思想內部的沖突,實為新舊思想之沖突,也就是西洋近代文明與中國傳統儒家文明之沖突。杜亞泉覺得黃遠生提出的新舊思想問題頗為重要,故一方面將其文章在《東方雜志》第13卷第2號上刊載,另一方面深入研究東西文化及新舊思想問題,闡明自己對東西文化問題的觀點。1916年4月,杜亞泉發表《再論新舊思想之沖突》,對黃遠生的觀點進行回應和發揮,認為東西文明的差異是民族性的差異,并非時代性的差異。他指出:“況兩種思想,各有悠久之歷史、龐大之社會以為根據,其勢自不能相下。然謂吾國民思想之沖突,即東洋思想與西洋思想之沖突,則殊未是。”③既然東西文明的差異不是簡單的東洋思想與西洋思想的沖突,那么東西文明之間的差異是怎樣的“性質之異”?杜亞泉在隨后發表的《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中,對東西文明的差異作了認真的觀察和深入的研究,斷然反對陳獨秀將東西文明視為“古今之異”的觀點,認為東西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蓋吾人之意見,以為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者。西洋文明,濃郁如酒,吾國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國文明,粗糲如蔬,而中酒與肉之毒者,則當以水及蔬療之也。”④
杜亞泉接著分析了東西文明“性質之異”的原因,認為這主要是由中西社會結構及歷史傳統的差異造成的。中西社會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西洋社會由多數異民族混合而成;二是“西洋社會發達于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島間,交通便利,宜于商業,貿遷遠服,操奇計贏,競爭自烈”,而“吾國社會,發達于大陸內地之黃河沿岸,土地沃衍,宜于農業,人各自給,安于里井,競爭較少”⑤。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造成了東西文明的差異,形成了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差異,導致了不同的社會歷史傳統。
東西文明之間存在著多方面的差異,這是非常明顯的現象。但東西文明的差異是文明發展程度上的“時代性差異”,還是根本性質上的“民族性差異”?杜亞泉提出了與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派根本相反的觀點:東西文明的這種差異,主要體現為兩種社會及兩種民族的性質上的差異。杜亞泉指出:“綜而言之,則西洋社會,為動的社會,我國社會,為靜的社會;由動的社會,發生動的文明,由靜的社會,發生靜的文明。兩種文明,各現特殊之景趣與色彩,即動的文明,具都市的景趣,帶繁復的色彩,而靜的文明,具田野的景趣,帶恬淡的色彩。”東西文明之間的動靜差異,自然會產生兩個民族完全不同的社會狀況:“動的社會,其個人富于冒險進取之性質,常向各方面吸收生產,故其生活日益豐裕;靜的社會,專注于自己內部之節約,而不向外部發展,故其生活日益貧嗇。”⑥
杜亞泉進而指出,歐戰的慘烈使“吾人對于向所羨慕之西洋文明”產生了懷疑,迫使中國人改變盲從的態度,用中國固有的“靜的文明”來救濟“西洋動的文明”的弊端。他指出:“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者。西洋文明濃郁如酒,吾國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國文明粗糲如蔬,而中酒與肉之毒者則當以水及蔬療之也。”⑦他告誡國人要以儒家思想為評判是非的標準,指責五四時期新思想的輸入“直與猩紅熱、梅毒等之輸入無異”,造成了民國初期的“人心迷亂”“國是喪失”及“精神破產”。由此可見,杜亞泉對東西文明的主張,實質上仍未跳出晚清時期“中體西用”的范圍。杜亞泉通過對東西文明差異性的比較認為,動的文明與靜的文明皆有利弊,只能取長補短,不能取而代之。西洋社會雖然科學先進,經濟發達,但已經“陷于混亂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濟”⑧。東方文明雖然也有陋弊,但在精神層面上高于西方文明。既然兩種文明各有特色,那么就不能盲目“西化”而否定自身文明的價值。他堅持認定東西文明各有利弊,不贊同舍棄中國文明而全盤采納西方文明。
杜亞泉清醒地意識到,說中國文明在精神層面上高于西方,并不意味著復古守舊,更不贊同人們像晚清守舊派那樣對西方文明采取盲目排斥的態度,認為“僅僅效從頑固黨之所為,竭力防遏西洋學說之輸入,不但勢有所不能、抑亦無濟于事”,而應該堅守中國“精神文明”優于西方“物質文明”的基本立場,去評判東西文明的優劣并實行相互的“取長補短”。他認為,“精神文明之優劣,不能以富強與否為標準”,西洋人于“物質上雖獲成功”,但“其精神上之煩悶殊甚”。相反的,中國社會在物質上抱著“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的態度,精神上確信中國固有之道德觀念,為最純粹最中正者。換言之,即“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因此,在杜亞泉看來,東西文明不僅是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的差異,而且還是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差異。西洋動的文明及物質文明,遠遠低于中國靜的文明及精神文明,是顯而易見的事情。既然如此,中國自然就沒有必要效法西方文明而走西洋化的發展道路,而應該立足于中國文明基礎上“統整”西洋文明。
二、為什么杜亞泉主張以中國傳統儒學“統整”西洋文明
杜亞泉盡管承認東西文明各有流弊,但因西方“動的文明”弊害更大,故其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西洋文明雖然可以輸入,但必須站在中國文明的基礎上,靠中國固有文明對其進行“統整”,將西方文明“納入吾國文明之中”。他不承認西洋文明在總體上比中國文明優越和進步,反倒認定中國固有文明可以“救濟”西方文明,乃至對世界文明作出補救性貢獻。
杜亞泉在分析東西文明特質后,突破以往文明比較時將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做法,提出了東西文化融合會通的調和主義。杜亞泉對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派的“西化”主張明確表示反對。他認為:“近年中以輸入科學思想之結果,往往眩其利而忘其害,齊其末而舍其本。受物質上之激刺,欲日盛而望日奢。”⑨這樣將會導致中國固有文化的喪失,同時所引進的西方文化也不能尋找到一條使國家富強之路,因而陷入進退兩失的尷尬境地。
杜亞泉在《戰后東西文明之調和》一文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東西文明的調和問題作了專門闡述,認為中國不必效仿西洋文明,應該充分肯定中國文明的價值和地位。他指出:“此次大戰,使西洋文明,露顯著之破綻,此非吾人偏見之言,凡研究現代文明者,殆無不有如是之感想。……平情而論,則東西洋之現代生活,皆不能認為圓滿的生活,即東西洋之現代文明,皆不能許為模范的文明;而新文明之發生,亦因人心之覺悟,有迫不及待之勢。”⑩正因為如此,杜亞泉呼吁,儒家所倡導的“名教綱常諸大端”,“為吾國文化之結晶”,是不能丟掉的;而西方輸入的“權利競爭,今日不可不使之澌滅”,故必須引起國人的密切關注。在他看來,東方文明的發展方向不是“西化”,而是立足本身傳統的基礎上吸取西方文化的長處,以彌補自身的短處,故必須進行東西文明的調和。戰后世界新文明“自必就現代文明,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而以適于人類生活者為歸”。
1918年4月,杜亞泉發表《迷亂之現代人心》,對西洋文明輸入后造成的精神生活的缺失及實用主義的興起表示強烈不滿,并警告國人說:“吾人之精神的生活既無所憑依,僅余此塊然之軀體、蠢然之生命,以求物質的生活,故除競爭權利、尋求奢侈之外,無復有生活的意義。”正是在批評中國社會精神生活缺失之基礎上,杜亞泉進而提出了“迷途中之救濟”辦法。
如何“救濟”中國社會出現的種種“迷亂”現象?杜亞泉認為不能指望西洋文明,因為西洋文明尚不能自救,故必須依靠中國固有文明予以拯救。中國文明不僅能夠救濟自己,而且能夠救濟陷入危機中的西方文明。他指出:“決不能希望于自外輸入之西洋文明,而當希望于己國固有之文明,此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蓋產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于混亂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濟。”既然杜亞泉希望以中國固有文明來“統整”西洋文明,那么究竟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及什么樣的路徑“救濟”中國當下的“迷亂”現象,并“統整”危機中的西方文明?杜亞泉并未對此關鍵問題加以闡述。這種情況表明,他僅僅是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張,而缺乏深入而嚴密的理論說明,故其論證是相當單薄的。
杜亞泉對東西文明的比較及提出的文化調和論主張,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反對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明,肯定中華文明有其自身的價值,這是應該肯定的,也是能夠站住腳的。他極力弘揚中國傳統文明的長處,也正視中華民族文化的短處,旨在通過東西文明的調和,創建以中國傳統文明為根基的中國現代新文明。這樣的動機及在這種動機下對東西文明問題所進行的分析和研究,體現了其對民族命運的關懷和對中華文明前途的擔憂。他在《迷亂之現代人心》中發出“國是之喪,為國家致亡之由”的慨嘆,表明了自己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以及反對全盤輸入西方文明的緣由。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代表了當時部分文化守成者的共識。
然而,杜亞泉對東西文明的分析及所得出的結論,從根本上是錯誤的。他過分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誤解了歐戰對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極影響,錯誤地認為歐戰標志著西方近代文明的破產,暴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和危機,而這種弊端和危機必須靠中國文明來“救濟”和“彌補”。這樣的論斷,顯然是對西方近代文明的誤解,沒有看到西洋近代文明所具有的自我調整能力及強大的生命力,也反映出他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落后性尚缺乏深刻的反省。他僅僅看到兩種文明的民族性差異,而否定了兩者之間更為明顯的時代性差異。實際上,東西兩種文明之間雖然存在著民族性差異,但并非根本上的性質差異,而是時代性的差異,是處于農業社會及宗法社會中的中國傳統文明,與處于工商社會及市民社會的西方近代文明之間的差異。時代性的差異,才是東西文明差異的主要方面。正因杜亞泉堅持東西文明的民族性差異的核心理念,因此他從根本上否認西洋近代文明優于中國儒家文明,否認中華傳統文明應該輸入并接受代表世界文明發展方向的西方近代文明,因而,他恰恰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西洋近代物質文明遠沒有中國精神文明優越,故需要中國儒家的精神文明去“救濟”西方近代文明之“弊”,需要儒家文明去“統整”西洋近代文明。這樣的結論,顯然是與整個時代發展的潮流相背離的,實際上是無益于中國現代新文明建構的。
三、如何看待杜亞泉的多元主義及其文化調和論
杜亞泉對東西文明的比較及對新文化運動的抨擊,在當時思想文化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引起陳獨秀等人的重視和反駁。1918年9月,陳獨秀發表《質問〈東方雜志〉記者》,同年12月,杜亞泉發表《答〈新青年〉雜志記者之質問》,對陳獨秀的觀點提出反駁意見;次年2月,陳獨秀接著發表《再質問〈東方雜志〉記者》,嚴厲批評杜亞泉提出的文化調和論。陳獨秀指出:“吾人不滿于古之文明者,乃以其不足支配今之社會耳,不能謂其在古代無相當之價值;更不能謂古代竟無其事,并事實而否認之也。不但共和政體之下,即將來寬至無政府時代,亦不能取消過去歷史中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及其種種黑暗之事實。”在他看來,西洋文明輸入后破壞中國固有文明中之“君道臣節名教綱常”是很正常的,故導致以儒家文明為根基的“國是喪失”及“精神界破產”,也是必然的。
在這場東西文化問題論戰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派堅持西方近代文明比中國固有文明優越的基本立場,堅持輸入西方近代民主與科學,對中國傳統文明進行激烈批判,其主流無疑是正確的,順應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但也存在著絕對化、簡單化的缺點。如陳獨秀強調:“因為新舊兩種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斷斷不能相容,要想兩樣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馬,一樣不成。”這顯然是僅僅強調了兩種文明存在的時代性差異,從而忽視甚至否認了文明的傳承性和東西兩種文明之間的民族性差異。這種偏激的論斷,因缺乏科學的分析態度難以為杜亞泉等人所接受。因此,五四時期關于東西文化的論戰盡管非常激烈,但并沒有使東西文化問題得到真正解決。
實際上,杜亞泉的東西文化調和論及作為調和論基礎的多元主義,是五四時期東西文化論戰中非常值得關注的理論,也是認識杜亞泉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論參照。調和主義是民初知識界很有影響的文化思潮。杜亞泉、章士釗、李大釗、高一涵等人皆為英倫自由主義的信奉者和調和主義的倡導者。文化調和主義旨在尋求思想多元和思想自由,意在調和東西、新舊、古今而熔鑄中國現代新文化。早在1914年發表的《論思想戰》中,杜亞泉就力倡思想界各派應該以開放寬容的多元主義,化解因新舊思想歧異而導致的思想沖突,初步形成了調和主義的觀點。杜亞泉指出,國民欲發達其思想而又避免思想戰的發生,必須有寬容的胸懷,承認多元思想的存在,不能獨斷專行。他提出四條主張:一是宜開濬其思想;二是宜廣博其思想;三是勿輕易排斥異己之思想;四是勿極端主張自己之思想。歸納起來就是必須明了并遵循社會發展的“對抗調和之理”。他分析說:“世界事理,無往不復,寒往則暑來,否極則泰生……地球的存在,由離心力與向心力對抗調和之故;社會的成立,由利己心與利他心對抗調和之故。故不明對抗調和之理,而欲乘一時機會,極端發表其思想者,皆所以召反對而速禍亂者也。”
新文化運動興起后,面對思想界新舊各派日趨激烈的爭論,杜亞泉發表《矛盾之調和》一文,以多元主義闡明多種“主義”并行不悖的調和主義原理,強調任何“主義”都不能包含萬理,各種主義皆有其獨立的價值。他指出:“天下事理,決非一種主義所能包涵盡凈。茍事實上無至大之沖突及弊害,而適合當時社會之現狀,則雖極鑿枘之數種主義,亦可同時并存,且于不知不覺之間,收交互提攜之效。”在他看來,主義的對立不是絕對的,兩種主義因其中有部分宗旨相似、利害相同,往往可以互相吸引聯袂而行。因此,“世界進化,嘗賴矛盾之兩力,對抗進行”,思想的發展同樣循此矛盾對抗調和之理。他主張,對于主義,國民應當選擇“其為心之所安、性之所近者”,并“誠實履行,毋朝三而暮四,亦毋假其名義以為利用之資;而對于相反的主義,不僅不宜排斥,更當以寧靜的態度研究”,以求調和協進”。以“寧靜的態度研究”各種對立的“主義”,使其并行不悖與調和協進,是推進思想發展的明智選擇。因此,杜亞泉主張持理性開放的態度對待從西方輸入的新思想,持多元主義的開放態度,而切不可教條主義地獨宗一說;他否認包含萬理而一統天下的絕對真理和終極目的存在,而承認文化價值的多元性。
杜亞泉這種理性的多元主義,旨在反對激進、保守、偏狹的一元獨斷精神,而倡導新舊思想兼容、調和的文化態度。杜亞泉的多元主義繼承英國經驗主義的理性、寬容、懷疑、反教條的傳統,主張各種主義皆有價值,進而推出其政治文化之新舊多元對立調劑的調和主義。這種多元主義的精神,成為杜亞泉反對陳獨秀激進主義文化觀的理論依據,也構成了其文化調和論的思想基石。正是基于多元主義認識,杜亞泉在東西文明問題上堅決主張文化調和論,并從經濟和道德兩方面分析了東西方文明的特點和缺陷,主張兩種文明互相調和。杜亞泉指出,東洋經濟和西洋經濟具有以下特點:“東洋社會之經濟目的,為平置的,向平面擴張;西洋社會之經濟目的為直立的,向上方進取。東洋社會之經濟目的,為周遍的,圖全體之平均;西洋社會之經濟目的,為特殊的,謀局部之發達。”“東洋社會為全體的貧血癥;西洋社會則局處的充血癥也。”所以,東西方經濟的調和,是戰后西方經濟發展的基本走向。
杜亞泉研究東西方社會道德狀態后認為,兩者各有優長和缺陷,新道德應該在兩者調和的基礎上產生。戰后西洋社會道德,將是東西方社會道德的調和而形成的新時代的道德。正因如此,中國應采取的調和之法,就是在經濟方面引進西方科學的手段,以實現中國經濟的發展;在道德建設方面學習西方道德中力行的精神,以實現我們理性的道德理想,用杜亞泉的話說就是:“是故吾人之天職,在實現吾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學的手段,實現吾人經濟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實現吾人理性的道德。”
陳獨秀對杜亞泉的東西文化調和論進行了嚴厲批評。他在《調和論與舊道德》一文中,斥責杜亞泉的調和論為“人類惰性的惡德”,堅持矯枉過正的激進主義。他指出,惰性是人類本能的一種惡德,是人類文明進化的障礙,新舊雜糅調和緩進的現象,正是這種惡德和障礙造成的。故陳獨秀反對調和論的理論依據,就是調和論助長了人類守舊的惰性,從而滯緩了社會進化過程。
陳獨秀與杜亞泉圍繞調和論展開的激烈論戰,其焦點不在于是否輸入西洋新文化問題,而在于如何對待中國固有舊文化問題上。兩者圍繞調和論的爭論,在學理與策略上都存在著深刻的分歧。陳獨秀激進的文化革命論,雖然具有深刻的歷史合理性,但其賴以立論的文化進化論在學理上是粗陋的并失之偏頗的;杜亞泉的文化調和論則在學理上契合了文化之新舊調和遞變的漸進演化法則,可以避免激進主義導致的破壞性流弊。這顯然是杜亞泉文化調和論的思想價值所在。蔡元培對杜亞泉的調和論曾有精當的評價。他說:“先生既以科學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詳審慎,力避偏宕,對于各種學說,往往執兩端而取其中,為[如]惟物與惟心,個人與社會,歐化與國粹,國粹中之漢學與宋學,動機論與功利論,樂天觀與厭世觀,種種相對的主張,無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長而調和之。”蔡元培對杜亞泉調和論之周詳審慎的“科學方法”和執兩取中的“折衷方法”的概括,揭示了杜亞泉思想方法之中西會通的基本特點。
總之,作為一位有著深厚自然科學底蘊的近代啟蒙學者,杜亞泉之周詳審慎的“科學方法”,體現了英國經驗主義之理性的科學精神,這是杜亞泉有別于新青年派的基本思想特征。而杜亞泉之理性寬容、和平中正的“折衷之法”,以宇宙社會之矛盾“對抗調和”法則,強調思想價值的多元性,進而主張在思想多元的張力中尋求中西新舊的“調劑平衡之道”。杜亞泉調和論的思想價值,在于順應并揭示了五四啟蒙時代東西文化交匯融合的發展趨勢:思想自由、價值多元與開放包容的格局。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派追求科學民主和反孔批儒,在民初共和流產、民情沉郁的環境中具有不同凡響的強大的社會影響,但也暴露了激進主義之武斷偏激的局限。因此,我們可以概括地說,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派以“武斷態度”傳播新思想而驚世駭俗;以杜亞泉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因“嚴守論理”的調和思想而具深邃的文化價值。
注釋
①相關論述可參看高力克:《調適的智慧:杜亞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②黃遠生:《新舊思想之沖突》,《東方雜志》第13卷第2號,1916年2月。③傖父:《再論新舊思想之沖突》,《東方雜志》第13卷第4號,1916年4月。④⑤⑥⑦傖父:《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東方雜志》第13卷第10號,1916年10月。⑧傖父:《迷亂之現代人心》,《東方雜志》第15卷第4號,1918年4月。⑨⑩傖父:《戰后東西文明之調和》,《東方雜志》第14卷第4號,1917年4月。陳獨秀:《再質問〈東方雜志〉記者》,《新青年》第6卷第第2號,1919年2月。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傖父:《論思想戰》,《東方雜志》第12卷第3號,1915年3月。高勞:《矛盾之調和》,《東方雜志》第15卷2號,1918年2月。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