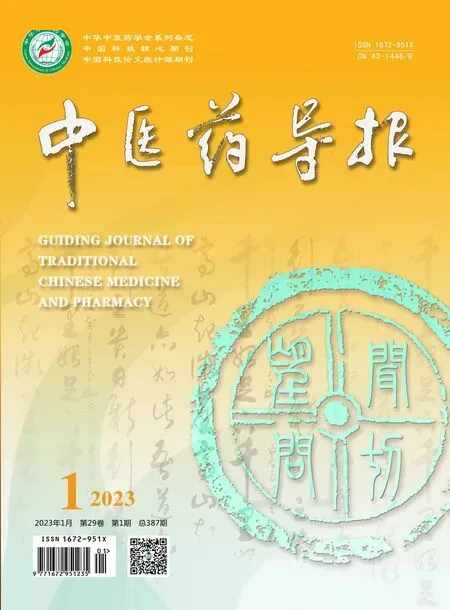《針灸大成》治療神志病特色分析*
董浩,鄒偉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神志病是指各種致病因素引起機體氣血陰陽失調,臟腑功能受損,導致個體的認知、情感、意志、行為等神志活動異常,包含現代醫學中的精神、心理、心身等多種疾病[1]。針灸治療神志病具有較好的療效,且安全、無副作用。明代是針灸學發展的高潮時期,名家輩出,其中由楊繼洲在家傳著作《衛生針灸玄機秘要》基礎上編撰而成的《針灸大成》被認為是針灸學術史上的第三次總結[2]。《針灸大成》[3]在編排上理論與實踐結合,重臨證而兼針方、病案,記載了大量關于神志病治療的方案,現論述如下。
1 神志病的癥狀表現及疾病歸屬
《針灸大成》中所記錄的與神志病相關的癥狀表現主要集中于席弘賦(卷之二)、蘭江賦(卷之二)、肘后歌(卷之三)、十二經井穴圖(卷之五)、臟腑井滎輸經合主治(卷之五)、十二經治癥主客原絡圖(卷之五)、八脈圖并治癥穴(卷之五)、各經腧穴主治(卷之六)、治病要穴(卷之七)、心邪癲狂門(卷之八)、治癥總要(卷之九)、附楊氏醫案(卷之九)等篇。如“癲、鬼擊、健忘失記、怪癥、鬼魅狐惑、恍惚振噤、中惡、癲狂、或歌或哭、晝夜妄行、夢魘、失志癡呆、悲愁不樂”等,可見于中醫學中的郁病、癲狂、癡呆、不寐、臟躁等病,歸屬于現代醫學的抑郁癥、焦慮癥、神經衰弱、癔癥、狂躁型精神分裂癥、反應性精神病、偏執性精神障礙、睡眠障礙、老年性癡呆、狂躁癥、急性短暫性精神病性障礙等疾病[4]。
由于所處歷史時期的局限性,《針灸大成》中對于神志病的命名多以癥狀、病因為主,具有樸素性。同一癥狀描述可散見于多種現代醫學疾病,多個癥狀描述亦可在一種現代醫學疾病中體現。故應進一步對文獻進行梳理,明確不同癥狀之間的區別與聯系,為臨床篩選有效的治療方案提供基礎。
2 神志病的病因病機
2.1 七情內傷 七情是指喜、怒、憂、思、悲、恐、驚七種情志活動,是人體生理及心理活動對內外環境變化產生的情志反應[5]。突然、強烈或長期的情志刺激超越了人體的調節能力,則會導致臟腑精氣受損,機能失調,進而誘發疾病。《治癥總要第一百四十二》中對于健忘失記一癥,認為與“憂愁思慮,內動于心,外感于情”有關。《針灸大成·附楊氏醫案》中提出:“百病皆生于氣……然氣本一也,因所觸而為九,怒、喜、悲、恐、寒、熱、驚、思、勞也。”其中,怒、喜、悲、恐、驚、思屬于情志致病因素。并以丹溪、子和、莊公等病案為例,指出其癥“困臥如癡”“久思而不眠”“甚悲,而不飲食”為九氣太過所致。七情內傷致病可影響臟腑之氣的升降出入運動,“怒則氣逆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不行、驚則氣亂、思則氣結”,如楊氏治療刑部王念頤公的咽噫之疾,其癥“似有核上下于其間”,認為“此疾在肺膈”,施以膻中、氣海等穴調氣而愈。同時氣機失調又可妨礙機體氣化,不能協調穩定體內新陳代謝,影響精氣血津液的化生輸布,導致其病“變化多端”,如怒氣逆甚則“嘔血、胸滿痛”,喜氣所致則“笑不休、毛發焦”,悲氣所致則“陰縮、筋攣、數溺、血崩”,恐氣所致為“骨酸痿厥,暴下清水,面熱膚急,陰痿”,驚氣所致為“潮涎,目寰,癡癇,不省人事,僵仆”,思氣所致為“不眠,嗜臥,昏瞀,中痞,咽噫不利,膽痺嘔苦,筋痿,白淫,不嗜食”等。現代心理學研究認為九氣中的情志致病因素可與人的基本情緒、復合情緒重合,其致病因素會在心理層面對個體的知覺、決策、信息加工產生負面影響,并可通過SAM系統、HPA軸改變機體穩態,誘發其他疾病[6]。
可見,情志內傷引起的病理變化復雜多樣,多種疾病皆與之有關。有研究指出抑郁焦慮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增加其死亡率[7]。抑郁焦慮、憤怒等可作為心肌梗死后病死率的有效預測因素[8]。由此可見,七情內傷以情志刺激為主因,可直接傷及內臟,影響臟腑氣機。另外,針灸在治病特點上與藥物有本質的區別。其作用實質是“調整”,可依靠激發機體自身的調節功能對機體多系統整體性調節,故對于一些病程持久的疾病,可同時觀察針灸對患者的情緒、心理等方面的影響,發揮其優勢。
2.2 痰邪 《治癥總要第一百四十二》中指出健忘失記一癥可由“有痰涎灌心竅,七情所感”引起。痰邪是人體水液代謝障礙所形成的病理產物,在致病因素上多指無形之痰。其形成與肺失宣降、脾失健運、腎陽不足、肝失疏泄、三焦水道不利有關。痰邪一旦形成,可隨氣流竄全身,阻滯臟腑經絡氣機。若隨氣上逆則易蒙蔽心竅,擾亂心神。由于痰邪隨氣流行的特點,其致病易兼他邪,使臨床癥狀表現復雜[9]。另外,正如楊氏所言,七情內傷和痰邪可相互影響,且七情內傷可直接傷及臟腑,使機體氣郁水停,產生痰邪;而痰邪留滯于臟腑,則使臟腑功能活動失調,五志失常。
現代醫家有“怪病多痰”的說法,針對一些臨床表現怪異、無法迅速明確其病因病機的疾病,如癔癥、精神分裂癥等,可考慮痰邪為患。由于痰邪易兼他邪致病,如日久化熱為痰熱之邪,兼夾寒邪發為寒痰等,在治療時,還應根據寒熱虛實調整治療方案。
3 神志病的治療
3.1 定神,正色 《針邪秘要》中楊氏提出“欲治之時,先要愉悅:謂病家敬信醫人,醫人誠心療治。兩相喜悅,邪鬼方除。若主惡砭石,不可以言治,醫貪貨財,不足以言德。”《素問·寶命全形論篇》言:“凡刺之真,必先治神。”治神即調神、守神,包括治醫者之神和治患者之神兩方面。在治療前,醫患雙方要加強溝通,加強患者對醫者的信任感,使患者能夠全心配合醫者的治療。在治療時,楊氏進一步指出要“定神”“正色”。醫者與患者要“各正自己之神”,若神不定則勿刺,待神定方施術治療。《素問·舉痛論篇》言:“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故要待患者情緒平穩,不可大驚大恐,有強烈的情感波動。正如《針灸直指》指出:“無刺大怒,令人氣逆;無刺大驚;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同時,患者心靜神定還可于醫者施術之時細心體會針感。醫者在持針時要做到“正色”,即“目無邪視,心無外想,手如握虎,勢如擒龍”。在操作過程中,醫者要專一其神,意守神氣,專心于手下針感,辨別疾病虛實寒熱,隨時調整針刺手法。
由此可見,在臨床診療過程中要充分調動醫者、患者雙方的積極性,醫者端正醫療作風,正神守氣,患者安神定志,意守感傳,如此才可提高臨床療效。另外,《針邪秘要》及《刺法論篇》還記載醫者針刺時要配合念咒、禱神、咒針。筆者認為一方面與古人思維方式有關,另一方面可能與此法能夠提高醫者注意力,有利于集中精神,同時可對患者起心理暗示,調整患者心理狀態有關。
3.2 針刺療法
3.2.1 選穴特點
3.2.1.1 按臟腑經脈功能特點選穴 心主藏神,具有主司意識、思維、情志等精神活動的作用。心神清明則各臟腑機能協調,全身安泰。情志傷人首先作用于心神。而古人認為心為君主之官,不得受邪,故設心包以“代心受邪”。督脈“入屬于腦”,益腦髓,與神志活動關系密切;神分之為五,即神、魂、魄、意、志,五神分藏五臟,主導于心,督脈沿脊柱而上,通過大椎與手足六陽經貫通,其絡脈“別走太陽”,通過足太陽膀胱經的背部腧穴調節臟腑功能活動,以養五神。基于此,《針灸大成》主取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經、督脈穴。在腧穴使用上,神門穴、大陵穴居于首位[10]。神門穴,手少陰心經的輸土穴、原穴,具有清心瀉火、養心安神的功效。《卷之六》言其:“主恐悸,面赤喜笑,狂悲狂笑,心性癡呆,健忘,心積伏梁。”《玉龍歌》言:“癡呆之癥不堪親,不識尊卑枉罵人,神門獨治癡呆病。”《通玄指要賦》言:“神門去心性之呆癡。”可見神門穴是治療心神疾病之要穴。有研究表明,針刺神門穴能夠激活額下回眶部,改善大腦磷脂代謝速率,改變以DMN和LPNN為主的腦網絡功能連接,使與情緒控制相關腦區發生變化[11],這為臨床針刺神門穴能夠治療失眠、癡呆、癲狂等提供了理論依據。大陵穴,手厥陰心包經的輸土穴、原穴,具有寧心安神的功效。大陵穴同時是本經子穴,別稱鬼心,屬十三鬼穴之一,能夠清心瀉火,祛邪安神。《卷之七》言其“主善笑不休,煩心,喜悲泣驚恐,狂言不樂。”現代研究表明,針刺大陵穴能夠激活額下回、額中回、顳上回、中央后回及頂下小葉,而額葉、顳葉的改變與精神性疾病密切相關[12]。在督脈腧穴中,常選取百會穴、水溝穴。百會穴位于巔頂,是手足三陽經、足厥陰肝經與督脈的交會穴,“主驚悸健忘,忘前失后,心神恍惚”。該穴善開竅寧神,治療頭腦疾患及神志病證。現代研究表明針刺百會穴能夠改善阿爾茨海默病大鼠的學習記憶功能,其機制可能與提高海馬區自噬相關蛋白1和微管相關蛋白輕鏈3-Ⅱ的表達有關[13]。這為百會穴可以治療“健忘”“忘前失后”提供了理論依據。水溝穴是督脈、大腸經、胃經的交會穴。其善啟閉開竅,是十三鬼穴之一,“主失笑無時,癲癇語不識尊卑,乍哭乍喜,鬼擊”,能夠治療清竅被蒙所致癲狂癇、癔病等神志病變。在《心邪癲狂門》中水溝穴亦配合百會穴治療“喜哭”。
3.2.1.2 按五輸穴主病特點選穴 《臟腑井滎輸經合主治》認為六腑與神志病密切相關,并根據五行理論參考患者脈象、面色確定所病之腑,選取六腑經脈的五輸穴。即首先根據患者脈象、面色、臨床表現定位所病臟腑,如“浮洪脈,病人面赤,口干喜笑”為小腸病,取手太陽小腸經的五輸穴;“浮緩脈,病人面黃,善噫,善思”為胃病,取足陽明胃經的五輸穴;“浮脈,病人面白,悲愁不樂欲哭”為大腸病,取手陽明大腸經的五輸穴;“沉遲脈,病人面黑,善恐欠”為膀胱病,取足太陽膀胱經的五輸穴;再根據“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輸主體重節痛,經主咳嗽寒熱,合主逆氣而泄”的五輸穴主病特點選擇相應的井穴、滎穴、輸穴、經穴、合穴治療。
另外,由于井穴位于四肢末端處,此處為經氣所出的部位,是十二經脈之根,陰陽經脈之氣相交之所,有開竅醒神、疏通氣血、交通陰陽的作用,故井穴使用頻率較高[14]。如《十二經井穴圖》《卷之六》記載“惡人火,聞響心惕,瘧狂,驚好臥,狂欲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刺厲兌穴,“呆癡忘事,癲狂”刺少沖穴,“癲狂”刺至陰穴,“善笑”刺中沖穴,“尸厥不識人,小兒客忤”刺隱白穴,“善恐,惕惕如人將捕之,嗜臥,善悲欠”刺涌泉穴,“魘夢”刺足竅陰穴。
3.2.1.3 善用絡穴 絡穴是指經脈分出處的腧穴,具有主治本經經脈和表里經經脈疾患的作用。如《針灸大成》載列缺穴“主善笑,健忘,癇驚妄見”;豐隆穴“主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見鬼好笑,癲狂”;支正穴“主驚恐悲愁,癲狂”;飛揚穴“主癲疾”;大鐘穴“主嗜臥,欲閉戶而處,善驚恐不樂”;內關穴“主失志”;蠡溝穴“主恐悸,少氣不足,悒悒不樂,咽中悶如有息肉”;鳩尾穴“主癲癇狂走,不擇言語,心中氣悶,不喜聞人語”;長強穴“主狂病”。
綜上所述,《針灸大成》在神志病的治療上選穴呈多樣性,重視特定穴的使用,如五輸穴、原穴、絡穴、交會穴。這與目前針灸治療學大多基于臟腑辨證取穴不同,但在相應篇章中未提及選穴原理。故在今后的臨床觀察可對特定穴進行分析比較,并可根據部分神志病不同分期的表現,篩選更具有優勢的治療方案。
3.2.2 配穴方法
3.2.2.1 原絡相配 原穴是臟腑原氣經過和留止于十二經脈的腧穴。原氣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原動力,通過三焦貫通運行全身。原穴與原氣有關,故取原穴可通達三焦,激發原氣,調整臟腑經絡的虛實[15]。原穴、絡穴聯合使用,稱為主客原絡配穴法,可增強療效,發揮協同作用。《十二經治癥主客原絡圖》中治療“惡人惡火惡燈光,棄衣驟步身中熱”,此為“胃主,脾客”,先刺足陽明胃經原穴沖陽穴,再刺足太陰脾經絡穴公孫穴;治療“臉黑嗜臥不欲糧,目不明兮發熱狂,若人捕獲難躲藏,心膽戰兢氣不足”,此為“腎之主,膀胱客”,先刺足少陰腎經原穴太溪穴,再刺足太陽膀胱經絡穴飛揚穴;治療“痢瘧狂癲心膽熱”,此為“膀胱主,腎之客”,先刺足太陽膀胱經原穴京骨穴,再刺足少陰腎經絡穴大鐘穴。該種配穴方法首先通過經脈病候判斷所屬經脈,此為主,先刺主脈的原穴,再刺與其相表里的客脈的絡穴,同時強調了針刺的先后順序。現代醫家采用原絡配穴針法治療抑郁癥、失眠、輕度認知障礙等具有較好療效[16],可供臨床參考。
3.2.2.2 多種特定穴聯合使用 除單獨使用五輸穴、原穴、絡穴、交會穴等特定穴外,《針灸大成》在治療某一種神志病的針灸處方中常聯合使用多種特定穴以提高療效。如《心邪癲狂門》中治療“鬼擊”采用表里經配穴法,選取手厥陰心包經的間使(經穴)與手少陽三焦經的支溝(經穴);治療“狂言數回顧”選取五輸穴中的陽谷(經穴)與液門(滎穴);治療“喜笑”選取水溝(交會穴)、列缺(絡穴)、陽溪(經穴)、大陵(輸穴);治療“卒狂”選取間使(經穴)、后溪(輸穴)、合谷(原穴);治療“呆癡”選取神門(原穴)、少商(井穴)、涌泉(井穴)、心俞(背俞穴);治療“發狂,登高而歌,棄衣而走”選取神門(原穴)、后溪(輸穴)、沖陽(原穴);治療“癲疾”選取前谷(滎穴)、后溪(輸穴)、水溝(交會穴)、解溪(經穴)、金門(郄穴)、申脈(八脈交會穴)。《八脈圖并治癥穴》中治療“心性呆癡,悲泣不已”選取通里(絡穴)、后溪(輸穴、八脈交會穴)、神門(原穴)、大鐘(絡穴);治療“心驚發狂,不識親疏”選取少沖(井穴)、心俞(背俞穴)、中脘(募穴、八會穴)、十宣(經外奇穴);治療“健忘易失,言語不紀”選取心俞(背俞穴)、通里(絡穴)、少沖(井穴)。
3.2.2.3 經驗配穴 《孫真人針十三鬼穴歌》中記載了13個治療“百邪癲狂”的穴位,命名為十三鬼穴,即鬼宮(水溝)、鬼信(少商)、鬼壘(隱白)、鬼心(大陵)、鬼路(申脈)、鬼枕(風府)、鬼床(頰車)、鬼市(承漿)、鬼窟(勞宮)、鬼堂(上星)、鬼藏(會陰)、鬼腿(曲池)、鬼封(舌下中縫),并記載了針刺深度。十三鬼穴分布于人體9條經脈,其中6穴分布于頭面部,具有調理氣血、開竅醒神、寧心安神的功效[17]。《附楊氏醫案》中記載了楊氏治療通州李戶侯患怪癥1例,針刺十三鬼穴后患者言語遂正,精神復舊,言“以見十三針之有驗也”,可見其獨特的療效。現代醫家亦多用于治療精神分裂癥、躁狂癥、癡呆、失眠、焦慮、抑郁、癔癥等。該組腧穴是一個完整的針灸處方,可視為臨床經驗的總結。但其選穴組方的原理仍尚不明確,需要進一步研究分析。這也提示我們要重視古代針灸醫籍針灸處方的挖掘整理。
3.3 艾灸法 《捷要灸法》中提出治療鬼魅狐惑、恍惚振噤可以選用鬼哭穴,具體方法為“以患人兩手大指相并縛定,用艾炷于兩甲角及甲后肉四處騎縫著火灸之。”該穴又名鬼眼。《經外奇穴》記載了其定位,即“在大拇指,去爪甲角如韭葉,兩指并起,用帛附之,當兩指歧縫中穴”,并指出足大指亦有兩穴,取法可參考手者。《捷要灸法》治療“一切急魘暴絕,灸足兩大指內去甲一韭葉”。依據現代腧穴定位可知,鬼哭四穴為少商穴、隱白穴,且足大指鬼哭穴為足太陰脾經所出,具有培土生金的作用,可借肺臟清肅之氣寧神。袁青強調灸鬼哭穴當用急灸的方法,并與針刺相結合。在患者鬼哭穴處速刺得氣并行瀉法留針,醫者雙手持艾條靠近針柄行瀉法灸,疾吹其火,以患者耐受為度,如此反復。因其病機為陰陽失衡,故多選擇陰陽交接的下午酉時(17:00:00—19:00:00)治療[18]。黎仲謀等[19]認為癲狂等神志病多責于腎,腎應驚恐,患者多為腎陰腎陽失于平衡,且久病陽氣虛衰,在治療上應注重補虛補陽。艾灸具有扶助陽氣的作用,一些神經易激性患者多不耐針刺,故可選用痛苦輕、取穴便捷的灸法。這為臨床采用灸法治療提供了參考。
《心邪癲狂門》中記載了癲狂病中26種病證的治療穴位。其中,治療“癲狂”采用灸曲池、小海、少海、間使、陽溪、陽谷、大陵、合谷、魚際、腕骨、神門等穴,并記載宜灸壯數。治療“癲疾”采用針灸結合的方法,針上星、百會、風池、曲池、尺澤、陽溪、腕骨、解溪、后溪、申脈、通谷、承山等穴,速出,灸百壯。治療“癲狂,言語不擇尊卑”則灸唇里中央肉弦上一壯,炷如小麥大,用鋼刀割斷更佳。治療“狐魅神邪迷附癲狂”灸鬼眼穴。此篇選穴多為四肢肘膝關節處的五輸穴,四肢為經脈的“本”,是經氣集中的本源部位,也是十二經經氣交接流注的重要部位,對治療遠隔疾病、協調陰陽具有重要作用。
與目前臨床治療神志病多采用針刺不同,《針灸大成》記載了多種艾灸療法。目前認為艾灸具有溫經散寒、扶助陽氣、消瘀散結等作用,主要用于陽虛證、腫瘍初起等,少見于神志病的治療,而《針灸大成》擴寬了灸法的應用范圍,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治療思路。筆者認為除古代醫家經驗的總結記載外,可能與艾灸可通過疏通經絡促進氣血運行,進而扶正祛邪使陰陽平衡有關。但目前的參考文獻較少,提示我們可對其記載的艾灸處方與針刺的療效差異及具體機制進行深入研究。
3.4 基于“九氣”“十少”“十多”情志致病理論的治療方法 楊氏在《附楊氏醫案》中提出“九氣”理論,認為人稟天地之氣,諸痛、百病皆生于氣,而氣本為一,因所觸而為“九氣”,即怒、喜、悲、恐、寒、熱、驚、思、勞,其中怒、喜、悲、恐、驚、思屬于情志致病的范疇,并根據以情治情、五行相勝理論進行治療[20]。如肝屬木,脾屬土,若怒傷肝,“怒則氣并于肝,而脾土受邪”,若木太過,則肝亦自病。金克木,而悲屬肺金,故悲可以治怒。另楊氏舉丹溪治一女“不食,困臥如癡,他無所病”一案,認為此癥是由該女婚后丈夫經商三年不歸致思氣結所致,思過則脾氣結而不食。根據思屬脾土,怒屬肝木,木能克土的理論,故激其大怒,哭之三時,木氣沖發而脾土開,即能飲食。楊氏在《卷之七》中提出“十少”“十多”理論,即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飲、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機。并認為多思、多念、多笑、多言、多飲、多怒、多樂、多愁、多好、多機會導致神散、心神邪蕩、志氣潰散、志慮沉迷、氣血虛耗等。許磊等[6]通過分析兩者源流及與現代心理學的關系指出,“九氣”“十少”“十多”理論皆認為情志因素在發病中占主導地位。“九氣”情志致病因素是機體對刺激性事件而產生的消極應對的結果,是對于超負荷事件的一種應激反應,其治療原則為五行生克原理對于驚的習以平驚療法,與現代心理學的系統脫敏法類似。而“十少”“十多”理論更著重于致病情志形成的前提條件是個體對自身的認知、行為障礙和認知的控制水平,并可通過去除誘因、改變認知的方式防治心身疾病,其治療方法類似于現代心理學的認知-行為矯正法。
由此可見,楊氏提出的“九氣”“十少”“十多”體現了中醫學五行學說、五臟藏神理論、形神一體觀獨特的治療方法,表明個體情志因素對于疾病的發生、發展和轉歸具有重要作用。這提示我們在治療神志病時要幫助患者正確認識、對待疾病,避免精神刺激,減輕患者的心理壓力,增強治愈疾病的信心。在治療過程中,家屬也應積極配合,并可結合語言暗示、誘導以提高療效。
4 小 結
《針灸大成》廣泛采輯明萬歷以前的針灸文獻,并集中反映了楊繼洲的針灸臨床經驗,為當今臨床治療神志病提供了豐富的方法,對提高療效具有重要意義。《針灸大成》指出神志病的致病因素是七情內傷與痰邪,二者可影響氣機,損傷臟腑,導致神志病臨床癥狀變化多端,病情復雜多變;在治療方法上,《針灸大成》強調治療時要充分調動醫患雙方的積極性,做到定神、正色,可采用針刺、艾灸及基于情志致病理論的多種治療方法。其中,針刺療法主要選取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經、督脈的腧穴,且重視五輸穴、原穴、絡穴、交會穴的使用,或可采用主客原絡配穴法、聯合使用多種特定穴、十三鬼穴針灸處方以提高療效;與目前臨床采用艾灸法不同,《針灸大成》多采用四肢部腧穴或針灸結合的方法治療神志病,擴大了艾灸法的應用范圍,為今后臨床提供了新思路;另外,基于楊氏提出的“九氣”“十多”“十少”理論,《針灸大成》指出個體情志因素的重要性,可采用以情治情、改變認知的治療方法。今后的研究應對書中腧穴主治、針灸處方整理歸納,并與目前主要使用的辨證取穴進行比較分析,優化治療方案,進一步挖掘灸法的應用,擴寬治療思路。另外,在治療過程中,應根據疾病發生發展的過程和階段,科學而靈活地運用針灸治療,及時選用或配合其他療法,以免延誤病情,如此,才能發揮針灸治療神志病的特色和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