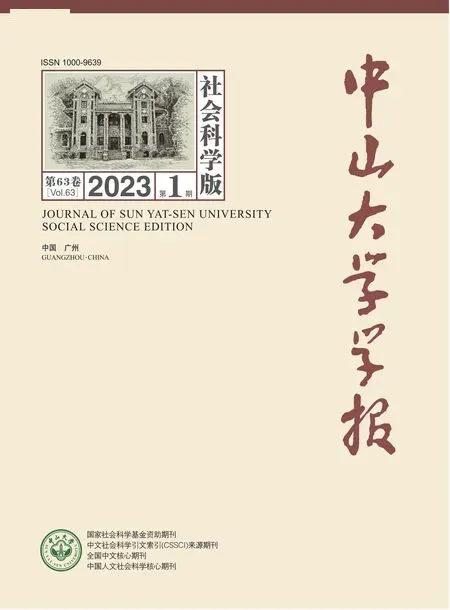美國政府與庚子大沽之役 *
劉 芳
在國際關系史領域,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始終交織影響著各國外交政策。其中,美國往往被認為在過去的200年中,“一直作為世界歷史上最富于理想主義的國家之一出現”①David Callahan, Between Two Worlds: Realism, 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1994, p.37.。這與其長期信仰的“美國例外論”(Exceptionalism)密不可分,而由此顯示出的強烈道德主義(Moralism)原則成為美國外交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道德主義既指用道德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社會、政治和外交,也指政治家傾向于用道德的語言來論證其政策和外交行為的合法性②有關美國外交中的道德主義討論代不乏人,較有代表性的可參見Hans Morgenthau,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s.Moral Abstractio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1950; George F.Kennan,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No.64, Winter 1985/1986; Bruce Nichols, Gil Loescher eds.,The Moral Nation:Humanitarianism and U.S.Foreign Policy Today,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9; Robert W.McElroy, Morali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Role of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國學者也對此多有論述,參見王曉德:《美國文化與外交》,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61頁;王立新:《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以20世紀美國對華政策為個案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70頁;周琪:《“美國例外論”與美國外交政策傳統》,《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楊衛東:《宗教倫理道德與美國外交》,《國際論壇》2010年第5期。。美國的道德特性塑造了其國家行為,進而深刻影響了國際關系、秩序與格局,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就是這樣一個經久不衰的神話,常被認為是美國道德外交之嚆矢。實際上,早在威爾遜之前,美國外交在某些實踐中就已富有道德色彩,對華政策就是典型代表。從中美交往開始,道德特征就一直是中國朝野能夠將美國同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區別開來的重要標志。
至19、20世紀之交,義和團運動興起,八國聯軍以保衛使館為由悍然侵華。美國亦派軍參加,但在首役大沽之戰中,卻并未開炮。此種獨立行動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國道德傳統的延續,但隨后美軍迅速參戰并與聯軍共進退,又事實上違背了它一直以來自詡對中國不動武、不結盟的道德外交。攻取大沽炮臺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關鍵舉措,也是聯軍主力的首次合作,以往學界鮮少注意到美國的置身事外,更遑論以其前因后果觀測美國外交的轉向。①中外學者從軍事史、外交史、文化史等視角考察過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的美國對華軍事行動和政策,布雷斯特德(William R.Braisted)指出美國政府尤其是海軍部出于各方利益考量,認為對華開戰是不合時宜的;韓德(Michael H.Hunt)和保羅·瓦格(Paul A.Varg)分別探究了戰后美軍在北京的占領和中外談判;劉青從文化角度解讀,提出國家榮譽是美國出兵的重要動因。可見既往研究多關注到美國不愿承認中美之間“存在戰爭狀態”,但除了馬士(Hosea Ballou Morse)曾稍有提及美軍在大沽沒有開炮外,鮮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美軍在大沽之戰的行動轉變及其背后的深層動因。參見 William R.Braisted,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897-1909,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58;Paul A.Varg,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s Influence on the Boxer Negotiation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8, No.3 (Aug.,1949), pp.369-380; Michael H.Hunt, “The Forgotten Occupation: Peking, 1900-190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8, No.4 (Nov., 1979), pp.501-529;劉青:《維護大國榮譽:義和團運動中美國出兵中國的文化解讀》,《史學月刊》2012年第5期;[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3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225頁。本文即由此研究視角切入,挖掘美國國家檔案館藏的軍事、外交檔案,輔以各類中外文史料,試圖通過還原大沽之役美軍動向的歷史細節,揭橥評析美國政府的政策抉擇及其將道德傳統與現實利益的雜糅融合,以期對世紀之交中外關系的復雜性有更深刻的認識。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美國東來及其對華政策的道德傳統
美國對華交往的道德傳統,最初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來華美國人較為遵從中國的法律和規則。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就曾指出法律和道德在外交上的天然聯系,“將正確與錯誤的概念引入國與國之間的事務,相信國家行為是一個可以從道德上作出裁決的問題”②George F.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p.100-101.。正如法律可約束國內行為一樣,將遵紀守法的觀念、準則映射到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通常會讓外交行動顯得更有道德。
自1784年“中國皇后”(Empress of China)號駛抵廣州,紛至沓來的美商常常抱怨他們被誤以為是英人而遭受冷遇,幾經解釋和接觸后華人態度才有所改觀。改觀之根源正是清朝官商發現美國人基本上是“循分守法”的③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9年,第2808頁。。1817年,兩廣總督蔣攸铦上奏嘉慶皇帝稱:“近來貿易夷船除英咭唎之外,惟咪唎堅貨船較多,亦最為恭順。”④《兩廣總督蔣攸铦奏報美鴉片船被搶現量予賞恤并曉諭嚴禁片》,嘉慶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頁。這在當時頗具代表性。而此說法于四年后的德蘭諾瓦案又得到良好印證。此案件的審理,清朝地方官完全行使了司法主權,按大清律例判處扔瓦罐致一華婦落水身亡的美船船員德蘭諾瓦(Francis Terranova)絞刑。美國領事、船員、商人等并未表現出強烈的反抗,美國媒體亦在事后評論道,美國人沒有包庇自己人是因為嚴格遵循了國際法(law of nations),“即一個外國人自愿進入一國管轄范圍之內后就有遵守該國法律的義務”⑤Execution of on Italian, North American Review, January, 1835, pp.58-59.。
相比于英人的桀驁不馴,遵守法度的美國人在中國人看來更加本分、恭順,也更有道德和修養,這份好感逐漸為美國人的在華活動贏得便利。不僅在私人層面美國商人從中國行商處獲得了不少好處:后來當上廣州領事的本杰明·威里各(Benjamin Wilcocks)曾經幫十三行巨富伍秉鑒在美收債,他本人因此被伍氏免去了72,000美元債務;伍秉鑒也曾在波士頓商人約翰·福布斯(John Forbes)開辦工廠時慷慨給予50萬銀元貸款①[美]雷麥著,蔣學楷等譯:《外人在華投資》,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381頁。。而且在官方層面,美國還往往因此免遭清政府的貿易制裁。1839年中英沖突爆發,在林則徐嚴禁鴉片時,美商雖然幾乎都曾參與過鴉片貿易并“發足了財”②[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十九世紀美國對中國、日本和朝鮮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03,87—88頁。,他們還是不顧英國的憤怒先與清廷“具結”,旗昌洋行甚至公開發出誓絕鴉片貿易的通知。結果是,英商被迫撤離廣州,美商卻能獲準恢復進口通商,“美船都駛入內河”“交易活躍進行”,最終“美商賺錢最多”③[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第266頁;《英軍在華作戰記》,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第5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0頁。。
美國在繼續展示友好姿態的同時,還曾試圖借英國之力“搭便車”實行“拾荒者”外交④參見[美]托馬斯·G·帕特森等著,李慶余譯:《美國外交政策》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58頁;[美]泰勒·丹涅特:《西華德的遠東政策》,《美國歷史評論》第28卷(1922年10月),轉引自[美]孔華潤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282頁。。只是以往研究多謂其結果是向中國索取了同歐洲人均等的貿易權力⑤參見李育民:《晚清時期中美條約關系的演變——從“搭便車”到“門戶開放”》,《人文雜志》2018年第2期。,而實際上美國在“搭便車”的同時亦以所謂“適當的尊重”攫取了一些獨享的好處。1840年,英國遠征軍侵華,美國也派遣海軍準將加尼(Lawrence Kearny)赴華統率東印度艦隊(United States Naval Forces, East India and China Seas),目的并非要聯英侵華,而是希望以“不必進行流血戰爭”的方式同清政府訂定條約⑥[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十九世紀美國對中國、日本和朝鮮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03,87—88頁。。加尼抵華后,一面宣稱中美友好拒不參加英軍的對華作戰,一面又以保護僑民為由派艦艇駛入黃埔,為一年前被炮擊誤殺的美國水手索取了7800美元賠償,還向廣州當局提出享受最惠國待遇的要求,為后面顧盛(Caleb Cushing)的來華談判鋪平了道路⑦Trip to Canton in the Constella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11, Canton: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 1842,pp.329-335.。
此后,美國逐漸明確了表面不訴諸武力以維系“友好關系”,但暗中支持列強以獲取共享或獨享利益的政策,不動武、不結盟的對華外交傳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臻于成熟。英法組建聯軍后曾試圖游說美國加入,白宮不僅多次拒絕,而且始終“認真反對”駐華代表麥蓮(Robert Milligan McLane)提出的聯合武裝封鎖白河等地的建議⑧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從鴉片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842—1918》,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35頁。。麥蓮回國后,伯駕(Peter Parker)在接任期間的兩個意外,更充分說明了美國政府的態度。
先是1856年10月,美國駐香港領事詹姆士·琪南(James Keenan)手持美國國旗率領美國海軍跟隨英軍攻入了廣州城。國務卿馬西(William Learned Marcy)在英國報章上讀到消息后十分緊張,認為琪南此舉嚴重違反了美國的中立態度,立刻訓令伯駕:如若倫敦報紙所載屬實,伯駕應立即將琪南免職⑨Marcy to Parker, February 2,1857, Diplomatic Instruc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4,1899-August 14,1906, M77, R38,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個月后,中英沖突升級,粵督葉名琛要求在廣州的外僑撤離。美艦在將美僑撤出時,被廣州橫檔炮臺誤以為是英艦而受到炮擊,出現7人死亡、20人受傷的情況。翌日,美海軍準將奄師大郎(James Armstrong)下令摧毀橫檔炮臺。當時在華西人看來,這似乎已標志著美國決心與英國合作,用武力對付中國。但實際上,此乃奄師大郎的個人行動。皮爾斯(Franklin Pierce)總統聞訊后反應激烈,斥責海軍“不審慎之舉動”。國務卿馬西緊急訓令伯駕:
我感到總統對于我國海軍事先行動欠審慎、事后又缺乏忍耐之舉,必引以為憾。顯而易見,英國政府目前對華的野心已遠超過美國的冀求。所以,無論英國如何渴望我們與之合作,我國均不應卷入漩渦。總統竭誠希望你及我們的海軍司令全力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不要卷入英、中兩國的沖突之中,亦不可使任何有礙美、中傳統友好關系的嚴重事態發生。①U.S.36th Congress, Ist Session, 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No.30, p.4.
這則訓令可以作為美國不動武、不結盟以維系中美“傳統友好關系”的最好詮釋。不僅在這次英法聯軍侵華戰爭中,而且在隨后數十年內發生的中法、中日等戰爭中,美國政府都反復強調其“并沒有和中國作戰”②[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十九世紀美國對中國、日本和朝鮮政策的批判的研究》,第261—163頁。。而它也逐漸找到這套政策更適合的角色,乃是中外沖突之間的“調停者”,既能表面以對華和平和尊重博取清廷一定信賴,更能暗中支持列強侵略。結果是這兩條路徑往往都能讓美國收獲事半功倍的意外之喜。
至19世紀末,美國人甚至相信,通過所謂的自我克制,美國的友善和無私不僅是無恥貪婪、自私自利的歐洲望塵莫及的,就連中國也須對其充滿感激。1899年,美國政府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正是這種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延伸③以柔克義為代表的美國官員認為美國已努力為中國保持了完整性,中國只需履行其條約責任罷了。參見Rock‐hill to Edwin Denby, January 13,1900, Rockhill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卻沒想到次年庚子春夏,由義和團運動引發的中外紛爭愈演愈烈,戰事將起、聯軍侵華迫在眉睫,美國亟需決定參戰與否這個關鍵問題。背負不動武、不結盟道德傳統的美國在事起之初有些反應遲鈍。美國總統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和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深知,八國聯軍這種方式是與美國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對華政策背道而馳的,一旦聯軍對華開戰,身處其中的美國也會被迫使用武力并與歐洲結盟,那么美軍是隨同聯軍奔赴戰場,還是抽身而出呢?他們反復斟酌,始終猶豫不決、難下決斷④事后海約翰深知他在這個春天延誤了,以致在接下來的酷暑中飽受想象中的“悲劇性恐怖場面”的折磨。參見[美]韓德著,項立嶺、林勇軍譯:《一種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國與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06頁。。正在這時,各國駐京使臣突然同外界失聯,傳統外交途徑被迫中斷。中外猜忌加深,列強軍艦齊聚大沽,于是突然介入的海軍將領們成為決定局勢走向的關鍵力量。
二、庚子美未開炮與“莫諾卡西”號遇襲
1900年6月9日,英國公使竇納樂(Claude MacDonald)向大沽發出了失聯前的最后一封電報,他請求海軍上將西摩爾(E.H.Seymour),“情勢萬分嚴重,除非設法立刻向北京進軍,怕要來不及了”⑤MacDonald to Salisbury, June 10,1900, China No.4 (1900):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Minister in China Respect?ing Events at Peking, London: H.M.Stationery Office, 1900, p.1.。與此同時,已于5月底抵達中國的美軍指揮官、海軍少將坎卜夫(Louis Kempff)也收到美國公使康格(Edwin Conger)類似的電報,康格呼吁“鐵路交通一定要打開,可能的話,向北京移動軍隊”⑥Mr.Conger to Mr.Hay, June 11,1900, No.391,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Washington: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 p.144.。當日,各國海軍將領在英國旗艦上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派遣一支遠征部隊進入北京救援公使⑦James W.Ragsdale to Conger, June 12, 1900, No.88, Letters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December 24, 1897 to May 1, 1902, pp.124-126, Consular Post Records: Tientsin, RG84,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elegram Consul W.R.Carles at Tientsin to Salisbury, June 10, 1900, No.104, China No.3 (1900):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Insurrec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London: H.M.Stationery Office,1900, p.45.。數小時內就從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八國戰艦上集合了約二千人,由軍階最高的西摩爾指揮,美軍派出了由麥卡拉(B.H.McCalla)上校率領的100人參加。10日凌晨,西摩爾未等及倫敦批準,就匆匆率領這支隊伍在塘沽登陸,乘坐火車前往天津租界,并從那里繼續搭乘火車前往北京。西摩爾本以為很快就能到達北京,遠征軍沒有攜帶足夠的口糧與彈藥,導致在遭到義和團襲擊時陷入被動受困的局面。不論像美國公使康格事后憤憤地表達對于該部隊為何沒有舍棄火車選擇徒步進入北京的不理解①Mr.Conger to Mr.Hay, June 18,1900,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151.,還是如馬士將其歸結為一個海軍軍人在陸地上指揮無法看清局勢②[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3卷,第231頁。,西摩爾聯軍的失敗,事后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而在當時,它帶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對留守大沽的各國將領們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此刻,同北京公使的聯絡也幾乎同時中斷,美國國務卿只能無力地向康格發送他收不到的電報,詢問他是否需要更多的軍隊③Mr.Hay to Mr.Conger, June 15,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155.。外交活動能夠發揮作用的空間急劇縮小,軍事力量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由西摩爾聯軍失聯,到決定奪取大沽炮臺,是各國海軍將領與駐天津領事反復商談的結果。事實上,爭論很兇,他們根據當時情勢,列出亟待保護的四類外國人:北京的公使僑民、天津的外僑、失聯的西摩爾遠征軍和分散在各內地的外國人。領事們擔心攻占大沽炮臺,會激起中國軍民的強烈反抗,勢必威脅到各地外僑的生命財產安全,聲稱“倘若你們奪取炮臺,你們將要為每個在內地的外國人簽署死刑證”,主張“緩占”。海軍將領們則認為若延遲行動,非但無法保證傳教士和外僑的安全,反而會使西摩爾聯軍的處境更加危險;而若迅速奪占大沽炮臺,一則可為挽救西摩爾聯軍“打開交通路線”,二則能為后繼的大批聯軍獲得登陸據點,三則可以排除對外國艦隊的炮火威脅。進而才能“代剿團匪”,真正保證外僑的安全④參見李德征、蘇位智、劉天路:《八國聯軍侵華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00頁。。
6月13日,海軍將領們將中方在大沽炮臺的異動,指控為源于清廷命令抓緊備戰的諭旨⑤Flag Lieutenant Victor Blue to Kempff, June 13,1900, Navy Area 10, Area File 1775-1910,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此后,他們又以清軍開始在海河布雷,向大沽口大量派兵,宣稱因為這些清軍已接到協助義和團、驅逐外國人的命令⑥Blue to Kempff, June 15,1900 (three separate letters), Navy Area 10, Area File 1775-1910,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Consul Carles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Telegram), June 15,1900, No.132, China No.3(1900):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Insurrec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p.56.Kempff to Long, June 21, 1900, No.29-D,Navy Area 10, Area File 1775-1910,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外加天津有多所教堂于14、15這兩日被燒毀。各國海軍上將(日本、意大利、奧匈三國為高級艦長)順勢于6月15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先派出300名日軍、250名法軍和俄軍分赴塘沽與軍糧城,保全這兩點之間的鐵路,為后續進京排除障礙⑦[英]阿諾德·亨利·薩維奇·蘭道爾著,李國慶、邱葵、周珞譯:《中國和八國聯軍》上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第98—99頁;[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3卷,第224頁。。軍事上的“速奪”論壓倒了外交上的“緩占”論,16日上午的將領、領事聯席會議最終決定向中方發出最后通牒。當日午后聯軍即開始軍事部署,至晚上才由沙俄水師艦長巴赫麥季耶夫向大沽守將羅榮光面交最后通牒,宣稱:“現在俄、英、德、法、意、奧、日七國約定,限令中國軍隊于17日凌晨兩點鐘讓出大沽南北炮臺營壘,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⑧《直隸總督裕祿折》,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64頁。明明是八國出兵,美國卻并未出現在最后通牒當中。這是為何?
因為美軍指揮官坎卜夫拒絕在最后通牒上簽字。這位年近六旬、經驗豐富的海軍將領畢業于美國海軍學院,參加過南北戰爭,在海軍服役了近40年,1899年3月剛由資歷最深的大校被擢升為少將①Many Naval Changes, Milwaukee Journal, January 5, 1899, p.9.Naval Promotions, Indiana State Journal, March 8, 1899.。庚子之役是坎卜夫晉級將軍后的首秀,還極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帶兵打仗,因為再有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就可以光榮退休了,當然,要是能在退休之前更進一步是最好不過。這樣一場關鍵之戰正是他施展畢生軍事經驗與才干的絕佳舞臺。但到達大沽之后,坎卜夫很快發現美國政府的指示遠不足以幫助他應付近日的緊張形勢。
大沽情勢急轉直下,列強海軍頻頻有所動作,坎卜夫接連致電海軍部報告時局,請示是否要與其他列強一致行動。但自派兵伊始,美國政府就深受既要維護利益又要避免聯盟的雙重目標困擾,海軍部無法作出明確答復,只能模棱兩可重復飭令他采取他認為最有助于保護美國利益的行動,但要避免被視為聯盟。坎卜夫反復致電,甚至明確詢問是否在奪取大沽炮臺上一致行動,渴望得到明確的指令,但結果是他再次被告知,如果他看來這項行動對保護美國的利益有好處,就可以采取,同樣要避免結盟。給坎卜夫的電報其實與麥金萊總統的指示一脈相承,代理海軍部長海克特(Hackett)此前曾告訴過他,美國政府很迫切想要避免任何對其與英國秘密聯盟的指控②Non-Committal Attitude: Administration Still Gives Indefinite Orders — Instructs Kempff to Do What is “Advisable”,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00, p.3.。這點坎卜夫由其上司、美國海軍亞洲區最高指揮官雷米(George C.Remey)上將的訓令中,也能深切地感受到。坎卜夫本以為是應美國公使康格的特別要求,他才派兵參加西摩爾遠征軍,而且鑒于局勢不斷惡化、各國軍事力量都在增加,他也多次要求增加赴華美國海軍。但都遭到雷米的拒絕,雷米嚴厲批評坎卜夫,指責他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太過密切,這將可能會使美國卷入歐洲國家的問題和對立之中③Remey to Kempff, June 4, 1900, Letterbook 1, pp.422-424,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鑒于上級指示的整體觀感,坎卜夫判斷美國尚未做好作戰準備,最終選擇暫不參與聯軍的對華作戰行動,不僅拒絕在最后通牒上簽字,而且不愿加入列強對大沽的炮擊。
6月14日,英軍將領布魯斯(Bruce)就曾為最后通牒向坎卜夫密探口風,后者答稱:“我沒有被授權同一個美國仍舊交好的國家開始戰爭,我的使命僅是保衛美國的利益。”15日,坎卜夫也拒絕參與聯軍攻占塘沽火車站的戰斗,理由是他“不能參加對中國政府財產的占有”④Kempff to Long, June 17, 1900, No.21-D, Navy Area 10, Area File 1775-1910,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6月17日凌晨,列強艦隊與大沽中國守軍展開了激烈對攻。而在坎卜夫的命令下,美國艦船沒有加入當日的炮擊行動,坎卜夫的船只甚至因為停泊得太遠,無法近距離觀察到戰火。
然而,一艘美國炮艇卻意外卷入了戰火,它就是由懷斯(Frederick Wise)上校指揮的“莫諾卡西”號(Monocacy)。“莫諾卡西”號隸屬于美國海軍東印度艦隊,常年被派駐長江沿線執行護僑任務,至庚子年已在華服役超過30年,船身早已破敗不堪,就連海軍軍官都不敢搭乘它前往馬尼拉⑤Senator Lodges Speech, The Sunday Herald, June 24, 1900, p.2.。開戰前,這艘老炮艇剛被緊急調往大沽,因為坎卜夫發現海河水特別淺,想要嘗試以吃水淺的“莫諾卡西”號上溯至天津。結果發現這個想法同樣是無法實現的⑥Low Water in the Pei-ho, Boston Herald, June 23, 1900, p.3.。這樣,“莫諾卡西”號在海河的任務就變成為大沽和塘沽兩地的外國僑民提供避難。為此,懷斯上校曾代表坎卜夫參加了16日的聯席會議,他同樣沒有簽署最后通牒,而是奉命在17日的軍事行動中保護僑民,這些人在戰斗開始前接到命令,為了安全起見須在1小時內轉移至美艦“莫諾卡西”號上⑦[俄]德米特里·揚契維茨基著,許崇信等譯:《八國聯軍目擊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9頁。。據懷斯給坎卜夫的報告,他在16日晚上9點左右共收容了37名婦女兒童。這艘破爛老舊的美國明輪木質炮艦選擇了一個遠離炮臺和進攻艦船的地方停泊,據說相當安全。卻沒想到,“莫諾卡西”號幾乎是最先被中國炮彈擊中的,馬士驚呼這真是奇怪得很①[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3卷,第225頁。!在一旁觀戰的英軍記者蘭道爾(Henry Savage Landor)恰好記錄下“莫諾卡西”號遇襲的過程:
莫諾卡西號的懷斯艦長站在艦橋上,試圖鼓勵和振作那些擠在甲板上的婦孺們,因為他們都被呼嘯爆炸的炮彈嚇壞了,幸虧這些炮彈都是高高地飛過了頭頂。他和他的軍官們向這些避難的人保證,他們的船停靠的位置絕對安全。正在此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一發炮彈打穿了他的船頭。②[英]阿諾德·亨利·薩維奇·蘭道爾著,李國慶、邱葵、周珞譯:《中國和八國聯軍》上冊,第103—104頁。
“莫諾卡西”號完全是在意料之外被擊中的。此前坎卜夫給懷斯僅有的命令是保護美國的利益,故而懷斯指示部下不要向清軍開火,除非受到射擊③Kempff to Wise, June 15, 1900, No.168-S, Navy Area 10, Area File 1775-1910,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突如其來的炮火襲擊,讓“莫諾卡西”號處在了一個相當危險的境地,除了持續遭受炮火轟炸的可能性外,更關鍵的是外交與軍事意義上的,應該如何看待被擊中的事實并作出反應?
懷斯艦長根據其軍官報告,將從附近飛過的或在周圍及遠處爆炸的炮彈全部歸為“來自炮臺的胡亂射擊”,試圖避而不談“莫諾卡西”號遭到中國軍隊射擊這一點,而將全部精力集中在“保護美國利益”的問題上。因此懷斯艦長作出的決定不是加入戰斗,而是將艦船撤退到了完全遠離炮臺的地方,按照他本人事后的報告,最終停泊的地方“空無一人,岸上沒有火車也沒有電報通訊”,以致于他最后“除了炮臺被占之外”,“對戰斗一無所知”④Wise to Kempff, June 17,1900, No.7, Navy Area 10, Area File 1775-1910,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三、打破不動武的道德傳統與美軍參戰
懷斯艦長當然想象不到他這個舉措會對當時的中美局勢產生怎樣的影響,他能做的就是謹遵上級指示,其來源正是美軍指揮官坎卜夫。然而諷刺的是,坎卜夫本人事后卻并不認可懷斯的解釋。坎卜夫將“莫諾卡西”號遭受的炮彈視為清軍發動對美戰爭的信號,認為美軍應該奮起反擊。事實上坎卜夫譴責了懷斯上校避不作戰的反應,在隨后的訓令中,他命令懷斯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制造相同的起因,幫助其他國家進行軍事登陸,以保護所有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⑤Kempff to Wise, June 18, 1900, No.175-S, Box636, Subject File to 1911, Class2, V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 China, 1894-1910,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就這樣,美國雖然全程抽離于大沽戰斗之外,但當奪取炮臺作戰結束后,335名美軍官兵隨同聯軍一道在大沽登陸了,從這一刻起,美軍就以一種相對“遲緩”的方式,加入了列強在中國的聯合軍事行動。
很顯然,坎卜夫的政策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因為若是奉行美國一貫的不對中國動武、不與列強結盟的道德原則,沒有開炮的美軍完全可以繼續置身事外,不必參與隨后的聯軍行動。加入聯軍則意味著對傳統的打破,是個相當大的事情!即便坎卜夫沒有說明政策轉向的根源,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得到了上級的授權。
因為美國海軍沒有在大沽開炮的行動引發了總統和海軍部的強烈不滿。當得知“莫諾卡西”號在遇襲后沒有反擊,麥金萊總統相當震驚,斥責坎卜夫要作出解釋①Non-Committal Attitude: Administration Still Gives Indefinite Orders — Instructs Kempff to Do What Is “Advisable”,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00, p.3.。海軍部官員毫不諱言對美軍參加大沽之戰的期待,故而在接獲坎卜夫坦承炮臺是由“其它國家軍隊”奪取的消息后大失所望,聲稱攻打大沽炮臺是救援使館的必要舉措,“坎卜夫也應該知道這是保護美國利益之職責所在,他必須承擔起這個責任”②A Report from Kempff,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00, p.3.。可見,坎卜夫的轉變根本來自于美國政府對參戰態度的改變,那么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又是何時下定決心要參戰的呢?事實顯示,就在美國政府向坎卜夫下達了一系列不結盟的命令后,因京津整體局勢牽動的國際形勢和美國國內情勢發生轉變,美國政府亦有轉向意愿,本可在大沽戰前的關鍵時刻傳遞給坎卜夫,卻沒想到在這個時候他們跟坎卜夫失聯了。
1900年6月17日,美國海軍部憂心忡忡,因為他們已經連續三天沒有收到坎卜夫的消息了,海軍部長與總統、國務卿緊急召開會議,討論向中國增兵問題③Admiral Kempff Cut off,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00, p.1.。從駐京公使到西摩爾聯軍再到海軍少將,關鍵人物的接連“失蹤”讓中國情勢愈發撲朔迷離,對在華美人安危的擔憂,對列強采取強硬行動的猜測,讓越來越多的美國媒體開始呼吁美軍不能再獨善其身(spared)了,聲稱絕大多數美國人已意識到美國正與其他列強同在一條船上,若無法聯合行動,將會一同沉沒④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Times, June 19, 1900, p.5.。美國政府雖然不愿率先對華開戰,但也逐漸發現,若始終自外于戰,美軍既有被排擠出八國聯軍的危險,更無法完成救援使館的任務,遂暗中已有放棄不結盟不動武傳統的打算⑤況且在多數美國官員看來,不結盟并不意味著不合作,在必要的時候美國仍可同其他列強為共同目標展開配合。。故而在接到大沽開戰的消息時,一位美國高官難掩興奮向媒體吐露他的喜悅,他相信美軍必須參戰⑥Non-Committal Attitude :Administration Still Gives Indefinite Orders — Instructs Kempff to Do What Is “ Ad‐visable”,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00, p.3.!
大沽的消息來自停靠在芝罘的美艦“約克鎮”(Yorktown)號,陶西格(Taussig)艦長向上級報告稱,大沽炮臺已于17日當天被聯軍攻占⑦Fleet Silences the Chinese Forts, New Haven Evening Register, June 18, 1900, p.1.。正一籌莫展的海軍部突然被注入了一針強心劑,迅速反應過來,代理海軍部長海克特馬上指示坎卜夫與其他列強一致行動,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保護所有美國利益,他還必須“讓海軍部了解列強的聯合遠征計劃,以便美國政府可以很好地履行其有大量利益維系的義務”⑧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Hackett to Kempff, June 18, 1900, McKinley Papers, Library of U.S.Congress.。所有人都明白,美國政府授予了坎卜夫奪取炮臺、戰斗等采取任何行動的全權⑨Kempff Has Full Power, Morning World-Herald, June 19, 1900, p.1.。既已開戰,海軍部甚至給了他不必經由在馬尼拉的上級而直接報告的便宜行事之權。
給坎卜夫的訓令直接發給駐在芝罘的陶西格,再由陶西格派人快馬送去大沽。按芝罘至大沽不到一天的路程來算,遲至18日坎卜夫就應收到指示,并由此指揮美軍登陸參與隨后作戰,而他本人也于20日發回一份報告,為其在大沽的復雜行為做了一番辯解。首先,針對他拒絕加入占領火車站和大沽炮臺作戰,他認為這是嚴格遵循了美國政府不愿與其他國家結盟的政策,不僅對華作戰會威脅內地美僑的生命,而且直至6月17日清政府都沒有承認對外國軍隊的敵對狀態。但當炮火打到“莫諾卡西”號時,坎卜夫看來“戰爭就事實上開始了”,因此“有必要加入其他國家軍隊,共同保衛外國人和我們國家的榮譽”⑩Kempff to Long, June 20, 1900, Navy Area 10, Area File 1775-1910,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解釋帶有明顯迎合之意,華盛頓官員們并不滿意。首先,坎卜夫沒能很好地說明既然“莫諾卡西”號遇襲象征中美戰爭開始,為何美軍未作還擊。因為在許多美國人看來,清軍無意間對美軍的攻擊恰給美國政府提供了加入聯軍的絕佳借口。在此之前,清政府尚未對外(美)宣戰,若由美軍先開戰,美國將被置于令人厭惡的侵略者的地位;而一旦清軍先襲擊美軍,情況恰好相反,美國將有權“自我防御”,從而師出有名了。因此,許多早已暗中期盼清軍先動手的美國官員對坎卜夫主動舍棄良機大為光火,海軍部官員們甚至將此舉視作是在列強面前將美國海軍置于非常荒謬的地位,因為他竟然沒能擔負起旗幟受辱時捍衛旗幟榮譽(the honor of the flag)的基本軍人責任①Cruiser Brooklyn Ordered to Taku, Times, June 25,1900, p.1.。
而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如前所述,美國政府的對華作戰決心在美艦遇襲前就已逐漸明朗。當大沽開戰的消息經歐洲大陸傳至北美時,美國政府和媒體即刻一邊倒向參戰。媒體紛紛將此視為一場歐美日聯合對抗“一個殘暴反動政府的戰爭”,就連歷來強烈反對使用武力的《紐約晚報》(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也公開宣稱:“文明和半野蠻之間的戰爭開始了,美國的加入是必要且別無選擇的。”②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Times, June 19, 1900, p.5.由此,如果說美國此前還要顧及一下對華不動武的道德傳統,美國總統始終在增兵和參戰問題上謹慎節制,許多派兵行動均是在高度保密的狀況下進行的;那么這時,麥金萊不僅主動向各界公開了政府的增兵計劃,而且授予坎卜夫毋庸請示即可采取任何行動的權力③The Powers And The Situation, The Times, June 20, 1900, p.7.。也正是如此,當得知美軍并未參戰的消息,美國政府大失所望;美軍甚至沒能抓住“莫諾卡西”號遇襲這一良機而有所行動,失望、遺憾變成了總統對坎卜夫的滿腔怒火。
麥金萊將“莫諾卡西”號的不回應歸結于受到不開火命令的限制,自然地遷怒于負有領導責任的美軍指揮官④The Monacacy and the Taku Fight, New York Times, June 26, 1900, p.2.。6月25日,正在外地的海軍部長朗(Long)被緊急召回華盛頓的同時,一條命令發至馬尼拉,雷米上將奉命即刻前往大沽,接管赴華美軍指揮事宜⑤Remey to Relieve Kempff, New York Times, June 29, 1900.Irritation with Kempff, New York Times, June 30, 1900.。所有人都清楚,這是對坎卜夫的公開責罰。而此時華盛頓的政治空氣里,不滿與惱怒仍舊在積聚。麥金萊甚至對海軍部不再信任,次日追加一令,剝奪海軍的指揮權,轉而任命曾參加過古巴戰爭的陸軍上將沙飛(Adna R.Chaffee)接替⑥Corbin to Chaffee (telegram), June 26, 1900,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ar with Spain: Including the Insurrec?tion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nd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April 15, 1898 to July 30, 1902, vol.1, Washington, D.C.: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3, p.418.。臨陣換帥乃兵家之大忌,美軍在如此短暫時間內的劇烈人事震動,足以反映華盛頓高層對大沽作戰形勢的態度。美國政府嚴厲批評美軍未在大沽及時參戰,正是美國決心躋身對華作戰陣營的根本體現,而本質上它始終并不在意美艦是否先受攻擊。被動反擊只是個借口:若無,不會影響其參戰;若有,則更順理成章罷了。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并不是美軍頭一回在華被誤傷。1856年在7死20傷后奄師大郎報復性炮轟清軍炮臺,遭到總統和國務卿的嚴厲斥責:要忍耐,不應動武!坎卜夫豈會不知此事,因而他本能選擇了遵循美國的既有政策。但這次在沒有任何人員傷亡的情況下被要求武力反擊,唯一的解釋就是美國政府自身不再按傳統行事了。事實證明,通過對華作戰,美國已經在主觀上和行動上撕下了其含情脈脈的道德面紗,成為公然武裝侵華的帝國主義重要一員。
四、非戰爭狀態下的進軍和調停并行
大沽戰局與國內外輿論讓麥金萊總統迅速調整政策,果斷做出了跟兩年前美西戰爭一樣的決定:是時候軍事干預了。而當白宮下定決心后,之前模糊的訓令獲得了全新的解讀。坎卜夫認為在大沽戰前美國政府只明確說要保護生命財產,他無權逾越訓令賦予的權限。而高層的說法是訓令實際上已向其暗示:“他擁有更廣泛的行動權限,并不只限于保護生命。他被寄予維護美國全方位利益的希望,也就是說,他可以采取任何行動阻止對美國在華商業和貿易的損害。”①Americans to Fight, Sun, June 20, 1900, p.9.
坎卜夫本人對此說法深感委屈,部分海軍官員亦對他被剝奪指揮權的遭遇表示同情。理由是大沽開戰那三天的通訊中斷極有可能讓坎卜夫無法接收到任何指示②Irritation with Kempff, New York Times, June 30, 1900, p.2.。對此,高層也并不認可。在總統、國務卿和海軍部長看來,同華府失聯是坎卜夫的問題,畢竟在重大的和戰問題上他沒能及時想盡辦法請示和接收訓令,反倒是先由海軍部這邊接通芝罘通道進行聯絡。何況在此期間,他發回美國的消息既簡短到無法闡明事態的進展,又不夠真實而容易讓人誤解中國的實際情狀,故而要為美國政府的遲鈍或錯誤反應負有很大的責任③The Powers And The Situation, The Times, June 29, 1900, p.7.。
麥金萊對坎卜夫的指責是不遺余力且堅定不移的。即將于該年底到來的總統大選牽動著他的神經,媒體、輿情代表著所謂的民意走向,在國內甚囂塵上的參戰呼聲中,他對美軍在大沽戰場的無所作為大發雷霆。因為這讓他不僅面臨著來自國內商人與傳教士團體對政府無能的激烈指責,其他列強對美軍的信任與觀感也會大受影響。八國聯軍雖號稱八國,實際進攻大沽的只有英、法、俄、德、意、日六國,奧匈帝國因為尚未有軍隊到達無法參加,美國則是正面拒絕了同其他列強的聯合行動,引起了其他國家軍隊的普遍不滿。歐日各國的報章紛紛撰文譴責美軍破壞聯合。而且由于列強在大沽遭到了清軍的頑強抗擊,甚至有許多人將聯軍在大沽戰斗中的損失慘重,歸咎于美國暗中向清軍提供了情報④Kempff’s Attitude at Taku, New York Times, July 6, 1900, P.9.。即便美軍迅速加入在大沽登陸的聯軍隊伍,也未能讓非議減弱。美國面臨來自盟友內部前所未有的壓力。
只是隨后列強發現,恰巧從聯軍奪取炮臺的17日當晚開始,天津紫竹林租界受到猛烈圍攻,不能不讓人聯想到是聯軍炮轟大沽遭致的這一后果;且聯軍上岸后,一路受到清軍和義和團的聯合攻擊,也很有可能是大沽之戰促成了這二者的結盟⑤Kempff Opposed Hostilitie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 1900, p.1.。若是如此,坎卜夫在聯席會議上反對攻打大沽炮臺似乎又變得富有預見性了,他當時言之鑿鑿警告各國將領奪取炮臺必會遭致中方的仇視和報復,進而威脅到京津僑民的安危⑥British Praise for Kempff, New York Times, July 4, 1900, P.2.。美國政府自然樂于接受這類觀點,因為它有利于減輕列強對美國的不滿,其中剛被陸軍奪走指揮權的海軍最迫切需要擺脫被各方指責的境地,朗部長立刻公開贊揚了不開炮行動⑦Why He did not Fire,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6, 1900, p.2.。英、法等國亦漸平息怒火,同意以觀后效⑧Kempff’s Attitude at Taku, New York Times, July 6, 1900, P.9.。
事實上,八國聯軍在7月的推進并不順利,中國東南省份的約定“互保”讓外交手段始終未盡失效。美國政府意外發現,大沽未開炮為其在折沖中外上贏得一絕佳位置:美國一躍成為最受清廷矚目的調停者(mediator)。
雖然美國聲稱清軍“應該知道‘莫諾卡西’號已經在那里停泊了好幾天了”⑨Kempff to Long, June 20, 1900, Navy Area 10, Area File 1775-1910, RG4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暗示中國守軍在明知美國軍艦的情況下還開炮轟擊。但這只是美方為制造參戰正當性的借口,“莫諾卡西”號如其艦長報告是被“來自炮臺的胡亂射擊”擊中的。清政府既沒有注意到最后通牒上少一美國將領的簽字,大沽守軍在射擊時亦不可能留意到美軍艦船并未開炮,戰斗慘烈得他們甚至無暇區分停泊在大沽口外炮艦上飄揚的各國旗幟。清朝官員們也是在事后由外國政府處才得知美軍的不同。大沽戰后4日,中國駐日本公使李盛鐸從日本外務省獲知此信息,在給兩廣總督李鴻章的電報中首次透露“惟美艦未開炮云”①《日本李使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巳刻到,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27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7頁。。同樣的消息,他也傳遞給了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張之洞由美軍沒有率先開炮的行動敏銳地覺察到美國的特異性,給予重視,不僅特別致電駐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國政府轉達他的“感佩”之情,請美國在“東南互保”中發揮表率作用,而且聯合多位督撫建議清政府先托請美國進行調停②《致華盛頓伍欽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未刻發,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0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008頁。《張之洞致總署榮中堂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輯第15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632頁。。東南督撫們積幾十年中西交沖之閱歷,本有各自屬意的調停對象,大體說來李鴻章親俄、劉坤一親英、張之洞親日,美軍自外于大沽之戰的舉動則成為美國受到清朝督撫關注的重要轉捩點。
報章輿論亦紛紛報道大沽之戰細節:“近有西友述及大沽炮臺未占之先,美國水師提督某君與各西員會議,堅持不可轟擊炮臺,并云如果任情轟擊,則天津租界難望保全……及占臺時,美提督未與。”③《美員先見》,《申報》1900年7月12日,第1頁。將此視為“是天留此一線機緣,以為中外言和之地”,呼吁以李鴻章為首的碩望重臣出面,“必能聯合美國出作調人”④《論中外將有言和之機》,《申報》1900年7月18日,第1頁。。又有建議在聯絡美國調和的基礎上,再以英日助之,更有轉圜全局之希望⑤《救時策》,《申報》1900年7月26日,第1頁。。
得此中國朝野好感,美國政府開始扮演起既是作戰對手又是居間調和者的奇特角色。沙飛出發前,陸軍部和國務院頻密與其會商⑥American Millitary and Naval Activity, Mexican Herald, June 27,1900, p.1.。一方面,陸軍部不顧駐菲將領麥克阿瑟(MacArthur)對兵力缺乏的抱怨,執意從菲律賓抽調軍隊赴華——第九步兵團成為歷史上首批進入中國的美國陸軍;還命令沙飛抵華后盡速向北京進軍,展現出美國武力威懾和不愿落人口實的決心⑦MacArthur to Corbin, June 16, 1900,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ar with Spain: Including the Insurrection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nd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April 15, 1898 to July 30, 1902, vol.1, p.412.。另一方面,海約翰在與沙飛的密談中,認真部署了在華軍事和外交的配合事宜。國務院更利用一切照會、媒體報道等在世界范圍內營造中外并非處于戰爭狀態的景況⑧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Times, June 19, 1900, p.5.,為交涉保留了渠道。
清政府這邊,李鴻章在奉命北上后,就接連通過駐美公使伍廷芳和上海美領古納(Goodnow)向美國政府作說和求助。中國招商局也掛上美國徽章,以表對“美廷之力”的仰仗⑨《美愿居間》,《申報》1900年7月17日,第1頁。。雖然由于各國駐京公使對外聯絡受限等問題,美國的調停起初能夠發揮的空間很小,聯軍持續向北京推進。而當清廷明發上諭,允各公使明電通信本國(實則以密碼亦可行)⑩《上諭》,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421~422頁。,8月初中美合作設計了一條送使出京的言和路線。伍廷芳與美國代理國務卿艾迪(Alvey A.Adee)商議,似乎可以由聯軍派一部分軍隊進京護送公使離開。此舉全靠駐華美軍執行。陸軍部向沙飛將軍發出命令,要求美軍同清廷配合,進入北京護送外國公使至天津,并稱美國政府正在牽頭同其他列強促成此事?Cobin to Fowler, through Fowler, August 12, 1900,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Cablegrams Received, July 1900~Mar.1901,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在國務院說服了各列強駐美公使后?《全權大臣李鴻章請代奏致軍機處總署電》,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辰刻,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6冊,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 180頁。Mr.Adee to Mr.de Wollant, August 13,1900, Records of Diplomatic Posts: Legation Archives (No.0217), RG84,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陸軍部再訓令沙飛,如果中方傳達出愿意將各國駐京公使和僑民交接給救援軍,授權沙飛毋庸請示,即與其他指揮官一道實施這項部署①Cobin to Chaffee, through Fowler, August 14, 1900,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Cablegrams Received, July 1900~Mar.1901,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當天艾迪告訴康格,美國政府已經接受中方提出的護送公使出京的請求②Mr.Adee to Mr.Conger, August 14,1900,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160.。李鴻章同時也上奏朝廷:“美愿與各國會商停戰之約,但須準各國酌撥援師進京,將公使及一切等救護到津。”③《全權大臣李鴻章請代奏電》,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6冊,第145頁。美國設想之外交、軍事配合的場景本有希望實現,只是他們高估了命令傳送給美軍指揮官的速度。由于京津之間電線中斷,美國陸軍部的命令都是發電報給駐煙臺領事法勒(John Fowler),再由法勒派人由陸路送至行軍途中的沙飛手里,這樣一耽擱,沙飛收到命令的前一天,八國聯軍就已攻陷了北京。
結 論
自踏上中國土地,遠道而來的美國人就非常注意在華樹立有別于其他列強的獨立形象。他們目睹了英國人的蠻橫跋扈,迅速摸索出一條自我約束、塑造親善形象的交往之道,長期的對華外交實踐基本上是在不動武、不結盟的道德語境下展開的。在此基礎上,1899年的“門戶開放”政策更進一步增加了不“瓜分”中國的內容。此種策略固然源于當時美國在華實力弱小的權宜之計,但就實際效果而言,18、19世紀美國確實因其柔軟身段而在中美關系中獲得了遠比付出來得豐厚的回報。
故而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之初,美國政府陷入了某種程度的政策兩難:一面是要避免卷入列強內斗糾紛的既定政策、尚未破壞的對華友好關系,以及不愿扮演的“侵略者”角色;而另一面既有要營救在華美國公民的所謂責任、利益與榮譽,還有要同其他列強并肩而立的國際形象。它給美軍指揮官坎卜夫最初的訓令就是既要維護美國在華利益,又要謹防對華動武、與列強結盟。而隨著中國情勢的愈發危急,這兩個目標愈發無法調和,終于在康格失聯、大沽開戰后爆發,麥金萊總統及其領導的軍事、外交部門一致果斷拋棄了道德傳統,斥責坎卜夫在及時參戰上的無能,特別是他對“莫諾卡西”號遇襲的錯誤應對,使美國幾乎喪失了對華開戰、加入聯軍的絕佳借口。
這一選擇揭示出,在美國對華交往的道德面紗之下,隱藏的始終是非道德的利益考量與權力角逐。在中美關系的早期歷史上,美國的道德理想與逐利現實絕大多數時候是能較好融合的。美國一直注意在對華政策中恪守一定的所謂道德準則,并切實在這種靈活政策中兩邊討巧,獲得不少益處。有關中美“特殊關系”的神話代代傳說著美國人扮演的仁慈角色④[美]韓德著,項立嶺、林勇軍譯:《一種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國與中國》,第2頁。。但1900年美國侵華的決心和大肆增兵,無情地揭橥出它在道德之名下的利益訴求。同兩年前的美西戰爭一樣,美國再次將其日益壯大的軍事力量和野心展現在世界面前。在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轉變的全球浪潮中,美國的擴張主義不僅表現在美西戰爭,也表現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從越過不會軍事侵略紅線的那一刻起,無論它自身是否承認,美國無疑已經具備了“帝國主義”特征⑤雖然美國反感并極力避免被稱作帝國主義,但歷史學家仍舊不留情面地指出它的帝國主義行徑和特征。他們稱,“帝國一直以來就是一種美國的謀生之道”,“合眾國早就是一個帝國,但并不以帝國之方式而存在,是一個不像帝國的帝國”,等。參見 William A.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Cleveland: World Pub.Co., 1959, pp.47-48.Thomas J.McCormick, China Market: 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 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7, pp.2-4.Gareth Stedman-Jones, “The History of U.S.Imperialism,” in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p.207-237。。
就在美軍極力向西方世界展示其在聯軍中“良好”表現的同時,不開炮行動在中外輿論場造成的反響也開始逐漸發酵,“道德主義”與“帝國主義”碰撞結合出全新形式的“道德帝國主義”(Moral Imperial‐ism)。在殖民侵略史上,歐洲列強擅長使用“情感帝國主義”(Sentimental Imperialism)以受害者自居為其侵略正名。八國聯軍集體侵華,英德等國制造受到義和團傷害的國際輿論,以受傷和復仇為其發動合法/正義戰爭(just war)的邏輯關鍵①德皇威廉二世宣稱:“我們的軍隊要為德國的公使報仇。必須把北京夷為平地。”參見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12頁。。美國則更愿意使用道德作為武器。同樣陳兵中國,美國在庚子之役中并未過分強調其受害者的心態,反而始終不愿放棄其道義的制高點,刻意與歐洲保持距離,維護自身政策的獨立性。但它所謂的道德準則并未能阻止其侵略行徑,在確實需要處美國可以將不動武拋棄,卻又同時宣稱中美并未處于戰爭狀態,繼續裝扮對華友好。它將聯軍的入侵強行解釋成只是在清政府無力壓制國內叛亂的時候,由列強代為鎮壓。就是這一美國自身都并不完全相信的假說(第二次門戶開放照會就只承認南方政權),既“道德綁架”了中國,也“道德綁架”了列強。各國被迫承認戰爭狀態并不存在②參見[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3卷,第245—246頁。此種中外共識不僅為聯軍侵華同時留下交涉調停的管道,也到最后的《辛丑條約》議結中體現在簽署文件并非結束戰爭狀態的一般“和約”(Treaty),而是“最終議定書”(Protocol)。參見戴海斌:《〈辛丑條約〉談判前后的中方“全權”問題》,《歷史研究》2018年第4期。,清政府寄希望于美國能夠調和中外矛盾。結果是,美國既參加了侵略行動,又在這次中外危機中巧妙地施予了它的道德影響(moral influence)③當時美國政府和各界輿論對美國的道德優勢是有清醒認識的,并且是主動且有意地在施加道德影響。參見A shot through the Bows, Boston Herald, June 22, 1900, p.2。,通過進軍和調停并行的吊詭操作,獲得了中國朝野的一定青睞和重視,從而再次根本維護了其在華利益,實現了“門戶開放”的初步目標。
經此一役,美國逐漸意識到,日益膨脹和堅定的擴張主義同其對華交往中的所謂道德傳統存在一定的捍格。但它始終不愿放棄多年來對“無恥”的歐洲與“道德”的美國的形象構建,從而誕生了“道德帝國主義”④對于是否要放棄道德傳統,美國國內一直存在爭議,到20世紀中葉喬治·凱南還在呼吁美國要將本民族利益置于那些為了迎合浮夸政治氣質的道德之上。參見[美]喬治·F·凱南著,柴金如等譯:《當前美國對外政策的現實:危險的陰云》,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28頁。。此后美國雖沒有再發動殖民戰爭,但美國的擴張主義/帝國主義仍舊在羅斯福和塔夫脫階段的對華交往中得到很好體現,“大棒加胡蘿卜”和“金元外交”難道不是“道德帝國主義”的另一種體現?
就中國而言,能從美軍在大沽未開炮一事,敏銳覺察到八國聯軍乃一松散的軍事聯盟以及美國的“特殊性”,并試圖利用之,清朝官員們的努力值得被看到。但從歷史結果來看,不論是“情感帝國主義”,還是“道德帝國主義”,都只是以情感或道德之名而行侵略之實罷了,列強多樣化的對華政策本質上是多樣地侵犯和攫取中國的利益,在被侵略國利益喪失的過程中,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具有欺騙性和隱蔽性。清政府的聯美構想終究是充滿悲情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