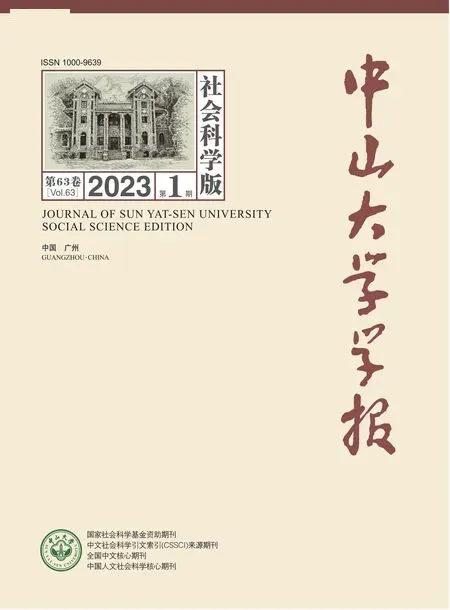曹植《髑髏說》及其生死觀 *
孫明君
曹植《髑髏說》曰:
曹子游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于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嘆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托夢以通情。
于是伻若有來,怳若有存,景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于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于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于纖微之域,通于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逾。
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于是髑髏長呻,廓然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子則行矣!予將歸于太虛。于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命旋軫,乃命仆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①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524—525頁。
此文寫曹子游于原野之時,偶然發現一具髑髏,伏軾問他因何而死。髑髏聽后認為曹子未達幽冥之情、未識死生之說。曹子表示可以懇請“上帝”恢復髑髏之形體,而髑髏則予以拒絕。與張衡的《髑髏賦》相似,本文也是一篇對《莊子·至樂》的模仿之作,其中又有“慕嚴周之適楚”以及關于“道”的討論,故與莊子思想關系密切。關于曹植《髑髏說》的寫作年代及其與《莊子·至樂》和張衡《髑髏賦》之間的關系、《髑髏說》的旨意等問題,前人已有相關論析①關于《髑髏說》的寫作年代,參見林童照:《曹植〈髑髏說〉之創作時間考辨》,《中國石油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關于《髑髏說》與《莊子·至樂》和張衡《髑髏賦》之間的關系,參見宋園園:《漢魏髑髏賦所反映的士人心態》,《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關于《髑髏說》的旨意,參見徐公持:《曹植年譜考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416頁。。但是,關于此文蘊含的玄學生死觀及其思想史意義,學界尚缺乏系統論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認為:曹植《髑髏說》以《至樂》和張衡《髑髏賦》為藍本討論生死問題,并且提出了有關生死觀的新問題,從而促進了魏晉玄學家對生死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和討論。
一、《髑髏說》與《莊子·至樂》及張衡《髑髏賦》之異同
髑髏形象首次出現在《莊子·至樂》(以下簡稱《至樂》)中。東漢時張衡有《髑髏賦》,魏晉時曹植有《髑髏說》、李康有《髑髏賦》、呂安有《髑髏賦》等②鑒于李康賦僅剩殘句,呂安賦亦不完整,且此二賦完成于曹植之后,故此處僅對比討論《莊子·至樂》、張衡《髑髏賦》和曹植《髑髏說》三篇作品。。《至樂》、張衡《髑髏賦》與曹植《髑髏說》,在文體上一脈相承,在思想上都與莊子有直接聯系,值得我們進行比較。《至樂》曰: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丑,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③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617—619頁。
舊時學者爭論的焦點之一在于《至樂》是否為莊子自作,今日學界則認定該篇為莊子后學所作④參見黃克劍:《〈莊子·至樂〉髑髏寓言抉微》,《哲學動態》2015年第8期。。張衡《髑髏賦》曰:
張平子將游目于九野,觀化乎八方。星回日運,鳳舉龍驤。南游赤岸,北陟幽鄉。西經昧谷,東極扶桑。于是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回軒駕,左翔右昂。步馬于疇阜,逍遙乎陵岡。顧見髑髏,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負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曰:“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為是上智,為是下愚?為是女人,為是丈夫?”于是肅然有靈,但聞神響,不見其形。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游心方外,不能自修。壽命終極,來此玄幽。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于五岳,禱之于神祗。起子素骨,反子四肢;取耳北坎,求目南離;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五內皆還,六神盡復;子欲之不乎?”
髑髏曰:“公子之言殊難也。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榮位在身,不亦輕于塵毛?飛鋒曜景,秉尺持刀,巢許所恥,伯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遙。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劍戟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與元氣合其樸。以造化為父母,以天地為床褥。以雷電為鼓扇,以日月為燈燭。以云漢為川池,以星宿為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渾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于是言卒響絕,神光除滅。顧盼發軫,乃命仆夫,假之以縞巾,衾之以玄塵,為之傷涕,酬于路濱。⑤張衡著,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7—248頁。
在這三篇作品中,張衡《髑髏賦》模仿了《至樂》,曹植《髑髏說》又模仿了《至樂》和《髑髏賦》。三篇作品的結構頗為相似。開端部分寫作者游于某地,于道旁發現了一具髑髏,正文部分寫作者與髑髏之間的兩次對話。作者先問髑髏因何種原因而喪命,待髑髏回答之后,作者表示自己可以幫助髑髏重回塵世,問他是否愿意。髑髏認為自己死后已經到了一個與道逍遙的世界,對作者的提議予以回絕。張衡《髑髏賦》和曹植《髑髏說》又多出一個結尾部分:在酬髑髏于路濱之后,作者離開此地。
此三篇作品皆意在表現作者對生死問題的思考,三位作者的思考同中有異。在郭象之前,已流行這樣一種觀點:《至樂》髑髏寓言意在宣揚“樂死惡生”思想。持這種觀點者代不乏人,至今未絕。其實,“樂死惡生”只是髑髏寓言的表層意思,并不能直接把它等于莊子思想。郭象注曰:“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①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19,229、242頁。《至樂》篇意在表現至樂無為的思想,文中的“樂死惡生”實質上是樂無為而惡有為。莊子的生死觀集中體現在《莊子》內篇中,《大宗師》曰:“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②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19,229、242頁。按照莊子的生死觀,生時不喜不懼,死時不樂不拒。不論是“樂死惡生”還是樂生惡死都不符合莊子本意。后世一些讀者并沒有嚴格辨析髑髏寓言與莊子思想之間的關系,簡單地視“樂死惡生”為莊子的主張。
張衡《髑髏賦》寫張平子路遇一髑髏,與之對話后得知原來是哲人莊周。兩漢時代,莊子思想的影響相對沉寂。張衡深受《莊子》影響,寫出了摹仿髑髏寓言的賦作。在《髑髏賦》中,張衡觸及了東漢社會的主要問題③宗明華:《張衡〈髑髏賦〉解析——莊子對漢魏抒情賦的影響》,《煙臺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與《至樂》篇髑髏寓言直陳“樂死惡生”不同,此賦中髑髏自云“游心方外,不能自修”,“死為休息,生為役勞”,“與道逍遙”,“與陰陽同其流,與元氣合其樸”,“合體自然,無情無欲”。張衡放棄了《至樂》髑髏寓言中“樂死惡生”的表層意思,進一步回歸莊子思想,準確地再現了莊子的生死觀。在結尾部分,作者“乃命仆夫,假之以縞巾,衾之以玄塵,為之傷涕,酬于路濱”,體現了張衡對哲人莊子的敬重。到了漢末魏晉,士人愈加發自內心地敬重莊子。湯用彤說:“溯自揚子云以后,漢代學士文人即間嘗企慕玄遠……則貴玄言,宗老氏,魏晉之時雖稱極盛,而于東漢亦已見其端矣。”④湯用彤:《魏晉玄學流別略論》,《魏晉玄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頁。此處的“宗老氏”也包括宗莊子在內。張衡可視為東漢一代貴玄言、宗老莊士人中的典型代表。
《髑髏說》在模擬古人的外表下,表現出曹植后期獨特的人生體驗和玄學生死觀。《髑髏說》中的主人公是曹子和髑髏,此髑髏雖非張衡《髑髏賦》中的莊子,然而髑髏所言所思,最為接近莊子思想。此髑髏能言而善辯,他批評曹子說“子則辯于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接著又宣講了自己對幽冥之情的理解和對生死世界的看法,儼然是一位漢魏之際的思想者。曹植《髑髏說》在玄學思想上的創新性主要體現在曹子與髑髏的對話之中(詳見下文),對話結束后,髑髏“言卒響絕,神光霧除”。此番對話并沒有徹底解決曹植心中的疑惑,在掩埋髑髏之后,他繼續沉浸在對生死問題的思考中。
《至樂》髑髏寓言意在表現莊子的無為思想,語言質樸自然;張衡《髑髏賦》回歸莊子生死觀,語言整飭,詞句駢儷,文人化色彩明顯;曹植《髑髏說》在繼承前人思想、藝術的基礎上又有思辨方面的創新,其義理具有時代特征,對魏晉玄學的萌發起到了先導作用。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曹植《髑髏說》與《至樂》、張衡《髑髏賦》之間具有一以貫之的道家思想淵源。
二、曹植接受道家思想的動態過程
曹植時代,民間道教已經盛行,佛教思想在社會上也產生了一定影響,綜合起來看,曹植終生沒有放棄儒家思想,他對道家及莊子思想的認識有一個動態的過程。為了更清楚地分析曹植對道家及莊子思想的接受,我們可以將他的一生分為四個時段:第一個時段為漢獻帝初平三年(192)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初平年間曹植還是一個幼童,是故將此時期稱為建安前期;第二個時段為建安二十二年(217)至二十五年(220),姑且稱之為建安后期;第三個時段為魏文帝黃初元年(220)至七年(226),稱之為黃初年間;第四個時段為黃初七年(226)至魏明帝太和六年(232),稱之為太和年間。
青少年時代的曹植以儒家思想為主,同時也受到了一些社會上流行的道家縱情任性思潮的侵蝕。他雖然服膺儒家思想,但不愿成為一個故步自封、循規蹈矩的“世儒”。曹植《贈丁翼》云:“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愿為世儒!”①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141,1,484—485,49,187—188,396頁。一方面他看不起那些固守書齋、一事無成的兩漢儒生,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沾染了漢魏之際的疏放任誕習氣。建安九年(204)曹操奪取鄴城之后,把家眷安置在此,鄴城成為曹操集團的大本營,此后曹植兄弟在這里過起了相對穩定的生活。《斗雞》詩云:“游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斗雞觀閑房。”②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141,1,484—485,49,187—188,396頁。《名都篇》云:“斗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云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③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141,1,484—485,49,187—188,396頁。《公宴》詩云:“神飚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飖放志意,千秋長若斯!”④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141,1,484—485,49,187—188,396頁。這種騎射之妙、游騁之樂正是曹植兄弟鄴下日常生活的寫照。正是這樣的生活給謝靈運造成了“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的印象。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平原侯植》云:“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游匪晝夜,豈云晚與早。眾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回鵠,余哇徹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⑤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頁。李白《將進酒》云:“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這種重視當下享樂的思潮發端于東漢后期,經過建安時代曹植等人的推波助瀾,對魏晉士人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舉止疏放、率直任誕之風并非莊子思想,它與《列子·楊朱》中的享樂主義思想如出一轍。雖然《列子·楊朱》的成書年代尚有爭議,但據《古詩十九首》中的“驅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等詩篇可知,及時行樂的思潮在東漢時期已經廣為盛行。
建安后期,曹植競爭太子失敗之后,在政治宣傳方面緊跟父王曹操的步伐,有時幾乎亦步亦趨。據《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曹植因為“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⑥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57,561頁。而失去父王寵愛。曹植此期不敢表現出獨立的思想和個性,一切唯父王馬首是瞻,著名的《辨道論》正是配合曹操政策的產物。此時雖然道教還未成熟,但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久已在民間流行。如果統治者不能妥善處理,就會威脅到政權的穩定。曹植《辨道論》曰:“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下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于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于云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⑦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141,1,484—485,49,187—188,396頁。湯用彤說:“曹魏之時,魏文帝之《典論·論文》、陳思王之《辨道論》亦皆反對方術,亦與當時政治有關。”⑧湯用彤:《貴無之學(下)——道安和張湛》,《魏晉玄學論稿》,第155頁。《辨道論》是對曹操政策的積極辯護和有力宣傳,是曹植表明自己“政治正確”的重要舉措⑨吳懷東:《論曹植〈辨道論〉的思想立場與現實指向》,《社會科學戰線》2021年第6期。。在癘氣流行、民心惶恐之際,曹植此論亦具有安撫民眾和穩定人心的政治功效。
曹操晚年熱衷于寫作游仙詩,并非完全是迷信神仙方術,其中也有一定的享樂主義成分。曹植此期寫作的游仙詩,如《五游詠》《游仙詩》《升天行》等,與黃初、太和年間的游仙之作有一定的區別。徐公持評《五游詠》說:“本篇亦寫現實生活之不能得意,故云‘九州不足步’也。然而篇中苦悶心情不明顯,更無憂生之嗟,與曹植太和年間所撰諸游仙作品如《仙人篇》《游仙》等有微妙差異。”⑩徐公持:《曹植年譜考證》,第246頁。曹丕立為太子后,曹植在精神上初受打擊,但還沒有黃初年間的那種性命之憂。到了黃初年間,面對曹丕及其爪牙的迫害,曹植開始重新認識道家和道教,時常用神仙道教思想來麻醉自己。據《三國志》本傳:“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57,561頁。傳言為曹植所作的《釋疑論》曰:“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141,1,484—485,49,187—188,396頁。他對道教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轉,難怪有學者懷疑此文非曹植所作。《贈白馬王彪》其七云:“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①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00,263,6—7,28—29,241、245,242,471,399,316頁。學者多據此認定曹植后期并不信天命,沒有沉溺于神仙道教。但我們換個角度看,“松子久吾欺”說明曹植后期久久沉溺在神仙學說中無力自拔。《莊子》書中有許多神人真人的描繪,他們對后世那些喜好游仙詩創作的詩人無疑有重要影響。此期曹植的游仙詩也受到莊子影響,其《仙人篇》云:“萬里不足步,輕舉陵太虛。飛騰逾景云,高風吹我軀。回駕觀紫薇,與帝合靈符。閶闔正嵯峨,雙闕萬丈余。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游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②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00,263,6—7,28—29,241、245,242,471,399,316頁。仙人自由而快意,與俗間形成鮮明對照。詩人之所以大量寫作游仙詩,就是因為在現實中太壓抑太苦悶,因而試圖借助仙境來消解痛苦,讓重壓下的靈魂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曹植集中多篇文章都涉及老莊和生死問題,但他前期和后期對老莊的理解迥然不同。前期作品可以《七啟》和《玄暢賦》為例,《七啟》曰:“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托喻,寧掉尾于涂中。”③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00,263,6—7,28—29,241、245,242,471,399,316頁。據《七啟序》中“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可知,《七啟》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王粲去世之前。趙幼文說:“曹操消滅袁紹,統治冀州,復取荊州。為了進一步發展統一事業,必需爭取士族與之合作……故疑此文作于《求賢令》之后,即建安十五年左右。”④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00,263,6—7,28—29,241、245,242,471,399,316頁。此處對于“道”的解釋,對于“老莊”“遺風”的仰慕是一種遠觀,不具有后期的切膚之痛。《玄暢賦·序》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此賦的寫作年代有兩種看法,趙幼文認為此賦似寫作于黃初二年⑤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00,263,6—7,28—29,241、245,242,471,399,316頁。,徐公持認為:“此是建安年間所撰無疑,后期的曹植不可能呼朋引類作如此貴游。”⑥徐公持:《曹植年譜考證》,第222頁。比較二說,后者更為恰切。《玄暢賦》也涉及了《莊子》,文曰:“希鵬舉以搏天,蹶青云而奮羽。”⑦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00,263,6—7,28—29,241、245,242,471,399,316頁。此處的“孔老異情”與“楊墨殊義”并列,并沒有多少深意。他對《莊子·逍遙游》的引用,突出的是鯤鵬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隨著曹叡繼位,曹植一度以為自己時來運轉,他把自己想象成輔佐成王的周公,燃起了投身政治、成就事業的希望。隨著曹叡對他一次次冷漠地拒絕,曹植終于陷入悵然絕望之中。到了曹叡時代,在殘酷的社會現實中,曹植逐步親近老莊,真正接受了莊子思想。《三國志》本傳曰:“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⑧陳壽:《三國志》,第565、576頁。正如《秋思賦》曰:“居一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⑨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00,263,6—7,28—29,241、245,242,471,399,316頁。曹植認識到人生短促,神仙遙不可及。《桂之樹行》云:“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澹泊、無為、自然。”⑩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00,263,6—7,28—29,241、245,242,471,399,316頁。桂之樹下是得道仙人聚會的場所,真人把“要道”歸結為“澹泊、無為、自然”,正是老子哲學的核心思想。其《苦思行》云:“綠蘿緣玉樹,光耀燦相輝。下有兩真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踴躍!思欲攀云追。郁郁西岳巔,石室青青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須發皆皓然,策杖從我游,教我要忘言。”?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00,263,6—7,28—29,241、245,242,471,399,316頁。詩人欲追隨真人而去,真人卻已飛逝,自己依然站在地面。須發皓然的隱士是曹植可以從游的智者,他教導曹植要做到“忘言”。
關于《髑髏說》的創作時期,迄今并沒有定論。以曹丕繼位為界,有前期說,有后期說,也有時期未定說。由于沒有出土文獻等史料方面的鐵證,學者們只能根據自己對文本的理解進行推斷。主張寫作于前期的主要有熊禮匯和林童照,林童照說:“前期:熊禮匯先生主此說。然熊先生并未提出論據。”“這種強調人世歡樂的傾向,以曹植后期困頓抑郁之精神生活而言,自然是難以出現的,因此‘生之歡樂不下于超越性世界’的觀點,只能出現于其前期生活中。”?林童照:《曹植〈髑髏說〉之創作時間考辨》,《中國石油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林說雖然可成一家之言,但畢竟是一種“推估”,并沒有提出富有說服力的論據,且對“死生之必均”一句的理解還有可商榷之處。
在曹植集中,《釋愁文》與《髑髏說》的思想傾向最為接近。徐公持將《髑髏說》《釋愁文》的創作時間均放在太和年間。《釋愁文》曰:“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澹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炙子以淳樸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游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青云以翱翔。”①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468,177頁。徐公持論《釋愁文》說:“本篇說主人之愁及其開釋之方。觀其自述‘愁’之狀況,則頗為嚴重……是當在曹植后期遭遇也。”又論《髑髏說》曰:“本篇寫‘曹子游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頗有落魄之態,是曹植后期之形容也……終究是人生無常滄桑之感甚為濃厚,其境界與以上《釋愁文》接近,當是曹植后期思想反映。”②徐公持:《曹植年譜考證》,第 415、416 頁。
結合前人的討論,本文推斷《髑髏說》撰寫于太和六年(232)曹植對政治“悵然絕望”之后。《三國志》本傳曰:“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又曰:“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③陳壽:《三國志》,第 576 頁。這里的“悵然絕望”與“喟然有終焉之心”在同一時期。據《魏志·明帝紀》,太和六年(232)二月曹植由東阿王徙封陳王,《髑髏說》中的死亡觀與曹植生命終結之前的思想狀態最為接近。《髑髏說》的出現標志著曹植的死亡觀從絢爛至極歸于平淡,象征著曹植關于生命的思考走到了終點。
張衡《髑髏賦》以“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其中并不包含佛教觀念。那么,曹植《髑髏說》是否具有佛教思想呢?劉敬叔《異苑》卷5:“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里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衿祗敬,便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游山,忽聞空里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④劉敬叔:《異苑》,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8頁。此外后世尚有多種同類記載。佛教徒通常用前條材料來證明曹植與佛教之間的關系,但“道士效之”證明道教徒也不甘落后,他們認定曹植更加親附于道教。這類材料充分說明因為曹植的貴族聲望、詩壇地位及玄學造詣,佛道兩家都想與他攀上關系。但在其《髑髏說》中尚難發現佛教思想因子。
需要補充的是,生死問題是自有人類以來就糾結、焦慮的問題,東漢末年的戰亂以及疫病的流行導致了民眾大面積非正常死亡,更加刺激了時人對死亡的敏感,死亡主題遂成為漢魏之際文學的普遍主題之一。曹植逐步關注道家并日漸親近莊子思想,除了自身的遭遇之外,也與漢末戰亂和疫情盛行的社會環境有關。關于戰爭之殘酷,曹操《蒿里》云:“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⑤曹操:《曹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頁。關于疫情的流行,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⑥張仲景著,劉藹韻譯注:《金匱要略譯注·傷寒雜病論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頁。其中建安二十二年(217)的疾疫尤為恐怖。曹丕《又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⑦曹丕著,魏宏燦校注:《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8頁。曹植《說疫氣》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⑧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468,177頁。長年的戰亂,再加上流行不已的疫情,促使曹植對生命的價值進行深入思考。
三、《髑髏說》的生死觀
在解析《髑髏說》中的生死觀之前,有必要先回答這樣一種質疑:為什么要把曹植《髑髏說》中的生死觀歸結于玄學思想?曹植與玄學思想有何關系?學界習慣于把魏晉時代祖述老莊的玄遠之學稱為“玄學”,而其中的生死觀是魏晉玄學的重要主題。曹植作為魏晉時代的名士,其《髑髏說》意在討論生死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不難看到莊子思想對他的深刻影響,是故從宏觀角度看,曹植《髑髏說》之生死觀也屬于魏晉玄學思想范疇之內。正始玄學領袖以何晏和王弼為代表,其中何晏(190—249)比曹植(192—232)年長兩歲,又比曹植晚去世17年。到了正始元年(240),曹植已經去世8年了,從嚴格意義上不能說曹植受到正始玄學的影響,但是反過來說則沒有問題:曹植及其作品有可能會影響到正始玄學的形成。曹植和何晏一度共同生活在曹魏后宮中,《三國志·魏志·何晏》裴松之注引晉魚豢《魏略》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為‘假子’。”①陳壽:《三國志》,第292,576頁。建安時期,曹丕不僅不喜歡對他構成威脅的弟弟曹植,同時也不喜歡作為假子的何晏。雖然沒有兩人直接交往的材料,但按照常理推斷,對于曹植的思想和遭遇,何晏一定會給予特別關注。《三國志》曹植傳曰:“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秘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后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副藏內外。’”②陳壽:《三國志》,第292,576頁。景初年間(237—239)曹植的作品已經公開流傳,何晏等人自然會給予必要的關注。
死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也是哲學關注的焦點問題,先秦時代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該問題。到了魏晉時期,士人們更加重視死亡問題。湯用彤說:“所謂魏晉思想乃玄學思想,即老莊思想之新發展。玄學因于三國,兩晉時創新光大,而常謂為魏晉思想,然其精神實下及南北朝(特別南朝)。其所具之特有思想與前之兩漢、后之隋唐,均有若干差異。”③湯用彤:《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魏晉玄學論稿》,第194頁。魏晉玄學以生死問題作為基本主題,然而,在魏晉玄學的研究中,學人們常常會忽略生死問題。杜維明說:“魏晉是大一統政局業已崩潰的衰亂時代,漢代名物訓詁的學風與忠義氣節的士風都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對‘宇宙之終始,人生之究竟,死生之意義,人我之關系,心物之離合,哀樂之情感’等存在課題的深思熟慮。”④[美]杜維明:《魏晉玄學中的體驗思想——試論王弼“圣人體無”觀念的哲學意義》,《燕園論學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198頁。這里的人生之究竟、死生之意義、心物之離合、哀樂之情感等都與生死問題關系密切。王中江說:“在已有的研究中,玄學的基本問題大都與‘有無’‘自然名教’和‘言意’這三對概念聯系在一起,并且有各種各樣的大量論述,而整體上能作為玄學主題之一的生死問題,既沒有被凸顯出來,也缺乏系統的考察。”又說:“玄學生死觀包含有豐富的內容,如果把它放在中國哲學生死觀的整個發展的歷程中來看,可以說它是中國哲學生死探求的又一次高潮,并能充分體現出中國哲學中的生死智慧。”⑤王中江:《玄學生死觀的理路及其主導觀念》,《中國哲學史》1997年第1期。在對魏晉士人生死觀的探索中,曹植是一個不應被忽略的歷史人物。
與張衡關注社會現實不同,曹植關注的目光離開了個人與國家的關系。《髑髏說》曰:“(曹子)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殉國君”“斃三軍”正是曹植后期的心愿。曹植的政治熱情體現在《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陳審舉表》《諫取諸國士息表》《諫伐遼東表》《請招降江東表》等奏表之中,曹叡《答東阿王論邊事詔》曰:“制詔。覽省來書,至于再三。”徐公持說:“嚴可均曰:‘當在太和三年’,故系于是。由此詔文可知,曹植入太和后不斷上書明帝言事,‘至于再三’;而所言內容,由此答詔亦可大體得知,涉及‘海內’形勢、‘邊將’用人等問題,要皆當時重大政治事務。”⑥徐公持:《曹植年譜考證》,第369頁。然而,作為皇帝的曹叡并不需要一個熱衷國是、積極議政的皇叔。曹植所抱的希望越大,他的失望也就會越大。
隨著曹植對社會的悵然絕望,其關注點轉向內心世界,從而表現出對老莊思想的無限向往,《髑髏說》的出現標志著曹植與莊子思想的匯合。《髑髏說》曰:“叩遺骸而嘆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托夢以通情……顧命旋軫,乃命仆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明知此髑髏并不是莊子,但面對一個具有與莊子思想相似的髑髏,曹子亦對它表現得極為恭敬。作于同一時期的《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玄靈)先生作色而言曰:‘……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澹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炙子以淳樸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游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①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467—468,382—383頁。無為、澹泊、玄虛、淳樸是道家思想的靈丹妙藥,曹植認識到只有老莊思想才能夠消解自己內心的愁苦。
在認識到生的有限性之后,如何度過有限的人生,人如何看待生與死,成為士人思考的重點。在建安前期,曹植追求當下的快樂生活;黃初年間,曹植幻想成為仙人的可能性;到了太和后期的曹植,不得不面對生死之變。《髑髏說》中借髑髏之口曰:“子則辯于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于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于纖微之域,通于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逾。”髑髏又說:“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子則行矣!予將歸于太虛。”已經“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的曹植,繼承和發展了莊子的自然無為思想。與《至樂》中的髑髏寓言以死為南面王之樂不同,張衡《髑髏賦》的“與道逍遙”和曹植《髑髏說》的“與道相拘”更接近莊子思想。張衡《髑髏賦》中的髑髏列舉了世間的“榮位”,涉及到“堯舜”“桀紂”等歷史人物,涉及“天地”“雷電”“日月”“云漢”“星宿”等自然物象,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更為緊密;曹植《髑髏說》在抽象思辨方面則更勝一籌,他延續了古人“死者歸也”的哲學命題,進而明確說“歸也者,歸于道也”,直接把死亡與大道聯系起來。生存者勞之以形,苦之以生,死后“偃然長寢,樂莫是逾”,此處所述的死亡之快樂并不是《至樂》中南面王一般的快樂,而是生命與大道融為一體的大樂,此時的曹植思想達到了“反吾真也”之境界。《莊子·漁父》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于俗,故不足。”②郭慶藩:《莊子集釋》,第 1032頁。《髑髏說》中這一段論述具有形而上學的思辨特征,曹植在漢魏之際對生命價值的重新思考,對生死問題的反思,具有一定的理論深度和時代特征,對他身后的魏晉玄學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曹植生死觀與莊子思想同中有異,二者的相同之處在于強烈關注死亡問題,故前文曰《髑髏說》最為接近莊子思想。兩者之間也有細微的區別:莊子生死觀主張生死齊一,曹植生死觀則重死而輕生。曹植之所以會輕視生存,是因為生存留給他的是無盡的痛苦。《髑髏說》表現了太和時期曹植的真實處境和心態,其文曰:“曹子游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叩遺骸而嘆息,哀白骨之無靈。”形影相吊、寂寥落魄的曹植,在路邊發現了塊然獨居的髑髏,與他展開了靈魂對話,將他引為知己。《髑髏說》曰:“髑髏長呻,廓然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子則行矣!予將歸于太虛。”髑髏用“勞我以形。苦我以生”八個字總結自己的一生。曹植《吁嗟篇》云:“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云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飚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若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飖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愿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愿與株荄連。”③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467—468,382—383頁。此時的曹植知道自己即將到達生命的終點,再也不會抱有飛升“天路”的幻想。
在魏晉玄學中,老莊思想固然重要,但玄學并沒有離開儒家思想。余英時說:“魏晉士風的演變,用傳統的史學名詞說,是環繞著名教與自然的問題而進行的。在思想史上,這是儒家和道家互相激蕩的一段過程。老莊重自然對當時的個體解放有推波助瀾之力,周禮重名教,其功效在維持群體的秩序。”①[美]余英時:《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7—358頁。換一個角度看,魏晉玄學想解決的主要問題正是儒家思想如何與道家思想互相融合成為一個整體。曹植《髑髏說》中儒道并重的思考理路,開啟了魏晉玄學家討論名教與自然問題之先河,不妨看作是魏晉玄學產生的序曲。貫通地來看,曹植思想具有儒道互補的特征,前期以儒家思想為主,后期道家思想逐步占有重要位置,但他始終沒有放棄過儒家思想。
《髑髏說》的結尾說:“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這數句是《至樂》和張衡《髑髏賦》中所沒有的內容,也正是曹植文章中的閃光點。與其說它是對莊子思想的懷疑和否定,不如說是曹植在惶恐于儒道思想之間時提出的人生疑問。文中的“曹子”是曹植,“髑髏”也是曹植。太和年間在曹植心中有兩種聲音,一種是莊子的齊同生死,一種是孔子的重生輕死。曹植生于亂世,長于軍旅,從小目睹了父親的英雄行為,形成了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白馬篇》中“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豪言壯語,正是少年曹植英雄氣概的反映。清人朱乾《樂府正義》卷12曰:“篇中所云‘捐軀赴難,視死如歸’,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②劉曉亮:《八代詩匯評》,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89頁。這樣的政治情感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晚年。曹植《鰕?篇》云:“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③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81,65頁。《雜詩》云:“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閑。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④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81,65頁。平治天下、建功立業是建安士人的共同心聲,不論是黃初年間身處危難之中,還是在太和年間成為圈養之物,曹植都沒有放棄過儒家思想。現實的處境讓他陷入巨大的思想矛盾當中,他的疑問是一個時代的巨大問號,這個問號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要說曹植《髑髏說》對魏晉玄學的啟發,主要就在這里。在他身后,魏晉名士接著曹植的疑問繼續探索名教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正始名士王弼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答案,竹林名士嵇康倡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向秀則踐行順名教而任自然的訓條。究竟是誰解決了這個時代的大問題?抑或這個問題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如果說魏晉玄學是中國哲學史上探究生死問題的又一次高潮,那么曹植《髑髏說》儒道并重的理路,發前人所未發,啟迪了后之來者。
綜上所述,東漢時,張衡等士人已經關注到莊子思想;漢魏之際,曹植進一步繼承并發揚了莊子思想。曹植《髑髏說》提出了“死者歸也”的哲學命題,同時也開始思考自然與名教的關系問題。曹植因為其獨特的身世遭遇和哲學悟性,儒道并重,奏響了魏晉玄學的序曲。他不僅是詩壇的建安之杰,同時也是魏晉玄學發展史上的先驅者之一。可惜曹植在魏晉玄學思想史上的貢獻為其詩名所掩,并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挖掘和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