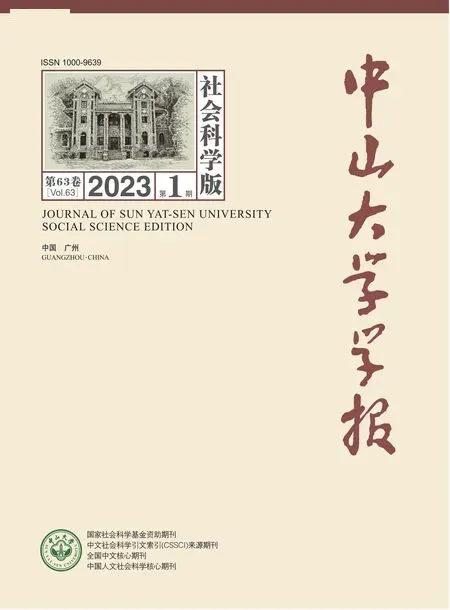論早期中國思想中的“物”概念 *
劉 偉
引言:百物與萬物
“物”在早期中國經典語境中有兩種頗為近似的用法,一為百物,一為萬物,皆可用以指稱物的復數形式。然深究二者之別,似又不止百與萬的程度不同而已,而是隱含著物概念的本質及其流變的關鍵消息。
說起“百物”,最為人熟知的用例在《論語》中。《陽貨》有云: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①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41頁。
孔子說,我不欲言說可以承傳的思想內容;子貢反問,如果您不言說,我們這些弟子傳述什么呢?于是,孔子說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言說,但不影響四時有序地運行,百物自發地生長。此處,孔子使用的是“百物”,而不是后世更習見的“萬物”。同樣的用例,也出現在《左傳·宣公三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②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02—603頁。
這同樣是一個讀者耳熟能詳的經典故事:相傳夏王朝建立時利用各地的貢金鑄造了九鼎,夏亡而入殷,殷亡而入周,是一組象征著王權合法統治的禮器,代代相承。楚子伐陸渾之戎,過成周而問九鼎之輕重,王孫滿答以“在德不在鼎”。依王孫滿的說法,夏王朝鑄九鼎之時,在鼎身上熔鑄了“百物”的圖像;這一行為似乎在神與人之間確立了一個和平相處的“約定”,由此,民眾進入川澤山林便不會遭遇“魑魅罔兩”,于是一個和諧而美好的秩序形成了。此處,作者使用的還是“百物”。又《周禮·大司徒》記載,大司徒有一項重要的職能是利用土圭測量日影,找準大地的中央,因為這個位置非常關鍵: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①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3頁。
大地之中是天地、四時、風雨、陰陽交會之處,在此建立王都,才能達成“百物阜安”的理想效果。此處,作者使用的仍然是“百物”。
說到“萬物”,最著名的用例非《老子》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莫屬。天地對萬物②王弼本《老子》作“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帛書甲乙本皆作“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朱謙之認為,“始”與“母”不同,又引《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為證,用以說明“天地”與“萬物”相對,王弼本更為合理。馬敘倫則引《史記·日者列傳》“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及王弼本人注云“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證明當作“無名萬物之始”。相較而言,作“無名萬物之始”似乎更合理。不過傳世本將“萬物”改為“天地”,也可以說明“天地”與“萬物”是一組常見的對子,影響頗為深遠。詳見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23頁。,是晚周諸子很流行的用法。使用“萬物”而非“百物”,不特老子為然,《孟子·盡心上》亦曰:“萬物皆備于我矣。”《荀子·禮論》則有云:
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③王天海:《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80頁。
荀子認為,人性就是質樸的材料,通過人為(偽)的加工,可以達到人所期待的“文理隆盛”。世間萬物的自然形態都是質樸而不合乎人之目的的材料,需要人工的介入;而萬物由天地而生,為人為加工提供了前在的基礎。天地對應萬物,依然是那個諸子常用的表述方式。
從上文征引的例子,大致可以獲得一個比較直觀的印象:前諸子文獻使用“百物”,而諸子文獻則使用“萬物”。這并不意味著在諸子時代,“百物”一詞徹底銷聲匿跡;不過,在前諸子時代,沒有“萬物”的用法,則是一個顯見的事實。這一現象,顯示了兩個概念有所不同,卻沒有道出更多實質性內容。問題仍是,“百物”和“萬物”有何區別?
一、萬物之“物”:可經驗的個體之物
晚周諸子中,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對萬物及其存在根據這一形而上學根本議題表現出了非同一般的興趣。萬物與其存在根據之關系,其實就是一和多的關系。其中,一又可以稱為道,多則代表萬物。而“萬物”的本質,就隱含在和“一”相對的雜多之中。關于“道”和“萬物”的關系,《老子》有云: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二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三十九章)④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17、105—106,117頁。
王弼說:“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于無也。”⑤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17、105—106,117頁。可見,王弼認為一就是道,而非從道派生出來的另一物事⑥蔣錫昌認為:“道始所生者一,一即道也。自其名而言之,謂之‘道’;自其數而言之,謂之‘一’。”詳見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30頁。。天地萬物獲得或分有了“一”而成為自身,這個“一”顯然是“道”的別稱。道生萬物,或者“萬物得一以生”,是一多關系的經典表述,但我們似乎無由獲得更多關于“萬物”或者“多”的實質性理解。在這一點上,《莊子·齊物論》提供了必要的線索: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①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66—70頁。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又是一組天地與萬物相對應的實例。莊子用“無物不然”說明萬物皆“固有所然”。其中“無物不”這一句型以否定的方式說明萬物包含所有的物,無物在萬物之外。具體而言,莛與楹或橫或縱,或小或大②《齊物論》郭象注云“莛橫而楹縱”,成玄英疏則認為:“莛,屋梁也。楹,舍柱也。”與司馬彪看法相同。俞樾則認為,莛為撞鐘之木,莛楹以小大言。諸家看法不一,然以莛楹為異類,則無不同。詳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1頁。,形制與功能迥然有異;貌丑之人和西施,同樣美惡有別。但在道的作用或觀照之下,則相通無二。莛、楹和厲,可以指稱同一類(事物),也可以指稱某一個(事物);而西施雖然可以借指所有美貌的女子,但終究為專名,特指一個叫作西施的美人。所以,當莊子說“物謂之而然”和“無物不然”時,其想象中的“物”是“每一個”具體有形之物。所謂“道通為一”,可以最直觀地理解為道將“每一個”物連接在一起,成為一個無分別的整體,就好像道路將大地上的每一個位置連接起來一樣。
莊子提醒我們,萬物為全體之物的總和,無有例外;而全體之物中的物,是以“每一個”的個體形式存在的。驗諸《老子》,今本第十六章有云: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③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35—36頁。
老子想象,萬物往復不已的死生輪回,有必然和恒常之道作用其間。如無盡的繁華最終將凝結為一粒種子,歸落于孕育其本根的大地中,開始下一個循環。圣哲觀察萬物的生生不已,體悟蘊于其中的恒常之道。“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并作”的蕓蕓萬物,“每一個”物最終都將回歸其本根,這是常道,也是宿命。“各復歸其根”,道出了“每一個”終將歸于自身之物的死生輪回。老子的箴言,不經意間表明了一個諸子的共識:萬物是“每一個”物的總和。《荀子·天論》對此說得更加直白: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④王天海:《荀子校釋》,第695,431,891—892,419頁。
如前所云,荀子認為萬物是人為加工的材質,故有“材萬物、養萬民”(《富國》)⑤王天海:《荀子校釋》,第695,431,891—892,419頁。的說法。所以,荀子的萬物似指所有有待加工的自然材質,而非世間所有存在物的總和,如“萬民”即不屬于萬物。“偏”意指部分,作為自然之物的萬物是整全之道的一部分,而“每一個”物(“一物”)都是萬物的一部分。可見,荀子同樣認可萬物是“每一個”物的總和,雖然這里的萬物指自然材質。
構成萬物的“每一個”物可以被經驗的前提,是作為個體的此物和它物有所區別,此物首先是一個邊界清晰、廣延明確的有形之物。有形的個體之物在天地間占據一個絕對屬己的空間,這一空間位置的排它性又反向證明了個體之物的同一性。《荀子·正名》說: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⑥王天海:《荀子校釋》,第695,431,891—892,419頁。
處于不同位置即便形狀完全一樣,也是兩個獨立的物體;同樣,連續處在同一位置即便形態前后不同——比如一株植物從青蔥到凋零——也屬于同一物體。故萬物之別首先表現為位置之別,占據不同位置的個體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天地間,此即荀子所謂“萬物同宇而異體”(《富國》)⑦王天海:《荀子校釋》,第695,431,891—892,419頁。。
在萬物的圖景中,世界表現為個體之物的總和。每一物都是不可化約的絕對存在,因此對個體之物的感知也必然作為原初經驗而成為認知的前提。諸子之學設定個體之物基于形體,形體的邊界規定了“每一個”物。由是,我們可以認真地打量眼前此物,動用全部感知能力,此物的大小、顏色、氣味、軟硬程度等屬性一一為人所知曉。正是這些屬性標識了此物,讓此物成為可經驗之物而被感知。所以,構成萬物的個體之物,并非自在自足之物,而是可以被經驗、被感知之物。“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莊子·達生》)①郭慶藩:《莊子集釋》,第 634 頁。,一切可以被人的感官覺知的對象都是物;反之亦然,構成萬物的所有個體之物,都是人感官覺知的對象。
二、形名:把捉個體之物的范疇
什么是物?這是形而上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其重要性在于,物關系著人們對于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理解,并決定了人們行為(處物)的基本方式。晚周諸子思想的諸多方面都建基于對物的理解之上,只是未通過專書或者專題文章的形式表達出來。這大概可以說明,物的問題并未成為一個有待論辯的顯題,可這并不妨礙存在一個關于物的觀念共識,來為各家思想言說提供基底,而還原這個基底,需要進行鉤稽索隱的工作。
“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一語,道出了晚周諸子對于物的基本理解。物是人感知的對象,或者更準確地說,“貌象聲色”是人感知的對象,物有“貌象聲色”但不是“貌象聲色”。物是什么呢?《墨子·經上》在劃分“名”的類型時曾言及物,對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或有幫助:
[經]名,達、類、私。
[說]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名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實也。②吳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479頁。按,標點有所改動。
作者將名區分為達名、類名和私名。所謂私名,即專有名詞,一個名稱只對應一個特定實體,比如美貌的西施,經說以人名“臧”為例說明之。所謂類名,指稱某一屬性相同或者相似的實體族類,比如莛和楹,而經說以馬為例,更直觀也更有代表性。所謂達名,指稱所有實體,經說舉例說物即達名。達,通達之義;經說所謂“有實”,即實存之事物。達名就是能夠通向所有實體的名。與之類似,《荀子·正名》的說法是:
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于無共,然后止。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于無別,然后止。③王天海:《荀子校釋》,第891頁。按,標點有所改動。
荀子所謂“大共名”,即《墨經》的“達名”;以鳥獸為例的“大別名”,即“類名”;將種類不斷細分,“至于無別然后止”,即表現為稱謂特定實體的“私名”。荀子所謂“萬物雖眾,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物”,是《墨經》“物,達也”最明白無誤的注解。作為概念的物是一個“大共名”,而這個“大共名”是在各級“別名”基礎上不斷“推而共之”的結果,直至無所不包。所以,“推而共之”的過程是一個概念之外延無限擴大,而內涵相應地無限稀薄的過程。最終,物作為一個“大共名”或“達名”,所指稱的含義是且僅是能夠被命名。
“貌象聲色”是人感知的對象,同時也是物向人顯現自身(“形”)的方式。而“物也者,大共名也”,則是基于人的感知進行命名(“名”)。說到底,晚周諸子對萬物的把握和界定,都是在形名這一范疇之下進行的。名是名稱、稱謂、符號,與之對應的則是實體、實物、實在。在現代語言學中,名稱是能指,實體是所指,二者的對應是隨機的、自由的。在古典語境中,則完全不同,名稱須揭示實體固有的屬性,故有“正名”或“循名責實”的說法。驗諸《老子》,今本第二十五章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④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62—63頁。
如上文所言,物是可以被命名者。此章老子討論道的性質和名稱,是以一種追問物的方式追問道。道不是物,但除此之外亦別無它法,故曰“有物混成”。“混”意味著并無清晰的“貌象聲色”可以如物一般進行把捉,所以,這只是一種不得已的言說方式。老子說,道這個東西,我并不知道它的“名”,如果勉強名之,則可以稱之為“大”。道這個語詞,并不是其名,而是字。二者之別在于,一個是形容詞,一個是名詞。作為形容道的名,大這個形容詞(勉強)揭示了道的屬性,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同樣,《老子》今本第十四章云: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①此文前三句帛書甲、乙本作“視之而弗見,名之曰微。聽之而弗聞,名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較之王弼本似乎更為合理。看不見的東西,其性質一般為微小;聽不見聲音,其性質一般為寧靜;捪為撫摸之義,撫摸而沒有阻礙,其性質為平滑。詳見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282—283頁。
微小、寂靜和平滑分別是視覺、聽覺和觸覺的感知效果,表征對象事物的屬性,老子認為它們屬于“名”。道不是物,當人們以物的方式去把捉道時,遭遇到的是“無物”而“不可名”。道無所呈現,不可狀象,老子稱之為“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所以人的感官無法覺知其屬性,也就無法找到一個對應其屬性的恰當稱謂(名)。
名是人賦予物的稱謂,而命名活動非隨意為這之,而是建立在對事物屬性的充分認知之上。人對事物屬性的認知基于感官知覺,而感官知覺的對象實際上是事物顯現(形)出來的“貌象聲色”(狀象)。一言以蔽之,萬物因形而有名,聯結形與名的是人的知覺。由此可知,形名是晚周諸子把捉個體之物的基本范疇,從這個意義上說,諸子之學皆可視為不同程度的形名之學。
名反映事物的屬性,相應地,也必然揭示事物自身的運行機制和操作原理。所以,命名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確立規范的過程。唯有圣人,才能恰如其分地為萬物命名,進而塑造整體秩序。《管子·心術上》云: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圣人。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②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764、771頁。
萬物皆“有形”,此形首先是作為視覺經驗對象的形體,又可進一步體現物的其它屬性,甚至是物之顯現本身。所有的物都向人顯現自身的狀象,而有狀象便有可以為人認知的屬性,于是可以根據事物屬性進行命名。只有圣人,能夠讓萬物之名都恰如其分。所以,形名關乎整體世界秩序,是將個體自然之物納入整體世界秩序的基本方式③《尹文子·大道上》有云:“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形名與整體秩序之關系,由此可見一斑。詳見厲時熙:《尹文子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頁。。
三、原物:前諸子時代的“物”概念
“萬物”在諸子文獻中是一個高頻詞匯,但在前諸子文獻中,卻并無一見。和“萬物”類似的表達是“百物”,曾出現于《論語》《左傳》《周禮》,這一點前文已有所論。什么是“百物”?“百物”和“萬物”有什么區別?類似問題非特經典本身并無明言,即使后世注解似也未曾有所分疏。現拈出這一問題,非欲故作驚人之語,而是“百物”一詞確實蘊含著追問古典“物”概念的重要線索①本文所謂“古典‘物’概念”,特指前諸子文獻中廣泛使用的、體現時人一般觀念的“物”的用法。而諸子以降對于“物”的理解,或為前文所論的萬物,或為鄭玄、朱熹所謂的“事”。后世學者對此多有不滿,相應地,關于“物”之古典義或者源始義的討論層出不窮。概而言之,大致可分為四類:其一,從《說文》出發,結合傳世文獻或出土文獻,修正《說文》取義“牽牛”之說,將“物”理解為“雜色牛”,或進一步引申為形貌色彩,此以王國維、章太炎為代表;其二,將“物”理解為精魅或瑞獸,此以宋翔鳳、牟潤孫為代表,裘錫圭似乎也不反對這一說法;其三,將“物”理解為圖騰或徽幟,此以阮元、孫詒讓、傅斯年、劉節為代表;其四,將“物”理解為青銅禮器上的動物紋樣,以張光直為代表。其中諸多觀點后文有說,此不具引。其余可參王國維:《釋物》,謝維揚等主編:《王國維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7—188頁;章太炎:《說物》,《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31頁;裘錫圭:《說“格物”——以先秦認識論的發展過程為背景》,《文史叢稿——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14—15頁。。
為此我們不辭繁冗,再次回顧一下“百物”比較有代表性的用例,以期獲得理解這一概念必要的線索。
例一: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國語·魯語上》)②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56,156頁。
例二: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周禮·大司徒》)
例三: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左傳·宣公三年》)
例一“黃帝能成命百物”云云,《禮記·祭法》因之,作“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③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03頁。。韋昭注曰:“命,名也。”④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56,156頁。“成命”就是命名。黃帝能夠為“百物”命名,才成就了一個和諧的秩序,民人由是以“百物”為財貨,利而用之。例二所云大司徒職能之一是確定大地中心,這一點是天地陰陽交會之所,于此奠立王畿,能讓“百物阜安”,天下和平。例三則透露了達至“百物阜安”的具體細節,是前兩個案例的有益補充。九鼎是夏王朝最重要的禮器,用各地貢金(青銅)熔鑄,鼎身則鑄有“百物”的圖像。由此,人和圖像背后的神明建立了保證和平的“約定”,民人進入并利用“川澤山林”,便不會觸犯神明(“魑魅罔兩”)。很明顯,“鑄鼎象物”的“物”就是“百物”。在熔鑄的過程中,刻畫到鼎身的“百物”不是作為個體的物自身(“萬物”之物),而是各個族類的代表。每一族類都有一個對應的名,而將各個族類納入秩序的重要途徑就是命名,即例一所謂“成命百物”(或“正名百物”)。只有做到“百物阜安”,才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百物”可以命名,也可以摹象。但熔鑄在鼎身的圖像并不是“百物”之“物”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重要的是形象背后的神秘力量(神格)。由此可知,“百物”不同于“萬物”之處在于:其一,“百物”不是個體之物的總和,而是族類的總和,每個個體之物都屬于一個族類,所以沒有純粹的個體可言;其二,“百物”有各自的形象可以被人經驗和想象,但人感官(特別是視覺)經驗到的只是物的表象,使物顯現并決定物成為物的是形象背后的不可見的力量,一般稱之為神。所以,與“百物”相匹配的一組認知范疇是形神。形可以摹象,但主要不是形體。形是顯現,可以感知,但是形背后的神則難以經驗,所謂“不測”“不可知之”者謂神是也。
“百物”之“物”,有神怪、精魅之義。前人早已指出,“物”可訓作神怪、精怪,其用例曾頻繁出現在早期經典文獻之中⑤牟潤孫:《說“格物致知”》,《注史齋叢稿》(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17—218頁。。《史記·留侯世家》有云: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
司馬貞《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①司馬遷撰,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49頁。贈予張良《太公兵法》的老翁自稱“谷城山下黃石”(《留侯世家》),故時人認為此翁乃黃石背后之神明幻化而成,故可謂之“物”,和稱熔鑄“魑魅罔兩”的圖像為“鑄鼎象物”一樣。此外,《周禮·春官宗伯》記錄了一眾掌管禮樂的神職人員,其職能是通過宗教儀式招致“天神人鬼”和“地示物鬽”(《家宗人》)。作為“春官”首腦的大宗伯,其職能就包括“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鄭玄注曰:“百物之神曰鬽。”②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1065頁。大宗伯所致之“百物”乃百物之神,即百物之精魅(鬽),它們是代表各自族類的神明。
“百物”可指百物之神或精魅,亦可指被神代表的各族類事物,和諸子所謂“萬物”的區別,顯而易見。但精魅、神怪只是古典“物”概念的內涵之一,并非全部。《說文》云:“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故從牛,勿聲。”解“物”為諸子常用的“萬物”,乃是用晚起的觀念追溯本字的源初意義,所得結論難以讓人信服。許慎為了解釋物字“從牛”,一方面說牛為有代表性的“大物”;另一方面又依星象為說,異義并存,更啟人疑惑。戴震便反駁說:“周人以斗、牽牛為紀首,命曰星紀。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于斗、牽牛也。”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3,453頁。其實,“物”的古典含義不取決于作為形旁的“牛”,而取決于作為聲旁的“勿”。這一點前人也早有所論:
《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笴。”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倳也。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勿。”④阮元:《大學格物說》,《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5頁。
阮元輾轉訓“物”為“事”,顯然是不欲破鄭玄“物猶事也”這一古訓,雖然迂曲,但仍不乏洞識,給人以啟發:第一,明確指出“物”本從“勿”取義,其后孫詒讓更是直接說“勿,即物之本字”⑤孫詒讓:《九旗古誼述》,《大戴禮記斠補 附尚書駢枝 周書斠補 九旗古誼述》,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第274頁。;第二,引《儀禮》之《鄉射禮》和《大射禮》,提示了“射時所立處”可稱為“物”,章太炎由此揭橥“物”的法度之義,此后文有說。
阮元說“勿”為“州里所建旗”,《說文》原文是:“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⑥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3,453頁。簡單說,勿指旗幟,由不同顏色的絲帛所為,上繪有不同圖案。《周禮·司常》云: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
此文兩“物”字含義有別。“雜帛為物”的“物”特指以赤、白兩色絲帛組成旗幟,一般為大夫士所用。“九旗之物名”,鄭玄注曰:“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⑦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1054—1055頁。這一用法道出了“物”字相對原始的含義——繪制于旗幟上的圖案或者形象,由此引申,可以指廣義的或者特殊的旗幟。《左傳·宣公十二年》有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杜預注曰:“物猶類也。”孔穎達則進一步解釋說:“類,謂旌旗畫物類也。”⑧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第637頁。今人楊樹達說得更直接:“物讀為《周禮·大司馬》‘群吏以旗物’、《春官·司常》‘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之‘物’,本是旌旗之一種,此則借為旌旗之通稱。”⑨楊樹達:《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24頁。此外,《國語·吳語》記載,文種曾問越王勾踐:“審物則可以戰乎?”韋昭注云:“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⑩徐元誥:《國語集解》,第558頁。凡此種種都說明,“物”字從“勿”,是一種旗幟。總言之,物為旌旗、徽幟,其本質是一種標志,于可以經驗的形象之中寄寓著不可經驗的神圣的義涵。
四、形神:古典之“物”的實質
基于形名的“萬物”,是純粹的對象為人所認知。形是人覺知的對象,名是人基于感知賦予物的稱謂。物可以被形名范疇把捉,源于一個更為根本的生存論前提:物是對人有用的材質。這一點在荀子的思想中表現得最為充分。《荀子·富國》曰:“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①王天海:《荀子校釋》,第 419 頁。萬物被有用性規定,其自身不存在可以規定自身的合宜性,一切都取決于人的目的。
“百物”所體現的古典“物”概念則不同,不論是作為精魅的物,還是作為徽幟的物,都包含著人無法完全對象化的“神”性因素。精魅為百物之神,前文有說,此不贅言。而徽幟之神性因素,需加以說明。《左傳·定公十年》記載,叔孫氏家臣侯犯以叔孫氏采邑郈邑投降齊國,其事不果。于是,侯犯率眾出奔齊國。到了郈邑的郭門,守門人表示,侯犯一行人可以出逃,但必須留下屬于叔孫氏的甲胄。關于此事,《左傳》原文是:
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和侯犯同行的駟赤說,出奔的一行人并不敢將叔孫氏的甲胄帶出郈邑,進入齊國,原因是“叔孫氏之甲有物”。杜預注曰:“物,識也。”②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第1592頁。認為此“物”屬于徽幟一類的標識。為什么駟赤和侯犯不敢穿戴有叔孫氏標識的甲胄逃離郈邑?難道因為穿戴有特殊標識的服飾容易暴露身份而成為抓捕的目標?這樣的想法顯然過于現代。關于這一點,傅斯年之說可謂切中要害:
《左傳》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又定十年,“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據此,則物為圖騰標識,更顯而易見……蓋物者,社會組織宗教信仰之所系,故知此重言之。③傅斯年:《跋陳槃君〈春秋公矢魚于棠說〉》,歐陽哲生編:《傅斯年文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84—285頁。
劉節同樣認為,包括《左傳》所謂“鑄鼎象物”和“叔孫氏之甲有物”在內的“物”字,“確乎都有圖騰的意義在里面”,又說這些物“確指圖騰中所繪的物象”④劉節:《說彝》,詳見氏著《古史考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6頁。。按傅、劉二氏之說,“叔孫氏之甲有物”的“物”非一般的標識,而是具有神圣宗教意味的圖騰。如此一來,駟赤和侯犯“未敢以出”的原因便不難理解了:叔孫氏之甲上的標識是叔孫氏一族的族徽乃至圖騰,只有叔孫氏之族眾可以佩戴;侯犯之黨一旦叛離,自然也就失去了佩戴的資格。這就如同今天未經授權不得使用某種特定的商標一樣,只是這一規則由現代法律保證;而非族眾不得佩戴或使用本族的徽幟這一原則,則由徽幟背后的神明保證。叔孫氏之“物”背后關系著叔孫氏一族全體祖先的神明,揭示這一原理,有助于我們更進一步理解“鑄鼎象物”的意義。依《左傳》之說,夏王朝建立時,各方諸侯(或者部落族長)除了貢獻本地特產的金屬之外,還將本土之“物”繪成圖像(“遠方圖物”),一并獻給夏廷。夏王朝會集各方的金屬和圖像后,熔鑄為九鼎,同時將“百物”鑄于鼎身之上(“鑄鼎象物”)。各方諸侯所獻之“圖物”,其實就是本族的族徽或者圖騰。不管是徽幟還是圖騰,大概都是繪制于平面上的物象,只是非一般的圖像,而是神明依憑的形象⑤張光直認為,《左傳》所云“鑄鼎象物”和“叔孫氏之甲有物”的“物”乃是可以用作犧牲的動物紋樣,是協助巫覡溝通神人的動物的形象。此說解釋“鑄鼎象物”似可,解釋“叔孫氏之甲有物”則略顯牽強,反不如傳統釋為族群象征之“徽幟”更為妥帖。不過,提示兩個“物”字的相關性,并揭示其宗教意涵,仍不失為洞見。詳見張光直著,劉靜等譯:《藝術、神話與祭祀》,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第60—63頁。。
形神之于“百物”,猶如形名之于“萬物”。其中,與神和名相匹配的皆可謂之形,但兩處形字的含義卻不盡相同。形名之形為形體,形神之形則為形象。二者都是物自身的顯現,但顯現的形式與內容有別。在諸子的思想語境里,形為形體、形貌,是有一定廣延、占有一定空間的物體①楊立華敏銳地注意到了《墨辯》所謂的“物”是“幾何意義的物”,并認為這一“物觀”反映了“戰國時期哲學理性的普遍狀況”。詳見楊立華:《〈墨辯〉中的物》,《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唯其如此,被形名把捉的萬物才可能被視作人為加工的材質。極具名辯意識的墨子后學曾舉例說:
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
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墨子·大取》)②吳毓江:《墨子校注》,第 614、615頁。
高山丘垤為自然景觀,宮室宗廟為人為建筑,一個是人為的對象,一個是人工的結果,但為有形體之物則無不同。刀劍為有“形貌”者,形體不同,為物亦有別。同樣,《易·系辭上》首章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形”為形體而非形象,明白無誤;十一章又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③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58、288頁。,則此形乃有形體之物,特別是人造的器具,更無異議。
不同于形體,形神之形多指形象。前者是在空間中擁有位置的物體,后者是平面上呈現的圖像。舉例來說,古人認為大地上的山石、花樹、宮室、車馬都是有形體之物,對于這些有形之物,人們可以觀察,可以利用,所以它們都是現實的或潛在的材質,用以承載人的目的。可是天上的日月星辰是一種沒有形體的表象(“在天成象”或“天垂象”),如同點綴在天幕之上的圖案一般。人的力量無法作用于日月星辰等天象,所以,這些形象非但不是承載人的目的的材質,而且還是超越性力量垂示于人的法度。
前諸子時代的“物”概念包含法度之義,與其背后的形神觀念密切相關。形象因為是神明賴以憑靠的載體,因此也具有神圣的法度意味。“鑄鼎象物”有法度效力,所以民入山林川澤能夠“不逢不若”,建立起人神之間和諧的秩序。叔孫氏甲胄之“物”有法度意味,所以侯犯之徒須脫甲而行。《左傳·隱公五年》載,魯隱公到棠地射魚,不合禮法,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④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第91頁。
文中“軌”“物”二字皆有法度的意義,君主一言一行都應該致力于將治下民眾納入法度之中。其中“軌物”之物,傅斯年和劉節都認為是一個部族的圖騰標識。準此,一國國君合理的狩獵行為應以增飾和彰顯本族圖騰(或族徽)為目的,以團結族眾和彰顯法度,所謂“取材以章物采”是也;其余細事,君主自不必躬親,以免給民眾帶來負面影響。又《禮記·哀公問》載孔子和魯哀公的對話,其文有云: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寡人憃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文中幾處“不過乎物”,鄭玄皆注云“物,猶事也”⑤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第1921—1923頁。,和《大學》“格物”的注法一致。然而章太炎將“物”訓為法度,似更符合古典本義:
問曰:記言格物者,何所取?應之曰:射者履物不可越者也。《哀公問》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故曰: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謂有軌度,不可逾也。其在《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格物者,格距于其軌度。若射者然,思慮辨難,不越隄封。⑥章太炎:《說物》,《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31頁。
和阮元以“射時所立處”理解“物”一樣,太炎也認為“物”從“射者履物不可越者”取義,意指不可逾越之軌度。射者所履之處有軌度、法則之義,只是何以稱之為“物”呢?恐怕仍根源于傅斯年所謂圖騰、徽幟之義。正如《詩·大雅·烝民》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古典“物”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法則之義,說到底,與其形神這一基本結構有關。
余論:形神之后
至此,我們可以略作總結。早期中國思想中“物”的含義在晚周之際發生了根本轉變,追問這一轉變,對理解作為整體之諸子學的思想品格有一定的助益。如文中所論,“物”概念的變化體現在從早期“百物”到諸子“萬物”的轉變上。“百物”之“百”指的是族類,而族類之所以成為一個整體,乃是基于形象背后的神明。而“萬物”之“萬”則指的是“每一個”,不是從整體中析出的“每一個”,而是作為整體得以構成之前提的“每一個”。這一轉變之發生,有賴于支撐古典“物”概念之神明的退場。所謂諸子學的人文主義品格,說到底,乃是建立在對古典神明觀念的揚棄(或轉化)之上。
神明退場,遂有個體觀念之發生。可是,如果整體世界由“每一個”個體構成,個體之物無窮無盡,關于個體之物的知識便無止境。為了克服這一難題,晚周諸子有不同的思路,其中最有解釋力且影響深遠的是訴諸“類”觀念。然而,何為同類?致思的方向有二:其一,同類者同性,同性者同類,即擁有相同性質(或理)之物為同類事物,也包括人;其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實也就是同類相感,主要指有生命之物,特別是動物和人。而“同類者同性”的意思是說,“每一個”個體之物都包含著“類”本質,人們可以通過個體之物顯現出的性狀探究背后的“類”本質,此即前文所謂晚周諸子形名之學的宗旨。
把捉個體之物的性狀,須訴諸人的知覺,這是一個非常關鍵卻未獲應有重視的概念。荀子說過,知識是通過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五種感官和心靈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正名》);前五者又稱為“天官”,而心靈則是“天君”(《天論》)①王天海:《荀子校釋》,第 891、677 頁。。以君主和官僚類比心靈和身體,乃晚周諸子的習慣用法,非特荀子如是。在這一比喻中,心靈是目的,身體及其知覺能力是承載目的的材質。所以,墨子后學有“知,材也”(《墨子·經上》)的說法,知覺是一種屬人的能力,其本質是承載心靈之目的的材質。如果身體之知覺能力是心靈的材質,那么作為知覺對象的萬物(的性狀)同樣是材質,甚至是“材質的材質”。
由此可見,個體之物成為知覺觀照對象有更深刻的生存論意涵:“每一個”個體之物千差萬別,但作為對人有用的材質,則無不同。在這一語境中,“萬物”被想象成有形體、可以操控和加工的對象。于是,形體不但取代了形象,而且將形象背后具有法度意義的神明也揚棄了。如此一來,諸子之學便要“發明”一種新的法度觀念,其原型為工匠使用的規矩繩墨。可以說,晚周諸子對于法度的理解幾乎都包含規矩繩墨的想象,墨子、孟子、荀子無不如是。直至漢代,才出現對法度和政教類型的全新理解,與之同步,經學取代諸子學成為塑造政治和思想主流的知識形態。
最后,關于諸子學之發生,可一言以蔽之:作為整體的諸子學思考的起點是“每一個”事物成為知覺觀照的對象,而這種觀照本身最終指向擺脫了神的人之目的。與這一思潮相應的是,個體的人從“族類”之中解放出來②西嶋定生在論述秦漢皇權性質時發明了一個極富洞見的說法——“個別人身的支配”,用以說明皇權的性質及其運作機制。在他看來,秦漢帝國皇帝統治的對象“不是像殷、周時代的氏族,而是一個人一個人的”,相應地,“所有的人,并非作為氏族集團被支配,而是個別的被支配,一個人一個人被皇帝權力所掌握,成為徭役、人頭稅的對象”。與之類似,杜正勝將“編戶齊民”視為秦漢帝國運作的社會基礎。所謂編戶齊民,乃是將治下所有個體民眾無差別納入戶籍的人口登記制度,由此帝制國家才能最大程度地控制人力和物力,進而形成強大的威權國家。詳見[日]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形成史論》,劉俊文主編,高明士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49頁;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年,第22—23頁。,由此,關于人和政治的知識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