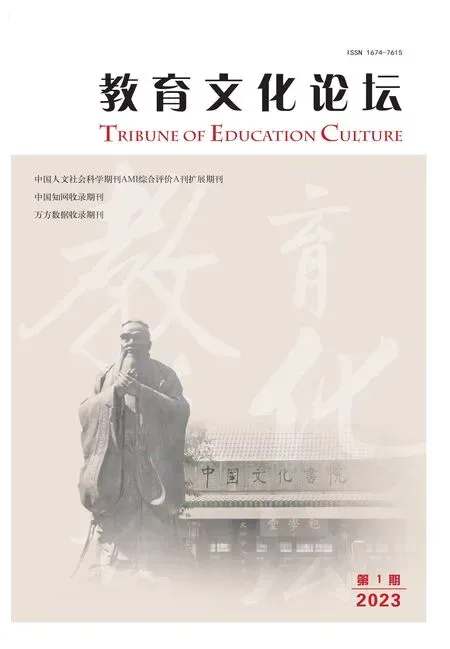論教育哲學的性質(zhì)、作用、核心問題和研究方法
——杜威實用主義哲學觀考略
朱鏡人,葛 琪
(1.合肥師范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安徽 合肥 230061;2.安徽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39)
在杜威生活的時代,對于教育事務中教育哲學是否重要的問題,人們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教育事務中教育哲學并非不可或缺,例如學校中的科學課程,采用的是非人格的術語,就與教育哲學無關;另一種觀點認為,教育事務中處處蘊含著教育哲學,教育哲學不可或缺。杜威是持后一種觀點的代表人物。他告訴人們:“作為所有教學和規(guī)訓方法的教育措施和建議都含有某種哲學。因此,在教育中被稱作‘科學’和被稱作‘哲學’之間不可能存在對立。因為,只要科學具有實際的用途,只要依據(jù)科學的行動發(fā)生了,那么,價值和結果便會隨之而來。作了選擇便會產(chǎn)生后果。由于哲學是一種待達成的或被拒絕的有關價值的理論,因此,就存在著哲學含義。”[1]78既然教育哲學不可或缺,那么,一些問題,如教育哲學的性質(zhì)是什么,教育哲學有什么作用,教育哲學應當關注什么問題,以及如何進行教育哲學研究,自然而然擺在了杜威面前,需要杜威回答。杜威也確實思考和回答了這些問題。本文旨在梳理杜威這一方面的主張,希望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主張,同時有益于我國教育哲學學科的建設。
一、教育哲學的性質(zhì)和作用
1.教育哲學的性質(zhì)是社會哲學
杜威認為,從性質(zhì)上看,教育哲學本身是一種哲學,屬于社會哲學的一個分支:“教育哲學是一種特別偏向社會功能的一般哲學”[1]84。對此,他解釋道:“我們的立場內(nèi)含的意思是,教育哲學是社會哲學的一個分支,像某一種社會哲學一樣,因為它要求用道德觀選擇品格、經(jīng)驗和社會制度問題。”[1]80作為教育哲學研究對象的教育,“是一個社會互動過程,其結果也是社會性的——也就是,它包含人們之間的互動,包括共享的價值”[1]80。
杜威認為,教育哲學的職責是在教育和哲學之間建立某種聯(lián)系。在他看來,按照柏拉圖的觀點,“教育是建設人類美好生活的手段。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美好生活的本質(zhì)、美好生活的構成和實現(xiàn)美好生活的條件。哲學和教育是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2]292,但自古希臘教育之后,“教育與哲學之間重要的連接鏈斷裂已經(jīng)為時久矣。教育和學校教育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哲學也走上了獨立的路徑。教育與哲學兩者都發(fā)現(xiàn)自己身纏大量的特別問題,在各自專業(yè)化進程中,兩者分道揚鑣了。”[2]292杜威認為,希臘時代教育中的問題相對簡單,而現(xiàn)代教育中的問題難以計數(shù),且復雜多樣,相互之間也有明顯差異,如果不對問題與問題間的聯(lián)系作研究,而是對單一的問題作研究,不但“每一個問題都難以解決,解決每一個問題都需要付出全部的時間和精力”[2]292,而且就教育與哲學而言,建立兩方面的聯(lián)系對雙方都有益處。他告訴人們:“今天的時代,人們對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
……人們對哲學思想的興趣也與日俱增。重建這種聯(lián)系難道不會有助于給予教育以指導和完整性,給予哲學以殷實的內(nèi)容和活力嗎?”[2]292
2.教育哲學的作用在于“指揮教育”和“改造教育”
杜威十分重視教育哲學的作用,出版過專著,如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義與教育——教育哲學導論》(DemocracyandEducation:AnIntruductiontotheEductionofPhilosophy)(1)這本書的一些中文譯本以及一些中文著作或教材在介紹杜威這本書時忽略了這個副標題,以致不少學生和讀者不知道這本書還有這樣一個副標題。就是一本教育哲學專著;發(fā)表過專門的論文,如他與蔡爾茲(J. L. Childs)1933年合作發(fā)表了專文《作為基礎的教育哲學》(TheUnderlyingPhilosophyofEducation)。此外,杜威還專門就教育哲學話題作過許多專題講演。如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11日,他在中國訪問講學的兩年多時間里,曾先后在北京教育部(1919年9月21日至1920年2月22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0年4月至5月16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0年秋至1921年夏)和湖南長沙尊道會(1920年10月26日和1920年11月1日)四個場所,以“教育哲學”為題作了許多場講演[3]。其中,在北京教育部的教育哲學系列講演16次,在南京高師的教育哲學系列講演10次[4]1-2。又如,1934年7月,杜威在南非開普敦和約翰內(nèi)斯堡的南非教育研討會上,再次以“教育哲學”為題作了“教育哲學的必要性”(TheNeedforaPhilosophyofEducation)的講演。杜威為什么如此重視教育哲學,或者說,為什么他要從教育哲學視角來探討他關心的教育問題,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在他看來,教育哲學有兩個重要作用。
其一,通過闡釋教育理念來“指揮教育”。在杜威看來,教育哲學可以將教育行動的含義闡釋清楚,即解釋清楚為什么應當選擇這種行動而不是那種行動,盡量避免盲目的教育行動。他明確地說:“教育哲學的使命(business)是厘清教育領域采取的行動的含義,將一種依據(jù)習俗而非依據(jù)思想的盲目偏愛變成一種理智的選擇——一旦完成這一任務,就會意識到目的是什么,偏愛某種行動的理由是什么以及采用的方法是否合適等。”[1]78按照杜威的說法,“教育哲學就是要使人知道所以然的緣故,并指揮人去實行不務盲從、不沿習慣的教育”[5]78。
其二,通過提供清晰的教育理念來“改造教育”。按照杜威的邏輯,新教育并非完全否定舊教育,而是要對舊教育加以改造,沿著新教育方向前進。對此,他作了非常形象的說明:“指揮教育,改造教育。好像駛一只船:裝載貨物,固然應該持平,不要使它畸輕畸重,然裝了以后,不能揚帆開駛,使裝滿了貨的船在船塢里腐爛,當然是不行的。古代傳下來的學問,就是裝載船里的貨物。現(xiàn)在的新潮流、新趨勢就是行船的風。我們應該把這裝滿貨物的船,乘風前進,不使它停在船塢里腐爛。”[5]81而要改造舊教育,教育哲學要做兩件事:第一件,教育哲學需要向人們解釋清楚改造的必要性,指明改造的路徑,應當告訴人們,如果人們希冀有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公正、更加開放、更加正直的社會,“希冀有一個改善了的和規(guī)模擴大了的教育以便建立一個所有一切措施都具有教育意義的社會,有益于意愿、判斷力和品格的發(fā)展,那就必須對脫離社會生活的舊學校教育進行改造”[1]103,因為“在與社會生活隔絕的學校圍墻內(nèi),所期望的教育不可能產(chǎn)生。教育自身必須承擔不斷增長的責任,參與社會變革理念的制定,并將理念賦予實踐以便使其具有教育意義”[1]103。他強調(diào)說:“教育哲學的職責(office)在于指明這種需要的迫切性,用我們自己的概念草擬出能夠?qū)崿F(xiàn)目的的路線。”[1]103第二件,教育哲學應該通過清晰的教育理念幫助人們對改造活動作出理性的選擇。在他看來,如果沒有清晰的教育理念作為基礎,人們的選擇可能出現(xiàn)錯誤,教育改革的活動也就不會順利。杜威告訴人們,一般而言,理智的選擇偏愛的是有價值的活動。他說:“理智的選擇依然是選擇。它依然含有偏愛追求一種目的而不是另一種目的,它含有一種信念,即這種那種目的是珍貴的,有價值的,而另外的則沒有。……公正的責任在于盡可能清晰地說明選擇的是什么和選擇的理由。”[1]78
杜威也承認,對于教育哲學有沒有用的問題,不同時代或不同社會的人們可能會有不同的認識,但他告訴人們,沒有教育哲學指導的教育只會是一種循環(huán)往復的無進步的教育。新時代的教育一定要遵從教育哲學的指導,選擇正確的教育行動。1919年他在北京大學講演時對這一觀點說得很明白:“我們并不是說教育哲學萬不可少,不過是很重要。我們且從反面看,倘使人類沒有教育哲學,對于教育事業(yè)必定不去研究它,思想它,但看人家怎么教,我也怎么教,從前怎么教,現(xiàn)在也怎么教;或者學他人的時髦,或由自己的喜歡,成一種循環(huán)的、無進步的教育。這就是沒有教育學說的流弊。……在一種保守的社會里,教育哲學是用不著的。從前的舊社會,大概都持這種態(tài)度。”[5]78但在新的時代,教育哲學是必不可少的:“當現(xiàn)在變遷很快的時代,多少潮流在外面激蕩,我們應該去選擇哪一種是對、哪一種是不對,辨別哪一種是重要、哪一種是次要。當這時代倘若沒有教育哲學的指揮,一定不能從這許多互相抵觸、互相沖突的里面,選出哪一種是我們應該采取的潮流趨勢來。”[4]4-5
二、論教育哲學應當關注的兩個核心問題
教育哲學應當研究什么,杜威雖然沒有特別地說明,但人們可以從他出版的著作和講演的內(nèi)容中發(fā)現(xiàn)他所關注的問題。他的《民主主義與教育——教育哲學導論》一書共有26章(2)《民主主義與教育》26章的標題分別為:“教育是生活的需要”“教育是社會的職能”“教育即指導”“教育即生長”“預備、展開和形式訓練”“保守的教育和進步的教育”“教育中的民主概念”“教育目的”“自然發(fā)展和社會效率作為教育目的”“興趣和訓練”“經(jīng)驗和思維”“教育中的思維”“方法的性質(zhì)”“教材的性質(zhì)”“課程中的游戲和工作”“地理和歷史的重要性”“課程中的科學”“教育的價值”“勞動和閑暇”“知識科目和實用科目”“自然科目和社會科目:自然主義和人文主義”“個人和世界”“教育與職業(yè)”“教育哲學”“認識論”和“道德論”。參見呂達等:《杜威教育文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 頁。,每章論述一個問題,也就是說,這本書論述的問題有26個。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克洛普頓(Robert W. Clopton)和香港新亞書院(New Asia College ,Hong Kong)吳俊升(Tsuin-Chen OU),于1973年將杜威在華涉及哲學的講演翻譯成英文,以《約翰·杜威在華講演錄(1919—1920)》(JohnDeweyLecturesinChina,1919—1920)為書名出版。該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社會和政治哲學”(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第二部分為“教育哲學”(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第二部分教育哲學的講演涉及的主題也有16個(3)這16個主題是:“教育哲學的必要性”“教材的誤用”“教育中的工作和游戲”“創(chuàng)造性演劇和勞作”“文化遺產(chǎn)和社會重建”“社團生活的紀律”“未來與當代”“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展”“科學與道德生活”“科學和認知”“科學與教育”“中小學教育”“地理與歷史”“職業(yè)教育”“道德教育——個人方面”“道德教育——社會方面”。參見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3:vi。之多。在教育哲學的議題中,有些是杜威特別強調(diào)的。例如,1919年,在教育部講演時他提出舊教育存在三種流弊:之一,能夠接受學校教育是特別的階級,即那些有權有勢有錢的人;之二,偏重古訓和文字;之三,學校“與社會不生關系”[5]79-80。因此,有三個問題是教育哲學需要討論的:“(1)怎樣可以使特別階級的教育變成大多數(shù),變成普及;(2)怎樣可以使偏重文字方面的教育與人生日用的教育得一個持平的比例;(3)怎樣可以使守舊的教育一方面能保存古代傳下來的最好一部分,一方面能養(yǎng)成適應現(xiàn)在環(huán)境的人才。”[5]80此外,杜威認為,教育哲學還需講清楚“教育為什么是必要的?教育為什么是可能的?教育必借何種機關,何種工具,何種方法,才可以推行出去?人既領受過教育之后,有什么結果發(fā)生?受好教育就得好結果,受壞教育就得壞結果。我們怎樣能判斷出這許多結果的價值是好是壞呢?”[6]4-5
根據(jù)前文,可以說,在杜威那里,幾乎所有包括教育哲學本身在內(nèi)的教育問題都是教育哲學需要關注和闡釋的問題。但對杜威教育哲學關注的問題作仔細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杜威列舉的教育哲學應當關注的問題基本都是圍繞兩個核心問題展開的,即圍繞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知與行的關系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展開的。
就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問題而言,杜威認為,教育的對象是個體的人,個體的人生活在社會中,與社會必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告訴人們:“社會與個人不是對立的,社會是處于相互關系中的個人組成的。遠離社會關系的個人是一個假想的人——或者是一個怪物。如果我們論及實際的人而不是抽象概念的人,我們的立場能夠這樣來表述:教育是實現(xiàn)統(tǒng)合了的個性(integrated individualities)的過程。”[1]80而統(tǒng)合了的個性只能在社團中并通過社團這一中介進行,換言之,必須在社會環(huán)境中進行。杜威因此強調(diào)說,“人不是在關系疏遠的籠統(tǒng)地被稱作‘社會’的統(tǒng)一體發(fā)展的,而是在相互間密切聯(lián)系中發(fā)展的”[1]80,由于“他們相互間聯(lián)系的環(huán)境,他們的參與和交流以及合作和競爭的環(huán)境是由法律、政治和經(jīng)濟的約定決定的。因此,為了教育的利益——而不是為了任何事先構想的‘主義’或法規(guī)——要強調(diào)的事實是,教育必須按照有意地偏好社會秩序的觀點來運轉(zhuǎn)”[1]81。杜威有關個人與社會的這些觀點,實際上是對他在《民主主義與教育——教育哲學導論》一書中提出的“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和“教育即經(jīng)驗不斷的改造”等主張作的進一步闡釋。換言之,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長”等主張的目的,旨在解決個人與社會關系中出現(xiàn)的矛盾或沖突問題。在杜威關注的教育哲學問題中,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的核心地位也因此顯而易見。
就知與行的關系問題而言,杜威強調(diào),在教育哲學中,“知和行的關系問題與個人和社會關系問題同等重要”[1]86。知與行的關系為什么重要呢?杜威作了這樣的說明:“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我們不得不行動,行動極其重要且不可回避。但同時,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知識是有條件的且依賴我們自己。而且,行動的后果,即行動之后會發(fā)生什么并作為永恒的積淀物余留下來,依賴——至少局限于——行動是否具有知識的特征,而且得到適當?shù)睦碇侵笇А!盵1]86-87顯然,在杜威看來,理智的行動,即希望行動的后果能夠作為“永恒的積淀物”流傳下去,是離不開知識的。杜威承認,通常人的行動由幾種方法或精神支配:一些行動受外部權威的方法支配,如外部權威通過懲罰或獎勵來規(guī)定人們的行動;一些行動受習俗的支配;還有一些行動屬于常規(guī)的方法,自動延續(xù),沒有理由,長期使用,輕車熟路。杜威認為,這些方法在實際生活中應用得很廣泛,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也最大。與這些方法相比,知識對行動的影響似乎遜色不少,因為在一般情況下,“生活是以知行之間的溝壑為特征的,也以理論與實踐的分離為特征”[1]88。也就是說,知與行之間是有距離的,它們之間也似乎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學校也一直踐行這種分離原則。杜威說:“作為教育的特殊工具,學校依據(jù)的是被廣泛采納的知識與實踐分離的原則,且與這一原則保持一致。它們堅持這一分界線而且拓寬了間隙。”[1]88對知識與行動之間分離的事實杜威是承認的:“在行動迫不及待地產(chǎn)生并不斷創(chuàng)新的世界中,理智和行動之間不可避免存在著某種分離”[1]87,而且,“從許多視角看,理智和實踐的分離依然會維持現(xiàn)狀”[1]89,但“只有首先在理念,其次在實踐的事實方面承認理論和實踐、知識和行動的密切合作,才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具有遠見和規(guī)劃能力的社會,以規(guī)范不可避免的變革進程”[1]90。他在1949年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人若預見不到自己行動的后果,那他即將從事的活動就沒有方向感。除非能預見到行動的后果,作出聰明的選擇,明智地而不是盲目地采取行動,不然還能如何避免不良后果呢?”[7]杜威也承認,對于因知識而形成的理智是否能夠成為指導人們行動的重要方法的問題,人們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杜威相信:“只要生活持續(xù)著,行動便不會停止。唯一能夠阻止它的方法就是摧毀人類自身的生活。價值能否實現(xiàn),價值實現(xiàn)是否遭遇阻礙,價值是否貶值,這些都取決于各種各樣的行動。在行動和撤銷行動之間不存在真正的抉擇。唯一的抉擇只能在不同的行動方法之間進行。如果可能的話,知識和思想提供的指導行動的方法要比外部權威、謀求私利和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依靠模仿、先例或者武力等提供的指導高明得多,否認這一點的人可能是膽大的人。”[1]91
三、論教育哲學的研究方法
在杜威看來:“‘教育哲學’并非把現(xiàn)成的觀念從外部應用于起源和目的根本不同的實踐體系:教育哲學不過是就當代社會生活的種種困難,明確地表述培養(yǎng)正確的理智的習慣和道德的習慣的問題。”[8]其中,所謂“現(xiàn)成的觀念”(read-made ideas)是指現(xiàn)有的理論。換言之,在杜威看來,教育哲學不是應用現(xiàn)有的理論來研究當代教育中的問題。那么,教育哲學用什么方法來作自己的研究呢?杜威認為,實驗法(experimental method)是最合適的方法。為什么呢?杜威告訴了人們其中的原因。他說:“在實驗法誕生之前以及遠離實驗法的時候,新的事實的揭示純粹出于偶然性,是一種意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在較大的系統(tǒng)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它們?nèi)匀皇枪铝⒌模蛘呤潜凰枷霃娦屑{入某種理性方案和系統(tǒng)中。另一方面,通過實驗觀察法發(fā)現(xiàn)的事實,要么因為作為實驗成果的理念提供了自然背景而自然地變得清晰起來;要么,如果所發(fā)現(xiàn)的事實是未曾預料到的或與這些理念不一致,人們會提出引發(fā)新實驗的新理念。這兩種情況無論出現(xiàn)哪種,它們都不會是荒謬的和令人困惑的,而是有助于確定進一步探究的問題。”[1]92-93
杜威認為,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實驗法已經(jīng)結出了豐碩的果實,社會生活中的實驗法也同樣可以結出果實,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實驗,我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說是某種嘗試”[1]94。“在一個許多復雜性和偶然性與我們相同的世界里,行動是需要的,行動也必須是實驗性的,即是一種嘗試,這是確定無疑的。”[1]94杜威相信,實驗法應該能夠“像在自然領域中的運用一樣作為社會知識和行動的基本方法。如果不能,處理人類事務的隨意性與處理物質(zhì)事務的精確性之間的縫隙一定會擴大,其結果可能摧毀人類的文明”[1]94。
杜威認為,“自然科學實驗法與人文學科實驗法有著明顯的區(qū)別”[1]102,但自然科學實驗法有一點值得人文學科借鑒,這就是分享和交流。他說:“科學之所以進步是因為通過探究獲得的發(fā)現(xiàn)可以立刻被同一領域所有的工作者分享。沒有不間斷的交流和相互促進,自然科學依然會處于未成熟階段。”[1]102而且在杜威看來:“自由的交流既意味著接受又意味著分享價值的能力。社會的最大問題是如何通過個人自由地體驗和發(fā)揮其能力的方法最大化地組合不同的價值,同時使摩擦和沖突最小化。這個問題唯有實驗法能夠解決,任何其他方法都無能為力。”[1]102因為民主“它首先是一種聯(lián)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種共同交流經(jīng)驗的方式”[8]87,在這方面,“實驗法是唯一適合民主生活方式的方法。作為行動方法的理智的發(fā)展拓寬了共同理解的領域。理解不能確保完全一致的同意,但是,它為達成一致同意提供了唯一堅實的基礎。在任何有不同意見的地方,它有助于允許彼此保留不同意見,有助于相互包容和相互支持,假以時日,便能獲得更加合適的知識和更好的判斷方法。”[1]102
杜威主張的教育哲學實驗法有兩個明顯特征。
其一,實驗法的實驗結果的不確定性有別于盲目行動的不確定性。杜威認為,實驗法是一種“有意識的嘗試”,即實驗法中的實驗是有目的和依據(jù)條件進行的嘗試,絕不是一種盲目的簡單嘗試的方法,他告訴人們,“如果實驗只是意味著簡單嘗試,那就毫無新鮮感了”[1]94。杜威承認作為嘗試的實驗法具有“不確定性”,而且多次論述過。如1929年4月,杜威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吉福德講演(Gifford Lectures)”(4)當時,“吉福德講演”一年一度由蘇格蘭幾所大學輪流舉辦。1929年4月17日至5月17日,杜威在愛丁堡大學就“確定性的尋求”共作了10次講演。參見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4卷,傅統(tǒng)先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頁(導言)。所作的“確定性的尋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系列講演中就說過:“任何哲學,如果在它尋求確定性時忽視了自然進行過程中不確定狀態(tài)的實在性,就否定了確定性之所由產(chǎn)生的條件。”[9]其言下之意顯然在說,教育哲學的研究過程亦需正視其研究結果的不確定性。又如,1934年,他和蔡爾茲在《作為基礎的教育哲學》一文中更是明確地宣稱,實驗法承認“不確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實驗法永遠反對自稱穩(wěn)操勝券的方法”[1]95。但在杜威看來,實驗法的不確定性與盲目行動的不確定性是有區(qū)別的:“實驗法與所有行動中隨處可見的不確定性嘗試是有區(qū)別的”[1]94,“實驗法能夠?qū)⒉淮_定性的條件轉(zhuǎn)變?yōu)榭梢蕴岢龃_切問題的術語,即提出確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95,從而促使人們思考行動的路線以便找到問題的答案。
其二,實驗法以數(shù)據(jù)資料為依據(jù)。杜威強調(diào),“有意識進行的實驗是以數(shù)據(jù)資料為基礎的”[1]95,它“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將經(jīng)驗主義作為習俗的規(guī)則,反對權威主義,也反對個人自我主義(egoism),等等。但是,它又有著自己實證的內(nèi)容(positive content)”[1]95。實驗法強調(diào)以行動的結果作為標準,以檢驗行動之前人們提出的理念、概念和理論。杜威強調(diào)說,在未得到檢驗之前,“所有的理念、概念和理論,盡管其外延明確,邏輯前后一致,具有美學吸引力,但在未受到行動檢驗之前,都只能作為臨時性的接受。確切地說,在行動檢驗之前提出的理念意義僅僅在于作為可能的行動的指南和計劃。”[1]95
需要指出的是,杜威并不認為實驗法是教育哲學研究的唯一的方法(5)杜威沒有談論過教育哲學的其他研究方法,但據(jù)我國(大陸)學者的研究,杜威在教育哲學的研究中,采用過的方法有好幾種。例如,石中英教授認為,杜威教育哲學采用過現(xiàn)象學方法、發(fā)生學方法、概念分析的方法、辯證的方法、反省思維的方法等,但這些方法是石中英在其研究中分辨出來的,并不是杜威自己論述的可以用來研究教育哲學的方法。參見石中英:《杜威教育哲學論述的方法》,《教育學報》2017年第1期第3-8頁。。在杜威那里,教育哲學研究并不排斥其他方法,而且,教育哲學的實驗過程需要靈活應變。在他看來,進行教育哲學研究所做的實驗需要堅定不移的信心,但不能過于呆板不知變通。杜威對此說得很清楚:“在追求所選擇的行動中,它并不緊閉大門拒絕其他方法。……早在思想轉(zhuǎn)化為行動之前,人們已經(jīng)思考了一批可作為選擇的假設,這樣,當需要改變方向時,實踐就變得具有靈活性和重新適應性。堅定不移是需要的,為的是行動的后果可能具有適當?shù)慕逃齼r值,但是,不允許堅定不移變得呆板以至于最終宿命論地走向未受批判的結局。”[1]96
四、幾點啟示
在對杜威有關教育哲學的論述作了一番梳理之后,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四點結論,或者說可以獲得四點有益的啟示。
其一,教育哲學屬于實踐哲學。按照《中國教育大百科全書》的界定,教育哲學是“運用哲學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問題,或者從教育基本問題總結出哲學問題的一門學科”[10]。從這一界定看,教育哲學的實踐性是明顯的。我國也有學者認為,“教育哲學的實踐性是教育哲學的首要特征”[11]。就杜威的意見看,教育哲學與傳統(tǒng)的抽象的思辨性的形而上學哲學是不同的,教育哲學屬于實驗哲學(experimental philosophy)。換言之,教育哲學應該面向?qū)嶋H,在生活和教育之間架設一座聯(lián)系的橋梁。在杜威看來,教育哲學并不深奧,教育哲學探究的對象就是生活中的教育現(xiàn)象和問題,與闡釋教育現(xiàn)象和問題的教育理論無異。正是這樣一個原因,杜威才說:“如果我們愿意把教育看做塑造人們對于自然和人類的基本理智的和情感的傾向的過程,教育哲學甚至可以解釋為教育的一般理論。”[8]316
其二,教育哲學不可或缺,作用重大。人們常常發(fā)現(xiàn),在教育過程中,“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有時總不免給自己提出一些含有哲學意味的問題。教師總是想知道:‘我為什么教?我為什么教歷史?什么是最好的教學?’學生也問:‘我為什么學代數(shù)?我為什么無論如何要上學?’追根究底,這些問題就成了含有哲學意味的問題,就成了關于人和世界的本質(zhì),關于知識、價值和有道德的生活的問題。”[12]而要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非教育哲學不可。所謂“教育哲學不可或缺”是就此而言的。在當前的教育改革中,教育政策和舉措以及改革中遭遇的問題都需要用教育哲學去闡明其中的道理,要特別闡明為什么要朝這個方向而不朝那個方向前進,為什么要采取這樣的行動或舉措而不那樣的行動或舉措,從而指揮人們朝著理想的目標或正確的方向前進,還要用新的理念對舊的教育理念、教育政策和舉措加以改造與調(diào)整,以適應新時代社會發(fā)展和人的發(fā)展需要,體現(xiàn)教育哲學“指揮教育和改造教育”的作用。
其三,教育哲學既需要關注教育的基本問題,也需要關注教育的具體問題。根據(jù)前文所述,可以發(fā)現(xiàn),杜威的教育哲學既關注教育的基本問題或教育的根本問題,如教育是什么,教育的價值何在,教育目的是什么,什么是經(jīng)驗與思維,以及什么是教育即生長,等等;杜威的教育哲學也要接地氣,關注一些具體的教育問題,如“課程中的游戲和工作”“職業(yè)教育”問題,等等。這樣,教育哲學才能真正發(fā)揮“指揮教育和改造教育的作用”。
其四,教育哲學的實驗需要謹慎進行。杜威關于教育哲學所提出的“實驗不是盲目行動”的觀點是正確的。按照杜威的想法,教育實驗要有充分的準備(包括應變措施的準備),目標或目的明確,措施得當,條件許可。因為教育實驗不同于其他實驗,其他實驗失敗了可以重新再來,無非是時間、物質(zhì)和投入的精力方面的損失;而教育的實驗一旦失敗,損失無法彌補,因為教育實驗的失敗將犧牲一批兒童甚至一代兒童的發(fā)展,所謂“地誤誤一季,人誤誤一生”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教育實驗應該謹慎施行,應該將實驗結果的不確定性降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