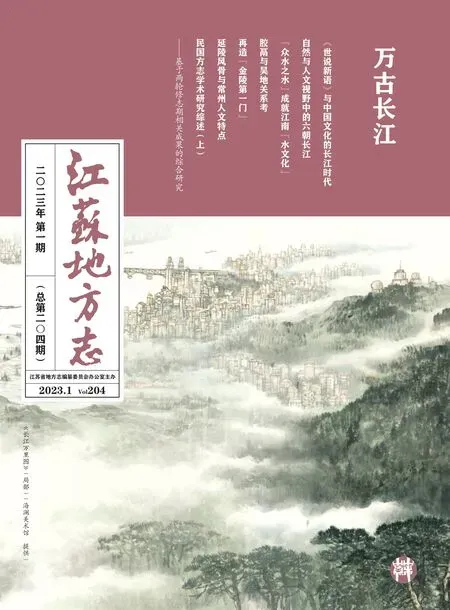大運河宿遷段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再認識
◎干有成
(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江蘇南京210023)
一部運河史,幾乎貫通整個宿遷城市史。宿遷是一座與大運河的歷史變遷始終相互依存的城市,大運河的千年演變,經歷了從“泗水行運”到“汴泗并流”,從“借黃行漕”到“避黃行運”,一直到近現代以來大運河的衰落與復興,宿遷均為大運河沿線的主航道城市,也讓宿遷成為擁有大運河三個歷史階段不同主航道遺產的城市。
一、宿遷大運河參與了中國古代漕運發展歷程
漕運是指中國古代中央政府將各地所征收的財物(主要是糧食)經水路(間有陸路)運往首都或其他指定地點的一種政府運輸行為。隋唐以后,伴隨著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東漸北移和經濟重心的逐步南移,漕運暢通與否關系到王朝的興衰,開鑿疏浚連結南北方重要交通運輸干線的大運河,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共識和奉行的基本國策。
宿遷作為中國古代漕運要道的歷史可追溯至先秦時期,《禹貢》中曾記載:“揚徐二州貢道浮于淮泗,則自邳宿而西,漕運之始也。”宿遷能夠見證漕運起始的原因在于大禹治水的古泗水因馬陵山脈的阻擋轉而南流入淮,在此穿境而過。這條古代中國重要的南北運道,勾連了東西流向的黃、沂、沭、濉、汴、淮等諸河,奠定了宿遷歷代處于南北水運交通要沖的區位優勢。公元605年,隋煬帝下令開鑿通濟渠,形成以洛陽為起點,涿州和余杭為終點的大運河,開啟了中國大運河的千年華章。隋煬帝開鑿的大運河,經今宿遷市泗洪縣青陽街道,從古泗州治所臨淮,注入淮河。唐宋時期,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東南漕運勃興,大運河作為黃金水道,支撐起了國家的漕運命脈,也讓宿遷開啟了以治水為主題的漫漫征程。在今宿遷市泗洪縣青陽街道至臨淮鎮還保留著一段古汴河遺跡,在古汴河邊上也發現了隋煬帝離宮舊址(在今泗洪縣青陽街道秦溝居委會)。
隋唐時期,在通濟渠(即汴河航道)漕運外,還有一條重要的航道—汴泗航道,該航道經徐州至今宿遷市宿城區轉而偏南,雖然航程較長,但一直通航。隋唐時期還多次疏鑿該航道,尤其是徐州洪、呂梁洪險段,使通航條件得以改善。當通濟渠漕運壓力過大或水運受阻時,朝廷往往取道汴泗航道。可以說,終唐之世,汴泗航道都是與汴河并行的重要航線。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的名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說的就是由汴水入泗水再入邗溝,到揚州江畔瓜洲渡口的航路。
北宋時期,通濟渠是王朝“國命”之所系。到宋真宗、宋仁宗時,汴河的歲運額高達800萬石[3],創造了中國漕運史上的最高紀錄。隨著南宋遷都杭州后,黃淮地區不再作為國家財賦重地,通濟渠缺乏管護,逐漸廢棄。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挖開黃河以擋金兵,黃河奪泗入淮,此后,宿遷自然環境及城市格局發生重大變遷,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宿遷由于地處泗水之濱,南依淮水,北鄰徐州,黃河多次大規模南泛入泗,宿遷首當其沖,成為黃泛沖擊的重災區。從最初的侵流、混流到最后的全流,黃河裹挾的大量泥沙逐漸使泗水原有河床日趨抬高,加之后期人為不斷筑堤防洪,導致泗水河道成為“地上懸河”,水患頻發,宿遷成為“洪水走廊”。

明末清初宿遷黃河北堤運口分布示意圖(干有成 制圖)
元初漕運,或從海路北上,或經淮揚運河(古邗溝)由淮水北溯泗水(黃河),經桃源(泗陽)、宿遷、徐州至山東轉陸運或海運,或由淮水經渦水入黃河,到中欒(今河南封丘縣境內)轉陸運再轉衛河水運。“海運多險”,兩條內河運輸,由淮溯泗最為便捷,但泗水本無堤防,且徐州至淮河的下游河段被黃河所奪,已淤墊百余年,幾為平陸。元至元十二年(1275),元世祖在興兵伐宋的同時,即命都水監郭守敬勘察、設計運河,同時命整修泗水(黃河)下游。泗水下游經無數民夫7年的整修,河床浚深,堤岸高聳。隨著會通河的開通,南漕由淮入泗,經徐州北上,在宿遷境內“借黃行運”,漕運河道在宿遷境內有121公里。
“一寸不通,萬丈無功”,明清時期宿遷因地處漕運咽喉地位,而成為河工頻仍的治河重地。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馴采用束水攻沙法,讓黃河歸于一泓,在黃河兩岸修筑遙、縷二堤,促使黃河行運安流數十年。到了明末清初,為了避開徐州、呂梁二洪黃河險段,先后在宿遷境內的黃河北堤開直河口、董口、陳口、皂河口、支河口、駱馬湖口等運口,漕船從宿遷黃河運口北上接入泇河,宿遷也因此成為明清黃河沿線運口最多的地區,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七省的漕運貢賦都要從宿遷運口北上泇河,甚至宿遷以北的徐淮二幫漕船也要沿著黃河南下從十字河入運,充分顯示了宿遷的漕運咽喉地位。
明末,為了防止駱馬湖湖水盛漲沖決黃河堤防,妨礙運道,總督漕運史可法指揮人工切嶺馬陵山,在馬陵山斷麓形成攔馬河,用以泄駱馬湖漲水。清康熙年間,河道總督靳輔自支河口向東開河,接攔馬河,又從攔馬河向南利用黃河遙、縷二堤之間開中河,形成了泇河、皂河、支河、中河相連的渠道型運道,最終實現了“黃運分立”的目的,避開了黃河一百八十里波濤之險,使得漕運安流,商民利濟。歷史上稱贊靳輔開中河:“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為國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浦下。”[2-3]
清中葉以后,由于黃河奪淮日久,中河墊高,河身淺阻,中泓如線,漕船膠柱,形勢每況愈下。至清道光四年(1824),因中河漕運阻斷,北京糧荒嚴重,一年多無解。次年,道光皇帝情急之下,決定招商海運。咸豐五年(1855),黃河自銅瓦廂決口,改道北徙,沖斷山東運河,中運河也枯竭淺阻,漕運有名無實,南方漕糧多靠海運。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令:“自本年始,直省河運海運,一律改征折色……”[4],至此,漕運完全廢除。
二、明清時期宿遷是大運河沿線“保漕濟運”的樞紐地區
明清時期宿遷成為“七省漕渠咽喉”,系“扼兩京咽喉”的漕運重地。在交通區位上,宿遷是運河水路交通和通京大道陸路交通的交匯之地,江淮一帶“四方之貢賦舟車達京師”,多由運河或通京大道行運,宿遷為其必經。〔萬歷〕《宿遷縣志》稱宿遷“北瞰泰岳,南控江淮,西襟大河,東連渤海,蓋兩京之咽喉,全齊之門戶也。”〔康熙〕《宿遷縣志》記載宿遷:“西望彭城,東連海澨,南引清口,北接沭沂,蓋淮揚之上游,誠全齊之門戶,七省漕渠咽喉命脈所系,尤匪細也。”〔嘉慶〕《宿遷縣志》稱宿遷:“北帶漕渠,西襟黃水,東臨榆沭,南引清口,淮海上游,水陸沖要。”
同時宿遷段在運河治理方面也有著獨特地位。明末,淮安至徐州段黃河運道常常決口淤墊,漕船不行,且呂梁和徐州二洪是有名的險段。黃河與會通河交叉口的茶城一帶經常淤積,極為影響航道通暢。此外,黃河善淤善決,經常決口改道,導致徐州以下運道常斷流不能通航。萬歷三十一年(1603),總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李化龍再次提出開挖泇河通運,深得萬歷皇帝的贊成,并受命即刻集中力量開工,由夏鎮南李家口引水,合彭河經韓莊湖口至泇口,又合氶(今嶧城大沙河)、泇、沂諸水,出邳州直河口接入黃河。運道由此大通,漕運狀況得到改善。直河口淤塞后,明末還開通宿遷通濟新河和順濟河,由黃河經駱馬湖口北上接泇河。
到了清初,運河借用黃河泛道作航線的僅有駱馬湖口至淮陰120公里,運河隱患多集中在泇河入黃口和淮陰的黃、淮、運交匯口上。康熙十九年(1680),河道總督靳輔以原直河口與董溝口之間開皂河口通黃河,由皂河口向西北偏西開河至窯灣接泇河,并組織筑堤,建萬莊、馬莊、貓兒窩減水閘3座。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皂河口淤墊,靳輔在皂河以東、黃河北側、駱馬湖南側挑浚支河,歷龍岡岔路口至張莊,長10余公里,使清水至張莊出黃河,是為張莊運口,一名支河口。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于支河口之南,隨河勢筑大堤10余公里,于是運舟常通,新開支河無淤墊之患。
自泇河與皂河開通后,黃運分立,宿遷以下至清口的運道仍然利用黃河行運。漕船重運溯黃河而上,每船須雇纖夫二三十名,花費甚大,為此,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686—1688),靳輔又在宿遷、桃源、清河三縣黃河北岸堤內開新河,稱為“中河”。再在清河西仲家莊建閘,引攔馬河減水壩所泄的水入中河。該河上接張莊口及駱馬湖清水,下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入平旺河達海。漕船初出清口浮于河,至張莊運口。后在中運河上建設了利運閘、亨濟閘、匯澤閘和瀠流閘,用來蓄水濟運,解決水位高差的問題。
中河開通后,雍正五年(1727)河道總督齊蘇勒建宿遷縣駱馬湖尾閭5壩,壩在西寧橋迤西,系三合土壩,5壩各長20余丈至30余丈不等,壩上各挑引河,堤埂相湮,南接黃河縷堤,北屬馬陵山,共長600丈,相機啟閉,以資蓄泄。又于駱馬湖口竹絡壩口門外筑鉗口壩,及汰黃堤,堵閉十字河通湖北口(今宿遷境內)。雍正、乾隆年間,在十字河以西修建了通駱馬湖和中河的王家溝和柳園頭石閘,并挑引河,用以宣泄駱馬湖的湖水濟運。至此,駱馬湖成為濟運水柜。每當運河水漲,則自王家溝、柳園頭閘放水入駱馬湖,由尾閭五壩減水入六塘河,一旦漕運重船起運,則堵閉尾閭5壩,放駱馬湖水至運河濟運。乾隆皇帝曾專門寫了一首《駱馬湖》詩:“濟運輸天庾,防霖安地行。相機資蓄泄,惟謹度虧盈”。表達了對駱馬湖濟運功能的贊譽。
清康乾時期,治河者逐步完善駱馬湖以西及以南的黃、運、湖沿線的復雜堤防系統,改變了駱馬湖與黃河直接的局面,避免了黃河對運河及駱馬湖的侵擾。尤其是駱馬湖、運河、黃河之間相互蓄泄的保漕濟運工程體系,客觀上在宿遷縣城東北部形成了一個人工開鑿修筑的,包含減水、濟運、切嶺、閘、涵、堤、壩、志樁、稅關、水神廟等綜合性漕運遺產樞紐區,這個位于中河之首的樞紐工程,在靳輔治理中河策略中地位突出,他認為中河治理應“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為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5],皂河至井頭地區的運河工程體系,就是其中之“首”,與中河之尾的清口樞紐同樣重要。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對此處河工都有指畫,河臣遵守不敢更改。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更如是,每有堵口、筑壩、修橋建閘等大工,多親自過問并派欽差監督。河臣守此一線,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決則堵,淤則浚,不惜人力物力。
清代早期,黃河徐州以下還是作為漕運通道使用,在中河疏通之后,徐州鎮口閘黃河故道淤塞,徐淮二幫漕船于徐州水次受兌,即由黃河至宿遷的十字河竹絡壩入中運河,在康乾時期通行無滯達數十年,十字河的竹絡壩就成了黃運兩河之關鍵,或以濟運,或以泄黃,互相資藉,而且徐、淮漕商民船只,皆就近由此出入,以省繞道轉口之煩,很有裨益。后來,由于河臣高斌在十字河南北分別建筑了臨黃、臨運二壩,筑后連年堵閉,水為壩遏,不能通暢,沙停淤積,上下閉塞,涓滴不流,導致漕船重運無法從黃河入運河,所有徐淮兩幫漕船均由徐州經黃河行駛至楊家莊轉口入運。此后,十字河雖然不再行走重運船只,但可行回空漕船。此外,若是清水過弱,則暫啟竹絡壩,引黃以助清濟運,若遇黃水過盛,宿遷以下工程險要,亦暫啟此壩,以泄黃漲,更遇清強黃弱之時,又得藉以泄清,以固下游中河一帶工程,閉于常以守其經,啟于暫以行其權,得以相濟為用。
通過明末清初的一系列治水工程的實施,駱馬湖南側黃、運、湖交界的地區,成為大運河沿線一個重要的治河保運的樞紐,再加上六塘河、劉老澗等關系到中運河蓄泄的系統性治運水工實施,宿遷成為保漕濟運的咽喉要地,也是付出犧牲和負擔河工最重的地區。
三、大運河深刻影響了宿遷地區的發展變遷
在宋元黃河奪泗入淮以前,泗水的常年行運和通濟渠的開鑿行運,促進了宿遷地區的開發和城鎮的繁榮。春秋時期,宿遷境內的泗水河畔有厹猶、鐘吾和徐等方國,其中徐國的范圍為今淮、泗一帶,國都建在今宿遷泗洪境內的大徐城。徐國不但創造了燦爛的青銅文明,并支持陳(國都在今河南淮陽)、蔡(國都在今河南上蔡)兩國開挖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人工運河—陳蔡運河。《水經·濟水注》中記載“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說的就是這一歷史事件,陳蔡運河與淮水、泗水共同構成了江淮平原上最早的水上運輸交通網絡。
秦國統一天下后,在宿遷建立下相縣,下相縣城位于古濉河與泗水交匯之處,因其水路交通的重要區位,成為一座重要城池。西楚霸王項羽就是下相人。由于泗水行運的便利性,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封常山憲王之子劉商為泗水王,統凌、泗陽、于三縣,凌城為王國首邑,轄2.52萬戶,人口11.9萬,其范圍相當于現在宿遷市泗陽縣、宿豫區的一部分及淮安市淮陰區部分地區。[6-7]唐代,由運河漕運而來的江南財賦支撐著唐帝國的存續。由于運河,淮泗流域的經濟、文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唐玄宗曰:“大河南北,人戶殷繁,衣食之原,租賦尤廣”。其中的“河南”就是淮河流域包含宿遷的淮北地區。唐人又說,天寶以后,“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極言江淮地區經濟的重要地位。北宋年間,政府在淮泗流域宿遷境內采取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鼓勵墾殖,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漕運、鹽運得到進一步發展。在農業上引進推廣“占城稻”,連年豐收,“紅稻白魚飽兒女”是這一時期的生動寫照。可以說,得益于淮泗水系的滋養,以及運河動脈的聯通,當時的宿遷是不折不扣的魚米之鄉。
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挖開黃河以擋金兵,黃河奪泗入淮,此后,宿遷自然環境及城市格局發生重大變遷,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宿遷由于地處泗水之濱,南依淮水,北鄰徐州,黃河多次大規模南泛入泗,宿遷首當其沖,成為黃泛沖擊的重災區。從最初的侵流、混流到最后的全流,黃河裹挾的大量泥沙逐漸使泗水原有河床日趨抬高,加之后期人為不斷筑堤防洪,導致泗水河道成為“地上懸河”,水患頻發,宿遷成為“洪水走廊”。據民國《宿遷縣志》載“自南宋以來的八百年間,水勢橫潰,河湖無涯,無歲不受患”。
黃河長期奪泗奪淮,使宿遷地區原始地形地貌以及河流湖泊等自然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洪水帶來的大量泥沙,淹沒了城鎮鄉村,將一座“山城”宿遷,淤沒成為平陸,當代地質鉆探資料也表明,以今宿遷馬陵公園為軸心,除其北部未見黃泛土層外,其余東、南、西三面均被黃泛土覆蓋,最厚處達40米,最淺處近10米。可見黃河過去在宿遷大地肆虐的程度,其無數次地泛濫和淤積,基本重塑了宿遷的地形地貌。如淮水、泗水、濉水、沭水、沂水等主要河流水系被打破,駱馬湖、埠子湖、白鹿湖、倉基湖等眾多湖泊被淤塞或積為平陸,原始植被也遭到破壞,土壤急劇沙化及鹽堿化等。黃河的頻繁決口更對宿遷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造成長期而深遠的影響。水利設施遭到破壞,良田不斷退化荒蕪,農業生產水平出現急劇倒退,致使“稻作為主”逐漸被“旱作為主”取代。宿遷人民也由此陷入災難之中,洪水所到之處,田廬飄蕩,村落成墟,人畜溺死無數,人民生活極為貧困而流民四起,賣兒鬻女隨處可見,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慘烈景象。明宿遷人張忭曾作《哀宿口號》律詩四首,其一:“流民連歲不堪圖,尤是今年景象殊。樹已無皮猶聚剝,草如有種敢嫌枯?插標賣子成人市,帶鎖辭年泣鬼途……”就真實反映了當時宿遷人民所遭受的沉重災難。與此同時,宿遷歷史上多座城池也因洪水泛濫沖圮而多次遷址,眾多古城古鎮今仍深埋在黃沙或河湖之下,歷史遺存遺跡也大多深埋地下而遺蹤難尋,民家屋舍被淹被毀更是不計其數。即便在1855年黃河北徙后,黃河“奪泗入淮”的遺患還持續影響著宿遷地區,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仍難以從根本上改變易旱易澇、多災低產的農業生產面貌和貧窮落后、經濟欠發達的狀況。但與明清以來黃河泛濫造成的地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相比,由于連年不斷的保漕舉措,宿遷在大運河沿線仍處于重要地位。如為管理運河各項事務,清代還在宿遷境內設立了運河同知、運河通判、中河縣丞、運河主簿等官員。
大運河帶來的交通地位的提升,對宿遷地方經濟的發展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特別是自從明嘉靖年間規定“準許漕船捎帶貨物兩成自由于沿途販賣,并允許沿途招攬貨源代客運輸”之后,宿遷水陸交通沿線的碼頭、集鎮,生意更加興隆。借助漕運的便利,一些從南方捎來的竹木器家具、綢緞、瓷器、茶葉等,從北方帶回的陶器、山貨、烤煙等大宗貨物往來貿易,在宿遷城及沿河集鎮銷售,或再取陸路轉銷附近各地,商業十分興旺。在清代中河開鑿以后,除漕糧和商品貨物運輸外,還有鹽業運輸。據《淮陰風土記》記載,清代淮安府屬八州縣食鹽2.771萬引(每引約為200市斤),其中宿遷銷鹽6240引,每年這些食鹽多從中河轉運而來,行銷縣域各地。此外,還有一條早在宋代就有鹽運記載的原鹽河(后改稱六塘河),在清雍正九年(1731)也經過一番疏浚,“于廟頭灣挑引河一道長613丈導水東注”而再度成為“宿(遷)、桃(源)、安(東)、清(河)、海(州)、沭(陽)六州縣之通川,直達東海”。“鹽艘資以浮運……商民運載鹽鹵,有沂(溯)六塘河至宿賈售者”甚多,是為宿遷當時通商運鹽的另一水上運道。
清康熙以前,黃河以北的大運河借河行漕,迂緩難行,非常危險,斷纜沉舟事故經常發生。因此,商人行旅凡是由南向北的,一般都是到清江浦石碼頭舍舟登陸,北渡黃河,到王家營換乘車馬。由北向南者,則到王家營棄車馬渡黃河,至石碼頭登舟揚帆。所以,石碼頭、王家營為“南船北馬”的交會之地。康熙二十七年(1688)宿遷中運河開通后,“南船北馬”交會之地由淮安北移宿遷順河集,乾隆南巡時,也是從通京大道至順河集下馬,轉水路,回京也是自順河集水路轉陸路。可以說,明清時期“南船北馬”的機關設在淮安,但運河水利工程都在宿遷段。

1702年運河圖中的宿遷段(美國國會圖書館 藏)
運河的流經帶來了南北客商和便利的運輸條件,極大地刺激了宿遷運河沿岸城鎮商品經濟的發展。〔萬歷〕《宿遷縣志》記載宿遷舊治有迎恩街、皇華街、新街、安福市、興福市以及梧桐、思政、敦信、岱宗祠、廣濟等巷。宿遷新縣治相比舊治街道數量有了明顯增加。〔萬歷〕《宿遷縣志》記載宿遷新縣治有平成街、宣仁街、聚秀街、云露街、太平街、通云街、永寧街、奠安街、長樂街、三元街、河清街、駐騘街、通岱街、還定街14條街道。鎮集則有劉馬莊鎮、堰頭鎮、邵店鎮、司吾鎮、小河口鎮、白洋河鎮、脫車頭鎮、歸仁集、仰化集等。民國《宿遷縣志》記載宿遷城內有宣仁、平城、云露、太平、聚秀、通云、奠安、永寧、長樂、三元、河清、駐騘、通岱、還定、馬路口、馬路口東、竹竿、富貴、如意、新盛等街,思政、梧桐、烈節、敦信、廣濟、豬市、吉慶、九曲等巷,市有草市、魚市等。宿遷周邊有新安、堰頭、司吾、橋北、邵店、窯灣、小河口、白洋河、皂河等鎮,集有歸仁集、仰化集、永慶集、耿車集、埠子集、街頭集、港頭集、王兒莊集、新店集、大興集、曉店集、蔡家集、新安集、永豐集、葉家集、唐店集、韓家集、黑墩集、李圩集、大墩集、南澗集、臧圩集、北澗集等。
運河的流經使得宿遷成為南北客商云集之地,外地商人在宿遷城內創建了眾多商業會館。民國《宿遷縣志》記載閩中會館,即天后宮,在新盛街。浙江會館在迎熏門外河清街,京江會館在洋河鎮西大街。涇縣會館在通岱街南,同治十三年(1874)建。蘇州會館即中天王廟,在前馬路口。廬揚鎮公所,又名江安公所,在前馬路口東。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山東,蘇北黃、運河道逐漸淤廢,宿遷商品經濟也迅速走向衰落。民國《宿遷縣志》記載:“當漕河全盛之日,歲有修防,蠅集蟻附,挽輸所至,百貨充盈,末技游食之民謀升斗為活。及時移勢異,徒噪空倉,私貨競趨,官征無億,轉徙日眾,莫之或拯也。”
四、大運河文化是宿遷城市文化的核心內涵
宿遷大運河匯集東西,交融南北,以汴河、古黃河、中運河、駱馬湖、六塘河、劉老澗、歸仁河、砂礓河、柴米河等為主體的運河水系,在此沉淀下了豐富多彩的文化遺存,構成了宿遷市文化遺產中體量最大、等級最高、范圍最廣的文化資源。由于宿遷運河水系具有全域性的特點,在以河道為文明源頭的背景下,伴生了眾多城鎮、村落、非物質文化遺產、人物、故事、文獻記載等文化內涵。總結宿遷大運河歷史發展的脈絡,可以見證宿遷人民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學精神,不畏艱險、久久為功的拼搏精神和無怨無悔、甘于奉獻的犧牲精神,古老的運河已經深深浸入城市肌理,融入人們記憶,植入城市文化百態。
在物質遺產層面,大運河淮北段歷史上經歷了泗水行運、汴泗并流、借黃行漕、避黃行運、運河廢棄與重新疏浚通航等數次變遷,留下了隋唐大運河遺存的古汴河宿遷段(33公里)、元明時期大運河的古黃河宿遷段(114.3公里,流域面積296.9平方公里)以及清初開鑿的中運河宿遷段(112公里)三條大運河遺存。其中,中運河宿遷段41公里和皂河龍王廟作為“一點一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其他與大運河息息相關的文化遺存則不勝枚舉,僅2016年水文化遺產調查結果顯示,工程建筑類遺產就有112處,涵蓋了大運河全部遺產類型。從歷史文獻和現場調查結果看,宿遷三條不同時期運河遺產的兩岸還有大量的運河文化遺存有待挖掘保護和傳承利用,如瀠流閘的遺存、古黃河堤壩、中河堤壩、六塘河堤壩、劉老澗遺跡、皂河遺跡、支口河遺跡、十字河遺跡、駱馬湖尾閭五壩、歸仁堤、皂河汛衙門、九龍廟遺址、隋煬帝離宮遺跡、乾隆行宮遺址、運河驛站、御碼頭遺址、大王廟遺址、御碑亭遺址等運河遺產。
此外,從漢代泗水國王劉賀設立千釀酒坊始,宿遷洋河美酒便與運河結下不解之緣,造就了宿遷酒文化的標簽。乾隆六下江南,特點飲洋河酒,并留下“酒味香醇,真佳酒也”的贊譽。處于京杭大運河沿線的皂河古鎮,早在明末清初就已是一處繁華熱鬧的集鎮,而其中的陳家大院就是當年的富商宅邸。乾隆六下江南,五次留宿皂河,按照皇家建筑的規格修建龍王廟,被稱為“乾隆行宮”,有“小故宮”的美譽,這為宿遷帶來了帝王文化。設立于中運河岸邊的東關口,歷史上是宿遷水路運輸的主要碼頭和進出口貨物集散地,也使宿遷成為連接華東華北水陸商貿的聚集中心。清代,閩商在這里留下媽祖文廟和泗陽天后宮,雕梁畫棟,磚雕石刻,小瓦飛檐,成為宿遷別樣的風景,給宿遷平添了多彩的建筑文化。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由于大運河的暢通,促進了外來文化與宿遷本土文化的交融共生,如安徽北部淮北平原上的泗州戲、山東南部和河南東部的柳琴戲,與宿遷戲曲相互融合,形成了流傳百年的淮海戲等。此外,黃水泛濫和保漕濟運使宿遷人民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治水過程,其間涌現出許多杰出的治水名賢,有倡導“遏制北流、分水南下入淮”的劉大夏;“束水攻沙法”“蓄清刷黃”的潘季馴以及殫精竭慮、治水有功的靳輔和陳潢等。在宿遷運河治理的歷史上,常常看到萬人治河的記載,宿遷人在治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顧全大局、犧牲奉獻、艱苦奮斗、追求幸福的精神,是留給后人的重要精神遺產,是當代弘揚運河文化的重要內涵,也是宿遷城市文化建設的核心內涵。
對于宿遷而言,今天的大運河不僅僅是一條河流,更是一個流淌的文化符號,一種悠久的精神象征。宿遷人民的溝通、融合,治河的堅韌、創新,在這里形成了兼收并蓄、開放包容的宿遷運河精神。如今,大運河成功申遺及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戰略的提出,賦予了大運河宿遷段新內涵,宿遷將以文化為魂,以生態為底,推動運河灣城市文化公園建設,以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和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形塑宿遷新城未來的發展格局和城市品質,繼續展現出它脈動世界的文化魅力,讓更多的人去觸摸大運河所承載的中華文脈,感受大運河宿遷段獨特無雙的古今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