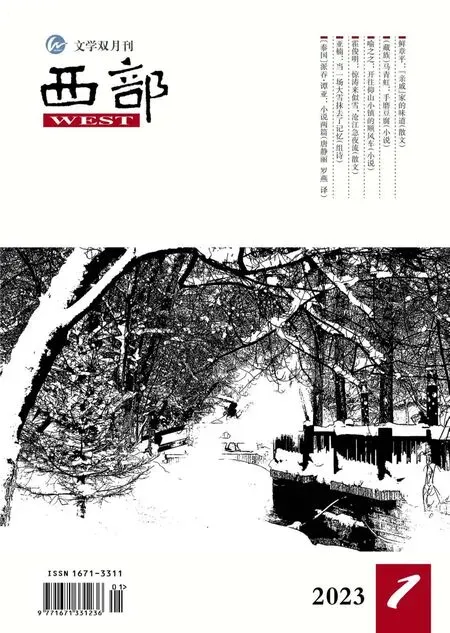途中的跋涉者(組詩)
麥豆
飛鳥飛過河面
飛鳥飛過河面
倒映出它的影子
永恒的身影
一閃而過
它在世界里飛
偶爾被看見
給予愉悅
但從不給予理解
途中的漫步者
在房子里,你也許會想
窗外還是冬天
因為房間昏暗
午休時分昏暗不明
但從你推開門
呼吸第一口空氣開始
世界就在改變你
你把自己交給世界
世界會告訴你
沿途的蠟梅正在盛開
金黃的蠟梅
無需語言
只要你站在它的面前
靜靜觀看
或者閉上眼睛
什么也不想
語言是什么
有時,你會覺得
世界并不說話
但世界的意思
你都能明白
那么,真正的
語言是什么
它必是一個
沉默的世界
眼前的喜鵲
如果它們只是喜鵲
字典里的喜鵲
甚至記憶中
童年的喜鵲
它就不可能是
在冷風中吹的喜鵲
眼前的這一只
站在樹枝上鳴叫
鳴叫即心靈在自語
即它是孤獨的、現實的
沒有同類的
擁有語言的這一只
雪
天空在飄雪
時斷時續
早晨,上班路上
它就在飄
中午,散步途中
它仍在
若有若無地飄
冷風中,我想
深夜,它應該會停
或者,它只飄落
在自己的世界里
嬰兒
他有一雙眼睛
我注意到他
只盯了我一眼
便迅速離開
繼續尋找
對一個新世界
而言,人類
再普通不過了
一生,或瞬間
有一天,我
突然發現
紅色的樹在蛻皮
具體哪一天,我忘了
事實上,人不需要
完整的一生
有那么幾個瞬間
就足夠了
表演
午飯后散步
這是什么表演
如果是,它的觀眾又是誰
觀眾是否也感到厭煩……
新開的桂花
讓我停下腳步
凋零的桂花樹
再次讓我停下腳步
沿途盡是詞語
走在路上
像對著觀眾朗誦
一本詩集的一些句子
12月14日,初雪
是這樣一個時刻,打開清晨的窗戶
記憶已是夢的一部分
飛鳥劃過屋脊,它不是飛鳥,是寒風中的
一片樹葉。太陽照著藍色的雪
陽光不再刺眼,兔子在雪上
留下一行清晰的腳印,沒有兔子
全村人站在一條河的河面上聊天,跺腳
不用擔心冰層碎裂
河水弄濕棉鞋
時間讓它們統統淪為夢境
在夢里,兔子開口說話,求饒獵人
放它一命,麻雀成排
站在電線上,一聲槍響,將它們全部驚散
我們鉆開厚厚的冰面
另一種以捕魚為生值得同情的動物
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時刻,雪后的窗戶里
只有我,鐵柵欄,覆蓋
薄雪的屋脊
飛鳥,兔子腳印,藍色的光,濕透的棉鞋
記憶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它們已連同夢,在太陽升起之后
消失得無影無蹤
加固河堤的挖掘機
河邊的挖掘機
讓我想到青年時代的父親
它們在挖土
將土從土中挖出
在土中挖出一條又長又深的坑道
供人類在坑道中施工
或者,它們將一根根長長的
涂滿黑色瀝青的松木
在人的牽引下
用它刨土的鐵斗
將松木用力壓進岸邊的淤泥里
它在加固一條蒼老的河流
它們埋頭干活,盡管它們從不咳嗽
也不會突然沒有力氣
但它們仍然讓我想起青年時代的父親
一身蠻力,像極了陷在泥水中
舉步維艱的父親
在一條河的岸邊,在記憶中
那塊栽種棉花的土地上
艱難地挖掘著……
雨季已過,危險的汛期
已過,它們在勞作
提防下一個雨季的到來
尊嚴或活著
冬天,大雪紛飛之際
我再次凝視窗外的世界
大雪紛飛的世界里
活著的意義再次被我深思
那些在寒冷中呼吸的生命
應該有尊嚴地活著
否則,只有死亡
配得上一個皚皚白雪的世界
遙遠的生活
有人將喝干凈的果凍袋子
吹了口氣,扔在路邊的
自行車籃子里
我知道它是空的
有人將正在腐爛的橘子扔掉
我知道它們其中有橘瓣
仍然甘甜
有人將啤酒瓶故意敲碎
扔在河岸上
但我知道,日子艱難的時候
碎玻璃也可以
撿起來,裝進綠色蛇皮袋
背到廢品收購站賣錢
遙遠的生活中發生過一些難堪的事情
但它們的真實使我更加富有
路旁的柵欄
路邊的柵欄是路的一部分
站在路的兩旁
規定著路的寬度
它同時也是我們的一部分
隨身攜帶
不可翻越
它在確認
也在懷疑
我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