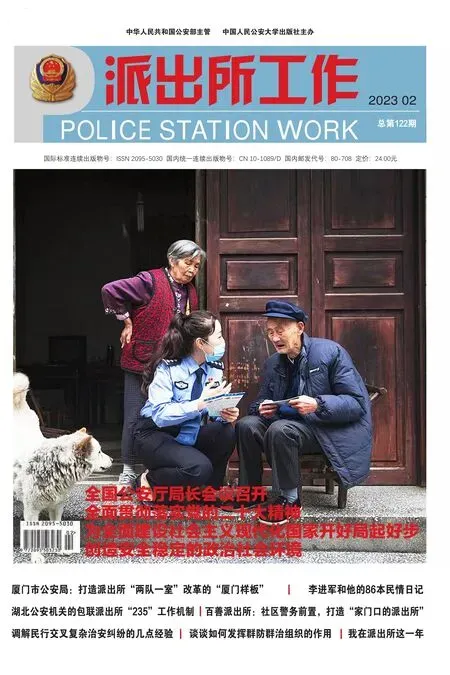如何加強民警在“最小作戰單元”下的語言控制能力
文/朱君杰
“最小作戰單元”是公安部部署的2019年至2022年“全警實戰大練兵”活動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各地公安機關通過“最小作戰單元”現場處置專項訓練,進一步提高了基層派出所民警隊伍的戰斗力,民警的快速反應能力和應對突發事件的處置能力都得到了高質量提升。但是筆者在調研中也發現,在模擬執法場景或是真實情境下,民警的語言控制能力還稍顯薄弱,對于法言法語的掌握還需要系統加強。在此,筆者結合“最小作戰單元”實訓及多年從警經歷,就如何進一步加強基層民警在“最小作戰單元”下的語言控制能力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最小作戰單元”的概念
“最小作戰單元”這一概念最早被提出來,其基本含義是從派出所勤務模式考慮,將社區防控、治安打擊、巡邏駐守等戰斗實體整合為一個整體的“作戰單元”,從而有效打破社區、治安、巡邏的警種界限,使基層公安機關的打擊和防控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但是近年來,在社會矛盾、暴力恐怖以及個人極端事件的風險挑戰下,從2015年開始,這個以基層勤務模式為主的“作戰單元”開始向應急處突實戰模式轉變。目前,“最小作戰單元”的戰斗小組一般是由2人至5人組成,2人一般指的是先期處置力量,5人指的是待后續增援力量到場之后形成的“最小作戰單元”。該作戰單元以“第一時間快速反應、第一時間現場處置”為目標,通過現場指揮、語言控制、戰術協同、徒手防控、警械武器使用、輿情應對、證據固定等方式完成現場處置任務,從而達到最大效果保護救助群眾的目的,進一步提升群眾安全感。然而,筆者在模擬和實際執法環境中也發現,戰術意識、警械使用和團隊協作等都可以通過反復訓練有效改進,但部分民警的語言控制能力因各種因素提升緩慢。而良好的現場執法語言控制能力正是一線執法民警所亟需提高的。只有切實提高現場執法語言控制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最小作戰單元”的戰斗力。
二、加強語言控制的重要意義
語言控制是指人民警察在依法處置各項任務過程中,使用口頭語言要求、命令或者責令執法相對人作出某一具體行為的控制方法。語言控制是執法過程中用到最多的控制方式,不僅表現在口頭制止違法犯罪,也貫穿了徒手控制、警械使用、武力壓制、控制帶離等執法環節全過程。常見的語言控制有“我是警察,請停止你的違法行為”“警察,不許動,放下武器”“你的行為已涉嫌違法,現對你進行口頭傳喚”等。語言控制是警務技戰術運用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執法程序的需要。
具有良好語言控制能力的民警,能夠有效控制現場人員和局面,及時制止違法犯罪,繼而對后續的戰術協同、輿情應對、證據固定等帶來優勢條件。而未受過專業訓練的民警在進入執法場景后,會產生緊張應急反應,導致心跳加快、肌肉緊張、思維混亂等問題。
以下舉兩個例子:一是2021年某日,某地派出所接報一起債務糾紛警情,2名民警帶好單警裝備和執法記錄儀迅速趕往現場。因經濟債務情況較為復雜且現場人員眾多,現場隨時有失控的可能,但處警民警未及時匯報請求支援。后在糾紛當事人發生肢體沖突之時,民警未采取合理有效的制止措施,而是直接摟抱當事人脖子進行徒手控制。圍觀群眾進行拍攝之時,一名民警將群眾的手機甩到了地上,并警告圍觀群眾不準拍攝。隨后現場出現混亂,引發了小范圍的群體性事件,民警工作處于非常被動的局面。二是2022年某天夜間,某派出所接報一起噪音擾民警情,1名民警攜帶出警裝備并帶領1名輔警前往現場。經向報警人了解,系樓上患有精神障礙的住戶在家敲東西,報警人求助警方解決。民警經現場評估,樓上住戶雖為精神障礙患者,但當時并未發出任何噪音,因此思想上并未引起足夠重視,也未和社區民警進行溝通了解。在與輔警就戰術與配合進行簡單部署后,民警準備上樓進一步了解情況。到達樓上住戶門口之時,發現大門為虛掩狀態,向內詢問卻無人應答。民警和輔警一前一后直接進門,在進入到臥室門口處之時,房內突然有一人手持菜刀奪門而出。民警本能地伸手去擋,手臂被刀砍傷。后經激烈搏斗,持刀男子被制服,但民警和輔警均不同程度受傷,被緊急送醫搶救后脫離生命危險。另經司法鑒定,認定該持刀男子事發當時處于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狀態,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
由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看出,在執法執勤中,具有良好的語言溝通能力可以更好地保護自身、把控現場、高效處置案事件,既能確保執法對象的合法權益,彰顯法律的公平與威嚴,又能取得良好的社會輿論效果。也就是說,語言溝通能力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公安機關的執法質量和執法形象。
三、“最小作戰單元”中語言控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最小作戰單元”警情現場處置中,民警要根據不同警情的特點,清楚地告知當事人該做什么和怎么做,以及一旦不聽從警方指令將承擔何種法律后果。這是語言控制最直接的外在表現。在實際執法過程中,“最小作戰單元”民警語言控制能力方面存在的常見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1.法言法語運用水平較低。語言控制能力的高低反映了民警對法律知識掌握的熟練程度。部分基層派出所民警對于法律規定的基本條款和必要措施一知半解,導致在執法現場不懂如何運用法律武器開展工作,對于執法對象的質疑無法進行專業解答,只能想當然地使用口語化語言簡單處理,甚至當場大腦空白,脫口而出“這事不歸我管”“這事找警察沒用”“你愛找誰找誰去”等不負責任、有損警察形象的言語,導致發生執法錯誤或者受到投訴。
2.語言組織表達能力不強。“最小作戰單元”講究的是警員之間語言配合、協同作戰。部分民警沒有接受過執法語言訓練,不善于語言控制和言語溝通,一方面對報警人、當事人、見證人等無法有效開展現場執法工作;另一方面也造成隊員之間溝通存在障礙,上級部門無法對現場形勢進行綜合研判。筆者剛接觸“最小作戰單元”實訓之時,和隊友之間經常在盤查、控制、媒體應對、傷者救助等環節出現語塞,頭腦里明明知道想要表達的意思甚至執法語言,但就是話到嘴邊開不了口。說到底還是由于實訓較少,沒有形成熟練的、條件反射式的反應。
3.對警務用語重視程度不夠。在各級舉辦的培訓班或是大練兵活動中,部分民警對警務體技能方面的重視程度遠高于群眾基礎工作這門課程,對法言法語、執法口徑看過算過、聽過算過,思想上仍然存在憑積累的工作經驗口語化執法就完全可以應付的想法。這種不夠重視、盲目自信的態度必然會影響“最小作戰單元”語言控制能力的有效提升。
四、加強“最小作戰單元”語言控制能力的幾點建議
專業規范的語言控制以及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有利于提高“最小作戰單元”民警的執法水平,也有助于為圓滿完成警情處置奠定基礎。
1.提高民警思想認識,樹立“規范化”執法理念。各級公安機關特別是基層公安機關要從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法理念的高度,不斷提升“最小作戰單元”民警的法律素養,促使其徹底摒棄“憑吃老本辦案、憑經驗辦案、憑感覺辦案”的錯誤思想,著力強化規范意識、證據意識和程序意識,規范警務用語,切實確保執法權力始終在法治軌道內規范運行。
2.強化警情專項培訓,提升“專業化”處置水平。警情處置過程中,情況可能錯綜復雜或者瞬息萬變,時時刻刻考驗著“最小作戰單元”的現場應變能力。而現場應變能力則取決于警情處置經驗的積累和總結。處置民警要在最短的時間迅速判明現場警情類別,從而利用語言控制把握整個處警環節。筆者將警情區分為兩大類:常見多發警情和重大突發警情。常見多發警情,即一般民事、治安和刑事警情;重大突發警情,即暴恐和個人極端警情。通過對常見多發警情和重大突發警情的分析得出,整個處置流程可以分為處置前、處置中、處置后三個階段。在對三個階段的模擬場景加入真實實戰案例形成詳細腳本,經過多次、反復且重點訓練之后,比如:執法相對人不配合、現場情況復雜、現場有人員受傷、有媒體和群眾拍攝等,筆者所在的“最小作戰單元”戰斗小組法言法語的規范使用和對現場的整體把控能力均有明顯提升。
3.加強培訓課程設計,打造“實戰化”訓練模式。在培訓過程中,應模擬各種真實場景和設置各類突發情況,使處置民警能夠在緊貼實戰的高壓狀態下不斷總結、積累經驗,從而形成“對抗演練——發現不足——訓練提升”的成熟有效訓練模式。“最小作戰單元”實戰化訓練內容源于實戰、高于實戰、服務實戰,整個訓練過程難度由簡入難、層層升級,才能發揮較好的演練效果:一是有利于檢驗民警的真實執法水平,對于暴露出的不足問題及時改進;二是有利于推動公安教育訓練從傳統模式向實戰化方向轉型升級,為提升公安機關整體素質提供專業保障。也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深化全警實戰大練兵活動要求,促使公安教育訓練工作真正緊貼實戰、服務實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