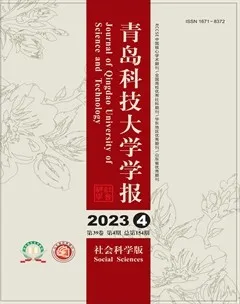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立法得失及其法理思考
王金堂 藺兮浠
[摘 要]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是繼土地承包改革以來我國農地制度的第二次重大變革契機。但從法律的規范分析角度看,以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改為標志的制度改革成果乏善可陳,此次修法未能全面達成農地“三權分置”政策所設定的目標。其核心問題是土地經營權可轉讓、可抵押的始定目標未能實現。而此制度效果的實證研究也支持上述結論。造成農地“三權分置”立法困局的原因主要包括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核心目標出現變化且多目標之間具有緊張關系、農地“三權分置”政策與法律的范式轉換障礙及現行農地制度的功能超載問題。盡管存在上述問題,但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本身具有合價值性和合規律性,應繼續保持對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研究,并通過創造性改造實現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初心。
[關鍵詞]“三權分置”立法;目標達成度;法理分析
[中圖分類號]D92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23)04-0061-12
Legislative gains and losses on the policy of separating the ownership,contractual,and management rights for contracted rural land and its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WANG Jin-tang,LIN Xi-xi
(School of Law,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The system for separating the ownership,contractual,and management rights for contracted rural land is the second major opportunity to reform Chinas agricultural land system since the land contract reform.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norm analysis,the system reform marked by the amendment of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8 has achieved little,as the amendment fails to fully achieve the goals set by the policy of separating the ownership,contractual,and management rights for contracted rural l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s that the initial goal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as transferability and mortgage has not been realiz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his system also supports the above conclus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legislative difficulties of the system include the change of the core objectives of the system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multiple objectives,and the obstacles of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cy of the system and the problems of functional overload of the current system. In spite of the above problems,the system of separating the ownership,contractual,and management rights for contracted rural land itself has its value and regularity,so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udy the system,and realize its original intention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legislation on separating the ownership,contractual,and management rights for contracted rural land;goal reaching degree;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一、引言
土地制度對于國家和社會的極端重要性已經為全社會所認識。就農業、農村和農民而言,土地制度安排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土地制度的重要性可謂無出其右。實施“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離不開科學的農地制度安排。事實上,從人民公社時期的土地集體所有、集體經營到“大包干”以來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經營“兩權分置”,直到近年來推行的農地所有權歸集體、承包(經營)權歸農戶、經營權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農地“三權分置”,中國社會對于農地制度的探索一直在進行。我國自2014年11月始在全國推行的農地“三權分置”政策藉由2018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下文簡稱“新法”)修改和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下文簡稱《民法典》)的通過而實現“法治化”。盡管有關條款仍嫌簡陋,但形式意義上的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立法已經完成。然而學界多年來圍繞著農地“三權分置”入法過程中的理論產生了諸多爭議,例如關于農地“三權分置”的必要性、土地經營權的性質[1]等問題,其實并未得到完全解決;而農地“三權分置”實踐中也存在農民認可度不高等問題[2]。認真梳理我國農地制度演變的邏輯脈絡,從法律的規范分析角度研判此次修法之于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目標的達成度,科學評價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立法的得失并分析其原因,可以為明確未來農地制度深化改革的方向提供參考。
二、農地“三權分置”立法績效分析
從法理上講,我國農地制度是由法律和政策雙重規范形成的規范綜合體,農地“三權分置”制度亦不例外。我國狹義的農地“三權分置”政策開始于2014年[3]。2014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以下簡稱《規模經營意見》)提出:“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 ‘三權分置,引導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三權分置”的概念,并做了初步的引導性政策安排。2016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以下簡稱《“三權分置”意見》)對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進行了系統性闡述并正式全面推開。而農地“三權分置”的法治化則是藉由2018年12月“新法”修改案和《民法典》的通過而實現的。
鑒于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立法的簡約,即使相關法律生效以后,此制度的運行仍依賴于政策的存在。嚴格來說,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績效的評價應區分政策績效和立法績效[3],但因為政策和法律之間存在交叉關系,而且不論是政策還是法律的實施均存在效應滯后性,所以學者們在實證分析中通常不做細分。因此,本文僅在規范意義上區分農地“三權分置”的制度立法和政策,但在實證分析中對二者不做區分。
(一)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立法的任務
評價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立法的績效必須確定評價的基準。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立法作為“命題作文”,其立法的目標是明確的。《“三權分置”意見》第3條指出:“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充分發揮‘三權的各自功能和整體效用,形成層次分明、結構合理、平等保護的格局。”學界一般認為這一表述明確了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入法的目標為“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因此評價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入法的得失,應對照這一目標展開分析。
(二)法律規范意義上的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立法的成績與問題分析
就制度層面而言,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入法已經實現,“新法”可以成為考察其政策目標達成度的適格樣本。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同時設定了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個目標,但就“落實集體所有權”目標而言,“新法”和2002年8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原法”)相比較,在此方面均著墨不多。對集體享有的土地所有權這一核心權能而言,“新法”基本維持了原來的規定,唯“新法”第27條為了在新形勢下穩定土地承包關系(保護進城農民的利益)刪除了“原法”第26條規定的發包方可以強制收回全家遷入設區市并轉為非農業戶口的農戶的承包土地的權力(利)。但鑒于實踐中此種情形原本少見,從總體上講,在本次修法中,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地位基本維持不變,其權能主要體現為管理性權能。有學者認為此項權利為一種治權[4]。盡管有學者認為“新法”“延續了無視集體土地所有權制度的流行觀念,將主要精力放在土地經營權制度構建上……至于如何踐行‘落實集體所有權的政策目標,該草案基本上無所作為”[5]。但依客觀情況而論,自2002年“原法”頒布以來,已分離出用益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之后的集體土地所有權民事權能有限,但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主體享有的管理性權能依然強大,基本能適應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現實需求。綜合評價而言,可將“落實集體所有權”目標的達成度定性為基本達成。
就“穩定農戶承包權”目標而言,本次修法的成績可圈可點。其一,保留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法律概念并對此權利加以持續保護,不但消除了農民對于農地“三權分置”制度下原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能否繼續存在的擔憂,穩定了廣大農民的基本預期,而且維護了農村穩定的大局。從“新法”的最終規定來看,立法者事實上已經將“土地承包權”概念等同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概念,并將前者定位為后者的簡稱。此后通過的《民法典》也延續了相同的規定。其二,在“新法”第21條關于期限問題的規定中增加了“前款規定的耕地承包期屆滿后再延長三十年”的規定,使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期限更長,進一步穩定了土地承包關系。其三,“新法”第23條確定了土地承包的統一登記制度,使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得到進一步保障。綜合以上規定,可以認為“穩定農戶承包權”的目標已經達成。
然而,最受人關注的“放活土地經營權”目標的達成與否狀況則不容樂觀,也存在較大爭議。農地“三權分置”制度下的土地經營權究竟應當是債權還是物權?學者們沒有形成共識。有一部分學者主張土地經營權應為權利用益物權或次級用益物權[6-8],也有一部分學者持債權說[9-11]。“新法”做了折中處理,即將土地經營權定性為可以采用某些物權化手段保護的債權。其標志一是,第41條規定:“土地經營權流轉期限為五年以上的,當事人可以向登記機構申請土地經營權登記。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二是,第46條規定:“經承包方書面同意,并向集體經濟組織備案,受讓方可以再流轉土地經營權。”三是,第47條規定:“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并向發包方備案,受讓方通過流轉取得的土地經營權,經承包方書面同意并向發包方備案,可以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其中,“新法”第47條采用的是“融資擔保”這一用詞,而不是“用益物權性的土地經營權抵押或債權性的土地經營權質押”的說法,表明“新法”擱置了用益物權論和債權論之爭,這就為債權和用益物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均預留了制度空間[12]。對于立法者而言,維持土地經營權性質的模糊性可以避免在用益物權和債權之間作出困難的選擇,因而不失為一種明智的立法策略。但對于“搞活土地經營權”的目標而言,其制度設計則難以令人恭維。就“搞活土地經營權”的內涵而言,土地經營權的可轉讓、可抵押應成為其應有之義。然而事實上,土地經營權的可轉讓、可抵押原本也是土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初心”所在[8]。盡管在獲得通過的修正案中,土地經營權部分內容被作為單獨一節而重點規制,并賦予了五年以上土地經營權的可登記性,允許土地經營權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再流轉、允許相關主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使用土地經營權進行融資擔保,等等。但是深入分析這些規范,不難看出,由于“新法”存在土地經營權定性問題上的“內傷”和“病灶”,在形式上必然會存在土地經營權的“可抵押”“可轉讓”嚴重缺乏可操作性的現象。例如,最受本次“三權分置”制度改革期待的新型農業生產主體利用土地經營權抵押問題,“新法”第47條附上了兩個先決條件,一是“承包方書面同意”,二是“發包方備案”。這就使得土地經營權抵押制度的實施存在重重障礙。不僅如此,即使當事人取得了承包方同意和發包方備案而設定了土地經營權抵押(質押),但抵押(質押)權人屆時如何實現其擔保權利也嚴重缺乏法律保障。從法理上講,實現土地經營權抵押權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土地經營權轉讓的過程,但遺憾的是,“新法”第36條在其規定的承包方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方式中,列舉了出租(轉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但沒有明確規定轉讓方式。而“新法”第46條所規定的“經承包方書面同意,并向本集體經濟組織備案,受讓方可以再流轉土地經營權”,則似乎意味著新型農業生產主體享有轉讓土地經營權的權利。若作此種解釋,金融機構在實現土地經營權抵押權的時候,應該可以徑行轉讓土地經營權(當然此權利有期限限制,不能超過承包期的剩余年限),并就此對價優者先受償。但是“新法”第46條又設置了“經承包方同意”條款,實際上卻大大限制了金融機構實現抵押權的權能,導致了土地承包權之抵押權價值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權利在市場上價值較低,而賦值較低的權利則難以承擔貸款擔保的重任。《民法典》對于土地經營權部分的規定完全延續了“新法”的相關規定。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現有法律構建的土地經營權在法理上存在不能自由轉讓的問題,并會直接導致土地經營權無法從實質意義上勝任貸款抵押或質押的任務。因此從邏輯上可以得出結論:“搞活土地經營權”的目標尚未達成。
(三)實踐視域下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成績與問題分析
“知政失者在草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講,評價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目標的達成度既需要依靠規范分析和邏輯推理,更需要到實踐中考察和檢驗。
關于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制度績效,學者們對總體制度效應展開了實證研究。周力等的研究表明,農地“三權分置”政策能夠促使農戶耕地轉出租金的提升、農業投資的增加、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本地非農就業的增加,進而促進農戶的收入增長。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法律明晰,可以促使農戶收入增長2.1%[3]。徐玉婷等研究認為,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對家庭農場和資本農場有積極影響,但對傳統農戶和種田能手則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對種田能手。“三權分置”制度對務工經商、農業雇工兩類主體收入有積極影響,但對賦閑農戶的作用并不樂觀[13]。杜姣的實踐調研結果顯示,“三權分置”出現了實踐異化,體現為以所有權主體絕對責任化、承包權主體絕對權利化和經營權主體權利弱化為表現形式的“三權”主體權利的失衡。由此提出土地流轉性質的政治化是形成“三權”主體權利失衡秩序的主要原因[14]。
筆者于2022年對山東省平度市、萊西市、諸城市等部分地區的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實施情況進行了調查。本次調查受訪農戶為62戶(人),其中對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做出積極評價的有21戶,占比為33.8%;而無法做出評價或負面評價的為41戶,比例為66.1%。在受訪農戶中,僅有2戶成功使用過土地經營權擔保貸款,占比為3.2%;而畝均土地經營權可以擔保的貸款數額僅為700元/年/畝,顯示土地經營權目前沒有普遍被金融機構所接受,土地經營權可抵押的目標達成率較低。在對土地經營權是否進行登記的專項訪談調研中,接受訪談的16戶種糧大戶或家庭農場均未進行“新法”第41條規定的土地經營權登記。在對“在未來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您主張加強哪方面的權能(權利)”題目(多選題)的問卷調查答案中,相對于集體的土地所有權(20.97%)、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43.55%)而言,有53.23%的被調查對象主張加強實際使用土地方的土地經營權。這說明現有土地經營權的權能安排還不能滿足這些農戶的需要。而在對家庭農場和種糧大戶的問卷調查題目(多選題)中,受訪對象則認為現存農地制度的最大問題是“流轉得到的土地權利不穩定”(35.71%),其他依次是“土地價格太高”(21.43%)、“流轉得到的土地無法進行融資”(14.29%)、“土地流轉困難”(7.14%)。在筆者的這次訪談調研中,絕大部分受訪農戶對于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的認識局限于基層政府對承包土地流轉的鼓勵態度及其配套措施,對于農地“三權分置”制度與之前的“兩權分置”制度的差別則沒有明確認知,這也反映出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在實踐中的尷尬境地。
綜上,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從政策推行到實現“入法”并制度化已近10年,但從其政策和制度的實踐來看,以土地經營權“可抵押、可轉讓”為標志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土地經營權并未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搞活土地經營權”的目標并未實現。
盡管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的前兩項權利目標在理論上已基本達成,但是搞活土地經營權的目標尚未達成,其影響依然是致命的。眾所周知,關于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戶承包(經營)權、土地經營權這三項權利,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行的農村“大包干”生產經營體制改革就已經實現了土地集體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兩權”分置,而且這兩種分置已被“原法”所確定和保護。因此,承包農戶將其承包土地通過租賃等債權性流轉方式流轉給其他農戶、合作社或公司等經營的行為,即使在2014年農地“三權分置”政策推出之前也已經在很多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區的農村中習以為常①。由此,如果說一個難以自主流轉的債權性土地經營權就是農地“三權分置”制度中的適格土地經營權,那么事實上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此種意義上的“三權分置”就早已在部分農戶和新型農業生產主體中實現了;如果說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僅僅是對農戶將其承包土地租賃給他人生產經營后農村集體土地權利配置狀況的客觀描述,那么,這不僅不符合原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2016年11月所講的“‘三權分置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這一重要定位[15],也不符合社會各界的期待。
當然,如果說立法者智識不夠或努力不足以至于沒能夠完全實現農地“三權分置”的政策目標,其實是不適宜的。從“原法”到“新法”的立法過程已經清楚地體現了這一點。自2016年《“三權分置”意見》提出“完善‘三權分置法律法規”“加快農村土地承包法等相關法律修訂完善工作”的立法任務以來,全國人大法工委工作人員和法學界一眾學者對“新法”的修改付出了巨大努力,先后于2017年11月、2018年10月和2018年12月形成了三個版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并分別由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但正式通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的立法重點恰恰是土地經營權部分,“新法”將土地經營權專列一節予以規定,維持了土地經營權的債權性質,但對期限較長(5年以上)的土地經營權卻采取了物權化的保護手段(登記)。“新法”第41條確立了土地經營權保護的登記對抗主義,第42條出于穩定土地經營權的目的對承包方的合同權利進行了限制,明確規定承包方除非法定情形下,不得單方解除土地經營權合同。由此為土地經營權的物權化準備了條件。當然遺憾的是立法者沒有能夠構建出一個適合進行再流轉的物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甚至也沒能夠構建出一個適合再流轉的債權性的土地經營權。其原因值得深入反思。
三、農地“三權分置”立法困境的原因分析
農地“三權分置”政策作為“我國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承載了拓展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豐富雙層經營體制內涵、順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時代要求,進而為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承擔了提供制度支撐的重要歷史使命[16]。在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出臺之初,各界均報以極大的關注和期待。2016年《“三權分置”意見》已明確提出農地“三權分置”的立法任務。在全面實施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通過“原法”修改和《民法典》制定等途徑,將農地“三權分置”法治化已成為全社會的共同期待。然而與《“三權分置”意見》出臺時的大張旗鼓的宣傳相反,“新法”通過后卻“波瀾不驚”,未見有關方面進行高調宣傳。這或許從某種意義上顯示了農地“三權分置”立法的尷尬處境。
(一)農地“三權分置”政策核心目標的變化及其多目標之間的緊張關系
關于此次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的目標,理論界不無爭議。高圣平認為,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政策目標在于優化土地資源配置,促進適度規模經營發展[17]。陳小君認為,“黨中央確立農地‘三權分置的政策意圖十分明確,即堅持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不變,農民利益保護與農業生產效率同等關注”[5]。兩位學者的不同觀點大致反映了當前各界在“三權分置”政策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側重。
由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受政策主導的路徑依賴特點,決策者或曰政策制定者對“三權分置”政策目標的認識至關重要,值得認真分析和探討。其一,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并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此《決定》明確了要賦予農民承包經營權流轉、抵押、擔保、入股等權能。盡管《決定》沒有將承包經營權和經營權明確加以區分,但是專家們普遍認為,其中已經內涵了“三權分置”的構想[8,18],且明確了經營權“可轉讓、可抵押”的政策目標[6]。其二,2014年1月中央1號文件《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將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目標表述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其三,2014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明確提出了“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這是“三權分置”概念在中央政策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出現,而此文件題目也明確了農地“三權分置”的政策目標,即“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其四,2015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對農地“三權分置”目標的闡述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堅守土地公有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防止犯顛覆性錯誤。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在這一文件中,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目標的表述側重點與上述2014年的兩個文件相比較而言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由原來置重“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目標轉變為“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三個目標并重。其四,2016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是對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進行系統性闡述的重要文件。此《意見》沒有使用政策目標這一概念,但在其“重要意義”一節中,提出了兩個“有利于”,即“有利于明晰土地產權關系,更好地維護農民集體、承包農戶、經營主體的權益;有利于促進土地資源合理利用,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提高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推動現代農業發展”。這兩個“有利于”可以被認為是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目標的間接表述,即同時內涵了三方(集體、農戶、新型農業生產主體)利益的共同保護和發展適度規模經濟的兩個方面的目標,且將三方利益共同保護置于第一位。
綜上分析不難看出,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在提出、部署和推進的過程中,其本身的目標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以2015年11月出臺的《方案》為界,在此前一階段的文件中,促進適度規模經營目標更受重視,而且為了回應新型農業生產主體的關切,實現土地經營權可抵押成為最重要的政策目標。但在此后一階段的文件中,政策目標更側重于三者利益的共同保護,并將其任務定位為“三條底線”。適度規模經營的目標盡管沒有放棄,但是被置于“放活土地經營權”目標之下,且在其之前加上了“多種形式”的定語,顯示了政策制定者對適度規模經營目標的開放態度。
出現上述變化的原因其實并不難理解。自2014年農地“三權分置”政策提出以后,社會各界對于此政策的理解其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別。就部分基層政權、部分基層干部和新型農業生產主體而言,普遍看重此政策所提供的土地流轉的廣闊空間和土地經營權的可抵押、可轉讓帶來的效率優勢。就廣大原承包農戶而言,其所關心的是已經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會不會被徒具外表的“承包權”所取代?會不會被“受寵”的經營權“架空”?甚或農地“三權分置”后,村組集體是否可以拋開原承包戶而以所有權人代表的身份直接與新型農業生產主體進行土地經營權交易從而損害原承包農戶的利益?這些擔心其實都是客觀存在的。就部分更屬意集體經濟、集體經營的基層干部而言,其所關注的是:既然“兩權分置”下土地集體所有權已經被“虛置”,那么多出一個可抵押、可轉讓的經營權后的“三權分置”架構中的集體所有權是否會被進一步削弱?上述種種不同的理解和擔心,其實是目前我國農村承包土地仍承擔多重社會功能所引致的正常反應,這些擔心和呼聲在現階段應當也必須得到重視。體現在農地“三權分置”改革過程中,其政策目標的微調和修正恰恰是社會和決策者良性互動的結果。
農地“三權分置”的政策目標由置重相對獨立的土地經營權調整為集體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三項權利并重,極大地增加了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建構難度。原因在于這三項目標之間存在緊張關系。其一,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政策目標要求是“落實”,政策底線是“不能把土地集體所有制改跨了”;其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政策目標是“穩定”,政策底線是“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其三,土地經營權的政策目標是“放活”,政策底線未予對應性的明確闡釋。在2016年10月的《意見》中,提到“不能把耕地改少了”和“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兩項要求,是否可以將此要求理解為土地經營權的政策底線尚在兩可之間。事實上這兩項要求應該是對三項權利的整體要求。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這些政策要求和給出的政策底線是基于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階段和各方利益關系綜合考量而提出的,其合理性和正確性毋庸置疑。問題在于基于傳統的土地權能關系框架,承包土地的現有權能難以同時滿足這三項權利目標的要求。例如,在是否賦予集體經濟組織定期或不定期調整承包土地權能問題上,落實集體所有權和穩定農戶承包(經營)權這兩項目標就存在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也體現在此次土地承包法的修改過程之中。2017審議稿中第10條規定:“承包期內,因特殊情形矛盾突出,需要對個別農戶之間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適當調整的……”①賦予集體經濟組織可通過民主程序在承包期內調整承包土地的權利。這一規定突破了“原法”第27條對承包期內集體經濟組織調整承包土地“因自然災害嚴重毀損承包地等特殊情形”的限定條件①。“原法”的這條規定是限定在“因自然災害嚴重毀損承包地等特殊情形”。2017年的這一規定在2018審議稿中予以維持,但在同年最終通過的修正案中被取消,相關規定恢復了2002年“原法”的相關表述。這意味著集體土地所有權中仍不含承包期內對承包土地進行調整的權能(自然災害等特殊情形例外)。不僅如此,承包土地到期后集體經濟組織是否擁有調整承包土地的權利是此次土地承包法修改中的另一個令人關注的重大問題。本次修法貫徹了黨的十九大確定的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的重大決策,最終通過的修正案規定是:“前款規定的耕地承包期屆滿后再延長三十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屆滿后依照前款規定相應延長。”比較三個文本,對此問題的規定基本一致。這表明為了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在未來近40年的長期限內,集體經濟組織仍沒有對廣泛意義上的承包土地進行調整和重新發包的權能。這意味著為了土地承包權的穩定,集體土地所有權“落實”的目標做出了一定的妥協。當然這一妥協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包干)改革的應有之意,但在此問題上的曲折決策過程也反映了落實土地集體所有權和穩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之間的緊張關系。
然而搞活土地經營權和穩定土地承包權及落實土地集體所有權之間的緊張關系則更為顯性。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的出發點是“解決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集約化經營及發展現代農業問題”[19],換句話說,是通過提供可轉讓、可抵押的土地經營權為新型土地經營主體提供制度條件[8]。而在提供這樣一種土地經營權的同時,既不能損害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利益,也不能損害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利益,更不能損害農地所承載的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等政治經濟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民法原理上,一種用益物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是實現土地經營權“可轉讓、可抵押”的最佳制度選擇,但是在已經屬于用益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之上再設定次級用益物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且同時不損害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和所有權人的利益,則需要極其精密的制度設計。
承包土地的流轉沒有也不可能待“法定而后動”。事實上基于“原法”提供的法律依據,以租賃為主要方式的承包土地債權性流轉已經成為“既成事實”,且規模巨大。通過考察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歷程,可以看出,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塑造成用益物權,需要在一定意義上限制土地所有權人的權利。事實上,在所有權之上設定用益物權或者擔保物權的同時,必然會伴隨原權人部分權能的限制。基于此原理,要將業已存在的較大數量的債權性土地經營權塑造成用益物權,必然伴隨著對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和所有權人權能的限制。這無疑會“損害”土地集體所有權人和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利益,從而難以全面實現“三權分置”的政策目標。基于這一考慮,在本次土地承包法修改過程中,立法者維持了農地“三權分置”狀態下土地經營權的債權性質。雖然允許此土地經營權在征得土地所有權人和承包權人書面同意的前提下再流轉和進行融資擔保,但是無論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均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此種制度安排下的土地經營權離“可轉讓、可抵押”的目標已經相去甚遠。
(二)農地“三權分置”政策與法律的范式轉換困境
農地“三權分置”立法的實踐體現了兩種范式轉換過程的糾結和艱難。新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大致遵循了從政策到法律的制度建構模式,農地“三權分置”制度亦遵循此模式。但如前所述,此次農地“三權分置”立法的實踐困難較大。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農地“三權分置”的政策范式與法律范式差別較大,且存在范式轉換的難題。農地“三權分置”政策提出后,在法學界引起較大的反響,也產生過較大爭議。有學者認為農地“三權分置”理論雖是經濟學界解決我國土地承包經營權困境的政策選擇,但不符合法律邏輯[20]。這一觀點盡管有絕對化之嫌,但農地“三權分置”立法的實踐證明了問題的存在。“三權分置”作為政策目標,通過行政性倡導、財政補貼等方式已形成客觀形態上的所有權、承包(經營)權、經營權在不同主體間的配置狀態是大勢所趨,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此種政策意義上的農地“三權分置”也已經成為現實。經濟學或政策范疇上的三種權利界定都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間,但法律意義上的三種權利界定則必須精確化,而且各種權能的配置必須做到邊界清晰。這是政策范式與法律范式的重要區別。
自2016年《“三權分置”意見》提出立法的任務以來,立法機關先后起草并提交審議了三個版本的修正案,分別是2017年11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0次會議審議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審議稿(以下簡稱“2017審議稿”)、2018年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第二次審議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2018審議稿”)和同年12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第三次審議后通過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修正案(以下簡稱“2018修正案”)。茲就三個法律文件中對三項權利的權能安排差別分析如下:
1.“2017審議稿”對三項權能的界定。“2017審議稿”就土地所有權權能而言,其在特殊情況下對承包地的收回權被取消①,但卻試圖放寬“原法”對集體經濟組織調整承包土地的限制,試圖擴大集體經濟組織在承包期內有限制地調整承包地的權能。對于土地承包權權能而言,“2017審議稿”與“原法”相比,對“原法”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權能予以維持,但對于承包土地的處分權能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2017審議稿”明確農戶可以“自由”流轉土地經營權,但另一方面卻又明確規定不得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范圍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就前者而言,土地經營權被“放開”,在理論上是一個進步。但是考慮到“原法”中承包土地的租賃權能本已存在且可以自由行使,因此這種進步缺乏實質內容的支撐。就后者而言,取消了“原法”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讓權,理論上似乎是“退步”,然而事實卻并非如字面那樣涇渭分明—盡管“原法”第37條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的規定,但結合原《土地管理法》第15條第2款來看,原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本權的權能原本就是被嚴格限制的形式上的權利②。因此,“2017審議稿”直接將此“形式上的權能”予以取消也在情理之中。與“原法”中規定土地集體所有權主體有權對“全家遷入設區的市,且轉為非農業戶口的”的承包方收回土地承包權相對應的是,“2017審議稿”對進城農戶的土地承包權予以保留。
對于土地經營權而言,“2017審議稿”將此權利界定為“土地經營權是指一定期限內占用承包地、自主組織生產耕作和處置產品,取得相應收益的權利。”但回避了對其法律屬性的明確。盡管從此文本的其他條款中可以分析出此權利的債權屬性,并在此權利屬性的基礎上被賦予經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承包權人同意的前提下再流轉的權能。但“2017審議稿”對三項權能的安排特別是對至關重要的土地經營權權能的安排受到了學界的批評。其主要原因是“2017審議稿”構建的土地經營權是一項純粹的債權,而債權所具有的嚴格的相對性和不穩定性會使其流轉受到極大的限制,而債權所具有的不穩定性也會大大限制其流通的屬性。因此,土地經營權所承擔的“可轉讓、可抵押”的本初目標也就成為空談。
2.“2018審議稿”對三項權能的界定。鑒于“2017審議稿”存在問題眾多且難以落實修法的主要期待,立法機關又重新起草了《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并形成“2018審議稿”。此審議稿相對于前者,其最大的亮點是舍棄了“2017審議稿”中對土地經營權的泛泛描述,并在維持“2017審議稿”中的土地經營權債權性質的同時,對此項權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造性塑造,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采用物權法手段保護債權性的土地使用權。“2018年審議稿”第24條規定:“土地經營權流轉期限為五年以上的,當事人可以向登記機構申請土地經營權登記。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此條規定可以被認為是對土地經營權的實質性構建的嘗試。其他兩項權利(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權)的權能基本上維持了“2017審議稿”的安排。
3.“2018修正案”對三項權能的界定。最終通過的“2018修正案”與“2018審議稿”相比,在土地集體所有權權能、承包(經營)權權能和土地經營權權能方面做了一些微調。一是取消了“2017審議稿”和“2018審議稿”出現的賦予土地所有權人在承包期內因特殊情形或矛盾突出而調整承包土地的權利;維持“原法”對此問題的規定,即在土地所有權人承包期內調整的權能僅限于“因自然災害嚴重毀損承包地等特殊情形”;維持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對特定承包地塊的權利。相對“2018審議稿”而言,“2018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限縮了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權能,強化了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權能。二是取消了“2018審議稿”中出現的將“連續兩年以上未按約定支付價款”作為承包方獲得單方面解除土地經營權流轉合同的法定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土地經營權的地位。
全面對比分析上述三個法律文件,不難看出,立法者對土地承包權的內涵界定、土地經營權的定性、發包方調整承包的條件限定等關鍵問題存在界定模糊、表述反復等問題。不僅是三權中的承包權即土地承包經營權人通過合同設定土地經營權并流轉出去后剩余權利的內涵和外延不清、權能不明,而且被寄予眾望的土地經營權也乏善可陳。登記后的土地經營權的權能因仍然缺乏獨立性、穩定性和經濟性,其可再轉讓或抵押的標的物缺乏法律保障,所以盡管立法者做出了極大的努力,但檢視“2018修正案”對“三權分置”政策法制化的成果,不能不說還有許多遺憾。其中,最大的遺憾莫過于原本讓大眾期待的“可轉讓、可抵押”的土地經營權并未出現。
(三)農地制度的社會功能超載困局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維持了歷史上形成的政治性、社會性、經濟性功能超載狀態。具體而言,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不但承載著表征和維持社會公平、實現鄉村治理、支持和落實地方行政管理、推行和發揮基層民主等政治性功能,還承載著促進公共利益和社會發展、協調和改善緊張的人地關系、實現農民的勞動權和社會保障權等社會性功能,更承載著構成農民固有財產利益和財產利益的經濟性功能。這些制度功能因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各異,所以各功能之間的結構性沖突在所難免[21]。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仍然保留了上述多樣化的制度目標和功能,導致協調其內在矛盾的難度極大。
四、農地制度深化改革的法理思考
農地“三權分置”立法陷入目前的困局及其不溫不火的實踐,表明此制度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其價值和合規律性仍存在再確認的需求。
(一)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內涵的再思考
農地“三權分置”制度自提出以來,學界對其內涵的界定一直存在爭議。關于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概念,有學者進行過歸納總結,認為“三權分置”就是在現有法律已經承認的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民家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新設“土地經營權”而形成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的分置狀態[22]。對于這一定義,筆者持肯定意見,并且認為應當通過新設的土地經營權而使得此制度能夠實現對承包土地經營權的全面利用。譬如實現承包土地經營權利的流轉、融資擔保等價值利用。然而通過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實行近10年的實踐來看,使得對此制度概念的另一種闡釋成為可能,即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是指實現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債權性的)經營權分別由不同的主體享有的一種新型農用土地利用狀態。此概念內涵的闡釋契合了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是由經濟學者提出和倡導的觀點。按照這一理解,我國的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已然成為現實①。然而若按照此內涵來界定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則又難以堪承“農地‘三權分置政策作為我國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的期待。原因在于,作為債權性的基于承包土地租賃關系產生的土地經營權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在我國部分試點地區通過承包農戶的出租等市場流轉行為出現了,由此實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主體和土地經營權主體的分離[23]。而到了農地“三權分置”政策提出之前的2011年,根據《中國農業年鑒(2011-2017年)》統計數據,在2011年全國2.29億農戶共承包12.77畝耕地。其中有0.39億農戶進行流轉合計2.28億畝,農戶流轉比例與農地流轉面積比例分別為16.94%和17.84%[24]。若將已然存在的狀態描述為一項重大制度創新顯然不符合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堅持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內涵應按照第一種闡釋來理解。但是不容否認的是,根據筆者的調查,目前基層干部和農民對于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理解其實維持在允許承包戶將其承包地在承包期內出租給他人耕種的層面。而承包戶的這一權能事實上早在2002年頒布的“原法”中已經被授予。而略顯尷尬的是,承擔將農地“三權分置”政策法治化任務并于2018年通過的“新法”修正案自頒行以來,其中規定的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卻令社會“無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而學界對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內涵的爭議最大的地方其實就在于對土地三項權利內涵的理解。對于土地集體所有權,盡管也有對此權利之公法屬性抑或私法屬性的不同理解[4],但考慮到此權利并非此次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的重心所在,且無論其名稱抑或權能均變化不大。因此此權利在本次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中爭議不大。爭議較大的是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關于土地承包權的內涵,從本質意義上分析,主要有資格權說和土地承包經營權說。資格權說主張承包權是指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農村土地的資格,屬于成員權中的一種[5];而土地承包經營權說則認為土地承包權是流轉了土地經營權后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簡稱[25]。分析修改后的“新法”和《民法典》的相關條款,筆者認為上述法律已經做出了明確選擇,即將土地承包權視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簡稱。筆者認同這一立法選擇。農地“三權分置”制度中爭議最大的是土地經營權,理論上主要有次級用益物權說和債權說。持次級用益物權說的學者認為,土地經營權應為從土地承包經營權中分離出來的對承包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8];而持債權說的學者則認為,土地經營權是權利人基于合同享有的在一定期限內對他人之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權利[26]。針對修改后的“新法”和《民法典》中規定的土地經營權的性質,有權利性質未定說和債權說。持權利性質未定說的學者認為,“新法”的修改“淡化了土地經營權性質”,因而屬于債權物權性質未定狀態[27];持債權說的學者認為,此次修法實質上將土地經營權界定為債權,但經登記的土地經營權具有類似物權的效力[25]。對于“新法”和《民法典》中規定的土地經營權的性質,筆者贊成債權說的判斷。那么一個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能否達成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目標和使命?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只能得出令人遺憾的結論。
(二)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合價值性分析
由于前述農地“三權分置”政策設想和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立法的現實出現了較大的反差和區別,為方便分析論述,將前者稱為“三權分置制度愿景”,后者稱為“三權分置立法”。
必須承認,農用土地“三權分置”制度愿景是一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農地制度創新,她承載了堅持土地公有制(并透過此制度實現公平和社會穩定)、保障農民既得土地利益(公平和社會保障屬性的具體體現)和實現土地經濟效益(規模經濟功能與融資功能的開發利用)的有機統一,其良善初心不容置疑。此制度愿景若能成功實現法治化,其先進性有望大大超越傳統土地私有制和傳統土地公有制,將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制度創造并有望對人類土地制度文明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但也正因為前述多重目標(多重約束)的同時存在,使得此制度法治化的難度超越了人類歷史上已有的任何一種農地制度。此次修法的曲折過程和留有遺憾的法律規定即是明證。要徹底解決三農問題,實現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就必須實現農地制度的現代化。新中國成立以來,土地制度的重大調整已經經歷了兩次①,此次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提出之初,曾被各界寄予很高的期待,有希望成為第三次農地制度的重大變革,并為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的土地問題提供根本性解決方案。從理論上講,若“三權分置制度愿景”能夠順利達成,那么完善后的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將可以確保集體土地所有權權能明晰,重大公共利益和集體利益保障有力;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將得到長久保護,農民可以獲得對其承包土地交換價值的索取權;而新型農業生產主體也將可以獲得物權性質的可流轉、可抵押的土地使用權,從而實現市場化資源配置下的農業生產適度規模經營。誠如是,則中國農村將迎來又一次帕累托式的制度變革,三農問題將獲得根本解決,而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將會在堅實的基礎上獲得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值得法學界和社會各界繼續努力,通過深化觀念、理論和立法技術創新等方式完善農地“三權分置”制度。
(三)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合規律性分析
此次“三權分置”立法的蹉跎和遺憾不免使人對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可行性產生疑慮,即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三個目標是否能夠同時實現?筆者認為,在上文分析的造成“三權分置立法”困局的諸多原因中,最關鍵的是需要解決落實集體所有權與穩定農戶承包(經營)權兩項目標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搞活土地經營權與穩定土地承包權目標之間的緊張關系。就前兩項目標的緊張關系而言,囿于現有法律規定的兩項權利中的權能范圍,兩者似乎是零和博弈關系。但筆者認為,通過創造性地對土地所有權人進行賦權,在保障土地集體所有權核心權能的基礎上大膽為農民賦權,那么則可能走出兩者之間沖突的困境。已經設立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集體土地所有權是一種特殊的所有權,除享有“新法”規定的權能外,還應考慮創造性地賦予土地所有權人兩項權利:一是明確土地所有權人享有承包土地的發展權(非農性質的商業化開發權),二是賦予所有權人在法定非常態勢出現時以付出法定補償為對價收回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土地所有權人獲得土地發展權能在經濟利益上能保障承包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而賦予土地所有權人在非常態出現時收回承包土地的權利則是土地集體所有制本質的體現,能夠有效地預防我國歷史上因人地矛盾突出而引發社會動蕩的問題。當然土地所有權人要收回承包權和經營權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并對被收回土地上的原權利人進行公平補償。就后兩項目標的緊張關系而言,破解兩者沖突的最優選擇是賦予農民永久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并在此基礎上允許設立用益物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筆者相信,通過此舉能夠把實現物權化、財產化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承包權)交給農民。而允許農民設立物權化的土地經營權,可將此權利通過市場化流轉手段配置給其他農業生產主體,將是實現農用土地“三權分置”制度理想愿景的關鍵。此外,針對目前承包土地超載的社會功能,亦應適當“減負”,還承包土地的生產資料和財產權法律地位。筆者認為,通過上述改革,“三權分置制度愿景”完全可以成為現實。
五、結語
世界上其實并沒有一種完美的土地制度,農用土地制度尤其如此。從我國的社會歷史來看,從井田制到授田制、從土地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出現過井田制、授權制、均田制等土地制度,形成了公田(官田)、私田、永業田、口分田、占田、科田、田底權、田骨權、田皮權等林林總總的土地權利類型。但農用土地制度始終存在基于某種程度和某種形式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化配置和基于“耕者有其田”理念而產生的行政性均田配置之間的博弈。前者側重于效率,放棄了農民身份和特定土地的“綁定”關系,允許土地市場化流轉而保障了擁有土地的民眾的財產利益,在社會秩序正常的狀況下,能夠實現土地財富效應并通過土地買賣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而后者則側重于公平,利于提供給農民穩定的土地耕作權利,能夠緩和社會矛盾。但基于其性質往往將土地權利和農民身份“綁定”,且不允許農民自由處分其土地權利,因而易使民眾陷入財產和融資手段匱乏的窘境。而且此種土地配置手段因需要時刻維持強大的行政權力而消耗不菲的社會資源,且歷朝歷代中,凡推行均田制政策的政權,即使在其統治權威最盛的階段,也無法阻止基層自發產生的某種形式的土地買賣,更遑論控制力下降的時期,此時土地私有制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礎的土地市場化集中變成了常態。前者側重于效率,放棄了農民身份和特定土地的“綁定”關系,允許土地市場化流轉,因而能保障擁有土地民眾的財產利益,在社會秩序正常的狀況下,能夠實現土地財富效應并通過土地買賣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如前所述,土地私有制下的大規模土地集中,特別是利用權力實現的大規模土地兼并往往會伴生大規模的失地流民,從而易引發社會動蕩。
從域外國家的土地制度實踐來看,受自然法理念影響,私權神圣觀念在土地制度中影響巨大,土地私有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土地制度的基礎。私人土地所有權基礎上的家庭農場成為歐美國家農業生產方式的典型業態。一般而言,在土地資源豐富或非農就業機會充足的社會,土地所有權歸私人所有并通過市場交易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是一種有效率的土地制度。但在土地資源不足或非農就業機會不足的社會,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配置實踐經常會出現種種問題。以日韓和我國臺灣地區為例,由于土地資源不足和長期以來由此產生的土地“價值”觀念,農民普遍存在濃重的“惜地”心理而普遍惜售土地。盡管這些國家和地區早已實行土地私人所有制并允許土地買賣,但農地所有權交易并不活躍,并由此導致政府雖一再出臺政策加以倡導和鼓勵,但由于土地所有權的市場化集中進程非常緩慢,農業規模經濟始終難以實現,分散占有的相當部分土地普遍處在“兼業化”低效經營狀態中,即擁有土地的農民一方面在二、三產業就職,另一方面利用業余時間經營自己所有的土地。這已經成為令上述國家和地區政府農業部門“頭痛”的痼疾。
農地制度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尤其是隨著科技和生產力水平的持續提高,建立在私權本位下的土地制度因其在應對新技術、新業態發展需求方面的表現差強人意,土地私有制對某些工程技術及社會進步的鉗制效應日益凸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和社會高速成長,特別是基礎設施領域的高速發展,事實上都得益于土地公有制帶來的促進效應。此外,現實世界中并沒有一種所有制包打天下的神話,西方法權觀念中土地私有制神圣的教條并不值得“拿來”。當然,土地權利在一定領域和一定范圍內歸私人所有,具有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活躍市場的作用。這已經從我國農村土地承包制和城市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的成功實踐中得到證實。
基于上述土地制度規律的認識,并基于對土地制度演進“路徑依賴”規律的認同,結合新中國成立以來農用土地制度的曲折實踐過程的經驗教訓,法學界應該也必須通過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的法治化契機實現我國農地制度現代化。盡管一些學者對農地“三權分置”政策構想有一些疑問,且有相當學者對目前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入法的成果稍顯失望,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所追求的堅持公有制、堅持土地承包制度和搞活土地使用權的目標是科學的,她不但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對社會進步所帶來的“鉗制”效應,保障了大多數農民基本土地權利,同時還可能會通過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流轉而實現規模經濟和財富效應,并且極有可能會成為一種先進的農用土地制度。當今之際,社會各界應該在繼續保持對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持良善初心認同的同時,致力于通過創造性的立法實現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核心目標。這就要求在2018年“新法”修正案通過以后,繼續保持對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深入研究,并通過“挖潛改造”實現其制度初心。
[參考文獻]
高飛.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法理闡釋與制度意蘊[J].法學研究,2016(3):13.
王金堂,王晶晶,楊惠杰,等.山東省承包土地流轉暨“三權分置”政策實施現狀調查報告[J].中國不動產法研究,2017(2):123-134.
周力,沈坤榮.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農戶增收效應:來自“三權分置”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22(5):141-157.
熊萬勝.地權的社會構成:理解三權分置之后農村地權的新視角[J].社會科學,2021,(5):70-81.
陳小君.土地改革之“三權分置”入法及其實現障礙的解除:評《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J].學術月刊,2019(1):87-95.
蔡立東,姜楠.農地三權分置的法實現[J].中國社會科學,2017(5):102-122.
朱廣新.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政策意蘊與法制完善[J].法學,2015(11):88-100.
孫憲忠.推進農地三權分置經營模式的立法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6(7):145-163.
陳小君.我國農村土地法律制度變革的思路與框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相關內容解讀[J].法學研究,2014(4):4-25.
姜紅利.放活土地經營權的法制選擇與裁判路徑[J].法學雜志,2016(3):133-140.
樓建波.農戶承包經營的農地流轉的三權分置:一個功能主義的分析路徑[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53-69.
高海.“三權”分置的法構造:以2019年《農村土地承包法》為分析對象[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100-109.
徐玉婷,黃賢金,陳志剛,等.農地三權分置改革對多元主體收入的影響:來自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實證經驗[J].自然資源學報,2022(9):2451-2466.
杜姣.權利失衡:土地流轉中“三權分置”的異化實踐及其破解[J].農業經濟問題,2023(7):29-38.
農業部部長:“三權分置”是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EB/OL]. [2023-04-22]. http://politics.com.cn/nl/2016/1103/c1001-2883291.html.
韓長賦.土地“三權分置”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N].光明日報,2016-01-26(1).
高圣平.承包地三權分置的法律表達[J].中國法學,2018(4):261-281.
陳小君.我國農地制度改革實踐的法治思考[J].中州學刊,2019(1):56-65.
李飛,周鵬飛.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劉振偉談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改[J].山西農經,2019(1):1-2.
單平基.“三權分置”理論反思與土地承包經營權困境的解決路徑[J].法學,2016(9):54-66.
趙萬一,汪青松.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功能轉型及權能實現:基于農村社會管理創新的視角[J].法學研究,2014(1):74-92.
肖衛東,梁春梅.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內涵、基本要義及權利關系[J].中國農村經濟,2016(11):17-29.
黃祖輝,王朋.農村土地流轉:現狀、問題及對策:兼論土地流轉對現代農業發展的影響[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2):38-47.
衡霞,張軍.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衍變歷程與演進邏輯:基于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J].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1):48-56.
高圣平.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改后的承包地法權配置[J].法學研究,2019(5):44-62.
趙鯤.共享土地經營權:農業規模經營的有效實現形式[J].農業經濟問題,2016(8):4-8.
劉振偉.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J].農村經營管理,2019(1):12-17.
[責任編輯 祁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