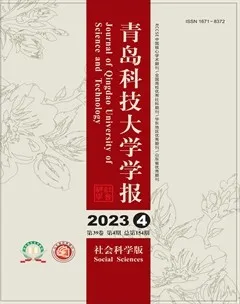新時代歷史劇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創新研究
徐好雯
[摘 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核心任務。新時代歷史劇創作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基于新歷史主義理論視角,對歷史場景、社會風情等進行高度還原,運用豐富鏡頭語言展示古風古韻;從個人、家庭、女性等微觀角度展開敘事,將歷史人物與家國、朝代變遷相糅合,在塑造立體化人物形象的同時展示時代風云變幻;突出以人為本的思想價值觀,使得新時代歷史劇在藝術性、審美性、思想性上呈現不同以往的新風貌。而新時代歷史劇在語言表達、虛構邊界以及時代精神挖掘上存在的欠缺,需要創作者們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關鍵詞]歷史劇;傳統文化;融合;創新
[中圖分類號]I05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23)04-0086-06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drama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XU Hao-we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the central task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rough respecting historical facts,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drama in the new era highly restores historical scenarios and social custo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theory. It uses rich lens language to show ancient styles and charms. The historical drama combines historical characters with family and country,and with dynasties changing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s,families,and women,which creates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s while showing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historical drama also highlights the people-oriented values,which makes the historical drama of the new era present a new style in terms of art,aesthetics and thought. However,due to the shortcomings in language expression,fictional boundary and spirit of the times,the historical drams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more in-depth exploration by the creators.
Key words:historical dramas;traditional culture;integration;innovation
歷史劇是傳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而歷史劇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創新一直是歷史劇創作中的難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立時代精神的重要性。2014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1],之后又多次強調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2]。這使得新時代歷史劇創作更擔負起連接斷裂文化、重塑歷史記憶、繼承傳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使命。而近年來出現的一系列歷史劇也日益呈現與傳統歷史劇不同的特色和風格。新時代歷史劇是如何與傳統文化融合與創新的,形成了怎樣的表達方式和藝術特色,是本研究的關心所在。
圍繞上述問題,本文在梳理新時代歷史劇創作理念轉變的基礎上,對2012年后出現的優秀歷史劇進行系統性考察,進而概括新時代歷史劇與傳統文化融合創新的路徑,并對融合與創新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與反思。
雖然關于歷史劇的概念歷來眾說紛紜,但歷史劇基本包括三類,即歷史正劇、歷史故事劇、歷史戲說劇。歷史正劇,可以理解為還原歷史真實事件、真實人物的劇作。歷史故事劇或歷史演義劇,可以理解為對官方記載中未涉及的歷史或“野史”類故事(其中不乏真實性的內容),在不影響歷史真實的大背景下經過合理改編或演繹而成的歷史劇。而歷史戲說劇,雖然也會汲取真實的歷史事件或人物,但在創作上更注重藝術表現,會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真實的歷史[3]。基于繼承和傳揚優秀傳統文化、重塑歷史記憶和文化精神的出發點,本文對歷史劇的范圍限定在故事背景為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正劇和經過合理演義的歷史故事劇,歷史戲說劇不包括在本文的考察范圍之內。
依據上述界定,本文選取《楚漢傳奇》(2012)、《大軍師司馬懿》(2017年)、《大明風華》(2019年)、《清平樂》(2020年)、《山河月明》(2022年)五部較有影響的作品作為考察對象,對新時代歷史劇進行分析。
一、新時代歷史劇創作理念的轉變
歷史劇與傳統文化的融合與創新離不開創作理念的轉變。隨著時代變遷和人們對于歷史認知的深化,歷史劇的創作觀念也在發生轉變。
(一)歷史劇創作觀念與創作爭議
20世紀20年代歷史劇初登舞臺之時,古為今用與歷史真實是當時創作者們的主要觀念。而之后由郭沫若先生創作的一系列歷史劇,引發了創作中歷史真實與虛構問題的討論,并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此問題的意見基本分為兩派:一派是要求完全的歷史真實。比如邵荃麟主張“寫歷史劇就老老實實只寫歷史,不要去‘創造歷史”[4]。另一派則強調允許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進行虛構。比如茅盾就認為寫歷史劇不必完全按照史實,“但將歷史加倍發揮也是可能的”[5];歐陽玉倩則提出寫歷史劇“只要把要點抓住了,其余的大可不必過于拘泥”[5]。
進入1960年代,對歷史劇創作的討論更加激烈。歷史學家吳晗認為“歷史劇必須有歷史根據,人物、事實都要有根據”,“歷史劇作家在不違反時代的真實性原則下,不去寫這個時代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而寫的是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完全可能發生的事情”[6]。而文學家李希凡則指出“所謂‘歷史劇,就是反映歷史生活的戲”[7],歷史劇的創作取材可以不限于真人真事,“可以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以虛構的人物和故事為情節線索”,“取材于真人真事的歷史劇,應當盡量地符合基本的史實,但也必須允許虛構”[8]。
兩派觀點對立的根本在于“史”和“戲”的性質差異,其共通之處是歷史劇創作都要以歷史真實為前提。而問題在于虛構是否一定要基于歷史事實,還是可以脫離歷史事實基于想象進行虛構。對此,茅盾提出折中意見,認為“史家不能要求歷史劇處處都有歷史根據,正如藝術家(劇作家)不能以藝術創作的特征為借口而完全不顧歷史事實、任意捏造”[9],“任何藝術虛構都不應當是憑空捏造,主觀杜撰,而必須是在現實的基礎上生發出來的”[9]。即不一定事事要有歷史依據,但要有歷史發生的可能性。如此一來,問題就集中在虛構被容許的范圍之上。
進入1980年代,余秋雨就虛構問題提出了7條建議,可以概括為除去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不能虛構外,其他虛構事件和人物要符合事件發生的歷史可能性、符合人物性格發展邏輯、事件與人物之間要有內在統一性[10]。這7條建議對歷史劇創作的虛構范圍進行了限定,得到了大批創作者的認同,成為進入新世紀之前創作者們的主要創作原則。
(二)新歷史主義創作理論
進入1990年代,源自西方的新歷史主義理論開始在國內興起,并影響了歷史劇的創作。新歷史主義基于“互文性理論”,思想核心在于所謂客觀的歷史事實并不一定就是客觀的、真實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直接面對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情而只能通過歷史的文本媒介從觀念出發去重新建構歷史事實”[11],而“歷史文本絕不是純粹的客觀資料,必定是混雜著歷史文本書寫者的各種不同的主觀意識形態酵素”[11]。也就是說歷史文本在構建之時就已經被書寫者根據自己的主觀意識進行了選擇、修改和加工,任何人在解讀歷史文本時又會有自己的主觀解讀。由此,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由一種客觀史觀轉到了主觀史觀[12],主體可以對歷史進行干預和改寫。
當然,這種干預和改寫并不是隨意的,而是闡釋者“基于當下社會語境的一種與歷史的‘對接,對歷史進行‘當代性的書寫”,“以一種人文關懷打破以往歷史表述中僵死的概念和史實,去復現歷史人物鮮活的思想、語言和行為,將其盡量‘還原成被當下的人們所理解的人”[12]。
如此,新歷史主義理論為歷史劇創作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消解了以往討論中歷史必須真實與歷史能否虛構的邊界。歷史劇創作者可以依靠主觀理解,在不歪曲重大史實的前提下對歷史進行闡釋與個人化重構,并提出自己獨有的思考和評價。這為歷史劇的創作提供了虛構或詩化的巨大空間,在符合歷史發生的可能性、歷史內在邏輯的基礎上可以更多地融入創作者的歷史觀,以及與時代語境相結合的敘事方式和現代意識。進入新世紀,創作者們又提出了“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盡管依然遺留了爭論的空間,但它成為創作者們的主要創作原則。
二、新時代歷史劇與傳統文化融合創新的方式
理念的轉換以及新時代傳揚優秀傳統文化的要求,促使創作者們進一步將傳統文化融入新時代歷史劇中。
(一)借助極致還原的服化道展現歷史
一部歷史劇的服化道是最先映入觀眾眼簾的內容,是體現朝代氣質、人物身份和社會面貌的重要方式。新時代歷史劇不僅在服裝、造型、道具方面極盡還原之能事,并且在禮儀、習俗等方面極盡準確化和精細化,比較完整地還原了歷史場景,營造了歷史氛圍。
古代的衣冠制度對服裝有清晰的分類和要求。在服飾上,各部劇所呈現的服飾、配飾皆有據可考。例如《大軍師司馬懿》中士大夫們黑金相間的官服、《大明風華》中女主角大婚時佩戴的“三龍二鳳鑲珠翠冠”、《山河月明》中的翟衣戰甲、冠冕頭飾等皆是依據歷史的高度還原。《清平樂》中女子將珍珠貼在額中、眉梢和嘴角裝點,被稱為“珍珠面花”或“珠翠面花”,此是獨具特色的宋代妝面[13]。這些傳統服飾、配飾、配色等都使畫面呈現典雅的氣質,為劇作提供了視像化的歷史之美[14]。
在禮儀方面,新時代歷史劇對古人的言語、禮儀等進行了模仿與還原。《楚漢傳奇》中大臣在朝堂兩袖張開、碎步疾行的禮儀是臣子對君主所施的“趨禮”,體現尊敬之意。各劇中的拱手、作揖、跪拜等禮節既是對古代禮儀的還原,也展示了禮儀之邦的傳統。稱呼方面,則根據歷史還原當時稱謂。例如,《清平樂》中皆稱自己為“吾”,對皇帝的稱呼亦不是“皇上”,而是“官家”;公主徽柔稱皇后為“嬢嬢”,稱生母為“姐姐”,這是因為宋代嬪妃的孩子皆稱皇后為母親、生母為“姐姐”的規矩所致。
在習俗方面,各部劇都對之進行了挖掘和展現。比如《大明風華》中對“安順地戲”的體現,演出之人佩戴所飾演角色的面具,通過唱、念、做、打來還原作戰場面。據傳此為朱元璋“調北征南”時從軍隊里衍生出來的戲種,而今已被認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平樂》中也較多地出現了傳統節日場面,如端午節、七夕節等。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女子相撲,她們身穿和男子一樣短袖無領的服裝,由此引發了劇中公主徽柔和司馬光之間的爭論。而不論是《大軍師司馬懿》還是《清平樂》,后人所誦讀的詩詞在劇中都以吟唱方式表現,可謂是極度還原的典型。
(二)打造精美的視覺景觀與豐富的視覺意向
除去服化道的精致還原外,新時代歷史劇更加借助影像、視像符號呈現視覺上的美,烘托意境,匹配事件發展、人物心理,在推動敘事的同時,讓受眾感受劇作散發出來的古風古韻。
《清平樂》對畫面構圖非常重視,力圖在有限的畫框內展現畫面構圖的意蘊之美。在劇中經常運用“黃金分割法”,即將拍攝主體放置在位于電視畫面約1/3的地方,以使畫面效果達到最佳,凸顯視覺美感與視覺張力[15]。
《大軍師司馬懿》則除了構圖與畫面精美之外,還善于運用鏡頭畫面將自然景物與人物心理的變化相結合,不僅僅通過自然景物暗示環境變化,還通過自然景物來隱喻人物關系、命運等。比如在第10集中,曹丕選擇司馬懿做自己的幕僚,司馬懿亦放棄不出仕的想法,決定跟隨曹丕。兩人沿山路策馬狂奔,在登高處并肩而立,俯瞰萬方美景,司馬懿朗聲道“于皇時周,陟其高山”,表明自己愿意從此追隨曹丕振翅凌云。此時懸崖外的全景,兩人并肩而立意氣風發的身形,顯示了兩人齊心協力、共赴前路、共看天下的心志。而在第13集中,楊修建言曹操調司馬懿長兄司馬朗入曹植府邸,輔佐曹植以牽制司馬懿。不明就里的曹丕奔至江邊質問司馬懿心意時,畫面靜謐,山水間霧氣繚繞,橋梁若隱若現,這里既表現了風景的空靈、優美,也暗示曹丕和司馬懿兩人關系中的陰霾,以及看不透前路的命運。
新時代歷史劇通過對服化道、禮儀、習俗等的極致還原,精美構圖與畫面意境的傳遞,在極大程度上還原和展示各個朝代的社會風情、社會環境,為敘事提供合理的環境,并傳遞出歷朝歷代風格迥異的審美情趣。
(三)個人化敘事與塑造立體化人物
新時代歷史劇基本將敘事視線集中在了個人身上,從個人成長出發,將個人與家、與國,甚至與整個朝代相聯結。通過個人成長來立體地展現人物、人性、社會風貌和時代氣質,破除固有的臉譜化形象,重構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理解。
電視劇《楚漢傳奇》以出身鄉野的劉邦為主人公,描繪其成長為杰出政治家和帝王的一生,同時全景式再現了秦末漢初的歷史風云。電視劇一改劉邦“流氓皇帝”的刻板形象,既表現他與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也刻畫出他能夠把握歷史機遇、具有政治眼光的政治家的一面,這在以往描述劉邦的電視劇中是少見的。
《大軍師司馬懿》更是突破了史書和小說記載中固定化的形象,以司馬懿的視角為切入點,圍繞曹魏內部的權力斗爭和帝王更迭展開,重現了波瀾壯闊的三國風云。此劇不僅挖掘了司馬懿隱忍沉穩、審時度勢的復雜形象,還將曹操、楊修、荀彧等人物也刻畫得淋漓盡致,塑造了魏國士族階層的群像。
《清平樂》以傳記的方式記錄了宋仁宗登基后治國治家的一生,通過宋仁宗在朝期間的重大事件,展現了宋仁宗的人生及北宋時期的社會生活面貌。全劇從宋仁宗為人君、為人夫、為人父的三個側面,通過朝堂上與言官的斡旋、后宮里與曹皇后的婚姻、女兒徽柔的愛情等線索對他的性格、內心糾葛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刻畫。其中對其“仁”的思想進行了深入的挖掘,符合《宋史》中“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的記載。
另外兩部《大明風華》和《山河月明》也采用同樣的個人化敘事,將主人公的個人成長與明朝歷史相糅合,從微觀入手展現宏觀的歷史風云變遷。
可以說,新時代歷史劇在人物刻畫上力圖脫離傳統歷史劇單一扁平化的塑造方式,更加注重人物多重性格的展現。
(四)家庭化敘事與日常生活化的表達方式
新時代歷史劇不約而同地將“家庭”“家族”視角代入了劇中情節,形成了個人、家庭、國家或時代三線貫通的敘事路線,借助家庭活動展示皇權下家庭內部的摩擦矛盾、和睦溫馨,展示了個人身處家與國之間的掙扎與糾葛。
《大軍師司馬懿》設置了魏國面臨外部戰爭時的內部權力問題、君臣關系、夫妻感情等線索,通過司馬懿及其家族與曹家四代君主之間博弈的暗流涌動,展示了司馬懿的智慧及其對家庭、親情維護的良苦用心。
《清平樂》同樣聚焦了宋仁宗的情感糾葛與家庭生活,卻未落入后宮爭斗的套路化表現,而是將家庭生活、相對零散的情感敘事服務于其勤勉朝政、寬厚待人的帝王人格形象建設[16]。曹皇后的隱忍、張妼晗的跋扈、公主徽柔的任性也都圍繞宋仁宗的“仁”而展開。趙禎的道德要求束縛了皇后活潑開朗的本性,卻放任張妼晗的熱烈情愛,而公主徽柔的婚姻雖然有為人父的考量,但終是想實現內心對生母的孝悌之愿。對宋仁宗情感與家庭的描寫展現了他在前朝、后宮、個人情感平衡中身不由己的悲哀。
《大明風華》則通過以家事寫國事的角度,圍繞以朱棣為中心的生活場景、溫情樸實的親屬、君臣關系,提供各色人物展現空間,將皇家“群像”展示給觀眾。將歷史典故融入家庭對話的敘事之中,將兄弟鬩墻作為希望獲得父親認可的家庭糾葛來處理,語言通俗風趣,使得嚴肅的皇家充滿了民間生活的煙火氣。
《山河月明》同樣充滿了家庭的生活化場景,朱元璋的簡單飯菜、與徐達圍繞兒女婚事上展現出的護子心切等表現,使觀眾感知到朱元璋細膩、真實的家庭生活。
新時代歷史劇將“家”帶入敘事視角,改變了1990年代末將“家”排除在外的創作方法。1990年代的歷史劇對“國家主義”的提煉,是為了將帝王將相或英雄從“家天下”的視角中擇選出來,擺脫以往對“家天下”中帝王將相的批判,轉而指出帝王將相對歷史的貢獻。新時代歷史劇將家庭敘事放入是為了展示人物的公私不同側面,使人物更立體化、人性彰顯更充分。
(五)增加女性敘事視點與女性角色比重
新時代歷史劇增加了女性視點的敘事和女性角色的比重。以往的歷史劇中多以帝王將相或英雄之類的男性形象為主線,女性形象多扮演從不同角度推動敘事發展的輔助角色。有學者將女性形象歸為“幫手”和“犧牲品”兩大類,前者為注定被毀滅和犧牲以成全男性主人公的女性,后者為充當對手的反面女性或淪為政治犧牲品的女性[17]。但在新時代歷史劇中這種現象有所改觀。
《大軍師司馬懿》中司馬懿的原配張春華在劇中與司馬懿相濡以沫,既能相夫教子,也能在危難之時披上戎裝奔赴戰場。比如在第23集中,張春華在曹操死后臨危受命,攜帶魏王璽綬躲避曹彰追殺至鄴城送與曹丕,表現了她的文武雙全和英勇果敢。
《大明風華》是以孫若微這個女性角色視點展開朱家與明代歷史的。孫出場之時的身份是復仇的靖難遺孤,在與朱家的交往中,她逐漸從誅殺朱棣復個人之仇轉向尋求拯救3萬靖難遺孤,顯示出她雖身世飄零,卻愿舍身救人的俠義之心,彰顯其不同于一般女子的見識。
《清平樂》中的曹皇后出身武將世家,入宮前曾跟隨范仲淹學習,可謂是一位文武雙全的女性。此劇雖然將曹皇后描寫成隱忍謙讓、識大體的女子,但也通過突發地震等危急事件,凸顯她在處理災難時臨危不亂、勇敢無懼的品質。
《山河月明》中的徐皇后在朱棣攻打大寧、北平留守薄弱之時,身披盔甲,與朱高熾一起死守城門,對戰李景隆大軍。夜深天涼,令兵士澆灌涼水于城樓,水結成冰,李景隆軍隊難以攻城,一直堅持等到朱棣回師,同樣顯示出了她的有勇有謀。
這些女性角色在劇中演繹得生動具體,豐富了劇中的人物關系,雖然仍是輔助角色,但已不再是單純的男性仰望者,而是雖身居宮闈但深明大義、有擔當的女性,呈現與以往單薄陪襯形象不同的豐富一面。
(六)挖掘以人為本的歷史價值觀
在精美的歷史畫面和波瀾壯闊的歷史變遷背后,新時代歷史劇秉承了“以人為本”的思想,不論是對角色人性化的體現,還是其中所體現的哲學精神都和“以人為本”的思想息息相關。
《楚漢傳奇》描寫了劉邦的“流氓”習氣,同時有層次地刻畫了他成長的心路歷程,即劉邦從開始的迫于秦軍殘暴要活下去,至后來產生為民求生的信念的心路轉變過程。其中,與項羽攻城后坑殺20萬降兵相比,劉邦對百姓堅持秋毫不犯的劇情,符合《史記·高祖本紀》中對他“仁而愛人”的描述。
《大軍師司馬懿》中的司馬懿為了不出仕而自殘雙腿,后為形勢所迫答應曹丕追隨其左右。妻子張春華不解,司馬懿解釋說,亂世之中一個小家風雨飄搖,一代人僥幸躲過戰爭,下一代不一定能如此幸運。良禽擇木而棲,自己的心愿就是能找一個明君,臣之輔之,結束一個亂世,表現了他對于普通人命運的關心。
同樣,《大明風華》中的朱棣之子朱高熾大力主張“仁愛”,幾次三番勸誡朱棣不要發動戰爭,不愿意民不聊生,對于民生的關心貫穿他的思想。
《清平樂》中的公主徽柔與內侍懷吉因行為親密而引起朝堂紛爭,前朝文官紛紛主張誅殺懷吉。趙禎讓懷吉到朝堂見大臣,他告訴朝臣自己維護臺諫制度就是為了民生,“而民其實就在朕的身邊”,趙禎講述了懷吉的悲慘身世,直言“但要天下平寧,亦不能親見一個無辜的生命被犧牲掉”。而大臣韓琦一句“在陛下心中,人最是要緊”,點明了仁宗一生要維護的勤政愛民的思想核心。
三、新時代歷史劇與傳統文化融合創新中的問題
通過上述方式,新時代歷史劇在創作、審美和價值探索上呈現還原、交融與創新的特征,但新歷史劇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創新中存在的問題也很明顯。
(一)過于日常化、現代化的語言表達
新時代歷史劇在歷史場景、文化習俗、服飾禮儀方面都追求極致的復古還原,但是在臺詞上卻呈現過于口語化、現代化的傾向。這固然是出于避免死板、融入現代感、易于觀眾接受的心理,但是臺詞的過于口語化和現代化讓觀眾游離于復古還原的歷史場景之外。這些臺詞基本出現在家庭戲的場景中。比如在《大軍師司馬懿》第6集中,司馬懿想給三弟司馬孚做媒,夸獎弟弟在8個兄弟中最為英俊,這時在一旁的侯吉表明也想讓司馬懿將張屠戶的女兒介紹給自己,司馬懿欣然同意后,侯吉謝道“啊呀,公子,你最英俊”。《大明風華》中此類口語化臺詞也較為常見。如在第2集中,當朱高熾向朱棣提出讓出太子之位時,朱棣也在向朱高熾解釋調其奏折的原因,雙方都在自說自話,最后朱棣說“要不你說,要不我說,搶什么呢”。這些日常化的表達固然給劇情增添了喜劇色彩,但是其語言風格與今人無異,令觀眾一時不知身處哪個時代。
(二)故事情節的過度虛構
新時代歷史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虛構部分。按照“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在符合內在邏輯的基礎上進行大膽假設是可以的,但是出現與歷史不符的人物和故事情節仍是最被詬病的。比如在《楚漢傳奇》中出現儒生在私塾中教孩童們宋朝才問世的《三字經》的鏡頭,稱呼趙高時使用了隋唐以后才有的“太監”一詞。《大軍師司馬懿》中表現了司馬懿不愿無辜者受害,但也有人指出史書記載他在征伐遼東時,曾在襄平城大開殺戒,將城內15歲以上的男子7000多人全部斬殺,與劇中體現的忠孝節義完全不符[18]。而《大明風華》更是將歷史上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的孫皇后和胡善祥演繹成親姐妹,出現了邀請歷史上此時并未抵達過中國的葡萄牙人訓練明軍使用火器等情節,這些劇情與史書記載事實相違[19]。
歷史劇不僅要承擔娛樂觀眾的作用,還要擔負正確傳遞歷史、重塑歷史記憶的使命,脫離基本歷史事實的虛構雖然有助于打破臉譜化的角色塑造,但也可能造成觀眾對歷史認知的混亂。
(三)時代精神融入與創新的欠缺
歷史劇創作不僅僅要傳播歷史知識,還原歷史風貌,也要與當下社會生活相契合,在繼承優秀傳統思想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精神創新出符合當代的思想價值,這是歷史劇在解構和重塑當代歷史記憶和精神方面應該發揮的作用。但部分作品存在止步于歷史事件再現、缺乏時代精神融入的問題。
《大軍師司馬懿》和《清平樂》分別對古代“士”與“仁”的精神進行了較鮮明的挖掘,給觀眾留下了思考與回味的空間。而《楚漢傳奇》盡管在對歷史事件的重新闡釋上體現出深刻的反思精神,但沒有通過劇情和人物刻畫更深入地進行價值觀上的探索,影響了作品的思想厚度。
同樣,《大明風華》和《山河月明》雖然借助個人成長過程展示了時代人物群像和時代變遷,但也僅僅停留于展示,缺乏對思想內涵的提煉,即使是編撰《永樂大典》這樣的文學事件也只是在強調朱棣的用心和功績而已[19],并未展現其應有的歷史價值。
四、結語
從客觀史觀轉向主觀史觀的新歷史主義理論,為歷史劇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創新提供了理論空間。新時代歷史劇在經過了1990年代末新歷史主義初期創作后,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更加敢于大膽假設,在極度還原歷史場景的基礎上,用現代人的思維解讀和闡釋歷史,挖掘古代的精神與智慧以觀照當下。如果說傳統歷史劇是讓現代人走進歷史,理解古人,以古鑒今的話,新時代歷史劇則嘗試做到古今互通,與古人對話,在力圖傳遞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對當今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塑造進行探索。
在新時代歷史劇創作中的虛構邊界問題上,創作者們需要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進行符合歷史邏輯、歷史本質的虛構。在語言表達上,需要把握古代和現代的關系,掌握兩者之間的平衡,在不失歷史氛圍感的同時,讓受眾更好地融入劇作所描繪的時代中去。在時代精神創新問題上,創作者們不僅要對傳統文化中的普世價值進行挖掘,還要思考當下的社會環境和當今時代所需的時代精神,將兩者結合后進行社會價值觀的創新。這對創作者們把握和處理歷史與現實問題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待于創作者們進行更深入的嘗試和探索。
[參考文獻]
習近平.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N].人民日報,2014-02-26(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光明日報,2017-10-28(3).
胡志毅,丁亞平,趙建新.關于戲劇影視歷史劇相關觀念認識的問答[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22(1):53-64.
荃麟.兩點意見[J].戲劇春秋,1942(4):50.
田漢,蔡楚生,胡風,等.歷史劇問題座談[J].戲劇春秋,1942(4):40-48.
吳晗.談歷史劇//[M].戲劇報編輯部.歷史劇論集:第1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265-270.
李希凡.“歷史知識 ”及其他:再答吳晗同志[J].戲劇報,1962(6):43.
李希凡.歷史劇問題的再商榷:答朱寨同志[J].文學評論,1963(1):44-63.
茅盾.關于歷史和歷史劇:從《臥薪嘗膽》的許多不同劇本說起[J].文學評論,1961(5):29.
余秋雨.歷史劇簡論[J].文藝研究,1980(6):43-55.
杜彩.新歷史主義“歷史若文學”的辯證分析:兼論目前歷史題材的電視藝術創作[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0(12):63-67.
白小易.論新歷史主義電視劇的興起與創作策略[J].中國電視,2008(4):47-50.
杜浩.讓傳統文化照進日常生活:從電視劇《清平樂》談起[N].團結報,2020-05-23(6).
牛夢笛.歷史劇:連接歷史 觀照現實[N].光明日報,2022-05-05(22).
王詩瑜.網絡小說改編劇熱播的美學風格探析:以《清平樂》為例[J].新聞前哨,2020(8):104-105.
朱婧雯,歐陽宏生.2020年歷史題材劇創作述評[J].中國電視,2021(5):17-20.
孟麗花.失聲的一群:歷史正劇中的女性形象[J].電影文學,2011(15):38-39.
馬玉林.放過歷史:當下影視劇創作與歷史教育之矛盾:以《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為例[J].南方電視學刊,2017(4):44-46.
曲苑.談古裝歷史劇的問題與出路:以《大明風華》為例[J].中國民族博覽,2022(11):184-186.
[責任編輯 王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