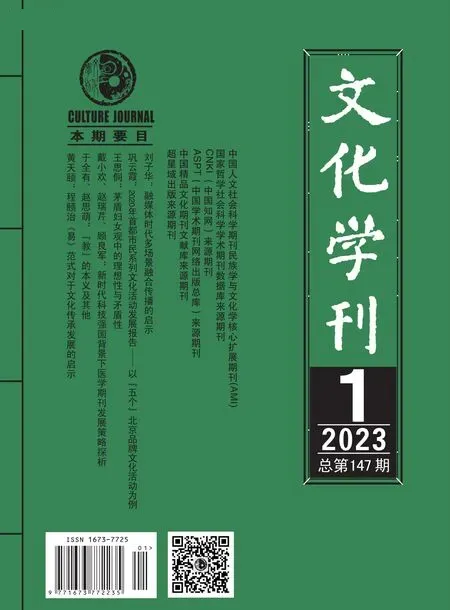山西文化發生·流變·發展:電視劇創作與地緣
頊 瑱
一、導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1]電視劇作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對文化傳播起著重要作用。隨著人民群眾審美水平的日益提高,電視劇創作在融媒體時代面臨著新的發展挑戰。通過中國的電視劇講好中國故事,通過地方電視劇講好地方故事,通過山西電視劇講好山西故事,成為讓世界了解區域文化的重要載體,是電視劇內涵發展的必由之路。
山西省隸屬于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之一,[2]地處太行山西側,名為山西,因古代區劃所致,又名“晉”“三晉”,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在長期發展和對外交往的過程中形成了強烈的地域認同和極具特色的地緣文化。
在電視劇的創作發展中,近年來呈現出以地緣為特點的表現,山西豐厚的文化根基使得這個表現在中國電視劇的創作中顯得尤為突出。呈現地緣特點的影視作品的定義,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認識,總歸而論,無外乎從狹義與廣義上進行區分。從狹義上講,是某一作品集中體現在由某一地區的人或機構作為創作和制片群體;從廣義來講,是某一作品的內容集中體現與某一地區文化、歷史、人物等相關的內容。誠然,山西電視劇必然不能認為就是體現山西題材內容的電視劇,但是,不論從廣義還是狹義的范疇進行研究,對山西文化通過電視劇的形式進行傳承與發展都是有所裨益的。因此,本文的研究內容,將從廣義的山西電視劇的界定入手。
二、山西電視劇發展的地緣結構
山西因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為電視劇的創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山西電視劇呈現出與山西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生與發展相統一的地緣特征。
(一)地緣政治與電視劇發展
山西地處中原,居于戰略要地,在王朝更替、吐故納新的歷史進程之中,地緣政治無疑是其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從幾千年前的傳說時代至今,山西經歷了無數的政權更替和政治變革,始終保持著一股生機勃勃的血脈。地緣政治因素為山西電視劇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提供了政治敘事的資源,補充著政治思想的養分,創作出《上黨戰役》《臨汾攻堅戰》《百團大戰》《八路軍》等優秀作品。
首先,地緣政治造就了山西發展的堅實基礎,長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使山西發展成農業、商業和工業并重的產業格局,較早開始了影視業的嘗試和探索,支撐著山西電視劇的可持續發展。從山西拍攝第一部電影起,山西影視業和山西電視劇就時刻保持著對時代的敏銳,使得思想的力量能夠滲透到基層,普及到人民。改革開放之后,山西電視劇沒有一味追求收視率,在《渴望》創造萬人空巷的收視奇跡的同時期,太原電視臺攝制的12集電視連續劇《新星》則將深邃的目光投向了改革前線,通過古陵縣的改革故事,與時俱進地宣傳黨和國家的先進思想和最新政策,開創了山西電視劇發展的新局面。
其次,地緣政治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歷史人物,為山西電視劇的創作提供了素材。山西古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在政治局勢的變革和邊塞軍事活動的影響下,山西出現了衛青、霍去病、狄仁杰等一批批名將賢臣,他們不僅是古代政治人才的杰出代表,更是古典傳奇和故事中的主角,由太原電視臺攝制的64集電視連續劇《狄仁杰斷案傳奇》不僅以其傳奇性書寫著“東方福爾摩斯”的故事,更以嚴謹的史觀展示了唐代政治的真實狀況。
山西的地緣政治,為山西電視劇的發展提供了積極而有利的條件,多產業兼容發展,繁榮穩定的政治格局為山西電視劇的生產提供了經濟與政策的支持;地緣政治造就的大批歷史人物為山西電視劇的創作提供了敘事資源的支持;任人唯賢、寬政施仁的政治理想為山西電視劇的化育表達提供了思想的支持。
(二)地緣經濟與電視劇發展
電視劇是一門藝術形式,也是一種文化形態,而究其根本則是一種媒介產品,根植于電視產業的發展,而又與地緣經濟狀況深刻地聯系在一起。電視劇的發展初期,并不完全依賴投入與產出平衡的經濟模式,其制作、發行、宣傳等經費更多來源于政府的支持。不可否認,這種傳統模式有其時代原因和現實優勢,使得電視劇的創作能夠不受營收的限制,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優質內容的打造上,第一批山西電視劇創作者,例如張紀中、張紹林等都成長于這種環境之中,他們精益求精的創業精神造就了山西電視劇的輝煌歷史。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市場意識和受眾意識成為了創作者們的必修課,收視率與口碑變為了評價電視劇的雙重標準,而投入與再生產就形成了電視劇生產與銷售的循環模式,顯現出兩極分化的趨勢,大制作、高投資創造著佳作,佳作又吸引著投資和團隊,一旦錯失良機,很容易落入谷底,面臨四面受敵的窘境。
隨著時代的發展,山西省作為能源大省,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經濟建設中,成為祖國能源的大后方保障基地,因持續進行能源輸出導致地方經濟滑坡,文化相對落后,從而形成山西電視劇創作上的壁壘。1980年山西創作出第一部電視劇《祝你們幸福》,[3]我們必須承認,山西電視劇的起步,因為地緣經濟的因素,是落后于全國電視劇的發展的,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山西電視劇很快憑借著其精良的制作和獨特的品格迎頭趕上,開啟了山西電視劇的蓬勃發展階段。
近年來,山西省委、省政府不斷探索,持續推動山西發展戰略的不斷深化、優化,以山西轉型綜改示范區、太忻經濟區為基礎,持續推進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加強對外交流和合作,使得山西經濟再度邁上新的臺階。當下,我們必須深刻意識到山西電視劇發展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在語態年輕化、視聽現代化、傳播全媒化的發展趨勢面前,地緣經濟占據的地位越來越重,山西電視劇也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產業屬性,與山西省產業融合、文旅融合的發展規劃路徑保持高度一致,共同造就山西電視劇發展的新局面。
(三)地緣文化與電視劇發展
文化是人類文明的遺跡和記載,而地緣文化則深深浸透著水土與人的血脈關系,山西襟山帶河的地緣優勢,滋養著山西豐厚的人文內涵,為山西電視劇的發展提供著不竭動力。山西擁有著豐富的地緣文化積淀,使得山西電視劇具備了一種獨特的底蘊和厚度,地緣文化在《一代廉吏于成龍》《日升昌票號》等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
在普通電視觀眾的印象之中,“地上文物看山西”已經成為了山西的一大標簽,山西擁有著豐富的文化景觀和歷史遺存,為山西電視劇的發展提供了一片宏闊的人文背景,古典建筑最直接地呈現出了山西古典文化的獨特魅力。這些承載了人居、信仰、商業、農事等功能的建筑遺存,不僅僅是一座座凝縮了歷史的文化豐碑,更是活態文明的舞臺,是中華文化動態化、影像化的一片富礦。
山西的文化景觀最突出的優勢就在于集成了多重功能,現實中,它是山西人祖祖輩輩營生繁衍的依托;文化上,它承載著晉商文明、三晉文化的厚重積淀;影像上,它展現出了一種獨特的視覺魅力。山西古典景觀與山西電視劇的接合,不僅是山西文化走出去的一種重要途徑,更是文旅融合趨勢中的有益探索。
山西電視劇之中,以《昌晉源票號》為代表的晉商題材電視劇,以一代晉商匯通天下的歷史故事作為依托,以山西第一代金融家的興衰成敗折射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勠力探索,獲得了全國觀眾的好評。晉商題材電視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山西的古城景觀,這種獨特的建筑群落不僅是影像表達的現實載體,更是古典文明的形象注解,使得崇信尚義的晉商文明與山西獨特的文化景觀產生了聯動,接續了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與喬家大院共同創造的文化奇觀,造就了作品推介景觀,景觀烘托作品的雙向互動模式。
山西電視劇對傳統倫理資源的活化和影像化,為中華古典文化的傳承和發揚提供了一條可資借鑒的道路。文化景觀造就了山西電視劇的人文背景,傳統倫理資源實現著電視媒體的化育功能,共同鑄就了山西電視劇在中國熒屏上獨具一格的氣派與格調。
三、山西電視劇創作的時代印記
在電視劇觀眾的刻板印象中,山西是一片傳統而厚重的土地,人們往往對山西的歷史掌故、人文特色耳熟能詳,對于現代的山西、開放的山西和發展的山西不甚了解,山西電視劇在現實題材和革命題材之中的探索,刻畫了山西從古至今的歷史足跡,為今天的山西勾描出愈加鮮明的輪廓,闡釋著山西發展的潛層密碼。
(一)山西電視劇中的故事
山西電視劇中的故事大多有著堅實的基礎,常常以真實的故事原型為依托,即使是原創的虛構作品,也擁有著扎實的故事質地。從時代和類型來看,主要來自歷史和現實這兩大區間,分為古典傳奇和現實故事這兩大部分。
山西歷來就是一片故事的沃土,從傳說時代就一幕幕地上演著數不盡的傳奇,這些故事形成了山西電視劇的重要資源寶庫。作為俗文學的代表,小說與戲曲一向是中國傳統觀眾最青睞的藝術形式,其傳奇性和故事性深深地吸引著一代代國人。山西是古典傳奇的搖籃,古典文化的現代化、媒介化轉譯需要從山西古典傳奇資源的豐富礦藏之中掇菁擷華,以現代意識和全媒手法重塑古典傳奇故事。
古代戲曲之中,三國戲、關公戲一向是舞臺上的壓軸曲目,“蘇三起解”“趙氏孤兒”“西廂記”等故事被一再改編,《狄公案》更是開創了中國探案小說的先河。自古以來的觀眾、讀者之所以對這些優秀人物如此青睞,主要原因還是他們身上承載了中華傳統倫理之中的優秀品格。“楊家將”的傳統曲目是晉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類,由山西電視臺攝制的32集電視連續劇《楊家將》就從晉劇之中獲益頗深,不僅繼承了傳統戲曲的傳奇手筆,更融合了戲劇性與思想性,以英雄與良將敘事結合受眾的接受趣味,以電視畫面的時空延展代替了戲曲舞臺的觀演局限,最大限度地拓寬了優質內容的受眾覆蓋面。
古典文化和當代生活為山西電視劇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故事資源,真實故事的活化和演繹為山西電視劇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和動人的感染力,故事和電視劇創作的雙向互動,既推廣著山西文化和山西魅力,更陶鑄了山西電視劇的獨特品質。
(二)山西電視劇中的土地
黃土高原是山西最具代表性的地理標志,孕育了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但山西還擁有著草原、黃河、峽谷等豐富的地理資源,對于土地這一概念,我們不應將其局限為耕地,而應該將其理解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地貌,一種根植鄉土的人文情結。
所以,山西電視劇之中不乏對農事、農人、鄉土的炙熱情懷,創作出了以《喜耕田的故事》等作品為代表的一大批農業題材作品,展現出了對高天厚土的山西大地的歌頌之情。更重要的是,山西電視劇還試圖對土地背后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進行解讀,在情景關系的古老命題之中為山西大地作出新的注解。《呂梁英雄傳》便是一例,深刻回答了“孕育豪杰之地,是否具有獨到之魅力?”這一問題。將呂梁山獨特的地理背景作為了英雄們施展抱負,保家護國的舞臺,展現出人與土地之間血濃于水的深刻聯系。
山西電視劇中的土地,是農耕文明的史書,是鄉土文化的舞臺,更是家國情懷的載體。
(三)山西電視劇中的印記
山西電視劇不僅具有動人的藝術感染力,更記載著山西發展的歷史,在山西電視劇留下的珍貴影像中,留存著具有史料價值和文獻價值的時代印記。這些影像是時代的寫照,也是文化的定格,如同文字記載一樣,幫助世界了解山西,指引后人洞鑒古今。山西電視劇的時代印記,無論從影像本體論而言,還是從媒介考古學的角度來看,都具有十足的史料價值。
從影像本體論的角度而言,影像是物質現實的復原,是比文字記載更為直觀的歷史,較之嚴謹的方志、正史,更具有個體敘事的色彩,深刻展現了日常生活的變遷、個體情感的流變。例如22集電視連續劇《駝道》,就在劇本的籌備過程中對古代山西的總體經濟狀況、個人收入和消費等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調研,力求還原歷史,在講述晉商故事的同時,對晉商店鋪的經營狀況、古代運輸的具體路線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以治史的嚴謹態度去創設故事的堅實背景。詳實的時代信息使得作品不僅可感可觸,更做到了可信。
從媒介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影像語言與時代一樣,都處于一種動態發展的進程之中,從20世幻80年代至今,電視媒介經歷了三網融合、全媒融合、跨屏傳播的發展歷程,其觀賞條件從過去的家庭觀看逐步走向了個體化欣賞,從有限的有線電視渠道發展為上星播出,目前走向了更加廣闊的新媒體市場。不斷變遷的媒介條件,使得山西電視劇不斷面臨著自我革新的契機與挑戰,從開始的摸著石頭過河,憑借經驗的積累和個人的探索走向了現代化、工業化的制作,從過去聚焦本地觀眾走向了面對全國市場。在媒介和語言的變遷之中,不僅展現了山西電視業的發展歷程,也記載著山西電視劇與山西轉型同頻共振的歷史。
四、結論
“凸顯地域文化的差異性就會形成影像表現和影像創作的多元化,正因地域文化的獨特性才構成了和其他地域的區別所在。”[11]47近年來,山西省在習近平總書記“希望山西在轉型發展上率先蹚出一條新路來”的指示下,銳意探索,踔厲前行,主動打破固有經濟格局和產業形態,迎來了山西經濟、文化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時逢盛世,山西電視劇的發展也迎來了各種利好條件,產生了幾大發展趨勢:全媒體時代呼喚受眾思維,影視工業引領制作升級,經典文化亟需現代轉向,傳奇故事期待時代敘述。
在這樣的背景下,山西電視劇首先必須守好傳統陣地,發揚地緣性優勢,利用好深厚的歷史遺產,以古典文化為依托,以紅色文化為引領,講好山西故事、闡發山西精神、塑造山西形象、展現山西氣派。其次還要利用好山西的中部地區優勢,將山西多元空間巧妙置入敘事背景之中,文旅融合,互相促進。再次,山西電視劇必須向外打開格局,學習和引進影視劇創作的最新成果,在個體化敘事和青春化敘事方面不斷創新,提升作品的時代感和觀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