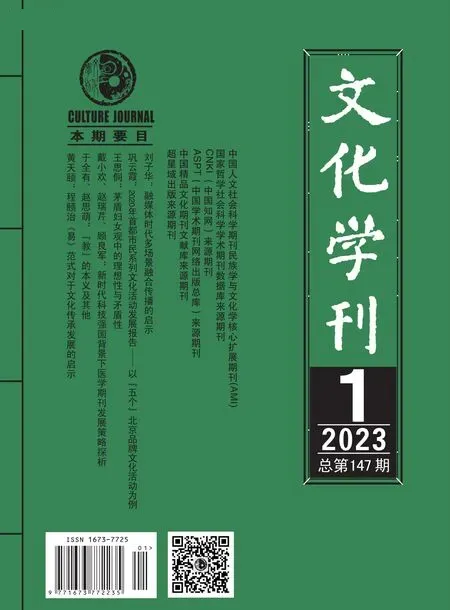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歌對工業(yè)化社會的警示
王靜靜
一、弗羅斯特其人
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 1873—1963)生活在新舊社會秩序交替的過渡時期,經(jīng)歷了傳統(tǒng)文學向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轉(zhuǎn)變。他的詩歌不僅是時代的產(chǎn)物,同時反映了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社會現(xiàn)象。羅伯特·弗羅斯特曾獲得四次普利策詩歌獎,是20世紀美國最具盛名的現(xiàn)代詩人之一。和同時期的其他詩人不同的是,他拒絕隨波逐流地追求形式上的新奇,轉(zhuǎn)而另辟蹊徑,通過傳統(tǒng)的詩歌形式表達新穎獨特的主題。早年的羅伯特·弗羅斯特致力于創(chuàng)作田園詩歌,歌頌自然之美。他善于運用最為質(zhì)樸的語言描繪幽美的田園風光,凸顯新英格蘭悠閑自在的鄉(xiāng)村生活,令人神往不已。到了20世紀30年代,弗羅斯特在他的詩集《新罕布什爾》(NewHampshire, 1932)和《詩歌全集》(CollectedPoems, 1930)中,運用夸張和象征的手法進行田園書寫,但又不局限于表面,賦予了田園風光新的時代和文化內(nèi)涵,同時通過詩歌創(chuàng)作表達其個人對人生的思考和對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社會的擔憂與警示。
當人們稱贊他為偉大的田園詩人時,弗羅斯特自己卻站出來,明確表示“我不是田園詩人,因為在我的詩作中,只有兩篇是沒有描繪人類和人類社會的純田園詩”[1]。因此,僅僅把弗羅斯特看作一位純粹的田園詩人是不夠全面的,他的詩作中一定還蘊含著更多的內(nèi)容。20世紀初,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影響,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的迅速崛起促使美國社會經(jīng)濟空前繁榮,但與此同時,工業(yè)化的快速發(fā)展也造成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失衡,從而引發(fā)了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羅伯特·弗羅斯特被后人譽為“工業(yè)社會的田園詩人”,他的詩歌也致力于揭露工業(yè)化社會急速發(fā)展所導致的消極影響。因此,雖然大部分讀者將弗羅斯特的詩歌歸類為田園詩,但是弗羅斯特在進行自然書寫的同時,也揭示了現(xiàn)代工業(yè)化社會的種種弊端與殘酷現(xiàn)實。作為一個熱愛大自然的現(xiàn)代詩人,弗羅斯特對自然環(huán)境出神入化的描寫映射了在工業(yè)化快速發(fā)展的進程中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同時給予現(xiàn)代社會的人們警示與啟迪[2]。
二、警示之一:工業(yè)化對大自然的破壞
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yè)化的蓬勃發(fā)展促使工廠、機器和商業(yè)產(chǎn)品逐漸走進人類生活。而隨著工業(yè)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田園鄉(xiāng)村也漸漸失去了原有的靜謐與平和。因此,許多詩人開始通過詩歌創(chuàng)作來諷刺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發(fā)展帶來的種種危害,羅伯特·弗羅斯特便是其中之一。但是,與絕大多數(shù)詩人不同的是,弗羅斯特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拒絕直接批評工業(yè)化,而是以自然意象反映社會現(xiàn)實,給讀者帶來警示和啟迪。弗羅斯特的詩集《西流的小河》(West-RunningBrooks,1928)中最后一篇《海龜?shù)芭c機車》(TheEggandtheMachine)[3]349鮮明地對比了緩慢移動的“海龜”和咆哮的“機車”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詩人將海龜擬人化,當看著自己賴以生存的家園——“海灘”即將被機車摧毀時,“海龜”對著機車吶喊,“你們最好不要再來打攪我/打攪這地方/我已全副武裝準備打仗/機車下次再敢開過來/血漿就將在它車窗玻璃上濺開(You’d better not disturb me any more,/ ‘I am armed for war’/The next machine that has the power to pass/ Will get this palm in its goggle glass)”[3]349。“全副武裝”“打仗”“血漿”“濺開”等詞語生動地刻畫出“海龜”在面對自己家園被摧毀時的憤怒,同時也展現(xiàn)了弗羅斯特對資本主義殘暴行徑的痛恨。在傳統(tǒng)的田園生活中,“海龜”這一自然意象本應該在海灘上愜意地享受著大自然饋贈的閑適生活。但是,不斷靠近的“咆哮機車”卻打破了這原本美好的景象,映射了工業(yè)革命進程對大自然的暴力侵占與肆意破壞。而緊接著的“血漿就將在它車窗玻璃上濺開”則清晰地表明了“海龜”想要與暴力“機車”同歸于盡的決心。然而,即使是濺開的血漿也無法阻擋機車的腳步,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家園海灘被繼續(xù)破壞。由此可見,在人力操控的工業(yè)化進程面前,大自然的力量是如此地薄弱,根本無法與之抗衡。
熱愛自然環(huán)境的弗羅斯特經(jīng)歷了美國的工業(yè)革命,他深知,人類為了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不惜以犧牲環(huán)境為代價換取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于是他們毫無節(jié)制地開荒毀林,導致森林銳減,生態(tài)遭到極大的破壞[4]。面對這些,弗羅斯特十分擔憂未來人類是否能與大自然和諧共處,但卻別無他法,只能將擔憂與憤怒轉(zhuǎn)化為文字,警示人們,如果人類繼續(xù)以破壞自然環(huán)境為代價進行工業(yè)發(fā)展,那么大自然將會像“海龜”一樣,壯烈犧牲,用 “血漿”對人類做出懲罰。
三、警示之二:工業(yè)化對人類的剝削
20世紀初,日益加劇的工業(yè)化進程在破壞大自然的同時,對人們的生活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熄滅吧,熄滅——》(“Out,out——” )[3]171-172是弗羅斯特的第三本詩集《山間》(MountainInterval,1916)中的一首詩。這首詩講述了20世紀初發(fā)生在美國佛蒙特州一個鄉(xiāng)村電鋸廠的故事。詩的開頭寫道 “有五道平行的山脈一重疊一重/在夕陽下伸向遠方的佛蒙特州(Five mountains ranges one behind the other/ Under the sunset far into Vermont)”[3]171,描繪了一幅靜謐幽美、夕陽西下的田園風景圖。但是,緊接著重復的“電鋸咆哮低吟(The saw snarled and ratted)”[3]171卻打破了原有的平靜。“咆哮”和“低吟”與“平行的山脈”和“夕陽下的遠方”一動一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此地山明水秀,景色宜人,但是人們卻沒有時間駐足欣賞美景,因為受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的影響,工人們必須爭分奪秒地工作。即使電鋸廠內(nèi)噪音肆虐,生產(chǎn)環(huán)境十分惡劣,鋸木工人們也毫無怨言。與此同時,和其他成年工人不同的是,電鋸廠的童人“男孩兒”卻“非常看重半小時空閑(giving him the half hour)”[3]171,他不停地祈禱,希望能獲得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由此可以推測,在電鋸廠,孩子們做著和成年人一樣辛苦的工作,甚至連“半小時”的休息都成為了一種奢侈,無法得到批準,使得男孩兒不得不“雖說有孩子的心,但卻干著大人的活 (Doing a man’s work, though a child at heart)”[3]171。 在工業(yè)文明的大環(huán)境下,每個人都像機器一樣,不停地運轉(zhuǎn),甚至連年幼的孩子們也難以幸免。資產(chǎn)階級控制的電鋸廠剝削著孩子勞動力的同時,也奪走了屬于孩子們原本幸福快樂的童年生活。
然而,更嚴重的是,當姐姐來叫男孩兒吃飯時,那電鋸卻“突然跳向孩子的手/似乎是跳向——/但想必是他伸出了手。可不管怎樣,電鋸和手沒避免相遇(Leaped out at the boy’s hand, or seemed to leap—/ He must have given the hand. However it was, / Neither refused the meeting. But the hand!)”[3]171。最終,男孩兒搶救無效去世。那電鋸似乎像被賦予了力量似的,刻意去扼殺男孩兒的生命,讓人措手不及。男孩兒的死亡是工業(yè)文明下成千上萬個勞動力被嚴重剝削的縮影。弗羅斯特通過血淋淋的故事警示人們,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的發(fā)展是在以人類的血肉為代價,毫不留情地剝削人類的身體甚至生命。
手被割傷后,男孩兒堅持懇求“姐姐,醫(yī)生來了別讓他砍我的手!( Don’t let him cut my hands off—)”[3]171生命垂危之時,男孩兒竟將“手”看得比“命”還要重要。年幼的他非常清楚,失去了手之后,他就沒有了勞動能力,只能成為家人的負擔。可最終,男孩兒還是因傷死去。這似乎是在告訴我們,生活在工業(yè)化社會,如果失去了手、失去了勞動能力,一切就等于都沒了希望,人類將無生路可尋。電鋸廠坐落在佛蒙特山脈上的一個村莊里。山里的村莊,本應山清水秀,一片祥和;孩子們也本該過著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但是,工業(yè)化的入侵帶來了以電鋸廠為代表的一系列工業(yè)文明,原本的田園生活也隨之被破壞,一去不復返了。弗羅斯特通過這首詩警示人們,工業(yè)化進程在破壞大自然的同時,也在殘忍地剝削人民群眾的勞動力。即使是生活在山間鄉(xiāng)村的農(nóng)民,也無法逃脫被資本主義剝削的命運。
四、警示之三:人際關系的疏離
在工業(yè)文明剝削人類勞動力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慢慢地發(fā)生了變化。在《熄滅吧,熄滅——》中,當男孩兒死去,旁觀者們卻認為“不再有指望了(No more to built on there)”[3]172,“于是他們都轉(zhuǎn)身/去忙各自的事兒(Turned to their affairs)”[3]172,只是因為“他們不是死者(Since they/Were not the one dead)”[3]172。面對突然失去的生命,周圍人的反應顯得極為冷漠。男孩兒家人和工友的麻木,也讓人難以想象。他們似乎來不及吊唁這剛剛逝去的生命,就要“轉(zhuǎn)身”去“忙各自的事兒”。對于他們來說,一條生命似乎還不如工作賺錢重要。在他們看來,物質(zhì)財富高于一切,于是便心甘情愿地接受資本主義的剝削,并樂在其中。這些旁觀者的態(tài)度何嘗不是被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影響的人性?他們麻木、自私、冷漠,只關心個人得失,對他人毫不關心。弗羅斯特用被扼殺的鮮活生命警示我們,“工業(yè)文明在剝削人類勞動力的同時,又剝奪了人們的共情能力”[5],使人的生命在物質(zhì)利益和工作效率面前失去了意義。
弗羅斯特的另一首詩《修墻》(“MendingWall”)[3]47-48是詩集《波士頓以北》(NorthofBoston, 1914)中的第一首詩。作為一首具有戲劇性質(zhì)的敘事詩,《修墻》同樣也反映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離。該詩講述了,因為自然界中“某些神秘的東西不喜歡墻(Someting there is that doesn’t love a wall)”[3]47,導致墻體石頭脫落,因此,敘述者“我”和鄰居相約每年春天都要修墻的故事。很明顯,詩中的意象“墻”是人與人之間隔離的屏障。但是,大自然卻不喜歡墻,于是 “大白天地把墻頭石塊弄得紛紛落(And split the upper boulders in the sun)”[3]47。“大自然”象征著原始的田園生活。那時,人們肆意地生活,鄰里之間是不需要用墻分隔開的。所以,即使人們后來建成了墻,“大自然的力量”還是會堅持讓石塊脫落,拆除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障礙。但是,即便墻體每年都脫落,“我”和鄰居還是不厭其煩,約定每年春天都要修墻。以詩中的敘述者“我”和鄰居為代表的人類,似乎是在不斷地與大自然作斗爭,非要在人與人之間修一堵墻。而他們堅持修墻的理由卻是“他那邊是松樹/我這邊是蘋果園(He is all pine and I am apple orchard)”[3]47,有了這面墻,“我的蘋果樹永遠不會踱過去/吃掉他松樹下的松球(My apple trees will never get across/ And eat the cones under his pines)”[3]47。言外之意就是人們是出于對自我財產(chǎn)的保護才修的墻。工業(yè)文明入侵以前,農(nóng)村的人們習慣了悠閑寧靜的田園生活,鄰里之間相處融洽,不分你我,幾乎沒有人會在意鄰里間的墻體是否脫落。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個人隱私和財富變得尤為重要,以至于鄰里之間形成了一種默契——“籬笆牢,鄰居好(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urs)”[3]48。人們一致認為,有形的高墻能夠保護隱私并阻斷雙方的來往,鄰里之間互不干涉便是最好的狀態(tài),哪怕每年都要修墻,也絲毫不嫌麻煩。可是,人們忽略的是,在“修墻”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也更加遙遠。
在羅伯特·弗羅斯特筆下,人們更加重視物質(zhì)利益和個人財產(chǎn),漠視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人際關系逐漸疏離,人性的冷漠躍然紙上。以至于詩人不由地擔憂“圍進來的是什么,圈出去的又是啥?(What I was walling in or walling out)[3]47”詩人用反問警示人們,如果工業(yè)化進程的方向不加以調(diào)整,那么總有一天,人類最真摯、最純真的情感能力,將會慢慢被物質(zhì)利益取代。
五、結語
通過分析羅伯特·弗羅斯特的三首詩,《海龜?shù)芭c機車》《熄滅吧,熄滅——》和《修墻》,本文揭示了弗羅斯特對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社會的警示。弗羅斯特痛恨人類肆意破壞自然生態(tài)的行為,對資本主義的殘暴行徑深惡痛絕,同時,對未來人與自然能否和諧發(fā)展也感到深深地擔憂。他通過詩歌創(chuàng)作警示人們,在工業(yè)化快速發(fā)展的同時,大自然被破壞,人與自然的關系逐漸失衡,人類的身體和精神被雙重剝削,變得麻木、自私和冷漠。而人與人之間也因為物質(zhì)利益、缺乏溝通,逐漸疏離。這使得詩人不得不憂心,人類社會未來的發(fā)展將何去何從。由此可以看出,羅伯特·弗羅斯特不僅僅是一位浪漫的田園詩人,更是一位憂心社會家國的思想戰(zhàn)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