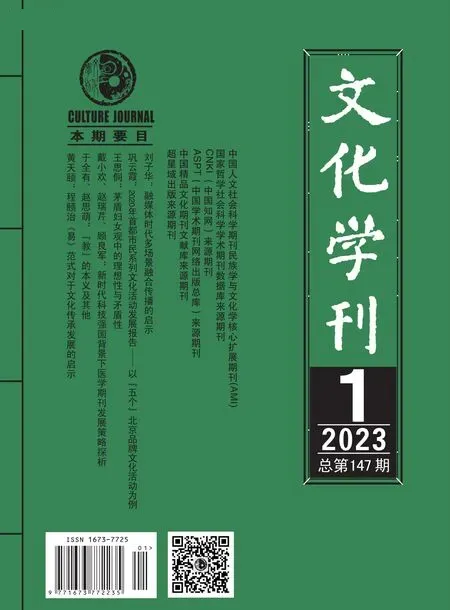嚴歌苓小說《扶桑》隱喻研究
張 覲
嚴歌苓在一次偶然間走入舊金山一間地下室,看到一幅名妓畫像。這位名妓不同于任何妓女,她是雍容華貴的,因此,嚴歌苓查找眾多資料了解這位名妓,最后通過對名妓的認識加之大量的想象創作出《扶桑》。《扶桑》創作背景是在美國淘金熱時期,舊金山淘金區除了男性勞力就是各國妓女,此外不允許任何女性進入,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扶桑——這位有著東方面孔的弱智女性。作為第一代中國移民,扶桑是被踐踏、被侮辱的中國女性,但在國外的艱難生存中,扶桑得到了克里斯和大勇的愛,她能寬容忍耐一切苦難,給第五代中國移民嚴歌苓以極大的鼓勵。[1]作者在文中借用大量的隱喻,表現女性的堅韌和自由,以及東西方文化差異下遠在他鄉的東方人生存的困難。
一、意象隱喻
(一)黑頭發、三寸金蓮——封建傳統東方女性的象征
白人固有的外貌特征是藍眼睛黃頭發,黑人是黑皮膚黑頭發,東方人也有其統一的外貌特征,但在傳統封建社會,黑頭發和三寸金蓮成為東方女性的標配,在國外這一顯著特征更是給東方女性打上烙印[2]。扶桑像所有中國傳統女性一樣,有著三寸甚至不足三寸的兩個木乃伊的玉蘭花苞。在1890年至1940年間,有的中國女性以三寸金蓮招攬顧客維持生計,向他們展示古老的東方,而西方人就在這種展覽中賞玩“退化的東方”。而作為第一代移民扶桑更是因三寸金蓮和黑長發成為白人的玩物,甚至最后一炮而紅成為響徹金山的名妓。阿媽對扶桑的黑發格外喜愛,在扶桑挨打時,阿媽稱贊“真是一頭好頭發——一天要用我半兩梳頭油”[3]6,并叮囑她將頭發緊緊系起,扶桑的三寸金蓮、黑發成為阿媽的賺錢砝碼。在金山這個滿是白人的城市,作為老外的扶桑顯得格外稀有,尤其她所擁有的東方特征引發白人的向往,成為阿媽賺錢的資本,在阿媽賣扶桑時,扶桑的頭發和腳成為阿媽加價的砝碼。扶桑作為東方女性的代表也吸引著克里斯對神秘中國的好奇,激發克里斯對她的憐惜,并萌生出拯救扶桑、拯救中國的理想,但對扶桑來說,克里斯不過是兩千多名白人青年嫖客中的一個普通男孩兒,像所有人一樣不記得他的名字和長相。
扶桑也是典型的封建傳統女性,她嫁給從未見面的丈夫并與公雞行拜堂禮,遵守著夫唱婦隨、相夫教子的傳統禮制,人販子騙她出國時她一心想的還是未給丈夫帶她親手做的八對鞋,到了國外之后服從一切安排,沒有頑強的抵抗,只有一味的忍受。
(二)紅色——中國文化美好的象征
紅色在中國代表喜慶、財富,是美好的象征,但在西方,紅色則成為貶義詞,是危險的標志,代表著殘暴、流血,是火、血的聯想。作為東方女性的扶桑出場就是穿著紅色綢衫,紅鞋,淺紅襪子,她臥室的墻是粉紅色的,帳子也是粉紅色的,作為妓院的一部分裝飾,這里的紅色成為誘惑、曖昧,朦朧的環境刺激嫖客的荷爾蒙。[4]但這也是她的婚禮,扶桑遠赴他鄉就是為了尋找丈夫,她是墨守成規的傳統中國女性,不難發現她在未愛上克里斯之前內心一定有對丈夫的期盼,而她到了金山后身穿紅色綢衫,既代表著阿媽的期盼——扶桑成為每個人的新娘,為阿媽實現賺錢的愿望,也暗含扶桑從未真正做過新娘。作者嚴歌苓如此設計是對扶桑婚禮缺失的彌補,讓她身穿紅色綢衫等待愛情的到來,因此當她再次穿上紅綢衫時是為了克里斯能夠認出她,她的愛情來了。無論紅綢衫,還是丹鳳朝陽的紅蓋頭都成為扶桑追求愛情的標志。她在那頂紅蓋頭下足足等了克里斯一年,在小說最后扶桑身穿紅色盛裝,頭頂丹鳳朝陽的蓋頭,從一匹紅鍛上走來,這是結婚,但她并不是嫁給愛情,是嫁給死亡的婚姻去追尋自由,扶桑得到了釋放。[5]
(三)動物——地位的缺失
扶桑在婆家被當作牲口看待,與一只紅毛公雞完成拜堂,并與這只公雞度過婚禮當晚,女性在古老的中國是卑賤的,沒有主體地位,甚至與牲口相提并論。在蕭紅《呼蘭河傳》中婦女與豬并無二致,甚至卑賤至還不如豬。這種女性主體地位的缺失不單在中國土地上發生,在西方,中國女性仍被當作動物看待,她們的地位并沒有因為環境的轉變而得到改善。扶桑被拐賣到金山時,三叔公用一桿大秤將女仔懸在秤鉤上稱體重,并拿動物與之對比,明碼標價女仔——六元一磅,妓女是他們賺錢的工具,但卻未得到相應的尊重。世界上除了男性就是女性,女性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男性與生俱來的強者姿態處處挾制著女子。大勇鐘愛扶桑,是因為扶桑像動物一樣溫順,不會質疑、詢問,不會做出任何對大勇來說多余的語言反應,文中這樣寫道:“大勇身邊不止坐著扶桑,還坐著狗、鸚鵡、首飾匣。他不時向這幾件寵物投一暼目光。當他見到男人們往扶桑身上瞟來瞟去,他得意地嘆口氣:是寵物就不該單單被一人寵。”[3]136大勇以一種至高無上的姿態審視扶桑,在男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掌控,像大勇對扶桑一樣——寵物可以任人觀之,這其中充滿了大勇對女性地位的蔑視。
在金山,中國男性也同樣受到了牲畜般的待遇,他們一改在中國男權主體的地位,淪為了白人眼中的老鼠,“那老伙夫趴在地上,花白的辮子斷了。他身旁有張紙,上面的字說:瞧這只老鼠,它多么像個人!警惕:我們的老板把老鼠養起來當寵物,因為這些游過太平洋的人性老鼠比人便宜!”[3]58這是男性主體地位的缺失,在他國,東方男性喪失了掌控權,丟掉尊嚴極力迎合該民族的生活方式,試圖取得他人的認可。嚴歌苓在小說中顛覆中國男性的社會地位,讓男性以反面教材出現,進而為爭取女性地位發聲。
(四)瓜子——平靜心態的微妙表達
瓜子一般是用來消遣時光,是人閑情逸致的表現,在《扶桑》中,瓜子只伴隨扶桑出現,扶桑給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身穿紅衫,嗑著瓜子,步姿婀娜,這不僅是給讀者的印象,也是克里斯內心扶桑的形象。克里斯認為沒有任何一個中國女子能像扶桑那樣嗑瓜子,嗑瓜子是扶桑極微妙的一種表達,這種表達對他產生極大的誘惑,使他對這個東方女子充滿了好奇。扶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卻能悠閑自在地嗑瓜子,她對一切苦難都能夠包容,她無力改變困境,而在苦難中享受是她最大的反抗。克里斯藏在扶桑家里時,大勇正好趕到,扶桑這時嗑出的瓜子皮是碎的,“大勇不出所料地嘎嘎笑起來。出了件大事,奇事,她心里章程沒了。瓜子嗑得碎成這樣。”[3]164克里斯的到來使扶桑心里蕩起了漣漪,一向平靜如水的扶桑開始慌了,大勇的出現讓她為克里斯擔憂。嚴歌苓很巧妙地用瓜子表現扶桑的內心。在動蕩不平的城市中,扶桑大概是最平靜的,不為生活煩惱,不為困境痛苦,嗑瓜子是她心境的表達,她是最強大的女人。這種強大對克里斯產生了巨大的誘惑,克里斯與扶桑在學校附近的茶館相遇時,扶桑依舊嗑著瓜子,克里斯驚訝扶桑竟有那么多嗑瓜子的方式,她嗑瓜子的每一舉動都極其動人,克里斯喜歡的不止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扶桑,更是在如此境遇中都依舊從容的扶桑。
二、形象隱喻
(一)扶桑——寬容堅韌的東方女性
扶桑是嚴歌苓本人的真實寫照,在《我的書》訪談中,嚴歌苓表示她所創造的每個人物都像她自己,因為她可以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理解別人,理解他們所做的任何壞事,所以她不恨任何人,就像扶桑的包容,同時她很知足,因為知足才能幸福。扶桑像極了嚴歌苓本人,無論是克里斯對她的強奸,還是其他嫖客對她身體的傷害,她都能夠寬容,她是呆傻的,記不住任何嫖客的名字長相,也可以說她是聰明的,故意不去記憶,因此她是每個人的新娘。扶桑像一個包容萬物的圣母,她愿意忘記每個人對她的傷害,她可以理解每一個人所做的壞事。此外她對任何環境、任何條件都非常知足,即使被拐賣,她只要能吃到東西就很滿足,被大勇安置在紅磚黑頂的小樓里每天接客也從未逃跑,照舊每天嗑著瓜子,享受著擁有的一切,包括苦難。[6]
此外,扶桑更像是受盡苦難但還能選擇包容的中華民族,嚴歌苓表示扶桑名字的寓意是你一直往東走,在最東邊有一棵樹,太陽從樹下升起,是東方的象征;此外扶桑擁有東方面孔、三寸金蓮,在西方國家她就是東方的代表,是東方的標志。中國在19世紀至20世紀遭受了多國的侵略,尤其在第一代移民的清朝時期,國家腐敗,人民愚昧,扶桑正像當時的中國,三寸金蓮是她封建的象征,無知地享受著包辦婚姻,這是封建社會壓制下的國民性,但在第五代移民時期,中國已經實行了改革開放,歡迎一切外來文化經濟的融入。中國在遭受侵犯后選擇包容,選擇和平,這正是中國海納百川的表現,也正像扶桑的寬容。扶桑在最后與大勇結婚,既是對大勇一切罪惡行為的寬容,也是對克里斯拯救般愛情的拒絕,所以她選擇了自由,正如中國可以容納萬物,但堅持獨立自主,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二)大勇——種族歧視的顛覆
大勇有魔鬼式的邪惡,也有天使般的善良。他小時候瞞著家人出國,在國外買馬比賽中設計圈套賺白人利潤,聚集中國勞力集體罷工,并在國外不斷變換姓名開始新的人生,游走自如。他對于第一代移民來說是神話般的存在,這是所有移民渴望的生活,不必受白人的歧視,甚至還能得到白人的尊敬。他別在腰間的飛鏢從未拿出來,只要隨手一撩就讓人聞風喪膽。在所有東方男性在西方受到不公待遇時,大勇憑借著他的機敏不僅使自身得到尊敬,還將白人耍得團團轉,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著中國人。
但大勇對中國人始終持一種矛盾態度:只有我可以欺負你們,別人不可以。大勇買賣妓女,不把東方女性當人看,但在中國勞力被白人打死后,大勇將死在路邊的尸體埋葬,并聚集中國勞力集體罷工。大勇是男權社會的產物,忽視女性主體,但內心存著一絲善良。對他來說他的安慰在于妻子,他明知他的行為邪惡,但那只是為了生存,他最后一定會洗心革面盡心做好一名丈夫,“只有一個人能使他做乏味的規矩人,就是這位妻子。她出現的那天,他將會就地一滾,滾去一身獸皮,如同被巫術變出千形百狀的東西最終還原成人。”[3]70在扶桑被強奸后大勇為了維護扶桑尊嚴產生殺扶桑的想法,東方男性的男權思想因為愛情發生了轉變——他第一次將女性當人看。在他知道扶桑是他的妻子時,他愛扶桑,但是他壓制著這種愛,他不愿意承認自己心目中美好的妻子淪為娼妓,在后來大勇真正愿意接納這個事實后,他兌現承諾改頭換面變為好人。他愛扶桑,但他忍痛將扶桑出嫁,這不僅是因為他知道扶桑愛克里斯,更是對扶桑的愧疚。大勇身上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男權思想,但扶桑成為例外,在國外他沒有曲意逢迎,仍然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顛覆了白人對東方的歧視,最后被囚是自投羅網,向白人展示東方人的尊嚴,中國人決不允許他們歧視中國女性。
(三)克里斯——救華的騎士
克里斯生在白人貴族家庭,歷來接受著反對華人的思想,當他愛上扶桑后,他反對華人意愿更加強烈,他要拯救這個飽受苦難的東方女子,但他并不知道反對華人也意味著反對扶桑。克里斯的名字寓意是圣者、保護者,他永遠在找扶桑,想要拯救她,因此加入反華隊伍去政府請愿,留學歸來成為中國學者,直至后來與扶桑在一起試圖實現對兩個民族的救贖,但克里斯的愛卻遭到扶桑的拒絕,扶桑愛他,但她不需要任何人的救贖與憐憫。
克里斯對扶桑的愛摻雜著私心,他愛扶桑的東方面孔,憐惜扶桑的小腳,沉醉于扶桑的紅綢衫,甚至欣賞扶桑在遭受苦難后仍嗑著瓜子的輕松自在。扶桑褪去紅綢衫穿上白麻襯衫卻未得到克里斯火熱的愛,但當她再次穿上紅衫,克里斯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沉迷于扶桑的紅衫,這樣的紅衫激起他心底的騎士欲望,他對扶桑的沉迷可以說是他救華的騎士欲望。他一直追隨著扶桑的步伐,但是在唐人街的白人暴亂中喪失意志強奸了扶桑,他對扶桑有性的沖動,但歸根結底在他心目中扶桑是一名女奴,因此他會在潛意識中去強奸她,這是不平等地位的開始,他幻想自己是救華的騎士,但扶桑不是他的公主。克里斯是真正使扶桑清醒的人,扶桑仿佛永遠對身邊的事物喪失興致,在船上人員互相毆打時她饒有興致地嗑著瓜子,但在愛上克里斯之后,她開始有了自我意識,記住了克里斯的名字和面孔,重新穿上紅綢衫倔強地逃出教堂,瓜子皮嗑得不再完整,蓋著紅蓋頭等克里斯,甚至最后選擇了死亡婚姻。一貫服從安排的扶桑開始有了意識,追尋自我,克里斯雖然沒有拯救整個民族,但是他喚醒了扶桑。
嚴歌苓豐富的生活經驗為她的創作奠定了基礎,在移民后她能從更深的層面審視民族之間的差異,以一個全新的角度創作了《扶桑》。在這部作品中作者進入歷史與扶桑對話,使小說真真假假,虛實結合,與馬原小說中經常出現的“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作者采用穿插手法對人物進行描寫,并留有空白,使小說極具韻味,加之作者賦予意象、人物獨特深意,闡明她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理解,并呼吁女性主體地位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