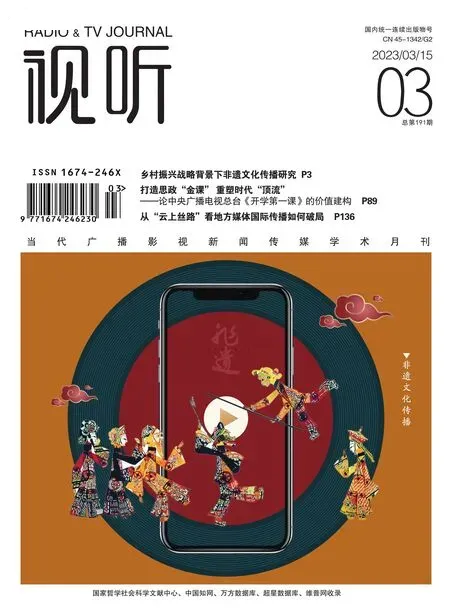認同構建·群像刻畫·精神書寫:法治劇《底線》的敘事研究
◎姚雁羽
法治題材電視劇通常從關乎人民自身權益的法治現實出發,聚焦社會熱點案件,以警察、律師、檢察官、法官為主要敘事對象,具有正義昭彰、天下大同、懲惡揚善等意蘊。近年來的法治劇多取自社會真實案件,如《人民的名義》《破冰行動》《巡回檢查組》《掃黑風暴》等,播出后引起了較好的社會反響。2022年,湖南衛視推出了展示國家司法改革成果的法治劇《底線》。該劇圍繞一系列社會民生的新型矛盾和典型案件,呈現一場場跌宕起伏的調解、扣人心弦的庭審以及公平正義的判決,樹立起新時代司法工作者的形象,彰顯出當代中國與時俱進的法治精神,為我國特色法治劇的敘事策略和社會價值提供了借鑒方向。
一、互文敘事與真實創作:現代法治社會的認同構建
“互文性”表達了不同文本之間相互交錯、彼此依賴的關系。“互文性”的概念最早由法國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認為,“任何文本的構建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引與轉化。”①雖然克里斯蒂娃的觀點是針對小說、文學等語言文本,但隨著影視藝術研究邊界的不斷拓寬,這一理論也逐步被引入到影像文本研究領域。
電視劇《底線》以人民法官為創作原型,以典型的法律案例為創作素材,構建起影像文本與社會現實之間的“互文關系”。例如,“雷星宇案”以2016年山東聊城冠縣的于歡案為原型,探討“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之間的邊界;“駱優優案”以調解節目《杭州和事佬》中“杭漂”女孩洛洛為人物原型,聚焦互聯網快速發展下MCN公司與主播勞動關系的認定問題;“唐嘯云案”改編自吳謝宇弒母案,強調家庭教育對孩子心理健康成長的重要性等。當觀看此類以真實案例為“底片”的電視劇時,大多觀眾已經通過報紙、電視、手機網絡等信息傳播渠道了解了案件的來龍去脈。影像與現實的勾連使得“過去完成時”的現實案件轉變為一種“現在進行時”的在場,不僅迎合了觀眾的好奇心,還極大地提高了觀眾的參與度。《底線》用19個既有普遍性又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作為劇集主要情節的支撐。這些案件關注的議題大多是現實生活中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并且討論度極高的話題。全職太太離婚案、跨國離婚案、校園欺凌案,緊扣婚姻、教育、女性、家庭等熱門議題;明星虛假訴訟案、跨國醫藥集團在華行賄案,探討娛樂圈亂象、跨國犯罪等社會問題。當家長里短的法律糾紛和公序良俗的社會議題在劇中齊聚一堂時,觀者在日常生活中用自身經歷與體悟構建的社會記憶與影像記憶同頻共振。這種互文敘事使得電視傳播內容“不僅作為一種內在驅動力保持了創作者對當下現實的高度敏感,也以一種‘當時當事’的就近時效將價值秩序的混亂和迷茫進行整合,以便更好地對觀眾進行價值共同體的認同構建”②。
需要注意的是,互文敘事在創作過程中要堅持“一切藝術都在于表現人和人的情感”的藝術訓條,平衡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之間的關系。藝術真實不是對社會生活的機械復制、單純還原,而是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對社會生活進行高度概括、提煉升華、變形想象,從而創造出具有審美效應、彰顯生活內在意蘊、反映社會生活本質的藝術形象。因此,藝術創作雖然是虛構的,但卻在更高層面上揭示著生活的真實。這種“內在的逼真”是藝術的根本屬性,也是它不同于歷史、現實的根本特質。③《底線》取材于現實,但并未成為法律案件的拙劣實錄。在選材創作階段,主創團隊牢牢把握溫暖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用一年半的時間深入長沙、北京、上海等60多家各級法院和調解組織采風調研,采訪了200多名一線法院工作者,整理了500多件代表性案件。在萬全準備之后打磨出的劇本做到了真實典型,符合法律規范。劇集拍攝期間,400多位主創歷經4656公里,在長沙170多處地點實地取景,并耗時1200小時搭建共3000平方米的40個法院內景,準備服裝10000套、道具30000件,力求將每個細節都做到極致真實。同時,該劇在扎根現實、保證專業程度的基礎上融入了主創團隊的藝術創作,生動突顯“法律有尺度,法官有溫度”的人性光輝。在“肝癌媽媽離婚案”中,秦玲身患重病,為了母親和女兒今后的生活,決定與假死的“亡夫”離婚,要回房子的繼承權。在離婚公示期結束的最后關頭,秦玲病情再次惡化,眼看丈夫烏剛的詭計就要得逞,她被女兒苗苗的歌聲喚起求生欲,撐過了法院判決,完成了自己人生路上的最后一個愿望。這種“奇跡”的處理為現實的殘酷增添了一絲暖色,讓觀眾在觀劇過程中不僅沉浸于案件的破解與判決,更動容于人與人的情感,彰顯出文藝作品的感化價值。
“我們人人皆知,藝術并不是真實的。藝術是虛構的,但是憑著這一虛構,我們得以認識真實——至少可以使我們了解我們已體會的真實。”④《底線》通過互文性創作將真實案件作為“底片”進行剪貼和復制。劇中的案件如同映射社會生活的鏡子與窗口,客觀展示出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中面對的難題和挑戰。在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指導下,創作者要平衡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關系,生動刻畫出法治改革進程下的具體司法實踐,用符合法律規范又具有戲劇吸引力的判決給人民群眾送上勇氣和希望,塑造觀眾對現代法治社會的價值認同,讓他們真正成為法治社會的參與者與維護者。
二、圈層細分與人物祛魅:現代法官群像的傾情刻畫
《底線》涉及各類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50多起案件貫穿全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該劇透過立案庭、民事庭、刑法庭、知識產權庭,展現了各級各類法官們的專業工作和生活日常,讓多條案件線索彼此交織、相互成全,拓寬了法治題材電視劇的社會面與現實感,僅用40集的體量描繪出豐富的民生圖譜。出于人物塑造及劇情發展的需要,該劇根據法院內部職能分類,對法官群體進行圈層化處理,在不同的職能部門中塑造出兼具司法信仰和人格魅力的圓形人物,樹立起一心為民、與時俱進的新時代司法先鋒群像。
以方遠、葉芯為代表的立案庭,負責受理當事人的請求,對可以調解的案件進行訴前調解,對簡易的案件進行速裁審理;以周亦安、陳康為代表的民事審判庭,主要審理自然人之間的傳統民事案件;以宋羽霏為代表的刑事審判庭,負責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判決;以唐薇為代表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專門處理知識產權案件。這樣的人物設置可以讓觀眾清晰了解到法院內部職能部門的劃分,在對人物的喜愛中潛移默化地接收了法治劇的普法宣傳教育。同時,圈層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緊密相關,例如劇集以張偉民、方遠、周亦安、葉芯為老中青三代法官的代表,設計了資深法官與年輕法官之間的師承關系;以立案庭和民事庭為代表,建構了方遠與法官助理王秀芳、葉芯,周亦安與書記員舒蘇等人的團隊關系。這些人物共同組成了基層法院群像圖譜,將司法職業場景與法官專業形象作為整體予以呈現,打造了一支新時代司法改革下捍衛法律尊嚴和維護人民利益的法官隊伍。除此之外,方遠的扮演者靳東、張偉民的扮演者張志堅都是演技精湛的優質演員,周亦安、葉芯的扮演者分別是近年來通過偶像劇進入觀眾眼簾的成毅和蔡文靜,舒蘇的扮演者是在章回體古裝情景喜劇《武林外傳》中飾演莫小貝的王莎莎。這樣的演員選擇能夠覆蓋老中青三代受眾,彰顯出較強的全民性。
影視創作中有兩種人物塑造方式,一是注重典型性和類型化的扁形人物,二是追求個性與變化的圓形人物。《底線》將敘事對象鎖定在新時代法官群體身上,運用符號和儀式化場景確立職業的神圣性和威嚴性,塑造影視文本的儀式感。法槌、法袍、法官胸前佩戴的法徽以及法庭內法臺后上方正中處懸掛的國徽等符號,強調了法官的責任感和正義感。周亦安入額儀式、張偉民退休儀式等宣誓場景突出了為人民服務的主題。“用判決來維護社會的公序良俗”這一法官的職業精神也在劇中得以彰顯。宋羽霏在“雷星宇案”的庭審中,不斷確認法理客觀和人性溫度所在;方遠努力克服對酗酒者的反感態度,揭開“中介醉酒跳樓案”的背后隱情;年輕法官周亦安為了幫助肝癌媽媽追討撫養費,在和時間賽跑的過程中尋得了人民法官的意義;心高氣傲的葉芯歷經眾多案件后更加堅定了扎根基層的初心。在強調人民法官使命和擔當的同時,《底線》以“祛魅”的手法用心塑造完整的法官人格,展現社會主義新時代法官新面貌,闡述“法官并非神,而是人”的含義,消解了以往法治劇中臉譜化的英雄人物,取而代之的是有笑有淚、有血有肉、立體多面的圓形人物,凸顯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傾向。方遠和“老閨蜜”陳康的斗嘴拆臺、周亦安和葉芯的點滴相處、辦公室里法官與法助的日常相處等情節營造出濃郁的生活氣息,讓劇中人物更接地氣,拉近了法官群體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劇中還運用了大量篇幅來展現人物內心的糾結與選擇,如周亦安在調解韓潔與董瑞的離婚案時,無心說出一句有導向性的話,間接使得男方被女方傷害,因此周亦安懷疑自己難以承擔法官所肩負的重大使命;方遠因離婚案中的孩子撒謊導致判決失誤,一度動搖,有了辭職跳槽進律師事務所的想法;舒蘇和葉芯同時面臨母親觸犯法律的境況,做出“大義滅親”的艱難抉擇。這些情節具有動人、質樸的煙火氣息,從側面證實法官的犧牲付出,讓觀眾看到法官“向上是法的執行者,向下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從而更加認同主人公形象。
作為現實人的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對法理、情理、公道的全面考量體現了中國式法治堅持以人為本的制度特色和堅守人民立場的國家意志。法治劇把司法體系內的法律人塑造為主人公,反映了時代需求。他們作為劇作的主要表現對象,承擔著傳遞國家法治建設方向以及國家法治精神的責任。《底線》通過圈層細分的手法,將法官內部結構劃分清晰,不僅讓觀眾更加了解法院組成結構,還完成了群像圖譜的構建。在單一人物的形象刻畫上,該劇利用各種符號特寫保證了正確的政治導向以及專業水準,又大膽運用“接地氣”的平民化敘事,塑造典型的新時代人民法官群像。劇中法官對法律尊嚴的捍衛、對司法底線的堅守,是支撐法官形象的筋骨與脊柱,更是法治中國的時代精神。
三、矛盾升級與話語更迭:現代法治精神的銀幕書寫
中國傳統文化以禮治為基礎,主張“法律只不過是情理的明確化,是強制性的情理”,認為“情、理結合,構成了傳統中國最普遍的審判基準”。⑤《底線》聚焦現代審判過程中深層次的情法矛盾,向大眾傳播現代司法的概念和精神,同時探索法治劇中法律話語的現代化轉向,展現法治建設成果及法治新思想,完成法治精神的書寫。
早期法治題材電視劇主要借助法律的權威性來懲惡勸善,并沒有深入探討法律本身及司法體系。⑥《底線》不再熱衷案件的動作性與懸疑感,而是將判決本身變成故事最大的懸念,在敘事上以案件審理為線索,通過強化權力與法治、情理與法理的矛盾,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傳遞法律精神,完成敘事戲劇矛盾向法律本體矛盾的升級。劇集以調解室和法庭作為敘事空間,訴訟雙方齊聚在此,提出各自的主張和證據。法官會在撲朔迷離的敘事線索里做出遵循司法正義的判決。在這種抗辯式的二元對立模式下,陳述案件經過是次要的,挖掘案件背后的人間百態和人情冷暖才是核心。內聚焦敘事視角的使用,使觀眾與法官所得到的案件信息是一致的。當觀眾跟隨著法官的動作探明真相,見證符合時代精神、滿足人民期盼、凝聚價值追求的判決時,才更懂得現代法治精神中的法理邏輯與情理考量。在“雷星宇案”中,雷星宇拒絕承認犯罪事實,但宋羽霏堅持法理,認為雷星宇存在主觀殺人動機,在一審中做出無期徒刑的判決處理。當宋羽霏親身經歷外賣員威脅后,她終于意識到自己在刑法裁量中犯了錯誤。二審判決中,宋羽霏改判雷星宇有期徒刑5年。經過這次案件,不僅故事的主人公宋羽霏對法律的理解又上升了一層,觀眾也伴隨著她的成長更加懂得法理和情理的平衡之道。
同時,《底線》借人物之口訴說法律細節,以微觀細節折射司法改革的進程,探索法律話語表達的新方式。第三集中,方遠在最高院和市法院的會議上向于明誠匯報新技術存在的問題,直言不諱這種改革過于急進,看起來更像是面子工程。于明誠接受了這些建議,當眾表揚方遠細心又顧全民眾需求。這其實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話語,表示司法改革不是“空有面子,沒有里子”,是真真切切為人民服務的。第四集中,方遠和周亦安針對“駱優優案”的判決結果展開討論。周亦安擔心類似的案子會接踵而至,方遠則表示中央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搞訴源治理,就是要從源頭上減少糾紛,多元化解決矛盾。知產庭女法官唐薇與丈夫陳濤的離婚案,通過智慧法院隔著大洋彼岸進行云調解。在吳華與符祥的離婚案中,符祥通過掛牌售賣股份來轉移夫妻共同財產,徐天準備飛往廣州處理時,周亦安主動提醒徐天可以通過網絡辦理跨域立案。智慧法院一站式建設、訴源治理、云調解、網上訴訟、電子卷宗這些司法改革成果被融入劇情中,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實現了法律話語的傳遞,讓觀眾對司法改革的創新探索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認同。
劇作還通過大量情節呈現法官們對案件的分析、爭論和審判,在觀念層面關注司法實踐與社會進步的關系,實現舊有法律話語向新興法律話語的更迭。在“駱優優案”中,方遠開創性地認定了主播和平臺的勞動關系,使之成為前所未有的判例。在“雷星宇案”中,宋羽霏二審改判雷星宇5年有期徒刑,將正當防衛的僵尸條款重新激活,不僅遏止了高利貸催收過程中的暴力行為,而且提振了老百姓對司法的信心。整部劇中,“雷星宇案”“中介醉酒跳樓案”“肝癌媽媽離婚案”等案件是對新型社會問題的深度折射,也尋求著與時俱進的理解與解答。在法庭內外關于法律適用與司法判例的辯論與思考中,《底線》改變了過往法治劇中強制性的法律觀念灌輸,用一種不斷進步、不斷反思的法律話語,讓觀眾在情理法的沖突碰撞中體會到新時代司法改革的巨大進步。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靈魂。如果人們沒有法治精神、社會沒有法治風尚,那么法治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根之花、無源之水。從客觀上說,法治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觀念熔鑄到人們的頭腦之中,體現到人們的日常行為之中。⑦《底線》通過情理矛盾的刻畫、法律話語的更迭,傳遞國家法治建設方向以及國家法治精神,培養起觀眾尊重法律權威的意識和依法維護自身權利的習慣等,實現法治劇的社會意義以及價值導向。
四、結語
《底線》在互文性的視野中進行藝術再創造,成功塑造了充滿熱愛和理想的中國式法官形象,折射出對當下重大事件與現代法律精神的藝術思考,成為一部全民普法的生動讀本。作為新時代下法治劇的“出圈”之作,《底線》以高度的社會責任和文化自信為觀眾描繪出生動鮮明的法治建設圖卷,在敘事中表達出“為何善治”“如何善治”等極具中國特色的法治思維,弘揚了現代司法精神,書寫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國法治故事。
注釋:
①[法]茱莉婭·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M].史忠義,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87.
②戴清.電視劇審美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121.
③戴清.論涉案劇中法律要求與藝術規律間的關系[J].電影新作,2004(03):19-22.
④[英]羅伯特.里德.現代藝術哲學[M].孫旗,譯.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67:188.
⑤陳亞平.情·理·法:禮治秩序[J].讀書,2002(01):63-69.
⑥池艷萍.法律的春天:新時期法庭題材電影的歷史語境與敘事探析[J].電影文學,2021(20):64-69.
⑦張宸,閆祥嶺.法治精神是法治的靈魂[N].新華每日電訊,2014-10-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