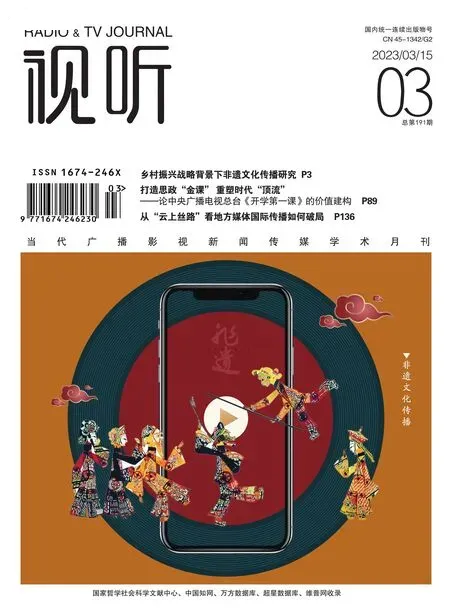青年群體收聽網絡廣播劇的行為現象分析
——以貓耳FM為例
◎陳順嬋
近年來,生活節奏的加快、信息獲取的碎片化、注意力分配的復雜化,使得“耳朵經濟”成為新的媒介特性選擇。“耳朵經濟”彌合了人們在進行視覺消費時可能因需要占有的其他感官而導致的注意力缺失,讓人們只專注于用聽力進行信息的消費,使注意力更加集中。網絡廣播劇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它產生于以社交媒體作為“強連接”的交往時代,以社交媒體為載體和傳播鏈條,有著強烈的后現代特征和亞文化屬性。貓耳FM是專注于ACG(Animation動畫、Comics漫畫、Games游戲)內容的二次元平臺,而網絡廣播劇的受眾多為青少年群體,所以貓耳FM中的網絡廣播劇收聽現象凸顯出亞文化色彩。針對貓耳FM的網絡廣播劇所形成的文化癥候,用伯明翰時期的亞文化理論不能進行充分的解釋,因此本文轉用后亞文化理論,更多關注青年本身的研究路徑,對這一新興的文化現象進行探析,試圖分析當下青年群體收聽網絡廣播劇的行為現象。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網絡問卷為數據收集手段,問卷用于采集收聽網絡廣播劇的群體特征信息,其中包含年齡、性別、學歷、題材偏向和網絡廣播劇收聽動機等。采用網絡問卷調查的方式是因為線下問卷調查會因地域限制而使調查的準確性降低,而網絡問卷調查的方式涉及的范圍和群體更加廣泛,可以獲得更加精準的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的問題是筆者依據對網絡廣播劇文化的了解和在各個網絡廣播劇播放平臺中的參與而設置,并通過問卷星軟件對問題進行編輯后,進行網絡問卷的發放、回收和統計。問卷發放群體的選擇設定為收聽過網絡廣播劇且對網絡廣播劇有一定了解的個體,因為只有對網絡廣播劇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反映出問卷中涉及的個人在收聽網絡廣播劇時的心理活動以及網絡和現實的聯動轉換。截至2022年8月7日,共計發放問卷322份,有效回收問卷320份,有效回收率為99%。
根據網絡問卷的統計結果,從年齡和性別兩個方面來看,收聽網絡廣播劇群體的年齡分布范圍主要是在18~25歲,占樣本的54.04%;收聽群體主要聚集在女性群體中,占比為74.22%。值得一提的是,網絡廣播劇的題材泛屬亞文化類,所以在受眾群體中還會涉及個體的自身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出現不對等的情況,這也在此次調查中出現。
在受訪者的學歷方面,“本科及以上”這一類別的數量最多,占比為52.48%。在此要進行一個說明,此處的學歷并非受訪者的最終學歷,因為此次調查問卷發放的群體涉及18歲以下的個體,這些個體的學歷還未最終定性,且已成年的個體也并非在以后不會對學歷進行提升,所以此處的學歷只能作為調查時間內的限定性參考。
受眾在收聽網絡廣播劇時使用最多的媒介是手機App,占比達76.4%。這與受眾群體的年齡分布大多處于18~25歲相符合,這一群體大多是駐扎在互聯網上的數字原住民,更多通過新媒介消費來進行娛樂。
二、青年群體收聽網絡廣播劇的行為現象
Z世代通常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作為數字原住民,他們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成長,習慣在信息社會中學習和工作,熟悉各種信息技術以及應用服務。因此,他們收聽網絡廣播劇的行為現象頗具代表性。
(一)流動場景:自由出入的情感收納所
在亞文化研究的領域中,場景是指某種具有地域性和亞文化性質的空間。這個空間可以是客觀世界中的實際存在,也可以是在虛擬世界中的想象空間。場景是一個開放性的物理空間,在這里,個體可以自由出入,不完全受制于階層、性別、種族等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體自身的興趣愛好與選擇。在場景中,一切都是流動的,沒有永恒的固定。人們就像是在咖啡廳般的隱喻空間中來了又走的顧客,幾乎沒有人對咖啡廳展現出留戀和不舍。他們只是短暫地停留,或帶有情緒地交談,或靜靜地觀察周圍,不久便又離開。每個人都匆匆來過,便去往下一個地方。而在這個空間中,情感是保留最完整的存在。
貓耳FM的網絡廣播劇涉及玄幻、刑偵、架空歷史等多種類別,通過以網絡小說為文本的結合,對準當前的Z世代,為這一群體描繪了一個個豐富多彩的“想象空間”。此外,互聯網的開放性和匿名性又為青年群體提供了如“狂歡廣場”一般的可以放飛心緒、張揚個性的異度空間。當用戶開始收聽網絡廣播劇時,便進入了這一流動的場景中。在這個媒介為用戶所搭建的虛擬現實的場景里,通過刺激用戶的聽覺,使用戶處于一個置身于故事之中的想象空間里,用戶的情感被他者控制和引導,甚至可以讓用戶產生虛擬的對話和體驗,從而使用戶的情感以無形的狀態存在于這一空間。而網絡廣播劇的彈幕和評論模式的開啟,使用戶能夠在虛擬空間中將可以被看作“所指”的無形的情感轉換成以文字表達的“能指”,讓情感在這一虛擬場景中留下痕跡。然而,用戶并不會長久地存在于這一場景中,它是媒介所創作的虛擬場景,當一節廣播劇結束時,用戶就會退出這一場景,回歸現實世界,但是其在場景中留下的情感卻被收藏。從調查問卷的結果中就可以看出,用戶表示在聽廣播劇時首選的互動方式就是在評論區評論,占比達到41.93%;其次是在粉絲群里討論和發送實時彈幕,占比分別為25.47%和24.53%。同時,有45.65%的人表示自己常在所關注劇集的評論和彈幕里活動。受眾群體在收聽網絡廣播劇時會有很強的畫面感,也會與劇中角色產生共鳴。這種與角色產生的共鳴便是用戶情感的無形表達,用戶在其活動范圍內進行互動之后,便將這一無形的情感轉化成為有形的“痕跡”并被保留下來。此外,在這一流動場景里,用戶的自由出入和場景的情感收納功能配以當代網絡社會的社交狂歡和快感消費,使用戶在現實世界中被壓抑的內心情感得以在虛擬世界中宣泄與釋放。
(二)生活方式:儀式展演塑造文化身份的表意實踐
后亞文化理論是以關注個體的體驗和經驗為主來解讀青年亞文化行為的。在當代都市中,青年個體通過生活方式的展演來認同和重塑自我身份。而在以媒介作為社交傳播載體的當下,“展演”通常是以媒介為表征,通過符號的消費、有品質的生活方式來構建亞文化資本。在一種青年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既有的商品資源、青年個體的生活體驗、青年所處生活區域的風俗與傳統都是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是青年綜合運用上述諸要素的現實結果和青年消費偏好的顯現。
貓耳FM的主要用戶是被稱作數字原住民的Z世代,數字化生存是他們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由于社交媒體幾乎嵌入了他們所有的日常生活實踐,因而他們自我生活方式的建構通常是通過社交媒體中的展演來進行。調查數據顯示,網絡廣播劇的受眾群體在進行互動時所使用的話術符號除了正常交流溝通的語言外,還包括emoji、原文摘錄語句、用角色語氣講話以及顏文字,占比分別為55.28%、52.17%、51.55%以及37.58%。
在貓耳FM這一網絡廣播劇文化聚集地里,用戶通過儀式展演來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呈現自身的生活方式。首先,基于貓耳FM深耕二次元領域的平臺特性,這一平臺的網絡廣播劇也帶有與之相應的二次元文化表征。在用戶的頭像、ID以及評論區中,“(っ╥╯﹏╰╥c)”“(?﹏?)”“兇.jpg”等文字符號,以及ID名“想沈倦了”“人間理想薄景川”等符號,都具有明顯的二次元文化風格。其次,他們還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范圍特點的語言表達模式。在評論區中,很多評論都是“原文摘錄”或“原著解讀”,這樣的方式聯動了廣播劇的文本內容,原文內容的跨媒介遷徙是這一群體生活方式展演的呈現。最后,在收聽廣播劇時,聽眾會同步網絡廣播劇的播放時間,進行定時收聽并發送實時彈幕,與在這一場景中的其他個體進行互動和交流,從而表明自身的文化身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36.34%的聽眾會定時收聽廣播劇并發送實時彈幕進行互動,有39.75%的聽眾表示自己偶爾會定時收聽并發送彈幕。網絡廣播劇的聽眾群體通過這些生活方式,在媒介中進行儀式展演,實現身份認同。
(三)新式部落:賽博空間創造虛擬自由的文化共同體
“新部族”(neo-tribe)一詞由米歇爾·馬弗索利提出,指的是個體通過獨特的儀式及消費習慣來表達集體認同的方式。更多時候,新部族是一種基于感情、共同趣味等聚集在一起的松散的情感部落。在以互聯網為載體的賽博空間,基于亞文化而形成的群體組成了一個新式的部落,在這一新部落中,他們的聚集共創了虛擬的文化共同體。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了文化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定勢而形成的社會群體,是一種特定文化觀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組織層面上的有機統一體。精神契合與情感認同是文化共同體所強調的,它可以給處于這一共同體中的人一種“家”的感覺,并通過情感這一紐帶給其中的人一種歸屬感,使成員有強烈的情感依賴并相互肯定。然而,后現代網絡社會中的個體呈現出分散化和“幽靈”化的社交模式。個體不會長久地聚集于這一部落中,但處于新部落里的個體在共時情況下會有極強的情感鏈接,因而展現出一種既緊緊相連又可能隨時消失的“撕拉”狀態,此處將其稱為“自由的文化共同體”。
貓耳FM網絡廣播劇的創作主要依托網絡文學,很多網絡廣播劇的聽眾都是其原始文本的愛好者與關注者,網絡廣播劇的出現使這些聽眾將關注焦點從文本游移至有聲平臺。在這些聽眾以網絡廣播劇為主體聚集的過程中,形成了后亞文化新部落的表征,即呈現出一個虛擬自由的文化共同體。在這個虛擬自由的文化共同體中表現出三個顯著特征:場域的流動性、社交的純粹化和情感的共享性。通過對貓耳FM網絡廣播劇的分析可以看出,用戶在收聽某一廣播劇時可以在評論區或彈幕區發表評論或實時彈幕,展開賽博社交。他們有時候并不需要處于共時狀態下或某一現實地點中,他們可以通過在賽博空間中留下的情感表達符號形成心理共鳴,從而采取一致的行動。用戶收聽的某一主題的網絡廣播劇就是維系這一部落的情感紐帶,在這一部落中的個體在得到了共同體的自我身份認同和他人認同時,就會因屬于這一共同體而產生對該共同體強烈的情感依賴和成員間的認同,變成如初級群體般的存在,并可以在其中積極互動時獲得情感能量。共同體中的成員將鏈接某主題的網絡廣播劇并視此為這一群體的“神圣物”。為了擁護這一共同體符號的“靈韻”,成員們會通過長期的自我規訓形成部落內統一的部落成員遵循準則,例如擁護作品版權、拒絕劇透、自愿“氪金”消費廣播劇內容、自愿為廣播劇增加流量等。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受眾收聽網絡廣播劇最大的原因是自身是原文愛好者,占比達41.93%;在收聽網絡廣播劇時大概率會遵守這一圈子的規則,占比達39.13%。此外,這一虛擬自由的文化共同體不像傳統的宗族部落一般有嚴格的成員進出準則,對于以某主題的網絡廣播劇為主的文化共同體,其成員是可以自由進出這一新式部落的。例如,當《魔道祖師》網絡廣播劇上線時,其原始文本的粉絲或新來的聽眾會跟隨著每一集的更新在這一部落中“進進出出”。當這一網絡廣播劇完結時,聽眾又會因其結束而離開這一部落。不久后,可能又會有用戶重新聽《魔道祖師》,再次進入這一部落,成為文化共同體中的一員,或是為了重溫劇情,或是為了重新獲取歷時節點中追這一劇集時所擁有的情感體驗。
(四)亞文化資本聚集:次元破壁締造聲優偶像
亞文化資本由桑頓提出,他表明亞文化資本標志著持有者身份的價值形式。同時,桑頓還指出亞文化體系里的媒介不僅作為象征性商品或區隔的標志而存在,還定義和傳播著文化知識。亞文化資本富有和貧瘠之間的區別與媒介的參與有關。在后亞文化視角下,媒介在亞文化傳播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媒介對于亞文化的傳播不再被視為主流文化對其的收編,反而是促進了亞文化對自身的宣傳。
網絡廣播劇在興起之時沒有如今這般的商業平臺和專業設備,其只是基于網絡文學愛好者的自我興趣。他們“為愛發電”,與共同的愛好者用手機或簡單的設備進行廣播劇的錄制,并發布在貼吧、LOFTER、B站等平臺,免費給愛好網絡文學的粉絲收聽,用最低的成本抒發創作者的創作情懷。2010年前后,資本關注到這一領域,發現網絡廣播劇的受眾都是基于其原始文本,即網絡文學,而網絡文學又擁有大量的受眾群體,所以資本開始入駐網絡廣播劇這一領域。網絡廣播劇從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戶原創內容)模式逐漸轉向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專業生產內容)模式,付費模式也應運而生。貓耳FM被B站收購后,得到了更多資本,為更多專業化劇集和專業CV(Character Voice,角色聲音)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在經濟和技術力量的加持下,配音演員的角色和身份被改寫,處于幕后的配音演員開始轉向“前臺”,參加各種商業活動,實現了聲音特質與身體實在的融合,變成了擁有完整形象的人。同時,CV在幕后網絡時期所獲取的流量積累又幫助其順利地打開了粉絲消費市場。這一閉環模式造就了具有造神特性的聲優偶像生產模式。對此,網絡廣播劇聽眾群體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41.93%的人大概率會因為CV去聽一部劇集,也有33.54%和24.84%的人表示自己偶爾會或大概率會去參加CV線下的粉絲見面會或相關廣播劇CV的線下活動。可以看出,經資本搭橋,CV從線上的網絡世界走進了現實中的客觀世界。粉絲為了靠近這一圈子里擁有最多亞文化資本的人,也在現實世界中展開追星模式,讓CV如明星偶像一般成為某一群體、某一范圍內的“神話”。
以貓耳FM網絡廣播劇的CV為例,他們大多是早先網絡小說的愛好者,出于興趣,將純粹的視覺信息獲取轉變為聽覺信息獲取。因為他們從最開始就存在于這種二次元文化中,所以他們是具身化般的存在,在其中的長期浸潤使他們獲得了關于這一文化的特有經驗、知識和技巧。這一點是可以區別于新來者的。與后伯明翰時期的亞文化群體特性不同,資本的入駐并不能直接影響和侵奪他們在具身化體驗下所獲得的“品味”,所以資本就與其合作,將CV所擁有的亞文化資本轉化成實在利潤。在這一過程中,CV在保持自身的“品味”之時還宣傳擴展了這一文化,二者之間并不是二元對立的抵抗式關系,而是“均勢妥協”般的合作關系。這一合作便成功助推了聲優偶像的出現。例如,楊天翔和劉琮兩位聲優出現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時,上千名粉絲舉著應援手符吸引注意力,尖叫和歡呼淹沒了大半個會場。這并不是在某個偶像演唱會上的景象,而是在一個二次元盛典——COMICUP23魔都同人展的廣播劇《默讀》的聲優見面會上。
三、結語
數字時代,個人的社會化與社會的進程都離不開數字媒介的參與。當代青年群體作為與時代同步的成長者和未來的希望,被賦予極高的期待。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青年所肩負的責任與擔當給予肯定:“青年猶如大地上茁壯成長的小樹,總有一天會長成參天大樹,撐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升的朝陽,不斷積聚著能量,總有一刻會把光和熱灑滿大地。黨和國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本文通過分析當代青年群體收聽網絡廣播劇的行為現象,對當代青年群體的文化行為進行展現,以期促進成年群體對青年群體的理解和認同。在成年群體對青年群體進行了解之時,也可以擴大網絡廣播劇這一“新事物”的傳播范圍,由此將當代青年文化的關注熱點與當前主流文化進一步融合,使青年不再被看作與主流文化對抗的邊緣群體,從而促進我國對當代青年價值觀和行為方向的積極引導,發揮青年群體對社會發展和國家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