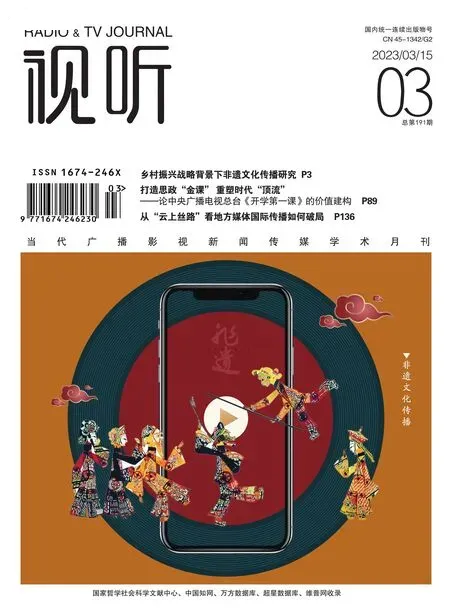從閱讀到觀看:融媒時代古籍文化視覺傳播的敘事轉向
——以《典籍里的中國》為例
◎李瑩瑩 汪雪吟 張赟
中國古典書籍是千年來先人智慧的結晶,書籍內容與背后故事所承載的思想精神對后世具有較大的借鑒價值。然而,文言文式的古籍“不易讀,不易傳”限制了其文化精神的延續與輸出。媒介融合時代,視覺技術的發展更迭了傳統文化節目形態,使中國文化實現多維度立體呈現,展示出我國文化精神的時代風采。《典籍里的中國》順應時代發展,挖掘典籍精神,打造典籍劇本故事,借助媒介技術可視化地呈現典籍文化,并打造時空場景創新典籍的視覺敘事方式,讓典籍里的文字活起來,使典籍平面化閱讀走向典籍立體化觀看,實現了經典的大眾化傳播。值得一提的是,該節目通過跨時空敘事使典籍文化與時代精神相連接,展示古今文化的一脈相承,塑造并實現了“今人讀古人,并汲取智慧,走向未來”的思想價值。基于此,本文立足于融媒時代,以《典籍里的中國》為例探究當下古籍文化視覺傳播的敘事轉向,并探討這種新視覺傳播給中國文化帶來的價值與意義。
一、融媒時代古籍文化的“新”視覺敘事
(一)時間維度:多主線并行的穿越敘事
數字化時代,信息的碎片化傳播難以支撐厚重的典籍價值,更不能使海量典籍文本發揮較大的社會價值。為了使典籍精神多維度呈現出來,可以采用“復調”的敘事方式。復調在影視創作中可以看作是一種多線并行的敘事方式,在不同思維敘事路線中,各自的故事都是獨立分開的,但又都是完整劇情的一個重要部分。只有了解所有的敘事環節,才能了解完整的敘事內容。①在《典籍里的中國》中,復調主要體現在節目的時間呈現上,其擺脫了傳統節目按單向時間進行敘事的邏輯,通過多個時間點切入,從今人與古人視角去展示他們眼中的書籍文化。古人、今人和專家解說看似獨立存在,但通過融合古今對話以及專家對文化的延伸,讓觀眾從多個視角了解典籍文化,放大文化的張力,呈現并詮釋了完整的典籍節目與深刻的價值觀。
《典籍里的中國》以多視角敘事為出發點創造平行時空。一方面,節目通過跨時空對比的敘事角度,突出典籍文化的傳承精神。節目打造“當代讀書人”與“古代讀書人”兩個視角,在道具上同時設置了古今元素,比如平板電腦、高鐵與竹木書簡、馬車的對比鏡頭,體現出千年以來時代的巨大變革。從紙質書到電子書,從書屋到圖書館,文化載體不斷變更,唯獨不變的是現代人對古人讀書毅力的繼承,發揮了節目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面,節目創新地使用了“穿越交流”的跨時空敘事。撒貝寧擔任“當代讀書人”,穿過“甬道”,遇見古人,由此誕生一場跨越千年的對話。由此可見,典籍里的文字脫離了紙張,活化為穿越時空的對話。這時,看書人變為觀眾或者聆聽者,一同隨撒貝寧與古人交流,可以近距離了解先人事跡,感受古人對我們思想的啟迪。
(二)空間維度:立體化場景的沉浸敘事
從“空間轉向”的視角看,有些節目開始打造異質性影像空間,即區別于現實空間的呈現,通過打造虛擬空間,強調人與空間之間的想象、認知、情節與回憶。②《典籍里的中國》通過舞臺布置與人物設定,為觀眾創造了一個近乎虛擬的空間場景,帶領觀眾跟隨人物走入歷史。以第一期《尚書》舞臺設置為例,一號主舞臺演大禹定九州、牧野宣誓等大場面;二號舞臺是浮生的書房;三號舞臺分為兩層,上層是大禹治水的空間,下層是浮生幼年讀書的地方;四號舞臺是甬道,可以通過聯通各舞臺體現跨時空對話的全新創作理念。多維度的舞臺設計既獨立又連接,通過留白帶給觀眾歷史想象,通過融合連接喚醒觀眾的歷史記憶。例如,扶生在幼年書房讀書,會讓人想象他的后半輩子是如何護書的,在老年與撒貝寧對話的書房則讓人回憶他一生護《書》的顛沛流離。
傳統的節目舞臺空間布局較為單一,并不足以滿足觀眾的審美需求。融媒時代的傳播更加注重用戶的在場化和具身化。在具身傳播中,認知、身體與傳播環境處在相互耦合的動力系統之中。③從這點來說,環境、認知與身體是具身傳播的靈魂。《典籍里的中國》中,空間環境的制作較大限度地利用了當下大火的智能技術,用4K高清大屏呈現千年歷史,觀眾席270度旋轉座位帶領觀眾感受多維空間,并通過現場空間舞美、道具以及老戲骨的演技再現歷史場景。這些視聽技術為觀眾帶來沉浸式的空間,連接觀眾的情感,讓觀眾仿佛身處其中。
(三)邏輯維度:情理雙維度的融合敘事
美國文學理論家杰姆遜認為,“文化從來不是哲學的,文化其實是講故事。觀念性的東西能取得的效果是很弱的,而文化中的敘事有著重要的作用和影響。”④可見,純觀念性的價值是難以傳播的,中國傳統典籍文化雖然承載著民族文化,但是枯燥難懂的觀念性文言文與閱讀受限的紙質媒介成為古籍文化傳播的隔閡。如何深耕并延續文化內核價值,創造完美的故事化敘事,實現更為廣泛的流動與傳播,是當下文化節目制作需要考慮的重點。
基于此,文化節目的制作需要將理性敘事和感性敘事相融合,在理性敘事邏輯中還原歷史的真實性,尋求其主流價值所在,防止胡編亂造導致節目成為無歷史依據的“戲說”。⑤應在感性敘事邏輯中重塑文化樣態,賦予其形象性和沉浸性的特點,使“文字活起來”。從理性敘事的價值維度來看,《典籍里的中國》節目組立足于我國海量的文學典籍,經過篩選過濾,找到了具有代表性的11部典籍,這些典籍對當下發展有著實用性指導與精神指引的作用。比如,《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一部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科技著作,為后世科技發展提供了參考。從感性敘事的傳播維度來看,《典籍里的中國》采取“戲劇+影視”的表現手法,將典籍文字進行戲劇化表達,以故事的形式呈現給觀眾,同時邀請業界著名專家進行參會品讀,保證了歷史節目的可信度,為觀眾講述典籍故事,打造典籍世界,使其更好地理解節目的文化價值。
二、融媒時代古籍文化視覺傳播的轉向
(一)經典內容的大眾化轉向
中國傳統古典書籍文言文式的呈現方式使其流傳人群固定于文學水平較高的群體,這難免會使古籍文化的傳播呈現“曲高和寡”的狀況。尤其是在如今娛樂節目遍地開花的時代,枯燥乏味的書籍難以激起年輕人活躍的熱情。融媒時代強調“用戶”理念,《典籍里的中國》基于此原則,成功創新,使得經典走向大眾。一方面,節目促使觀眾從被動變成主動,一改傳統文化節目以“舞臺為主,觀眾為輔”的敘事風格,突出觀眾視角。最能體現這一點的就是主持人功能角色的轉變。傳統節目主持人向觀眾介紹內容,但是《典籍里的中國》的主持人被賦予觀眾的身份,主持人撒貝寧和王嘉寧與觀眾一樣,都是“當代讀書人”,他們帶領觀眾置身于典籍之中。這種“以我為主”的敘事形態帶動了觀眾觀看的熱情。另一方面,節目將典籍文學延伸為典籍故事。正如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里說的“世間的一切盡是故事”⑥,文學里也是如此。當把典籍文學以故事的形式呈現出來時,它就不再是望塵莫及的高嶺之花,而是走向大眾,綻放它的獨特魅力。《典籍里的中國》第一期扶生傳書的故事播出后,引發圈層化傳播,節目的網絡播放量超過1.6次,微博話題閱讀量超過7億次。⑦觀眾在各個平臺紛紛談論文化傳播、民族精神等相關熱詞。可見,典籍故事不僅使得文化走向大眾,而且通過多平臺的跨媒介敘事實現了典籍文化的破圈傳播。
(二)文字傳播的多模態轉向
文字作為承載信息的媒介,可以被劃分到麥克盧漢提出的“冷媒介”范疇中,其信息呈現不夠清晰,需要讀者根據想象彌補文字留下的空白。但是基于中國典籍的特征,讀者難以理解其深層含義。首先是文本特點,中國典籍文言文的寫作方式不利于當下讀者的閱讀習慣。其次是典籍創作環境,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帶來生活背景的不同也會造成古人與今人的理解差異,如果把純文字的古籍照搬到讀者面前,讀者可能難以理解其思想含義。由此可見,當下文化傳播需要借助專業的文化研究團隊對典籍進行思想挖掘,再結合視覺技術對古籍文字進行具象化多模態轉型。
《典籍里的中國》節目主創團隊聯合歷史專家對典籍文化深入剖析考究,使典籍文化從單一的文字轉化為影像、戲劇等多模態形式,并在道具、舞美、專家、演員等認真磨合下深度再現歷史場景,講述典籍文化。從文化場景展現來看,節目演員出場的試衣間里,每件衣服都參考了當時朝代的服裝背景,演員服裝造型依據書中人物原型設計。比如,倪大紅老師把近百歲的扶生演得深入人心,蒼白的頭發、佝僂的身型以及精心的妝造可謂是入木三分。從文化內容來看,高清影像畫面、環環相扣的故事情節與清晰的音效等元素相互融合,直擊觀眾心靈,拉近他們與典籍文化的距離。比如《本草綱目》這期節目,當王世貞先生問起李時珍多少年著成《本草綱目》時,畫面給了李時珍特寫,音效悲壯且激昂,使觀眾產生共情。值得一提的是,專家解說、演員讀書等環節讓觀眾進一步了解典籍文化,集體感受典籍力量。當下古籍文化傳播將文字從書中拎起,以多模態方式活化文字力量,傳遞典籍精神,立體真實地展示出古籍文化與先人精神。
(三)閱讀方式的立體化轉向
千百年前,古人以文字記得失,讀者以文字識知識,考生以文字獲功名。通過閱讀文字學習知識,已經延續了幾千年。電子信息時代,電子書呈現在讀者面前,但是獲取文化知識仍然離不開平面閱讀。直至今天,在技術賦能的融媒時代,“全程、全息、全員、全效”的四全媒體格局早已更迭了傳統文化節目的呈現樣態,VR、3D裸眼等技術的發展甚至使文化信息的傳播突破了平面化的紙張或屏幕,走向立體化的空間。讀者閱讀模式的改變表明,視覺文化傳播維度逐漸從單一化走向多樣化,從平面化走向立體化。
《典籍里的中國》借助新媒體技術,通過打造立體化文化傳播的視聽盛宴,將讀者轉變為觀眾,實現從閱讀書籍到觀看文化的升級。在空間維度上,多舞臺的布景與觀眾席旋轉的設置為觀眾提供了沉浸式的場景。在視覺維度上,節目通過古香古色的場景構建加深歷史感,深化主題;借助投屏技術,將歷史場景適宜地展示在環屏上,展示壯闊激揚的大場面,與主舞臺相互融合,共同演繹典籍故事。在聽覺維度上,節目通過音樂的助力,突出場景的立體感。比如《尚書》中武王伐紂的場面,視覺場景里的人物演繹與聽覺維度上的雷鳴聲、宣誓聲融為一體,突出反紂的決心,強烈的視聽沖擊引發觀眾的共情。由此可見,文化知識的三維呈現改變了傳統的閱讀方式,通過立體化閱讀進行沉浸式觀看,通過共情完成觀眾對節目價值觀的認同。
三、立體觀看視角下古籍文化視覺傳播的價值
(一)場景化敘事激發觀眾共情,增加文化的集體認同
場景化敘事致力于為觀眾創造超真實的空間,進行立體化演繹,以達到從感官維度喚起共鳴、從情感維度喚起共情、從認知維度打造認同的目的。從感官角度看,通過AR、4K等媒介技術和節目中服飾、舞臺、道具等的綜合應用,《典籍里的中國》為觀眾打造了沉浸式空間,增加了節目的儀式感,從聽覺維度到視覺維度,全方位引發觀眾共鳴。從情感維度看,節目通過實力派演員的演繹和互動調動觀眾情緒。比如王勁松老師扮演的李時珍角色,耗費30年著成《本草綱目》,但一生未見其出版。當他“跨越時空”,看到王嘉寧手中的《本草綱目》出版后,難以置信地說:“謝謝你,讓我看到了《本草綱目》。”真情流露的表演瞬間使觀眾產生共情,引發對古人精神毅力的敬佩。從認知維度看,節目通過塑造先賢人物形象、打磨劇本,將中國文化融于人物、融于故事,深化了“為人民服務”“堅毅勇敢”等價值觀,促進了觀眾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認同。
(二)跨時空敘事書寫古今文化,強調精神的一脈相承
德國學者揚·阿斯曼認為,在文化記憶中,過去不是表現為一個事件接另一個事件的時間順序,文化記憶的選擇是依據當下的需求對過去賦予新的意義的過程。⑧觀看視角下,文化傳播最重要的節目內容就是抓住觀眾眼球,強調敘事邏輯。按照文化記憶的邏輯,我們對于過去的回憶不是按照時間順序一個個堆著來的,而是選取有價值的事件,從中獲得啟示,從而以古鑒今。《典籍里的中國》打破傳統時間敘事,通過跨時空敘事書寫中國古今文化。在思想連接方面,節目制作團隊與專業歷史研究員對典籍文化進行深入了解,并立足于當今中國形勢,挖掘典籍中值得傳承的中國思想,引導觀眾將典籍思想與當下時代精神相聯系。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與當下“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理念相互承接。在思想延續方面,節目通過古人和今人的互動,以比較視角突出歷史對當下的影響以及當下時代的巨大變革,從而引導今人延續典籍思想,書寫當下中國故事。比如,袁隆平與宋應星穿越千年的握手意義非凡。兩人共同的“禾下乘涼夢”說明,從古至今,“農本思想”一直是人們關注的重點,當代人依然需要為此努力。
四、結語
《典籍里的中國》深挖主流價值,活化典籍文字,創新視覺敘事方式,打造了典籍傳播的新型視覺盛宴,使視覺文化傳播方式從平面閱讀走向立體觀看,改變了傳統典籍“不易讀,不易傳”的困境,真正樹立了典籍文化“立時代之潮流,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的價值傳承。融媒時代,文化的新型敘事方式通過增強文化的視覺張力和塑造文化傳播的沉浸場景,使文化精神映入人們的眼簾,嵌入人們的認知體系中。未來,古籍文化節目會更好地與融媒體技術相結合,持續傳誦經典,傳播華夏精神,書寫中國故事。
注釋:
①潘源.《典籍里的中國》:沉浸式電視文化節目的敘事特征與空間呈現[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1(08):49-51.
②湯天甜,溫曼露.譜系并列、空間敘事與價值書寫——文化類電視節目的媒介推演策略[J].中國電視,2020(06):68-71.
③楊國藏,張立改,馬瑞賢.中國文化的多模態具身傳播——以《典籍里的中國》為例[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2(04):118-120.
④[美]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唐小兵,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77.
⑤林陽,徐樹華.融媒時代中華傳統文化視聽傳播的新范本——論《典籍里的中國》的創新價值[J].中國廣播,2022(03):56-60.
⑥[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M].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0.
⑦《典籍里的中國》:讓典籍“點”亮來路[EB/OL].中國新聞網,2021-02-2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659632036235501&wfr=spider&for=pc.
⑧羅奕,張小姣.《典籍里的中國》的文化記憶建構機制解析[J].傳媒,2022(18):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