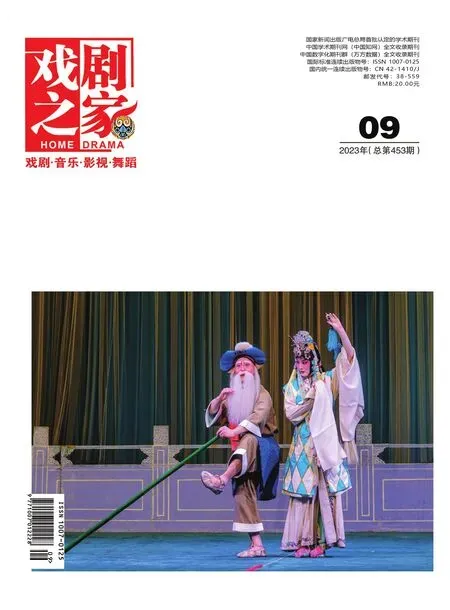歌劇《沂蒙山》中海棠主要唱段的音樂特征與演唱分析
——以《等著我,親愛的人》為例
馬 瀅
(聊城大學 山東 聊城 252000)
一、《沂蒙山》選段《等著我,親愛的人》概述
(一)歌劇《沂蒙山》的創(chuàng)作背景
從第一部反映抗戰(zhàn)題材的大型歌劇《秋子》,到具有里程碑式的中國第一部新歌劇《白毛女》,從歌頌了革命者堅貞不屈精神的《江姐》,到我國知識分子敢于向封建舊勢力挑戰(zhàn)的《傷逝》,中國民族歌劇從發(fā)展至今誕生了非常多優(yōu)秀作品,以中國紅色革命故事為題材,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頑強斗爭的革命精神,民族歌劇的發(fā)展在中國音樂領域熠熠生輝。
為加強文化自信和貫徹習總書記對紅色沂蒙精神的重要講話與指示,由山東省委宣傳部直接領導,山東歌舞劇院創(chuàng)作并演出的歌劇《沂蒙山》立足于沂蒙淵子涯這片革命熱土,將中國地方音樂與西方音樂的創(chuàng)作模式相結合,充分展現了沂蒙精神的文化內蘊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經過兩年的精心打磨,于2018年12 月正式登上舞臺。該歌劇制作團隊專業(yè)且龐大,由欒凱作曲,李文緒、王曉嶺作詞,演唱形式豐富,包含獨唱、重唱、混聲合唱等。整部歌劇分6 幕,共有39 個唱段,其中《沂蒙山小調》作為發(fā)展動機貫穿全曲,出現在每一個重要的節(jié)點,展現了獨特且濃郁的山東地方特色。
(二)《等著我,親愛的人》的劇情脈絡
歌劇《沂蒙山》共有六幕,其中歌曲選段《等著我,親愛的人》共出現了三次,分別以男女二重唱和女高音獨唱的方式呈現。第一次出現在第二幕林生家旁邊的場院,此時正值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山東戰(zhàn)場發(fā)展為全省性的革命根據地,在沂蒙山深處的崖子莊村口,村民們正在緊鑼密鼓地操辦林生和海棠的婚禮,大紅綢緞映在人們喜氣洋洋的臉上,熱烈而美好的氣氛卻隨之被打破——鬼子進村了!村民們決心跟隨八路軍上陣殺敵,新婚的林生和剛剛懷孕的海棠也面臨著分別,他們的命運也隨著劇情的發(fā)展,成為整部歌劇的重要轉折,重要唱段《等著我,親愛的人》便出現在這里。歌曲第二次出現是在第四幕中,海棠因疲勞過度昏倒了,在夢里她和林生重逢了,雖然唱的還是他們離別時唱的歌,但這次表達的更多是對相隔萬里的愛人的思念。在這段表演中,男女主的目光從頭到尾沒有交流,也隱隱地展現了夢境的虛幻以及為林生的犧牲埋下了伏筆。第五幕的海棠獨唱中,雖然是相同的唱段,觀眾體會到的卻是不同的感情。從最初的滿懷希望,到在無盡的思念中感到絕望,在這種情感的轉變中,海棠這一形象也深深地印在了觀眾心里,讓人不禁感嘆她舍小家保大家的勇氣與犧牲。
二、《等著我,親愛的人》的音樂特征分析
(一)曲式結構分析
本曲的整體結構為單二部曲式,由A、B、B1 三部分組合而成,4/4 拍子。
歌曲引子部分為前8 小節(jié),降G 宮調式,在樂曲開頭采用了模進的發(fā)展手法,為橫向的旋律展開提供了動力性,為新的對比材料的形成做鋪墊。第五到第八小節(jié)音的骨架不變,但節(jié)奏變得更加規(guī)整,織體加厚,體現了樂思的延續(xù)和發(fā)展。
歌曲的A 部分為9—17 小節(jié),由a 和a1 兩個樂句組成,a 句落在降D 徵,a1 句結束在降G 宮,該樂段為收攏型非方整性結構。此段相較于開頭的引子部分,節(jié)奏型沒有太大改變,旋律發(fā)展采用同頭換尾的發(fā)展手法,男女主相互把對方比作風雨與星月,寄情于景,娓娓道來。第二句比第一句多出一小節(jié),充分表達了海棠對林生的思念之情。樂段的最后結束在主旋律位置主和聲構成的收攏性終止中,完成了樂思的局部收束。
歌曲的B 部分為18—33 小節(jié),由b、c、b1、c1四個樂句構成,b 句結束在降A 商,c 句結束在降D 徵,b1 句結束在降A 商,c1 句結束在降G 宮,該樂段為收攏型方正性結構。該段為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力度增強、旋律線上升、織體加密都在推動著音樂情緒的高漲。小附點和連音線的使用,使音樂上的固定強弱韻律結構臨時被突破,改變了原有節(jié)拍的強弱律動規(guī)律,造成了重拍位置的轉移,不穩(wěn)定的節(jié)奏處理使得音樂進行充滿了動力,推動了樂思邏輯的發(fā)展。該段在歌劇中以男女輪唱的方式呈現,林生與海棠的旋律此起彼伏,把兩個人彼此呼喚、彼此守護的情感發(fā)揮到極致。
第34 小節(jié)為B 段與B1 銜接的間奏部分,連續(xù)的八度跑動,增強了音樂進行的緊張度,將歌曲推向下一個高潮。
歌曲的B1 部分為35—42 小節(jié),由b1、c1 兩個樂句組成,兩句尾音都結束在G 宮,該段為收攏型方整性結構。整首歌從降G 宮調式轉向G 宮調式,轉調的處理也讓整首歌曲層次更加豐富,演唱方式由輪唱變?yōu)槟信R唱,這樣的音樂表現方式一方面使得人物情感得到升華,另一方面使觀眾體會到作品中包含的更多家國情感和老百姓不畏敵寇的斗爭精神。
歌曲的尾聲為43—49 小節(jié),該段旋律為B1 段的重復,在最后四小節(jié)中速度變慢,力度加強,持續(xù)的高音貫穿樂曲結尾部分,旋律運動雖然停滯,但音樂的動力性并沒有減弱,最后樂曲結束在G 宮調式的主音上,將飽滿的情緒宣揚到極致并促進了樂曲的完滿終結,加深了全曲的整體統一性。
(二)旋律特征分析
如果說節(jié)奏是歌曲的骨架,那么旋律便是歌曲的血肉,一首歌曲能否被人們記住,關鍵在于其主題旋律的記憶點是否鮮明。《等著我,親愛的人》之所以能夠成為整部歌劇的經典選段,被無數聲樂人廣為傳唱,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濃厚的沂蒙風情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歌曲開頭的引子部分,作曲家欒凱將《沂蒙山小調》悠揚舒緩的風格糅合進旋律,前奏一響,引人入勝,村里綠油油的麥田和村民們淳樸的笑臉仿佛在眼前浮現。除了在該歌曲中,這段旋律還作為整部作品的音樂動機和主題旋律出現在歌劇的引子和序曲部分,在劇中作為各部之間的連接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
歌曲A 部分的旋律多采用級進和跳進的方式進行,連續(xù)級進使音樂產生的停滯感以跳進的方式擺脫跳進之后所產生的動蕩感,以之后與跳進方向相反的級進來平衡。此段旋律在小字一組的d 至小字二組的e 之間進行,流暢舒緩的旋律淺淺地烘托出林生和海棠“星月相伴、風雨相隨”的畫面。
在歌曲B 和B1 部分,旋律起伏變大,音區(qū)在小字一組的e 至小字二組的a 之間,歌曲強弱對比也更加明顯,力度記號由mp 到f,再由f 到mf,旋律呈現上行級進的走向,伴隨著大跳的進行,突出了歌曲昂揚激動的音樂情緒,使得樂思的發(fā)展更具動力性。
在最后的結尾部分,力度強至f,最高音區(qū)由小字一組的b 推至小字二組的g,節(jié)拍由八拍子變?yōu)槿淖拥谋3郑?jié)奏型織體前后形成明顯的疏密對比,和聲上,持續(xù)的主和弦加強了色彩性對比,音響效果上增強了和聲輝煌的感覺,而后持續(xù)長音的節(jié)奏與旋律走向完成了平息高潮的任務,拉長了音樂的整體結構,使旋律高潮點的出現形成必然的發(fā)展趨勢。
(三)伴奏織體分析
這歌曲的前奏中右手采用的是由《沂蒙山小調》改編而成的單音主題旋律,配合左手的分解和弦,慢慢把聽眾引到歌曲情境中去,后四小節(jié)右手變?yōu)橹郊臃纸夂拖遥瑴p弱了右手聲部的旋律感,左手也加上了八度疊置的低音,使得音響集中、厚重、力量性較強,推進了樂思的進展,為后續(xù)材料的展開積蓄了力量。
在歌曲的A 段中,第9—15 小節(jié)中右手聲部以主和弦的半分解加柱式活躍姿態(tài)呈現,左手則以主屬分解和弦的織體勻速進行,放慢了音樂的和聲進行速度,使得伴奏聲部富于流動性、歌唱性,表現了抒情的特征。
在歌曲的B 段中,大跨度的分解式和弦為旋律增添了極強的音樂色彩對比,右手連續(xù)的三連音也讓歌曲的高潮部分增添了更加激烈和飽滿的情緒。不同旋律層的疊加與交替產生的此起彼伏的多元聲部進行,豐富了主題音樂形象,各聲部之間形成了音響效果差,加強了音樂發(fā)展的氣勢與進行動力,同時與前段單薄的旋律織體形成對比,為音樂的展開提供了新的方向。
歌曲的B1 段與B 段相比,在織體的選擇上沒有太大變化,但在強度的變化上更加明顯,將整首歌的旋律推向最高點,尾聲是對B1 段的一次重復,最后一句反向八度的推動加上震音的演奏技法,把歌曲推到最后一次大爆發(fā),不管是演唱者還是聽眾的感情抒發(fā)都跟隨旋律釋放得淋漓盡致。
三、《等著我,親愛的人》的演唱分析
(一)聲音技巧處理
《等著我,親愛的人》這首歌曲,除了朗朗上口的旋律令人過耳不忘,其所表達的真摯動人的感情更能引人產生無限感動。所謂以情帶聲,以聲傳情,美好的聲音能夠架起歌曲與聽眾之間的橋梁,成為作曲家和大眾溝通的紐帶,而好聽的聲音所需要的是強大的氣息支撐和穩(wěn)定的行腔吐字,兩者共同作用才能為好聲音的形成提供強力保障。
在氣息的處理上,首先要明確每句話的換氣點在哪里,才能為每句話的表達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特別是在歌曲的高潮部分“等著我,不變的心”這里,氣息充沛的演唱者會選擇一口氣完成,以保證高音和情感的持續(xù)輸出,但對于聲音技術不太強大的演唱者來說,如果強撐著一口氣堅持下來,會造成氣息流動不起來,聲音聽起來死板又僵硬的情況。其次,在不同片段對氣息的運用也不同,在歌曲前半段,旋律較為柔和、舒緩,控制氣息的流動緩緩訴說,“等到再相逢”的“到”長音唱完,換一口氣再去唱“在”,加上嘆氣時候的感覺,使得整句話聽起來有說話時的語氣感,也突出了海棠對于離別的無奈和期待林生平安歸來的心情,推動著后續(xù)感情的持續(xù)發(fā)展。副歌部分的旋律大部分在中高音區(qū)且有大量的長音,更加考驗演唱者對氣息的掌握,特別是第二句“等著我”,在旋律上的遞進和情緒上的推動可能會出現提氣、擠嗓子的現象,一方面要扎穩(wěn)氣息,腰腹的肌肉把氣牢牢地“霸”住,另一方面下巴放松,上口蓋也要開合到位,這樣才能扎實穩(wěn)定地發(fā)出高音。
在咬字行腔方面則需要氣息的高度配合,可以說二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在開頭部分“你是家鄉(xiāng)的雨”中“雨”的咬字,因為是閉口音又正好處在旋律上揚的位置,要去找哼鳴的感覺,同時繼續(xù)保持住腔體,笑肌微微提起,把“雨”字自然地“說”出來,隨后“遠行的風”中的“風”以及“再相逢”中的“逢”的咬字也是采取同樣的處理方式。歌曲A 部分整體偏抒情柔緩,旋律起伏較小,就像林生和海棠面對面相訴衷腸,在咬字時除了腔體的保持,還要注意放松下巴,特別是輔音咬字貼近門牙,切勿含在嘴里模糊不清地去咬,破壞了歌曲的美感。在副歌部分,“不變的心”中“不”的咬字是極難控制的,一方面它處在小字二組的a 上,為全曲最高音,另一方面閉口音發(fā)高音會比開口音更難控制,加上前面是換氣口,口腔位置可能會因換氣而受影響,因此這里使用鼻子去吸氣會更加有助于腔體的保持,同時自然放松,更深地去吸氣,然后堅定地唱出來。
(二)情感表達及角色塑造
在歌劇《沂蒙山》中,海棠這個角色無疑是最重要、最牽動人心的存在,海棠的成長史、她充滿戲劇化的人生以及每個轉折處發(fā)生的內心情感變化,這些都是發(fā)生在抗日年代千千萬萬個老百姓的真實寫照。從新婦到母親,再從母親到紅嫂,海棠的蛻變引領著整部歌劇的劇情發(fā)展。在《等著我,親愛的人》片段中,剛懷孕不久的海棠卻要面臨與丈夫分離的兩難境地,她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毅然決然地做出了選擇。在歌曲高潮部分的“等著我,親愛的人”中,一聲聲親切呼喚,不僅是海棠對林生的思念,還有無數中華兒女對親人的思念。在海棠這一角色塑造上,她是有血有肉的普通農村女人,在大是大非前,雖有掙扎和不舍,但國家危難當頭,她堅定地看著林生離去,體現了海棠感性和理性并存、外剛內柔的鮮活形象。
在歌詞中,男女主以“星月”“風雨”相擬,但“星月”只在夜晚相遇,“風雨”不會時常出現,A 段的演唱滿懷期待卻又有一些傷感,海棠和林生期盼著終有一天相見,卻不知這一天何時才能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