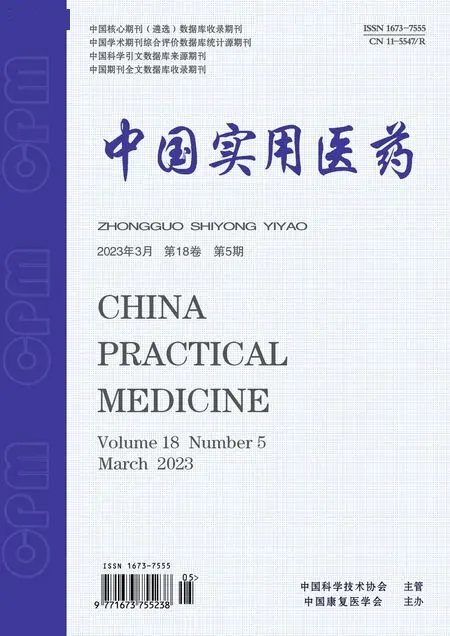芻議白術對腸道疾病的雙向調節作用
王夢琪 熊航 劉亞軍 沈洪 劉軍樓
白術,味甘、苦,性溫,歸脾、胃經,具有健脾益氣、燥濕利水、止汗、安胎等功效。白術被奉為“安脾胃之神品”,其健脾補中之功相較蒼術更勝一籌,作用偏重于里。按照《中國藥典》2015 版[1]和《中藥學》[2]教材的記述,白術治療脾胃病主要針對食少便溏、脘腹脹滿、脾虛痰飲等病證,其中腸道疾病僅涉及泄瀉。藥理研究表明,白術中揮發油組分、水洗脫液組分和多糖組分能促進胃腸蠕動,石油醚組分和醇洗脫液組分能抑制胃腸蠕動[3];動物實驗表明,白術既可使被過度抑制的胃腸道平滑肌恢復正常運動,又能緩解胃腸道平滑肌的痙攣,對胃腸功能具有雙向調節作用[4,5]。近年來,包括潰瘍性結腸炎、腸易激綜合征、慢性腹瀉及便秘等在內的多種腸道疾病發病率逐年增加,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本文試追溯白術的本草學沿革,探討古今醫家運用白術雙向調節治療腸道疾病的辨治思路,以期在臨床能靈活運用白術,進一步提高治療腸道疾病的臨床療效。
1 白術的本草學歷代沿革
1.1 白術的功效演變 白術的運用歷史悠久,古書中有大量描述白術功效的文獻記載。秦漢《五十二病方》[6]中即用術入復方治金傷疼痛,《神農本草經》[7]列術為上品,不分蒼、白,名山薊,其“主風寒濕痹死肌,痙疸,止汗,除熱,消食”。東漢時期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廣泛運用白術,功效涉及健脾益氣、消痞、利水化飲、祛風除濕、止嘔止渴、安胎[8]。魏晉南北朝時期陶弘景《名醫別錄》[9]首次區分赤術(蒼術)和白術,但未對其功效及運用有所區分,對白術的味和毒性進行補充,認為白術味甘、無毒,在《神農本草經》的基礎上提出白術具有治風眩頭痛、痰水、心下急滿、霍亂吐下、利腰臍間血、益津液的功效,基本延續了張仲景對白術的認識。唐代對白術功效的認識在《藥性論》[10]中得到進一步完善,并在此時期白術被全面應用在諸如橘皮湯、鯉魚湯、白術散等方劑中。金元時期《醫學啟源》[11]言白術“能除濕益燥,和中益氣,利腰臍間血,除胃中熱”,對白術的功效進行完整概括。明清時期的本草專著更為全面地對白術的功效進行歸納和總結,清代張璐在《本經逢原》[12]中認為白術“生用則有除濕益燥,消痰利水,治風寒濕痹,死肌痙疸,散腰臍間血及沖脈為病、逆氣里急之功。制熟則有和中補氣、止渴生津、止汗除熱、進飲食、安胎之效”。
1.2 白術雙向調節的理論溯源 歷代醫家對白術功善止瀉的論述較為深入。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13]中指出白術可治“霍亂、吐下不止”。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14]四君子湯(人參、白術、茯苓、甘草)成為后世健脾益氣的基礎方劑。明代醫家李中梓所著《雷公炮制藥性解》[15]中認為白術“除濕利水道,進食強脾胃……止泄瀉”。清代黃元御《長沙藥解·卷—白術》[16]認為白術“入足陽明胃、足太陰脾經。補中燥濕,止渴生津,最益脾精,大養胃氣,降濁陰而進飲食,善止嘔吐,升清陽而消水谷,能醫泄利”。
白術的通便功效鮮有在歷代本草學著作中提及。《傷寒論》第174 條“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術湯主之”是直接闡述白術通便作用的最早記載。張仲景用“術”雖未分赤白,但在功效運用上已有所區分,此條文實為仲景通過白術祛在表濕邪,宣通營衛之氣,使肺氣得以宣降,津液下布大腸,則大便硬得解[17]。清代《王旭高·醫書六種》云:“白術生腸胃之津液,大便硬是腸胃之津液干枯,故加白術”[18]。葉天士在癥見饑時垢血通爽、飽時便出不爽之案中,辨其為脾陽失運,用理中湯去參加桂圓肉(白術、干姜、甘草、桂圓肉)辛甘化陽以通便[19]。京城名醫魏龍驤提出脾胃之藥首推白術,大便干結責之陰液不足,運化脾陽促津液得復實為治本之圖,重用生白術治療老年便秘療效甚佳[20]。
2 白術治療腸道疾病的中醫學理論基礎
白術屬脾、胃經,為治脾胃病要藥,然脾與胃相表里,胃與腸同為腑,脾、胃、腸共同參與了消化、吸收、排泄的全過程,因而腸與脾、胃在解剖位置、功能特點和疾病發生上存在諸多聯系,主要體現在生理和病理兩個方面。
2.1 腸與脾、胃的生理聯系 脾、胃居人體中焦,脾與胃以膜相連,運納協調,升降相因,燥濕相濟,化生氣血,灌四旁,滋養后天。脾、胃與大腸、小腸關系密切,脾運化水谷,主升清,胃受納腐熟,主通降,小腸泌別清濁,大腸傳導糟粕,脾、胃、大腸、小腸共同完成了運化-腐熟-吸收-排泄的消化過程,脾氣充沛,氣機暢達,則輸布津液精微如常,腸道得潤,糟粕可出。
2.2 腸與脾、胃的病理聯系 脾胃功能失常可導致腸道疾病的發生,主要表現為排便的異常。《素問·臟氣法時論》[21]云:“脾病者,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素問·太陰陽明論》[21]亦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脾胃受損,脾不升清,濕困脾土,腸道分清泌濁失職,清濁不分,下注腸道,發為泄瀉。《素問·厥論》[21]云:“太陰之厥,則腹滿脹,后不利,不欲食”。脾氣不運,升清降濁失司,中焦氣機不暢,則腑氣不通;脾氣虧虛,推動無力,大腸傳導失常,則排便困難、大便艱澀難解;脾不健運,氣血化生無源,津液布散不利,腸道失于濡潤,則糟粕聚于腸中難下;脾運失常,脾濕內生,水濕不化,濕阻腸道,則見排便不盡感[22]。
基于上述對腸與脾、胃生理病理聯系的討論,可知白術具有治療腸道疾病的中醫學相關理論支撐。
3 古今醫家運用白術雙向調節治療腸道疾病的辨治思路
基于上述中醫學理論基礎,古今醫家在治療腸道疾病時常根據白術的本草學特征,發揮其止瀉與通便的雙向調節作用。作者試對歷代醫家運用白術治療腸道疾病的辨治思路進行整理,主要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3.1 補脾益氣燥濕土 《素問·太陰陽明論》[21]即有“濕勝則濡泄”的論述,泄瀉的病理因素在于濕。李中梓“治瀉九法”之一即為燥脾,濕皆本于脾虛[23],脾胃受傷,水反為濕,谷反為滯,清濁不分上下,精華之氣反下降,加用白術可強健脾氣,使脾氣得升,胃氣可降,升降相因。正如明代李中梓《本草通玄》[24]所言:“得補脾胃之藥更無出其右者……土旺則清氣善升而精微上舉。濁氣善降,而糟粕下輸,故吐瀉者不可缺也”。同時白術苦而溫燥,可燥脾土之濕,以助泄瀉止。
金代醫家劉完素在《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25]中認為白術味甘能入胃而除脾胃之濕,表現為四肢倦怠、小便不利、納谷減少的泄瀉病證宜用調胃去濕之法,擬白術湯(白術、芍藥 干姜、甘草)用治秋冬寒泄,擬白術芍藥湯(白術、芍藥、甘草)治太陰脾經受濕而水泄注下、水谷不化者。元代醫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26]中提出脾瀉者當補脾氣,用炒白術四兩使健運復常,屬氣虛所致瀉水腹不痛者宜用四君子湯(人參、白術、茯苓、甘草)倍白術,并首創痛瀉要方(白術、白芍、陳皮、防風)以白術為君藥用治脾虛肝旺之痛瀉。明代醫家王肯堂認為泄瀉所致五臟虛弱、中焦脾胃陽氣衰竭的危候,參附湯之力已不足以挽救,必加七味白術湯(炒白術、白茯苓、白芍、陳皮、炙甘草)溫復脾陽而固元氣[27]。清代醫家李用粹在《證治匯補》[28]中選用白術茯苓湯(白術、茯苓、甘草)統治泄瀉,四苓散(白術、茯苓、豬苓、澤瀉)治清瀉不分因作泄瀉。此外,含白術的著名方劑如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參苓白術散、健脾丸、理中丸等均可補脾益氣止瀉。
3.2 運脾和胃生津液 《素問·太陰陽明論》[21]云:“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亦為之行氣于三陽。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于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水飲入胃,經脾運化,化生津液,脾主升清,輸送津液以濡潤胃腸。若脾虛不運,水飲難化則水濕困脾,胃腸失潤則大便堅硬。張壽頤在《本草正義》[29]中提出白術“最富脂膏,故雖苦溫能燥,而亦滋津液,且以氣勝者流行迅利,本能致津液通氣也”。黃宮繡在《本草求真》[30]中認為白術“既能燥濕實脾,復能緩脾生津”。因此便難之證運用白術健脾益氣,使津液生化有源,脾能為胃行其津液,津液得以正常輸布,所謂“增水以行舟”,腸道得潤,則大便可通。此外,胃氣不降可認為是便秘的基本病機[31],胃腑以通為順,運用白術以健運脾氣,促使中焦氣機升降恢復,胃氣得降、津液得生,血運得旺,腸道澀滯可解,則腸腑得暢。
枳術丸源自《金匱要略》中枳術湯(枳實、白術),張元素改湯劑為丸劑,將枳實與白術的比例變為1∶2,用于飲食所傷所致痞證,傷食必有食積,食積日久致脾胃受損,脾胃虛弱亦可加重食積,故用白術補脾胃元氣,枳實消胃腸積滯,李東垣在此基礎上繼承枳術丸原方補元氣、通胃氣、瀉邪氣的基本原則,進行多種化裁以“治痞、消食、強胃”,如《內外傷辨惑論》中枳實導滯丸、草豆蔻丸等[32],后代醫家基于此學術思想,常將枳術丸用于治療脾虛便秘或功能性便秘[33-35]。
4 影響白術雙向調節作用的因素
4.1 炮制方法 根據臨床治療需求的不同,白術主要有生用白術、土炒白術、麩炒白術和焦白術等多種炮制品。白術中的揮發油組分、水洗脫液組分促進胃腸蠕動,白術內酯抑制胃腸蠕動,而多糖是健脾止瀉的物質基礎,炒制后多糖含量更高,并且經過炒制的過程后白術燥性得到緩和,揮發油含量明顯降低,白術內酯Ⅲ的含量增高,因此白術炒制時對胃腸道蠕動的抑制程度更大,故臨床用炒白術抑制胃腸蠕動以達到健脾止瀉的功用,用生白術促進胃腸蠕動以達到通便的功用[36-38]。
4.2 劑量大小 白術在藥典中記載常用量為6~12 g,臨床醫家用生白術瀉下通便的劑量可用至30~60 g,甚可達90~120 g[39-41],取“補藥之體作瀉劑,但非重用不為功”之義健脾助運以通降,生津液以濡潤腸道,治療虛秘或虛實夾雜秘[40]。并有實驗證明高劑量生白術水提取液對小鼠便秘具有明顯的腸道推進作用[42]。
5 白術的配伍應用及使用注意事項
當便秘辨證為脾虛不運或脾虛致津液不足而濡潤腸道失常時,運用生白術通便的療效會更佳。對于飲食積滯所致大便不通者,可配伍枳實、陳皮等理氣消積;對于便秘伴氣虛不行、氣滯者,可配伍枳殼、柴胡等行氣理氣;對于肺燥而肅降失常致便秘者,可配伍桔梗、紫菀等宣肺下氣;對于便秘伴腸燥者,可配伍火麻仁、郁李仁等果仁類潤腸通便;對于陰結脾約證及寒證便秘者,可配伍肉桂、附子、厚樸、干姜等溫陽散寒;對于便秘伴脾腎陽虛者,可配伍肉蓯蓉等補腎潤腸;對于氣血虛弱之虛秘者,可配伍當歸、熟地等養血補血[43];對于陰津虧虛之便秘者,可佐用生地、麥冬、玄參等增水行舟[33]。
《雷公炮制藥性解卷二·草部上》[15]中對白術的配伍禁忌進行闡述,即“防風地榆為使,忌桃、李、雀肉、青魚菘菜”。“防風地榆為使”,可理解為白術甘溫除濕,功能止瀉、定嘔、止汗,從三焦而言,防風主上焦,辛散行風而勝濕,白術主中焦,健脾而燥濕,地榆主下焦,收斂而祛濕,防濕熱下注,濕邪流走血分,從六經而言,白術入脾、胃,防風入肺,地榆入胃、大腸,肺脾同屬太陰,濕土為本,白術佐防風,太陰陽明互為表里,除內外之濕,白術佐地榆,地榆闔陽明,寒溫并用,助燥濕之力,收斂大腸。“忌桃、李、雀肉、青魚菘菜”,從藥性而言,可理解為白術性燥,桃、李、雀肉、青魚菘菜為發物一類,雀肉亦屬熱性,若與白術配伍則恐助其燥性,從脾病病機而言,白術為脾家要藥,所治皆為脾弱,脾胃不足之源,為陽氣不足、陰氣有余,脾胃陽氣虛衰,心火下乘土位,陰血受火邪而陰盛,則上乘陽分,陽道不行,不能生發,陰火伏血,津虧血燥,《脾胃論·用藥宜禁論》[44]云:“病禁者,如陽氣不足,陰氣有余之病,則凡飲食及藥,忌助陰瀉陽……諸姜、附、官桂辛熱之藥,及濕面、酒、大料物之類,助火而瀉元氣”。若同食桃、李、雀肉、青魚菘菜一類,會助火傷陰,加重脾胃衰弱,故忌之。
6 小結
泄瀉與便秘是臨床常見腸道疾病,又常可交替出現,白術雖具有雙向調節的作用,但在臨床運用的過程中仍當謹記辨證論治的原則,尤其是在用白術通便時,因其不同于傳統攻下及潤下之法,不可只顧其“癥”而忽視其“證”,宜結合舌脈征象,善用配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