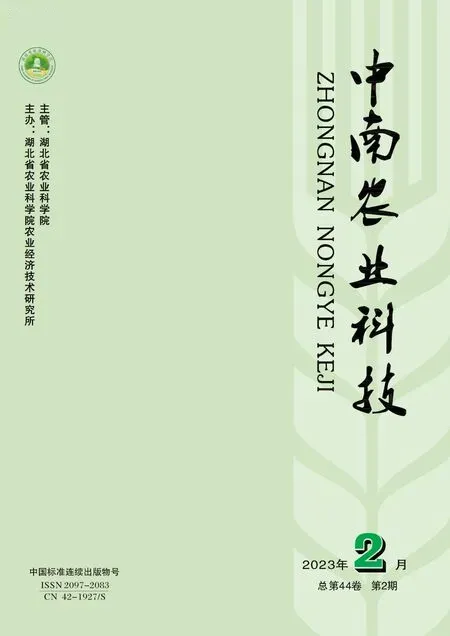南疆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影響因素及對策
——以喀什和和田地區數據為例
阿卜杜蘇普爾·如則,阿布力孜·布力布力
(新疆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烏魯木齊 830000)
合作社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之一,其帶動農戶數量最多,發揮作用比較突出。農業農村部發布了關于實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升行動的通知,提出力爭到2025 年末,縣級及以上示范社和示范家庭農場分別達到20 萬家,提出創建一批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輔導隊伍。農民專業合作社能夠了解農民最深切的愿望,在農民與政府之間起橋梁和紐帶作用[1]。南疆地區合作社涵蓋了種養殖業、林果、手工業、農機等領域,有效促進了農業規模化經營、農產品銷售及農戶收入的提高。“合作社+互聯網”等新型模式的涌現拓寬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為農民增收致富發揮了積極作用。關于合作社發展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較多,合作社的發展不僅受到外部因素影響,還受到注冊資金、專門網站、機構運行的完善程度、合作社自身品牌等因素的影響[2,3]。合作社成立時期的初始資產規模、政府資金扶持等對合作社發展有較大影響[4]。合作社發展的影響因素中內部因素的影響比較明顯。
1 南疆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現狀
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一種新型的市場主體,對于調整農村經濟結構、轉變農業經營方式以及深化農民增收機制具有重大的意義[3]。南疆地區合作社數量得到了快速提升,無論是從合作社的輻射帶動作用還是合作社的規范發展方面,與過去相比有明顯的改善。本研究對喀什和和田地區的217 份調研數據進行深入分析,剔除了變量嚴重缺失或無效問卷7份,有效問卷共210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7%。
1.1 合作社成立情況和發起人類型
在黨中央的高度關注和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數量得到較快提升(表1)。由表1 可知,喀什和和田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在2010 年之前較少,從2011—2017 年合作社成立數量保持持續增長態勢,2018 年以后合作社成立數量逐漸下降。

表1 合作社成立情況
合作社發起人類型見表2。由表2 可知,合作社發起人的類型主要以民間能人為主,占總樣本數量的55.71%,其次是村兩委,占樣本總量的21.90%,民間法人組織占比16.19%,基層供銷社占比最少,為1.43%。

表2 發起人類型
1.2 經營類型多樣化和銷售途徑多樣化
大部分合作社的生產經營以及產品類型銷售途徑等比較單一。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生產經營方式和產品的銷售途徑等方面有了新的拓展。由表3 可知,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經營產品類型拓展到糧食、果蔬、花卉木苗、畜牧養殖、水產養殖、手工紡織、勞動力轉移等類型,其中畜牧養殖類型占比最高,為47.14%,其次是果蔬類和糧食類,分別為15.71%、9.52%。

表3 合作社產品經營類型情況
合作社的農產品銷售途徑見表4。由表4 可知,自己銷售農產品的數量最多,占樣本總量的65.24%,合作社在組織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方面發揮著實際作用。合作社除自己銷售方式外,還有直營店和柜臺銷售、經紀人銷售、合作社與龍頭企業聯合銷售等方式,這些銷售途徑的作用也逐步呈現,發揮著積極作用。

表4 合作社農產品銷售途徑情況
1.3 輻射帶動作用更加明顯
從合作社帶動周邊非農戶以及當地非成員農戶成員數量的多少,可以看出合作社的輻射帶動作用的強弱,合作社帶動非成員農戶數量也可以作為衡量合作社輻射帶動作用強弱的重要指標。由表5 可知,帶動1~5 人的合作社有69 家,占樣本總量的32.86%,帶動6~10 人的合作社有65 家,占樣本總量的30.95%,帶動農戶人數40 以上的有48 家,占樣本總量的22.86%。這表明合作社的輻射帶動作用明顯增強。

表5 帶動非成員農戶情況
2 南疆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影響因素
南疆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總體的發展速度較快,政策也鼓勵農戶積極創辦合作社增收致富,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影響合作社發展的因素較多,基本上可以分為2 大類,宏觀因素和微觀因素,影響合作社發展的宏觀因素主要是國家政策、市場環境等方面。微觀因素則是合作社的內部環境因素,因宏觀因素是國內所有合作社共同面臨的共性問題,本研究主要針對南疆地區影響合作社發展的微觀因素進行研究,研究發現理事長能力不足、農戶對合作社信任度低、社員素質低和技術指導不到位等因素正在制約著合作社的發展。
2.1 理事長能力不足
合作社是一個以農戶為主導而建立的經營主體,然而農戶具有組織能力不強、對市場信息的敏感性不強等特征。在這種背景下理事長能力就成了合作社發展中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單純的依靠傳統的運營方式會導致合作社無法融入到市場競爭而慘遭淘汰。南疆地區大部分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戶增收方面的推動能力不強,農戶加入合作社后的收入增加不明顯。這說明合作社盈利能力不足,這反映理事長的帶動能力不強,然而合作社的發展離不開理事長等核心社員的發力。
2.2 農戶對合作社信任度低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離不開農戶對合作社的信任,如果合作社沒能實實在在地幫助到農戶,就會導致農戶對其失去信心。南疆地區合作社的數量有明顯增加,其中也存在“空殼社”“假合作社”,這些合作社的不作為、亂作為嚴重影響了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戶心中的形象,農戶自身對合作社的運行、組織方式等因素了解不夠,導致農戶對合作社信任度大幅度降低。
2.3 社員素質不高
對南疆地區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調查發現,包括理事長在內的社員最高學歷以初中為主,大部分社員都沒有上過初中。在社員文化程度普遍低的情況下,會影響社員對合作社作用、生產技術管理理念等的理解,導致運用效率很低。社員素質偏低還造成社員與合作社脫離的情況,當社員生產的農產品市場價格較好時農戶就自行出售農產品。然而,農戶對市場信息的掌握和對其敏感程度往往偏低,進而造成經濟損失。農戶對未來信息的判斷會受到農戶年齡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5]。趙玲蓉等[6]基于扎根理論對合作社發展三產融合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社員學歷普遍低,對于新事物、新政策的理解能力有限,合作社內部意見不合導致了合作社不敢嘗試發展三產融合。
2.4 技術指導不到位,生產效率不高
農戶是“弱勢”群體,其特征表現為文化水平不高、技術水平低等。大多數農戶的認知范圍較狹窄,不了解新技術新生產管理理念會導致生產效率低下,所以必須在組織層面上解決群體問題[6]。對待農戶牽頭創辦的農戶合作社等經濟組織也不例外,要加以引導才能發揮其作用,國家大力倡導發展智慧農業、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實現數字化、智能化的背景下發揮合作社等經營主體的作用更有實際意義。南疆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社員的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不高,說明對合作社的技術培訓和指導幫助尚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3 促進合作社發展的對策
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脫貧攻堅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贏得了大眾的認可,在疫情防控等復雜的社會背景下,喀什和和田等地區的新梅、桃子以及別具一格的手工藝品,依托農產品供銷社等民間合作經營主體的渠道作用將產品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為當地的增收發揮了積極作用。針對上述南疆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影響因素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3.1 加強對理事長等核心社員的能力提升培訓
人才是第一生產力,合作社運行機制、制度建設規范而人才培養跟不上,合作社將越來越依賴政府。研究發現,合作社牽頭人(理事長)需要具備一定的能力和意識,并對于種植或養殖等生產方式有一定的經驗。在生產技術等培訓中,首先要對理事長加以培訓指導,從而引領合作社進一步的發展,效果會更好;其次,政府要持續關注合作社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整合資源創造條件,為理事長等核心社員的學習、自我提升搭建舞臺,進而增強他們的帶動力。
3.2 進一步加強合作社規范化發展
合作社的發展規范取決于合作社合理的運行機制、規范的制度建設等。抓好合作社規范化建設才能體現其自身的本質屬性,始終堅持服務社員的宗旨[7]。合作社的制度建設不規范會導致合作社逐漸出現分裂。加強規范化建設、加強對運行不良的、徒有虛名的“假合作社”的清理,讓合作社走上健康發展之路,這樣才能在農戶心里扎根,合作社有了良好的形象才會有發展后勁。
3.3 提高社員素質的同時,不斷吸收新成員增強合作社活力
社員作為合作社發展的直接受益者自然也會參與到合作社的生產或銷售等過程中,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合作社發展也需要懂運營、懂信息技術的復合型人才。研究發現,合作社成員大部分年齡偏大,對互聯網等技術了解甚少,讓這些群體在短時間內具備技術技能、操作新型設備等生產工具不現實,合作社持續發展必須吸納年輕成員,讓懂技術運營的年輕群體帶領周邊的農戶加入生產生活,以此增強其活力才能實現使合作社不斷發展壯大的目標。
3.4 加強對合作社的技術指導
2020 年初農業農村部官網公布了數字農村發展規劃,并提出到“十四五”期末中國數字農村建設將會取得重要進展,有力支撐數字鄉村戰略實施等。這需要合作社等農業經營主體積極發揮其作用,從數字鄉村建設、智慧農業等方面對社員加以培訓。從對社員的管理技術、操作技術、市場營銷、農業技術等方面加強對合作社的技術指導[8]。讓合作社成為連接新型技術和農戶之間的橋梁,以此來增強合作社的社會化服務功能、逐漸成為數字鄉村建設中的中堅力量。各級政府部門為社員創造理論學習,并結合實踐加以應用,做到學以致用。
4 小結
建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9]。南疆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總體數量得到了快速的提升,社內外環境也得到了明顯的改善。但合作社內部,社員本身還存在不少問題,其中理事長等負責人能力上不足、農戶對合作社信任度低、社員素質不高、對合作社的技術指導不到位等問題比較突出,這些問題制約合作社的發展[10]。合作社的發展不能只依賴于政府部門的扶持,最大限度地激發合作社的“造血”能力,建立合作社考核制度,對運行良好、帶動作用明顯的合作社給予資金獎勵,從而形成合作社之間良好競爭的局面。根據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實際情況針對性地提供政策支持、加強合作社規范化建設、引導合作社健康穩定發展等措施對合作社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