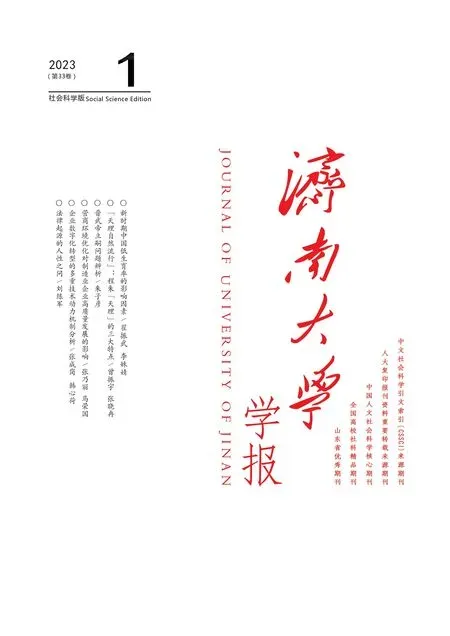以日觀中:羅蘭·巴特認識中國文化的渠道與方式
田樂樂
(廈門大學 中文系,福建 廈門 361001)
古典時期,中國是日本的學習對象,近代以來,國勢易位,日本在向西方學習的進程中領先中國。于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日本成為中國學習西方的中介。同時,因為日本熟悉中國,并率先采用現代學術方法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所以在“中學西傳”領域,日本也充當著中介角色(1)曾軍:《從“西學東漸”到“中學西傳”》,《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2月19日第3版。。學界目前關注較多的是中國的現代學術體系通過日本渠道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消化和重述,進而影響中國。而我們很少去思考,西方學者了解和認識中國時,也有一個“日本渠道”問題。為補足這一缺陷,本文選取羅蘭·巴特作為個案,探討西方文論中的以日觀中現象。羅蘭·巴特文論中的“以日觀中”現象,主要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禪宗思想,二是道家思想。
一、鈴木大拙禪學思想對羅蘭·巴特“中性”思想的影響
在禪學思想方面。“巴爾特在談到禪宗時,征引的多為譯自日文的著作”(2)[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張祖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頁。,羅蘭·巴特研究過日文,可以準確理解日文著作的原意。羅蘭·巴特最主要的引用對象是鈴木大拙,他關于禪宗的知識基本來自鈴木大拙的著述與翻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西方,鈴木大拙掌握著禪思想的解釋權,而且鈴木大拙傳向西方的禪思想,并非中國的禪思想,而是日本禪。
“禪”源于印度,傳入中國之后,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禪、道家思想融合,8世紀時,在慧能及其弟子的努力下,《壇經》這部禪宗唯一經典出現,禪宗思想最終形成。傳至宋代,禪宗形成了五家七宗的分布狀況,五家七宗中的曹洞宗、臨濟宗黃龍派、臨濟宗楊岐派傳入日本,成為日本禪宗。禪觀念雖來自印度,但是卻形成于中國,禪宗是一個純粹的中國宗教派別,古典時期的日本禪宗是中國禪宗的一個分支。然而近代以來,伴隨著中日國力消長,日本在西方的影響力日益超過中國,中日禪宗的影響力也逐漸易位。鈴木大拙的老師釋宗演是日本臨濟宗僧人,也是將東方禪學帶到西方的第一人。釋宗演1893年在芝加哥參加世界宗教大會,鈴木大拙是其翻譯。此后釋宗演與美國出版家卡魯斯(Paul Carus,1852-1919)成為朋友,并將其翻譯助手鈴木大拙介紹給卡魯斯,協助其翻譯東方宗教、哲學經籍。此后鈴木大拙逐漸引領了西方世界的禪學熱潮。當今世界上,禪的普遍稱呼之所以是日文發音的“Zen”,而非中文發音的“Ch’an”,就是因為禪文化西傳的主力是鈴木大拙,他被西方學者譽為“了解佛教禪宗的唯一來源”(3)Masao Abe,ed., A Zen Life:D.T. Suzuki Remembered. New York:Weatherhill,1986.。日本是中國禪宗文化西傳的中介,許多西方學者都是以日本學者的禪文化著作為渠道來了解、認識中國禪文化的。
古典時期,中日禪學同源同質,近代以來,以鈴木大拙為代表的日本禪師援引西方思想發展日本禪學,這導致近代以來中日禪學不僅影響力不同,二者的思想特點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中國禪學一貫講求“中道”,既肯定真理方面的“真諦”,也肯定世俗方面的“俗諦”。在真諦方面,中國禪學超越世俗的二元論,認為“是非”“善惡”“美丑”等等二元判斷的符號只是世俗之見,并非人的本性,也非真實的世界。中國禪學認為人的本性是清凈的,人需要直觀本性,順應著本性生活,而不能沉溺于虛幻的世俗符號之中。中國禪學在真諦方面具有非現實、非理性、超越語言的特質。在俗諦方面,中國禪學也積極使用理性、邏輯、語言參與現實生活。因為中國禪學教導人認識到語言、概念判斷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最重要的指向是教人操著不執著的心進入生活,繼續使用理性、邏輯、語言勇猛精進,而不是拋棄語言、現實等,一切斷絕。因此中國禪宗在入世方面積累了大量的實踐與理論。宋代是中國禪宗的大力發展時期,其時禪宗具有一種“入世轉向”(4)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0-106頁。,當時的禪宗教徒認為政治秩序如果得不到重建,佛教也就難以發展,因此禪宗積極參與到社會與政治的建設中,體現了禪宗的積極入世。而且,當時的高僧契嵩、智圓十分推崇儒家經典《大學》《中庸》,將儒家的入世思想引入禪宗,發展了禪宗的入世理論。明代的王陽明將禪學與儒學結合起來,被稱為“孔門大乘”。他將儒家的“善心”與禪學的“本性”融合無間,認為良知就是人的本性,人只要“致良知”,探求到自己的本性,就能夠以真心參與生活,在世俗生活中成就功業。清末民初的太虛法師,將禪學與三民主義結合,主張人間佛教,建設人間凈土,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的佛教精神,使用寺院財產興辦學校教育,積極參與俗世活動,體現了中國禪學的入世精神。
鈴木大拙所繼承的禪學主要來自日本臨濟宗,由于學術傳承上的問題,他的禪學思想與著述缺乏對禪宗其他宗派思想的吸收(5)龔雋:《禪史鉤沉——以問題為中心的思想史論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395-396頁。。鈴木大拙所繼承的臨濟宗認為修行最注重“開悟”與“公案”,“開悟”即獲得般若(智慧)。禪宗認為人人皆可成佛,“見性成佛”,即認為人的本性是清凈自在的,人自己產生顛倒幻想,遮蔽了本性,人一旦了悟自己對世界、對自己的種種判斷其實都是虛假的,終止幻想,就可以回到清凈的本性,獲得智慧,這就是開悟。而獲得智慧的方式,臨濟宗認為要超越語言、理性對于世界所做的概念性解讀,回到無判斷的清凈本性。禪師與弟子超越語言與理論的例子,就是公案,鈴木大拙經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公案:
一個禪僧,來自臨濟門下的寺院,遇見屬于另一寺院的三個結隊游歷的僧侶,其中一個大膽的僧侶向禪僧問道:“禪河有多深?”……臨濟因訴諸直接行動而不訴諸語言解釋而聞名。于是,禪僧說:“你自己去找答案吧。”接著,欲將那個大膽提問的僧侶扔下橋。(6)[日]鈴木大拙:《禪與日本文化》,錢愛琴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頁。
臨濟禪僧認為語言與理論是對世界所做的概念性判斷,它們無法探討出世界的本象與人的本性,因此臨濟禪僧回避語言、理性,企圖將問禪的僧人拋下河。鈴木大拙所繼承的臨濟宗思想,本身具有反語言、反理性的因素,當鈴木大拙來到西方之時,彼時西方思想界恰好流行著反思理性、邏輯、語言局限性的思潮。鈴木大拙故意順應著西方思潮,特別突出闡發禪宗思想反理性、反邏輯、超越語言、神秘主義的一面(7)鈴木大拙的這種思想傾向已經被許多中西方研究者指出,參見龔雋:《禪史鉤沉——以問題為中心的思想史論述》,第391-395頁。,而對于禪宗的入世思想,則采取消極態度,很少闡發,從而塑造了一種新禪學,一種屬于鈴木大拙的日本禪學。鈴木大拙的日本禪學在西方接受度極廣,許多著名學者都認為禪宗只是一種反理性、反語言的思想,比如弗洛姆就接受鈴木大拙的觀點,認為開悟體驗無法使用語言解釋:“假如開悟可以通過某種解釋來讓那些從未有過此種體驗的人能夠有所理解,那么開悟就不能被稱為開悟了。因為這樣一來,開悟就脫離自身,不能再成為禪修的一個部分。”(8)Daisetz Teitaro Suzuki,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with a Forward by C. G. Jung,London,1960,p.92.另一位學者榮格也認為:“任何嘗試解釋、分析禪與開悟的行為皆為徒勞。”(9)C. G. Jung,Psychology and the East,trans. R. F. C. Hull,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142.
要而言之,近代以來,中、日禪宗存在很大差別。中國禪宗一貫兼顧出世與入世,既反思理性、邏輯、語言,又使用理性、邏輯、語言積極參與世俗生活。而以鈴木大拙為代表的日本禪宗則順應西方思潮,特別突出禪宗思想反理性、反邏輯、超越語言、神秘主義的一面。這就是中日禪宗之不同。
上文已經說到,羅蘭·巴特接受的是鈴木大拙的日本禪學。1966至1967年,羅蘭·巴特來到日本,又親身體驗了禪學。日本之行,羅蘭·巴特十分關注日本禪宗的“無”觀念以及“免除一切意義”的思想取向(10)[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帝國》,湯明潔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第2頁。。在《符號帝國》一書中,羅蘭·巴特探討了日本俳句、筷子、建筑等因素中所體現的“無”觀念,他在日本發現了一種異于西方的符號體系,這種“空無”的禪宗思想及符號系統也被他生動地記載在文章中。無論是中國、西方,還是日本,日常生活中都遍布著“有”的觀念以及種種“意義”,“無”與“免除一切意義”的思想取向體現了以鈴木大拙為代表的日本禪宗反理性、反邏輯、反語言的超越現實特性,羅蘭·巴特顯然接受并推崇這樣一種異于西方的禪學思想。同時,有一種整體性的東方觀,他把東方哲學視為“一種真切的外異性”(11)[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4-5頁。。在羅蘭·巴特的敘述中,中國、日本、印度,都被稱為“東方”,這是一種整體性、概括性的敘述。敘述東方的特質是為了矯正“西方”的一些問題,羅蘭·巴特說:“我并非鐘情于某種東方本質,……它只是為我提供了一個保留著諸多表達方式的地帶……‘撫慰’了我對聞所未聞的、完全被我們[西方人]丟棄了的那個符號系統的構想。”(12)[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帝國》,湯明潔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第2頁。羅蘭·巴特存有一種東西比較、東西不同的思維,他樂于在東方發現不同于西方的符號體系,這種思維傾向使他有意無意地發掘東方的共同本質——一種異于西方的共同特性。羅蘭·巴特認為,西方的特性是“西方人使一切事物無不沉浸在意義里,就象是一種有獨裁主義色彩的宗教,硬把洗禮儀式施于全體人民。”(13)[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帝國》,孫乃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05頁。而相應地,羅蘭·巴特樂于在東方發掘“空無”“免除意義”的符號系統。日本之行,中、日、印禪宗便被羅蘭·巴特視為一個整體,視為一種“東方本質”。而且在《符號帝國》中,羅蘭·巴特只是保有這樣一個整體性的印象,他既沒有論述中、日、印如何可能成為一個整體,也沒有過多論及中、印禪宗,他的寫作集中于日本禪宗,他是以日本禪宗的“空無”“免除意義”等思想特性來認識、理解整個東方禪宗的,中國禪宗的入世思想并不在羅蘭·巴特的視野之中。這極有可能是因為中國禪宗的入世思想也會參與意義、語言、理性的建構,它太“像”西方的充滿意義的符號系統了。而實際上,中國禪宗取一種中道的態度,既肯定又否定語言、理性、意義,是既不同于西方思想也不同于日本禪宗的。
羅蘭·巴特于1974年訪問中國,當時傳統文化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羅蘭·巴特關注了毛澤東思想,而對中國傳統文化印象不深。在《中國怎么樣》中,他以“零度寫作”的態度看待充滿著政治話語與意識形態的中國,他說:“關于中國,這個無限的對象,以及對于許多人來說模糊的對象,我認定的真理是:我試圖生產的話語既不是肯定的,也不是否定,還不是中性的;我試圖生產的評論是不做評論;我試圖產生的認可(是一種語言模式,突出了一種倫理學或是美學),并非無法避免地不是一種贊同就是一種拒斥(這種模式突出一種理性或者一種信念)。”(14)Roland Barthes. Alors la Chine?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1975,pp.13-14.這種不介入的惰性態度,正是他所推崇的“零度寫作”。在當時的西方,紅色中國以及毛澤東思想或被左翼人士奉若圭臬,或被自由主義者妖魔化。而羅蘭·巴特不認同這兩種態度,他采用一種“零度”的惰性態度來認識中國,他持這種態度穿行于中國的種種“意義”以及他人所賦予中國的種種“意義”之中,卻不去試圖定義中國,既賦予中國無限的可能性,同時又使中國成為他“零度寫作”的一個論據,參與到其思想建設中去。“零度寫作”是他思想的核心,也是羅蘭·巴特對西方“充滿意義”的思維狀態反思后的成果,日本禪宗那反理性、反邏輯、反語言的特性參與了他“零度寫作”理論的創造與發展。當他以“零度寫作”理念來認識中國時,我們也可以說羅蘭·巴特在以日觀中。由于當時中國流行著反傳統的思潮,所以中國禪宗沒有進入羅蘭·巴特的視野之中,在《中國行日記》中,羅蘭·巴特只是略微提及孟子、《紅樓夢》、秦始皇等中國傳統人物、作品(15)參見[法]羅蘭·巴爾特:《中國行日記》,懷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除此之外,更加重要的是,禪宗方面的以日觀中現象也存在于羅蘭·巴特的中性理論之中。“中性”思想在羅蘭·巴特文論中占據著理論樞紐的地位(16)金松林:《“中性”:羅蘭·巴爾特美學的輻輳》,《美育學刊》,2017年第2期。。在1953年出版的《寫作的零度》中,羅蘭·巴特就闡釋過中性:
創造一種白色寫作,它擺脫了特殊語言秩序中的一切束縛。我們知道,某些語言學家在某一對極關系(單數與多數,過去時和現在時)的兩項之間建立了一個第三項,即一中性項或零項。這樣,在虛擬式和命令式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個像是一種非語式(amodale)形式的直陳式。比較來說,零度的寫作根本上是一種直陳式寫作……這種中性的新寫作存在于各種呼聲和判決的環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它正好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構成……這是一種毫不動心的寫作……它完成了一種“不在”的風格……于是寫作被歸結為一種否定的形式,在其中一種語言的社會性或神話性被消除了,而代之以形式的一種中性的和惰性的狀態。(17)[法]羅蘭·巴爾特:《寫作的零度》,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頁。
零度或中性的寫作是一種不動心,作者不介入的寫作。在這種寫作中,人的心就像鏡子一樣,它能照到經過它的事物并忠實地記錄下來,即使外部事物是如何的喧嚷,作者都能不將自己的判斷參與其中。在這樣的寫作中,事物能恢復到它們的本來面目。而從語言秩序中講,零度與中性是想要破除語言中的種種對立,建立一種語言中的第三項,尋求直陳式寫作。以上思想在羅蘭·巴特后來的《中性》一書中得到了展開:
我把中性定義為破除聚合關系(paradigme)之物,或者不如說,我把凡是破除聚合關系的東西都叫做中性……什么是聚合關系?它是指兩個潛在的項次之間的對立,我為了說話,為了顯示意義而顯現二者之一……聚合關系屬于意義方面,凡是有意義的地方,就有聚合關系;凡是有聚合關系(對立)的地方,就有意義。(18)[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11頁,第187頁,第186、188頁,第188-189頁,第109頁。
中性態度是一種不動心、不介入的惰性態度,中性思想破除意義,破除聚合關系,具有超越語言、理性的特征。中國禪學對于現實、語言、邏輯都具有既肯定又否定的綜合態度,鈴木大拙的日本禪學順應西方潮流,吸收了西方哲學家反思理性、邏輯、語言的思想,故意強調禪學的非理性、非邏輯、超越語言、神秘主義特質。羅蘭·巴特的中性理論追求不動心、不介入、破除意義,這決定了羅蘭·巴特會著重關注禪宗思想中的出世部分,而鈴木大拙的日本禪學自然成為了羅蘭·巴特的思想資源。羅蘭·巴特引用鈴木大拙的觀點,認為禪宗的“公案”就是“糾結”,禪應該回避糾結,回避華麗的哲學,回避長篇大論(19)[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11頁,第187頁,第186、188頁,第188-189頁,第109頁。。在此處,羅蘭·巴特強調了禪宗反思語言的特性。羅蘭·巴特認為禪宗的規則就是“反相關性”,是“動搖社會性自我的邏輯,動搖相關性”,他還認為,禪“涉及抗拒邏輯的和論理的習慣”(20)[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11頁,第187頁,第186、188頁,第188-189頁,第109頁。。在此處,羅蘭·巴特強調了禪宗非理性、反邏輯、非現實的特性。羅蘭·巴特引用鈴木大拙的觀點,主張不要根據公案推理,不要試圖給詞語作出闡發(21)[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11頁,第187頁,第186、188頁,第188-189頁,第109頁。。羅蘭·巴特舉了一個禪宗公案,當我們用手指指月之時,愚人關注手指,而真正應該關注的是月亮。這則寓言中的月亮,比喻的就是真實的世界,而手指,比喻的則是語言與概念(22)[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11頁,第187頁,第186、188頁,第188-189頁,第109頁。。在此處,羅蘭·巴特強調了禪宗反邏輯、反語言的特性。以上的舉例表明,羅蘭·巴特認為禪宗是一種非現實、反理性、反邏輯、反語言的思想。羅蘭·巴特在論述禪學時是不分中日的,在他的敘述中,中日禪學是一個整體,他所引用的許多公案也都來自中國。而實際上中日禪學是有區別的,羅蘭·巴特以鈴木大拙的日本禪學為渠道來認識中國禪學,認為禪學是一種反語言、反理性、非現實的理論,回避了中國禪學中的入世理論。需要說明,在講授“中性”課程時,羅蘭·巴特因為母親的去世而處于一種低沉的狀態,并想離開社交界、學術界,這使他對中國文化的“篩選”變得無拘無束,所以他的文論中所存在的以日觀中現象并不是他對東方文化不認真,而是他的個人狀態及日本文化的影響所致。
二、鈴木大拙、岡倉天心影響下的羅蘭·巴特的道家觀
羅蘭·巴特對中國道家思想的認識也是以日本文化為中介的,深受鈴木大拙、岡倉天心等日本思想家的影響。這里需要說明禪宗與道家的關系,禪宗是中國人借佛教之名,對道家思想整合、大眾化的產物,“禪宗思想是大眾化的老莊哲學”(23)麻天祥:《中國禪宗思想史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禪宗、道家思想是緊密結合、息息相關的,許多禪師與居士都兼習禪學、道家思想,使用老莊思想來闡釋禪學。鈴木大拙也經常在他的禪學著作中引用、闡釋道家思想,受其影響,羅蘭·巴特也常常禪學、道家思想并稱、合用。
中國道家思想與中國禪宗一樣是入世、出世理論的綜合體,中國的道士一方面歸隱山林,另一方面又被尊為國師,參與到政治之中。東漢末年的太平道發起黃巾起義,天師道雄霸漢中,都是政教合一的集團。唐朝道士一方面入山修行,另一方面又直通皇帝,李白就是通過道士的引薦而被玄宗認識,即“終南捷徑”。中國古典文人基本上都是儒道兼修,儒學與道家思想水乳交融,出世與入世的理論并存于中國道家思想中。而鈴木大拙則使用他的禪宗思想闡釋道家思想,強調道家非現實、非理性、超越語言的部分,他說:“也許老子的描述比那些禪宗大師更接近于我們大多數人。”(24)[日]鈴木大拙:《禪與日本文化》,第11頁。鈴木大拙的禪宗思想本身就是非現實、非理性、超越語言的,更不必說經其闡釋的道家思想了。
羅蘭·巴特對中國道家思想的認識受鈴木大拙日本禪學、日本道家思想的影響,同樣強調道家非理性、超越語言的部分。在《中國怎么樣》中,羅蘭·巴特是這樣認識道家的:
稍稍把中國幻想成一個置于艷色、濃味、粗暴意義之外的對象……在我眼中,即中國這種,安靜和強力地,從意義漫溢出來(déborder)的奇特方式——以及一種使用特殊話語的權利:一種輕快漂移的話語,或者又一次地,一種欲望沉默——欲望“智慧”的話語,也許,與在斯多噶主義的意義相比,這個詞被放在道家的語境中理解會更加適宜。(25)Roland Barthes. Alors la Chine? Paris: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1975, p.14.
《中國怎么樣》是羅蘭·巴特1974年中國旅行之后所寫的文章,其法文標題是“Alors,la Chine?”,可以直譯為《好吧,來說說中國?》,標題中的“好吧”盡顯沉默。與在《符號帝國》中對日本“空無”“免除意義”的符號系統盛贊不同,羅蘭·巴特在中國呈現了一種沉默狀態。我在上文指出,這是因為羅蘭·巴特反對西方人使用既定邏輯來判定中國,他使用“零度寫作”的態度來認識中國。從這里的引文可以看出,羅蘭·巴特同時認為這種沉默與零度也是屬于中國道家的特性。實際上,沉默與零度只是中國道家出世思想的體現,鈴木大拙發揮了道家這種非理性、反語言的思想,而較少闡釋中國道家的入世思想,在此處羅蘭·巴特對中國道家的認識顯然是受了鈴木大拙日本禪學以及他對中國道家的闡釋的影響。
在《中性》一書中,也存在著道家方面的以日觀中。在《中性》中,羅蘭·巴特認為禪、道思想是一體的。在論述中性思想的“無為”時,羅蘭·巴特認為禪宗與道家都是通過打坐來忘記功利、語言,獲得寧靜的生活(26)[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289-297頁,第48頁。。這強調了禪、道思想反語言、非功利的一面。在論述中性思想的“疲憊”時,羅蘭·巴特認為能指與所指物的分離,體現了符號內部的距離,這就是道家所說的大道之難,即符號內部的距離所產生的認識道的困難性。而佛祖拈花微笑,摩訶迦葉心領神會這一典故也體現了能指與所指物的分離,但是禪學并不糾結,而是直接領悟微笑背后的含義。這強調了禪、道思想反語言、反思符號局限性的特性。在論述中性思想的“沉默”時,羅蘭·巴特認為“禪宗不信任高談闊論”,引用老子的“了解道的人不談論道,談論道的人不了解道”一語來說明沉寂的境界,羅蘭·巴特認為在禪學、道家的這種境界里,大自然返歸沉寂,人類在大自然中消散,成為大自然中的一縷聲音(27)[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289-297頁,第48頁。。這強調了禪、道思想反語言、非現實、追求超越的一面。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受鈴木大拙的影響,羅蘭·巴特認為禪學、道家思想都是非現實、反語言、反理性的。
羅蘭·巴特對《莊子》的認識也受鈴木大拙日本禪學、日本道家思想的影響。道家兼具出世、入世思想,不同的思想家會根據自己所需選取不同的內容加以闡發。為顯明鈴木大拙對中國道家思想的闡發傾向,我們可以選取一個中國近現代人物與他進行對比。章太炎的《齊物論釋》是道家思想在中國近現代發展的里程碑式著作,章太炎認為莊子不想隱居,因為莊子要解決世人的苦難;章太炎又認為莊子也不想參與政治,因為莊子認為政治無法救世。章太炎認為莊子的思想超越了語言;章太炎又認為莊子批判了世間人吃人的局面,特地留下《莊子》一書拯救人間(28)章太炎:《齊物論釋》,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實際上,莊子思想就是這樣的矛盾綜合體,他既避世又救世,他既超越語言又使用語言留下自己的思想。在章太炎的對比下,鈴木大拙對莊子思想的闡釋就更顯其特點了:
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貢看到一位農夫親手從井中汲水澆灌田地,就問“為什么不能利用桔槔?”農夫說“做什么都依靠機械,則其中必有機心。因為我厭惡這種機心,所以不使用機械。” ……機心就是有謀劃之心。……如果心的活動不能在沒有任何中介物的情況下從本然的無意識中流露,就是不純白的。……(29)[日]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第20卷,東京:巖波書店,2001年版,第349-350頁。
鈴木大拙闡釋的是《莊子》中的一則寓言:子貢看到漢陰丈人在井中汲水,就問他為何不用工具(桔槔)。丈人回答“有機械者有機事,有機事者有機心”,孔子稱丈人有“渾沌之心”。他認為“機心”就是謀劃之心,為了欲望而去謀劃,人的心會沉溺于欲望之中。他使用日本禪學與弗洛姆對話,闡發禪的無意識特性,在引文中,他同樣使用無意識思想闡發莊子的“純白之心”與“渾沌之心”。他還順應著當時西方對現代文明的批判,認為莊子“的做法就是反對當今文明的傾向”(30)[日]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第20卷,第38頁。。他顯然突出闡發了莊子思想非現實、反理性、反邏輯的特性,而沒有同等對待莊子思想中的入世部分。在鈴木大拙的影響下,羅蘭·巴特同樣引用《莊子》來論述他沉寂的理想境界:
莊子:“完人運用心思如同鏡子……對于外物既不引導,也不趨奉(依照禮數);他回應外物,但不存留外物。……對于泰然自若而無所存留于心的人,事物自然會顯露本來的面貌;他的舉止淡如止水,紋絲不動如鏡,應答如同發出回聲……(31)[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290頁,第50頁。
這段話出自《莊子·應帝王》,完人即至人,這種人可以使心變成紋絲不動的鏡,他能夠回應外物,這就是羅蘭·巴特文論中的“說”“語言”。而當物離開,至人的心中也不留存。在中國,莊子的“心鏡”思想并不排斥“說”“語言”,其要義是不“執著”說、語言。《齊物論》說:“大言淡淡,小言詹詹”,章太炎解釋道:“大言淡淡,《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小言詹詹,李云小辯之貌是也。”(32)章太炎:《齊物論釋定本》,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7、80頁。沉溺于語言而不見真實世界之人,說的是“小言”。而至人能運心若鏡,不執著于語言,這樣的人使用語言應物,語言就淡乎無味,人才不會為語言所累。中國的莊子思想是指導人修心如鏡,在不對世間萬物(包括語言、概念等)產生執著心的基礎上使用語言、概念進入世間生活。而羅蘭·巴特引用莊子這段話是為了補充說明前述禪、道思想的沉寂境界,主要強調了道家超越理性、超越語言、沉默應對的出世傾向,受鈴木大拙影響,羅蘭·巴特未提及莊子的入世思想。
在論述道家思想時,羅蘭·巴特又引入了茶藝,羅蘭·巴特說“茶藝=改頭換面的道教”(33)[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290頁,第50頁。,這是引用了岡倉天心的原話:“茶道就是道家思想”(34)[日]岡倉天心:《茶之書》,高偉譯,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頁,第52頁,第47頁。。岡倉天心認為道家思想與茶道的特點是“簡潔自然”“物我一致”(35)[日]岡倉天心:《茶之書》,高偉譯,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頁,第52頁,第47頁。,岡倉天心此處所闡述的正是日本所特有的“寂”美學,這強調了日本茶道與道家思想的非現實、非理性、返歸自然的特性。當羅蘭·巴特說茶道等于道教時,他是受了岡倉天心的影響,以非現實、非理性、返歸自然等特性來認識道家思想、茶道,而對中國道家的入世思想同樣并不措意。不僅如此,受岡倉天心的影響,羅蘭·巴特還以日本茶道為渠道觀察、認識中國茶道。在東方藝術領域,岡倉天心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1903年,他在英國John Murray出版社出版了《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1903)一書,成為西方世界了解中國藝術史的初始來源之一。在這本書中,岡倉天心認為亞洲的歷史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岡倉天心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是與當時的亞洲局勢息息相關的。1893年,岡倉天心來中國考察,1901年,他又前往印度考察。在考察中,岡倉天心認為印度、中國雖然曾經擁有偉大的文明與藝術,但是她們現在已經衰老,只有日本繼承了亞洲文明的精髓且在向西方的學習中具備了生機,因此他認為日本是亞洲文明的“博物館”,日本將成為未來亞洲文明、藝術的領導者,他以此理論為基準,寫出《東洋的理想》。在此書中,岡倉天心將印度、中國視為古老但行將就木的來源,將日本視為綜合亞洲文明的時代引領者(36)其目錄次序為:理想之范圍、日本原始藝術、儒教的北方中國、老莊思想于道教的南方中國、佛教于印度藝術、飛鳥時代、……明治時代、展望。,這是岡倉天心對中、印、日三國藝術史的闡釋。《東洋的理想》一書以英文寫作,且出版甚早,是西方了解中國藝術極其重要的資料。此后岡倉天心還向西方國家介紹茶道,出版了《茶藝》。《茶藝》同樣延續《東洋的理想》的結構,以日本茶道為主體闡釋中國茶道。他認為茶道雖產生于中國,但是元代蒙古族入侵中斷了中國的茶道,此后茶在中國只是一種飲品,與人生理念無涉(37)[日]岡倉天心:《茶之書》,高偉譯,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頁,第52頁,第47頁。。日本茶道則繼承了中國茶道的正宗,并發揮形成了一種人生哲學。因此他只在《茶藝》第二章介紹了一下中國茶道,剩下的章節則屬于日本茶道。實際上,中國茶道與日本茶道也是不同的,茶道等于道家思想這個判定只在日本語境下成立,在中國是不成立的。比如羅蘭·巴特以日本茶道的“寂”美學來認識、理解中國唐代的一首茶詩(38)[法]羅蘭·巴爾特:《中性: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1977-1978)》,第59頁。,這個觀點是對岡倉天心《茶藝》的引用(39)[日]岡倉天心:《茶之書》,第41頁。,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 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如果僅僅看上面的引文,我們確實也會產生“孤寂”的感覺,但是,岡倉天心與羅蘭·巴特只引用了這首詩的一部分,全詩是這樣寫的: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里,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一碗喉吻潤,……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全詩前面一部分充滿著對人事、對茶的樂趣的體味,體現了“趣”而非“寂”。后半部分則批判當權者不知人間疾苦,充滿著政治意味。全詩并不符合日本茶道的“寂”美學,中國茶道也并不能用日本的“寂”美學來涵蓋,因為“寂”是日本特有的一種美學范疇,它在中國沒有形成系統的審美觀念,中國所特有的審美范疇是“趣”(40)參見周建萍:《“趣”與“寂”—中日古典審美范疇之比較》,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岡倉天心故意截取這首詩的一部分,使用日本茶道美學來闡釋中國茶道,羅蘭·巴特也就跟著岡倉天心使用日本茶道美學來認識中國茶道,在中國的茶詩中投射了日本文化的影子。
羅蘭·巴特清晰地知道道家思想屬于中國,他在著作中也認為自己所論述的老莊思想是“中國的”。而實際上,羅蘭·巴特對中國道家的認識受到了鈴木大拙、岡倉天心二人的影響,回避了道家思想中的入世部分,認為中國道家思想是反理性、超語言、非現實的理論。鈴木大拙與岡倉天心必然知道中國道家是兼有入世與出世理論的,他們是順應著西方反理性的思潮集中闡釋了道家思想的出世部分,而羅蘭·巴特則是透過二人的道家觀念來觀察和認識道家思想,以日觀中。
三、結語:世界學術中的中國,多元網絡的方法
我們此前的“中西對話”研究強調的是中、西二者“之間”的對話,這種研究方法聚焦于對話雙方,會忽視二者的周邊因素。曾軍先生確立了一種“多元網絡”的研究方法(41)參見曾軍:《巴赫金對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影響不是一條思想的河流……影響更像是網絡,而不是整體性的思想傳統。”(42)生安鋒:《后殖民性、全球化和文學的表述——霍米·巴巴訪談錄》,《南方文壇》,2002年第6期。學者在接受影響時,都有一種學術背景與期待;任何接受也都不是“整體性”的接受,多是有選擇性的部分采納;對話與影響的雙方之間又常常存在中介因素,使影響充滿層級,呈現出一種“多元網絡”的狀態。羅蘭·巴特的個案就體現了“多元網絡”式的影響。儒釋道三教是中國文化的主體,禪宗又是中國佛教的主體。在禪學、道家思想西傳的過程中,榮格、弗洛姆、羅蘭·巴特等西方重要思想家都以日本學者的中國文化觀念為中介渠道來觀察、認識中國文化,“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中存在著廣泛的以日觀中現象。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在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中,日本占據著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在“西學東漸”中,在引進、翻譯、闡釋西方文化的過程中,近現代日本是得風氣之先的。1885年,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認為經過向歐美國家的學習,日本已經進入文明國家行列,中國、朝鮮則仍是落后的文明,為改變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應該“脫亞入歐”(43)參見[日]富田正文:《福澤諭吉選集》第5卷,東京:巖波書店,1989年版。。在這種文化風向的指引下,日本大力引進西方文化,中國的留日學生也得以從日本的翻譯書籍和著述中學習西方文化。在這場中、日、西文化大交流中,日本作為中介,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大量西方術語經由日本譯介,進而傳入中國。現代漢語中的哲學、美學、封建、物理、經濟、科學等術語都是經日本學者翻譯再傳入中國的,有研究者發現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借得詞844個(44)[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327-335頁。。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中,“西學東漸”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學西傳”則處于弱勢地位。在“中學西傳”進程中,日本同樣處于重要的中介地位。在遭遇西方文化之前,中國一直是日本的學習對象,日本文化之中蘊含著許多中國文化的因素。而在“脫亞入歐”之后,西方國家對于日本的好感度上升,其對日本文化的了解程度也遠超中國文化。并且,許多日本學者率先采用西方學術理論整理、闡釋中國文化。受這種種因素影響,在“中學西傳”的過程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日本都處于中介位置,許多西方學者直接閱讀日本學者的著作,有意無意地以日本學者的中國文化觀念為基準來觀察和認識與日本文化相近的中國文化。
為適應“多元網絡”影響的現實與研究方法,我們需要超越“之間”視野,引入“之中”視野,即“世界之中”這樣一種高度。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種種事實。比如鈴木大拙與岡倉天心為何會使用日本禪、道思想闡釋中國禪、道思想?羅蘭·巴特又為何會輕易地接受?這是因為他們都存有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區域型視野,鈴木大拙與岡倉天心是在“東亞”“亞洲”文化圈中看待禪學與道家的,羅蘭·巴特是在與“西方”相對的“東方”視野中觀察與認識禪、道思想的。在大的視野之中,他們皆愿意尋找禪、道思想的共性,所以他們才會立足一個國家的思想特質去理解大的區域共性。具體到中國,我們應該具有“世界學術中的中國”視野,劉康先生指出,應該用“世界的中國(China of the world)”,來代替“世界與中國(world and China)”的說法”(45)劉康:《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一個思想史的角度》,《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世界學術中的中國”指的不是存在一個既定的世界,中國去加入它,而是中國通過自己的行動,參與到世界學術建設中去。通過“世界學術中的中國”這個視野,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學者通過以日觀中的方式認識了中國,比較了中西文化,并產生了許多思想成果,對于中國學者來說,這既是遺產,也需要反思。因為以日觀中只使西方學者認識了中國文化中符合日本文化規范的那部分,而中國文化的其他部分則被忽視。在東升西降的歷史趨勢下,中國學者必須反思以日觀中現象,正視、發掘中西對話之間的日本因素,辨明遺產中的成果與糟粕,在此前思想的基礎上,揚棄日本這個中介因素,在直接交流中真正全面比較中國與西方文化,實現世界文化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