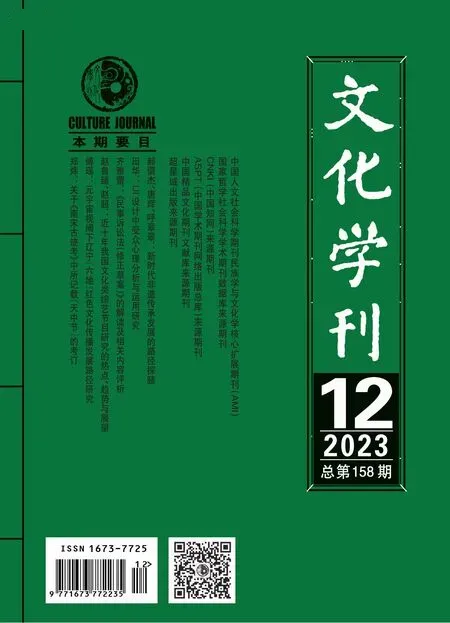論水墨電影《山水情》的審美意境
陳思彤 房玉柱
中國的水墨電影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上海美術電影廠先后拍攝了一系列具有中國風格的水墨電影。1960年拍攝的《小蝌蚪找媽媽》標志著水墨電影的問世,隨后《鹿鈴》《牧笛》等接踵而至,水墨三部曲打開了中國水墨電影的大門,自此中國的水墨電影在全世界名聲斐然。《山水情》由上海美術電影廠在1988年拍攝,該影片的導演是特偉、馬克宣、閻立春,片長約19分鐘。該部電影被稱為水墨電影發展史上的巔峰,獲得第14屆蒙特利爾最佳短片獎。水墨動畫不僅追求國畫中“似與不似”的古典美學意境,還展現“禮曰”“詩云”古老中國的精神追求。
一、《山水情》所呈現的意境之美
意境作為美學范疇孕育在先秦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在老子思想、魏晉玄學和禪宗美學的推動下,在唐朝形成關于意境的成熟理論[1]。唐朝劉禹錫提出:“境取之象外”。近代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境非獨謂為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也”[2]。《山水情》用山水等意象表現出師徒之間深厚的情感,用墨色勾勒出寬廣遼遠的意境。
(一)“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意境美
《山水情》影片僅有19分鐘,沒有一句對白,但更加具有“味道”,整部影片沒有鮮亮的色彩,只有黑、白二色渲染,此片無聲勝有聲,無色勝有色,無聲便是最高聲,黑、白則為天地間最高級的顏色,表現出“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美感。展現的意境如這八字所言。短片猶如一首四季詩:春時,冰雪融化,處處聞啼鳥;夏時,池塘蛙鳴,荷花滿堂香;秋時,楓葉變紅,悄然掉落;冬時,大雪紛飛,落滿茅檐。雖然人物之間沒有對話,但里面細膩的情感、動作都表現得恰到好處,整部影片的動景和靜景都與意境融入在一起,將觀賞者引入水墨世界當中。該影片不僅表現了師徒之間的深厚情誼,更難得的是表現出水墨動畫的寧靜淡泊、空靈遼遠意境美。影片并沒有把水墨作為主題,而是以“山水”為主題,通過水墨寫意的形式表現出來,《山水情》里的景象并沒有與實際事物復刻得一模一樣,而是將重心放在流動的畫面上,借此來表現其靈動之氣。影片還追求一種田園牧歌式的情懷,師徒生活的地方宛如世外桃源,不被外界所打擾,表現出隱居山林的心境,淡泊自然的情懷和一種輕靈優雅的境界,體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融的理念,抒發哲學主題。
(二)民族音樂的意境之美
《禮記·樂記》中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之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音樂作為人們表情達意的工具,可以跨越國界、種族、階層。人都具有相通的共通感,音樂的浪漫在于能夠將人們心中封存的記憶迅速拼接起來,回憶起藏在腦海的某個時刻,音樂是自由的藝術,在這種熏陶下,一千個聽眾就有一千種感覺,獨特的意境美也蘊含其中。自音樂誕生后,人的情感就有所寄托,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帶有民族氣息的樂器不在少數,常出現在我國的藝術作品中。
影片《山水情》的一大特色就是運用民族樂器,古琴的使用能形成與西方音樂的強烈對比,民族音樂把水墨和電影完美地契合在一起,從而讓畫面和主題相呼應。《山水情》將各種音樂技法融合在一起,不僅表現出我國傳統音樂的特色,還創造出世界音樂史上獨具中國特色的民族音樂的意境美,在琴聲的伴奏下表達了師徒之間情感的起伏,在影片的結尾處,琴師隨著少年的琴音消失在茫茫的山水之間,琴音將觀眾間接地引向更遼闊的意境之中,觀眾仿佛想象師徒臨別情景,具有一種獨特的韻味,感受到離別的痛苦。音樂構成的意境妙不可言。影片為了加深觀賞者對人物角色的理解,特地用風聲、水聲、鳥鳴聲等自然客體來表現人物情感,讓觀眾群體能夠身臨其境感受影片所展現的環境,能夠切實體會人物的情感變化。例如,影片開頭的老琴師抱著古琴時,“嗖嗖”的風聲,有兩重含義,不僅渲染出自然環境的惡劣,還表現老琴師的自身處境艱難。可見世道并不太平;漁家少年在船上吹起清脆的笛聲,襯托少年的天真活潑的性格;還有春天的鳥鳴聲,為影片注入了新的活力,具有一種動態美。
民族音樂是一種陰柔之美,如潤物細無聲般浸入人的心田,而西洋的音樂是一種陽剛之美,如歡快的樂符,氣勢磅礴。民族音樂的柔緩、靜遠是西洋樂器所不具備的,更能表現出師徒之間濃濃的情誼。
二、《山水情》中的審美意象
“意象”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核心概念,對后世文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最早可以追溯到《易傳》,提出“立象以盡意”,由哲學命題轉化為美學理論,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正式提出“意象”,“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3]。美在意象,“意”是內在的,直指人的內心,為胸中之竹;“象”是指“物的形象”,實時客觀物體,表達“意”的思想內涵。書畫是我國意象傳統的藝術之一,通過“氣定神閑”,給觀賞者一種回味無窮的審美享受。
(一)古琴意象
古琴具有深刻的美學底蘊,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獨樹一幟,作為“琴棋書畫”之首,被認為是高雅的意象。子期、伯牙因琴相識,后結為知音,古琴代表“知音”。在影視作品以琴會友的例子數不勝數。在《山水情》里老琴師和漁家少年也為一種知音關系,老琴師如伯牙一樣,鐘愛古琴,技藝高超,少年如子期,是老琴師的知音。影片中老琴師在渡船的時候聽到了少年的柳笛聲,不禁對少年流露出贊賞之情,在老琴師彈琴時,少年對琴也表現出濃厚興趣,因此,兩人之間有一種惺惺相惜之感,才能領略藝術的真諦。
古琴在影片中有兩大作用。首先是故事發展的紐帶,老琴師因琴與少年結緣,才有后續的故事情節的展開,否則觀眾無法理解兩個相差幾十歲的陌生人之間深厚的情感,古琴是銜接老琴師和少年情感的媒介,他們之間的情誼都寄托在古琴中。少年的幽幽琴聲闡發出意境美,古琴不是冰冷的樂器,而是少年情感的延伸。理解古琴意象更能把握人物內心的情感。
古琴的另一作用是對禮樂文化的傳承,古琴象征著我國禮樂文明,傳承著士人精神,是精神的物化形態。自古以來,我國十分重視禮樂文化,在《禮記·樂記》中提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樂文化使我們步入文明時代,在物質沖擊下還能追求精神享受。孔子用禮樂來教導民眾,達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孔子提出“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在孔子的教育思想里認為一個人的修養可以通過三步形成:通過詩歌引起人們的共同感,在潛移默化中讓人們遵守規則,最終到達“禮”,禮也能維護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讓社會具有秩序感,從而使社會和家庭更加有秩序。“樂”是世間最美妙的聲音,通過音樂的熏陶來讓人格得到完善,主要是對人們內在的約束,在“樂”的教導下使得民眾從心底得到感化,“禮”和“樂”在相互配合中更好地發揮教導的作用,讓社會穩定有序。
古代“禮”為“六藝”之首,“琴”為“八音之冠”,影片中的老琴師就是“禮樂”文化的化身,他既體現著孝悌忠信的君子之風,也表現出士人精神。影片的開端就是蕭瑟的呼呼風聲,這一方面渲染自然環境的惡劣,另一方面也暗含著老琴師處境的險峻。老琴師出場時的穿著是一位飽讀詩書的文人,古人學而優則仕,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們最崇高的理想,老琴師的出場會讓我們聯想到屈原,即“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因此,老琴師可能是一位被迫害的政客形象,理想無法得到實現,只能將志向藏在古琴里,當然古琴也是他高潔品格的象征,不為世俗所折腰。影片中古琴不僅僅是意境的締造者,也代表著品行的熏陶,在潛移默化的熏陶下,少年也會成長為一位偉岸的君子。古琴的音樂美感中所映射的正是古人對意境之美的向往,《山水情》將水墨的朦朧之美與古琴的意境之美融合在一起,從而流瀉出含蓄而古樸的中國韻味。
(二)山水意象
山川之美,古今共談。山水在我國文化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歷來我們都具有崇拜山水、親近自然的傳統,山水文化在我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魏晉時期山水已經成為獨立的審美意象,謝靈運與陶淵明使得詩歌由玄言詩轉向山水詩,將山水作為抒情對象,文人由外發現了自然,由內發現了自我。山水成為文人漂泊心靈唯一的歸宿,增添了我國的藝術表現形式,從而誕生出山水畫與山水詩。山水作為抒情對象,還表現出對自然山河的禮贊。我國作為農業大國,所有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饋贈,在文學中多表達對自然山水的贊美。我們所理解的山水存在于客觀世界之外,即“靈想之所獨辟,總非人間所有”,是文人自由的心靈藝術,具有無限的意境和生命力。
山水中的情趣代表著中國人所具有的生存狀態和基本的人生追求。縱觀我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進程,山水是獨特的存在,山水中暗含的情趣早已超越了停留在表面的含義,成為抽象化的意境和精神追求。山水由實在的景物走向了虛擬的靈境,這為情感宣泄提供了窗口,使得山水情結走向了藝術化,從而構建出具有山水情懷的詩性思維。在影片《山水情》里通過水墨的形式將山水的存在變化狀態進行了細致描繪,顯示著山水中蘊含的深厚情懷。
《山水情》中的“山水”已經不是實在的景物,而是抽象化的符號。《山水情》在創造時是用律動的水墨來展現山水的形態,具有一種靈動美,在靈動的山水中滋養萬物,老子說過:“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4],莊子也提出:“通天下一氣。”[5]因而在中國人的認知中才有“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在這種情感的影響下,謝赫在繪畫六法中將“氣韻生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表現物體時不在惟妙惟肖,而在于物體的神態、氣韻。觀賞這部電影時,山水承載的是人物情感,體現出“一切景語皆情語”,能夠讓觀眾領會到山水的真諦。山水已經不是實實在在的客體,而是對人物所處的時間和地點的超越,突破客體的局限,將情感和意境引向更高處,山水成為了師徒之間表情達意的工具,影片中師徒兩人在水墨映襯的山水下來表現他們的情感,二人在用山水烘托氛圍,在觀賞時感受到萬物合為一體,天地之間只有師徒兩個人,體現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高遠意境。
三、《山水情》的審美文化特征——天人合一的精神
“天人合一”的思想作為我國哲學最重要的命題之一,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哲學最核心的思想,道家認為“至美至善”的境界即人與自然和諧共融,這不僅是生命的真諦,也是藝術的真諦。在天地之初,盤古死后,身體化成山川河流、樹木金石,莊子《齊物論》中“莊周夢蝶”,均體現人與自然相互交融。在漢朝獨尊儒術的背景下,儒家提出“天人同構”,即人的器官都與自然一一對應,人的頭足如同天地,雙眼如同日月,具有一種化生關系。自此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哲學要求下,將人置于自然之中,要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達到審美自然的境界。
《山水情》置身于我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完美地體現出來,表現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藝術理想。“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指人在面對自然時,以自然為師,關注自然山水的外在,認識自然山水的運行規律,形成“眼中之竹”,為把握自然山水之“道”將“萬象立于胸懷”,建立自然之象,形成藝術化的自然,得到“胸中之竹”。在這個過程中,自然以人化,呈現出心靈化的自然,賦予其主體性精神,達到人、自然、藝術的同一。石濤說:“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于大滌也。”表明藝術家在創造藝術作品時不只關注外在形態,更要把握山水之道,所謂“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在該影片中,老琴師認為少年琴藝雖已學有所成,但達不到物我同一“道”的境界,老琴師將大自然作為少年的老師,帶著少年行走在山水之間領悟自然的奧妙,云山蒼蒼,江水泱泱,此刻他的心境與自然融為一體,將眼中之景投射到心中,產生獨有的自然意象,在這時他懂得藝術的真諦,在影片快完結時,少年的一曲將影片帶向高潮,少年坐在山谷之間,仿佛天地中唯有師徒二人,自然與他們合而為一,融為一體,也讓琴曲的意境走向了巔峰,由有限的個體進入到無限的時空之中,具有一種“天人合一”的意境美。影片中表現了天與人、自然與藝術的關系,達到一種真善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