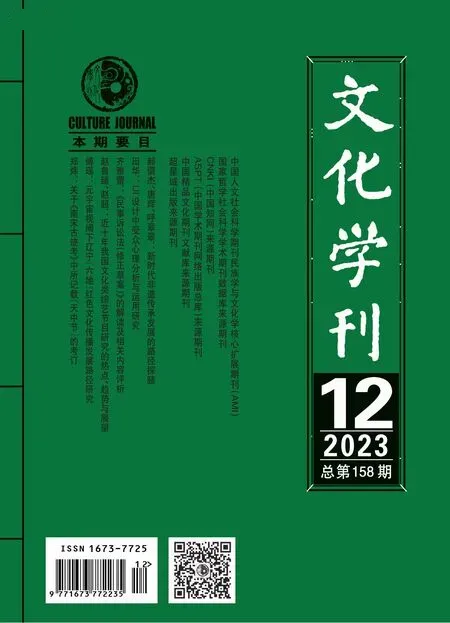超越與世俗
——試論中國傳統建筑“臺”的文化價值演變
杜娟娟
臺是中國傳統建筑中起源最早、形制多樣、應用較廣的建筑形式之一。早在遠古時期,相關文獻中就已有關于臺的記載,如軒轅臺。此時,臺以部落首領的名字命名,是舉行紀念性活動的場所,沒有實用性。在現代大眾的認知當中臺是沒有分別的,各式各樣、各種功能的臺被混在一起統稱了事。但是,先秦的鹿臺、靈臺與唐宋的超然臺、靈虛臺是一樣的嗎?明清時期的觀星臺、觀象臺可以和現在所說的陽臺、站臺等同嗎?顯然,它們是不同的。這種不同不僅體現在臺的物質形態和功能方面,更體現在它的文化價值方面。臺在我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在其發展過程中,臺經歷了內涵、形態、功能和文化上的分化與演變,最終促使一些相關建筑類型的出現,同時促進了自身文化價值內涵的更新。
一、什么是“臺”
由于內涵上的差異,并不是所有的類臺之物都可以用簡體字“臺”來代替。1956年,《漢字簡化字總表》將“臺”“臺”“檯”“颱”四個含義差別極大的字均簡化為“臺”。本文所論述的臺是指“臺”。按照《說文解字》中“臺”的篆體書寫來看,“臺”指:“觀,四方而高者。從至從之,從高省。與屋室同意。”[1]在這里,“之”是往前走,“至”是到達,整個“臺”的意思是指能夠到達上面行走的高大的建筑物。由此觀之,早在殷商時期,臺已具備“觀”和“居”的功能。此外,臺還是紀念性活動的場所、限制人身自由的監禁場所和古代官署,比如“帝堯臺”“夏臺”“尚書臺”。
按照《爾雅·釋宮》的記載:“四方而高者曰臺。”[2]這是有關臺的命名最早且最為普遍認可的文獻。漢代劉熙在其《釋名》中對臺的內涵也作了解釋:“臺者,持也。言筑土堅高,能自勝持也。”[3]據此可以得知,中國傳統建筑中臺的結構特點大多是四方而高,高而平的。建筑材料選擇上,臺由最初的土筑高臺發展到后期石制高臺和木制高臺,呈現出更加豐富的面貌。園林設計中對臺的建筑材料和形制描述最為詳盡的是明代園林設計師計成。在《園冶》一書中計成這樣定義“臺”——“園林之臺,或掇石而高上平者;或木架高而版平無屋者;或樓閣前出一步而敞者,俱為臺”[4]。臺可以是石制抑或木制,沒有一定之規。材料選擇上的靈活、多樣與臺發展過程中內涵、形態、功能上的轉變密不可分。
歷史上,關于“臺”較早的史實性記載來自商紂時期的鹿臺。“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巨橋之粟。”[5]這是史料中有關臺的形態的較早記載。后世所說的“酒林肉池”概念便是出自商紂時期有關鹿臺的記載。“林”和“池”的出現說明商紂時代已有具體的自然景觀觀念[6]。綜上觀之,鹿臺實際上是指這一時期的皇家園林,它包含了“宮”“苑”“園”三部分,具備居住、畋守和觀賞等多種功能。無獨有偶,文王靈臺與鹿臺在形態與性質上相似,即都是“臺”“囿”“沼”的結合,《詩經·大雅·靈臺》中已將三者并提。除了鹿臺與靈臺,先秦時期,周穆王的中天之臺、楚靈王的章華臺、吳王闔閭的姑蘇臺等都展現出同樣的形態與性質。秦漢時期,“臺”的內涵開始逐漸縮小,成為皇家庭園中多種構筑物中的一種——“宮”的代名詞,也即“以臺稱宮”,臺上只承載宮室。魏晉南北朝之后,“臺”的形態表現得更為獨立,既可以上承屋宇,也可獨立成臺,臺在功能和文化價值上呈現出逐漸分化的趨勢。唐宋之后,“臺”作為一種文化載體開始頻繁出現在詩詞文藝的創作當中,如亭臺樓閣體詞、界畫、園林設計等。此時的臺在形態上多為獨立狀態,上無屋宇。唐宋之后,“臺”的精神氣質變得更為“內省”,形態上也更加個人化、審美化和世俗化。“臺”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地分化和拆解的歷史,它“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混合到特化的過程,衍生出眾多類型,并不斷與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人文精神結合,最終達到極高的藝術境界”[7]。
臺在結構、形態、功能上的差異會影響臺的空間大小,而空間大小的不同又會使登臺者產生不同的空間感受,也就是所謂的“空間感”。“在古人看來,人與建筑文化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人與天地宇宙的關系。”[8]可以說,建筑物就是人與自然、人與天地宇宙之間的媒介與連接點,人們通過它去認知世界、求真索道、確定價值乃至安頓人生。這樣的筑造不只是出于生存上的需求,更是出于某種價值訴求。
臺以四方作為觀測的方向和確定方位的標桿,東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中的一些記載可以加以證實。當臺作為一個點確定下來時,周圍的河流、山峰、平原、樹木也便一一浮現,并且與臺產生關聯。臺的空間感源于其空間大小及其周遭景觀的差異。與西方藝術中一往無前的空間意識相比,中國傳統藝術的空間意識通常是回環往復的。正如美學家宗白華所言:“中國人看山水不是心往不返,目極無窮,而是‘返身而誠’,‘萬物皆備于我’。”[9]“追及遠方”與“逐漸返歸”本就是中國空間的一體兩面。
二、“臺”的歷史演變過程
在“臺”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其在功能上經歷了一個由混合到分化、由實用性到審美性、世俗性到超越性的演變過程。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一些考古發掘資料,按時間的先后順序可將臺的功能劃分為以下五類:一、避濕、藏寶、囚閉;二、觀天象、察災祥;三、祭祀或紀念;四、軍事防御;五、登高、遠望、游樂觀賞。
《說苑·建本》有言:“今夫辟地殖谷,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藥草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10]可以確定的是,最初臺的建造是出于防水防潮、加固地基、防御等生存性目的,只是這些目的達成之后,臺在功能上開始轉向其他方面。關于藏寶之用,《史記·殷本紀》《史記·周本紀》中有關商紂鹿臺的記載最為明確。臺作為囚閉之用,最早見于《史記·夏本紀》中對“夏臺”的記載。《左傳·僖公十五年》記載秦穆王夫人登臺履薪自囚之事,也是臺作為囚閉之用的最好體現。
周制天子曾筑三臺,且各有功用。《毛詩正義》指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囿臺以觀鳥獸。”[11]實質上,作為一種禮制建筑,靈臺最初就是用來觀察天文的。宋朱熹《詩集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氣祲,察災祥,時觀游。”[12]古時,星象通常是與國家歷法以及政治上的興衰“掛鉤”的,所以才要觀天象以察災祥。歷史上諸如周穆王、周靈王、楚靈王、楚莊王等都曾筑高臺用以“登浮云”“窺天文”“招神異”“待‘化人’”。《列子》卷三“穆天子”章開篇說的就是周穆王招待“化人”的故事。周穆王招待他,“敬之若神,事之若君”[13]。由此可知,先秦時期,諸侯筑臺以觀天象、察災祥、通神明的做法十分普遍,而且這一做法一直延續到了近代。
作為祭祀或紀念用的臺,被稱為“禮臺”。“禮臺”是古代帝王用來受天命、定秩序的臺,在象征意義上,人們認為臺具有與神溝通的功能。上古就有以部落首領名字命名的軒轅臺、帝堯臺、帝舜臺等具有紀念性功能的臺。到了西漢,“禮臺”開始廣泛出現在各種禮制建筑群中,或作為大型禮制建筑的基底,如明堂、太廟等,或作為統領眾多附屬建筑的中心,如天壇、地壇、社稷壇等。除了用于祭祀天地的皇家祭臺外,民間亦有用于旱祭的舞雩臺。除了祭祀,具有紀念意義的臺還有很多,如秦趙澠池會盟時的會盟臺、蘇秦掛印六國的拜相臺。
防御性是臺的一個基本功能。古人建臺的初衷就是為了防水防潮、防御災害,在此基礎上才有了觀天象、祭祀、游樂等其他功能。古時的臺既高且大,站在上面既能看得遠,又方便察看周遭情況,居高臨下利于防守。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墻開始取代臺的功能,起到防御作用。為了進一步加強防御,人們專門設置了城門臺,后又出現了專門用于預警的烽火臺。到了漢代,烽火臺被普遍應用于軍事防線和重要通道上,具備軍事堡壘作用。
對于從哪一段時期來劃分臺的游賞功能的問題,筆者暫時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因為“臺”在產生之初往往是多種功能混雜,或雖以某種功能為主,但并不排除其他次級功能的一個存在。比如,同樣用于觀測天象的靈臺也可以用來游觀。純粹出于觀賞目的而建造的臺出現時間較晚,大概在春秋戰國時期。這種臺一般上面不建造建筑,或只建造體量較小、視線通透的亭、榭,比如山東瑯琊臺、廬山主峰頂漢陽臺。這種純粹的觀賞臺的發展在后世江南園林設計中達到了頂峰,如眺望臺、釣魚臺、賞月臺等。
從以上分析可知,臺在功能上呈現出由混合到分化,由實用性、象征性向審美性、世俗性轉變的發展趨勢。“而正是功能內涵上的延伸導致分化出一些相關的建筑類型……正是這些有著不同功能的臺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漸出現差異,才逐漸影響了城市形態的結構與特征。”[14]
三、“臺”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一)“臺”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
幾千年來,中國人與其所生存的自然環境緊密結合。這“既出于情感,又是一種與現實保持距離并對其進行反思的美學思考”[15]。“情感”與“反思”可以代表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的兩個階段。以高山為例,原始時期,人們供奉犧牲祭祀山神,以保佑四季平安,這是出于強烈的崇拜情感和功利心理。后來,隨著了解程度的加深以及掌控能力的增強,山川便成為人們歌詠與敬愛的對象。此時,山已經抽離了原始時期的實用性,借助其物質形態升騰為一種純粹意義上的審美性。人與自然關系的轉變進而影響到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溝通媒介——人造物“臺”的功能與價值轉化。臺由先前用于觀天象、通神明、防御的實用、象征之“臺”,變為用于觀覽、登高、清談之“臺”。同樣,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除了體現為一種哲學上的信仰外,還表現為另一種中國傳統文化——風水。風水最為恰切地體現在了傳統筑造物上。傳統筑造物最為真實地體現了文化意識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博弈與平衡,如閬中古城觀星臺的設置。
(二)臺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另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古典詩詞上
“臺”的意象很早就出現在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且最易讓人發思古之幽情。陳子昂登幽州臺而覺時空之綿遠和個人之渺小;杜甫滿腹悲苦,登臺嘆息;李白曾對金陵鳳凰臺發過感慨。這樣一種悲愁的情緒,一種有關個人、國家、人生的“憂患”意識始終貫串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之中,而臺則成為他們抒發此種情緒、意識的審美載體。首先,臺以其高大莊嚴的建筑特點體現出了強烈的宇宙時空之感。李允鉌先生指出:“建造臺的目的有一種希望達往高空伸展的意圖。”[16]臺之實體高聳入云,登臨其上會瞬間使人感到個人之渺小、人生之短暫,由此而生感傷。事實上,臺在文人墨客的詩詞中不僅具有審美性,某種意義上更具有一種超越性和永恒感。其次,文人墨客書寫的大多為歷史名臺,這些臺承載了歷史歲月之洗禮,容易讓人產生滄桑之感,比如古琴臺。最后,登高遠望、寫詩作詞,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表達情志,完成自我實現。“個人”“歷史”“宇宙”,古典詩詞通過“臺”這一媒介將傳統文人的所有情感、意緒全部展出。“‘亭臺樓閣’是作者感興的一個契機,使具體有限的物象事件、場景進入到無限的時間和空間,在歷史感、人生感、宇宙感的對照下創造深邃的意境。”[17]除了展現悲愁之外,臺還可以讓人獲得極目遠眺的愉悅之情。隨著臺純粹觀賞功能的增強,登高攬勝,開闊視野、披襟快意、獲得自然的美的享受便成為身為物理實體的臺最基本的功能。蘇軾曾作《超然臺記》,袁中道也曾作《清蔭臺記》作為對所造之臺給自己帶來歡樂的一種紀念。歷史上,嚴子陵隱于釣魚臺,目的同樣是為了獲得心靈的自由與詩意的人生。
(三)臺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更體現在文人推崇的雅文化上
與臺相關的雅文化最典型地體現在傳統園林設計中。晚明文人文震亨所撰《長物志》是我國古代造園名著之一,全書共十二卷,直接與園藝有關的有室廬、花木、水石、禽魚、蔬果。按照文震亨文中所述,《長物志》這本書是寫給幽人、韻士看的,而非普通大眾,這表現出他強烈的文人趣味。他將“古”“雅”“隱”作為園林建造上意趣追求的最終標準,排斥時尚俗制,整本書展現了一個異常主觀化的文人精神世界。“臺”位于《長物志》室廬卷,“筑臺忌六角,隨地大小為之。若筑于土崗之上,四周用粗木,作朱闌亦雅”[18]。位置、樣式、大小、材料、裝飾都有詳細的描述和建議,文震亨對園林風格的追求正是明代文人審美趣味的縮影。除了《長物志》,園林設計家計成的《園冶》也是明代一部造園名著,它也向我們展示了明代文士階層日常生活的真實細節和文化品位。
研究中國傳統建筑“臺”及其文化價值演變,某種意義上是要以此為基點,從一個獨特的側面來揭示中國傳統建筑的空間精神。因為,建筑作為一種空間藝術,其功能不只是“生理意義上的‘安身’”,更是“生存整體意義上的‘筑’和‘居’”[19]。正如諾伯舒茲所言:“人不能僅由科學的理解獲得一個立足點。……人的基本需要在于體驗其生活情境是富有意義的。”[20]這里的“生活情境”“富有意義”均是指建筑空間精神層面的內涵。中國傳統建筑“臺”在后世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剝離了早期的實用功能,留下了登高遠望、游樂觀賞等審美游覽性質的文化(活動)功能。而這樣一種功能性質的臺,它所達成的就是一種“意義空間”。人們在其中所要獲得的是人與天地宇宙融為一體的在家居住的歸屬感,而這也就是中國傳統建筑獨特的空間精神內涵。
四、結語
將“超越性”與“世俗性”作為建筑物臺的文化價值特征并不是說兩者分別代表了兩個時期,而是說大多數情況下兩者是混雜的,處于一種混合狀態,只是說混合時哪一種狀態鮮明一些罷了。臺的價值演變往往反映了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動態。無論如何,臺是一個媒介、一個人造物,古人通過登臺來追尋宇宙之道、契合自然之律、理解前人,最終與自身達成和解。因此,臺是人們溝通世界的“永恒橋梁”。現代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比較淡漠,反映在城市規劃和設計上就是城市中與人的心靈緊密相關的趣味性的文化建筑不多,功能性的西式建筑卻到處都是。在西方人眼中,建筑是作為“奇觀”來建造的,而在中國古人眼中,建筑是作為世界的一部分被體驗到的。中西方建筑思想上的這種差異需要引起我們的城市規劃者和設計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