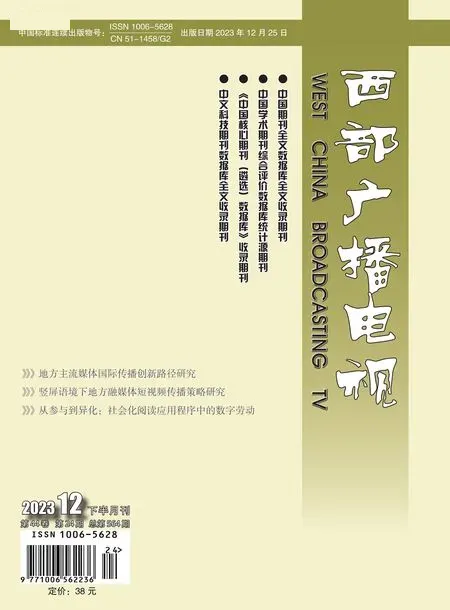新媒體環境中獨立紀錄片的傳播策略
閆綠春
(作者單位:西安財經大學文學院)
筆者通過在中國知網上以“獨立紀錄片”為主題詞進行檢索,發現近五年來對于這一方向的研究僅有192篇文獻,多數研究方向集中在以典型案例來分析該類型紀錄片的特點與發展上。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發現對于瞬息萬變的新媒體環境下的獨立紀錄片傳播路徑優化策略分析的文獻較少。通過觀看相關獨立紀錄片與查找總結文獻資料,得出新時代的獨立紀錄片應抓住新媒體這一新機遇,獨立紀錄片制作者應在保持初心的基礎上更多地去關注那些還未或者正在走向大眾視野的人群或事物,運用多樣化的制作形式與新的技術手段去吸引年輕受眾的注意力,借助網絡傳播這一快車道讓獨立紀錄片在各渠道與平臺上實現快速傳播。而在此基礎上本文也旨在豐富關于獨立紀錄片的思考和研究。
1 獨立紀錄片的概念
獨立紀錄片是記錄電影美學的第一集團,是紀錄片市場的第二集團。它沒有固定的操作模式,具有個性化明顯、個人化顯著的生產模式,相比電影、電視劇等搶占商業市場,獨立紀錄片更注重導演或創作者本人的意識形態立場與藝術表達[1]。1991年年底,在北京西單某公寓里, 張元、吳文光、時間、蔣樾、郝志強等人聚在一起,準備“掀起一個什么運動,我們要和別人對著干,要和腐朽的電影人傳統對著干”。這個“新紀錄運動”強調制作的獨立性, 在當時的中國語境里,這個所謂的新紀錄片是一個獨立紀錄片的概念[2]。這次聚會雖被寫入了歷史,但是其中的獨立主要是指創作精神層面,并未對獨立紀錄片的概念做具體的定義。
隨著獨立紀錄片作品不斷被創作出來,有學者對這一新紀錄片形態進行了闡釋。峰萬里將獨立紀錄片定義為官方之外的“民間力量”制作的“民間紀錄片”。詹慶生和尹鴻在《中國獨立影像發展備忘》中對獨立影像進行定義:所謂“獨立影像”是指沒有進入這種體制內的審批程序或者沒有在體制內的主流媒介渠道播映的影像作品[3]。這其中所提到的作品既包括傳統的電影、電視作品,也包括當時比較興起的數字影像(DV或者HDV),并且這些作品在類型上,既涵蓋了長短不同的劇情片、實驗片,又包括了紀錄片。這一定義也被后來的學者多次肯定與引用。
當時學者對于獨立紀錄片的定義參考還主要停留在1990年代到二十世紀之前的作品,而今獨立紀錄片在中國已經發展了三十多年,因此應結合當下社會語境對獨立紀錄片概念進行厘清與更新。筆者認為,獨立紀錄片應當是其制作資金與團隊不受官方的顯性控制,且其創作者能夠不被輿論、市場、社會等因素束縛的一類作品。
2 獨立紀錄片的傳播困境
傳統的傳播渠道中,獨立紀錄片往往以藝術電影、電影節、學校巡映,以及以內部創作圈為主的人際傳播為傳播媒介,有著以導演為創作中心的生產模式,制作成本較低,主要突出創作者本人的藝術個性與社會思考。其受眾定位也主要是小眾人群,不具有特定性。相較于其他類型的紀錄片,獨立紀錄片多關注于社會邊緣人群,而媒介環境的變化使得獨立紀錄片在保留創作自由的基礎上,傳播路徑也有了新的變化。本文主要從傳播渠道與受眾兩方面對其傳播困境進行分析。
2.1 缺少經濟支撐,傳播渠道局限
獨立紀錄片當下面臨的困境之一是傳播渠道狹窄,傳播平臺有限,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經濟來源缺乏。獨立紀錄片制片人大多沒有固定收入,資金主要來自個人籌措,國家以及組織給予的資金有限。對于獨立紀錄片創作者來說最困難的便是如何進行處女作創作,因為在其證明自己有創作實力之前是不可能有任何外部的投資的,且相當一部分創作者即便拍攝了很多部紀錄片也依然沒有得到任何外部資助。比如胡杰自1995年拍攝第一部作品后的十來年,其作品都是自費完成的,蔣樾的《彼岸》拍攝完成前后花了十幾萬,除了廣告的投入外還借了很多錢,此后的許多年才慢慢還清。因此,很多創作者在作品的后續發行方面大都面臨著困難。2017年大家都為一部紀錄片淚流滿面——《尋找手藝》,但是受限于資金,無法進行更全面的宣傳甚至是多個渠道的放映,當《尋找手藝2》在B站悄無聲息上映后,三個月里的播放人數甚至比不上一個小網紅一場直播的觀看人數,面對采訪,這部獨立紀錄片的導演張景卻說:“覺得自己挺失敗的。失敗的根本原因則是自己沒有將這些傳統手藝很好的展現給社會,只能任憑這些手藝最后消失在時間的洪流里。”因此可以看出,獨立紀錄片的宣發存在著一定的現實困難。
由于歷史原因,獨立紀錄片很難在國內的商業院線進行放映,只能通過少數平臺放映或者通過民間組織進行傳播,主要是少數人之間的人際傳播,比如電影節、大學巡映會、各種民間社團以及官方半官方組織的活動。這種渠道的優點是觀眾忠誠度比較高且效果比較明顯,創作者能夠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但是也存在弊端,具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受眾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地點才能觀看,并且需要場地的布置,因此,導致了傳播規模的不夠。國外獨立紀錄片的傳播渠道則更為廣闊,這保證了獨立紀錄片的生存空間,例如美國、法國等公共電視臺會設立一個專門的時段去放映一些具有現實與社會意義的紀錄片,相比之下,在國內有利于獨立紀錄片傳播與發展的渠道還亟待完善。
2.2 獨立紀錄片的受眾選擇
獨立紀錄片的重點并不在經濟效益與流量上,其內容多體現創作者本人的思想意識和審美,也就意味著其很難引起受眾的較大興趣。在新媒體環境下的文化商品時代,獨立紀錄片處于一種非常尷尬和無奈的狀態,但很多獨立制作人仍然堅持創作,如蘇青、米娜的《梧桐樹》、郭熙志的《渡口編年》系列、李維的《塵默呼吸》等。獨立紀錄片內容選擇上主要從個體切入,通常是對底層人民的真實寫照,也是對邊緣群體精神狀態的展現。例如,對民俗傳承、罕見病群體、留守兒童等問題的深度調查與挖掘。創作者的鏡頭更像是一種記錄,像鏡子一樣傳遞影像內容,是對社會中小角落的人物生活、工作的聚焦,以此呈現這些人的生活百態。這種題材大都體現著創作者的一種責任與使命。獨立紀錄片導演將創作主體瞄準社會中的邊緣人群,獨立紀錄片的主題可能與大部分大眾普遍喜歡的題材不同,加之受眾的素質水平不同,因此在傳播上其主題選擇可能并不為部分受眾所接受。
除了創作題材可能不為大眾所感興趣外,隨著新媒體技術催生了新的內容傳播方式及社會話語權的下移,用戶在視頻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序(Application, App)觀看視頻時發送彈幕已經是基本操作,他們能夠及時將自己的觀點反饋給創作者以及觀看該視頻的用戶,受眾的身份也發生了轉變。同時,大批類型單一視頻的涌現大大降低了受眾的體驗感,導致受眾產生審美疲勞。另外,有時候彈幕數量也會成為受眾決定是否觀看視頻的原因。在新媒體時代,如何吸引更多的受眾關注,成為當下獨立紀錄片亟待解決的問題。
3 新媒體環境下獨立紀錄片傳播優化策略
伴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以互聯網技術為支撐的新媒體快速成長起來。新媒體環境對獨立紀錄片的傳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4]。新媒體技術為獨立紀錄片的創作注入嶄新的血液的同時,也為其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間。這是新媒體環境給獨立紀錄片帶來的新機遇,也是這一類型的紀錄片即將或正在面臨的新挑戰。面對這一全新的挑戰,創作者抓住機遇便可將自己的作品廣泛傳播,從而向社會受眾傳達自己的思想,達成自己的創作初衷,豐富中國影視創作業態。
3.1 積極參加比賽,促進多平臺傳播
伴隨著電子設備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對影視有著天然的親切感,當然也有表達心理訴求的強烈愿望。智能手機、微單、單反的普及方便了創作者制作獨立紀錄片,為全民創作提供了技術支持。在全民創作的獨立紀錄片的質量和數量都有所上升的情況下,一些國內外紀錄片比賽逐漸增多,且越來越受到受眾的歡迎,各大互聯網平臺或者官網也在增設舉辦紀錄片比賽等相關活動,這無疑為好的獨立紀錄片的宣傳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創作者積極參與線上投稿或線下競賽,讓自己的作品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傳播范圍也將進一步擴大。
短視頻和視頻平臺的涌現,對獨立紀錄片的傳播起到了助推作用。例如,優酷、騰訊、愛奇藝等視頻平臺專門設立了紀錄片頻道,使得觀眾發現、欣賞獨立紀錄片更加方便,也使得更多名不見經傳的作品有了能更大范圍傳播的舞臺。另外,相較于傳統媒體和以往的獨立紀錄片的傳統傳播渠道受到時間、空間的限制,網絡媒體完全可以避開這些因素的限制,這也是獨立紀錄片在新媒體時代必須要重視網絡與新媒體傳播途徑的原因之一。
近十年來,獨立紀錄片創作者首選的傳播渠道還是線上放映,并且在新媒體環境下創作者既可以選擇將自己的作品作為商業影片,以折扣價格授予視頻網站等途徑進行傳播;或者使用微博、小紅書、抖音等平臺上的領域大V或者KOL(Key Opinion Leader,意見領袖)進行轉發推廣,也可以在網站上公布自己的作品下載鏈接,拓寬作品的傳播渠道。此外,獨立紀錄片專題網站的設立也為創作者傳播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渠道。創作者也應利用好視頻網站、網絡社交媒體、移動終端等媒介,拓展獨立紀錄片的傳播范圍,多傳播平臺的呈現是非常有必要的。
3.2 結合受眾心理,平衡時代話語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手段的不斷迭代,就獨立紀錄片自身的發展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在網絡媒體飛速發展的大環境下找出一條適合獨立紀錄片發展的路線,不斷創新紀錄片創作模式及制作方式,以多樣化的呈現方式突破傳統紀錄片創作瓶頸[5]。自媒體普及以來,受眾對紀錄片的要求也愈來愈高,視頻內容吸引用戶注意力的難度越來越大,如果內容的主題或者題材不符合受眾口味,他們就很容易關閉掉視頻頁面。因此,新媒體平臺可以結合受眾的心理和觀看習慣,通過大數據算法分析,給受眾打上不同的標簽,針對受眾喜好進行精準的內容推送。獨立紀錄片應打破傳統紀錄片的受眾群體組成,細分受眾標簽,精準定位傳播更多故事,讓受眾成為“真愛粉”。借助新媒體平臺,創作者與接收者之間形成“面對面”的交流,這樣一個網絡傳播體系的形成,既能激發創作者的熱情,也能使得受眾對其滿意并愿意向其他人安利其作品,從而達到不錯的傳播效果。
受眾關注的即獨立紀錄片需要擁有的,創新與創意是決定受眾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年輕人無疑是當下紀錄片的主要受眾,所以獨立紀錄片需平衡時代話語,結合當下社會最主流的受眾人群,逐漸與時代腳步并齊,實現作品更有效、迅速的傳播。另外,作品內容與題材能夠吸引年輕受眾,但這不是增強用戶黏性的唯一要素,創作者在剪輯過程中可以加入特定的動畫特效,既能推動情節發展,又能增強獨立紀錄片的生動與趣味性。當下年輕人對新事物充滿著好奇,他們時刻準備迎接挑戰的姿態是值得獨立紀錄片創作者注意的。抓住年輕受眾這一特點,在獨立紀錄片的視覺呈現上使用3D、跳剪、快切等影視制作手段,打造電影質感,呈現高質量、精良的視覺效果,更符合年輕受眾的審美偏好,有助于提升獨立紀錄片的傳播效果。
4 結語
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獨立紀錄片的傳統傳播渠道總是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雖然也有優秀作品出現,但傳播效果卻不佳。在萬物皆媒的時代,互聯網讓社會更多的角落被照亮,因此獨立紀錄片創作者要借助各種短視頻和互聯網平臺傳播更多有價值的主題與內容,并且積極參與線下比賽,將作品上傳至各種視頻App、網站等,以此提升自己作品的傳播范圍。在吸引受眾方面,偏向營造更適合年輕人審美偏好的影視風格,并且創作更多高質量、精良的作品去吸引受眾的注意力,然后利用新媒體的多種渠道、多個平臺去宣傳自己的作品。在這個傳播效果有著明顯變化的網絡媒體時代,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拿起手中的手機與相機參與到獨立紀錄片的制作與傳播當中,這也是創作者提高自己制作能力與水平的時機。獨立紀錄片創作者通常比普通大眾有更廣泛與深入的觸角去接觸社會上不同的群體,因此如果他們可以在主流渠道中展示自己的才華,在民生方面關注社會、傳播人文關切、承擔責任,也能夠大大促進獨立紀錄片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