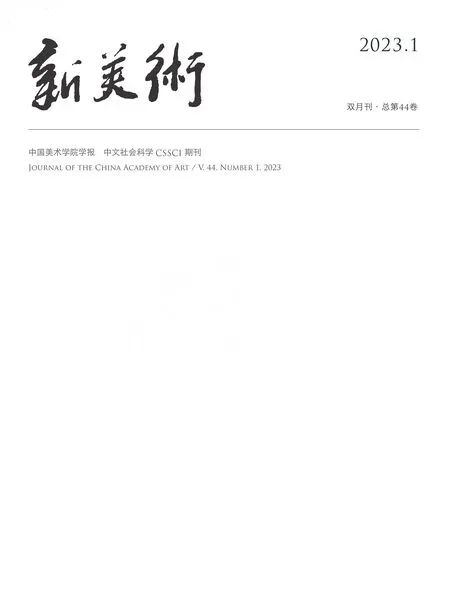視覺紋理的再現(xiàn)(三) 展現(xiàn)瞬間運(yùn)動(dòng)的筆墨紋理
楊崇和
49 注32 中所引高居翰著作,第124、125 頁(yè)。
“視覺紋理再現(xiàn)”的前兩篇文章主要關(guān)注10 至17世紀(jì)的畫家們?nèi)绾谓鉀Q自然紋理的再現(xiàn)問題。1楊崇和,《視覺紋理的再現(xiàn):十至十七世紀(jì)中國(guó)山水畫中的例證》,載《新美術(shù)》2019年第3期,第55—73頁(yè),后文簡(jiǎn)稱《紋理再現(xiàn)》;楊崇和,《視覺紋理的再現(xiàn)(二):自然、古典與氣韻生動(dòng)》,載《新美術(shù)》2021年第5 期,第181—196 頁(yè),后文簡(jiǎn)稱《紋理再現(xiàn)(二)》。雖說(shuō)數(shù)百年間文人畫中常常流露出頗具個(gè)性的筆墨,但嚴(yán)肅的畫家從未放棄追求自然紋理的再現(xiàn)。在《視覺紋理的再現(xiàn)(二):自然、古典與氣韻生動(dòng)》中,我們還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分析了山水畫,試圖建立紋理再現(xiàn)的客觀標(biāo)準(zhǔn)。同時(shí)也應(yīng)看到,元代之后,文人畫家對(duì)再現(xiàn)的興趣漸漸從自然景物的紋理轉(zhuǎn)向筆墨自身生成的紋理。到了晚明,董其昌(1555—1636)終于提出顛覆性的山水畫審美標(biāo)準(zhǔn):“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立志將山水畫變成筆墨之藝術(shù)而獨(dú)立于自然景物的再現(xiàn)。2石守謙先生在研究董其昌《婉孌草堂圖》已經(jīng)指出這一點(diǎn),參見石守謙,《董其昌〈婉孌草堂圖〉及其革新畫風(fēng)》,載《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第548—568 頁(yè);石守謙,《山鳴谷應(yīng):中國(guó)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石頭出版社,2017年。本文是此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試圖從董其昌的視角出發(fā)觀看和討論山水畫中筆墨紋理自身的再現(xiàn)。
一 運(yùn)動(dòng)再現(xiàn):瞬間與片刻
在討論筆墨之前,有必要先了解“運(yùn)動(dòng)再現(xiàn)”[Representation of motion]的基本觀念。1964年6月貢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在瓦爾堡研究院舉辦的“時(shí)間與永恒”系列講座上做了題為“藝術(shù)中的片刻與運(yùn)動(dòng)”的演講,他在開場(chǎng)白中說(shuō):“在藝術(shù)領(lǐng)域,空間及其再現(xiàn)問題以近乎夸大的程度占據(jù)了藝術(shù)史家的注意力;而時(shí)間與運(yùn)動(dòng)的再現(xiàn)卻被莫名其妙地忽略。”指出這一課題缺乏系統(tǒng)性的研究。3Gombrich,E.H.“Moment and movement in art.” The Image and the Eye:Further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Phaidon Press Limited,1982,pp.40-62。中譯本可參見貢布里希,《圖像與眼睛:圖畫再現(xiàn)心理學(xué)的再研究》,范景中等譯,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3年,第39—60 頁(yè)。此后的數(shù)十年中,這個(gè)被忽略的課題逐漸受到學(xué)者們的重視,豐富細(xì)致的研究成果接踵而至。一方面,再現(xiàn)畫面運(yùn)動(dòng)感的主要元素被梳理清楚,它們是:動(dòng)態(tài)平衡、傾斜、運(yùn)動(dòng)時(shí)產(chǎn)生的(有時(shí)是想象的)軌跡、運(yùn)動(dòng)的方向、離開起始點(diǎn)或平衡點(diǎn)的距離等等。4例如參見:J.M.B.de Souza and M.C.Dyson.“An Illustrated Review of how Motion is Represented in static Instructional Graphics.” 1st Global Conference-Visual Literacies:Exploring Critical Issues,Mansfield College,Oxford,July 3-5,2007。也就是說(shuō),具有這些元素的繪畫能讓觀者感受到畫中景物的運(yùn)動(dòng)感;另一方面,運(yùn)動(dòng)再現(xiàn)與時(shí)間密切相關(guān),瞬間[Instant]和片刻[Moment]這兩個(gè)原本并無(wú)嚴(yán)謹(jǐn)定義的時(shí)間單元在表述運(yùn)動(dòng)再現(xiàn)時(shí)也被明確區(qū)分,5Cutting,J.E.“Representing Motion in a Static Image:Constraints and Parallels in Art Science and Popular Culture.” Perception,vol.31,no.10,2002,pp.1165-1193。事實(shí)上,片刻和瞬間在照相技術(shù)發(fā)明之前并沒有被藝術(shù)史家嚴(yán)格區(qū)分,這可以從貢布里希引用的18世紀(jì)文獻(xiàn)中看出。在歷史文獻(xiàn)中用瞬間表達(dá)片刻時(shí)有發(fā)生,為使上下文順暢,貢氏也會(huì)沿用瞬間來(lái)代指片刻,但貢氏本人在論及二者時(shí),是將它們區(qū)別對(duì)待的。它們的含義分別簡(jiǎn)述如下:
瞬間高速照相機(jī)拍攝到的運(yùn)動(dòng)圖像相當(dāng)于在某一特定“時(shí)間點(diǎn)”上凝固了運(yùn)動(dòng)的一個(gè)剎那,它捕捉到的瞬間圖像是肉眼難以分辨甚至無(wú)法看到的。這句話在今天很容易理解,但在1878年之前則不然。那時(shí),大眾對(duì)瞬間的認(rèn)知主要是基于日常的經(jīng)驗(yàn),它幾乎是“真實(shí)和可信的代名詞”。6Prodger,Phillip.Time Stands Still:Muybridge and the Instantaneous Photography Move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3.1878年,邁布利奇[E.Muybridge,1830-1904]經(jīng)過數(shù)年努力終于成功拍攝出一組賽馬奔跑的清晰照片,7邁布里希為斯坦福[Leland Stanford,1824-1893]拍攝奔馬照片的工作始于1872年,但直到1878年才拍出一組令人信服的清晰照片。奔馬的姿態(tài)被瞬間攝影[Instantaneous Photography]所“凝固”(圖1)。它和人們?nèi)粘!翱吹健焙汀罢J(rèn)為”的奔馬姿態(tài)是如此不同,照片記錄的馬腿在奔跑時(shí)的真實(shí)動(dòng)作與人們自以為是的姿勢(shì)差異甚大。那種四蹄前后伸展、同時(shí)離地的動(dòng)作雖然被千百年來(lái)的中外藝術(shù)家反復(fù)描繪(圖2、圖3),但其實(shí)并不存在。恰恰與之相反,當(dāng)奔馬的四蹄同時(shí)離地時(shí),它們是收于腹下的。因此當(dāng)照片發(fā)表后不僅在普通民眾間,也在科學(xué)和藝術(shù)界引發(fā)震撼和爭(zhēng)議。隨著攝影技術(shù)的不斷進(jìn)步,照相機(jī)捕捉的瞬間越來(lái)越短,以至于被一些學(xué)者稱作“時(shí)間的膠囊”[Encapsulation of Time]。8參見 Eisner,W.Comics and Sequential Art.Poorhouse Press,1985。例如,在子彈擊中玻璃瓶的剎那,高速攝影捕捉的瞬間能凝固玻璃碎片飛散在空中的形狀,好比將時(shí)間裝入膠囊,不再流動(dòng)。今天,人們對(duì)照相機(jī)拍下的五花八門的瞬間圖像早已見怪不怪,眼見未必真實(shí)而真實(shí)也未必可見的觀念已融入我們的認(rèn)知文化中。

圖1 邁布利奇于1878年首次成功拍攝的賽馬奔跑瞬間的清晰照片

圖2 唐代章懷太子李賢墓壁畫中的奔馬姿態(tài),陜西歷史博物館

圖3 法國(guó)畫家西奧多·杰利柯繪于19世紀(jì)初的奔馬姿態(tài),巴黎盧浮宮
片刻 在攝影技術(shù)能夠“凝固”瞬間圖像之前,畫家繪制具有運(yùn)動(dòng)感的圖像時(shí)所對(duì)應(yīng)的時(shí)間是片刻。如果說(shuō)瞬間意味著一個(gè)“時(shí)間點(diǎn)”,片刻可以理解為是一個(gè)“時(shí)間段”,其較前者更為寬泛,能完整囊括畫家要敘述的故事。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維納斯的誕生》為我們很好地展示了時(shí)間片刻中的運(yùn)動(dòng)再現(xiàn)(圖4):先看畫左方懸在空中的兩位風(fēng)神,他們向右傾斜的上身與身后飄舞的衣裾讓觀眾感受到他們正飛向畫面中央的維納斯,其中一位鼓起腮幫,另一位微微張嘴,一起吹出白色煙霧,那是想象中風(fēng)的軌跡;此時(shí),維納斯和春神的秀發(fā)、長(zhǎng)裙以及手中的繡花斗篷迎風(fēng)揚(yáng)起(在靜止的情況下它們本該垂向地心——靜態(tài)的平衡點(diǎn),但風(fēng)力的作用使它們達(dá)到一種動(dòng)態(tài)平衡);還有風(fēng)神扇動(dòng)的翅膀、空中飄舞的花朵等等,上文提到的產(chǎn)生運(yùn)動(dòng)感的幾種元素幾乎全部被畫家恰到好處地融入畫中的情景中,完美地構(gòu)建了他要敘述的故事。不過我們要問:這樣一個(gè)既有完整的敘事又充滿運(yùn)動(dòng)感的畫面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是否真的存在?貢布里希的回答是:幾無(wú)可能!貢氏用電影拍攝的過程來(lái)解析類似《維納斯的誕生》這樣的畫面:9貢布里希所引用和分析的畫作是保羅·德·馬太斯[Paolo de Matteis,1662-1728]的《赫拉克勒斯的選擇》,參見注3所引貢布里希文章。設(shè)想一架攝影機(jī)正拍下《維納斯的誕生》中的動(dòng)態(tài)場(chǎng)面,這個(gè)過程也許經(jīng)歷了幾秒鐘并耗用了上百?gòu)埬z片,每張膠片可以看作是一個(gè)瞬間。現(xiàn)在我們要從其中尋找一張與《維納斯的誕生》畫面完全一樣的膠片,卻發(fā)現(xiàn):當(dāng)風(fēng)神的姿勢(shì)和畫作上相同時(shí),維納斯的右腿可能正跨向岸邊,或者春神的右手尚未舉過頭頂;也許確有一張膠片,其中所有人物的肢體動(dòng)作都和畫上相同,春神卻可能因風(fēng)的吹拂剛好閉上了眼睛,或者飄在空中的花朵已落入水中……總之,和畫面完全相同的那張膠片(或者說(shuō)那個(gè)瞬間)幾乎沒有可能存在,若想得到它只能通過“擺拍”,相當(dāng)于在上百?gòu)埬z片中找出局部效果滿意的幾張(幾個(gè)瞬間),然后將它們“合成”從而得到滿意的畫面,即這幾個(gè)瞬間的集合剛好組成了一個(gè)藝術(shù)家想要的片刻。19世紀(jì)中葉之前,西方繪畫中的運(yùn)動(dòng)再現(xiàn)大約如此,其所對(duì)應(yīng)的時(shí)間是片刻并非瞬間。如此才能將不同時(shí)間點(diǎn)、不同層面的多重?cái)⑹氯谟谕划嬅嬉詽M足故事情節(jié)在人們心理上的真實(shí)感。相反,瞬間所“凝固”的物理真實(shí)由于缺乏時(shí)間上的延續(xù)性,常常無(wú)法滿足畫家或觀眾所期待的敘事。

圖4 波提切利,《維納斯的誕生》,佛羅倫薩烏菲齊美術(shù)館
另一方面,即使畫家想要再現(xiàn)照相機(jī)所捕捉的瞬間圖像,其可行性也微乎其微。1981年,馬克·坦西[Mark Tansey,1949-]創(chuàng)作了一幅“畫中畫”,圖中一位女畫家正在繪制車禍發(fā)生一剎那的場(chǎng)景(圖5),這當(dāng)然只是畫家的想象,現(xiàn)實(shí)中是無(wú)法做到的,它暗示了運(yùn)動(dòng)的瞬間再現(xiàn)和畫家能力之間的矛盾。馬克·坦西是位頗具哲學(xué)思辨的藝術(shù)家,他為這幅作品起了耐人尋味的名字:《行動(dòng)繪畫》[Action Painting],用以批評(píng)和諷刺那些不再關(guān)心具象再現(xiàn)的行動(dòng)畫派的畫家們。如果說(shuō)威廉·德庫(kù)寧[Willem de Kooning,1904-1997](行動(dòng)畫派的靈魂人物)所作的人像畫還保留一些具象元素,那么畫派的另一位巨擘,杰克遜·波洛克[JacksonPollock,1912-1956]的“滴畫”[Drip Painting]則完全擺脫了具象的約束。傳統(tǒng)意義的圖像在杰克遜·波洛克的畫布上不復(fù)存在(圖6),畫布上滴濺的色彩真實(shí)記錄了他揮灑顏料的每一個(gè)瞬間,“運(yùn)動(dòng)造成的視覺記憶,滯留在空間里”,10杰克遜·波洛克題在自己照片背后的句子,照片攝于他的畫室,時(shí)間大約在1948—1949年間。“畫布上出現(xiàn)的不再是圖像,而是事件”。11羅森博格[H.Rosenberg,1906-1978]首先使用了行動(dòng)繪畫一詞,并對(duì)行動(dòng)繪畫做了定義和分析。參見Rosenberg,H.“The American Action Painters.” Art News,vol.51,no.8,1952。而畫布上再現(xiàn)的瞬間運(yùn)動(dòng)不僅記錄下創(chuàng)作過程,同時(shí)它就是作品本身。

圖5 馬克·坦西,《行動(dòng)繪畫》,1981年,美國(guó)私人藏

圖6 杰克遜·波洛克的“滴畫”作品,紐約當(dāng)代美術(shù)館
事實(shí)上,運(yùn)動(dòng)的瞬間再現(xiàn)也同樣存在于古典繪畫,只是它們往往保留在原創(chuàng)畫稿中,在最終完成的畫作上已被刻意掩蓋。16世紀(jì)時(shí)瓦薩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已經(jīng)意識(shí)到“無(wú)論是繪畫、雕塑還是別的什么東西,它們的美麗的草圖[una bella bozza]要比精細(xì)的完工之作更優(yōu)美、更有力”。12轉(zhuǎn)引自貢布里希,《藝術(shù)與錯(cuò)覺》,楊成凱、李本正、范景中譯,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2年,第163 頁(yè)。話雖如此,瓦薩里的這種超前的審美并未在當(dāng)時(shí)形成主流,多數(shù)藝術(shù)家和鑒賞家還是更喜愛“精細(xì)的完工之作”。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創(chuàng)作《自由引導(dǎo)人民》時(shí)留有一張油畫稿(圖7),畫布上橫涂豎抹的筆觸,儼然是一幅行動(dòng)畫派的佳作。但在“精細(xì)的完工之作”中,這些反映畫家最初創(chuàng)意的激情筆觸都不見蹤影,正是所謂一種藝術(shù)掩蓋了另一種藝術(shù)。直到19世紀(jì)后半葉印象畫派的出現(xiàn),創(chuàng)作時(shí)的筆觸才被畫家刻意保留在完工之作上,13在19世紀(jì)之前的一些畫作上刻意保留的筆觸也偶爾可見,例如在倫勃朗的某些作品中,但那還只是實(shí)驗(yàn)性質(zhì)的探索,既沒有引起當(dāng)時(shí)畫家群體的廣泛回響,也沒有得到多少觀眾的賞識(shí)。它們忠實(shí)記錄了行筆著色時(shí)的瞬間運(yùn)動(dòng)痕跡。

圖7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導(dǎo)人民》油畫稿,上海私人藏
基于運(yùn)動(dòng)再現(xiàn)的觀點(diǎn),我們可以這樣說(shuō):古典繪畫最終呈現(xiàn)給觀者的是運(yùn)動(dòng)場(chǎng)景,是片刻的再現(xiàn),例如《維納斯的誕生》;印象畫派刻意保留在所描繪景物上的筆觸,是瞬間的再現(xiàn)。而行動(dòng)畫派(及其他一些現(xiàn)代畫派)更進(jìn)一步,在波洛克的滴畫里,景物完全消失,作品只再現(xiàn)了畫家揮灑油彩的行為本身,即瞬間運(yùn)動(dòng)的痕跡。
二 筆墨紋理的再現(xiàn)
大約于14世紀(jì)初,趙孟頫(1254—1322)明確提出繪畫的筆墨應(yīng)與書法相通并將其付諸實(shí)踐,他說(shuō):“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huì)此,方知書畫本來(lái)同。”14趙孟頫此詩(shī)題在其《秀石疏林圖》(故宮博物院)卷后。 事實(shí)上,繪畫以書法用筆并非趙孟頫首倡,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就有“善書者往往善畫”的議論,但在趙孟頫的倡導(dǎo)和實(shí)踐之前,書法用筆在主流繪畫中未受到廣泛的重視,也未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這個(gè)主張被當(dāng)時(shí)的文人畫家群體迅速接納,逐漸演變成其后數(shù)百年間中國(guó)繪畫的主流。從紋理再現(xiàn)的視角觀看自趙孟頫至吳門諸家的山水畫,我們發(fā)現(xiàn),自然再現(xiàn)與古典筆墨時(shí)常出現(xiàn)在同一作品中,15《紋理再現(xiàn)(二)》中討論的兩幅文徵明的作品即屬于這種情況。那時(shí)的名家巨手兼有傳統(tǒng)筆墨的訓(xùn)練和洞見自然的能力,是董其昌所說(shuō)“畫家以古人為師,已自上乘,進(jìn)此當(dāng)以天地為師”的年代。16[明]董其昌,《畫禪室筆記》,載《景印文淵閣四庫(kù)全書》,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第867—448 頁(yè)。進(jìn)入晚明后,吳彬(生卒不詳)這樣的天才仍然能從自然紋理中發(fā)現(xiàn)靈感,17關(guān)于這個(gè)時(shí)期畫家再現(xiàn)自然紋理的討論,參見注1 所引二文。但總體而言,在經(jīng)歷數(shù)百年的發(fā)掘之后,依賴自然紋理汲取養(yǎng)分的筆墨創(chuàng)新幾近枯竭。此時(shí),董其昌另辟蹊徑,徹底回歸古典,在其中尋找創(chuàng)新的基石,以構(gòu)建筆墨的新形式。他將皴法從匹配自然的任務(wù)中解放出來(lái),走向展現(xiàn)筆墨自身紋理的新境界,形成了“山水畫與自然的對(duì)立”。18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duì)18世紀(jì)中國(guó)山水畫的一個(gè)新理解》,載《山鳴谷應(yīng):中國(guó)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第308—331 頁(yè)。那時(shí)的多數(shù)畫家在董其昌的影響下更專注筆墨形成的畫面效果,山水的自然屬性反而淪為陪襯。事實(shí)上,明清之際人們?cè)谡劶袄L畫的氣韻生動(dòng)時(shí),關(guān)心最多也正是筆墨本身。19這一點(diǎn)王世襄在《中國(guó)畫論研究》中做過較詳細(xì)的討論,本文不再贅述。參見王世襄,《中國(guó)畫論研究》,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283—286 頁(yè)。張庚(1685—1760)有一段關(guān)于氣韻發(fā)自筆墨的論述:
氣韻有發(fā)于墨者,有發(fā)于筆者,有發(fā)于意者,有發(fā)于無(wú)意者。發(fā)于無(wú)意者為上,發(fā)于意者次之,發(fā)于筆者又次之,發(fā)于墨者下矣。何謂發(fā)于墨者?既就輪廓,以墨點(diǎn)染渲暈而成者是也。何謂發(fā)于筆者?干筆皴擦,力透而光自浮者是也。何謂發(fā)于意者?走筆運(yùn)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疏密多寡,濃淡干濕,各得其當(dāng)是也。何謂發(fā)于無(wú)意者?當(dāng)其凝神注想,流盼運(yùn)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謂之為足則實(shí)未足,謂之未足則又無(wú)可增加,獨(dú)得于筆情墨趣之外,蓋天機(jī)之勃露也。然惟靜者能先知之……20[清]張庚,《浦山論畫》,載秦祖永輯,《畫學(xué)心印》卷七,清光緒四年(1878)刻朱墨套印本,葉四十三至四十四。
張庚自問自答地議論了筆墨和氣韻之間的各種相關(guān)性后,最終回歸到“天機(jī)之勃露”這一關(guān)鍵點(diǎn)上,“天機(jī)” 即大自然,它存在于“筆情墨趣之外”。那么接下來(lái)的問題是,脫離對(duì)自然的再現(xiàn),繪畫筆墨如何“天機(jī)勃露”?21關(guān)于氣韻生動(dòng)與再現(xiàn)自然的關(guān)系,請(qǐng)參見《紋理再現(xiàn)(二)》第二節(jié)“氣韻生動(dòng):一種假設(shè)及其客觀評(píng)測(cè)”。一句簡(jiǎn)單的“惟靜者能先知之”似乎過于玄虛,我們準(zhǔn)備從墨筆的運(yùn)動(dòng)及其紋理再現(xiàn)的觀點(diǎn)來(lái)回應(yīng)這個(gè)問題。
讀者可能會(huì)問,筆墨紋理并非自然景物,何以云“再現(xiàn)”而非“表現(xiàn)”?事實(shí)上,不論真山水中的自然紋理亦或紙絹上的筆墨紋理,都是客觀之存在,對(duì)視網(wǎng)膜來(lái)說(shuō)生成的都是視覺紋理;而中國(guó)畫家臨仿、借鑒經(jīng)典已有千余年的傳統(tǒng),既然被臨仿之物是客觀存在,將之稱作“再現(xiàn)”或許更加合適。如若借用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三個(gè)世界”的概念來(lái)理解,那么自然紋理是“世界一”中的客觀存在,畫家將其再現(xiàn)于紙絹之上所形成的筆墨紋理則是“世界三”中的存在,是波普爾所稱的“客觀的知識(shí)”。因此,以古典畫作為范本的臨仿或創(chuàng)作可以視為對(duì)“世界三”中客觀存在的再現(xiàn)。我們知道,再現(xiàn)自然(空間感或紋理)的繪畫,其任務(wù)是將三維世界中的景物轉(zhuǎn)換到二維平面上。而不論是“寫實(shí)”畫法追求的“形似”還是“寫意”畫法展現(xiàn)的“神似”,22此處“寫意”是指畫家所寫景物的客觀之意,而非畫家胸中的主觀之意。參見《紋理再現(xiàn)(二)》“附錄”中關(guān)于“寫意”的討論。成功的作品都會(huì)讓筆墨構(gòu)成的圖像產(chǎn)生逼真的錯(cuò)覺,這是一項(xiàng)頗具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不過,再現(xiàn)筆墨紋理(世界三)和再現(xiàn)自然(世界一)的情況有所不同,需要稍做區(qū)分。
(一)對(duì)古典筆墨的精確復(fù)制
筆墨紋理最直接的再現(xiàn)莫過于一絲不茍地臨摹古代大師的作品,人們或許認(rèn)為此種臨摹缺失了再現(xiàn)自然時(shí)需要的創(chuàng)造性,然而這樣的評(píng)論是否恰當(dāng)須在具體歷史環(huán)境下考察。在20世紀(jì)中后期的美術(shù)史主流語(yǔ)境里,清初“四王”(在王時(shí)敏的引領(lǐng)下)忠實(shí)于古典原作的嚴(yán)謹(jǐn)臨仿往往被視作了無(wú)創(chuàng)意。羅樾[Max Loehr,1903-1988]甚至認(rèn)為,像“四王”那樣的畫家是“畫家學(xué)者”[Painter Scholar],他們的作品與其說(shuō)是藝術(shù)不如說(shuō)是學(xué)術(shù),并建議將之排除在繪畫史的發(fā)展之外。23Loehr,Max.“Phases and Content in Chinese Painting.”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Taipei,1972,pp.285-297.這類觀點(diǎn)忽略了17世紀(jì)中國(guó)畫壇的狀況:當(dāng)時(shí)的“畫中有習(xí)氣惡派,以浙派為最。至吳門云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贗本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24[清]王原祁,《雨窗漫筆》不分卷,清光緒刻《翠瑯軒館叢書》本,葉一。最近的研究指出,“四王”正是在當(dāng)時(shí)古典繪畫語(yǔ)匯的真貌幾近湮沒,人們不再清楚經(jīng)典為何物時(shí)重新構(gòu)建了古典圖式和筆墨,“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是重新發(fā)現(xiàn)并厘清了已經(jīng)變得模糊的古典語(yǔ)言,從而推動(dòng)了一場(chǎng)文藝復(fù)興式的繪畫復(fù)古運(yùn)動(dòng),這在中國(guó)千年繪畫史上是絕無(wú)僅有的”。25章暉、范景中,《〈古典的復(fù)興〉序》,載《古典的復(fù)興: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第iv 頁(yè)。這種對(duì)經(jīng)典的重構(gòu)或許缺乏羅樾語(yǔ)境下的創(chuàng)新,但卻在畫史上具有文藝復(fù)興式的功績(jī)。26事實(shí)上,在“四王”創(chuàng)作的后期,特別是王時(shí)敏和王原祁祖孫,他們都在保存古典圖式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立了自己獨(dú)特的筆墨紋理(詳見下文關(guān)于王原祁畫作的討論以及注39 引文中有關(guān)王時(shí)敏繪畫的分析)。今天雖然去古已遠(yuǎn),但經(jīng)典畫作的真跡、高清印刷品或電子圖像均可通過各種渠道看到,古典的范式清晰無(wú)誤。如果有人可以忠實(shí)地復(fù)制古代大師的杰作,我們會(huì)贊賞其精湛的技藝,但它是否仍具有畫史上的重要性則要后人來(lái)評(píng)說(shuō)了。將畫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作品置于歷史環(huán)境中考察,不僅避免了觀看“四王”時(shí)的盲點(diǎn),還讓我們意識(shí)到,明中期的吳門畫家們何以沒有亦步亦趨地規(guī)模元人,而是融合前代的風(fēng)格,孕育出吳門新風(fēng)。蓋因其時(shí)去“元四家”未遠(yuǎn),真跡流傳尚伙,人們不難分清他們各自的風(fēng)格特征,重構(gòu)和復(fù)興的價(jià)值還沒有顯現(xiàn)。
(二)對(duì)筆墨理趣的再現(xiàn)
以上是筆墨紋理再現(xiàn)的第一種情況:精確復(fù)制古典筆墨。現(xiàn)在來(lái)看與之不同的另一種再現(xiàn):“復(fù)制”古典筆墨中的“理趣”。這樣的再現(xiàn)更關(guān)注古典筆墨紋理形成的理念和趣味,27事實(shí)上,這種“理趣”(理念和趣味)本身也是“世界三”中“客觀的知識(shí)”。而并不追求準(zhǔn)確復(fù)制筆墨舊貌。那么,何為文人畫中筆墨之理趣?
上文中我們談及印象派畫作上刻意留下的筆觸,這讓人聯(lián)想到文人繪畫中的筆墨。而討論文人畫的筆墨,不能不談及書法。書法是相對(duì)抽象的藝術(shù),除了字的間架結(jié)構(gòu),墨筆痕跡生成的運(yùn)動(dòng)感也是書法審美的要素。從運(yùn)動(dòng)再現(xiàn)的視角觀看書法,可以理解如下:書法被寫到紙絹上時(shí),筆畫記錄了筆鋒運(yùn)動(dòng)的瞬間,即它再現(xiàn)了墨筆的瞬間運(yùn)動(dòng),而這個(gè)記錄就是作品本身,這一點(diǎn)與攝影產(chǎn)生的瞬間圖像性質(zhì)類似。例如,圖8-1 的楷書“年”字(白謙慎教授書寫),其最后一筆“懸針豎”再現(xiàn)了行筆的三個(gè)動(dòng)作,頭部較粗的部分反映了起筆時(shí)的下按;豎直下行的墨跡記錄了毛筆移動(dòng)的途徑;而底部出尖的收尾則預(yù)示了筆鋒最終離開紙面。書寫結(jié)束時(shí),筆跡完整地再現(xiàn)了墨筆的瞬間運(yùn)動(dòng),作品也隨即完成。這種運(yùn)動(dòng)感在行、草書中更為明顯。圖8-2 的行書“百年”二字取自文徵明(1470—1559)《五岡圖》上的題詩(shī)。二字連寫,連接處從漸細(xì)到漸粗,宛若兩字之間的婀娜腰身,墨跡的粗細(xì)變化令人感到提按筆尖的動(dòng)作就在眼前;“百”字筆畫邊緣偶有墨色滲出,表明該處筆速較慢,最后懸針豎的收尾帶有飛白,顯示提筆時(shí)筆速增快。相比楷書,行書再現(xiàn)墨筆的運(yùn)動(dòng)時(shí)還讓觀眾領(lǐng)略到行筆的節(jié)奏和速度感,尤其是帶有飛白的筆畫。蘇軾(1037—1101)曾贊美文同(1018—1079)所作的飛白書,說(shuō)它“盡萬(wàn)物之態(tài)也。霏霏乎其若輕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zhǎng)風(fēng)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28[宋]蘇軾,《文與可飛白贊》,載《蘇軾文集》卷二十一,孔凡禮點(diǎn)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二冊(cè),第614 頁(yè)。文同的飛白作品今不可見,蘇軾的描述可藉董其昌所書來(lái)體會(huì),圖8-3 中“及之”二字取自思翁跋《五岡圖》,二字全用飛白,婉轉(zhuǎn)流暢,說(shuō)它“若游絲之縈柳絮”“若流水之舞荇帶”可謂恰當(dāng)。用大自然中“萬(wàn)物之態(tài)”比擬書法,在唐宋詩(shī)文中在在可見:29米芾對(duì)類似的比喻頗有微詞,他說(shuō)“歷觀前賢論書,征引迂遠(yuǎn),比況奇巧, 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是何等語(yǔ)?!或遣詞求工,去法逾遠(yuǎn),無(wú)益學(xué)者。”(米芾《海岳名言》)或許這樣的修辭無(wú)益學(xué)書法者,但從接下來(lái)的討論中我們會(huì)看到,它將自然物的動(dòng)態(tài)和抽象的書法筆跡聯(lián)系起來(lái),通過自然之美引發(fā)人們對(duì)書法筆跡的欣賞。

圖8-1 白謙慎教授楷書“年” (左)

圖8-2 文徵明行書“百年”(中)

圖8-3 董其昌飛白書“及之”(右)
“飄風(fēng)驟雨驚颯颯。”“時(shí)時(shí)只見龍蛇走。”
([唐]李白《草書歌行》)
“飛沙走石滿窮塞,萬(wàn)里颼颼西北風(fēng)。”
([唐]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
“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
([唐]孟郊《送草書獻(xiàn)上人歸廬山》)
“墨作龍蛇紙上飛。”
([宋]蘇轍《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龍蛇夭矯鎖黃塵。”
([宋]黃庭堅(jiān)《題蘇才翁草書壁后》)
“勢(shì)從天落銀河傾。”
([宋]陸游《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后》)
在《紋理再現(xiàn)(二)》中我們指出,自然物在生長(zhǎng)、形成或演化的過程中往往會(huì)留下痕跡,這些痕跡作為自然物本體的一部分,是觸發(fā)人們美感的因素之一。不言而喻,自然物運(yùn)動(dòng)的形態(tài)也是觸發(fā)人類美感的因素,詩(shī)人的比喻在運(yùn)動(dòng)的筆墨與生動(dòng)的自然之間建立了關(guān)聯(lián),藉以激發(fā)觀眾(讀者)的聯(lián)想,打通抽象的書法與“氣韻生動(dòng)”這個(gè)最高審美準(zhǔn)則之間的通道。30氣韻生動(dòng)與自然物的關(guān)系,請(qǐng)參見《紋理再現(xiàn)(二)》中的相關(guān)討論。
“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于八法通。”在了解到書法筆墨的運(yùn)動(dòng)感、特別是瞬間運(yùn)動(dòng)感關(guān)聯(lián)著自然之美后,我們或許對(duì)趙孟頫何以倡導(dǎo)繪畫須書法用筆有所領(lǐng)會(huì),他要構(gòu)建的文人繪畫理趣是將書法筆墨,尤其是它的動(dòng)感引入繪畫,喚醒“潛藏在那些靜穆的樹石形象中永恒而盎然的活力”。31書法用筆的動(dòng)感除了楷、行和草書,篆書也具有動(dòng)感,“篆書圓潤(rùn)微妙的彎曲與均衡似乎蘊(yùn)蓄著自然界原動(dòng)力徐緩幽深的搏動(dòng)”(方聞,《心印:中國(guó)書畫風(fēng)格與結(jié)構(gòu)分析研究》,李維琨譯,陜西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4年,第114 頁(yè))。關(guān)于書法與繪畫關(guān)系的更廣泛的分析和討論可參見方聞的相關(guān)著作。事實(shí)上,從景物到筆觸/筆墨,千百年來(lái)中外畫家們一直探索著如何在靜止的畫面上展現(xiàn)運(yùn)動(dòng)感,趙孟頫無(wú)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鵲華秋色》中將董源的披麻皴演繹為“典雅的楷書用筆”,而《水村圖》全用水墨,皴筆中夾帶著行草書中的飛白,加強(qiáng)了畫面的運(yùn)動(dòng)感。不過,這些具有書寫意味的山水作品仍然帶有實(shí)驗(yàn)的性質(zhì);32《水村圖》所采用的純水墨繪畫手法,也被認(rèn)為是“風(fēng)格極端主義”的體現(xiàn)(參見范景中、高昕丹編選,《風(fēng)格與觀念:高居翰中國(guó)繪畫史文集》,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11年,第107 頁(yè))。而我更愿意接受另一種說(shuō)法,“他(趙孟頫)那些以書法用筆探索的多種山水畫語(yǔ)匯,尚未自成一家。應(yīng)該承認(rèn)……他本人也未能創(chuàng)造出一種出色的山水風(fēng)格。趙孟頫去世30 多年之后,才出現(xiàn)了真正個(gè)人書法風(fēng)格的山水畫”(同注31,第115、116 頁(yè))。也就是說(shuō),在趙孟頫那里,山水畫的書法用筆還在探索和實(shí)驗(yàn)中,盡管《水村圖》的筆墨比起《鵲華秋色》已經(jīng)成熟了不少。到了學(xué)生黃公望(1269—1354)創(chuàng)作《富春山居圖》時(shí),同樣是披麻皴,卻已有較多的變化,墨的濃淡、筆的疾緩都比松雪齋要復(fù)雜,一方面它們更逼真地再現(xiàn)了山坡上的紋理,33可參見《紋理再現(xiàn)》中圖-8 和圖-9 及其相關(guān)文字。同時(shí)也比經(jīng)典筆墨更富含運(yùn)動(dòng)感,“在山水畫中創(chuàng)造出充滿活力的新形貌”;34方聞,《夏山圖:永恒的山水》,談廣晟譯,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年,第168 頁(yè)。松雪翁的外孫王蒙(1308—1385)將本來(lái)直筆中略呈弧形的披麻皴改造成短促且彎曲的“牛毛皴”,皴筆面貌雖與松雪和大癡明顯不同,動(dòng)感卻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了。到了明代中期,吳門諸家融合各種皴法,推陳出新,發(fā)展出運(yùn)動(dòng)感更為豐富的筆墨紋理。
總之,盡管不同時(shí)代的不同畫家其筆墨紋理之形態(tài)各異,他們雖然并未精準(zhǔn)復(fù)制古典筆墨,但都不約而同地再現(xiàn)了筆墨的運(yùn)動(dòng),在新穎的筆墨紋理中呈現(xiàn)出古典筆墨的理趣,我們將此類繪畫歸為筆墨紋理的第二種再現(xiàn),也許可以將其比作自然再現(xiàn)中注重“神似”的“寫意”畫(在此再次強(qiáng)調(diào),“寫意”是指寫自然景物的客觀之意);與之相對(duì),紋理圖樣的逼真模仿可類比自然再現(xiàn)中注重“形似”的“寫實(shí)”畫。而不論前者還是后者,如能在經(jīng)典之上再現(xiàn)筆墨的運(yùn)動(dòng)感,則距離張庚所云筆墨之“天機(jī)勃露”相去不遠(yuǎn)矣。
我們?cè)谙鹿?jié)中討論兩幅繪于17世紀(jì)前后的畫作,一方面看看畫家是如何在脫離自然再現(xiàn)的情況下讓筆墨紋理仍然生動(dòng),同時(shí)也藉此展示古典筆墨的理趣是如何被再現(xiàn)的。
三 理趣再現(xiàn):從“皴筆重疊”到“熨干再畫”
《婉孌草堂圖》(圖9)是董其昌43 歲時(shí)為好友陳繼儒(1558—1639)所作,畫中實(shí)驗(yàn)了具有創(chuàng)新手法的“直皴”,讓畫面的運(yùn)動(dòng)感洋溢楮墨。石守謙先生分析指出,“由于那些甚有清晰運(yùn)動(dòng)方向的直皴作用,不僅使土坡的各面顯得含有飽滿的動(dòng)態(tài),也使得整個(gè)坡面在各單元的連續(xù)之中產(chǎn)生斜向的充沛動(dòng)勢(shì)”,“崖壁卻因(具有‘運(yùn)動(dòng)方向’的)直皴的作用,而產(chǎn)生似乎隨時(shí)要釋放而出的巨大動(dòng)能”。此處的“運(yùn)動(dòng)方向”和“斜向”正是前文言及的生成畫面動(dòng)感的元素。不僅在山石上實(shí)驗(yàn)了直皴,思翁還將它們用于樹干上,“由于那種似其山石皴擦的直筆的作用,更富有蒼厚的動(dòng)態(tài)力量,使得幾棵看似安靜的直挺樹干,本身即產(chǎn)生其后方作扭曲姿態(tài)之小樹所不能比擬的內(nèi)斂動(dòng)態(tài)”。35樹與山體使用同樣的皴法,我們?cè)谖尼缑鞯摹段鍖鶊D》中也看到了,參見注1 引文中的相關(guān)討論。總之,董其昌“自信掌握了理想之‘勢(shì)’的直皴,也帶給《婉孌草堂圖》中諸多取自古人之形象更豐富的活躍生氣”。石先生的研究闡明了三個(gè)重點(diǎn):一、董其昌采用了源自古典繪畫中的直皴;二、對(duì)直皴的改進(jìn)營(yíng)造出畫面的整體動(dòng)感;三、畫中山水之圖式與婉孌草堂的實(shí)景之間無(wú)直接關(guān)聯(lián)。三點(diǎn)歸結(jié)所得的結(jié)論是,《婉孌草堂圖》的生動(dòng)畫面并非源于對(duì)自然景物的再現(xiàn),而是基于對(duì)古典畫法——“直皴”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36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教授曾撰文對(duì)石守謙先生的“直皴”分析提出異議。他認(rèn)為《婉孌草堂圖》山體上的皴法受到西洋版畫的影響,特別是畫面右上方云邊的山體上那些交叉的皴筆,班宗華推斷那是董其昌模仿西洋繪畫中的交叉排線光影法[Crosshatching]之結(jié)果。不過從中國(guó)山水畫古典圖式的視角觀看,那些“橫線”更像是米家云山上的橫點(diǎn),特別是在整幅畫中,它們僅出現(xiàn)在云朵附近。董其昌拉長(zhǎng)了那些橫點(diǎn),因此看起來(lái)似乎成了橫向的短線。類似的畫法還見于臺(tái)北故宮所藏《奇峰白云圖》,董其昌在這幅仿米家山的立軸上也在縱向的皴筆上施以拉長(zhǎng)的橫點(diǎn),其畫面效果和《婉孌草堂圖》頗為相像。事實(shí)上交叉排線光影法中的線條主要是為了在版畫(或素描)中表現(xiàn)陰影深淺的程度,不論是木版畫的刀刻還是銅版畫的蝕刻,其線條都粗細(xì)一致,間隔均勻,沒有變化,亦無(wú)層次感,而線條之間近乎機(jī)械的交叉更凸顯了人為的刻畫(圖10-1)。自然山體不會(huì)產(chǎn)生那樣的紋理。難以想像,一味追求筆墨精妙的董其昌會(huì)借鑒如此機(jī)械刻板的方式來(lái)呈現(xiàn)筆墨自身的紋理。參見白謙慎編,《行到水窮處:班宗華畫史論集》,劉晞儀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第332—350 頁(yè)。

圖9 [明]董其昌,《婉孌草堂圖》,臺(tái)北私人藏

圖10-1 意大利畫家Giovanni Francesco Grimaldi 創(chuàng)作于17世紀(jì)上半葉的版畫(紐約大都會(huì)博物館藏)中山坡局部

圖10-2 董其昌《婉孌草堂圖》山體局部紋理
事實(shí)上,在采用直皴使整幅畫面釋放出“巨大動(dòng)能”的同時(shí),思翁還在處理直皴的筆墨上做了創(chuàng)新,制作出如石先生所說(shuō)的“皴筆重疊的現(xiàn)象”,這種新手法讓筆墨紋理本身更富于運(yùn)動(dòng)感。現(xiàn)在我們來(lái)觀察畫中山體局部的細(xì)節(jié),圖10-2 中山石上的紋理呈現(xiàn)出半透明的特質(zhì),上一層墨跡壓過下層墨跡之后,下層墨跡仍然依稀可見,這就是用“皴筆重疊”繪出的效果。雖然這類畫法在前人的畫作中也偶爾出現(xiàn),但思翁在此是有意為之,并實(shí)施于整幅畫作中,效果顯著。自然界中,不論是樹皮的皴裂、山坡上的植被,或是山石的風(fēng)化,其紋理的形成過程是新紋理取代或覆蓋舊紋理,致使舊紋理不復(fù)可見。例如山石的風(fēng)化,隨著大自然的持續(xù)侵蝕,較早的風(fēng)化紋理層會(huì)被后來(lái)形成者所取代或掩蓋,新舊紋理層之間不會(huì)有透明的重疊。在《紋理再現(xiàn)(二)》中,我們談及山石的風(fēng)化紋理中蘊(yùn)含著大自然的動(dòng)感,由于自然紋理(或傳統(tǒng)的皴法)不具備透明性,觀眾感受到的是“單層的動(dòng)感”。而“皴筆重疊”構(gòu)成了一定的透明度,這使得紙面上的筆痕墨跡產(chǎn)生了“立體的動(dòng)感”,因而記錄了更加完整的創(chuàng)作過程、再現(xiàn)了更加豐富的瞬間運(yùn)動(dòng),讓脫離真山水的筆墨紋理呈現(xiàn)出超出自然的生動(dòng)效果。
“皴筆重疊”的技法在董其昌晚年的繪畫中愈顯成熟和徹底。《江山秋霽》卷是他70 歲左右仿黃公望的作品,我們?cè)噷⑵渑c大癡作品中的筆墨做一比較(圖11)。先看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wú)用師卷)中的皴筆,皴法基本是單層的,偶有重疊也并非刻意(全卷均如此),它們逼真地模擬了山坡上的自然紋理。37見注1 引文中的相關(guān)分析和討論。再看《江山秋霽》的皴法,長(zhǎng)條的披麻皴不時(shí)夾帶著飛白,和圖8-3 中書寫時(shí)的用筆施墨幾乎相同,是典型的書法用筆。卷中坡岸、樹木乃大癡圖式,紋理的透明度和層次感比《婉孌草堂圖》更為明顯,“皴筆重疊”的技法此時(shí)已進(jìn)入爐火純青的境界。較之大癡,思翁的重疊皴法凸顯了筆跡透明的層次,增強(qiáng)了畫面的運(yùn)動(dòng)感,卻于再現(xiàn)真山方面去大癡遠(yuǎn)矣,然其生動(dòng)之處真可謂“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思翁對(duì)筆墨獨(dú)立性的意識(shí)和實(shí)踐已然高出古人,在《江山秋霽》的題跋中他情不自禁地高呼:“恨古人不見我也!”

圖11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wú)用師卷(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局部(上)和董其昌《江山秋霽》(美國(guó)克利夫蘭博物館)局部(下)的筆墨比較
值得指出的是,董其昌雖然認(rèn)為畫家在掌握了古典技法之后“進(jìn)而當(dāng)以天地為師”,不過他自己并沒有“以天地為師”去追求形似,他非但沒用筆墨模擬、匹配自然,反而讓自然淪為陪襯筆墨的形模。他“以天地為師”是學(xué)習(xí)天地的創(chuàng)造力,用“皴法重疊”演繹古典筆墨,畫出超越真山水的透明紋理,令觀眾的注意力轉(zhuǎn)移到充滿動(dòng)感的筆墨本身,從而感受到半抽象的山水釋放出的彰彰在目之躍動(dòng)感。陳繼儒曾這樣評(píng)論董其昌臨仿的米家山:“米家畫在似山非山之間,玄宰畫在似米非米之間。”38董其昌自題《九峰春霽圖》手卷,跋文載《啟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年,第215 頁(yè)。“似山非山”可視作對(duì)自然紋理的再現(xiàn),“似米非米”則是對(duì)筆墨紋理的再現(xiàn)。如此看來(lái),思翁不僅不以天地為師追求形似,即便臨古亦不求形似,而是復(fù)現(xiàn)古人的理趣,這正是我們所說(shuō)的第二種筆墨紋理的再現(xiàn)。
書法筆墨用于繪畫幾乎被董其昌實(shí)踐到極致,他的學(xué)生王時(shí)敏(1592——1680)和王鑒(1609—1677)超越老師的地方更多是在古典圖式的重構(gòu)上,39參見章暉,《重構(gòu)經(jīng)典:王時(shí)敏對(duì)董其昌的超越》,載《新美術(shù)》2022年第5 期。而將筆墨紋理再現(xiàn)推向新高度的是王時(shí)敏的長(zhǎng)孫王原祁(1642—1715)。雖然依舊留心大自然的“陰陽(yáng)顯晦,朝光暮靄,巒容樹色”,40同注24,葉四。并在自然紋理的再現(xiàn)上繼續(xù)取得成就,41王原祁用云的分形結(jié)構(gòu)和紋理繪制山峰,雖然采用了紋理置換的手法,但置換所用的紋理仍然源于自然(云),仍可看作是對(duì)自然紋理的再現(xiàn)。參見楊崇和,《王原祁繪畫中的幾何學(xué)問題》,載《新美術(shù)》2015年第3 期。不過王原祁彪炳畫史的貢獻(xiàn)則是筆墨上的創(chuàng)新。張庚在《國(guó)朝畫征錄》中記錄了王原祁為友人“克大”作畫的情景:
折簡(jiǎn)招克大過從曰:“子其看余點(diǎn)染。”乃展紙審顧良久,以淡墨略分輪廓,既而稍辨林壑之概,次立峰石層折、樹木株干,每舉一筆,必審顧反覆,而日已夕矣。次日復(fù)招過第,取前卷少加皴擦,即用淡赭入藤黃少許,渲染山石,以一小熨斗貯微火熨之干,再以墨筆干擦石骨,疏點(diǎn)木葉,而山林屋宇、橋渡溪沙了然矣。然后以墨綠水疏疏緩緩渲出陰陽(yáng)向背,復(fù)如前熨之干,再勾再勒,再染再點(diǎn),自淡及濃,自疏而密,半閱月而成。發(fā)端混侖,逐漸破碎,收拾破碎,復(fù)還混侖。流灝氣,粉虛空,無(wú)一筆茍下,故消磨多日耳。古人“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洵非夸語(yǔ)也。42[清]張庚,《國(guó)朝畫征錄》卷下,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9年,第85 頁(yè)。
我們知道,書法講究筆畫單純簡(jiǎn)潔,線條一筆而就,披麻皴就頗能體現(xiàn)這種書寫特性。即使董其昌“皴法重疊”中有筆畫的重復(fù),它們?nèi)匀皇且还P而就的披麻皴重疊,并未逾越單純簡(jiǎn)潔的書法用筆原則。反觀王原祁作畫,卻是“以墨綠水疏疏緩緩渲出陰陽(yáng)向背,復(fù)如前熨之干,再勾再勒,再染再點(diǎn)”,其中反復(fù)“熨之干”是關(guān)鍵步驟。這種“熨再畫”的方法可以按“畫—熨—再畫—再熨”的次序記錄下筆墨落在紙面的每一次過程,43這種畫法應(yīng)接近“積墨法”,但未見積墨法有用熨斗熨干的記載。為強(qiáng)調(diào)熨干的步驟,特將王原祁的這種畫法稱之為“熨干再畫”。避免了前一層墨色未干時(shí),新的渲染皴擦與之相互滲透、混合。因此,筆墨的層次更加清晰可見、豐富鮮活,令畫中的山石煥發(fā)出“妙如云氣騰溢”的動(dòng)感。44參見[清]秦祖詠,《繪事津梁》,載于玉安編輯,《中國(guó)歷代美術(shù)典籍匯編》,天津古籍出版社,第16 冊(cè),1997年。然而,這種費(fèi)時(shí)耗力的“熨干再畫”方法顯然與書法用筆的簡(jiǎn)潔原則背道而馳,但實(shí)際上,他比董其昌又進(jìn)了一步,不僅擺脫了再現(xiàn)自然的羈絆,還突破了自元代以降的書法用筆成規(guī),創(chuàng)造出文人畫審美的新境界。下面我們來(lái)看看“熨干再畫”會(huì)產(chǎn)生怎樣的視覺效果。
圖12 是王原祁六十三歲時(shí)為友人陸毅(1654—1726)45陸毅生年據(jù)其子陸履謙等撰《陸毅行狀節(jié)略》:“王父之歿,府君才九歲。”又據(jù)黃與堅(jiān)(1620—1701)撰陸毅父母合葬墓志銘,知毅父榮卒于康熙元年(1662)9月,時(shí)毅九歲,則毅生于順治十一年(1654)。陸毅卒年據(jù)民國(guó)《太倉(cāng)州志》(卷二十,人物四,葉十七)載:“卒年七十三。”時(shí)在雍正四年(1726)。所繪設(shè)色立軸《春崦翠靄》,陸毅與王原祁同鄉(xiāng)且同朝為官,故此幅乃精心之作,非同一般應(yīng)酬。尺幅超過七平尺,在王原祁的作品中堪稱大幅。構(gòu)圖藉鑒了黃公望《天池石壁圖》,但畫面復(fù)雜的色墨融合則超過古人。在有色彩的山石上用墨,宋畫中已可見到,不過墨筆的使用通常收斂且單純。趙孟頫在《鵲華秋色》青色的山體上布滿墨筆披麻皴,乃開風(fēng)氣之先。此后吳門諸家、董其昌均有類似實(shí)踐,王時(shí)敏后來(lái)居上,其色墨交融的畫法勝過前賢,王原祁繼武乃祖將之推進(jìn)到更高層次。圖13 是王原祁《春崦翠靄》山體上的皴擦細(xì)部,其筆墨的變化比之董其昌那種雖然重疊但單純的書法用筆要復(fù)雜很多(圖10):筆跡不但有輕重緩急,墨色亦呈現(xiàn)出干濕濃淡的變化,披麻皴只有寥寥幾筆,成為點(diǎn)綴。墨筆混合在山石的色彩中達(dá)到了色墨融合,而又層次分明,那些斑駁雜沓、墨色交融的紋理正是麓臺(tái)所追求的“墨中有色,色中有墨”的境界。應(yīng)當(dāng)指出,雖然王原祁在形式上突破了書法用筆,但其追求仍然是筆墨瞬間運(yùn)動(dòng)的再現(xiàn),因此在理趣上,“熨干再畫”和書法用筆的主張一脈相承。鑒賞家王季遷(1906—2003)曾用音樂比喻王原祁的繪畫,說(shuō)他“比元代畫家更進(jìn)了一步”,“元代彈的是二重奏、三重奏,王原祁則像個(gè)小的室內(nèi)交響樂,聲音豐富得多”。46徐小虎、王季遷,《畫語(yǔ)錄:王季遷教你看懂中國(guó)書畫》,臺(tái)北典藏藝術(shù)家庭,2013年,第216—219 頁(yè)。17世紀(jì)由董其昌發(fā)起的那場(chǎng)筆墨獨(dú)立于山水的革命,被王原祁推向高峰并在他的筆下畫上了句號(hào)。

圖12 [清]王原祁,《春崦翠靄》,縱133 厘米,橫61.5 厘米,上海私人藏(左)

圖13 王原祁《春崦翠靄》局部(右)
從本節(jié)的兩幅作品中我們看到,董其昌的“皴法重疊”和王原祁的“熨干再畫”既未用于再現(xiàn)自然紋理,也沒有單純地重復(fù)古典筆墨紋理的舊貌,而是在再現(xiàn)筆墨運(yùn)動(dòng)感方面“復(fù)制”了古人的理趣。它們都是上文討論的第二種筆墨紋理再現(xiàn)的佳例。
四 余論
紋理再現(xiàn)的前兩篇文章主要討論了畫家對(duì)自然紋理的再現(xiàn),并嘗試建立一個(gè)評(píng)測(cè)再現(xiàn)自然紋理的客觀標(biāo)準(zhǔn)。本文借用“運(yùn)動(dòng)再現(xiàn)”的觀念探討了山水畫的筆墨紋理再現(xiàn)。作為“世界三”中“客觀的知識(shí)”,筆墨紋理的再現(xiàn)也應(yīng)有其評(píng)判的“客觀”標(biāo)準(zhǔn)。設(shè)置這樣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本文未打算展開討論,僅借余論談一點(diǎn)初步想法。
由于沒有自然景物作為再現(xiàn)的參照,我們需要建立一個(gè)由經(jīng)典作品構(gòu)成的參照系以資比對(duì),類似書法中的臨書范本。有了參照系,筆墨紋理再現(xiàn)的優(yōu)劣評(píng)判才有意義、才能達(dá)成共識(shí),而不至言人人殊。對(duì)經(jīng)典作品的選擇需要根據(jù)繪畫自身的性質(zhì)劃出邊界,有些經(jīng)典雖名聲顯赫,卻未必適合納入這個(gè)參照系。例如米芾的《珊瑚筆架圖》,嚴(yán)格地說(shuō),這是一張示意圖,誠(chéng)非繪畫,能逼真臨摹此圖的人與其說(shuō)是畫家不如說(shuō)是書家。就筆墨紋理的第一種再現(xiàn)而言,評(píng)判其優(yōu)劣的標(biāo)準(zhǔn)似乎直截了當(dāng),那就是摹本比之參照系中的經(jīng)典原作要“形神俱似”。至于第二種再現(xiàn),即筆墨紋理之理趣再現(xiàn),情況會(huì)比較復(fù)雜,我們?cè)谏衔闹幸雅e例說(shuō)明,這是董其昌提倡的那種“脫去拘束”“神會(huì)意得”的臨古。47見[清]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十二中《明董香光臨古卷》落款。對(duì)第二種再現(xiàn)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究竟如何建立,還有待研究,不過陳繼儒的“似米非米”論似乎給了我們一些啟示。當(dāng)然,不論這標(biāo)準(zhǔn)如何建立,它最終要能衡量作品是否“氣韻生動(dòng)”,這條中國(guó)繪畫審美的最高準(zhǔn)則。
從視覺紋理再現(xiàn)的觀點(diǎn)探討10 至17世紀(jì)中國(guó)山水畫的發(fā)展至此大致告一段落。48紋理再現(xiàn)的三篇文章中主要討論了10 至17世紀(jì)的山水畫,沒有涉及18世紀(jì)之后的畫家和作品,在此簡(jiǎn)述如下:雖然其時(shí)山水畫的主流延續(xù)了“四王”建立的正統(tǒng)畫派,但有成就的畫家仍然在筆墨紋理的再現(xiàn)上顯現(xiàn)出個(gè)性化的特點(diǎn)。同時(shí)乾隆朝的詞臣畫家們“以筆墨合天地”,用精致的筆墨再現(xiàn)實(shí)景山水,(參見注18)讓“世界三”中的紋理重回自然,正可謂“空山獨(dú)立始大悟,世間無(wú)物非草書”(翁方綱詩(shī)句)。19世紀(jì),以張崟(1761—1829)、錢杜(1764—1844)為主的一批江南畫家厭倦了董其昌的“筆墨少含蓄”和王原祁的“有筆墨而無(wú)丘壑”(錢杜語(yǔ)),重新回歸吳門追隨文沈,發(fā)展出丘壑分明,筆墨精雅的頗具裝飾趣味的畫風(fēng),他們的努力也可視為是對(duì)明代吳門畫派的復(fù)興;同時(shí),追隨正統(tǒng)的畫家如王學(xué)浩(1754—1832)、戴熙(1801—1860)等在筆墨紋理的再現(xiàn)上推陳出新,各有建樹。抽象繪畫在20世紀(jì)興起,趙無(wú)極(1921—2013)將中國(guó)山水畫筆墨紋理的局部圖像放大,改造后用油彩繪在畫布上,產(chǎn)生了前所未見的、基于運(yùn)動(dòng)瞬間的抽象視覺效果(圖14)。進(jìn)入21世紀(jì),紋理再現(xiàn)的創(chuàng)新并未停止,畫家張洪[Arnold Chang]與攝影師秋麥[Michael Cherney]合作,創(chuàng)造出筆墨紋理與自然紋理融為一體的“混合山水”(圖15);泰祥洲根據(jù)《紋理再現(xiàn)》一文中的討論,巧妙地將靈璧石紋理植入董其昌《青弁山圖》中,揭示古人以賞石“造山”之秘密(圖16)。在書法方面,王冬齡的“亂書”讓書法的筆墨徹底從漢字的結(jié)體中解放出來(lái),全面展現(xiàn)筆鋒瞬間運(yùn)動(dòng)的節(jié)奏感和韻律感,而書寫過程最終呈現(xiàn)出的筆墨紋理構(gòu)成了一幅具有強(qiáng)烈運(yùn)動(dòng)感的抽象畫面(圖17),令人想起波洛克的“滴畫”。它或許可以化解“超越再現(xiàn)”從畫面之外分析繪畫時(shí)所遇到的一些困境:一、無(wú)法看見宋元繪畫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宋元間的畫風(fēng)轉(zhuǎn)變被視為一種突變;二、無(wú)法察覺元代以降的繪畫風(fēng)格在筆墨上的演變,從而導(dǎo)致了元代以后畫史終結(jié)的結(jié)論;三、難以評(píng)判繪畫質(zhì)量的優(yōu)劣,當(dāng)“動(dòng)聽的言辭與蹩腳的繪畫之間明顯地存在著令人痛苦的差距”時(shí),49矛盾、尷尬的局面就會(huì)發(fā)生。需要注意的是,一種觀點(diǎn)只能提供觀看繪畫的一個(gè)特定視角,好比畫家關(guān)注的是畫中的構(gòu)圖和筆墨,鑒定家和收藏家則更在乎畫的真?zhèn)危牧蠈W(xué)者感興趣的是紙絹的結(jié)構(gòu)、色墨的成分,而拍賣公司和畫廊卻在考慮給它定價(jià)等等。因此,我們也再次強(qiáng)調(diào):“紋理再現(xiàn)”的觀點(diǎn)并非要取代或否定“超越再現(xiàn)”,而是為觀眾提供另一個(gè)視角,讓中國(guó)山水畫的觀看更為完整和有趣。

圖14 趙無(wú)極,《28.02.67》,香港佳士得亞洲20世紀(jì)和當(dāng)代藝術(shù)(夜場(chǎng)),2018年5月26日

圖15 張洪、秋麥合作《仿蕭云從》(陳霄女史收藏)局部,圖中深色方框內(nèi)是秋麥所攝真山山體的照片,方框外是張洪用墨筆繪制的山體。自然紋理和筆墨紋理在此作品中融合如一

圖16 泰祥洲,《紋理變形之三:董其昌青弁山圖》(畫家本人提供)
49 注32 中所引高居翰著作,第124、125 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