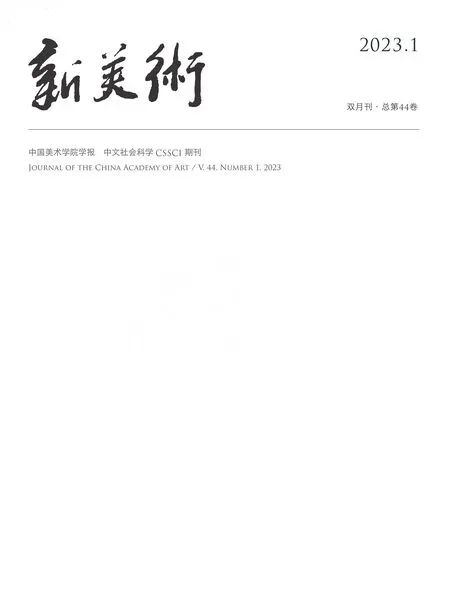陳之佛留日時期相關史料考* 以新見《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為中心
譚小飛
陳之佛是中國近代以來重要的美術家和美術教育家,也是中國現代設計的拓荒者之一。陳之佛早年在東京美術學校的留學經歷,構成了中國現代設計史、設計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歷史節點。陳之佛一生著述豐富,在圖案學、美術學多個領域獲得令人矚目的成就。20世紀50年代始,關于陳之佛的畫集、圖案作品集開始陸續出版。80年代以來,大量美術、設計學人開始撰文介紹陳之佛的生平活動、思想和學術成就。國內除大量文章與文集之外,還有多本專著陸續出版。2020年《陳之佛全集》的出版,更是在學界引起廣泛反響。陳之佛的早期美術活動主要集中在圖案領域,美國學者朱莉婭·安德魯斯[Julia F.Andrews]提道:“作為中國首位職業平面設計師,陳之佛的重要性尤為突出。”1Andrews,Julia F.and Kuiyi Shen.A Century in Crisis:Modernity and Tradition in the Art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Solo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1998,p.185.可見,對于陳之佛的重要性,中外學者基本形成一致共識。
一 起因
近年來,關于陳之佛的研究愈發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各種論文、專著、展覽、文集頻出。筆者在查閱陳之佛材料時,發現以下幾個疑點。
第一點:關于陳之佛留學時間的起止。在吉田千鶴子《東京美術學校的外國留學生》、陳日紅的《對〈陳之佛年表〉中留日學習圖案經歷的相關考證》、李華強的《設計、文化與現代性:陳之佛設計實踐研究(1918—1937)》等新近成果中已經形成共識,即陳之佛于1920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1925年畢業。但在《陳之佛全集》之中,編撰者依據所掌握的材料,考訂為“1919年至1925年”。可見,關于陳之佛在東京美術學校的入學時間,仍存有爭議。
關于陳之佛的具體赴日時間,現有成果基本沿用了《陳之佛年表》中的表述方式,即“1918年考取留日官費生,東渡日本。1919年入東京美術學校工藝圖案科……”2陳修范、李有光,《陳之佛年表》,載《美術與設計》1982年第1 期,第19 頁。不難看出,由于缺乏原始檔案,這部分材料需要詳細考證。
第二點:陳之佛留日期間的費用形式。已有成果同樣沿用了《陳之佛年表》中的“官費”說法,同樣缺乏史料佐證。并且,陳之佛的官費與同時期其他留學生的官費有何異同,也未能加以說明。
第三點:陳之佛留日期間的住所。住所是陳之佛能夠完成學業順利回國的重要前提。陳之佛子女編寫的《陳之佛年表》中提到,陳之佛留日期間“一直住在神田區猿樂町二·一清壽館一號房間”,這部分材料也是經不住推敲的。
第四點:陳之佛的歸國時間。關于陳之佛的回國時間,現有成果主要有1923年4月、1924年、1925年3月、1925年7月四種說法。考察發現,這些觀點無論在史料可信度上,還是在解釋層面上,都顯得不可靠。
早有研究者發現,藏于浙江省圖書館的兩本《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分別為1923年和1928年版(其中,1928年陳之佛早已畢業回國,該版對本話題不具有討論價值)。并且,《中國近代教育文獻叢刊 留學教育卷04》3田正平主編,《中國近代教育文件叢刊 留學教育卷04》,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年。還對1923年版進行了影印重刊。遺憾的是,目前尚未有研究者發現該文本對于陳之佛留學史料的研究價值。
筆者于2020年研究陳之佛檔案時發現,浙江省檔案館網站“數字檔案”查詢欄目有“留日學生同學錄”專題,因系統錄入信息中有明顯錯誤,筆者進一步考察該檔案的原始來源,查找到浙江省檔案館館藏1920年《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1921年《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會報》、1922年《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1924年《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四本重要史料。并且,在該館《浙江大學校友錄》中還發現了分別以“陳杰”和“陳之佛”名字著錄的浙江大學畢業生和教員校友身份。此外,筆者自藏一本1917年版《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在此基礎上,結合浙江圖書館藏1923年版《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筆者發現已有成果有語焉不詳、甚至訛誤之處,本文通過對這部分原始檔案的梳理,結合民國時期公開發行的報紙、雜志等材料,試圖修正陳之佛留日期間的相關史料。
二 陳之佛的赴日時間
謝海燕先生在《陳之佛的生平及花鳥畫藝術:〈陳之佛花鳥畫集〉前言》一文中,最早提到陳之佛的赴日時間為“一九一八年,陳之佛考取留日官費生。十月去日本。次年四月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工藝圖案科”。4謝海燕,《陳之佛的生平及花鳥畫藝術:〈陳之佛花鳥畫集〉前言》,載《美術與設計》1979年第2 期,第4 頁。其后的成果在表述上有些許差異,但大體沒有超出這個范疇。
《陳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中刊出一張陳之佛在1947年受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委員兼美術組專員時所填的履歷表手稿 。5陳修范、李有光,《陳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8—19 頁。履歷表有多處涂改痕跡,確切地說應該是一張草稿。在履歷表“教育經歷”一欄中,“1919—1925日本文省部東京美術學校”一行的年份和校名有多處涂改,涂改之前的“1920—1926”依稀可辨。可見,盡管出現了年份上的模糊,但陳之佛對于自己在日本留學的六年時長是肯定的。
盡管履歷表為陳之佛親手所填,但并不意味著這個時間就沒有疑問。1919年,美術家、教育家劉海粟曾赴日考察美術現狀,據劉海粟的專文《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記錄,東京美術學校圖案科的學制為預備科(一年)加四年本科。6劉海粟,《對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商務印書館,1925年,第109—113 頁。可見,陳之佛手填留學時間與東京美術學校的學制有明顯沖突。考慮到陳之佛本人是留學活動的親歷者,結合吉田千鶴子與陳日紅的研究成果,不難看出,1919年應該是陳之佛在日本的考前準備期,1920至1925年才是東京美術學校的學習期。陳之佛在日本的六年經歷,是符合當時一般留日學生基本時需的。
1920年3月刊印的《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中,有一條陳之佛的信息介紹:
姓名:陳杰;字:之偉;年齡:25;籍貫;余姚;費別:官;學校:西洋畫圖案;科級:……;現住所:神田猿樂町二ノ一清壽館;國內通信處:余姚滸山。7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會員姓名錄》,《浙江留學生同鄉錄》(內部資料),浙江省檔案館藏(編號:學校-474),1920年,第21 頁。
需要注意的是,陳之佛的信息中,“學校”一欄為“西洋畫圖案”,參考同期《同鄉錄》內周天初(1919年考入東京美術學校)的信息,該欄則標注“東京美術學校”。8同注7,第14 頁。進一步查閱1921年版、1922年版和1923年版《同鄉錄》,陳之佛的學校信息均為“東京美術學校”。可見,直到1920年3月之前,陳之佛都尚在預備考學階段。
《陳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對于陳之佛在東京美術學校留學時間的界定,正是依據“陳之佛手填履歷表,及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寄來的檔案”,考訂為1919年至1925年。9同注5,第17 頁。至于東京美術學校所寄檔案,作者并沒有在文中公布。但在吉田千鶴子依據東京美術學校檔案所撰寫的《東京美術學校的外國學生》文中,認為陳之佛是“大正九年(1920)4月7日臨時編入圖案選科第一部第一年級,同年9月11日編入第一年級。大正十四年(1925)3月畢業”。10[日]吉田千鶴子,《東京美術學校的外國學生》,韓玉志、李青唐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62 頁。陳日紅依據東京美術學校原始檔案所撰的《對〈陳之佛年表〉中留日學習圖案經歷的相關考證》一文,同樣認為是陳之佛的留學時間是1920年4月7日至1925年3月30日,歷時五年。吉田千鶴子與陳日紅在文中詳細列出了原始檔案的來源及條目原文,結合《同鄉錄》中陳之佛的信息記錄,顯然二人的時間斷定更可靠。
既然陳之佛為1920年4月進入東京美術學校,那么他有無可能如謝海燕所說,1918年考取留日官費生,十月去日本?查閱《教育周報》(杭州)顯示,1917、1918、1919 三年,由于浙江省留日官費生尚有余額可備選補,浙江省教育廳均有發布留日《考試留日學生》相關公文,并舉行過專門考試。這表明,陳之佛有機會通過該途徑考取官費留日,但1918年1月30日《教育公報》曾發布一則教育部令《指令留日學生監督新生預備限一年應照準文》:
據呈已悉,所請新補官費生預備考入高等學校期間,概以一年為限,一節尚屬可行,應即照準此令。11中華民國教育部,《公牘·指令留日學生監督新生預備限一年應照準文》,載《教育報》1918年第2 期,第40 頁。
原文由留日學生監督處呈報,意在將原預備期的一年和一年半兩種情形,齊整劃為一年,即:春季抵達日本者以次年春季為限,秋季抵達日本者以次年秋季為限,否則即行停止官費。
倘若陳之佛1918年赴日,那么次年(1919年)他將面臨被官費除名的現實。因而陳之佛應該是在1919年赴日,次年(1920年4月)考入東京美術學校,這又可與陳之佛1947年所填履歷表上的“1919—1925”六年留日時間相互印證。
三 陳之佛留日的費用形式
由于陳之佛的突出貢獻,他的留學經歷構成了中國近現代設計史、圖案教育史上的重要節點,至于他留學的費用形式問題本已不那么重要,但考慮到中國圖案教育史的完整性及陳之佛的重要性,還是有必要作詳細的考訂。
最早提到陳之佛官費留日的,還是前文提到的《陳之佛的生平及花鳥畫藝術:〈陳之佛花鳥畫集〉前言》一文,其后,陳之佛家屬的《陳之佛年表》《陳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均采用這一表述;吉田千鶴子從東京美術學校的原始檔案中考察的結果同樣為官費;筆者在查閱資料過程中發現, 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后,《申報》為統計留日學生受災情況,刊載了《留日學生最近情形之調查》系列報道,其中有“姓名:陳杰(陳之佛);學校:美術;費:官;受災情形:無恙 ”。12《留日學生最近情形之調查》,載《申報》,1923年10月10日第十四版,第四張。可見,陳之佛官費留日無疑。
吉田千鶴子的考察結果,僅能表明陳之佛在東京美術學校期間享受官費。根據謝海燕、陳修范、李有光的觀點,陳之佛是帶著官費赴日的,也就是說,陳之佛在預備期起就享受官費待遇。考察《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極少發現留日學生在預備期就享受官費待遇。
陳之佛的友人章克標,也曾于1918年赴日留學,《浙江公報》1918年11月11日發布的指令中,有令浙江省教育廳核準章克標自費留學的材料。13指令原文為:“浙江省長公署指令第10661 號,令教育廳:呈一件呈送海寧吳敩、章克標等,自費留學日本填送留學書表請核準給文由”。參見:《浙江教育公報》1918年11月11日第2381 號,第5 頁。章克標在《九十自述》一書中回憶了當時留日學生“獵取官費”的一般做法,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自由往來,出入國境無需簽證、護照,只需買到船票。1918年9月,章克標與友人同赴東京,先入預備學校,只需準備一年的學資。次年春季章克標考入東京高師,從此開始享受官費待遇。14章克標,《九十自述》,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第32—38 頁。章克標的經歷可與《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相印證,《同鄉錄》中刊錄有大量尚在預備期的會員信息,這部分留學生均為自費。如1920年浙江諸暨籍留日學生何時慧、何乃賢二人在預備期均為自費,15同注7,第20 頁。考入東京高師后,費用也變為“公”。16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會員錄》,《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內部資料),浙江省圖書館藏,1923年,第13—14 頁。這種方式是當時官費生的常規途徑。
1918年4月21日《教育周報》發布了《留日官費學生一覽》,據留日學生監督處報告給浙江省教育廳的名單,共有一百零六名留日學生獲得浙江省1918年官費資格。17浙江省教育廳,《留日官費學生一覽》,載《教育周報》1918年第199 期,第16 頁。這部分留學生需要自備預備期費用,被日本高等學校錄取后,可通過留日學生監督處獲得官費資格。1918年5月7日,《浙江公報》第2197 期發布了《浙江省教育廳布告第三號:為應考留學日本官費生報名及考試日期由》,布告內容是為選拔留日官費生,“據留日學生監督處冊報,浙江留日官費生尚有余額可備選補”。18浙江省教育廳,《浙江省教育廳布告第三號:為應考留學日本官費生報名及考試日期由》,載《浙江公報》1988第2197期,第8—10頁。通過該考試選拔的官費生被為“選補生”意為補充該年留日學生之余額,是帶著官費待遇進入預備期的。
與留日學生監督處所呈報的《留日官費學生一覽》中的官費生不同,據1920 版《同鄉錄》中的記載,陳之佛預備期已經是官費,顯然是選補生。根據前文提到的教育部于1918年1月30日發布的《指令留日學生監督新生預備限一年應照準文》,這類新補官費生需在一年內考入日本高等學校,才能繼續享受官費,否則將面臨取消待遇。
四 陳之佛留日期間的住所
《陳之佛年表》的輯錄表示:“(陳之佛)在日期間一直住在神田區猿樂町二·一清壽館一號房間。”直到2020年《陳之佛全集》的出版,仍保持這一說法。
陳之佛留日期間所經歷的重大事件,莫過于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地震加之引發火災和海嘯,導致房屋損毀和人員傷亡,屠殺朝鮮人事件的擴大化更使局勢動蕩,受此影響,大量留日學生隨后歸國。
前文提到,在《留日學生最近情形之調查》中,陳之佛的受災情況為“無恙”。查閱其他居住神田區的留日學生,多有財務、行李全燒,甚至生死不明,陳之佛何以如此幸運?查閱《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1920年、1921年版中,陳之佛留日期間的住所都在神田區猿樂町二ノ一清壽館;1922年版《同鄉錄》中,陳之佛的地址已經改為下谷區真島町一番中華學舍。19浙江留日同鄉會,《會員錄》,《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內部資料),浙江省檔案館藏(編號:學校-475),1922年,第19 頁。比較兩區在地震中的受災情況,可見端倪。
《申報》1923年9月系列專題《日本震災之調查》,報導了當時日本的震災損毀詳細狀況,現摘取神田區和下谷區的部分資料以作對比。
區分: 神田區 下谷區
全面積: 一九九三 三二七一
燒毀面積: 一八七一 一五六〇
未燒面積: 〇一二三 一七一一
燒失步合: 九四 四八20《日本震災之調查》,載《申報》1923年9月22日第六版,第二張。
從燒毀面積來看,下谷區損毀幾近一半,而神田區幾乎全無幸免。據《申報》1923年9月6日《日本大地震損害紀》(四)記錄了東京具體燒毀區域:
“神田區”全燒,……“下谷區”:二長町、竹町、御徒町、西町、南北稻荷町、東町、西黑右門町、南大門町、仲町、長音町、山伏町、阪元町、中入谷町、豐住町、金杉町、龍泉寺町、日本堤、三輪及夾在此間數街,全燒。21《日本大地震損害紀(四)》,載《申報》1923年9月6日第七版,第二張。
材料顯示,神田區全燒,在下谷區燒毀區域中未見真島町。可見,陳之佛從神田區搬到下谷區真島町,才是能夠幸免于震災的關鍵。陳之佛的一次住所搬遷,對于設計史來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話題,但對該話題的糾偏,可能是他能夠順利回國的前提。
五 陳之佛的回國時間
陳之佛的回國時間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在《陳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中,盡管陳之佛的畢業時間從1923年改為1925年,但對陳之佛1923年4月之后在國內活動年表輯錄,基本沒有改動,可將該觀點歸納為“陳之佛1923年4月回國”;謝海燕先生在《陳之佛的生平及花鳥畫藝術:〈陳之佛花鳥畫集〉前言》一文中,提到“一九二四年陳之佛回國”;李華強在《設計、文化與現代性:陳之佛設計實踐研究(1918—1937)》一文中認為,陳之佛是在1925年3月畢業之后歸國;蔡仕偉在《陳之佛書刊裝幀探源與發展考略》一文中,通過考察官報和航運記錄,認為陳之佛是1925年7月回國。
可見,目前主要存有1923年4月、1924年、1925年3月和1925年7月四種觀點。并且,極少有研究成果出示了有效的史料檔案(有證據表明,陳之佛早在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之前就返回國內并從事美術活動,這里所說的回國時間與其畢業時間不可混淆)。理清陳之佛具體何時回國,不僅對于陳之佛早期美術活動的考察,乃至于對中國現代設計史的研究,都有重要價值。
關于陳之佛留日期間在中日之間的短期往返情況,我在拙作《陳之佛留日期間的回國時間問題—兼陳之佛早期美術活動再考察(1920—1925)》一文中已有較詳細的考察,文中還對以上四個時間版本作了相應考證,在此不復贅述。本節主要考察陳之佛正式回國從事美術活動的時間,借此對拙作進一步修正。
限于材料,拙文原先的考證結果認為,陳之佛的回國時間應該在1923年9月至1924年8月之間。從材料來看,這應該是目前最可靠的。但就結果而言,時間范圍仍過于寬泛,需要進一步縮小、明確。
1920年、1921年、1922年、1923年版的四本《同鄉錄》中,陳之佛均作為浙江留日學生會員出現,1924年版的《同鄉錄》中,不再出現陳之佛的名字(陳杰)。22參見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內部資料),浙江省檔案館藏,1920年(編號:學校-474)、1922年(編號:學校-476)、1924年(編號:學校477);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會報》(內部資料),浙江省檔案館藏(編號:學校-475),1921年;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內部資料),浙江省圖書館藏,1923年。1924年1月距離陳之佛的畢業時間尚有一年有余,這意味著,在1924年1月《同鄉錄》統計會員信息時,陳之佛已經退去位于下谷區真島町一番中華學社的租住房,并返回中國。
至于陳之佛離開日本的具體時間,僅憑現有材料難以考訂。已有材料表明,大地震發生時(1923年9月1日)陳之佛在日本無疑。事實上,直到1923年10月10日《申報》發表《留日學生最近情形之調查》之前,陳之佛還在日本。“中國留學生在東京未回者,尚有二百余人,以官費生為多,皆系五個月以上未領官費者,積欠店賬,已多欲歸不得。”23《留日學生回國代表之談話》,載《申報》1923年9月20日第十三版,第四張。
依據《同鄉錄》中的現有材料能夠確定的陳之佛歸國時間大體在1923年10月至1924年1月之間,比此前的“1923年9月至1924年8月”縮進了八個月。盡管在現有條件下無法再進一步詳細,但它仍是目前最貼近的(筆者系統查閱了在此期間上海與長崎、東京之間的航運記錄,關于陳之佛的回國時間,目前尚未發現價值的材料)。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陳之佛之所以能夠提早一年有余回國,一方面是與地震的影響有關。“(地震)直接襲擊了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樞部門,從而使這些部門一度陷入完全癱瘓狀態。”24[日]有澤廣巳編,《日本的崛起:昭和經濟史》,鮑顯銘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 頁。另一方面,還受惠于當時“日本留學教育的兩個顯著特點”—管理制度松,平時上課與否也不檢查;學科考試嚴,畢業考試更難。25沈殿成,《中國留學日本百年史1896—1996》,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47 頁。1925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的許幸之,在一次訪談中也提道:“那時學校(東京美術學校)的畢業創作可以國內做了寄回學校,審批合格就可以畢業。”26沈欣生,《沈西苓在日本留學時及回國后的情況:訪許幸之教授》,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德清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德清文史資料第六輯:現代德清名人》,內部資料,1997年,第163 頁。東京美術學校的畢業創作執行制度,也反映出當時日本留教育學的特點。 陳之佛回國時間的重新考訂,將會進一步對此期間其他史料的發掘形成助力。
六 余論
對于設計史、設計教育史來說,陳之佛留日期間的史料研究是一個細微的話題,但是,作為中國第一代接受現代設計教育的設計家和教育家,陳之佛的求學經歷又是繞不開的話題。對這段歷史的澄清,顯然是必要且迫切的。
由于缺乏系統的考察,現有成果中,對于陳之佛的赴日時間、留學費用形式、留日期間的住所以及歸國時間等問題的表述,還是存有諸多不實之處。本文通過對五本《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的考察,結合部分已有檔案文獻,對以上四點進一步廓清。陳之佛1919年以官費“選補生”身份赴日,并1923年10月至1924年1月之間回國,是對中國現代設計發端時期的再梳理。通過以上材料的考證,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一定的補充和完善,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本文的考察雖然僅涉及陳之佛早年留日期間的幾個重要事實,但對于設計史研究中史料的挖掘與運用不無啟示。一方面,已有成果中對于史料的運用,包括陳之佛手填履歷表,是兼顧自傳與口述特點的,經年日久,口述者記憶發生偏差等原因,導致口述材料的可信度降低,通常都會與史實發生偏差,需要與檔案材料進行相互佐證;另一方面,設計史研究的當務之急,不是急于提出一些理論框架,而是需要加快基礎材料的挖掘、鑒別和考證,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審慎地提出理論模式,這需要大批志同道合的理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陳之佛赴日時間,現只能根據1920年版《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中的記錄進行邏輯推理,有待新史料的印證;陳之佛的歸國時間,想必也是有據可循的,遺憾的是,限于當下材料,目前只能給出一個大體的時間段作為增補,更期待新材料的糾正。
本文對于四本《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的參考,根據浙江省檔案館的管理規定,檔案材料查閱全程禁止拍照,僅能通過手抄轉錄,這也是文中無法插入檔案原文圖片,不能讓讀者直觀閱讀史料的原因,留有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