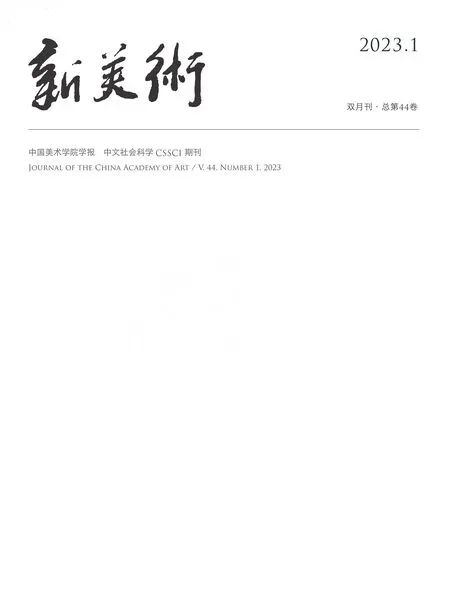在“詩的學校”完成“游戲的作業” 論陶行知教育的藝術性
王 爍
陶行知從美國留學歸來投身教育的第二年,在某次演講中提出了對未來教育者的期待,其中一條為“視教育為游戲的作業、作業的游戲”1陶行知,《師范生應有之觀念》,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0 頁。,自席勒的《美育書簡》提出“游戲沖動”的對象是“現象的一切審美性質”即“最廣義的美”,人只有在擺脫了目的、義務、煩惱的游戲狀態中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2[德]席勒,《美育書簡》,徐恒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12-116 頁。后繼教育學者不斷發掘并闡釋“游戲”這一概念的內涵,使“游戲狀態”被普遍視為教育應達到的理想狀態之一。同時,“游戲”是理解教育與藝術關系的樞機,最直接影響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杜威在論教育時說:“始終充滿游戲態度的工作是藝術——即使在傳統中不是這樣稱呼它,在性質上依然是藝術。”3[美]杜威,《民主與教育》,俞吾金、孔慧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50 頁。陶行知以西方美學和教育學中的游戲觀為起點,隨著其教育實踐的深入發展,他對教育之游戲性的理解帶上了中國社會現狀、文化教育傳統,乃至個人性情相關的特點,最終超出了“游戲”的范疇,形成了其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獨特藝術性。
本文的研究范圍包括陶行知針對教育的專門論述和作為教育家的職業行為,也涵蓋了他初衷未必是“施教”的日常生活、思想情感。陶行知一向將教育視為“自化化人”的事業,而從發生學角度分析其起源,每一個教育者必先自化、方能化人,即“正如一個藝術家的作品一樣,一個教育家的作品首先就是他自己的靈魂”。4鄧曉芒,《教育的藝術原理》,載《湖北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 期,第103 頁。若以“化人”的真正效果來審視教育的各種途徑,“身教”必重于“言傳”,可謂“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陶行知的完整生活是他教育思想最徹底的實驗對象,考察它就是對其教育事業最直接的檢驗。
一 從美育手段到生命狀態的游戲與閑暇
陶行知對游戲與教育關系的理解有兩個層面:一是以游戲作為教育(特別是美育)的手段;二是將游戲性作為教育的本質特性之一,又因其生活教育理論中教育與生活的親密無間,游戲狀態則成了人生通過教育而應達到的一種理想狀態。這兩個層面的含義相輔相成,游戲之所以能成為教育的手段,即因它與人的生命欲望相通。
作為生活教育的組成部分,“游戲”首先回應著緊迫而具體的現實需求:如何糾正民國時盛行的“玩賭、玩煙”等民風之弊?如何在傳統價值體系窮途末路、西潮猛烈沖擊的時代,以“化民易俗”的教育造新民、成新俗?陶行知選擇了以游戲、玩樂為重要途徑,這一選擇背后是他對美育之樞機何在的判定——在于人的欲望;就個體而言是通過整理欲望而整飭性情,從社會層面來說便是移風易俗。
陶行知一向正視人的欲望:
我們承認欲望的力量,我們不應放縱他們,也不應閉塞他們。我們不應讓他們陷溺,也不應讓他們枯槁。欲望有遂達的必要,也有整理的必要。5陶行知,《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36 頁。
陶行知始終秉持對人之欲望既承認、順應,又約束、利用的態度,隨著生活教育理論的成型,他再次闡釋了這一觀念:“主張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來達民之情,順民之意,把天理與人欲打成一片。”6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97 頁。關于欲望,陶行知的主要對話對象是中國傳統儒學中天理與人欲關系的探討,他贊成戴震的“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并將戴震“圣人治天下”的語境改換為具有現代意義的普及教育。陶行知的欲望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其視為一種中性的存在,而非社會弊病、人生苦痛的根源,持后種觀念者典型如王國維:“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倦厭之情即起而乘之。”7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載《王國維文集》第一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 頁。即欲望不得滿足而苦痛,欲望既償而倦厭,倦厭也是苦痛的一種。而陶行知認為欲望本身無對錯、無大小,關鍵在教育的調節、管理之功:“欲望不可大,太大苦局促;欲望不可小,太小易知足……能力勝欲望,精神廢儲蓄。欲望勝能力,煩惱勞苦哭。兩樣差不多,人生真幸福。如此教學生,才算好教育。”8陶行知,《欲望》,載《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第159 頁。將人天然具有的欲望視為教育者的機會,顯示出他對教育之能動力量的一貫強調與信任。
陶行知認為遂人之玩樂欲望的“較好的法子”主要是音樂、戲劇、美術等通常用來作為美育的藝術門類,因為它們是引人向上而非沉迷的娛樂,即在玩耍的同時承擔起煥發精神、涵養人格的作用。比如1924年他對某縣的禁煙禁賭政策表示贊同后,進一步建議:
但根本之謀在“遂民之欲,達民之欲”。民不能苦而無樂,忙而不玩。我們既要除他玩賭玩煙之樂,就必須用較好的法子使他們樂,使他們玩。9陶行知,《希望于縣知事的:給歙縣知事汪鏡人先生的信》,載《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52 頁。
與他同期或更早的知識分子持類似觀點者不在少數,如王國維曾說:“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則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則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雕刻、繪畫、音樂、文學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則所以慰藉彼者,世固無以過之。”10陶行知,《去毒篇》,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第25 頁。又如朱光潛:“你如果沒有一種正常嗜好,沒有一種在閑暇時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東西,將來離開學校去做事,說不定要被惡習慣引誘。”11朱光潛,《談讀書》,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
陶行知以戲劇、音樂、出游等作為使民眾獲得“正當的娛樂”“正當的愉快”的方式,同時重視活動過程中生發的精神與情感狀態;游戲玩樂既是移風易俗的手段,其本身所代表的趣味和閑適又是教育應當引導生活達到的美好狀態。于此,教育手段和目標合二為一。作為其教育實踐的第一對象,陶行知擁有的自然不是干癟枯燥的禁欲主義者的生命,而處處展現出由游戲帶來的活潑、愉快和生機。平日自不必說,即使在其教育事業最關鍵或危機最嚴重的時刻,依舊玩興盎然。
1926年底,陶行知正為籌備曉莊學校四處奔走,這是他離開擁有極大話語權的半官方行業協會系統而獨立辦學的轉折點,也是其事業與個人經濟狀況由寬裕無憂到時常捉襟見肘的轉折點。在思想與經濟雙重緊繃的時刻,1926年12月7日他給友人的信中自述“近兩星期來,上午做計劃,下午拜活財神,夜間訪友看戲。”12陶行知,《衛生運動:給凌濟東先生的信》,載《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94 頁。“做計劃”即思考鄉村教育的方向與出路,“拜活財神”即募款,“看戲”則是“席地而坐”的狼狽和快活,是純粹的娛樂。類似的,1930年元旦所做《我今年的計劃》中,在大額籌款、投稿上百篇、復信七百封、譯書三十萬字等工作安排之間,突然冒出了種園一分、學燒菜四樣、學騎馬、巡游大都市鄰近村莊等事項。13陶行知,《我今年的計劃》,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406 頁。對陶行知的性情稍有了解便可知,這些固然可以視為“工作”,但對他而言更是真正的“玩耍”。即使到了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他依然承認“玩”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我們自身的教育在過去是片面的,現在亦應該全面起來,全面的自我教育。就是要:看、想、玩、談、干。……有疲勞,就得玩;有雙手,就得干。”14陶行知,《抗戰的全面教育》,載《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256 頁。陶行知以鄭重的態度對待游戲玩樂,全身心投入,使其作為教育家的生命和他推行的教育都棄絕了愁苦之色,呈現出真實的生活之樂。
與游戲玩樂相關,陶行知的教育深刻認同生活中“空閑”的價值。1934年7月,正是在公告“知行”改名為“行知”這一重要決定的同一天,陶行知發表了《閑談》,充分表述了自己的“忙閑之辯”觀:
我一生之中沒有閑年,一年之中沒有閑月,一月之中沒有閑日。一有閑日,就會害病。但是一日之中,我是愿有閑時。我的閑時,現在每天大約有一兩個鐘頭。這一兩個鐘頭的閑時是多么的寶貴啊!你就拿世界的一半來,我也不肯把它與你調換。15陶行知,《閑談》,載《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489 頁。
陶行知曾多次表達其“不以忙為苦”的生活態度,卻也一生珍視“閑”。寫《閑談》前后他正忙于推行在其教育生涯中占重要地位的工學團和“小先生制”,而此時的他已經歷了曉莊被查封、逃亡日本險喪命、曉莊復校幾經周折終無望等一系列打擊,加之中日戰爭就像隨時可能落下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多重刺激令他正處于一生中最激進的階段。客觀而言,其思想和情緒不免時有偏激。但這篇《閑談》卻真誠地表現出陶行知在極度的繁忙和惡劣的政治環境中,依然(希望)保有的淡定與閑適。
陶行知近三十年的教育實踐在大多數時候充盈著一種“雖急而緩”的從容。若將陶行知的教育實踐放回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一方面教育之于救亡圖存的重要性已是舉國共識,另一方面成效難以立即判斷的教育時常承受著亡國滅種的深刻焦慮所帶來的懷疑,所謂的“教育救國論”及其批判,部分來源于對各項事業優先級的不同判定。陶行知曾以幼苗一旦不得灌溉必將枯萎為喻,表明教育長期性與緊迫性的辯證關系,即“雖緩而急”。16陶行知,《致育才之友書》,載《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31 頁。強調回應現實需求的生活教育理論自然呼應著時勢之“急”,但若深入體察陶行知的具體教育實踐,又可時時處處感到一種并不“急”的從容氣質。陶行知的教育在內外交患的局勢中“急”和“緩”并存,于奮力追趕歷史(當時中國的“落后”已是共識)和氣定神閑之間,呈現出奇妙的張力與和諧。
陶行知所擔任的第一個校長職務是1923年創辦的南京安徽公學,《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中便強調時間余裕的意義:“將無益的時間騰出,則從事有益的時間有余裕了。然后學生可從容問學,怡然修養,既不匆忙勞碌,那身心也就自然漸漸的有潤澤了。”17同注5。在陶行知看來,時間之余裕是從事問學、修養等“有益”之事的重要條件,寬松的時間仿佛一個足以讓學生舒展的巨大容器,身心充分浸淫其中,方可獲得人格上的長進,達到“潤澤”的境界。到1939年中國已處于抗日戰爭的硝煙中,陶行知談論特殊時期針對特殊人群(難童)的教育該如何辦時,竟依然掛念于“先生太忙”這個貌似不那么緊迫的問題:
庖丁解牛,運斤成風。倘使他的前后左右上下擠得滿滿的,則手兒動也不能動,又何能運斤成風呢?先生太忙,便無暇溫故知新,依孔子的話,便不可以為師了。18陶行知,《兒童保育問題》,載《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365 頁。
可見陶行知在強調教育內容與現實生活保持高度一致(即“有抗戰的生活,就有抗戰的教育”)的同時,并不認為教育應該跟著政治形勢的緊張而亂了方寸,甚至生存的危機也不能完全征服教育而打亂其自身的內在節奏和規律。面對常有朝不保夕之患的兒童保育院,陶行知依然相信這里的先生和學生都有空閑的權利。
若說戰時兒童教育尚且是一般性的社會問題,那么陶行知在抗戰期間創辦的育才學校的困境則更加切近而具體。然而,即使到了“只剩下一個鼻孔在水面上呼吸”的危急,陶行知所辦之教育可能拮據艱難,但從不忙亂張皇。1941年11月,陶行知正在兩件關系到學校生死存亡的“麻煩”中來回輾轉,一是學校所在的草街鄉鄉長試圖趕走育才,二是米價飛漲,需要為學校爭取平價米以渡難關。19本文對陶行知生平活動的表述,參考王文嶺,《陶行知年譜長編》,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周洪宇、劉大偉,《陶行知年譜長編》,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年。兩件事耗用了陶行知幾個月的巨大精力,前一事因其背后政治勢力復雜,已到了直接致信蔣介石的程度,為后一事陶行知曾訪糧食部部長、教育部部長,皆“不遇”,可見他當時經濟與人際的雙重境遇。正是在四處奔波的焦頭爛額中,陶行知1941年11月11日給育才學校師生寫信交代了十二件事,起首一件卻充滿了閑情逸致:自己在北碚兼善中學看到校園里分栽芭蕉,“可愛可學”,便立刻讓學生們去取經并“回校即干”,因為“本校有芭蕉一株,迄今兩年,仍舊是一株,曷勝浩嘆。我們應該有一個芭蕉林”。20陶行知, 《數事備忘:致馬侶賢》,載《陶行知全集》第九卷,第171 頁。在火燒眉毛的關頭仍能注意到其他學校里的芭蕉樹,并將美化校園放在與吃飯、自衛等生存問題同等地位,可見陶行知永遠想方設法(或者說自然而然)在十萬火急的境況中為自己和所辦之教育留出時間上的空閑、精神上的余裕,有了“閑時”,方能有“閑心”與“閑情”。 正如陶行知在給妻子的信中勸她“吃飯、睡覺、散步時不想家中事,如我不想校事”,因為“工作切不可太緊張,更不可不涵養一種海闊天空的境界”21陶行知,《病未愈工作不可太緊張:致吳樹琴》,載《陶行知全集》第九卷,第22 頁。。從某種意義上說,“閑”正是陶行知和育才學校那留在水面上的“一個鼻孔”,是一個人、一種事業從現實困境中修煉出、并上達至從容淡定境界的重要途徑。
陶行知的教育對游戲玩樂和閑暇的珍視,與中國傳統教育理念中“游”和“息”之于學問進展、人格涵養的重要作用相通。《禮記·學記》中列舉了“教之大倫”的七個要點,其中一點便是“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此處之“禘”,即《論語·八佾》中出現兩次的祭祀族姓所出的祖先的大禮,逢禘必占卜,應由天子進行。22孔子被問到關于禘的問題時用“不知也”回避,“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然后“指其掌”,意為對于能明白禘禮的人而言,治理天下都輕而易舉。關于“卜禘”,參見張文江,《古典學術講要》(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6 頁;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5 頁。由此可見,卜禘是規格極高的儀式,在這個時刻“視學”即考核學習成果,自然有其莊嚴的意義。但《學記》強調的反而是不舉行禘禮的“非關鍵性時刻”:在細水長流的絕大多數日子里一概“不視學”,讓學生充分思考、從容生活,并在各種學問之間自由往來,以此舒放性情、涵養人格。《學記》此處之“游其志”,與《論語·述而》“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泰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均相關。“游”既是依照個人稟賦性情、將各種“藝”的門類融會貫通的自覺修習,更是在此過程中獲得的與學習對象(作為操練或典籍的“六藝”)融為一體、往來無礙的自信和愉悅,兩者的前提均是擁有充分的、可以自主支配、進行自主思考的時間和精力。
《學記》在“教之大倫”后論述了“安弦”“安詩”“安禮”“樂學”的條件,此皆“藝”之范疇,繼而總結以“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這句話可以有三種理解,彼此間并不矛盾且相輔相成:一是君子對于學,真正地將其放入心里(藏),勤勉不懈地修習(修),休息和游玩的時候也不忘(息、游),即“念茲在茲”之敦促;二是“學”需要藏、修,也需要息、游,四種活動同樣重要,均為學問達成之途徑;三是“學”可以使君子藏(安身立命)、修(修習長進)、息(休憩,亦有生長之意)、游(愉悅身心),藏修息游共同構成了君子將日常活動與問學求道徹底貫通后擁有的生命境界。息與游,和藏與修一樣,都既是達到目的(“學”)的手段,也是目的本身。正如陶行知之“閑”,既是其對“留有空閑”這一教育方法的重視,也是教育乃至生命本身應呈現出的張弛有度的狀態。
較陶行知早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引進西方美學思想以提倡美育時,多受以康德、席勒等為代表德國古典主義美學的影響,如王國維十分贊同席勒對于“游戲”的論述,并以其為基礎探討藝術的來源:“希爾列爾(即席勒)既謂兒童之游戲存于用剩余之勢力矣,文學美術亦不過成人之精神的游戲。故其淵源之存于剩余之勢力,無可疑也。”23王國維,《人間嗜好之研究》,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第30 頁。由此出發,王國維明確指出達到“游戲狀態”這一生命理想狀態的條件——超脫于生存競爭:“爭存之事亟,而游戲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勢力獨優,而又不必以生事為急者,然后終身得保其游戲之性質。”24王國維,《文學小言》,載《王國維文集》第一卷,第25 頁。這種將藝術置于生存競爭之外、之上的思路,根源是康德“審美無關利害”的基本論斷,王國維的借鑒也繼承了其二分結構——“生事”與“游戲”,生存與藝術:超越了伴隨生存競爭而來的憂患和功利,才能產生并保有藝術。另外,與前述王國維對欲望的認識相連的是“人生固苦”的基本判定,從而將藝術視為解藥——“(文學美術)其作用皆在使人心活動,以療其空虛之苦痛”,這就使得藝術超脫于欲望的一面得到了格外強調——“故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25同注7,第4 頁。。作為生活之救贖的藝術自然要與生活劃分較為清晰的界線,此界線即以“非功利、無欲望”為標準——“無欲故無空乏,無希望,無恐怖;其視外物也,不以為與我有利害之關系,而但視為純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觀美時有之”26王國維,《孔子之美育主義》,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第156 頁。。
無空乏、無恐怖的境界當然為陶行知所向往,他的美育觀中也強調非功利態度對于發現和獲得“美”的重要性,但他更多地指向一種主觀狀態(類似王國維所說的“汲汲于爭存者,決無文學家之資格”),并非從客觀上否認“生事”與藝術境界共存的可能。陶行知并不認為斷除欲望是達到游戲狀態的前提,也不認為只有“觀美”這一從現實生活中抽離出來的“通道”,而應該在與現實人生緊密相關的事業中(教育為其一種),追求與藝術境界的相通。陶行知的教育從不將生存競爭與游戲(即藝術)精神對立,它引導人們在積極回應前者的同時依然追求后者,甚至從應對前者危機的過程中培育、生長出后者。于貌似二分中尋求統一是陶行知的教育所一貫奉行的思維方式,其背后是他對于世界和生活的整全式的體認。
二 “過程性”與“非功利性”之辯
陶行知從美國留學歸來投身教育改革的第二年,便提出了對“教育之終極目標與樂趣何在”的看法:
現任教育者,無不視當教員為苦途,以其無名無利也。殊不知其在經濟上固甚苦,而實有無限之樂含在其中。愚蒙者,我得而智慧之;幼小者,我得而長大之;目視后進骎骎日上,皆我所造就者。其樂為何如耶!故辦教育者之快樂,當在手續上,而不在其結果之代價。換言之,即視教育為游戲的作業、作業的游戲也。27同注1。
引文意在闡釋教育得以自足的過程之樂,即“游戲的作業、作業的游戲”,并在這一點上與藝術的創造過程真正相通。類似地,梁啟超在《教育家的自家田地》中論教育者之快樂,第一點就是“快樂藏在職業的本身,不必等到做完職業之后,找別的事消遣才有快樂。”陶行知以“游戲”喻教育并強調其過程性本質,除康德、席勒一脈的潛在影響,如康德所謂一切互為目的與手段、具有“內在目的”的事物,28[德]康德,《判斷力批判》,載《美,以及美的反思:康德美學全集》,曹俊峰譯,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526 頁;[美]加勒特·湯姆森,《康德》,趙成文、藤曉冰、孟令朋譯,中華書局,2002年,第114-116 頁。更直接的思想來源是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杜威認為,從教育的本質來看,“教育即生長”,從教育過程與目的的關系來看,“教育過程本身就是它的目的,在自身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目的”。29同注3,第62 頁。意即兒童的生長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這是一種內在于教育歷程的“實然”的目的,而不是由家長、教師,乃至社會期許強行加諸教育的“應然”目的。30顧紅亮,《實用主義的誤讀:杜威哲學對中國現代哲學的影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44-251 頁。仔細辨析可發現,“教育無目的論”其實是教育無“外在”目的論,而非徹底無目的;教育的內在目的是“成人”。陶行知在這一點上基本與杜威一致,亦將“人”作為教育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成果”:
(學校舉辦的)活的展覽會,決不是以陳列館的物品為范圍,我們生活所表現的地方,就是我們展覽會的地方。最好的展覽品,就是我們一個一個的活人。我們大家從現在起,要把自己徹底的改造,使自己藝術化。31陶行知,《活的展覽會:給曉莊全體同志》,載《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149 頁。
以“一個一個的活人”作為“最好的展覽品”的教育,與藝術相通于兩者共同擁有的不假外物的過程性本質。學界對“什么是藝術”較為普遍的共識之一即藝術是“獨立自足的審美范疇”,其建構本身就能提供審美愉悅,而無須依靠任何其他東西。32參見曹意強,《美術鑒賞與智性模式》,載《藝術與智性》,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5年。與藝術的目的只是創造美類似,教育的目的應該只是“成人”,即人的本質力量的全面實現,不是附屬于任何其他目的的手段。33同注4。正因如此,教育一定程度上應該免受外在目的的限制與評判。
在以“自足的過程性”貫通了教育與藝術的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陶行知的教育在何種意義上可稱為無目的性?清末民初,強調“以教育或美育自身為其目的”的觀點從中國傳統儒家教育中明顯地分化出來,例如王國維認為“教育之宗旨”是“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謂完全之人物,則“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34王國維,《論教育之宗旨》,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第57 頁;《孔子之學說》,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第153 頁;參見曾繁仁主編、劉彥順著,《中國美育思想史·現代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15 頁。。蔡元培也多次論及“教育獨立”,特別是相對于政治的獨立:“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于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且在個人與社會間似乎更重前者:“(對于如何改造教育)……‘養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社會的各分子都有健全人格,此外復有何求?所以第二句話離不了第一句話。”35蔡元培,《對于新教育之意見》,載《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4年,第130 頁;《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與社會〉社演說詞》,載《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95 頁。即便如此,仍有學者認為蔡元培“養成人格之事業”的教育定位隱藏著工具化的危險,容易被納入“教育救國論”的政治實用主義視野中去,即為了既定環境的需要而塑造一定模式的人格。36同注4。不過,“成什么樣的人”這一相對具體的期待(而非抽象的“成人”),是否應該、且能夠被視為教育的“外在”目的?
落實到真正的教育實踐中便可知,若對“所成之人”的品質徹底不設期待與引導,則教育根本無從開展,遑論具體而有效。梁啟超曾論教育之不可無“宗旨”:“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茍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寸毫不能有成。何也?宗旨者,為將來之核也,今日不播其核,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有莖、有干、有葉、有果,必不可期之數也。”37《論教育當定宗旨》,第86 頁。由此點明了明確的目標對于教育實踐的錨定作用。學界普遍接受“培養自由的人格”可以算教育終極且“內在”的目標,但“自由”的定義是時代、政治、文化、族群的產物,人類并不共享某種具有形而上意義的、永恒的“自由”的理解。故只追求純粹“內在目的”的教育并不存在,也無從實現。
清末開始,傳統中國對西方文明的認識伴隨著后者帶來的巨大沖擊,艱難地由“船堅炮利”進入到政治制度的改革再到思想的徹底更新,而文化運動改造“人”的目標得以長期、真正落實的重要途徑就是教育。陶行知積極參與的教育改革,其目標必然具有特定的方向性而不可能達到純粹的無“外在目的”,必定要回應救亡圖存的民族和時代問題而帶有較強的道德及倫理指向。同時期的教育者們,只要不是坐而論道的空談家而真正投身實踐的,所辦之教育都無法滿足“徹底”獨立的標準。例如強調“教育獨立”的蔡元培并非機械地堅持抽象的這一原則,在提倡世界觀教育和美育主義教育的同時,也重視軍民國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顯然就與“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的現實緊密相關。蔡元培亦不反對教育呼應時勢變化之要求,如其1927年底創辦國立藝術大學的提案中說“我國民政府,為勵行革命教育計,尤不可不注意富有革命性之藝術教育”38《對新教育之意見》,第131 頁;《創辦國立藝術大學之提案摘要》,載《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180 頁。。
陶行知和同代教育家在不同程度上都贊同“美”的自足性,承認其與道德的分野,但落實到美“育”上,則不可避免地與道德、倫理價值相結合,典型例證之一是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出。依蔡元培的觀察,彼時宗教已在科學、道德、審美各領域進入全面消解階段,更何況與西方相比,中國宗教傳統并不發達。39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載《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0 頁。美育為何要以一種已衰落的勢力為首要針對對象?其實蔡元培的矛頭真正指向的是宗教之弊的根源——刺激感情,具體體現為“擴張己教、攻擊異教”,其本質是打著教義旗號的“私”。40《中國美育思想史·現代卷》,第161 頁。由此可見,“以美育代宗教”不是為了取代宗教本身,而是為了以美育治私。蔡元培從康德審美判斷的四個契機中提煉出他認為最核心的兩個——超脫、普遍;41蔡元培,《美學的進化》,載《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22 頁。如此選擇,有將美的本質轉化為美育之基礎的強烈現實需求和鮮明的針對性。蔡元培以物質上“一人有了,他人便無法分潤”的不相容與美的對象“人人得而游覽、賞玩、暢觀”為對比,發出美“純然有‘天下為公’之概”的感嘆。42蔡元培,《美育與人生》,載《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158 頁。“天下為公”本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理想,將其與美相聯系,自然使后者不再可能局限于藝術品鑒賞這樣“純粹的”美學范疇。由美之普遍、超脫而培養出人的“高尚純潔之習慣”,即“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之計較”,于此就將美“無關利害”的非功利性本質轉化為了美育的倫理價值。
一般認為,對陶行知影響甚大的杜威對于教育目的的界定到“成人”為止,若規定成什么樣的人,則有用“外在目的”干擾真正的教育過程的危險。但杜威在中國之行的演講中,或許是受當時中國教育改革迫切意愿的感染,其實對何謂理想的“人”曾有更詳細的闡釋,概而言之便是“做一個好的公民”,其含義包括好鄰居、好朋友、樂于奉獻的人、在社會經濟方面生利而非分利的人、好的消費家、好的創造者或貢獻者等,即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造就社會的有用分子。”43杜威,《關于教育哲學的五大講演》,載《杜威在華教育講演》,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9-20 頁。把個人的生長、成人與社會需求聯系起來,實質上已經從純粹的“內在”目的向外邁出了一步,不論是將其解釋成教育目的之抽象與具體(即抽象而言教育目的在于生長和生活,具體而言在于培養良好公民),44同注30,第249 頁。還是解釋成目的與結果之辯證(即良好公民不是教育的目的而是結果,正如杜威所反對的“預備將來生活”和教育應有的關系)。
陶行知比他的老師更進了一步。1918年陶行知曾論“正當之領袖”和“健全之公民”是“共和國之長城”,教育乃造就此長城的不二途徑,尚與杜威之“好公民”論類似。45陶行知,《教育研究法》,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227 頁。同一年他推行“生利主義”教育,所謂生利主義,特點在于“發舒內力以應群需,所呈現象正與衣食主義相反”,強調“應群需”、區別“生利主義”與“衣食主義”,清晰顯出陶行知教育回應社會需求的倫理和道德屬性。46陶行知,《生利主義之職業教育》,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0 頁。至鄉村教育時期,陶行知明確提出教育之目的是教人“在勞力上勞心”——“人人在勞力上勞心,便可無廢人,便可無階級。征服天然勢力,創造大同社會,是立在同一的哲學基礎上的,這個哲學的基礎便是在勞力上勞心”47陶行知,《在勞力上勞心》,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08 頁。。這一目標針對的是傳統教育重知識、輕實踐以及將社會區分為勞力與勞心兩個階級,意在打破由教育造成的階級劃分。隨著中日戰爭的陰云密集,陶行知的教育對現實需求的回應也愈發明確,1936年提出“救國教學做”是眼下生活教育的唯一功課,抗戰全面爆發后,教育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更是變為“教育的目的不是為教育而教育,乃是為抗戰而教育。”48陶行知,《全面抗戰與全面教育》,載《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277 頁。即使被質疑推崇“天才”教育的育才學校,陶行知也一再強調其目的是“為著增加抗戰建國的力量而培養特殊才能的幼苗。”49陶行知,《談生活教育:答復一位朋友的信》,載《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357 頁;《育才學校教育綱要草案》,載《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381 頁。由此可見,陶行知的教育即使不能算是純粹的社會本位,也自始至終具有鮮明的社會指向,教育作為“生活所必需”,此“生活”既是個人的生活,即生長、成人,也是全社會的生活,即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更具體地,落實為救亡圖存、抗戰建國的緊迫任務。
綜觀同時期世界范圍內的“新教育”運動,杜威所在的美國作為其更早發生的場域,面臨的狀況與中國顯然不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科技與工業的大發展使得標準化、機械化的社會運作淹沒了個性,故杜威反對教育由外在目的來控制,強調兒童自由生長發展的重要性。陶行知和杜威都強調教育與生活的關聯,所面對的生活不同,教育自不同;且如前所述,杜威對教育目的之“內在”與“外在”之間的界限劃分得并不絕對。陶行知對教育之過程性本質的認識,更多的是從教育者與受教者的角度出發,強調雙方在此過程中獲得的不假外物的、自足的成長愉悅。若于更高的站位將教育視為人類在具體歷史情境中的一種實踐活動,陶行知顯然希望其能兼顧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兼顧美學、文化、政治、倫理等多方面的價值。
一般認為對應人的知、情、意的教育是智育、德育、美育,總體而言“美感教育是一種情感教育。”50陶行知,《談美感教育》,載《大美人生:朱光潛隨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中國和西方的教育傳統中都承認三者相通處,也都有對于美育妨礙德育的警惕。育才時期的陶行知已在理論上徹底打破三者間的界限,并且強調情感教育的價值觀傾向:
感情教育不是培養兒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調節并啟發兒童應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調節與啟發中使兒童了解其意義與方法,便同時是知的教育;使養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與奉行,便同時是意志教育。51陶行知,《育才學校教學綱要草案》,載《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382 頁。
既然情感教育不可能沒有“方向”,與其緊密相關的美育就不必以純粹的非功利性為標準,陶行知教育的藝術性也就不必諱言其中的道德、倫理訴求。當論及抗日戰爭中的育才學校該如何“創造藝術之環境”時,除了“有其內必形諸外”、外在環境與內在修養之辯證關系外,陶行知對于學校環境應表現出“什么樣”的藝術精神做了明確的描述:
校容要井然有條,秩然有序,凜然有不可侵犯之威儀。什么東西應該擺在什么地方或只許擺在那個地方,應該怎樣擺也只有那樣擺,而不許它不得其所。……通身以樸素之藝術精神貫徹之,便成了抗戰建國中應有之校容。52陶行知,《育才二周歲之前夜》,載《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410 頁。
創辦育才之前,陶行知曾任南京安徽公學、曉莊學校校長,期間均論述過教育環境的藝術性改造問題,但并未明確其“方向”。隨著教育實踐的深入,也由于社會環境的重大變化,育才的藝術化校容明顯帶有了與民族存亡息息相關的政治及道德取向:樸素中的威嚴。“樸素”一詞可以歸入美學范疇,但若將此“樸素”背后的物質因素——育才的經濟窘境,以及造成物質匱乏的直接原因——抗日戰爭一并考慮進去,則不復能以單純的美學風格視之。“威嚴”更是如此。陶行知雖然反對嚴苛死板的道德律令,卻贊許“不許它不得其所”這類具有道德感的規范所呈現出的令人振奮的愉悅。現實生活及人之生命中知、情、意的統合不可分,使得陶行知教育中所追求的美感不可能是一種純粹的獨立存在。
三 徹底的日常化
所謂美者……所辦之事,亦宜有美術。表格最貴整潔;信件亦宜雅致。……當作不作,不當作而作,皆不美。53陶行知,《辦公原則》,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413 頁。
收條寫字要令學生寫得端正清楚,紙張亦宜裁得端正,這是無聲之樂,也可說是辦事音樂化,辦事美術化,是諸生所應受之教育之一小節,但是必要之一個螺旋。54陶行知,《依照經濟手續也是一種教育:致李凌》,載《陶行知全集》第九卷,第337 頁。
我們應當秉著美術的精神,去運用科學發明的結果,來支配環境,使他們現出和諧的氣象。55同注5,第37 頁。
鄉村教師應當用科學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術的觀念去改造社會。56陶行知,《我們的信條》,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75 頁。
以上引文在時間上涵蓋了從陶行知早年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時期直到最后的育才學校時期,可明顯看出其教育實踐的藝術性滲透在一件件具體的“事”中。按照哲學家對“物的世界”和“事的世界”的劃分,陶行知的教育美學堅決扎根由具體活動構成的、動態的事的世界,是“做”出來的,而非來自對世界之“物”的靜觀與思考。57趙汀陽,《第一哲學的支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196 頁。“生活即教育”的信念自然將“做教育之事”延伸為做任何生活之事。因事而起、蘊于事中、隨事完成,在一個由“行”而非“思”構建的世界中,陶行知實施美育的時機和其教育所呈現的藝術性擴大為人類的全部生活。
陶行知對灑掃庭除之類生活瑣事相當在意,一方面是依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教育模式,即通過“掃一屋”來培養“掃天下”人才的必要品質,另一方面則是重視勞動和美化環境的過程中自然生成的原發性、直觀性愉悅體驗,一種未經分析或前分析的愉悅狀態,這些體驗和狀態構成了審美的生活。58劉彥順,《中國美育思想通史·現代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8 頁。陶行知經常掛念的一件事是“燒飯”,認為這是一個人、特別是鄉村教育者最基本的生活力(“師范生初到鄉間去充當教師,有的時候,不免餓得肚皮叫,就是因為他們不會炊事”59陶行知,《試驗鄉村師范學校答客問》,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90 頁。),同時從中體會到真切的美:
燒飯是一種美術的生活。做一樁事情,畫幅圖畫,寫一張字,如能自慰慰人就叫做美。一餐飯燒得好,能使自家吃得愉快舒服,也能夠使人家愉快舒服,豈不是一種藝術嗎?60陶行知,《湘湖教學做討論會記》,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15 頁。
在陶行知看來,任何能“自慰慰人”的活動都可以具有審美價值。引文中的畫圖、寫字,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藝術創作,它們的結果也并非西方古典美學中作為審美對象的藝術品,而燒飯、吃飯相關的口腹之欲,按照康德對審美和感官判斷的截然區分更是屬于“為了獲得愉快而要求摻進刺激和感動的因素”的“粗野”鑒賞。61《判斷力批判》,第400 頁。陶行知將種種根植于人性、最世俗化的愉悅與純粹的藝術鑒賞提高到了相同的地位。綜觀他一生留下的文章、日記及書信,因某家店的“花生是有特別的香味,炒的方法已經達到藝術的境界”62陶行知,《我現在是一只獅子:致吳樹琴》,載《陶行知全集》第九卷,第347 頁。而跑很遠的路去買花生、夜里加班才能完成工作的行為比比皆是,這樣一位教育家所推行的美育以最普通的日常活動為契機,其教育的藝術性具有鮮明的日常化傾向。
這一特點背后是陶行知對“美”之本質、人和世界關系的理解。西方的神學美學推崇靈性與神圣,而古典美學通向現代美學的橋梁人物康德甚至將樂器發出來的悅耳聲音都視為“刺激”,只承認單純的“形式”才能構成“純粹鑒賞判斷的真正對象。”如此區分使審美價值與感官快適、與“善”劃清了界限并獲得了獨立和自律,同時“自由美”標準之嚴苛,使審美活動限定于“單純靜觀”。63《美,以及美的反思:康德美學全集》,第400-403 頁;參見《中國美育思想通史·現代卷》,第6-7頁;鄧曉芒,《康德哲學演講錄》,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156-164 頁。有學者將西方美育總結為一種“游戲”范式,從康德開始這種“游戲”便等同于“思想的游戲”,席勒雖在審美活動中統合了知性和感性,依然強調其精神性。而中國傳統美育可視為“游藝”范式,對“學”的強調中包含了躬行實踐的“習”,情理交融。兩種美育范式背后是文明存在論結構的不同,即西方人-神、靈-肉、主-客區隔的“兩個世界”和傳統中國天人合一、禮法交融、身心一體的“一個世界”。64參見柏奕旻,《中西美育精神的比較闡釋及“游藝”范式的當代轉化》,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 期。不過就西方美育的學脈而言,杜威在實用主義哲學的框架內“作為經驗的藝術”已經使藝術大大貼近了生活現實,他認為藝術的審美價值和勞動創造相統一:“圖畫和音樂或者繪畫的和聽的藝術是代表所進行的一切活動的頂點、理想化和優美的極致。我想,凡是不用純粹文學的觀點來看這種學科的人們,都承認真正的藝術是從工匠的工作中產生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是偉大的,因為它是從生活的手工藝中產生的。”65于文杰,《杜威實用主義美育與現代中國》,載《江蘇社會科學》1998年第3 期,第189 頁。
將無窮無盡的生活全部納入美育范疇并承認日常萬物中蘊含的潛在審美價值,陶行知的教育顯然更貼合“一個世界”的存在論。而在西方諸多哲學家中,杜威的美學思想確實是陶行知借鑒最為明顯者。陶行知將杜威在“頂點”和“極致”的純粹藝術中發現的來源于手工勞作的美感,更加廣泛地發現于日常生活,徹底超出了在藝術創作的范疇中談論美的界限。
陶行知對傳統儒家的美育觀念亦有所突破。后者將美育的完成主要依托于詩、禮、樂、射、御等“學習”活動,而非稼穡之類的“鄙事”。儒家雖強調教育需由思行合一、身心發動而完成,但因“思”的對象(可概言為內圣外王)與“行”的內容(主要是道德實踐)都有側重和局限,故其教育所追求的美感僅從生活的一部分中抽象而來,而非全部。另外,這一套美育觀的行為主體和教育對象顯然以士人君子為主,繁復的祭祀儀式、高雅的詩歌和音樂都與廣大民眾存在距離。明清之時,儒家曾出現明顯的日常人生化趨勢,不過其重心還是普通百姓如何能在日常生活中各自成圣成賢,基本落在修身的道德范疇內。66余英時,《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載《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32-133 頁。儒家絕不否定世俗的意義,但其精英化的傾向使其并不太關心最基本而瑣碎的日常生活與禮樂教化在美學上的溝通。
經過對中國傳統教育與西方教育的反思與觀察,強調日常生活與美學、與藝術的密切關系已成為民國時期教育界的普遍傾向,比如梁啟超曾說“據多數人見解,總以為美術是一種奢侈品,從不肯和布帛菽粟一樣看待,認為生活必需品之一。我覺得中國人生活之不能向上,大半由此。”67豐子愷,《美術與人生》,載《中國美育思想通史·現代卷》,第65 頁。蔡元培也在論及美育時“一直從未生以前,說到既死以后”,“未生以前”主要指公立胎教院中的美育,“既死以后”則是墳冢墓園中的美育。不過,仔細分析蔡元培美育的具體措施,則可發現民眾的美育主要依托專門的“機構”展開,比如胎教這一伴隨著婦女整個孕期日常生活的美育“時間窗”,最終也落實為公立胎教院這一“機構”,而其中的美學元素相當專業化,如“選毛羽秀麗、鳴聲諧雅的動物,散布花木中間”,“室內糊壁的紙、鋪地的氈,都要選恬靜的顏色、疏秀的花紋”等等。68《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211 頁。秀麗、諧雅、恬靜、疏秀,作為胎教美育的美學環境當然適宜,但以當時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而言,達到這種美之境界的手段不免“奢侈”。陶行知將教育對象擴大至全人類,特別是其前期教育的重心傾斜向廣大民眾,在主觀意愿和客觀現實條件的雙重作用下,其美育活動必然與全部生活重合并從中獲得最直接而普遍的契機。日常生活中每一處微小易得的美在被體會、領悟的那一刻便自動打開了通向理想之“美”的道路——因為兩者就是一個東西,而陶行知的教育在引導人們體會、領悟的過程中,自動浸染了徹底日常化的美學風格。
四 藝術化境界之追求與詩化困難之傾向
陶行知的教育實踐以藝術化的境界為最高追求之一。他在不遺余力鼓吹、踐行教育應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同時,堅持認為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具體生活問題的解決尚不能視為“教育”的終極目標。相應地,落實到任何一件教育上,也只有“已臻化境”方算是最高境界。比如在論如何教育、引導學生自治時,陶行知曾說:
我們若想得美滿的效果,須把他當件大事做,當個學問研究,當個美術去欣賞。當件大事做,方才可以成功;當個學問研究,方才可以進步。這兩種還不夠。因為自治是一種人生的美術,凡美術都有使人欣賞愛慕的能力;那不能使人欣賞的、愛慕的,便不是真美術,也就不是真的學生自治。所以學生自治,必須辦到一個地位,使凡參與和旁觀的人,都覺得他寶貴,都不得不欣賞他、愛慕他。辦到這個地位,才算是高尚的人生美術,才算是真正的學生自治。69陶行知,《學生自治問題研究》,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27 頁。
在這里,陶行知明確提出將教育當件“大事”做、當個“學問”研究還不夠,因為人生在成功和進步之上,還有令人欣賞和愛慕的“美術”即藝術境界。在幫助人生變為“高尚的人生美術”的同時,教育也不僅是為目標而使用的手段,其本身也應追求藝術化的境界,正如陶行知在為兒童教育家陳鶴琴的著作所寫序言中稱贊的:“我現在要舉一兩個例來證明陳先生的藝術化的家庭教育……他神乎其技的教育法。”70陶行知,《評陳著之〈家庭教育〉:愿與天下父母共讀之》,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45 頁。技進乎道,被陶行知當作是應滲透于教育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最高要求。
陶行知是個極富詩意之人,這種性情對其教育事業的影響學界已有所分析與評判。有學者認為,陶行知并未對杜威的教育哲學做過扎實系統的研究,他從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中所獲得的教育改革工具,多半是模糊性的格言、啟迪性的原則和諺語,用類似“民主”“科學”“實驗”“創造”的口號捆扎在一起;但同時正是其教育信念的不定型,使他擁有了廣闊的余地和種種變化的可能。71[美]休伯特·布朗,《中國教育中的美國進步主義:陶行知個案》,載《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編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89 頁。的確,陶行知并非為“學術研究”這“一大事”來,更不承認自己是教育“理論家”,他對杜威思想的理解,并不以忠實“還原”和“再現”為目的,更多是抓其要害、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在“啟迪性的原則”下,和美國截然不同的社會現實和陶行知鮮明的個人特色相互碰撞,催生出對某一理論的創造性運用,與其原始形態可能已相去甚遠。而這一創造的過程,即使陶行知自始至終強調教育的科學性、實驗性,也無法遏制地呈現出浪漫化的傾向。
有學者認為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是一種社會化的、運動式的普及教育。72這一觀點來自喻本伐,見劉大偉,《繼承與嬗變:陶行知研究的學術譜系》,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150 頁。褒貶暫且不論,“運動式”若作為一種中性描述,確實指出了陶行知教育實踐的核心氣質之一。“運動”一詞的概念史顯示出它的廣泛運用是憑借“五四運動”的影響,正是“五四”的過程充分顯示了“運動”中蘊藏的巨大社會能量。73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54 頁。“運動”與“社會”間相互呼應的磅礴氣勢,運動“喚起廣泛社會反應”所伴隨的熱烈情感,運動過程中投身廣大民眾、投身歷史“事件”而觸發的自我責任與昂揚斗志,都是陶行知的教育事業所具有的典型浪漫。他曾于1926年前深度參與平民教育運動,特別是1923年下半年至1924年上半年,可視為他跨出學校體系、走向社會教育的重大改革的“集中體驗期”,僅1923年10月、11月兩個月,便在不同城市組織發動了多次動輒上萬人參加的平民教育大游行。74陶行知在安慶、南昌推廣平民教育之情況,參見《平民教育下鄉:致金鳴岐先生的信》,載《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30 頁;《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給文渼的信》,載《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33 頁;關于安慶、南昌、武漢、蕪湖等地游行之情況可參證1923年11月2日北京《晨報·安慶通信》、1923年11月7日北京《晨報》,1923年11月29日《申報》、1923年12月6日《申報》,轉引自《陶行知年譜長編》,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除了在中國教育史上的意義,平民教育運動對陶行知個人而言極其重要。第一層重要性已由他本人點出——重新發現自身的“平民性”,其實還有第二層:正是在此番運動的推廣過程中,他找到了自己在教育這件“大事”上偏愛的行事風格——揮灑激情,理想主義,既堅定又浪漫。
陶行知最常用來概括其心目中教育最高境界的意象是“詩”,或詩意。這是教育扎根社會現實而又超越了物質條件與政治環境、運用施教技巧而又貫通了教育目標與生命意志,方能擁有的觸動靈魂、感化人心的力量。陶行知生命的最后一年仍對曉莊念念不忘,因為那是他記憶里“陽光下的詩意生活”。陶行知曾借著為學生文集作序的機會,描繪出理想中學校(教育)的境界:
充滿曉莊的只是詩,詩的神,詩的人,詩的事,詩的物。曉莊是一部永遠不會完稿的詩集。他不是個學校,若拿個學校的名目來找曉莊,一定要迷路、失望。如果硬要派他算個學校,他最多只能承認是個詩的學校。可是要拿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白話詩這些名目去找曉莊,又要迷路、失望了。他所有的是“詩生活”“生活詩”。除了這種詩以外,他別無長物。只有詩能說明曉莊生活的一切。75陶行知,《〈破曉〉序》,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44 頁。
陶行知一生主持的歷次教育實踐中,曉莊學校作為公認的“高峰”,確實也是其教育之詩意最濃者。這種詩意在于教育與生活的融合無間,故曰“生活詩”;在于教育應對生活之需求的靈活變通、不拘形式,故“拿個學校的名目來找曉莊,一定要迷路、失望”;還在于教育追隨生活之生生不息而擁有的自新與變化,故是“一部永遠不會完稿的詩集。”曉莊教育所呈現出來的靈活、開放與通達,一方面來源于陶行知向往的“四通八達”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卻與其創辦之初極度窘迫的經濟狀況相關:這是一個沒有校舍而舉辦開學典禮的學校,自然更沒有圍墻,師生們的課業之一就是在與周圍村莊完全連通的土地上自建容身之處。直到曉莊被查封,出于經濟條件和教育理念的雙重原因,學校依然沒有建起劃定領地范圍的“大門”,封條竟無處可貼。既沒有教學樓,也就談不上固定上課地點,學生們的學習與鄉村生活最大限度地結合,并根據實際生活的需要隨時調整。物質上的極端簡樸在客觀上去除了教育與生活間、師生與民眾間、師生之間、知識與行動間的阻隔,教育在與生活的互動中尋得了和諧的詩意。當然,“別無長物”既象征著陶行知對曉莊精神內核之珍視(即“其余皆可拋”),也是學校物質狀況的真實反映,陶行知以藝術的態度將教育中的具體困難詩意化的傾向已十分明顯。
相對于曉莊,育才學校代表了陶行知一生中不那么“激進”的時期,學校的教育對象是精挑細選的天才兒童,音樂組、戲劇組、繪畫組等實行的是嚴格意義上的藝術教育,以培養專業藝術人才為目標。然而,正是通過對“詩的學校”的一貫追求,陶行知將校內的教育理念延伸到了學校的范圍之外:
我要把育才辦成一個詩的學校,盼望大家幫助我。我要以詩的真、善、美來辦教育。我并不是要學生每個都成為詩人,那太困難了。但我卻要由我們學校做起,使每個同學、先生、工友都過著詩的生活,漸漸的擴大出去,使每個中國的人民、世界的人民,都過著詩的生活!76陶行知,《關于詩的談話》,載《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442 頁。
過詩的生活不必都是詩人,即梁啟超所謂固然不能人人都做“美術家”,但不可不個個都做“美術人”。詩的學校,按照陶行知“宇宙為學校”的胸襟,其范圍與能量遠遠大于一所(專業)藝術學校,而無處不在的詩意原本就具有眾生平等之含義。正是靠教育追求的最高境界,貫通了學校和社會、人才和大眾、教育和生活的關系,使陶行知前后期的教育實踐保持了精神上的一致性。
遇到困難而能以詩意面對,使陶行知的教育常常出人意表又感人至深:
困難詩化,所以有趣;痛苦詩化,所以可樂;危險詩化,所以心安;生死關頭詩化,所以無畏。這是建設的達觀主義,也可以說是創造的樂天主義。77同注75。
乍一看,這仿佛是陶行知對于自己心愛的教育實驗過于理想、文學化的描述,但他一生教育實踐中遇到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困難”確有所指,“危險”“生死關頭”也絕非抽象的夸張(比如曉莊就是在北伐戰爭的槍林彈雨中堅持開學)。可知陶行知的詩意并非停留在文字層面的自我陶醉,而是由真實的教育實踐中升華出來的精神力量。當然,“詩化”是陶行知面對困難時所采取的主觀態度,絕不是他遇到問題時的唯一應對,大多數情況下現實問題在現實層面的解決(比如教育經費問題、學校如何不被戰火摧毀的問題),要靠他在文化教育界的威望、超凡的社交能力、靈活實際的處事方式等。然而,這一切的根本來源,依然要歸結到陶行知能使克服困難變得“有趣”“可樂”“心安”“無畏”的、對于教育的詩意化信仰上。
實際困難未必都可以靠“詩化”獲得實際的解決,在上引同一篇文章中就有一個現成的案例——一位曉莊校工的離開:
在詩人的目光里,高大哥混身都是詩。倘我們用佛眼來看他,他何嘗不是位彌陀佛呢?畢竟佛眼不常開,詩神也大意了些。高大哥乃不能容于曉莊,于今不知流落到何方去了!……詩的曉莊而不能給詩的高大哥一回旋之地,實為我們終身之大遺憾。78同注75。
陶行知曾給這位叫高祥發的校工寫信,好言相勸,從信中可推知后者離開學校主要因為“不受調度”的個性不適合這個崗位。陶行知對此念念不忘,十分遺憾,可見他相當欣賞高大哥誠實的性情,甚或覺得他“頑皮”的個性頗具詩意。“用佛眼來看”,可謂審視教育事業的最高站位,站在佛的角度望眾生,自然人人都有可貴處。可惜現實中陶行知依然要降回到“校長”的位置,一校之中教育的實際運行并不能為“詩化”提供足夠的空間。陶行知在高大哥的境遇中寄托了教育詩意之理想和對現實困境的洞察,以及兩者間無法完全調和的矛盾。
類似矛盾在陶行知一生的教育實踐中還有不少。曉莊開學時沒有現成的教室,陶行知在帶領師生自力更生的同時,根本上是以“詩意”來應對這一困難:“學堂是有的,不過和別的學堂不同。他頭上頂著青天,腳下踏著大地,東南西北是他的圍墻,大千世界是他的課室……”79陶行知,《曉莊三歲敬告同志書》,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449 頁。而同一時期推動鄉村幼稚園建立的過程中,陶行知延續了這種將辦學物質條件壓低到近似于無、既極度實際又極度浪漫的思路:“鄉村幼稚園不限定要房屋。倘使無校舍,便可在露天里辦起來。天晴開,雨來散,有何不可?”80陶行知,《推廣鄉村幼稚園案》,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21 頁。但最終被證明“天晴開,雨來散”的幼兒園畢竟超出了當地民眾的接受程度而“不可守”,未能持續。
相對于外在客觀條件和困難本身而言,對條件的評估、應對困難的態度是主觀的,陶行知詩化困難的傾向是將教育過程部分轉化為了審美過程,并將審美活動的主觀性運用到了教育中。以主觀之詩情看待客觀之困難,陶行知作為同代中受康德影響較淺的教育者,倒是在主體性問題上與康德美學的核心真正相通。81《美,以及美的反思:康德美學全集》,第5 頁。陶行知將教育者的主體性發揮到了極致,故其教育關心的重點時常落在教育者的精神力量上,而不在具體的教育實踐的即刻結果上。作為生活教育的提倡者必然要警惕對主觀意愿的過度強調,但這種傾向在陶行知的教育實踐中十分常見,無法否認。在將教育審美對象化的過程中,困難若得到了解決則向上升華,體現為“詩化困難”之目標和手段、精神力量和操作技巧合二為一的爐火純青、出神入化;而無法解決的困難,則向下落實,產生出以功利標準衡量不成功的教育實踐。
五 陶行知教育美學風格初探
基于對游戲與閑暇意義的肯定、教育過程性本質與現實訴求的兼顧、美之日常性的發掘、困難的詩化等,加上教育家本人的性情特點,陶行知一生的教育實踐總體呈現出如下鮮明的美學風格:樂觀豪邁,棄絕了哀愁和消極的蹤影,渾然忘我,超越了個人與一時的成敗得失。以往對陶行知的討論常在“教育救國”的語境中展開,而他對教育與國家關系的獨特理解,頗能反映出其教育的藝術性中的樂觀精神:
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國,但救國一語,似覺國家已經破壞,從而補救,不如改為造國。 ……若云救國,則如補西扯東,醫瘡剜肉,暫雖得策,終非至計。若云教育造國,則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蓋教育為樂觀的而非悲觀的也。82同注1,第219 頁。
綜觀陶行知留下的文字,確實較少將“教育”與“救國”直接相連(“救國”較多出現于“抗日救國”“救國會”等直接指向抗日戰爭的用法)。這種樂觀的來源,除了在教育過程中獲得的自足的快樂外,也與自化化人、自立立人的教育活動所天然蘊含的創造性愉悅相關。學者在追溯教育行為的本質時指出,“第一個”教育者并無現成的東西可以用來進行教育或自我教育,只能通過自由自覺的感性實踐活動,而這種創造性的實踐是人與萬物的區別所在,既具有審美和藝術創造性質,也具有教育的性質。83參見《教育的藝術原理》。
教育作為樂觀的事業,是對人生的積極引導,而非對痛苦的消極補救;美育不為現實世界之解脫,而是扎根其中所發出的對生活之美的由衷贊頌。“以之為補救或解脫”的預設是人生本為痛苦,如王國維對人生本質的認識:“故人生者,如鐘表之擺,實往復于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84同注7。有學者認為王國維將審美活動定義為一種能對人生時間進行拯救的游戲,這與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已有所區別,已是審美向日常時間的積極介入。85《中國美育思想通史·現代卷》,第50 頁。但較陶行知而言,依然可謂相對消極。如前所述,陶行知將王國維眼中人生苦痛的根源——欲望——視為中性的,它只是教育得以發揮作用的一種客觀存在。“宮殿住過來,還安茅草屋。吃過魚翅席,也喜喝米粥。街市固好玩,逍遙樂鄉曲。既上千仞崗,也愿下深谷。能力勝欲望,精神廢儲蓄。欲望勝能力,煩惱勞苦哭。兩樣差不多,人生真幸福。如此教學生,才算好教育。”86同注8。安、喜、樂、愿,正是教育對人性進行改造的過程中應該引導生命達到的境界,教育或美育的最終期待是“真幸福”的人生,而非僅僅“解除了痛苦”的人生。陶行知一生教育實踐所呈現出的樂觀氣質,來源于他對人生和人性的根本態度。
即使“救亡圖存”是當時教育所要承擔的現實重任,陶行知仍時常超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界限,關心全人類的解放——此“解放”,既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所有受壓迫民族的獨立斗爭,也指向更普遍意義上的“人的解放”。因此,陶行知的教育實踐向往達到的是一種與宇宙同頻的波瀾壯闊的浪漫:
“從野人生活出發,向極樂世界探尋”,是我們今天所立的宏愿。學堂是有的,不過和別的學堂不同。他頭上頂著青天,腳下踏著大地,東南西北是他的圍墻,大千世界是他的課室,萬物變化是他的教科書,太陽月亮照耀他工作,一切人,老的、壯的、少的、幼的、男的、女的都是他的先生,也都是他的學生。87同注79。
青天、大地、太陽、月亮、東南西北、大千世界,萬物及人類,這些氣魄宏闊的意象首次集中出現于曉莊時期陶行知對教育的描述中,其背后當然是“沒有現成教室”的經濟現實,但也促使原本就強調精神力量而非物質條件的陶行知對教育的認識進一步浪漫化。用這一組意象對應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境界想必令他相當滿意,之后多次有類似表述,如1931年的詩“宇宙為學校/自然是吾師/眾生皆同學/書呆不在茲”(十多年后改寫為“世界為學校/真理是老師/人類皆同學/學寫創造詩”),又如為重慶社會大學創立而作“青天是我們的圓頂/大地是我們的地板/太陽月亮是我們的讀書燈/二十八宿是我們的圍墻/人民創造大社會/社會變成大學堂……”88組詩《詩的學校》第一首,載《陶行知全集》第七卷,第83 頁;組詩《詩人節祝詞》第三首,載《陶行知全集》第七卷,第994 頁;《社會大學頌》,載《陶行知全集》第七卷,第955 頁。中國士人或知識分子中,鴉片戰爭一代是從地理學開始了解西方世界,如最早的《瀛寰志略》《海國圖志》寄托著經世匡時的苦心,是中國文化近代的標志性開端之一。89陳旭麓,《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第60 頁。而到了陶行知一代則已完成了地理啟蒙的階段。他對教育事業所能達到的邊界的理解,以世界為學校、以天地為教室的胸襟與眼界,部分建立于出洋留學、環球旅行的親身經驗上,并非源自純粹的想象,也不僅是文學層面的修辭。
將教育實踐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中展開,是個體投身于教育活動時達到“事我兩忘”、渾然一體之境的基礎。陶行知曾論及教育家在業內交流時應采取如下態度,亦可視為教育從業者處世之道的普遍準則:
忘己忘人,俱為要道。忘己則大公無我,真理是徇;忘人則獨抒己見,不畏誹謗。90同注45,第229 頁。
二十年后,在寫給兒子的信中,陶行知明確將“忘己”與投身更大的事業相聯系:“在你們的周圍有著幾百、幾千、無數的孩子,都是你們的朋友,你們的同伴,你們的服務的對象。從家庭的小世界里把自己拔出來,投入大的社會里去……”91陶行知,《投入大的社會里去:致陶曉光》,載《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357 頁。將個人生命投入大眾,使教育作為一種人類事業得以超越一時的成敗得失,即陶行知對自己歷次教育實踐的終極期待“成亦成,敗亦成,而不是世俗所謂之成敗了。”
1930年2月1日,以曉莊學校為核心力量的雜志《鄉村教師》創辦,陶行知為其寫了一篇發刊詞。1930年4月7日,曉莊學校查封停辦,《鄉村教師》隨之停刊。這個只存在了兩個多月的雜志,是一群教育者一段短暫生活的記錄,在變化多端、滾滾向前的世界教育史中未及充分現其光芒,便銷聲匿跡。然而這篇發刊詞卻絕佳展示了陶行知教育實踐的藝術性,它以戲劇為譬喻,隱伏著其教育實踐鮮明美學風格的根源——對教育在歷史進程中位置和作用的認識,對教育者個體與全人類關系的認識。發刊詞中所談“鄉村教育”實質上是一切教育,所對話的“鄉村教師”可擴大為所有既自化、亦化人的教育中人:
……有人問:“小的村莊為什么要與大的世界溝通?”世界是一個大劇場,人生便是演戲。個人的活動無論如何獨立,只是歷史劇中之一幕……鄉村教育運動只是一出歷史劇,全世界的鄉村教師都同是這一出戲中的演員。這周刊里有我們的劇本,有我們的導演。這里可以找得出藝術生活的過程。這里可以找得出那愿意我們藝術更進一步的批評……總說一句:這個周刊便是我們鄉村教育運動的一出永遠不會閉幕的歷史劇的寫真。92陶行知,《〈鄉村教師〉宣言》,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408 頁。
如前所述,陶行知一向重視戲劇之美育功效,因為它作為“游戲”之一種格外滿足了人與生俱來的游戲傾向,并與人生存在著深層呼應——戲劇即人生,人生即戲劇,以有生之人演人生之事,正是教人“為生之美術”。這篇發刊詞將重心落在“教育”上,將世界喻為劇場、教育喻為演戲,清晰顯示出陶行知以藝術之眼光看待教育的浪漫傾向。
這一譬喻蘊含的更深含義在于陶行知設置的以世界為劇場、鄉村教師為演員的結構——個體與外界之溝通,教育者的活動與全人類發展的關系。引文中對教育事業的理解融合了西方近代的進化論、中國傳統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道家“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和“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等諸多思想資源。與陶行知同時代知識分子亦常見這種由中西碰撞、古今交融而生出的嶄新的宇宙觀,例如梁啟超在某次演講里深情贊美傳統儒家文化時卻明顯透露出西方思想特別是進化論的影響:“宇宙的進化,全基于人類努力的創造……宇宙永無圓滿之時……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點,所以他的人生觀,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盡的宇宙當中,不過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點是一點,既不望其成功,苦樂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謂‘無入而不自得’。”93陶行知,《治國學的兩條大路》,載《中國美育思想史·現代卷》,第77 頁。
將古今中西思想資源融會貫通而獲得的豁達積極,是陶行知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危機感轉化為歷史的饋贈,同時,波浪壯闊的時代也在一定程度上托舉了其中個人的高度。陶行知將這種宇宙觀運用到具體的教育實踐中,使后者獲得了藝術性的升華。只要世界這個“大劇場”一直存在,教育之歷史劇便“永遠不會閉幕”。只要置身于人類不斷向前的進程中,任何一項具體的教育實踐便帶有了與世界聲息相通的責任感與宏闊意境。教育的過程性本質呈現出自足的價值,加上超越一時成敗、一己得失的豪邁忘我,由此煥發出永不衰竭、與生活共同向上向前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