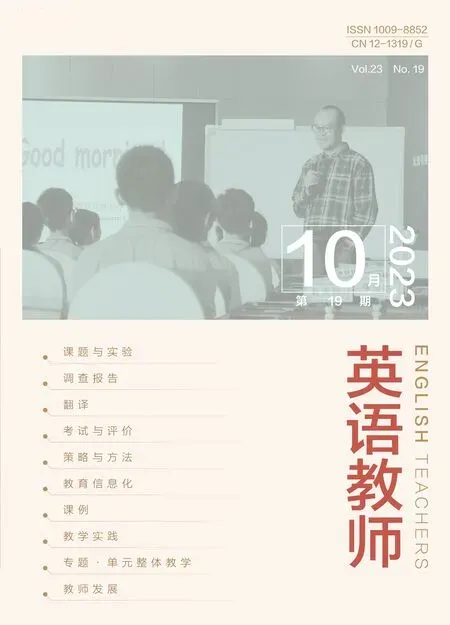新時代翻譯語境下中國傳統譯論的傳承與發展芻議
張發亮
引言
中國傳統譯論文獻卷帙浩繁,跨越漫長的歷史歲月,包括眾多人物和理論觀念(朱徽2004),在近兩千年中國翻譯歷史長河中,傳統譯論如璀璨珍珠,散落于不同的時代(陶友蘭 2015),其主題也大致經歷了“按本—求信—神似—化境”(羅新璋1983)的演變和“肇始階段(佛經序翻譯理論)、古典階段(正名論翻譯理論)、玄思階段(哲學化翻譯理論)和直覺階段(文藝學翻譯理論)”(王宏印、劉士聰 2002)四個發展階段。在西方近現代翻譯理論對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沖擊逐漸淡化,而中國譯學研究快速發展的新時代翻譯語境下,中國傳統譯論如何守正創新、繼承發展,亦為譯界所熱議,主要有王宏印、劉世聰(2002)對中國傳統譯論經典的現代詮釋,朱徽(2004)對王宏印著作《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論事釋——從道安到傅雷》的評論,李林波(2005)認為傳統譯論的現代轉型是它得以被傳承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途徑,并提出了觀點的提取術語、范疇的現代轉換、中西互釋三個方面的轉型,陶友蘭(2015)從教材建設視角提出了加快經典性傳統譯論外譯步伐,面向國際傳播和加大傳統譯論教學力度兩大路徑,黃忠廉、傅艾、劉麗芬(2022)從基礎、系統、目標三大方向探討中國譯論發展研究的未來走向,唐瑛(2023)則以《全譯求化機制論》為例探析了中國傳統譯論當代闡釋的路徑。綜觀當前研究,都具真知灼見,且各有側重,卻忽略了當前新時代翻譯語境的顯著特征因素對中國傳統譯論的繼承與發展的影響。例如,神經網絡機器翻譯系統、ChatGPT等大型語言生成和輸出工具等人工智能技術對翻譯實踐和理論帶來的巨大沖擊。有鑒于此,在分析新時代翻譯語境的基本特征的基礎上,探討中國傳統譯論在極具特色的新時代翻譯語境下的傳承與發展路徑,讓傳統走進現代,隨時代譯學潮流同步發展。
一、新時代翻譯語境的基本特征
(一)機遇與挑戰并存,使命與擔當同在
中國翻譯實踐和理論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蓬勃發展。具體來說,隨著我國“一帶一路”“中國文化走出去”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等的推進,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和使者,雖任務艱巨,但前景廣闊。然而,機遇和挑戰往往是并存的,機遇充滿著挑戰,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往往需要克服一定的挑戰。例如,隨著網絡科技的迅猛發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對傳統翻譯實踐模式造成了顛覆性的革新。對于機器翻譯的研究,從20世紀后半葉開始,時至今日已經取得了驚人的發展。甚至有人提出“機器翻譯將取代人工翻譯”的論調。如何處理機器翻譯對傳統翻譯實踐模式的顛覆性革新成為當今譯界面臨的巨大挑戰。更甚者,如處理人與機器的關系成為當代人類面臨的巨大挑戰。又如,在新時代語境下如何充分挖掘中國傳統譯論的時代價值、精神標識,結合新時代特色推陳出新,加快構建中國特色譯論的話語和敘事體系,也是當今譯界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自古以來,翻譯就承載著文明交流與傳播的使命,并且與政治密切相關。例如,漢武帝通西域后,印度佛教和哲理通過翻譯相繼傳入中國。佛經翻譯對華夏文明和中國社會文化的構建產生了極其深刻而又深遠的影響。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擔當與使命。新時代翻譯人自然也有新時代人的使命與擔當。首先,新時代翻譯人擔當著培養多語種人才,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其次,新時代翻譯人擔當著梳理“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家與中國古往今來文學互動的文化使命。最后,新時代翻譯人擔當著“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服務于外宣活動的政治使命。毫無疑問,在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期,新時代翻譯人的責任和使命愈顯重大和光榮。
(二)西方譯論對我國傳統譯論的沖擊逐漸淡化
20世紀末,西方翻譯理論如潮般涌入我國譯壇,對中國傳統譯論造成強烈且持久的沖擊。一時間,大量專家、學者沉迷于對西方翻譯理論的引進、介紹及研究,致使對傳統譯論的研究進入短暫沉寂期。然而,在西方譯論進入“后理論”時代的情況下,我國本土翻譯理論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而繁榮發展,理論體系也逐步構建起來。大多數學者逐漸意識到西方翻譯理論并不完全適合中國翻譯實踐,也不能完全解決中國翻譯實踐問題,因此不再一味沉迷于西方現當代翻譯理論,而是充分結合傳統文化、傳統譯論及中國翻譯實踐建構中國翻譯理論體系。例如,辜正坤提倡的“玄翻譯學”、胡庚申提出的“生態翻譯學”、陳東成提出的“大易翻譯學”、吳志杰提出的“和合翻譯學”、周領順提出的“譯者行為研究”、黃忠廉的“變譯理論”等理論體系的構建充分說明我國學者構建本土翻譯理論體系意識的覺醒和決心。因此,西方現當代翻譯理論對中國傳統譯論和現當代本土譯論的沖擊逐漸淡化。相反,在新時代語境下,西方現當代翻譯理論與我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與中國譯論融合發展之勢比較明顯,如認知翻譯學、語料庫翻譯學、社會翻譯學等譯學研究發展迅速,方興未艾。
(三)新技術、新媒體對傳統翻譯實踐與傳播模式產生顛覆性革新
隨著現代數字技術的迭代式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日新月異,催生了ChatGPT等大型語言生成和輸出工具的問世,給社會各行各業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撼動了人的社會價值定位,引發了一系列人們對“技術”的價值審視和“人機”社會倫理關系的討論。這種由海量數據與巨大算力共同催生的深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無疑給當下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造成了前所未有、革命性的沖擊。例如,近幾年機器翻譯研究突飛猛進,從最初的基于規則的轉換系統演變至今日的神經網絡機器翻譯系統,對于一般的科技、法律等文本的翻譯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且翻譯速度是人工所無法比擬的。又如,ChatGPT的橫空出世,它可以提供多語種問答、檢索、翻譯、寫作等服務,而最新的GPT-4能夠更好地回答即時性、邏輯性、創造性要求更高的問題(朱永新、楊帆 2023),這很可能完全顛覆傳統的翻譯實踐模式和研究模式。傳統的以紙質版書籍、報刊等為主的譯語文本傳播模式,在新媒體數字時代已經轉變成以電子文本、網絡渠道、多模態形式為主的傳播模式。不得不承認,在人工智能的強力介入下,傳統“人機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正以不擋之勢向當下“人機協同共生”思維模式轉變。毋庸置疑,新時代“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對翻譯實踐模式帶來的顛覆性變革和沖擊是新時代語境的一個鮮明、引人注目的特色,且極具發展潛力。
二、傳承與發展
(一)充分挖掘傳統譯論的時代價值和精神標識推陳出新
雖然中國傳統譯論一步深于一步,一層高于一層,但是表現出分布零散,言簡意賅,在系統性和方法論上缺乏科學性的特點。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國傳統譯論的價值及其蘊含的豐富的人文精神。羅新璋(1983)說:“我們的翻譯理論自有特色,在世界譯壇獨樹一幟,似可不必妄自菲薄。”足見對中國傳統譯論的肯定。后來,譯界專家、學者在對中國傳統譯論進行批判性研究時,幾乎都肯定了中國傳統譯論深邃的內涵和豐富的人文精神。例如,佛經翻譯大師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中潛藏翻譯本體論的卓見,彥琮的“十條八備”字里行間透露著對譯者主體性的闡釋。后來,章士釗與胡以魯關于音譯、意譯的爭論,已凝聚著有關譯名的本質的探求;賀麟的“言意之辨”中折射著哲學思辨的精神(李林波 2005),嚴復的“信、達、雅”更是蘊含著對“真、善、美”的追求,足見中國傳統譯論內涵之深邃。于是,王宏印、劉士聰(2002)將中國傳統譯論的人文精神作了“以道德為本位”“群體本位思想”“人文主義的語言觀”等方面的總結,足見中國傳統譯論的人文精神之豐富,而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文化在譯論領域的折射。由此觀之,在新時代語境下,充分挖掘傳統譯論的時代價值和精神標識推陳出新是其傳承與發展的基礎。
(二)博采眾長,融西立中
自從20世紀80年代引進西方譯論以來,西方譯論似乎一直一枝獨秀于中國譯壇。然而,自西方譯論經歷了語言學派、闡釋學派、功能學派、文化學派、解構學派、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描寫翻譯等翻譯理論的繁榮之后,當今西方譯論發展似有放緩之勢。與此相反,中國的譯學研究正在異軍突起(孟凡君 2018)。中國傳統譯論和現當代譯論在新時代語境下要實現“走在世界前列,自立于國際譯壇”(穆雷 1995)的目標,就應該批判性借鑒、吸收古今中外各派譯論的優勢,順應當代譯學發展趨勢,中西合璧,博采眾長,融西立中,走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道路。“中西合璧”就是把現當代西方翻譯理論與中國傳統譯論和新時代本土譯論結合起來推陳出新,是新媒體時代全球文化交流互鑒互通的大勢所趨;“博采眾長”就是批判吸收、借鑒西方譯論之精華,集百家之長,成一家之言,是必要的途徑;“融西立中”主要是“以中為體,以西為用”建立中國特色譯論體系。
(三)熱擁“技術”革新研究方法,創新研究熱點
“人機協同共生”是技術革命和人類社會實踐相互適應的結果,是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必經階段。因此,新時代中國傳統譯論的繼承與發展理應順應時代潮流,熱擁“技術”革新傳統以探索研究方法,豐富研究視角,創新研究熱點,守正創新。然而,如ChatGPT這樣的賦能工具的使用需要注意人機社會倫理關系問題和技術的“雙刃劍”問題。首先,正確定位人和機器的社會價值地位。無論機器神經網絡多么發達,或自我意識有多強,我們應該認識到機器的工具性和使用價值,它是為人所創,亦為人所用,而不應該本末倒置把有“靈”的人變成無“靈”的機器的附庸。其次,任何技術都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使用科學、合理,就會促進人類社會實踐的進步和發展,如果使用有悖社會發展和進步,就會造成一系列不可挽回或彌補的影響。例如,如果將ChatGPT正確、合理使用在翻譯實踐和研究方面,就會提高譯文質量和翻譯速度,節省人工成本等,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研究數據和檢索結果;反之,則會引發學術論文濫造亂象,擾亂學術研究秩序。
結語
新時代翻譯語境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為:機遇與挑戰并存,使命與擔當同在;新技術、新媒體對傳統翻譯實踐和傳播模式產生顛覆性革新的同時,西方譯論對中國傳統譯論的沖擊逐漸淡化。在這樣一個極具特色的新時代翻譯語境下,內涵深邃,富含人文精神,但分布零散,缺乏系統性的中國傳統譯論要在傳承的前提下取得長足發展,應該順應國際翻譯學發展潮流,充分挖掘傳統譯論的時代價值和精神標識推陳出新;博采眾長,融西立中;熱擁“技術”革新研究方法,創新研究熱點,以此在新時代傳承與發展中國傳統譯論并構建中國特色譯論體系,與曾經一度一枝獨秀于中國譯界的西方近現代譯論爭相媲美,美美與共。